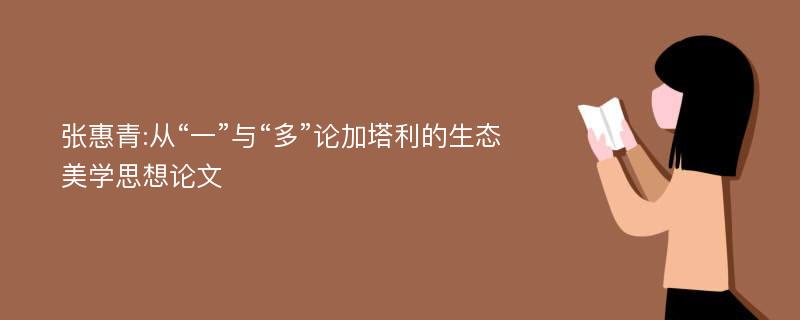
[提要]加塔利的生态哲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系统地反映在以多元性为特征的生态世界观、伦理美学范式与生态智慧三个维度。以“多”及“一”的生态世界观,将人类生态系统纳入一种“多”元共生的机器式装配关系中,彻底化解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走向一元论的彻底融合、以“一”生“多”的伦理美学范式,以混沌互渗作为本体论依据,倡导通过伦理规范下的审美创造走向异质性和多元性,以“美学-本体”论颠覆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以“多”对“一”的生态智慧,以主体性生产为目标,倡导以多元价值逻辑和多元化生活方式(“多”)作为对抗以物欲为中心的单一价值逻辑(“一”)的生态救赎之道。加塔利生态美学思想究其实质是一种通过顺遂人性来尊重物性的减法智慧。
[关键词]加塔利;生态美学;机器装配;伦理美学范式;生态智慧;主体性生产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是法国20世纪一颗璀璨的思想巨星,他终身在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和各种实践活动中驰骋纵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加塔利顺应人类生态危机的时代语境,将理论转向了对生态学和美学的关注,以其生态智慧给出了人类文明的生态救赎之道。相较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对多元性的逃避——它们往往将多元性(“多”)容纳于整体的一元论(“一”)之中或者将其划分为二元对立的“二”,加塔利的生态智慧则延承了多元论哲学家斯宾诺莎、尼采和柏格森等的思想路线,以创造性的生成为核心应对了世界原初的多元性。基于此,本文以加塔利(和德勒兹)的“多元论=一元论”为理论依托,拟定了超越“一”和“多”之间的二元对立的三组关系:以“多”及“一”的生态世界观,以“一”生“多”的伦理美学范式和以“多”对“一”的生态智慧救赎,探讨加塔利伦理美学范式庇护下的生态智慧是如何以人类欲望为中心、通过伦理规约下的审美创造履行人类文明的生态救赎的。围绕创造性(生成)展开的美学救赎恰恰反映了加塔利生态美学思想的内涵。
一、机器装配:以“多”及“一”的生态世界观
加塔利的生态智慧遵循严格意义上的一元论世界观,和笛卡尔以降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二元论世界观划清了界限。加塔利的一元论世界观可以追溯至贝特森的“有机体与环境加权”(organismplusenvironment)式生态世界观。贝特森沿袭盖亚假说的理论构想,将有机体对其作为一部分参与其中的环境的影响,归因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自发的相互调节:一方面,有机体与环境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耦合关系;另一方面,有机体作用于环境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为对生态系统的具体影响。“有机体与环境加权”传承至现代进程之父怀特海(Whitehead)。怀特海从人类学的立场将“有机体与环境加权”的内涵诠释如下:在任何生命系统中,有机体的行为都必须既有利于环境又有利于有机体自身,如果背离了这种“双重有利”原则,有机体将遭受灭顶之灾。[1](P.66)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加权关系,可视作一种由“二”及“一”的耦合关系——有机体+(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在加塔利与德勒兹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中,以机器论将这种耦合关系诠释为一种机器装配(machinic assemblage)关系。
尽管本次遥感监测数据还存在少量的错误和遗漏,但已比较准确地掌握了成茶种植区的空间分布和种植面积,实现了监测目标。
机器论将世间万物都视作欲望机器(desiring machine)——遵循二元法则或联结机制的“二元”机器[2]——在“欲望”驱动下,一台机器总有与另一台机器进行耦合的倾向,每一次耦合都是一次加塔利(和德勒兹)所谓的“生产的连接综合”(connective synthesis of production),亦即完成一次欲望生产(desiring production)。每两个机器之间所进行的连接综合,都呼应于《千高原》中“根茎”所遵循的“和”(and)的逻辑,其连接的形式表现为一种“……和……”的装配关系,从而由“二”及“一”形成机器装配的基本单元——一种“二元”机器,其中,每个机器都作为摧毁“俄狄浦斯情结”之枷锁的“部分对象”(partial object)而存在,其自身的生命也都因“装配”过程而得到转化和升华,进而走向创造性和全新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此装配的基本单元在加塔利的封山之作《混沌互渗》中被命名为“横贯性实体”(transversal entities),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形式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在一种创造性过程的绝对视阈下确立自身,因此被加塔利称之为“机器的超文本”(machinic hyper-text)。[3](P.109)“横贯性实体”生成于参与“装配”的两个“部分对象”之间,每一个“横贯性实体”复又作为“部分对象”,随时等待着另一台机器与之进行“装配”,从而再度生成新的“横贯性实体”,如此循环往复,完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自创生过程。
要理解“横贯性实体”的内涵,必须要洞悉加塔利的横贯性(transversality)①理论。一、萨特首次将横贯性概念引入了加塔利的学术视野。萨特在《自我的超越性》中指出,意识通过“横贯的”(transversal)意向性实现自身的统一,意向性是对过去的意识的真实记忆,从而否定了人类意识活动的先验性和“先验自我”,瓦解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根基。然而,萨特的融贯性理念因现象学的“此在性”而受到了质疑,因为“此在性”只关注了当下时间中“过去”的向度,而使面向“未来”的潜在性向度被搁置。二、加塔利在拉博德(La Borde)诊所的精神分析实践为横贯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在拉博德诊所,加塔利创造了“机制性对象”(institutional object),来替代“沙发上的个体”这一传统精神分析的对象,从而将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不对等的移情(transference)关系,转化为分析师和群体(groups)共同参与下的“机制性对象”之间的关系。“机制性对象”在弗洛伊德和拉康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移情关系之外,设想了第三个要素,该要素作为中间对象或媒介,为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空间,此空间就相当于温尼考特(Winnicott)的“中间经验区域”(intermediate area of experience)和“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三、加塔利追随温尼考特的“潜在空间”理念创造了“横贯性实体”,并充分强调了其“潜在的潜能”(virtual potential)的发掘,使之成为一个根本开放的创造性空间。“横贯性实体”遵循“在其中”(included middle)或“在中间”(in-between)的横贯性逻辑,这是一种“黑与白不分、美与丑共存、内与外一体、‘好’与‘坏’比肩”[4](P.37)的上帝视角,是对弗洛伊德的“初级过程”(primary process)理论中前对象的(pre-objectal)和前人格的(pre-personal)逻辑的批判性继承。横贯性逻辑下,一切“存在首先是自体一致性的、自体确定的、施展特定的他异性(alterity)关系的自为(for-itself)存在”[3](P.109),“自为”存在是同时生存于所有向度中的存在,在这里,从本体上化解了一切二元对立,彻底走向“一元论”的创造和融合。
以“横贯性实体”作为参照,就不难洞见,为何加塔利在诠释其一系列核心概念时,总是会同时出现“二”个相反相成或“二元”对立的概念,而这“二”个概念又都最终生成了“一”个概念或解决了“一”个问题。比如:混沌与复杂性之于混沌宇宙,有机体与环境之于生态系统,潜在性与实在性之于主体性生产,感知与认知之于审美过程,无意识与意识之于审美心理机制,等等。然而,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加塔利本无意建构“横贯性实体”,“横贯性实体”只不过是他以二元论作为原型,反过来质疑和瓦解二元论的一个工具。简言之,“横贯性实体”只不过是借以打倒二元论这一敌人的一种过渡性手段,借助它,加塔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抵达那个看似不可思议、却是人人寻觅的公式——多元论=一元论(Pluralism=Monsim)[5](P.27)——二个“部分对象”通过机器装配形成“横贯性实体”(“二”=“一”);此“横贯性实体”又可以作为“部分对象”重新参与装配,形成新的“横贯性实体”(“三”=“一”)……如此循环往复,其结果是,“多”个“部分对象”最终融贯成了“一”个整体(“多”=“一”),此整体即为多元体或聚合体。
加塔利的生态智慧究其实质是一种以“多”对“一”的减法智慧。无论是对个体主体性的特异性的强调,还是对群体主体性的异质化的诉求,都是为了产生与“一”相对抗的“多”:“多”指向一种多元价值逻辑和多元化的可持续生活方式;而“一”则指向以“物欲”为中心的单一的价值逻辑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单一的繁荣观。以“多”对“一”实质上就是通过“多”化解或分散人类欲望导向下的“一”,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加塔利在因势利导地进行“欲望消减”的同时,关注了人类精神健康的尊重:一、就个体来说,既主张个体主体性走向特异性,倡导一种可持续的心智模式;又主张尊重个人精神健康,其手段是付诸“多元价值逻辑”[4](P.46),倡导艺术地生存。二、就群体来说,既主张群体主体性走向异质化,倡导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又主张尊重群体精神健康,其手段是付诸“群体爱欲原则”[4](P.46),通过爱欲宣泄重建社会关系和谐。[4]无论是“欲望消减”还是精神健康的尊重,究其实质都是在顺遂而非捆绑人性的前提下履行生态救赎之道,这或许正是加塔利之生态智慧的高明之处。
(6)在保持油井正常生产的情况下,继续摸索稠油井出砂、排砂规律,制定和优化工作制度,为今后的工作方向打下基础。
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既是公共部门的行为“标尺”,也是私人部门的利益“保护网”。PPP模式下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有产权,两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任何一方的失信或失责都会给整个项目的运营造成极大的损害。公私部门双方应明确各自的职责与定位,公共部门做好土地、政策、补贴等工作,私人部门投入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因此,需要一整套统一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来明确双方的权责关系,保证项目运营的协调性,以法规规章来统一标准、规范程序,保证项目运营的规范性。
综上所述,机器论将世间万物都纳入一种多元共生和生成流变的机器装配关系之中,作为生态世界观核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诠释为一种人把自然“作为生产的进程来经历”的关系,“不再有人,也不再有自然,只有彼此之中生产的、把种种机器进行耦合的进程。”[2]“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更多的区别:自然的人性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在作为生产或工业的自然中成为一体,……自然是作为人的与经由人进行的生产。人不再作为创造之王,反而作为这样一种存在,即全部形式或全部类型的深层生命与之关系密切,他甚至要对星星与动物负责”。[2]这就彻底化解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了人类生态系统这一最大的格式塔(“一”)。加塔利对混沌和复杂性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化解,则生成了混沌宇宙这一真正意义上最大的格式塔(“一”),也是加塔利生态哲学思想的原点。
二、混沌互渗:以“一”生“多”的伦理美学范式
在一般使用场景下,我们很难区别哪台相机的细节还原更好,不过在细节丰富的场景中,E-M1 II的细节更加丰富,G9由于时不常出现的涂抹问题会影响细微细节的还原。
闲聊中得知,丁香花的丈夫于几年前的一次车祸中致残成了跛子,便在小区内开了一家小超市。车祸留下的阴影随着时光慢慢地散去,但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今年却高考失利。夫妻俩望子成龙的希望破灭,儿子受不了父母的责怪和冷眼,偷了家里三千多元现金离家出走,今天傍晚才打来电话告诉他爸,背包被小偷拎走了,在昆明某收容站等着家长领人,这给本来就心存烦闷的她更添了一腔怒气。
伦理美学范式作为加塔利终身理论的汇总和升华,起始于加塔利在拉博德诊所的精神分析实践,继而从理论上借鉴了福柯的“生存美学”并将其延伸到对艺术领域的思考。在拉博德诊所的精神分析实践中,加塔利通过对心灵和无意识的再诠释,反思与批判了以弗洛伊德的“心灵的普遍结构”和拉康的“无意识图式”为代表的科学范式,重新发现了“心灵”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新大陆,以及“无意识”在生成异质性和多样性中的作用,为伦理美学范式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伦理美学范式祛除了所有科学或伪科学范式,代之于从伦理学和美学中汲取灵感。这是因为,科学范式的局限性在于“将重点放在了关系和功能所界定的对象性世界上,这就程式化地将主体性的情动(subjective affects)搁置在一边,其结果是,有限性、限定性和可协调性总是优先于无限性及其潜在性的指涉。”[3](P.100)与之相反,美学范式则通过对前个人的、非人格的无意识维度的把握,“借助艺术,以可感质料的有限性来支撑感动(percepts)和情动(affects)的产生,从而逐渐偏离既定的结构和秩序”,[3](P.101)赋予被科学范式所悬置的感动和情动以优先性。正如加塔利所说:“我只想强调,美学范式——变异的感动和情动(mutant percepts and affects)的创造和创作——已经成为任何可能的解放形式的范式,它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弗洛伊德学说所指涉的旧科学范式。”[3](P.91)总之,借助艺术实践重拾人类稀有的感动和情动,是美学范式迥异于科学范式的地方,也是伦理美学范式走向异质性和多样性(“多”)的关键之所在。
那么,主体性生产到底是怎样通往创造性的呢?这就要重新回到混沌互渗。混沌褶皱作为主体化区域是创造性的发源地,吸引着有机体作为感知点向它敞开自身,同时完成了双重表述(double articulation):有机体面向混沌及其混沌褶皱之“拓扑空间”敞开自身,创造了“价值世界的超感无限性”;有机体通过形成一个作为“我”的自身形象得以被区分,创造了“存在之域的可感有限性”。前者在无限速度的世界呈现为异质化的“存在-性质”(being-quality),构成主体性生产的解辖域化的一极;后者在减速的有限世界呈现为同质化的“存在-物质-虚无”(being-matter-nothingness),构成主体性生产的辖域化的一极。[3](P.111)正是通过存在之域和价值世界之间持续的辖域化和解辖域化过程,主体性完成了异代生成,走向再特异化(resingularization)——个体层面走向特异性(singularity)和群体层面走向异质性——构成以“多”对“一”的生态智慧救赎的逻辑起点。
加塔利的生态世界观建基于其宇宙观之上。在加塔利看来,地球生命之外存在着一个匀质的、自组织的混沌宇宙(chaosmos),其物质遵循内在的(immanent)、自然涌现(emergent)的自组织模式。抽象机器作为混沌宇宙最重要、最普遍的自组织模式,通过在各种物质关系中的运转进程——伴随着宇宙发展及其生命演化过程中的差异化(differentiation)和固结(consolidation),分别生产出另外两种机器:具体的机器装配(concrete machinic assemblages),作为装配的内容而存在;多样性的表述装配(collective assemblages of enunciation),作为装配的表达而存在。两种机器相互作用将混沌宇宙依次分化为无机层、有机层、异质成形层。生命形态就这样历经物质、生命和文化的演化进程,一步步从混沌宇宙中涌现、从地球演化中产生、从物种历史中走来,最终,从匀质化的混沌宇宙发展为异质性的世间万物——以“一”生“多”——达成多元论=一元论。加塔利生态哲学思想的生发,以混沌宇宙作为思考的原点,秉承伦理美学范式,走向以“一”生“多”的创造性道途。
混沌互渗以混沌褶皱拉开了审美创造的序幕。混沌褶皱最初产生于混沌的力量与高度复杂性的力量的共存之中,进而超越混沌而位居思考的核心:从复杂性到混沌,多样性实体震荡于混沌与复杂性之间,以无限速度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往返运动,分化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异质性状态,消解了其形式上的多样性,回归同质化的混沌状态;从混沌到复杂性,多样性实体持续不断地冲入混沌的中心地带,在这里,它们丧失了外在的指涉和坐标,可是也恰恰是在这里,它们得以重新显现自身,从而被赋予新的复杂性。上述两种相反相成的过程,持续的震荡于减速的有限世界和无限速度的世界之间:一方面,在减速的有限世界中,一个界限紧随另一个界限,一个限制紧随另一个限制,一个坐标系紧随另一个坐标系,人们从未抵达无处不在的存在-质料(being-matter)的终极界限;另一方面,在无限速度的世界中,无形之物的存在不再被否定,它通过内在的差异呈现自身,亦或通过异代生成(heterogenesis)的质性呈现自身。[3](P.110-111)混沌互渗的过程,亦即抽象机器运作于内在性平面上的过程,也是异质性的存在-质性(being-quality)和同质性的存在-质料-虚无(bing-matter-nothingness)在内在性平面上取得一致性(consistency)的过程,此过程发生在有限和无限的交叉口、复杂性和混沌的接洽点。综上所述,混沌互渗“是一种在可感知的有限性的基础上把握创造性潜力的力量……它把有限速度的事件置于无限速度的中心,前者带来的潜力将后者建构为创造性强度。无限速度承载着有限速度,将潜在转换为可能,将可逆性转换为不可逆性,将延拓转换为差异。”[3](P.115)混沌互渗从本体论意义上厘清了伦理美学范式是如何通过有限重建无限,并因此而走向创造性的。
内在性平面犹如从混沌中摆渡的木筏,是加塔利借以对抗混沌的思维的平面。人类思维像梭子一样以“无限速度”折返(掠过并返回)于内在性平面上——从混沌到复杂性(复又折返),从无限性到有限性(复又折返),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即为混沌互渗(Chaosmosis)。混沌互渗也可译为混沌界,是一种从内在性平面出发的超验的创造过程,“互渗”一词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思维以无限速度震荡于(同时也横贯于)混沌与复杂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现实性与潜在性、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动态的、相互转化的过程,为我们诠释了伦理美学范式是怎样通过潜在性与实在性的一致性来颠覆本体论的,与此同时,又是怎样以“一”生“多”——从匀质性的混沌宇宙(“一”)生成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生命形态(“多”)的。然而,帕斯卡尔意义上的无限速度只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本体论上同质的无限性(homogeneous infinity),这是一种被动的、未经分化的无限性,而伦理美学范式的创造性诉求,则需要一种主动的、活跃的混沌褶皱(chaosmic folding)。
那么,伦理美学范式到底是如何重拾被科学范式悬置的“变异的感动和情动”来激活创造性的呢?加塔利以混沌互渗(Chaosmosis)为理论支点对此做了本体论思考。思考的切入点为:如何赋予潜在性的无形之物以本体论的厚度,把它们等同于现实的能量-空间-时间坐标中的实存对象;思考的关键点为:如何取得潜在的无形之物之无限性与现实的实存对象之有限性的一致性,这无疑是潜在的无形之物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加塔利在《混沌互渗》中就此问题发出了如下设问:“如何将无形之物的织体(texture)的非话语的、无限的特性与能量-空间-时间之流及其相关命题的话语的有限性联系在一起?”[3](P.100)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借用了帕斯卡尔(Pascal)在《思想录》中的思考:“你以为上帝无限且无法分割为各个部分是不可能的吗?那么,我要向你展示某种无限而又无可分割的东西。它是一个以无限速度到处运动着的质点:因为它在所有地方都是一,而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整体”。[3](P.110)加塔利笃信:“只有寄希望于一个被无限速度激活的实体,才能同时囊括一个被限定的指涉对象和各种无形的场域,并因此赋予此命题的各个矛盾项以可信度和一致性。”[3](P.110)毫无疑问,此“无限速度”正是思维本身,而思维过程则在内在性平面上进行,加塔利(和德勒兹)在《千高原》中就曾明确了这一点:“内在性平面……是一副思维的图景……思维的图景由无限运动构成”。[5](P.250-251)
Jia Ren has an indolent nature while Shylock believes effort leads to wealth.
正是从表达实体和表述装配入手,加塔利在机器装配理念的基础上,将一致性平面绘制在四个象限上,形成了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四象限装配模型”顾名思义,就是将参与装配的四个本体论函子——机器语系(Φ)、价值世界(U)、存在之域(T)和流(F),[3](P.60)分别绘制在一致性平面所界定的四个象限内,这就通过表述装配的无限性,将真实的、话语性的主体性组件——流(F)和机器语系(Φ),与潜在的、非话语性的主体性组件——存在之域(T)和价值世界(U),密切联系在一起,[3](P.59)实现了实存世界与潜在世界的横贯性,赋予潜在的无形之物以本体论的合法性。“四象限装配模型”通过四个本体论函子的设定,摆脱了那些最终被化约为二元论的三元结构,这是因为,第四项就意味着第n项,可以使主体性生产面向多样性敞开,同时也面向创造性的生成敞开。
三、主体性生产:以“多”对“一”的生态智慧救赎
伦理美学范式庇护下的生态智慧以主体性生产为中心,把生态危机作为“重塑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产的生产目的”[4](P.18)的伦理学和美学工程,旨在重建“可栖居”的人类星球。加塔利在《混沌互渗》的最后一章“生态智慧的目标”中,将“物质、能量和符号的流(Fluxes)、具体的和抽象的机器语系(machinic Phylums)、潜在的价值世界(incorporeal Universes)和有限的存在之域(existential Territories)”列为生态智慧的四个目标。[3](P.124)这四个目标恰好对应于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中的四个本体论函子,最终被安置在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三重向度内完成。加塔利在《三重生态学》的结尾部分对此做了明示:“借由这些横贯性工具,主体性能够同时将自身安置在自然环境领域、主要的社会和机制装配中,并相应地安置在对个体的最私密领域的描绘和幻想中”,主体性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创造性发展,都将促进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所有这些领域的良性发展,将“从最细微处开始,逐步再造和重建人类自信心”[4](P.47)。由此可见,三重生态向度内完成的主体性生产可以实现生态智慧的目标,旨在通过人类自信心的重建履行生态救赎。
那么,到底何谓主体性生产呢?主体性生产是加塔利在主体终结的语境中,对精神、社会场域、机器界、生物界和混沌宇宙的制图学探索。加塔利对主体性生产的制图学思考,建基于精神分裂分析语言理论——反意指符号学(a-signifying semiotics)之上,将主体性视作语言建构的结果。反意指符号学批判地继承了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的“四元图式”,并将其拓展到语言学之外的整个混沌宇宙:以一致性平面取代叶尔姆斯列夫“四元图式”之外的“第五项”——要紧之事,④以双重表述(double articulation)作为抽象机器,通过对一致性平面上的无定型的、无从定位的“要紧之事”进行编码和辖域化,使其成为内在性的自我表达和自我组织,这就“在一个扩展的机器范畴重新定位了符号学,把我们从表达/内容的语言学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将诸如生物编码或社会组织形式等无限多的表述实体(enunciative substances)整合进表述装配(enunciative assemblages)”,[3](P.22-23)建立了主体性生产的关键性理论范畴。表述实体实现了内容和表达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使主体的存在功能得以安驻;表述装配容纳了语言的和机器的多样性表述实体,超越了叶姆斯列夫的三分法(物质-实体-形式)结构,为主体性生产觅得了新的表达支持。[7]
伦理美学范式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的本体论铁幕。伦理美学范式预设了横贯于实在性和潜在性两个领域的实体——横贯性实体的存在,这无疑以一种“和”的逻辑化解了实在性与潜在性的二元对立,赋予潜在性的无形之物以本体论的厚度。哲学思维的重心也从本体论的一般等价物存在(being),转换到存在物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生成(becoming)过程,加塔利在《混沌互渗》中对机器论的重新定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机器论意味着一种双重过程——自创生-创造的(autopoietic-creative)过程和伦理-本体论的(ethical-ontological)过程……存在(being)并不先于机器的本质,过程先于存在的异代生成。”[3](P.108)这就通过创造性(生成)的“过程”相较于“存在”的优先性,颠覆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创造性是人类文明走向“多”样性的根本动力,多样性从本质上正是生态精神的体现。
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伦理美学范式是加塔利贯彻其一贯的横贯性逻辑的结果,它在以美学范式抗衡科学范式的同时,也设定了伦理范式对美学范式的牵制。在加塔利看来,“谈及创造,就必须谈及对所创造之物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关注事物状态的拐点、预先设定的图式的分叉,以及对于极端模式下他异性(alterity)的境遇的考虑。”[3](P.107)也就是说,伦理规范和审美创造应该同时得到关注:前者强调责任和必要的参与性,倡导各个相关领域的人都应该参与个人/群体的主体性生产;后者强调差异和创造性的力量,认为“一切必须不断地创造,重新从头开始,否则,将陷入一种固步自封的死循环过程。”[4](P.27)对伦理范式的诉求,使加塔利倡导:所有影响人类心理的个人和集体,包括精神分析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时尚设计师等,都应该参与主体性的重塑;[4](P.26)对于审美范式的诉求,使加塔利倡导:所有从事与主体性相关的过程的人,都有责任走出当前存在之域的死寂的“自在”状态,走向一种开放性的“自为”状态。[4](P.36)伦理美学范式的精神实质就是对创造性的诉求,“自为”存在构成伦理美学范式的核心。
加塔利在《三重生态学》中就其生态智慧救赎之道进行了阐释。以三重生态向度内的主体性生产为轴心,生态智慧救赎的策略如下:一、精神生态向度,个体通过“艺术地生存”走向持续的再特异化,个体主体性走向特异性,人类的精神价值体系走向多元化,达成可持续心智模式;二、社会生态向度,每个个体主体性的特异性,必然意味着群体主体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从而使人类社会关系因差异性和多样性而走向“和而不同”的局面——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方式,最终使整个社会群体走向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三、精神生态向度和社会生态向度以“二律背反”之势反作用于自然生态向度,无论是个体层面可持续心智模式的达成,还是群体层面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形成,最终都通过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更好地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向度。
行文至此,让我们把目光再度锁定“一”与“多”,借以揭开加塔利机器装配式生态世界观的面纱。一、“一”就是一个根茎(rhizome)②。根茎是由众“多”异质性的“部分对象”装配而成的多元体,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始终居于中间。“部分对象”犹如异质共存的“碎片”,以不可预知的方式聚合成根茎,聚合的方式遵循“和”的逻辑——将连词“和……和……和……”作为根茎的织体[5](P.33)。“和”的逻辑使思“在其中”或“在中间”获得其最高速率,③在与宇宙共思(而不是思考宇宙)中,以连词“和”撼动了动词“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也由“它是什么”变成了“它生成什么”,从而以生成论颠覆了传统的本体论。二、“多”表征了异质的多样性(multiplicity)。在机器装配过程中,众“多”异质共存的“部分对象”中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部分对象”之间彼此充满了差异,它们聚合成的整体,不再指涉统一性和全体性,唯有多样性这一范畴可以阐释其特性。在加塔利(和德勒兹)看来,“欲望生产是纯粹的多样性,也就是不可简约为统一性的肯定性。”[6]三、“多”与“一”再定义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反俄狄浦斯》第一章“欲望机器”的结尾部分,加塔利(和德勒兹)借普鲁斯特之口指出:“整体……作为与诸部分并存的一部分生产出来,各个部分既未被整体统一,也未被整体全体化,不过整体与各个部分协调一致,因为整体……在诸要素之间确立了横贯的统一性,而这些要素在它们特有的维度上保留它们全部差异的因素。”[6]由此可以推论,生态系统是通过多元生命形态的“横贯的统一性”生产出的内在性的生命整体,诸生命形态的异质共存确保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异质性和多样性将机器论引向生机论,生机论构成加塔利生态世界观本质。
“‘无脂’并不意味着吃多少都可以,”美国营养学专家、《先看再吃》一书作者邦妮·塔布迪克斯说,“包装上自称‘无脂’,但其实它可能含有大量糖;而那些自称‘无糖’的,可能含有大量脂肪。”因此,要仔细检查热量标识,并与相应的“全脂”比较,才能得知真实情况。
综上所述,加塔利的生态美学思想,究其实质是一种通过顺遂人性来遵从物性的减法智慧。如果说都江堰的“鱼嘴”之所以被视为是防洪工程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它通过顺遂“水性”对岷江水进行了分流,那么,生态智慧之所以能够履行生态救赎,在于它对人性中欲望的洪流进行分流和疏导,而不是相反的施之于制约和束缚。伦理美学范式正是加塔利顺遂人性的范式,它巧妙地通过伦理和美学的横贯性展开了与人性的博弈:如果将人类“欲望”比作一只放飞的风筝,伦理美学范式则犹如拽在人类手中的那根风筝线:伦理范式对责任和参与的诉求,表征了人类通过收紧风筝线对人性施之以适度的辖域化——通过泊定人的存在之域(T),赋予人性适度的规范;美学范式对艺术实践及其创造性的诉求,表征了人类通过放松风筝线,对人性施之于适度的解辖域化——通过更新人的价值世界(U),赋予人性适度的自由。总之,伦理美学范式以一种横贯于美学创造与伦理本体的本体论——“美学-本体”论,颠覆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使加塔利的生态美学走向一种异代生成的本体论美学。
注释:
①加塔利是横贯性理论的创始者,横贯性是贯穿于加塔利的哲学思考和社会实践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我们了解加塔利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加塔利在他的文章《横贯性》中首次提到横贯性,此文章可追溯到1964年,并于1972年收录进其著作《精神分析与横贯性》。横贯性真正频繁为学界认知,是在加塔利与德勒兹合作的系列著作中,诸如:《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与此同时,横贯性也出现在了德勒兹的论著《普鲁斯特和符号》中。
②加塔利(和德勒兹)在《千高原》的导论部分论证了作为十五座高原之一的根茎高原,深度剖析了根茎的内涵及其特征,诸如:可连接性、异质性、多重性、生长的不可预知性、可以对之绘图但不可对其模仿等特性,从认识论层面上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通过生成来把握存在的思想图像。
③[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和”的逻辑对于“在中间”的推崇,是加塔利(和德勒兹)的根茎哲学颠覆传统本体论的关键,《千高原》中如此论述“在中间”的力量:“……中间决不是均值,相反,它是事物在其中加速的场所。在事物之间,……一种(卷携着一方和另一方的)横贯的运动,一条无始无终之流,它侵蚀着两岸,在中间之处加速前行”。
④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以“四元图式”取代了索绪尔的能值-所指的“二元系统”,重新将能值与所指命名为“表达”与“内容”,这两个要素自身又都由形式与实质咬合而成,形成了“双重表述”(double articulation):第一重咬合将内容的形式与实体关联起来;第二重咬合将表达的形式与实体关联起来。除此之外,还添加了第五项,作为内容与表达的双重表述所欲以传达的意义,称之为要紧之事(matter)或要旨(purport)。
参考文献:
[1]Harries-Jones,P.ARecursiveVision:EcologicalUnderstandingandGregoryBates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5.
[2][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欲望机器(上)[J].董树宝译.上海文化,2015(8).
[3]Guattari,F.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Translated by P.Bains& J.Pefanis.Sydney:Power Publications,2006.
[4]Guattari,F.TheThreeEcologies.Translated by l.Pindar &P.Sutton.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4.
[5][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6]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欲望机器(下)[J].董树宝译.上海文化,2015(8).
[7]张惠青.混沌互渗:走向主体性生产的生态美学[J].浙江社会科学,2017(8).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4—016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18ZDA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惠青,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山东 济南 250000
收稿日期2018-12-20
责任编辑申燕
标签:范式论文; 美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生态论文; 混沌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美学与现实社会生活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 (18ZDA024)阶段性成果论文;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