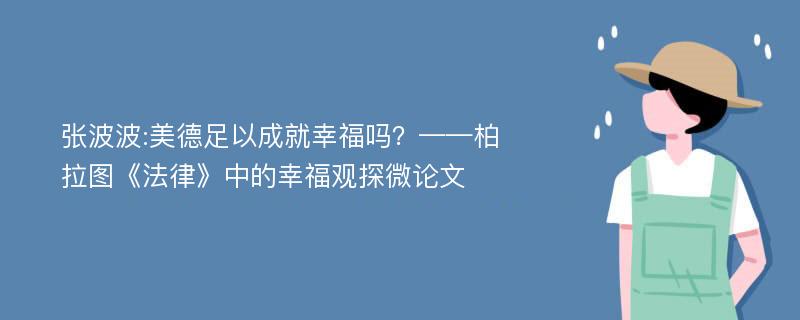
【摘 要】美德作为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被普遍认为是最高善和至高目的——“幸福”所不可或缺的成分。然而,柏拉图在后期对话录中究竟坚持美德是幸福的主要成分还是唯一要素,这在西方古典幸福论研究传统中颇有争议。亚里士多德及古希腊悲剧的现代研究者基本上都不认同“美德的充分性”论点,而是强调运气等外在因素对幸福的实质性影响。不同于以往片面否定柏拉图在晚年仍坚持“美德足以成就幸福”的做法,本文结合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试图从《法律》这一目前受关注较少的晚期文本出发,论证《法律》其实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充分性论点”,而且这一论点与一系列直觉上可信的、对自身构成明显威胁的要求与主张并不矛盾;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把“对某些外在物的需求与快乐是幸福的必需之物”与“美德是幸福的充分条件”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观点统一起来的可行思路。
【关键词】柏拉图;《法律》;快乐;美德;外在物;幸福
一、引论
“美德(arete)足以成就幸福(eudaimonia)”(简称“ST”(1)“ST”是“the Sufficiency Thesis”(充分性论点)的缩写,英文是“virtue is sufficient for happiness”(可理解为“美德对于幸福是充分的”“美德足以使人幸福”“美德足以带来幸福”或“美德是幸福的充分条件”),这是学界的一般标注法,参见T. Irwin,Plato’s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59;G. Rudebusch,Socrates,Pleasure,andValu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5.,下同)被普遍认为是柏拉图伦理学的中心论题(2)Julia Annas,PlatonicEthics,OldandNew,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44-45.。这个论题让柏拉图避免了“幸福论”(eudaemonism)和“义务严格论”(deontological rigorism)之间的冲突,即在“幸福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因此,道德反思集中于“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幸福”)这一观念和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坚持认为的“一个人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应该只看对或错、正义或不正义”这一信条之间的冲突。如果美德足以带来幸福,那么对幸福的追求就不必与正义发生冲突。有美德的人,在决定如何行动时总是考虑什么是正确(正当)的,因此是幸福的。
有些学者否认“美德足以带来幸福”这一观点贯穿于柏拉图的整个中期对话,尤其是《理想国》。安纳斯(Annas)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中期柏拉图学派显然同意她的观点(3)Julia Annas,“Platonic Ethics,Old and New,” Reviewed by Donald Morrison,Ethics,vol.111,no.3,2001,p.618.。
N,W,V仍然是P-独立的,变换前后各个参数都对应存在明确的数量关系[6-7]。为记号简单,下面假设p,q,ξ,η1,η2,λ已经文[7-8]求出。
然而,柏拉图晚期的对话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赞同“美德足以成就幸福”这一命题,这在当今学术界掀起了不小波澜。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它不只关乎历史的好奇,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原则上讲,该命题对我们的直觉似乎构成了一个不小的挑战,即一个有美德的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幸福的,不管他遭遇了什么,如是否处在迷茫痛苦中,是否患有重病等。事实上,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经验“直觉”告知:一个人可能是有德性的,但却造化弄人,无法享受外在之物(如美貌、权力、金钱)以及由此带来的快乐(和所谓的日常“幸福”)。用古希腊悲剧研究者的话语来说,撇开品性的好坏不谈,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无论是好是坏,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成功或满足,也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核心伦理元素:诸如我们是否在公共生活中正义地行为,我们是否能够爱和关心他人,我们是否有机会勇敢行事等等(4)关于古希腊运气与个体幸福之关系的详实探讨,参见M. Nussbaum,TheFragilityofGoodness:LuckandethicsinGreektragedyandphilosophy(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xiv.。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在哲学、古典学或阐释学领域,人们当前对这个难题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对ST嗤之以鼻,付诸一笑(5)对柏拉图的质疑,对照Aristotle,NicomacheanEthics VII 13 1153b19-21;《尼各马可伦理》的中译本,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M. Nussbaum遵从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参见[美]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萌、陈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19、345页;对于这种批评传统的概述,参见J. Annas,TheMoralityofHappines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31;对ST的嘲笑和其他批评,参见R. Sorabji,EmotionandPeaceofMin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07;关于道德(内在善)与运气(外在物)之间关系的现代论述,参见B. A. O. Williams & T. Nagel,“Moral Luck,”AristotelianSocietySupplementaryVolume,vol.50,issue 1,1976, pp.115-152; T. Nagel,MortalQuest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4-38;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0-151页。;另一种则认为即便柏拉图在早年持有过它,他也不可能在生命后期的思想成熟阶段仍一如既往地拥护它(6)这种观点,主要参见T. Irwin,Plato’s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99,p.249.而且,Irwin认为柏拉图从《理想国》第二卷起,热衷于捍卫“比较性命题”(the comparative thesis),而不是充分性命题,参见T. Irwin,Plato’s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92.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柏拉图在晚期对话录中仍坚持ST。他们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这两部作品中的观点是,美德足以让人幸福,但以后来的理论标准来看,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并不明确。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这两部作品中,美德对于幸福是必要的,参见J. Annas,PlatonicEthics,OldandNew,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138; G. R. Carone,“Pleasure,Virtue,Externals,and Happiness in Plato’s Laws,”HistoryofPhilosophyQuarterly,vol.19,no.4,2002,pp.301-317;最近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参见D. C. Russell,PlatoonPleasureandtheGoodLife,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5,p.168;另参见J. Annas,“Virtue and law in Plato,”in Plato’sLaws:ACriticalGuide,edited by C. Bobonic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71,footnote 1.本文的总论点与后一种立场保持一致,但采取的论证方式很是不同。。不难看出,这两种回应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对ST近乎鄙夷的漠视,仿佛ST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
本文提出疑问,尝试挑战这种根植于哲学传统中的常识至上论的顽固偏见。
jieba 分词支持三种分词模式:一是精确模式(默认模式),试图最精确地切分,适合文本分析;二是全模式,把所有的可以成词的词语都扫描出来,速度非常快但是不能解决歧义;三是搜索引擎模式,在精确模式的基础上对长词再进行词切分,以提高召回率,适合用于搜索引擎分词。前两种模式使用jieba.cut()函数,通过参数进行选择模式和具体算法,第三种模式使用jieba.cut_for_search()函数。三种模式的常用格式分别为:
这些说法反过来指出了混合着痛苦的快乐和纯粹的快乐之间的区别。尽管《法律》并没有对纯粹与混合的快乐进行详细的处理,正如在《理想国》和《菲丽布》中所发现的那样,但它仍然假定这些处理是为了支持它对美德生活的偏爱,因为后者在定量上更令人愉悦(cf. II 6164b,V734d)。因此,在那种生活中,痛苦更小,也更少发生(734a);甚至柏拉图认为,适度的神性满足的生活应该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快乐与痛苦的激烈混合的生活(VII792-793a)。这样就可以把《法律》看作是证实了柏拉图在之前的对话中试图将美德的生活与享受全部快乐的生活调和起来的尝试。此外,《法律》试图通过论证美德的存在本身取决于一些先决的外部条件,来调和某些外在的明显需要和充分性的论点,这表明,美德的生活更有可能以一种更纯粹、更持久的方式享受着外在奖励。
本模式以低碳环保为目标,电源方案以发展省内核电、新能源等非化石能源电源为主导方向,应重点关注系统调峰问题。2030年广东较已明确核电机组再新增装机15 GW,新增风电装机20.5 GW,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9.4 GW,无需新增煤电装机。
然而,这个反驳不是决定性或无可辩驳的。即使将美德所必需的外在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所有其他外在因素对美德而言变得无关紧要,柏拉图仍可坚称,美德的生活确实比邪恶的生活更令人愉快(V734d,cf. II 662d)。因为,许多人常把“夹杂痛苦的”快乐和“纯粹的”快乐混淆在一起,从而忽略了某些快乐的痛苦代价,而这些快乐实际上使一种狂妄自大、贪得无厌(以及追求外在物)的生活以痛苦告终。《法律》用了大量例子来说明,混合、贪得无厌的快乐是如何给人和城邦带来坏运气、不幸的(VIII 831e-832b),以及伴随过度的外部因素而来的傲慢(hubris)是如何注定导致人走向毁灭的(VI716a-b,V742e-742c)。同样,缺乏智慧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会导致一个人行动的失败(V732a),而不诚实的人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注定没有朋友,只与寂寞为伴,与孤独为伍(V730c-d)。相比之下,最好之人即是那些正义而明智的人,能认识到快乐的真正本性,从而把正义的生活标识为更愉快的(II 663c,cf. III 734d)。不仅如此,《法律》甚至暗示,美德的生活蕴含了其自身的快乐,因为“每当我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好时,我们就会乐得欢欣鼓舞”,反之亦然(III657c)。美德本身的特征是,理性所规定的一个人应当做的事和自然的愉悦感之间的完全和谐(II653a-c)。因此,如果快乐来自于对一个人的精神(灵魂)运作良好或“卓越”(优秀)的意识,甚至构成了美德定义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美德的生活是如何内在地令人愉快的,它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外在物的分享;即便在外部因素上没有任何分享,它都可以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一种有美德的生活,就像一种享受快乐多于痛苦的生活一样,不需要依赖外在东西,除非后者是美德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必要条件。当然,这并不排除美德本身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好处,如好的声誉(III 734d)。美德的生活可能会带来一些外在的东西,这些东西会增强一个人的幸福,并从长远上证明对个人有利(cf. II 662d)。
其次,可以肯定,苏格拉底在早期对话中所持的观点,远未被普遍接受。因为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段落表明,某些环境本身独立于美德,会使生命不值得活下去。在一些对话如《克里同》和《高尔吉亚》中,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对话者们理所当然地假定,如果一个人身患绝症,生命就不值得活下去(10)参见Crito47d-e;Gorgias512a.。鉴于此,一些当代的声音支持这样一种解释,即在早期对话中美德归根结底并不足以使人幸福(11)参见G. Santas,“Socratic Goods and Socratic Happiness,”Apeiron,vol.26,1993,pp.37-52; T. Brickhouse and N. Smith,PlatoandTheTrialofSocrates,New York: Routledge,2004,p.183; G. Rudebusch,Socrates,Pleasure,andValu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p.115;对于柏拉图是否在早期的对话中致力于ST的深入探讨,参见T. Irwin,Plato’s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73-74.。若是如此,那在“苏格拉底式对话”中充其量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即一些段落强烈地暗示了对ST的承诺,而另一些则似乎在软化或完全否认ST。
这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首先,柏拉图与“充分性论点”的批评者们一道,认为不受冤屈在某种程度上是eudaimonia(幸福)的必要条件。然而,他补充了额外的说法,即与充分性论点一致,一个完全善良、有德性的人将手握防止被冤枉的手段。可是,他所说的这种人人向往的“完美”或“完全的善良”是指什么?一个完全良善的人怎样才能免受不公正的待遇呢?
二、美德、外在物与幸福
首先,美德对于外在善(External Goods)(12)或译作“外在益物”或“外在好”。的意义何在?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始于《法律》第一卷。在《法律》开篇,柏拉图开门见山地用略带挑衅性的口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外在物(13)或表示为“外界因素”,英文通常译作“externals”或“external factors”. 参见G. R. Carone,“Pleasure,Virtue,Externals,and Happiness in Plato’s Laws,”HistoryofPhilosophyQuarterly,vol.19,no.4,2002,p.329; Gerd Van Riel,Pleasureandthegoodlife:Plato,AristotleandtheNeoplatonists,Leiden : Brill,2000,p.31.与美德之关系的主张。第一,他把“善”分为人的和神圣的,并提出“人的善”(human goods),包括我们所说的外在东西,如健康、美丽、体力和财富。这些东西与以美德(智慧排在第一,节制、正义和勇敢依次排在其后)为代表的“神圣的善”(divine goods)形成鲜明对照(631b-d)。第二,关于二者的关系,他紧接着提出了三个著名说法:(1)人的善“依赖”(ertetai)于神圣的善;(2)接受更大的(即神圣善),也获得较小的(即人的善);(3)如果不这样做,他就失去了这二者(631b)。(1)和(3)表明,神圣善是人的善所必需的,而说法(2)则表明,神圣善对人的善是充分的(14)对于这两种善的细分,参见Plato:Laws1and 2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Susan Sauvé Mey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p.109.。
柏拉图指出,美德对于外在善是必要且充分的。人们通常将其理解为,拥有美德对于拥有外在物来说是必要和充分的,这显然是有问题的(15) 如Prauscello,参见L. Prauscello,PerformingCitizenshipinPlato’sLa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28.。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反驳这一说法的事例。例如,生活中有很多人是有德而面貌丑陋,或者富有而心地邪恶。这些例子显然支持外在物和美德是相互独立甚至分离的。
然而,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这并不是柏拉图所暗示的。他的这一观点并不是指美德对于绝对外在的东西是必要且充分的,也不是说外在东西本身就是“善”,而是指美德对于人(或“外在的”)的善是必要且充分的。因此,应该这样理解柏拉图的说法:美德对于外在的真正善(即变成了真正之“好”的外在物)是必要且充分的。所以,虽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可能有美而无德,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不可以称这个人的美为一种“善”。相反,只有当一个人有美德时,才能称他的健康、美丽、力量和财富是对他而言的“善”。唯有这样理解,《法律》第一卷中涉及美德对于外在善的必要性和充分性的说辞才可以与《法律》第二卷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
其次,美德对于幸福是充分的吗?在《法律》第二卷中,柏拉图对此的总体看法是,健康、美貌、财富、权力和长寿等所谓“善”的价值与美好或幸福的生活无关。具体而言,第一,他指出一个人只要适度(节制)而正义,无论他是强是弱,是富是穷,都将会幸福(660de);第二,“所谓的恶”,如疾病和短暂的生命,对不义之人是有好处的(661d)。可见,健康、美丽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或价值中立的。就其本身而论,它们到底是好是坏?柏拉图的回答是,这取决于它们分别是与正义还是不义相结合。如此看来,美德对于外在善是必要且充分的,而恶习对于外在恶是必要且充分的(16)有关美德与外在善的关系,参见G. R. Carone,“Pleasure,Virtue,Externals,and Happiness in Plato’s Laws,”HistoryofPhilosophyQuarterly,vol.19,no.4,2002,p.341,footnote 9.。因此,在这一点上,《法律》第二卷与第一卷一致表明,美德使外在物变得美好。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美德本身也能带来幸福。这些说辞显然构成了关于ST的一个简明陈述。
最后,快乐在幸福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人们通常认为有两种生活,即最正义的生活和最快乐的生活,或认为可能有不义的人过着总体上愉快的生活(17)正义生活与愉快生活的关系,参见D. C. Russell,PlatoonPleasureandtheGoodLife,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5,p.75.。然而,在《法律》第二卷中,柏拉图继续争辩说,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他认为,具有最多快乐的生活和具有最多美德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664-c),二者都是最幸福的(662d-e)。可见,对柏拉图而言,快乐是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662e-663a)。
但是,如果快乐是幸福所必需的,且与美德携手同行,我们就会对先前的说法感到困惑,即为何外在物本身对美德和幸福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像《法律》里的克利尼亚斯(Cleinias)这样胸无点墨、无知妄作的观众来说,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一个有美德的人若是没有健康,或者又穷又丑,那他的生活怎么可能会是愉快的呢?在这一点上,现代学者们的通常看法是,在《法律》关于幸福的论述上,外在因素确实扮演了“内在善”的角色,而美德完全不足以构成幸福。(18)如Irwin,参见T. Irwin,Plato’s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46-347;André Laks,“Plato’s truest tragedy: Laws Book 7,817a-d,”in Plato’sLaws:ACriticalGuide,edited by C. Bobonich,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28.但如果是这样,当前面临的难题便是如何解释柏拉图在《法律》660d-661d处的这个说法所造成的矛盾:他在这里否认那些所谓的“善”(如健康等)的内在价值,并提出一个人在贫穷软弱、悲伤忧愁的时候也有可能幸福。
第二,应指出,这一结论与《法律》中强调外在物对于幸福无关紧要的说法并不矛盾(LawsII,660d-e)。柏拉图认为健康、金钱等,对于美德之人确实是好的(即工具性的善)(661b),即使它们对不义的人有害。此外,当柏拉图表示同意克利尼亚(Cleinias)的这一说法——“你迫使诗人说,善良而正直的人是幸福的、有福的,无论他是大是壮还是小是弱,无论他是否富有”(660e)——时,应根据上下文理解后一句话,即,只要使美德得以实现的最小条件得到满足,对某些外在物的剥夺就对美德变得无关紧要。
毫无疑问,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否认柏拉图实际上指的是最多的美德和最多的快乐(和幸福)之间的联系。因为,他确实指出,即使事情的真相不是他描述的那样,该描述也会构成一个最有用的谎言(663d):它至少强调,正义与快乐是相辅相成的,这一论点有助于人们虔诚而正义地生活(663a-b)。如是这样,柏拉图就不需要在哲学上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美德至上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最大快乐的生活。在此情况下,美德的吸引力仍然相当模糊。例如,一个人可能愿意选择美德,即使没有从中获得快乐。
然而,了解了柏拉图在第五卷中对快乐的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后一种观点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它清楚地表明:(1)快乐是每个人自然追求的目标,痛苦则是每个人自然厌恶的目标;(2)最好的生活包含了更多我们自然追求的东西,即快乐(732e-733a)。有美德的生活比邪恶的生活更令人愉快(734a-b)。事实上,正是基于正义的生活是愉快的,每个人才都愿意追求快乐。对柏拉图而言,没有人心甘情愿选择不义的生活(734b)。所以很明显,柏拉图确实想要维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快乐与好的生活密不可分,这也是快乐对我们人类有致命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一点上,可以把《菲丽布》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菲丽布》清楚地表明了柏拉图的观点,即快乐实际上是“行为人”(agent)自身善的一部分,因为后者的善在于他的态度和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观点,而他的快乐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态度和观点。当柏拉图说快乐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好的品格在没有快乐的情况下对于幸福是永远不够的。相反,他揭示了快乐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是好的品格的一部分,是理性改造自我的所有维度的产物。既然良好的品格或美德是这样一种整体,那么快乐对于幸福是必要的,美德对于幸福是充分的(19)有关快乐与好生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探讨,参见D. C. Russell,PlatoonPleasureandtheGoodLife,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5,pp.167-168.。
但即便快乐是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II 663a),我们仍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难题:这一观点是否可以与第二卷中的另一主张——健康、美丽、财富并不没有被“正确地”或“恰当地”(orthos)称为“善”(661a),因为它们也可以是坏的,而一个好人不管有没有它们,都可以是幸福的——保持一致(660d-e)。
定时。种苗培育饲料投喂是关键,严格按照固定的时间投喂有利于鱼类尽快形成摄食习惯,便于鱼群集中等候。要求少量多餐,一般推荐一天投喂次数不少于四餐。即早上第一次投喂8:00-9:00,第二次10:00-11:00;下午第一次投喂14:00-15:00,第二次17:00-18:00。
对于这个难题,柏拉图总体上强调某些外在物对于美德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对外在物或所谓“善”的极端剥夺,确实会阻碍美德的培养,甚至使其完全不可能。如果是这样,柏拉图仍可以一致地坚称美德足以使人幸福(如II 660d-e),同时宣称健康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在某种最小程度上是美德所必需的。在此,第五卷的内容很具有启发性:在那里尽管灵魂被视为人类最高的财产(726),我们仍需适当地尊重我们的身体,只要认识到对某些外在东西的过多拥有或缺乏会导致自己染上各种各样的恶习。财富是为了身体而存在,而身体是为了灵魂而存在(IX 870b)。因此,过分丑陋,被明确说成是卑鄙吝啬的,而太少的钱则产生奴性(728d)。同时,身体健康的生活比身体不健康的生活更愉快(734b);肉体上和灵魂上的卓越(优秀)生活比邪恶的生活更愉快(hedio)。假设柏拉图在《法律》中一如既往地将肉体设想成灵魂的工具(20)参见harma,X 899a; cf. ochema,Tim. 41e,44e,69c.,那么,万一我们的身体——本应是灵魂的载体——运转不良(如由于极度贫困而引起的饥饿),精神和谐(或美德)(21)美德被认为是心灵的和谐,对于这个观点,参见II 653b,I 626d-628d,III 689d.的生活将会受到阻碍或完全不可能实现。在这一问题上,诸如最低限度的财政资源和健康等外部因素确实与美德相关,甚至在手段上变得必要(22)关于身心平衡是过一种美好(kalonkaiagathon)生活的必要条件,对照Tim. 87c.。
MICHEL制帽坊位于巴黎的Rue Sainte Anne大街。设计师Pierre Cardin率先采纳了MICHEL的新设计,其后Christian Dior、Givenchy 及 Yves Saint Laurent亦相继跟随。不久,Karl Lagerfeld、Jean-Paul Gaultier、Yohji Yamamoto、Christian Lacroix、Kenzo等品牌设计师也成为了MICHEL的客户。
在家庭中,尤其是夫妻之间,心平气和的说话是一个理论上正确,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这样做的沟通方式。更多的人在和伴侣交流时只想表达自己的情绪,比如:“你总是不洗碗不扫地,什么家务活也不做,这日子真懒得和你过了。”“让你干个什么事总是拖拖拖,对我说的话一点都不上心!”等等。
当然,关于这些最小的先决条件或必需品(anankaia)的清单应该有多少,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23)对照V 729a,cf. 742a,VI 774c,VIII 828d.。可以将《法律》本身看作一个计划,其目的是构建一个解答方案(24)对照IV 766a.。例如马格尼西亚(Magnesia)城邦,将限制财富和贫困(742V,742d-e)(25)对照V 728e-729a,743a-744d; VI 774c; XI 918b-919d;有关这个城邦的性质的探讨,参见D. Cohen,“Law,Autonomy,and Political Community in Plato’s Laws,”ClassicalPhilology,vol.88,no.4,1993,p.311.,实施一套以身体和灵魂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使其尽可能地优秀(VII788c)(26)有关《法律》中第一教育的探讨,参见E. Georgoulas,“The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First Education in Plato’s Laws,”apeiron,vol.45,2012,pp.338-353.。但是,除了这一特别建议的细节之外,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某种程度的外部因素份额对于美德来说是必要的,而更大的份额,虽然不是过度的份额,也可以对于幸福构成有益的或增强的(尽管不是必要的)条件。
对比两组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包含电解质失调、呼吸道堵塞、舌咬伤)、护理的总有效率,疗效判定标准:显效:经护理,患者意识、感觉障碍、抽搐等症状基本消失;有效:经护理,患者意识、感觉障碍、抽搐等症状发作次数减少50%;无效:经护理,患者意识、感觉障碍、抽搐等症状无明显改善,以有效加显效例数占总例数之比计量总有效率。
三、快乐、权力与完美美德
首先,在幸福、外在物和快乐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人们常常抱怨,把美德(和幸福)所必需的外部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不能使我们更接近这样一种说法,即美德的生活比邪恶的生活愉快百倍(cf.Laws,V734b)。此外,有人甚至可能会反驳说:如果邪恶的人能通过其恶行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财富等外部因素,那么他们的生活至少可以和美德的生活平分秋色,一样令人愉快,甚至比之更愉快。(27)对于这种反对的详细内容,参见R. F. Stalley,AnIntroductiontoPlato’sLaws,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3,p.63.
于是乎,苏格拉底关于美德与幸福之关系的主张通常被他的现代追随者们表述为:美德本身就能保证足够的幸福,从而产生深沉而持久的满足,尽管美德仍然允许由于拥有和使用非道德的善而带来的小而不可忽视的幸福之增强。(9)如Vlastos和Irwin,详情参见G. Vlastos,Socrates:IronistandMoralPhilosophe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T. Irwin,Socrates the Epicurean? IllinoisClassicalStudies,11(1 & 2),1986,pp.85-112.
首先,ST的第一个明确论断是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提出的,而《理想国》第一卷则承前启后,继续坚持这一命题,强调“正义的人是幸福的,不义的人是悲惨的”(354a)(7)对于这一命题的详细解读,参见T. Irwin,Socrates the Epicurean? IllinoisClassicalStudies 11(1 & 2),1986,p.85.。《高尔吉亚》同样声援《理想国》,提出“可敬善良的男女是幸福的,不义而邪恶的男女是悲惨的。”(Gorgias,470e)(8)参见507c,Crito48b,Charmides173d,174b-c.这些主张无不强烈地暗示了:即使某人正遭受着最严重的不幸,或处于许多人认为的对他的幸福有害的环境中,但除去这些表象,实际上对他的幸福来说,最重要的是美德。因此,苏格拉底即便以不公正的理由被告上法庭,但不向恶人低头,仍会声称“好人不会被坏人伤害”(Apology,30c6-d5)。甚至在被判处死刑之后,他还重申“好人,无论在生时或死后,都不会有邪恶降临于他,他的事迹不会被神明所忽视”(41c-d)。尽管在《申辩》中,苏格拉底承认,财富、健康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可能因一个人拥有美德而对此人有益,但他认为,原则上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一个人都是有可能幸福的。
其次,权力与完美的美德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紧密相连:是否有美德的生活只可能带来一些外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会增加一个人的幸福?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尤其是在外部因素方面,如荣誉或受到他人的公平对待。而哲学家们往往认为,不仅这些外部因素的严重损失对幸福有影响,而且它们对幸福严重有害。(28)对照Laws II 660d-e; Laws V 731a.亚里士多德对此颇有微词,指责“那些说饱受折磨的受害者……如果是好人,便是幸福的,不管他们的意思是不是认真的,都是在胡说八道”(NicomacheanEthics, VII 13 1153bl9-21)。(29)对这段话的经典点评,参见R. Kraut,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PhilosophicalReview 88,1979,p.171;另参见D. C. Russell,PlatoonPleasureandtheGoodLife,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5,p.164,footnote 76.很显然,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如果一个人遭遇了重大不幸,他的幸福便打了折扣。美德并不足以带来幸福,这是亚里士多德所深信不疑的。因为美德足以使人幸福,这一论点在他看来与直觉背道而驰。即使我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追求美德——这毕竟是美德的意义所在——我们也为了幸福而追求美德,而这幸福不仅包括美德,还包括其他类型的东西——身体上的和外在的善,运气或财富(30)有关亚里士多德对于“充分性论点”的态度,参见J. Annas,TheMoralityofHappines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373.。同样,一些追随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现代学者也常常这样评论:“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什么能保证正义的人不会受到别人的伤害,也不能保证他会得到良好的声誉。因此柏拉图既没有证明正义的生活必须幸福,也没有证明它必定是最快乐的。”(31)如Stalley,参见R. F. Stalley,AnIntroductiontoPlato’sLaws,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3,p.63;Sara Brill,PlatoontheLimitsofHumanLife,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3,p.172.可是,这样的评价合理吗?
事实上,即使是柏拉图本人也认识到,一个有德性(善良)的人,如果他没有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没有损害自己的名誉,那么他的快乐就会比一个受到这样伤害的人的快乐来得多——如果快乐是我们寻求不受冤屈的原因之一(II 663a)。然而,他也认为最正义的生活是最快乐的(II 662d),就好像最正义的生活本身就能给那个人带来最高程度的快乐似的。然而,正是在这点上,《法律》给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很少被人提及。例如,最重要的一则建议出现在《法律》第八卷中:
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首先,不作恶也不被别人冤枉,是必要的:在这些事当中,前者并不难做到,但非常难的是获得不受冤枉的能力(dunamis),而要完全拥有这种能力是不可能的,除非变得完全良善(teleos agathon)。(829a)
1.2.4 电泳检测。PCR扩增产物采用6%的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进行电泳检测。点样后,1 000 V电泳预热30 min,上样后稳压1 000 V电泳60~90 min。电泳完毕后,用10%冰醋酸溶液(1 L)固定30 min,用2%硝酸银溶液染色30 min,用预冷的3%无水碳酸钠溶液显色,ddH2O漂洗1~5 min,室温下自然晾干。拍照、观察带型、统计结果数据。
鉴于这个问题明显的不确定性,不管早期对话录中的情况如何,试问柏拉图在其后期作品中仍保持了对ST的承诺吗?作为柏拉图最后一本著作,《法律》包含着关于这一问题丰富而复杂的论述,且避免了以上提到的对ST最常见的哲学异议。然而,人们却常常忽视《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所做出的贡献。因此,本文拟通过《法律》重新展开讨论。尽管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法律》作为一篇独立的对话上,仍可以独立地评估《法律》对ST所持有的承诺的特定版本是否构成了对苏格拉底式立场的背离或延续,甚至是关于苏格拉底式的一个解决方案。因此,本文主要意在分析《法律》中涉及外在物、快乐、美德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的说法是怎样的。通过这种分析,我们试图提出这样一种走出困境的解决思路,即,将把对某些外在物的需求(甚至是对外在物的渴望),与快乐是幸福所必需的观点以及表面上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美德是幸福的充分条件”的观点协调起来。
答案出现在第五卷中:要避免遭受冤屈的折磨,需以多种方式展示美德。首先,一个人需要有勇敢和激情的本性,这样他就能孜孜不倦地同在“品性”上患有不治之症的邪恶者施展的不义行为作斗争。但此人也需要有“适度”“节制”之德,这样才能温和地说服那些在“品性”上有药可救、可治愈的人(731b-d)。如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会成为一个“伟大而完美的人”,会“以德取胜”(nikephoros aretei),而非以暴制暴(730d)。与此同理,最值得尊敬的人,不是那些仅拥有节制和智慧等美德的人,而是那些能够并确实可以将这些美德传授给他人的人(730e)。《法律》第四卷中的那位年轻的僭主或许是最佳的人选,他具备这些能改变别人进而追随自己的美德、力量(711a-712a)。以此方式看,“完美的美德”将是一种状态,它使得其拥有者知道如何成功地应对各种挑战,从而获得对人类所能获得的运气的最大控制权(cf.VIII 828d)(32)对照II 662dl,664b8;另参见R. F. Stalley,AnIntroductiontoPlato’sLaws,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3,p.63.。
四、完美美德、运气和自杀
首先,关于美德(尤其是完美的美德)的真正本性和诸美德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追求完美是人的天性(33)参见赵汀阳为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黄慧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一书所写的序言《完美是最好的吗?》。,在某种意义上,美德的统一性是以这种“完美美德”的最高境界为前提。因此,尽管从逻辑上看有些美德如勇敢和节制,如果仅仅被视为“通俗的美德”或自然倾向,那么不管教育如何,它们可能在没有彼此的情况下也存在(34)对照III 696b,XII 963e.,但《法律》明确表示:所有的美德都应该包含在“完整的美德”(complete virtue)的概念中。“通俗的”美德本身不足以使人幸福,而没有正义和节制的“勇敢”必然会使人陷入痛苦(II 661d-e),而且,通俗的节制若是从神性善中抽象地抽离出来之后,是不值得考虑的(IV 710a-b,cf. II 696d-e)。
与此相反,柏拉图在《法律》中提出绝对的勇气或“无条件限制的勇气”(haplos),必须通过训练来控制自己对快乐和痛苦的自控力,才可以变得几乎等同于节制(I 635d-e)。虽然不得不承认一个人在战斗中可能是勇敢的,也可能是非常不义的,但不得不否认这样一个人在战争中可能是值得信赖的、忠诚的、健康或健全的,除非他具有“美德的全部”(sumpases aretes)(630b)。但是,柏拉图又补充说,危险中的忠诚可以被称为完美的正义(dikaiosune telean)(630c-d)。同样地,正义需要智慧、节制和勇气的结合才能存在(63ld,cf. 696c)。这样看来,正义是所有美德(sumpasês aretês)的先决条件(630b2-3)。因此,优秀的立法者必须与现行政制的设计者不同,不仅要着眼于美德的局部,还要着眼于美德的全部(I 630-e,cf. IV 705d)。(35)有关美德之整体与幸福之关系的探讨,参见C.Bobonich,Plato’sUtopiaRecast:HisLaterEthicsand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09.
⑲Gerlind Werner,Ripa's “Iconologia”:Quellen,Methode,Ziele,Utrecht,1977.
采用Agilent公司GC7890-MS5975进行样品检测分析,以CP-Wax(50 m×0.25 mm i.d.×0.25 μm)毛细柱分离,GC进样口温度250℃,不分流模式,载气为高纯氦气,恒流模式,流速1 mL/min。柱温箱升温程序:起始温度45℃保持2 min,以5℃/min速率升温至210℃保持15 min。MS条件:EI电离源,离子源温度230℃,电子能量70 eV,扫描范围35~350 amu。
同样,节制是“有尊严的”节制,这种节制在教育的影响下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于被证明等同于智慧(IV 710a)。很明显,智慧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相反,它对应的是一个人对真理的理性能力的实现或努斯(nous)——这只有在成年生活中才能实现(II 672c)。然而,智慧并不仅仅在于“聪明”和论辩技巧,这些技巧可以在仍然有冲突的情感倾向的情况下获得(688-689d,691a)。实际上,智慧本身被赋予了激情和欲望(III 688b)。必须假设一个人对善与美的正确推理(orthois logo)与一个人对什么该被爱、什么该被恨的先行感受之间是完全和谐的(696c,689d-e)。因此,当这种和谐在成熟的个体中出现时,他就会立刻变得适当温和而明智。以这种方式,可以说“最好和最伟大的和谐可以最公正地被称为最伟大的智慧”(689d)。因此,当把目光投向节制、智思或友爱时,会发现目标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相同(hoautos),即便人们使用了不同的名字(693c)(36)这种“统一”或“同一性”意味着,这两个名字要么指的是同一种精神状态(即和谐的一种),要么就是,即使它们保持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它们至少也相互暗示。就美德的统一问题而言,对于这两种可能的解读方式的探讨,参见T. Penner,“The Unity of Virtue,”in PhilosophicalReview,1973,pp.35-68; Irwin, Plato’s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1.。
进而言之,通过教育,一个有幸分享智思(phronesis)和稳定真实推理(其里面装着所有的善)的人,他是完美的(teleos)(II 653a-b)。快乐和痛苦的感觉和理性(logos)之间的和谐(sumphonia)是“美德的全部”(sumpasa arete)(653a)(37)对照IV 721e ,VII 789d,817e;相关解释,参见Irwin,Plato’s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50-353;C. Bobonich,Reading the Laws,in C. Gill & M. M. McCabe(eds.),FormandArgumentinLatePla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49-282.。这表明,智慧——所包含的和谐——暗示着所有其他神圣的善,而拥有它们的人是完美的(38)有关智慧对于完善之德的作用的讨论,参见C. Bobonich,“Plato’s Theory of Goods in the Laws and the Philebus,”ProceedingsoftheBostonAreaColloquiuminAncientPhilosophy,vol.11,1995,pp.101-139.。同样地,如果一个人想要实现正义(V731a-c),那么他的这一理想既富有血性又温柔,这样他就配得上“完美男子汉”的称号(730d)。虽然《法律》本身并不包含对美德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充分处理(39)这种研究被提到是夜行理事会成员课程的一部分,参见XII 963a.,上面列举的文本确实强烈地表明了这一点:有一种“完美的美德”的状态,它以某种方式暗示着所有美德和它们相互的逻辑依赖的结合(40)更多关于美德的统一或不统一的讨论,参见Irwin,Plato’s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47-353; R. F. Stalley,AnIntroductiontoPlato’sLaws,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3,pp.56-58.。
其次,运气、完美的美德和自杀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柏拉图是否希望以及如何能够让所有其他外在物都由这种最高形式的美德产生(因为它们的加入能增进一个人的幸福)?他非常乐观地相信,完美的好人已获得或将会获得几乎所有能帮助他过最充实的生活的东西,包括身心平衡和外在的成功。(41)事实上,《蒂迈欧》似乎已经相信,某些做法(这些都是达到平衡所必需的,这样才能使一个人,既配得上“美”又配得上“好”)足以预防疾病(Timaeus87c-88c);对照Laws II 654e,VII 788c ,807d-e.在人与运气之间经常存在的因果关系上,柏拉图强调,一个人应该认为他自己(而不是别人)要为他最大的罪恶负责,而不是因为没有力量去面对辛苦和痛苦而伤害他的灵魂(V727b-d)。此外,他还强调,这是一种宇宙或神圣的正义法则:相类似的人或物应与相类似的人或物相伴,因此善传达了吸引更多善的内在奖赏,而恶人最坏的惩罚,是生活在自己的邪恶中,与恶人结交为伍(cf.V728b,X 904e)。
这并不是说,正义的人的一生绝不会遭遇厄运或失意。其实对柏拉图而言,让人一生免遭厄运的侵袭,不仅非人力所及,也非神力所及,因为“甚至连神明都无法与必然性作抗争”(V740e-741a)。然而,即便如此,柏拉图仍坚持认为,在厄运的考验面前,正义的人不该向命运低头,而应时刻心怀克服命运的希望与决心(V732c-d)。而且,正义的人如果达到了那种完美的美德状态,就一定会成功。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对某些与坏运气交织在一起的外在物的剥夺,看作是在安全的基础上确立“美德”(和幸福)所必需的“品性”测试(III 695a-b)。同样,柏拉图通过一个具体的事例强调了一个人抓住时机并运用技艺,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处理“运气”的重要性,技艺伴随着运气与机遇(709c)。这个例子是关于风暴中的领航员的,他试图从他没有造成的情况中获利,得到锻炼(Laws,IV709a)(42)“运气”与“幸福”的相关解读,参见R. Mayhew,“The theology of the Laws,”in Plato’sLaws:ACriticalGuide,edited by C. Boboni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98.。
徐州传统地方戏曲梆子戏在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梆子剧院有限公司(前身江苏省梆子剧团),现已实行企业化管理。梆子戏在徐州、河北地区目前仍继续上演,有一批固定观众。
然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人无法控制的情况可能会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有美德的人将从根本上丧失行使美德的能力(43)参见G. R. Carone,“Pleasure,Virtue,Externals,and Happiness in Plato’s Laws,”HistoryofPhilosophyQuarterly,vol.19,no.4,2002,p.338.。因此,根据晚期对话中提出的身心相互依存理论(44)参见Carone,Plato’sCosmologyandItsEthicalDimens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98.,即使一个运转良好的灵魂确实存在于一个运转良好的身体中,体内的过度痛苦也会阻碍最好的灵魂的活动,从而阻碍完美的美德。同斯多亚派一样,柏拉图也认为:美德不仅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所拥有的状态,而且是一种经过锻炼的性格。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行使美德的机会,那么生活就不值得过下去(45)自杀的探讨,参见J. Annas,TheMoralityofHappines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408.。还有一个问题是,名誉的严重丧失在原则上可能发生在一个有美德的人身上。尽管《法律》中的马格尼西亚城邦是柏拉图已获得的荣誉应该公正分配的地方,但仍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之外),一个头悬梁锥刺股地努力追求完美美德的人,无论他为实现“正义”经历多少磨难,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都会遭遇一种不能忍受、无法释怀的耻辱。在这一点上,最有趣的莫过于,《法律》并不认同“好死不如赖活”,而是允许人在极端情况(46)这种情况似乎与《斐多》61d-62e处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后者认为自杀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是神的财产。然而,一些人学者认为《斐多》篇的文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从而开辟了与《法律》保持一致的途径,参见J. Cooper,“Greek Philosophers on Euthanasia and Suicide,”in SuicideandEuthanasia,B. Brody(ed.),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1989,pp.14-19.下选择自杀,如“被极度痛苦和不可避免的不幸所迫,或陷入某种无法解决和无法生活的耻辱之中”(IX873c)(47)这与法律上禁止的懦弱或懒惰导致的自杀形成对比。因此,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根植于自然之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自杀在道德上是可谴责的(cf.Laws IV 713e-721e),参见G. R. Carone,“Pleasure,Virtue,Externals,and Happiness in Plato’s Laws,”HistoryofPhilosophyQuarterly,vol.19,no.4,2002,p.344,footnote 37。柏拉图关于自杀者的埋葬,参见Laws IX 875b-d。有些人(如Cooper)认为柏拉图在IX 873c处提到的耻辱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不是为让读者联想到俄狄浦斯的行为所带来的,参见Cooper,1989,p.19.但正如另一些人指出的,文本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这样的限制:这样的耻辱可能会单独降临到某人身上,就像降到普里阿摩斯(Priam)身上一样,参见G. R. Carone,“Pleasure,Virtue,Externals,and Happiness in Plato’s Laws,”HistoryofPhilosophyQuarterly,vol.19,no.4,2002,p.344,footnote 37.另对照Aristotle,N.E. I9,1100a4-8;柏拉图与斯多亚学派在自杀问题上有许多共识,参见J. Annas,TheMoralityofHappines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409.。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甚至没有希望”采取有德性的行动,那么自杀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与柏拉图强调的重要的是好的生活,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生活,是一致的(IV707d)。(48)对照《克里同》(Crito48b):“最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因此,幸福不仅是行为者被动地具有美德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他行使美德、使行为高尚的状态。可以把所有这些不同的策略看作是通过给人类提供其所能拥有的对运气的最大控制来强化“充分性论点”的证据。
五、结语
综上,《法律》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版本的“充分性论点”,该版本使这种论点与一系列直觉上似乎可信的、对ST构成明显威胁的要求相一致。首先,《法律》仍同《理想国》第一卷一样坚持美德足以使人幸福,且对于幸福是必要的。《法律》认为外在物(如健康和财政资源)的一些最小份额是美德的必要手段,而美德是内在愉悦的,包括带来愉悦生活的能力。其次,《法律》展示了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巧妙地将“完美的美德”的概念描述为一种以所有美德的结合为前提的状态,还包含以巧妙的方式处理运气的能力,化障碍或不幸为工具或机会;而“完美的美德”以某种方式包含了最大化正义状态的能力,从而为那些在美德道路上行走的人们呈现了一种伦理理想(49)对于《法律》中伦理理想的性质的阐释,参见G. R. Carone,“Pleasure,Virtue,Externals,and Happiness in Plato’s Laws,”HistoryofPhilosophyQuarterly,vol.19,no.4,2002,p.339.。再次,《法律》为有德性的人提供了自杀的可能,让他们有机会把自杀作为克服厄运的最后一根“拯救稻草”。在所有这些方面,可以明晰地看到,虽然某种程度的外在因素如“好运”对于美德是必要的,但仍可以把美德本身看作是一种控制运气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确保好生活的实现。
不难看出,在美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以现代人眼光看,柏拉图的作品无疑代表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认为人的整个一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受运气的影响”(50)参见B. Williams, MoralLuck:PhilosophicalPapers 1973—198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0;类似的说法,参见M. Nussbaum,TheFragilityofGoodness:LuckandethicsinGreektragedyandphilosophy(revised e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8.,因此倡导一种以“消除外在力量”(51)参见[美]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萌、陈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0页。为目标的生活。相比之下,古希腊悲剧作家强调价值的脆弱性和易损性的观点被很多人认为更具吸引力。(52)参见B. Williams,“Philosophy,”in TheLegacyofGreece:ANewAppraisal,ed. M. I. Finle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4,pp.202-255;[英]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5-18页。柏拉图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幸福在于美德。他反对悲剧作家所说的“人的生死、福祸等一切遭际皆由命运决定”(53)对照儒家所讲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与墨家的“非命”之说的张力,分别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0页;墨翟:《墨子译注》,辛志凤等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3-215页。。美德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能力,又是幸福最重要的构成元素,这是柏拉图所指给的新幸福观。就《法律》而言,柏拉图一方面展现了外在物(钱权名等)对美德之存在的前提需要,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运气在限制一个人获得完美美德(正义)的能力方面所起的作用(54)《法律》中对于运气的重视,参见R. Mayhew,“The theology of the Laws,”in Plato’sLaws:ACriticalGuide,edited by C. Boboni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99.。然而,即使是人力几乎不可挽回的“运气”的力量,也是柏拉图想要克服的,因此呼吁社会变革,创立理想之国。他想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是,如果为完美的美德而战,我们就会为更少的贫穷和疾病而战,为更少的不义和野蛮而战,为更少的无知和虐待而战,而这些恶正是阻止人类成为优秀人类的许多因素和障碍之一。
总而言之,柏拉图的呼吁中的确有一种微妙的张力:虽然我们人类中的佼佼者,或者那些能够为此革新而战的人,幸运地拥有这种变革所必需的最小外部条件,但我们应该为使这些条件被许多人所享有而战,这是他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大家共享好才是真的好,这样,我们改变世界、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就成了对我们自身美德的一种检验。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他伦理-政治理论的根本缺陷。本文也希望播下一些质疑求异的种子。然而,不要忽视《法律》的一个重要要求和提醒:要求我们打破传统思维,积极行动,而不是被动地对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听之任之;提醒我们,我们所向往的美德的最高境界是我们创造“好运”的境界,也就是说,好运必然来自于我们的美德,即所谓“越有德越幸运”。
IsVirtueSufficientforHappiness?——ANewStudyonPlato’sConceptionofHappinessinLaws
ZHANG Bobo
(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As a core concept of western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virtue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the supreme good and supreme“happiness”. However,Plato’s insistence on whether it is the main ingredient or the only element of happiness in his later dialogues is controversial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the study of happiness. Aristotle and modern researchers of ancient Greek tragedy generally do not agree with the argument of “the sufficiency of virtue”. They repeatedly criticize Plato for exaggerating its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emphasize the substantial influence of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luck on happines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partial negation Plato in his later years still adhere to the practice of “virtue is sufficient for happiness”,combining with the late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tries to start from the Laws which has less attention at present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Laws actually provides a rich and complex “sufficiency thesis”, and this argument does not contradict a series of intuitively credible demands and claims that pose a clear threat to themselves.Under this premise,an attempt will be made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hat reconciles the need for some external object with the idea that happiness is necessary for happiness,and th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idea that virtue i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happiness.
Keywords:Plato,theLaws, pleasure,virtue,externals,happiness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723(2019)02-0038-13
【作者简介】张波波,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田海平]
标签:美德论文; 柏拉图论文; 幸福论文; 外在论文; 的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古代哲学论文;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