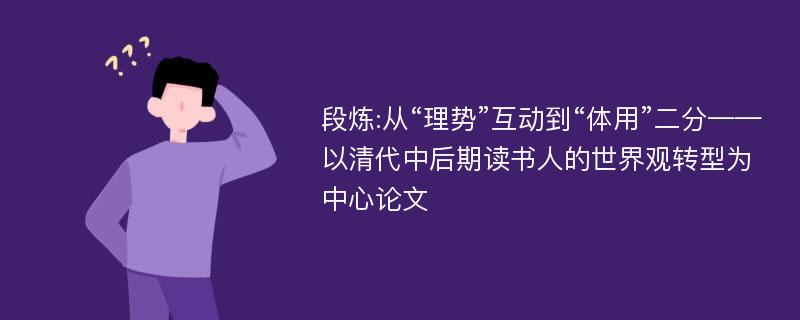
支配中国社会千余年的“天理”世界观在清代中后期的瓦解,与嘉道年间读书人在经学框架下重新思考“理势”的问题密切相关。无论是今文经学、理学抑或经世之学,都在试图重新回答何为“理”与“势”以及如何重新诠释“理势”关系的思想命题。同时,正是基于对“理势”关系及其诠释策略的内在调整,拓展了朝野各界因应时势的理论视野,也形塑了当日读书人世界观转型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清代中后期的多元思想“内变”,既是对传统“天理”世界观修正与扬弃、推陈而出新的过程,也由此埋下19世纪90年代以至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世俗转型的历史伏笔。
《意见》明确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坚持优先发展、压实责任,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坚持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坚持绩效导向、加强管理,将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管理与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成效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时势”与“变易”:“天理”世界观的内在转型
自宋代以来,在理学支配之下,儒家“天理”世界观逐渐成为支配中国政治思想与道德观念的正当性依据。有赖于“天理”概念的确立,儒家读书人通过“天理”世界观重建以人的伦理秩序为轴心的道德体系。同时,“天理”世界观强调现实世界对于天的政治责任、强调“天理”与政治、道德结合的倾向,不断向更深层次发展,构成支配未来数百年中国社会道德实践、文化认同和王朝政治正当性的核心依据。然而,进入18世纪以来,清代政治社会危机的持续爆发,带来读书人思想主张和学术旨趣的渐变。这使得自乾、嘉以来,作为读书人理解国家政治基本视野的“天理”世界观开始发生“内变”。在全球化的历史情势与数千年来培植政治观念的经学传统的共同催化之下,从18世纪儒家思想体系的内部,衍生出读书人对于王朝内外关系和政治制度变革的重新思索。
延续千年的“天理”世界观在清代中后期的历史转型,是儒家学术思想自身的内在张力与彼时社会动荡的外缘刺激交互作用的结果。正如清初儒者以切实的“道问学”的经学方式,表达对于晚明王学末流“空辨心性”的批判那样,18世纪的今文学者开始积极主动地从清代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内部,寻求一种更能合理地平衡“理”与“势”的制度尝试。而此时经学表达方式的改变,从思想本质上看,其实正是“天理”世界观不断“内变”在学术上的必然反应。因此,如何借助变动不居的视野,通过对于“理势”互动的敏锐理解,实现王朝政治合法性的新诠释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仅是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深层动力,也使得今文经学成为清代后期日趋广泛的政治变革的合奏当中一个嘹亮的声部。
“理势合一”:今文经学与“天理”世界观的“内变”
18世纪今文经学的勃兴,为读书人针对内外时势所进行的道德与政治评价,进而思考新的因应策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契机。一方面,今文学者所倡导的“通经”、“明经”的主张,其思想实质是力图从儒家经典的内部,依托制度变革,探寻“经世济民”的政治策略。因此,围绕“时势”与“变易”现实前提展开的今文经学,其背后的深层动力,是读书人世界观初步的“内变”。同时,依托于儒家经典的理论张力,今文经学依然深受传统“天理”世界观的支配。这使得经学、王朝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诠释三者的结合,体现出今文学者与清朝国家正统学说在思想上一致而非对立的立场。
从龚自珍内心弥漫的强烈的“衰世”意识,到魏源因应时势而戮力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努力,当日读书人已经敏锐感知自身所处的时代特征——“惟王变而霸道,德变而功利,此运会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而“时势”之变,最直接的后果是带来了读书人对于世界观的修正。龚、魏均认为,在“王道”取代“霸道”的“时势”压力下,单纯依靠传统“内圣”的道德修养,已经不足以实现经世济民的目的,尚需外在的事功(政策措施)和税收、盐政、边防、漕运与军制等专业知识作为补充。因此,对嘉、道以降的读书人而言,历史不仅是一个“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的道德衰替的过程,同时也包含时势发展的世俗化趋势——“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后,历史发展的价值诉求,不再局限于“王道”的道德空谈,而是强调通过对时势的认知与把握,不断提升并强化国家治理能力,进一步扩大读书人的政治参与,从而建立起“王道”与“霸道”之间新的平衡。
然而,“中体西用”之说意味着传统儒家的道德价值只能在“体”的层面发挥作用,而在“用”的层面上,则不得不采用西力所引入知识与技术的尺度。换言之,“体”与“用”之间的关联,在道德意义上的相关性已大为弱化。儒家德性的价值逐渐只在“体”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却必须从“用”的层面悄然引退。面对现实的时势,张之洞在着力守卫传统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却又同时在“天理”世界观之上打开了缺口。“体用二分”的思考方式,也开启了未来中国变革的契机。中西、体用、内外等范畴的界定,在时势的刺激下,随后亦成为20世纪读书人持续思索的世界观议题。
其次,曾国藩“以礼经世”的思想努力,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清代学者汉、宋之争的学术范畴,而是延伸到对于时势表达出深度关切的经世之学。曾国藩一方面肯定“理势合一”,强调“理势并审,体用兼备”。另一方面,曾国藩也认为“礼”不仅指涉礼仪与德性,更包含了制度与政法的内容。礼的意义不仅在于修身处世,也在于治国经世。“兼及内外”由此成为嘉道之际经世实践的核心理念。因此,曾国藩的救国方案分为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卫旧,通过恢复民族固有美德,以理学精神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以坚船利炮的实用技术来提升王朝实力。因此,在19世纪中叶读书人心目中,曾国藩既是重视“明道救世”的理学名臣,也是重视事功的经世大儒。
作为传统中国“天理”世界观支配下的重要哲学范畴,“势”指力量的强弱及总体趋势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战略上的发展趋势和演变形式中蕴含的力量与潜能。出于对“势”的意涵的丰富理解,读书人推衍出对学术风气、政治局势、社会发展趋势的进一步裁断与把握。可见,“势”具有造成社会变动外在力量的现实意涵,也与支配社会发展趋向和道德评价的“天理”,构成密切互动的思想关系。理解“势”及其内外条件的关系,洞悉“势变”的基本走向,进而以更具功利和权变的姿态提出因应策略,必然成为身处危机时代的晚清读书人的重要思想使命。
论及东洋哲学,便是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笔者刚论述圆了在日本“发现”中国哲学。那么,圆了何时自觉地认识到被称为印度哲学的佛教中有哲学?从现有的资料看,是在写向东本愿寺提交之呈报书的草稿之时(1884即明治17年秋,4年级)。其中一节对西洋哲学与佛教论作比较:
“以礼经世”:理、势互动的道德认知
身处于这一“天心”与“人事”愈加变动不居的时代,顺应时势的基本路径就从龚自珍、魏源时代的“重估功利”,提升为“兴功利”以自强。因此,“自强”成为这一时期士大夫的精神目标,而洋务实践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策略。与此同时,部分士大夫对“势”的讨论,亦已逐渐超越科学新知、技术以及商务的内容,开始涉及政治制度与民主思想的内容。郑观应强调,“达民欲”和“与民协商”正是《周礼》、《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古意,与西方议院思想沟通吻合。薛福成在《出使日记》里,就其在欧洲所见写道:“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王韬更进一步指出,英国富强的根本在于上下协调,特别是“通下情”的政府机构。他大力赞扬西方议会政治的作用,认为只有“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才能真正做到“有公而无私,民无不服也”。
对青岛市2017年1月--2017年12月参与街头无偿献血的104021人次献血者进行调查,其中58例献血者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献血不良反应,包括男性30例,女性28例。年龄:20--58岁,平均年龄(34.06±0.29)岁。上述所有献血者均符合献血标准,献血规规格分别为200ml、300ml和400ml。
“以礼代理”的思想在18世纪的兴起,并非简单学术门派上的分野,而是从理学内部对“理势”关系及其平衡策略的重新理解。它尝试改变在“天理”世界观支配之下读书人因应时势时所采用的心性论取向,拓展他们思考道德与政治问题的新空间。但“以礼代理”的思想趋势中,对于“礼”的意涵的高度重视与重新提炼,又使得儒学内部道德论的主张被重新激活,为清代中叶理学家“以礼经世”的道德转向提供了依据。19世纪中叶,湖南人曾国藩正是以宋儒义理之学成就经世大业的清代中兴名臣,也是这一时期“礼学经世”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这一“礼学经世”的尝试,在曾国藩的世界观认知当中,呈现出几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在“天理”世界观的支配之下,曾国藩尝试借助重整礼学,构建起汉、宋之间的学术关联,以此化解清代中叶以来两者之间的纷争。因此,清代学者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学术分歧,只有通过对于“礼”的重新研习,方能得以弥合。从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看,曾国藩调和汉宋的努力,是在儒家道德义理层面,对宋儒“格物穷理”的信念与清儒“实事求是”的精神的一次贯通理解。
在魏源的思想脉络中,从早期《老子本义》的“以道治器”,到中期的《诗古微》的“三统说”,再到晚期的天道循环论,其中内涵虽颇多反复曲折,然其脉络大致是强调“时势”的变换有其循环规律,“势”永远在“道”的轨迹中运转。当此之时,面对“世变日亟”的时代刺激,“理势合一”的论说表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即主张由制度的安排、政策的运用以及法令规范的约束,以达到儒家所谓的“治平”的理想。
从更长时段来看,曾国藩通过“以礼经世”为“理”与“势”之间的平衡寻求道德的依据,对于清代中后期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直至20世纪的诸多改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礼经世”意味着,经世与变革的思想与实践,并不以否定“天理”世界观作为导向。另一方面,“以礼经世”同样以一种道德实用主义的态度,为读书人反思如何平衡“理”与“势”的矛盾纠葛,提供了经学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范式,也为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新一代读书人,提供了突破经学藩篱的潜在动力与内在依据。
“环球大势”的刺激:寻求富强与“体用”二分
伴随19世纪中后期朝野各界寻求富强的整体努力,“势”的比重在“天理”世界观当中日渐凸显。它不仅成为士大夫研判内外时势的一般认知,也为“天理”世界观的深度转型提供了思想的内部动力。正是基于对“时势”巨大动力更为深切的认知,在清代中后期的部分士大夫眼中,世界是一个在时势推动下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而读书人自身也必须在“求变”中顺应时势——而非如同他们的祖辈那样,兢兢业业致力于“复兴三代”的道德使命。
清代中叶以来,时势刺激之下的世界观转型,并不局限于今文经学的理论框架与知识范畴,而是彼时读书人面对“尊德性”与“道问学”思想之争(汉宋之争)所寻求的另一共识。理学与今文经学,从不同层面促成传统儒家“天理”世界观的深度演变,共同形塑重视实际事务、因应时局演变的经世传统。从戴震、程瑶田到凌廷堪以降兴起的“以礼代理”新思潮,意味着“天理”世界观逐渐从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形式,积极转向“礼学治世”的实用形式。
到了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当中,尝试沿用自洋务运动以来即已喧腾众口的“体用”论述,对中学与西学的合理融通,作出更为系统的阐释。《劝学篇》着力阐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实际上暗示在读书人的一般认知当中,当时两类“体用”(道器)并存的现实业已存在。因此,张之洞将针对时势的因应策略,理解为限定在“器”的领域所进行的改革,竭力以西方的“器”来求变通,以中国之“道”来固国本。可见,在张之洞“体用”二分的思想背后,依然贯穿清初以来“天理”世界观“兼内外”的思想脉络,也不难找到19世纪中叶以来“道器贯通”的理念。
因此,这一时期的今文学者,通过强化儒家思想当中古已有之的“经世”观念,将“天理”世界观所包含的诸多制度原则(“理”),从传统的经、史所构建的道德范畴之中解放出来,组织成为因应“时势”的“自改革”方案,进而从经学范畴内部,开启了这一时期对于“天理”世界观“内变”的新阐释。龚自珍试图藉助公羊“三世说”,捕捉“古之世”、“今之世”与“后之世”之间如风一般“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的“时势”变化。龚自珍强调“规世运为法”,从“顺/逆”的角度来看待时势,将“顺”与“逆”视为互相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取代,从而引起“时势”变动的力量。“三世说”中所蕴含的线性演化因素,之后通过龚自珍以及好友魏源的论述得以强化,极大影响到后世读书人对于历史发展的看法。
例如,教师可以结合着社会生活的热点来创设相应的教学情境。如在湘教版数学七年级上册第3章《一元一次方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入一个飞机拦截的情境:中国在2013年划设了东海放空识别区,中国空军和海军经常会出海拦截外国的不明飞机。我们假设小李是一名飞行员,驾机执行拦截任务,他从地面匀速加速起飞,10秒后达到了350km/h的离地速度,随后到60秒时匀速加速到了1500km/h的巡航速度赶赴目标空域。根据这个情境,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们解相关的一元一次方程。这是一个新颖的话题,而且是两段情境,具有挑战性;初中生又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解题情境中表现积极:
2.1.3 诊断结直肠狭窄时超细鼻胃镜的通过率 对25例结直肠狭窄性病变的诊断性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在结直肠癌中57.14%镜身可通过狭窄处,在15例术后吻合口瘢痕性狭窄中,鼻胃镜可全部通过,1例术后复发患者镜身可通过,1例外压性肠狭窄中镜身可通过。超细鼻胃镜的总通过率为88.00%(表4)。
余论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面对一连串内外危机的刺激,清代中后期读书人的世界观发生了从“理势”互动到“体用”二分的思想“内变”。首先,在庄存与、刘逢禄的时代,今文学者开始以“变易”作为理论预设,借助“时势”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以及对清代中叶以来“六经皆史”、“道器一体”等学术议题的重新理解。在继之而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论述当中,他们依托今文经学对于“理势合一”这一思想关系的强调,将“天理”世界观所包含的诸多制度原则(“理”),从传统的经、史所构建的道德范畴之中解放出来,组织成为因应“时势”的“自改革”方案,进而开启了这一时期“天理”世界观的“内变”。另一方面,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思想之争(汉宋之争)的合力作用之下,理学与今文经学均从思想的不同层面,促成传统儒家“天理”世界观的深度演变,并且共同形成重视实际事务、因应时局演变的经世传统。
其次,在传统经学的思想范畴中,“理之是非”的刚性价值原则,开始在“势之利害”的现实主义和世俗逻辑面前节节败退。这一世界观的嬗变,折射出自18世纪末期以来,晚清社会所面临的儒家道德超越价值不断衰退的“世俗化”进程。读书人以更具权变和实用性的思路,消解传统儒家德性与现实制度之间的价值关联。同时,清代中后期的读书人清楚地意识到,朝野各界如果无法在儒学内部,有效地发展出因应这一“世俗转型”思想策略,进而从国家政权的内、外视角重塑晚清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形态与王朝合法性的根基,在西力日渐强劲的冲击之下,儒学自身将无法摆脱最终衰亡的命运。
最后,读书人的世界观所发生的从“理势”互动到“体用”二分的转型,以一种从儒家思想边缘深入到中心的节奏,部分地协助朝野双方回应日渐急迫的内外时势。随着“天下”观念的瓦解,中国最终亦无法自外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经学最终也无法为晚清的朝野各界,提供一个解释世界和内外关系的整全性知识体系。因此,晚清中国面临的“天朝的崩溃”,其实质正是支配中国千余年的“天理”世界观的崩溃。在这一大的思想背景之下,“体用二分”为转型时代的中国描绘出因应时局的“未完成的方案”,也由此开启了晚清读书人探寻新世界观的复杂面向。
五是要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各级党委都是上级党委决策的执行者,狠抓落实的能力是由决策意志向实践结果转化的根本。在部署与落实的关系中,习主席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落实能力就是执行力,提高执行力重在3个要点:其一,速度,以明确的时间表,按照时间节点走,绝对不能拖。其二,力度,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和态度推进工作,下大力完成既定任务。其三,信度,改革创新而不离经叛道,使最终结果与先定目标相一致。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所研究员;摘自《史林》2018年第5期)
标签:世界观论文; 时势论文; 天理论文; 读书人论文; 经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清代哲学(1644~1840年)论文; 《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2期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 中国思想史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