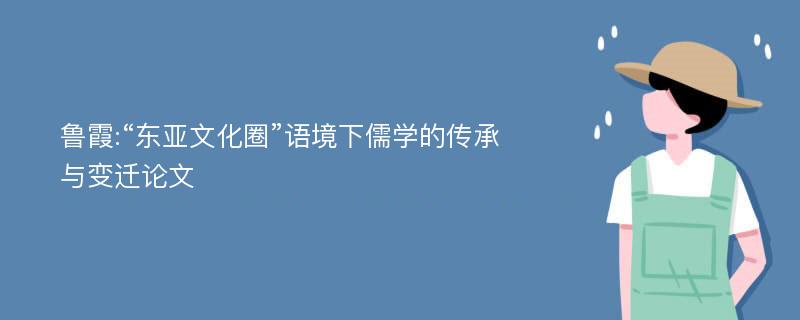
摘 要:本文以“东亚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等概念,作为分析的范畴依托,沿循“一带一路”之背景,尝试在历史与现实的双层轨迹中进行对应性考察。思考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儒学在当下网络化、大数据环境中如何传承?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元素,在当下“一带一路”轨迹上如何展示其特有之能量?
关键词:“东亚文化圈”; “一带一路”; 儒学
东亚区域内所共有、共持的学问或文化,谓之“东亚文化圈”。东亚,寓意着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文化圈,涵盖着学问或文化的共性、个性与关联性。事实上,当“东亚文化圈”的概念与儒学并入到一个命题中予以展开论述之时,这个命题似被摄入内在矛盾的状态之中。因为,“儒学”,作为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思想,不仅在思想领域素养了士、农、工、商、兵各阶层;而且,在政治层面驾驭了中国的封建王朝。作为超越中国界疆、更宏阔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这样大空间的“东亚”,以儒学为中心涵义,“文化圈”作为限定框架,似有矛盾的感觉。然而,儒学,并非只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单纯意义上的延续。儒学,在有限的“东亚、文化、圈”等范畴的认知中,蕴育着“网络、信息、国际化”等一系列无尽的想象。
一 、“东亚文化圈”:地域历史与思想文化交织中的儒学再定位
如果按照概念来界定“东亚文化圈”,一般是指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亦即汉文化影响的东亚(包括部分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普通惯例所给出的“东亚文化圈”基本要素包括:汉字、汉式律令制度、农工技艺、中国化佛教。上述要素给东亚诸国及其诸地区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乃至于社会风俗等方面带来很大的影响。
⑰王绍媛、刘政:《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竞争中立规则审视》,《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东亚文化圈,作为学术问题的研究首先当推日本学者西岛定生。1983年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西岛提出了“文化圈”四大共同文化要素: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成为学术界研究领域的普遍共识。“东亚文化圈”在学术界的正式呈现,一般以2000年韩国学者李成市《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一书的问世,此书(由日本山川出版社出版)明确使用了“东亚文化圈”的概念①西岛定生:(1919-1988)东京大学文学部、新泻大学等任职。主攻中国古代史,着眼于从东亚的视角来看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等相关研究。。随后,“东亚文化圈”研究不仅用于学术研究领域,甚至用于经济、政治等多重领域。西岛定生、李成市两位学者对东亚文化圈的研究思路又进一步带动了历史学界“东亚世界论”理论的研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兴起的所谓东亚研究认识论、以及将日本史置于东亚区域史研究的范式推而广之,形成将东亚史置于世界全球范围内的研究方式。此外、2005年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推出了高明士所著《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这部论文集,将诸学者对东亚、儒家思想研究的片块领域成果做一汇集,展示了“东亚文化圈”、儒学范畴相互关联作用之新视点的统合性考证。《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中最具时代性观点的是杜维明所提出的以下内容:传统作为界定现代化过程所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是持续存在的;地区知识具有全球性意义;文化传统继续在现代化过程中有着强有力的作用[1]。这样一种以地域、文化、全球大格局的思维路经,不仅开拓了学术界研究的视野,更进一步助推了“东亚文化圈”与儒学研究的深度性与全方位化。那么,上述“东亚文化圈”范畴中“东亚”所涵盖的空间何所指?
中国学者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提出,第一“东亚”在自然世界中,空间主要只是物理空间(space),比如地形、植被、矿产、气象等等;第二在政治世界中,空间主要只是一个和领属关系相关的地域(domain),比如国界、省界、政治中心;第三在人类社会中,有很多人所生活和需要的空间布局,比如城市、集镇、交通路线等等[2]。那么,这种地域范畴的“东亚”在“东亚文化圈”学术研究中是否应当包含东亚圈内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呢?历史上,古代“东亚文化圈”是以中国历代王朝为中心的,是中国王朝与周边邻国关系的构建。正如学术界研究所示,除了个别朝代或某一个时期外,总体上彼此之间是睦邻的,中国对邻国主要是通过文化进行交流的,在彼此的交流过程中,形成了区域文化圈。文化圈内各国,除了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之外,还存在受到中国先进封建文化影响的共有文化要素②王金林《东亚文化圈的历史回顾与展望》2011年 7页。。因此,东亚的地域,地域中的不同国别史、区域史,历史上的文化发展与互动,是“东亚文化圈”范畴中更重要的元素,是“东亚文化圈”研究的一个多方位、多渠道平台。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又可以呈现学术研究中所呈现的百家争鸣之观点。诸如东亚文化圈的核心文化基本上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进入近代、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后,它的部分价值渐渐与今天的社会乖离,其部分的衰败和被淘汰是时代变化的结果,等等后续诸多商榷的观点与论述,让“东亚文化圈”相关研究更趋丰富化、国际化。
依据研究,福泽谕吉开始使用“脱亚”一词是在1885年,而且仅仅出现了一回发表在日本《时事新报》的社论上。背景源于1884年12月李氏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及其政变的短命崩溃冲击下日本方面对东亚时局观察而执笔的,阐述这个政变中表演主角的金玉均、朴永孝等李氏朝鲜内部的“开化派”(又名独立派)的立场。当甲申政变仅维持“三日天下”就遭受失败时,福泽是极其失望的。“脱亚论”“可以说是福泽在这种挫折感和愤怒中迸发出来的”[4]8。但“脱亚论”发表后,并没有过多影响到日本的政治、思想领域。追寻当时东亚历史发展的轨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国土上开战,两场战争带给日本与“东亚文化圈”诸国极大的震惊。换而言之,两次战争的结果表明日本已不再是古代历史上东亚区域中的日本,俨然是当下世界列强中新的一员。“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强国,企图通过侵略中国、掠夺领土和资源来谋求亚洲盟主的地位。这两场战争,使日本不仅得到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占领了中国台湾和辽东半岛广大的土地,而且还获取了清政府大量的赔款。这彻底打垮了自古以来日本眼中的中国大帝国形象,也削弱了日本对俄罗斯帝国持有的恐惧心理,更使日本国民在精神上得到了巨大鼓舞。”[6]可见,在“东亚文化圈”区域空间中的日本与“东亚文化圈”诸国思想文化的认知相去甚远。
应该看到,儒学成为东亚国家中共持的文化,受到中国以及东亚许多国家、地区学者们的关注,在多经纬视点的关注与研究中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这种研究跨越了本地区的儒学与发展态势,趋于多方位、多视点的自我与他者多向性研究。《古代东亚政治环境中天皇与日本国的产生》便是将日本置入东亚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考察的成果之一。书中提到“古代东亚地区诸国之成立与发展,因共处在同一文明圈内,均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同在儒教为正本之影响之下,日本国家之成立与发展又是其中之异数。观今日本,进食用箸,起居坐卧多在蓆上,习惯跪坐与盘腿坐,仍存汉代遗风。日常用文,以汉字表义;接人待物,点头弯腰,如得周礼之教。”[2]日本,作为东亚文化圈内的国家,对于儒学的吸收与应用相当可观。当然,对儒学的研究也有相当的积淀。“以儒教观念为媒介来把握近代国际关系的方法,并没有产生于儒教的祖国中国,反而先出现在日本。这个问题关系到日本与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整个差异。”[4]144从丸山真男的话语中我们可以逆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使用“儒教文化圈”这一概念研究东亚之时,是否意识日本、中国和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相异的语言特点、历史特色与社会特质呢?中国、日本、韩国历史轨迹中呈现了各自民族、国家形成以及演绎的不同特征。近代历史时期,在同样面对西方重压的局势中,三个国家的民众以及统治者所采取的回应策略都呈现出差异,如此,我们在东亚文化圈语境下对“儒教文化圈”内与外的研究怎样把握这些差异?怎样把握这些差异的内在性呢?“日本的学界已注目于中国与日本的儒教的相异问题,其研究成果证明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确实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在读到丸山先生对福泽的儒教批判的解释时,没有必要将之直接看成对中国儒教的解释。尽管日本自古深受中国儒教文化的影响,但把日本文化作为一个异质文化来理解,会有利于我们中国人正确把握日本。”[4]14因此,即便是在东亚同一文化圈内的儒学研究,倘若我们不站在他者的、客观的立场上去辩证地把握被称之为“圈”中的文化特质,是很难为儒学研究的空间增添光彩新色的。正如丸山真男向中国读者“我所希望的是,中国读者不要受日本对福泽的先入之见或流行观念束缚,应亲自根据福泽的论著去理解福泽为自由和独立所作的思想苦战。如果我的研究能对作出上述努力的读者提供某些启发,我将感到非常荣幸。我还希望有这样的读者,他们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日本思想家福泽做‘意译’并按照中国的历史状况去‘改读’之。假如这些读者能进而站在自主理解和学习的基础上对我的福泽研究提出疑义和批判,那么不管其意见是多么严厉,我都将衷心欢迎。”[14]10
二、“儒教文化圈”: 儒学在东亚文化圈内与圈外的国际化互动
式(6)中S为卷积网络经过卷积层,池化层,非线性层的输出,是特征提取过程,X为输入图像,W为模型参数,式(7)表示输入为xi时,输出为类别k的概率值,sk为S向量的第k个值,式(8)为softmax损失函数yi为xi对应的正确标签值,训练的目的为最大化输入为xi输出为yi的条件概率,即为最小化负的正确类别的对数概率。考虑批量样本时对应的损失函数为式(9)。
①使用MATLAB中自带的神经网络工具箱进行操作,首先建立BP神经网络模型,隐含层采用单层神经元,隐含层神经元的激活函数采用S型正切函数(Tansig),输出层神经元的激活函数采用线性函数(Purelin),训练方法采用收敛速度较快的Levenberg-Marquadt带反弹算法(Trainlm函数);之后导入标定得到的四次单维数据,设定电压信号为输入,理想的力值/力矩值为目标输出。模型建立好之后,通过调整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进行训练,随着神经元个数的增加,训练速度逐渐变慢,训练精度逐渐提高。
读书方法不对头,读得再多也是消化不良,无以致用。书或许是好书,可惜读书的人只带了眼睛没带上大脑(或者大脑容量不足),再好的书也是耳边风一般,什么痕迹也没留下。这种情况在所谓的“读书人”当中并不鲜见。比如,当年高考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候,不乏这样的学生:每天起早摸黑苦读狠读教科书,拿起书本可以倒背如流,答起试卷却无从下手或离题万里。众多的事实表明,读书是讲究方法的,没有好的方法,书籍中的营养不会自动跑进你的大脑。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读书,需要的是“善读”。陶行知也说过:“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而没有方法的“死读书,读死书”,只会把人读成毫无实际能力的书呆子。
事实上,以他者为坐标超越文化圈的界限思维,客观研究历史文化的方法在学术界并不少见。葛兆光在研究宗教思想史中,就建议这样一个方法——以佛教为背景考察亚洲几个国家时可以互为背景、互为资源。为此还撰写《互为背景与资源—以近代中日韩佛教史为例》[5]170,并在另一部《宅兹中国》中做了更为直观的历史论述。“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直言”,进而提出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作为反思,他“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似乎无可非议”作为考察前提。作为反论,他从亚洲主义的研究视角,质疑“日本、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什么时候成为过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5]170作为问题意识“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空间?”[5]171所以“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5]170的方法。无论是“东亚文化圈”还是“儒教文化圈”的研究,都不是单向性的圈内思维,需要圈内与圈外的双向性考量,更需要国际化的视野。
在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占据怎样的份量并非本论文所关注的重点;福泽谕吉为何要提出“脱亚入欧”也不是所要探索的内容。然而,“脱亚入欧”究竟与日本儒学甚或是“东亚文化圈”的儒学传承与变迁存在怎样的关联?脱亚入欧的日本是否不再需要儒学文化的支撑?
“儒教文化圈”特指接受儒家文化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一种民族精神主导着这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圈”一词的产生源于近代文化学和文化史学领域,以全球视角关注各种文化的个别性与联系性来强化概念③最先提出此概念的是德国学者格雷布内尔(F﹒Craebner 1877-1934)奥地利学者施密特(W﹒Schmid1868-1954)。。“文化圈”可以从地理、民族、语文、宗教、民俗等多种角度来划分。“儒教文化圈”在学术界使用于东亚乃至于亚洲的政治、经济等研究领域并进而推及全球的状态,是韦伯与汤因比这两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在两位学者学术研究中凸显出对“儒教文化圈”的关注度。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宗教——儒家与道家》等论著中,一则肯定基督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精神动力,二则认为儒家过分的“理性化精神”不能激发起自由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并依次为据推论从儒家文化中找不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态势;与此相对应,汤因比则从一个全然对立的立场阐明儒学不仅拥有内在美德与和谐精神,而且,西欧在人类史的下一个阶段将会把主导权转交给东亚。上述这二位学者研究的理路沿于基督教区域与儒教区域范畴中的视点。
二十世纪以后,“儒教文化圈”的范畴日益显现于人文社会学甚至于跨学科领域,并占据相当活跃的话语权。这一现象缘起于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起飞,以及如何面对当时欧洲现状的社会背景。日本政府在平成元年度起从1987年至1989年连续三年间以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补助金的形式,将“東アジアの経済的·社会的発展と近代化に関する比較研究”设为重点课题之研究项目。于是,以日本学术界为中心,兴起了围绕近代化的主题,对儒教文化所涉及的各个国家与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北朝鲜、越南、香港、台湾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问题开始了相当高调的研究。该项研究汇集了中、日、韩等国家与地区的诸多资深学者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且以系列的形式推出。首先,围绕“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経済発展と儒教の影響”这一主题召开了国际性学术会议;其次,将会议中的学术报告汇总为论文,并增添各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出专辑著作。因此,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④中嶋嶺雄(日)《アジア比較研究》日本学術振興会出版 平成4年1月3日。。纵观研究成果可归纳如下:普遍性的共识是,日本、南朝鲜、新加坡等国的经济腾飞缘于拥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源头正是中国的儒家传统伦理。上述观点以日本学者加地申行(儒教とは何かー「儒教文化圏」の歴史と社会)、韩国学者金日坤「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経済発展と儒教の影響」的研究为代表。随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翻译出版了金日坤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一书。由此,带动了这一时期“儒教文化圈”课题研究的走向,从儒教文化圈”的概念、儒家思想的范畴出发,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地区“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现象,进而,再追溯上述国家地区的文化态势,以此背景进行的分析。这些研究并非限定在检讨儒教文化之概念,而是以重新认识东方文化的思路再深入西方社会的路径,同时又回归到儒学与近代化进程的命题上进行探讨。
三、 “脱亚入欧”: 儒学在“西力东渐”中的对峙困境
在谈及“东亚文化圈”问题研究时,一个重要的话题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所谓的“脱亚入欧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及其随之对儒学的批判被认为是影响近代日本对外思想的主流意识,是影响日本近代思想界乃至于东亚诸多国家问题的一个重要点。同理,在“东亚文化圈”语境下的儒学探讨更是无法回避。如何在“东亚文化圈”的语境中思考日本近代历史上的“脱亚入欧”?
所以,在“东亚文化圈”这个多方位、多渠道的平台上,儒学是重中之重的支点,儒学架构了东亚文化圈的骨干框架。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如何解读儒学?如何解读儒学在东亚文化圈中的运行轨迹?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课题,也是东亚文化圈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课题。
19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以“西力东渐”的方式渗入到亚洲并单纯延长。“19世纪以后逼迫东亚开国的西方压力,是饱经了西方史上也未曾有过的产业革命实践或正在经历这个实践的列强的压力。这种压力具有不能单纯用狭义的军事侵略来解释的性质,它包含着渗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全部领域的巨大力量。面对这种力量的涌来,日本、中国、朝鲜等东亚三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4]3特别是1840年中国以鸦片战争被迫开国;1853年日本以佩里来航被迫开国。随即朝鲜等东亚各个国家相继陷入民族危机。国家何以存而不亡?民族何以强而不辱?问题摆在了统治阶级、广大民众甚或是知识分子面前。“东亚文化圈”诸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了各自近代社会转型的前沿,他们带着各自思维意识的内在矛盾,面对各自社会所要解决的课题本身内在的自我矛盾去思考。“这种情况不仅限于日本,而且中国、朝鲜或者越南等儒教影响的国家地区。现在,亨廷,汤因比要解决的世界文化圈的课题内部也包含这自我矛盾。”[4]19面对上述的历史状况,丸山真男在谈及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和儒学批判时,希望中国的研究者注意福泽的两个态度:第一,在思想上从来是把政府(政权)和国家清楚地区别开来看待的。把政府的存亡与人民或国民的存亡严格地作为不同的问题来思考,这个原则始终贯穿于他的思想中;第二,在理解福泽对“儒教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和反对态度时,也必须考虑上述的这个区别。即他的攻击目标,与其说是针对儒家的教义本身,不如说是针对被歪曲为体制意识形态的“儒教主义”这个病根,其在国内表现为父子君臣等上下关系的绝对化,对外方面表现为区分“华夷内外”的等级性国际秩序观。正是政治权利与儒教在结构上的这种结合,使中国的体制的停滞和腐败不断地重复出现。福泽是深刻地认准了这一点的。他所说的“脱亚”,实际上是指“脱满清政府”和“脱儒教主义”。如此从思想意义的角度来对福泽的所谓“脱亚”作上述的解释,也许更符合事实吧。上述意义的“脱亚论”,在针对德川政府的场合也不例外。福泽明确说:“我日本的德川政府亦为之(丸山注:为了19世纪80年代的文明)而倒台。难道唯有满清政府能抗拒哉?不导入文明,必受外国的欺凌而亡国。若导入文明,则人民得权而政府之旧物颠覆[4]9。上述,丸山真男对中国学者的呼吁,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丸山真男对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局势性说明。从这种说明中,可以扑捉到“脱亚”并非“脱儒”的意识。
作为“东亚文化圈”外的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特在《日本文明—一个比较的视角》中的分析可以作为参考。他说“不过,也许是日本不断与中国的接触、与儒教和佛教接触、后来又与西方接触,以及不断需要在既不否定外来价值又承认其优势的情况下将其本身与中国和西方区别开来,这就导致了将日本区别于其他大多数非轴心文明的激烈、复杂和成熟的思想话语模式之发展。这种高度发达的话语,自相矛盾地构成了一个有意识、高度反省地否定基于轴心文明之前提的思想类型,但同时,又以衍生自这些思想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7]日本历史上的儒学学习、儒学批判、儒学再实用化的轨迹。
历史研究要求在“充满内在矛盾的历史状况中”去解读、去分析历史轨迹上的点滴,这也是我们当下研究历史问题与现实所需要的一种基本姿态。“对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而言,把现成的陈述融入他自己的历史知识体系,是一种不可能的行为。面对一个他正在研究的主题的现成的陈述,科学的历史学家永远不会问自己:‘这个陈述是对的还是错的?’也就是‘我要不要把它融入我的关于那个主题的历史呢?’他问自己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陈述的意思是什么?’这和‘做出这个陈述的人做出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同的,尽管它无疑是历史学家必须问、而且必须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⑤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年 213页。循着科林伍德的观点,考察“东亚文化圈”、“儒教文化圈”、“脱亚入欧”、“儒学”这一系列元素对东亚诸国的影响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在这些影响的轨迹中客观定位儒学的价值势必对中国乃至于东亚各国的未来发展都将会是意义非凡。
四、一带一路:儒学在大数据与网络化中的再定位
“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重要方针政策,也是被世界各国所注目的全球化导向。在这样一个国内国际背景下的“一带一路”会带给儒学一种怎样的运行空间?亦或,儒学会以怎样的态势运行到“一带一路”的空间?所谓“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涵盖。这种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展示了宏贯历史、当下与未来偌大空间。在这偌大的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空间中,需要和谐、包容、文明、宽容、尊重、互信、共荣、共生等等元素。“一带一路”需要全球各国的参与才能发展,据统计,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中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这个统计数字目前还在增长中。那么,如何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如何才能达到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儒学,将会是最重要的支撑力点之一。儒学不仅是“东亚文化圈”的思想文化的共同文化元素与符号,也会是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方相互认识与共同完善的文化桥梁。
长期以来由于受政策限制,广西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体系的建设起步较晚、规模尚小、机构数量很少。近几年,该类机构主要以大型健康养老项目为依托进行建设和发展,目前正在规划和建设的大型养老项目有:广西太和—自在城、中国(崇左)乐养城、桂林国际智慧健康产业园、中脉巴马国际长寿养生都会、梧州市岭南生态养生城、贺州市生态健康产业示范区、北部湾国际滨海养生健康服务基地。其中前3项已正式运营。目前广西投入运营的大型高端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数量还相当少,其在地方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
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物质文明的发达与精神文明的升华,这亦人皆尽知。同样,物品流动也会带来文化的交流,“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正式这种物品流动促进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当今“东亚文化圈”的儒学之关键在于共同面对的现实与未来:所谓大数据与网络信息化时代东亚各国如何以各自独立的身份实行多元交流;儒学如何以其发展连续性和思想类似性续写“一带一路”进程中的文化、精神财富。谋求国家繁荣,拓宽地域交流与合作,当今已经逐渐成为全球中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网络数据语言缩聚了这种交流与合作空间的经纬距离度,同时也抽象化了这种交流与合作的精神色彩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儒学,承继和、礼、仁、德、义于数据网络化空间的模式与途径成为我们当下与未来的希望前景。
参考文献:
[1]高明士.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M].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
[2]葛兆光.宅兹中国[M].中华书局, 2011:104.
[3]吕玉新 .古代东亚政治环境中天皇与日本国的产生[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4]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M].区建英,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144.
[5]葛兆光.宅兹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11:170.
[6]何为民.脱亚论解读过程中的误区[J].日本学刊,2009(4),137.
[7]S.N.艾森斯塔特.日本文明—一个比较的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58.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
LU Xia
(College of History,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lks about East Asian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it aims to conduct a corresponding investiga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trajectory, discussing how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Confucianism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and big data era, and how to make Confucianism,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lemen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lay its specific role in “The Belt and Road” process.
Key words: 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 the Belt and Road; 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9)04-0040-06
收稿日期:2019-03-06
作者简介:鲁霞(1960-),女,大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标签:东亚论文; 文化圈论文; 儒教论文; 日本论文; 儒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大连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大连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