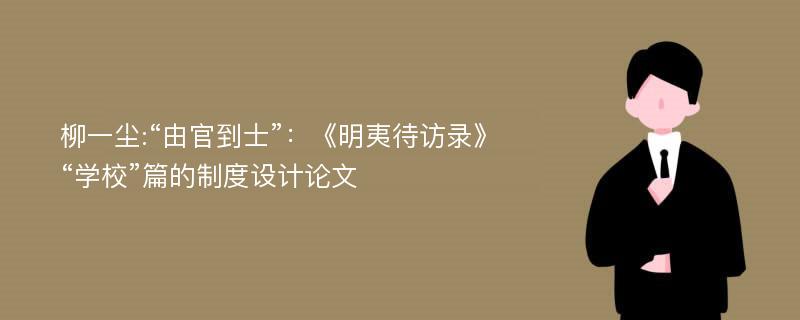
摘 要: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是一种以“皇帝——官僚”为总体形态的政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士”只有为“官”,才能获准进入和参与政治。而身在对于“道”的责任和作为“官”的现实处境,也就是“道”与“势”的张力之中,“士”不由地陷入了困境。黄宗羲欲以“学校”——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设计,调整帝国政治结构,从而为“士”群体开辟独立的参政空间,以保证“士”作为政治主体的责任履行。这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儒家式方案,具有独特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同时也不乏理想主义色彩。
关键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士”的困境;“学校”;制度设计
一、导 言
黄宗羲亲历了明清之际的风云变幻,目睹了明王朝的衰亡,此时“故国的恢复已然无望,然而兴亡之理的探究、故国文明的保存、未来理想的设计,这些天崩地解之大时代的叩问,都需要亲历其中的人们去痛定思痛,做一番深沉而痛彻的思考”。[1]20黄宗羲恰是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怀着深刻的家国兴亡之痛,反省和探究明王朝灭亡的根源,写下了他最重要的,也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在《明夷待访录》的题辞中,他说:“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2]1寥寥几语,我们体会到了梨洲先生在是时处境下的复杂思绪,感受到他积极主动谋求发展变化的坚定信念。这些都决定了《明夷待访录》不只包含对于过去的反思,更加聚焦朝向未来的设计。
二、“士”与儒家的理想
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封建秩序被彻底地打破了。与之相应,“士”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贵族,而是伴随着阶级的流动变成了“民”的一部分。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士”灌注了精神价值,遂又使得“士”的内涵完成了从“有位者”向“有德者”的转变,带有儒家特质的“士君子”便产生了。而“士君子”与儒家的理想,也就是“道”之间的关系,注定了他们将会面临一个“仕”的问题,同时必然要做出“仕”的选择。
(一)“士”的产生
在周代所行的封建制度下,“士”有着贵族身份,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孟子“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3]321的论述中了解得很清楚。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不论是“田氏代齐”还是韩、赵、魏三家分晋,都意味着以血系亲疏为权力传承准则的宗法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具体表现在诸侯国中有实力、有威望的卿大夫可以随时挑战国君的权威。显然,力量的强弱对比已经事实地取代了等级的高下规定,成为了那个纷乱时代新的游戏规则。而原来的封建贵族没能适应这一新规则,于是便随着旧的封建秩序一起消失崩溃了。
合规概念的使用始于会计金融领域。目前,合规风险指“不符合法律规定”所导致的风险,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由于内部控制和治理机制不完善,企业活动未能与法律、法规、制度、政策、行业规则等有关规范保持一致,而可能面临主管或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
我们注意到,在历史的潮流中,“士”不得不接受失去贵族身份的命运,所谓“士之失位”[3]270是也;“士”还不得不面对失去固定职业的状况。与此同时,庶民以学问、战功等条件进而为“士”的情况也值得关注。于是,在封建贵族下降和庶民有机会上升的共同作用之下,在不断的阶级流动的过程当中,“到了春秋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4]12。从此,“士”被包涵在了“民”的范畴当中,以“士民”群体为主体的全新的“士”应运而生。
(二)“士”与“仕”——儒家“士”的特质
如果说“士”的产生——由封建贵族到“士民”是社会情况变化使然,那么儒家“士”的诞生则必须归功于孔子。余英时先生指出:“由于孔子恰处在士阶层兴起的历史关头,他对这一阶层的性格形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4]25具体地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怀着积极救世的理想[5]53,“为礼注入一种道德的精神,又把礼的规范总结为一些道义的原则”[6]31。而以上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无疑是让儒“士”的内涵实现了自“有位者”向“有德者”的扩展,儒“士”从此成为了“士君子”。
补课的角度,从问题入手。就“问题”概念而言,问题就是目标与现实的差距。差距越大,问题越大;差距越小,问题越小;差距为零,就没有问题了。每年找准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一系列破解问题的措施和行动,将目标与现实的差距降低到零了,效果就产生了。具体到忻州的情况,其主要问题是“硬件不硬,软件不软” 。“硬件不硬”是短板,“软件不软”是长项。扬长避短,精准发力,这是补课的功夫所在。
那么,实际地处在与现实君主权力的复杂关系中,“士大夫”对于自身的定位又是什么呢?可以说,“士大夫”既有着服务于君主、维护庞大帝国运转的一面,同时也不乏以“道”自贵,即凭借“道”的权威与统治者相抗衡的一面,两重面向是并存的。具体地看,一方面,“士大夫”对于帝国的行政事务负具体责任,处在不同部门、不同位置上的他们各司其职,为帝国的运转提供保障。这是他们作为“官”的分内事。并且,“士大夫”之所以不拒绝服务于帝国政治,是因为他们有着更高的目标——实现价值上的规范,即欲使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和帝国的政治走向与儒家的“道”相统一。余英时先生说过:“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4]88而服务于帝国政治,对于“士大夫”而言,恰是他们实现价值上的规范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必须被接受的方式。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面对强势的君权和庞大帝国的政治体系,想要以“道”自任——履行其对于“道”的责任、完成好作为价值规范者的使命是十分困难的,毕竟“士大夫”的自身力量还是过于微弱了。此时,符合儒家历史文化传统的“道”遂又成为了他们的武器,他们也只有选择依傍“道”的权威,才有可能捍卫自身的尊严。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察觉到“士大夫”的理想与现实环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以上两点,从君臣、官民关系的角度,为我们一并呈现出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总体形态——一种内部高下等级森严、对外权力界限分明的“皇帝——官僚”政治。而这样的政治形态意味着,只有皇帝和官僚处在政治权力结构当中。其中,皇帝决定治国方略,官僚则负责处理具体行政事务,他们作为“关键少数”控制着整个帝国。至于皇帝和官僚之外,如士、农、工、商等,虽为社会的大多数,却不在政治权力结构当中。而这之中,又属“士”最为特别,因为他们是有机会选择进入政治的。“士”所拥有的这一选择的机会,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仕”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大背景下,又以传统政治的总体形态为具体前提,再联想到“士”对于“道”的责任,我们有理由认为,选择进仕实际上是“士”进入政治的唯一机会,“仕”对于“士”而言意义非凡。
三、进仕为“官”——现实政治中“士”的两重性与困境
“仕”的问题,自然地将儒“士”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关联了起来。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当中,有两个政治主体,一个是作为统治者的“君”,另外一个,则是作为官僚的“臣”。王亚南先生分析指出:“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异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7]55这说明了两点,第一,从“君”和“臣”的关系看,“君”以其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绝对支配地位而可以发号施令,反观“臣”面对他们的“大头目”,只得惟命是从。第二,从帝王和臣僚二者与百姓之间的关系看,帝王及其臣僚分别掌握着大小不等的权力,对于百姓而言,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样品CH4浓度用带FID检测器的气相色谱(岛津GC-12A)测定,柱温80 ℃,检测器温度200 ℃。以氮气为载气,流速40 mL·min-1;以氢气为燃气,流速 35 mL·min-1;以空气为助燃气,流速为 350 mL·min-1。样品 N2O浓度用带 63Ni电子捕获监测器(ECD)的气相色谱仪(岛津GC-12B)测定。色谱柱为80/100目PorapakQ填充柱,进样口温度100 ℃,柱温65 ℃,检测器温度300 ℃。载气为95%氩气-5%甲烷,流速40 mL·min-1。CH4和N2O标准气体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提供。
由上述讨论,我们明确了儒家的“士”与“道”的两重关系,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决定了儒“士”不只要关注自身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还一定要投身于现实社会,积极担负起社会责任。而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当中,“仕”是“士”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的唯一方式。所以,在面对“仕”的问题时选择出仕,成了儒“士”的普遍选择。
孟导突然眼前一惊。这个中年人手里拿着的,正是自己一个月之前被老贾花言巧语糊弄走的钱盒子!孟导不禁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的钱币盒子吗?”
梨洲先生认为,在旧制度痼疾的影响下,原有的学校变得名不副实。他指出:“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2]10学校早已为朝廷势利所驱遣,而日渐沦为了功名利禄的跳板进阶。“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2]10,饱学才能之士多是通过自学,而不再借助于学校的培养。这进一步表明,在学校功能变化的过程中,甚至连最基本的“养士”功能也消失殆尽,全然不存了。
欲分析“士”的两重性,还须从儒家学说的特点入手。郑永年教授明确到:“在中国的传统中,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上说,儒家学说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为王权服务的,并且依附于王权的;二是儒家是提倡‘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也就是说,儒家主要是用道德来感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10]75从中我们发现,儒家学说在面对现实政治权力的时候,既有服务性、依附性,更有倡导和规范性,这些属性与“士大夫”的特点是一一对应起来的;儒家学说与现实政治权力的关系,亦是最终落实在“士大夫”和统治者的关系上的。于是,“士”的两重性问题即可以从“士大夫如何进行自身定位”以及“统治者怎样看待士大夫”这两个角度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并且,它本身就是在两者的拉扯和相互冲突中凸显出来的;更进一步讲,它是对于符合儒家传统文化的“道”与现实政治权力所构成的“势”之间紧张关系的外化表达。
我们注意到,“有德者”的“士君子”,与儒家的理想——“道”之间的关系可谓十分紧密,不能分离。这样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方面,“士君子”一定要坚持“道”。“士君子”对于“道”的坚持决定了他们作为“士”的自我身份认定,此亦即孟子所指出的“士”之“恒心”,是“士”所以为“士”而不同于“民”之所在[3]211。另一方面,“士君子”是“道”在现实世界的具体呈现。余英时先生强调说:“道统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4]91此既确认了“士”彰显“道”的能力,又以“道”之彰显作为“士”所必须履行的责任——“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4]25。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3]204我们有理由认为,通过“士君子”的努力,一个长幼有序、贵贱有等、高下有别的合乎于“道”的社会图景完全具备了现实化的可能性。
而“士大夫”的理想与现实状况间之所以反差巨大,这与统治者看待“士大夫”的方式息息相关。对此,梨洲先生指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2]2君主将天下看作其一人一姓之私产,他们往往以一种洋洋自得的心态、同时又不乏焦虑的情绪,总是在考虑如何保全和延续这份产业。王亚南先生具体总结了统治者所要面临的状况:“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愈大,要使宇内道一风同,心悦诚服就愈感困难。”[7]69所以,如何有效解决统治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及时扼制化解可能危及统治的因素,这些自然成了帝国统治者关注的重点。基于此前提,有一点是毋需怀疑的,那就是统治者一定会注意到“士大夫”自身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重要的价值。正如阎步克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代表古典文化上,儒者显然具有更充分的资格,这便使儒家学派在文化领域处于得天独厚的有利地位。对于那个社会的政权来说,它需要充分利用结晶于‘诗书’‘礼乐’之中的高级文化来强化其合法性和整合社会,把它们转化为其政治象征;对于社会来说,也需要这种能够体现其基本道义的高级文化来自我维护,通过它们来形成政治期待,促使国家保障那些价值,并仅仅赋予这样的政权以合法性。”[9]289文化优势的延伸,契合国家、社会的迫切需要,“士大夫”服务于帝国政治所发挥的作用,是他者不能比拟的。而统治者却更加希望“士大夫”的功能发挥仅止于此,即停留在能为他们所用、为庞大帝国服务的层面上,正所谓“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2]5是也。至于“士大夫”进行价值规范的一面,可以说是君主极不愿情接受的部分。反过来,把“士大夫”群体转化他们的附庸则一直是统治者最为强烈的愿望。
而对于统治者来说更为有利的是,借助于“势”的巨大优势,他们迫使“士大夫”屈从的方式又是那样繁多。首先,统治者决定着“士大夫”的生存。虽然余英时先生研究表明“个别士人的言行可以超越他所属的阶层利益,终为不可抹杀的客观事实”[4]200,但是,个别总归是个别,并且,个别的存在往往还意味着,普遍的情况与之不同。梨洲先生概括了“士大夫”的总体状况:“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2]5可见,面对现实中巨大的生存压力,“士大夫”的自身定位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或许他们根本不曾察觉到这种变化,又或者,他们早就全然接受了现实。作为结果,统治者实现了对于“士大夫”的掌控,还使他们心甘情愿、感恩戴德。其次,统治者实际掌握对于“士大夫”的评判权。蜀汉名臣诸葛亮在出祁山伐魏前,特上《前出师表》,并在文中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11]204两相对照,言辞恳切地劝导幼主刘禅,嘱其“亲贤远小”。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肺腑之言,更代表了“士大夫”群体的共同心声。孰不知,“士大夫”们“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在现实中竟是那样不堪一击。梨洲先生指出,后世之君“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贤之,不能事我者否之”[2]8,可见,当考量“士大夫”的标准已由“利天下”转向“事一人”的时候,则“士大夫”的“贤”与“否”完全为君主的好恶所左右,并由他们个人来决定。再者,统治者能够随时对“士大夫”进行打击。具体来讲,统治者既忧心“士大夫”群体做大形成威胁,更是不愿意时时受到以“道”为根据的、具体来自于“士大夫”的约束和规范,便会自然选择对“士大夫”进行打压。其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频繁撤换宰相,到了明太祖朱元璋那里甚至直接罢相,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是采取控制“士大夫”领袖的方式,削弱“士大夫”整体的力量;二是利用外戚、培植宦官来对“士大夫”进行直接的打击,发生于东汉的“党锢之祸”便是例证。“官僚、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顺帝以前,第二阶段为桓灵时期”[12]284,而经此二阶段,“士大夫”群体遭受到重大打击,更为紧要的是“此以前士大夫领袖尚具以天下为己任之意识,故其所努力以赴者端在如何维系汉代一统之局于不坠;此以后,士大夫既知‘大树将倾,非一绳所维’,其所关切者亦唯在身家之保全,而道术遂为天下裂矣”[4]259,“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被彻底地摧毁了。
在最后一刻,我看见了康美娜,她充满了怜惜和爱意的目光让我沉醉,在死神来临的瞬间,我真实地拥有了母亲的怀抱。
透过王亚南先生批判官僚士大夫的立场,我们可以窥见此时的“士大夫”与统治者间的关系:“官僚士大夫们假托圣人之言,创立朝仪,制作律令,帮同把大皇帝的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他们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样,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7]55我们发现,所谓合作的形式之下,其实质是“士大夫”对于现实君权的主动趋从和绝对依附,这就是统治者一手打造的新的游戏规则:屈从之,“士大夫”须以“宦官宫妾之心”行“私暱者之事”;对抗之,“士大夫”将旋即遭到放逐,自动退出游戏。我们既然无法要求早已习惯了“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2]4思维的官僚履行“道”的责任,也就根本没有理由期待“道尊于势”的理想能够在现实中实现了。
2018年,空调在库存周期及景气周期的双重压力下,增长放缓趋势日益明显。从第二季度开始,补库存周期结束,市场销售就落入负增长区间。而在叠加地产不景气后,空调增长压力在第四季度凸显,并将至少持续到2019年第一季度。
四、“学校”——黄宗羲在制度层面的全新设计
着眼于“士”在现实政治中的困境的破解,黄宗羲给出了他在制度层面的全新设计——“学校”。透过先生在其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中的具体分析和论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梨洲先生对于新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他对于原有制度发展演变过程的仔细考量和深刻把握基础之上的。
“学而优则仕”[3]191说的正是在自身条件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就应该不甘做政治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当在庞大帝国的政治结构中争取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真正地占据一席之地。这就是儒家对于“士”的期待,亦即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在“士”身上的最切实的表达。而到了汉朝,汉武帝时期,这一理想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与强调“以吏为师”的秦朝不同,伴随着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尊孔氏,明天人”[8]291的建议,从而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以儒家思想成了官学所倡之正统思想为契机,“专门性的政治角色——文吏,开始向另一种颇具弥散性的角色——儒生‘君子’,让出了独踞政坛的地位。”[9]308在从此往后的漫长岁月中,儒“士”一直是政治的主体。
一朝进仕,“士”便成了“官”。阎步克教授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他说:“中华帝国的特殊之点在于,这里的文人角色与官僚角色分别都有了相当的分化,同时二者又紧密地融合为一种‘士大夫’形态。”[9]10同时,他还总结性地指出:“士大夫所谓‘一身二任’,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产物。”[9]10一方面,阎步克教授重申了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结构框架下,非“官”而不能从政的现实,强调了进仕为官是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阎教授所说的“士大夫”形态,自然引出我们对于现实政治当中的“士”的两重性问题的重点关注。
需要明确的是,梨洲先生不仅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揭示了原有的学校已经名存实亡这一事实,同时还对于社会力量试图改变学校的现状所做的努力保持了相当的关注。“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2]11,梨洲先生指出,社会力量不再寄希望于朝廷的学校,而是开始用自办书院的形式,以求摆脱现实政治权力对于人才培养的干预。但是,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2]11,也就是说,朝廷的态度总与书院相左。很显然,现实政治权力并不允许一个处于制度之外的“书院”安然存续,从一开始便对其保持着一种排挤和不信任的态度。梨洲先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2]11朝廷视书院为其对立的一方,而两者的斗争往往以书院的惨重失败为结局。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注意到旧制度当中的学校演变为了现实权力的附属品,不再能发挥其应有之作用;而跳脱到政治领域之外的书院,又深为现实权力所不容。就功能发挥的意义上而言,二者都是失败的。
以此为鉴,梨洲先生所设计的“学校”,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学校”是全新的,既不是对于过去某种制度的因袭、也不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上的改良,它的产生完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梨洲先生对于“学校”有过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分为三点来把握:第一,“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2]10,“学校”的确应该具备“养士”这一功能,但绝不能将“养士”作为其全部的意义;第二,“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2]10,必须要让“学校”成为治理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发源地,方才是对于“学校”功能作用的完全理解和最为完整呈现;第三,“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2]10,更具体地说,“学校”意在使社会中逐步形成一种风气和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为统治者的“君”,其个人意志不再是唯一的标准,统治者本人亦未敢独断自专,而一定要付诸公议于“学校”。如此一来,“学校”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由其“功能之新”出发,从而确立了它在庞大帝国政治结构中的位置。
而在将“学校”现实化的过程中,又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对此,梨洲先生也做了充分的说明,总结其要点有三:其一,强调独立性的保持。“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2]11、“大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2]12,郡县学官和太学祭酒,其人选来自公议、推择,而非朝廷的指派任命;“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2]11、“或宰相退为处之”[2]12,人选范围中全是“民”而无“官”,须从朝廷去职,才能作为候选;由此二者,可见“学校”之人事是独立的,不受朝廷干预;其二,注重权威性的彰显。“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2]12、“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2]12“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2]12,无论是地方学官面对郡县官,抑或是大学祭酒面对天子,会当讲学则处师位,纵以“民”之身份,亦有批评谏言的权威;其三,坚持全面性的负责。“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2]12、“每三年,学官送其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2]12-13、“凡乡贤名宦祠,毋得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功业气节则考之国史,文章则稽之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2]13、“凡郡邑书籍,不论行世藏家,博搜重购。每书钞印三册,一册上祕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本学”[2]13、“凡一邑之名迹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章,皆学官之事”[2]14,从学子培养到人才选拔输送、从书籍收录到人物价值评定、从教化风俗直到修葺陵墓祠宇,一应事务统归于学官总体负责,其处置标准依据事实、体现民意,而非出于皇帝的意志和朝廷的命令。
设计“学校”如此,实质上是想要实现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学校”的诞生为契机,帝国政治从原有的“皇帝——官僚”两重结构模式转化为“皇帝——官僚——学校”三者联动的模式。而这样的变化对于“士”群体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在先前的“皇帝——官僚”的政治结构之下,“士”没有独立的价值,他们通常是作为官僚的“后备军”而存在的,而成为官僚——“士大夫”是他们获准进入政治,继而进行政治参与的唯一可能、可行的方式。且“士大夫”会旋即陷入到“道”的责任与“官”的现实命运纠结拉扯当中,这是一个由“士大夫”的两重性所带来的必然困境。“学校”的出现,让一切变得不同,“学校”对于“士”的意义在于:第一,“学校”开辟了专属于“士”的政治空间,“士”藉此空间而直接进入帝国政治;第二,“学校”保证了“士”群体可以独立地进行政治参与;第三,“学校”使得“士”从此不再受制于“道”与“势”之间的张力,即得以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切实履行其对于“道”的责任。
五、结 论
梨洲先生通过回望前代,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当中的“士”群体的两重性及其所带来的困境有了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先生深入挖掘并积极调动儒家思想资源,设计出“学校”,以放眼未来。而“学校”使得“士”群体获得了独立的政治参与空间,有效地保证了“士”在帝国治理过程中承担起应当之角色的可能性,切实满足了儒家对于“士”在传统政治领域的期待,显然,黄宗羲所做的“学校”这一制度设计,具有理想性的一面。
南宋时期的县衙在处理刑事、民事诉讼中,都会涉及对待证人的问题。比如,在已发的命盗案件中,除了追捕罪犯外,还要“勾追取问”那些与罪犯相关的证人、关系人和原告,这些关系者又被称为“干连人”“干系人”“干证人”或“干照人”等。南宋绍兴四年,高宗了解到州县多将无罪人和犯人一样拘禁“动经旬月”,要求“鞫狱干证人,无罪依条限,当日责状先放”,这些事居然都“惊动”了皇帝,可见其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过,即便有皇帝的诏令,政府也经常发文“不得长期禁留”干证人,但当时将干证人拘系实为常事,有的竟致干证人“破家失业,或至死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参考文献:
[1] 顾家宁.士魂以经世——黄宗羲与传统士人精神的再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
[2] [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M].吴光,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 陈来.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17.
[7]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8]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0]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重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11]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12] 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第5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From Official to Scholar: Mingyidaifanglu——System Design of the “School”
LiuYich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of ancient China is a kind of politics with “emperor-bureaucrat” as the overall form. In such an environment, “the scholar” can only be allowed to enter and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if he is an “official”. And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Dao” and as “official”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that is, “Dao” and “potential” tension, “the scholar” can not help but fall into a difficult situation. Huang Zongxi wants to take “school” as a new political system design, adjust the imperial political structure, so as to open up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pace for the “scholar” group,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scholar” as the political subjec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be fulfilled. This is a distinctive Confucian-style program, with unique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t value as well as idealistic color.
Key words:Huang Zongxi; Mingyidaifanglu; dilemma of the scholar; “school”; system design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19)04-0091-06
收稿日期:2019-05-16
作者简介:柳一尘(1995—),男,北京市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编校 邓胤龙)
标签:士大夫论文; 政治论文; 儒家论文; 学校论文; 统治者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清代哲学(1644~1840年)论文;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