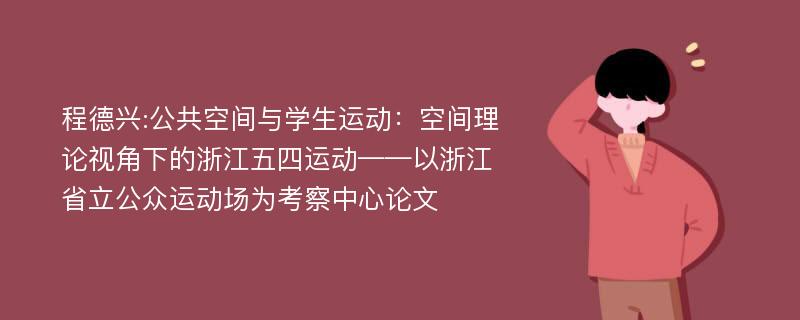
摘 要:始建于1916年,位于杭州湖滨公园内的浙江省立公众运动场见证了五四运动在浙江的波涌起伏,是浙江五四运动的地标性城市空间。从空间生产等理论出发,省立公众运动场出现是新旧政治力量斗争和社会变迁的结果,是新政府权力建构起来的空间符号。省立公众运动场不仅为浙江五四运动提供了物理空间,而且还孕育出了具有革命性的政治群体——学生,以及运动所需的意识和观念,助推了浙江尤其是杭州五四运动所需要的阶级力量和思想观念的产生。在总结浙江五四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要高度重视网络这一当代青年集聚空间的治理,加强网络空间青年思想引导工作的力度,推动形成良性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
关键词:五四运动;空间理论;省立公众运动场
一、文献简述、理论介绍和概念界定
(一)文献简述
五四运动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研究成果丰硕。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既有从宏观层面上对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政治状况、社会组织、社会心态等方面的讨论,又有从微观层面上对运动过程中人物、细节等方面的研究。如,周策纵在其著作中描绘了五四运动全景的历史画面,并对其中的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1]。再如,陈平原在其著作中对“五四”当天的天气、路线、人物着装等细节进行了“深描”。他指出,“五四”当天,学生游行的路线、具体的行动方案受到诸多细微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如,学生当时并未有“火烧赵家楼”的计划,而正是在时间、天气等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火烧赵家楼”这一历史性画面。[2]陈平原的研究正好与周策纵所提出的观点“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的交互关系,虽然是构成像‘五四运动’这一类重大事件的主要因素;其他的因素……以及看起来微小也许深具关键性的偶发事件,凡此种种都对‘五四运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研究给予了笔者学术灵感,让笔者意识到: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件写在教科书上的“宏大叙事”,而且是一个有着生动细节和故事性的事件过程,可以跳出原有历史叙事的框架,将五四运动与其他细小事件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除此之外,学界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文学性与政治性、领导人等议题也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这方面的讨论对本研究暂不具有参考性,故不细表。总体而言,学界对五四运动的地方性实践以及运动过程中的细节关注较少,多聚集北京的学生运动、上海工人运动。
(二)空间、政治与社会关系的生产:空间理论的相关学说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出现了“空间转向”,开始重新审视“空间”的实质和内涵。[3]空间的社会学研究是以齐美尔为起点的,他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一书中以专章“社会的空间和空间的秩序”讨论社会中的空间问题。[4]但对空间概念进行系统阐释的学者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他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首先系统提出“社会空间”理论。他认为空间并非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产生于人类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打上人的目的和人的意志的烙印,具有社会历史性。所以,在列氏的观念里,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并且空间的变动又往往会引起社会关系的变革。[5]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学者所开启的社会理论之空间转向,彰显了空间的实践性、历史性、社会性与社会生产本质,告别了传统的将空间假定为一个客观、中性的对象的认识论,迈向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本体论建构。[6]当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关注从自然属性转向社会属性之后,他便很快意识到空间并非一个剥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的科学对象,它一直保持着政治性和战略性,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产物,即空间的变迁不仅是城市空间重组的过程,而且还是社会转型、政治重构的过程,“是一种政治产品,具有行政和残暴统治性的产品、由政治国家上层统治关系和战略决定的产品”。可见,空间生产与政治权利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之间是彼此建构、相互影响的关系。新的政治权利关系是生产新空间的主要力量,同时新的空间也在巩固、塑造和生产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最后,同英国一样,美国也认为缅甸政府和军队都不可靠,大量的军援在缅甸不能被有效、正确地利用,这一点也得到英法美三国新加坡军事会谈的一致背书。1951年,美国国务院内部反对向缅甸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理由是即使缅甸拿到了大量的、超出其实际需求的军火,也不能增加缅甸政府的防卫能力和平叛能力,多余的武器会被变卖或用于私人武装,因此美国首先应满足盟友的需要,拒绝缅甸人的援助要求。[40]
(三)概念界定:何为浙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最早是由五四运动参与者罗家伦1919年5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提出的,这个概念最初是指“五四”当天发生的事件。后来随着社会各界讨论的深入,五四运动的概念逐渐被扩大化。周策纵将五四运动和五四事件加以区分,将五四运动指向为“一场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的时间跨度为1917年到1921年之间。而五四事件特指发生在“五四”当天的历史事件。[1]
浙江五四运动作为全国五四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也是相当宽泛的。广义来说,浙江五四运动也应该是一个过程,包含了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等内容。但是与北京的五四事件相比,浙江的五四运动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性。五四事件发生后,浙江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影响力较大的学生运动发生在五月十二日,其后浙江学生还组织了多次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如著名的“一师风潮”。本研究中浙江五四运动广义层面上主要是指五四运动期间(1917—1921年),尤其是北京五四事件发生后浙江省的学生爱国游行示威、罢课,工人罢工等活动。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无法穷尽浙江省所有的五四运动活动,而是选取了发生在杭州、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个别场次的“学生运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二、研究的问题
湖滨公园的位置原是清军占领浙江后出于军防和巩固统治的目的而圈地修建的八旗驻防营。该旗营始建于顺治四年(1647年),顺治七年(1650年)竣工,顺治十五年(1658年)扩建。旗营位于浙江西湖之东、濒湖处中间地段,西边濒潮,东边至俞家园,北边至井字楼,南边至将军桥,并建有迎紫门(东面)、平海门(东面)、延龄门(南面)、拱辰门(东北面)、承乾门(西北面)五大营门。旗营砌石为墙,城墙高1丈9尺,厚1度,长1962度,绕起来9里有余。[10]
彼时,《申报》亦有报道:“自山东问题失败后,浙省人士愤激异常。先由之江大学学生发起‘浙江中学以上学生联合救国团’,请愿军民各长官转电政府,争还青岛,惩办国贼。于月之十二日晨八时,各校学生齐集于湖滨公园……学生三千余人,每人各执‘还我青岛’‘誓雪国耻’‘惩办国贼’‘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劝用国货’‘众志成城’等白旗不胜枚举。”[9]
当时公众运动场是建在湖滨一公园内,属于湖滨公园的一部分。所以《经亨颐日记》和《申报》中的记载并不矛盾。其后在著名的“一师风潮”中,学生也是在公众运动场集合、出发。所以,公众运动场见证了五四运动在浙江的波涌起伏,成为浙江五四运动的地标性城市空间。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的公共活动场所并不丰富,通常是庙宇、祠堂等地,并没有“公园”“运动场”等现代化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湖滨公园和公众运动场是浙江城市近代化发展的结果。学生们为什么会去公众运动场集合,为什么公众运动场能够成为五四运动期间浙江的政治舞台,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政治空间?随着近些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转向的出现,出现了不少从公共空间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公共空间与现代性、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等视角研究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空间变化的研究成果。而综观国内外对五四运动的学术研究,从空间视角对其进行研究的可谓凤毛麟角。因而,本研究将从“空间”视角出发,将目光聚焦在浙江五四运动中“公众运动场”这一地点,探寻浙江五四运动与民国时期浙江城市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以窥探浙江五四运动背后的深层社会变迁,这研究视角较为新颖,而且还有巨大的言说空间。
三、权力更迭与新型公共空间的出现:省立公众运动场的出现
(一)从旗营到湖滨公园:民国初期浙江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浙江后,浙江省各地学生纷纷奋起响应。杭州之江大学于1919年5月6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商议联络在杭各校学生一致行动。5月9日,各校代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举行示威游行,致电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5月12日上午八点,杭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三千多人,齐聚湖滨公园的浙江省立公众运动场(以下简称“公众运动场”),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宣布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成立;九时许,游行队伍从公众运动场出发,前导以“浙江省垣中等学校以上救国联合会”大旗,每人各手执小旗一面,上写“还我青岛”“同胞速醒”“拒签和约”等,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游行队伍至省军署(位于湖滨路),大呼“还我青岛”三声,过省长公署(1916年7月,省行政机关改名为“省长公署”,长官改称为“省长”),大呼“还我青岛”六声,以此示威。[7]但当时省军署、省长公署“都大门紧闭,上了刺刀的警察站满了岗,无法进去”,游行队伍遂临时决定转入省议会。最后议长出面,让游行学生推出五六位代表进入会场。学生代表要求致电巴黎和会,交还青岛,否则拒绝签字;并要求惩办卖国贼曹、章、陆等人。到下午三时二十分,游行队伍才回到公众运动场的原地,各校散归。轰轰烈烈的浙江“五·一二”学生大游行才暂告段落。整个过程,游行队伍秩序井然。如,彼时浙江省最高学府——渐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走出校园时,都是踏着体操课教员训练他们的整齐而有序的步伐,像是去参加联合运动会一般。时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经亨颐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十二日,六时余先到学校,学生尚未发,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举。即至教育厅,缄甫接踵,谓学生全体黎明已自后门逸出。电话因风雹,多不通。分别与军警接洽,免致误会。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8]
辛亥革命后,清朝被推翻、浙江光复,浙江省军政府成立了。1912年2月,新政府与原满清政府的旗营代表签署《浙省旗营善后办法》,将旗营的土地收归为新政府官产,并做重新规划:“原旗营公产如牧地、旗地、营地、坟地,均作为新政府官产所有;对于旗民的生计,浙军政府允与一般人民,一律妥为筹划;旗营的土地均系新政府官产。”[11]
评审意见:评审后根据报告书的等级。对不合格和合格可直接形成专家组意见。对合格待定的,各专家应形成书面的意见,方便不同意见的表达,防止出现只有专家组整体的意见,而忽视其他意见的表达。
1912年7月22日,浙军政府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1913年,开始拆除旧旗营城墙。旗营被拆除之后,新政府开始重新规划这块区域,对这片土地逐一进行标卖,将这一地区打造成公共的商业中心,定名为“新市场”:“除了马路和公共用地,其余土地予以出售,以建商业场。”[12]
(5)茶产品常规成分检验。内容有:①蛋白质和氨基酸检验;②糖类检验;③脂类检验;④酸度检验;⑤维生素检验。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公众运动场以其巨大的开放性和公众性给学生参与集体活动提供了可能。这种公共生活空间和集体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形成一种新的群体关系、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即学生(青年)群体关系和意识的产生。一系列的公众活动和公共空间还形塑、培养和强化了学生的集体观念与公民参与意识。经常性的运动会使学生们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还是一个有着共同生活经历、共同传统和共同感受的集体。同时,运动场这一公共生活空间建构了学生群体的民主意识。
新政府将旧旗营基址至西湖沿岸的空间设计成供市民休闲娱乐的湖滨公园,以与湖滨路相交的四条公路平海路、仁和路、邮电路、学士路为界,将湖滨公园分为5段,分别称湖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公园:“以离湖岸起20公尺之地辟为公园,平草设栏,内杂植花舟,设置座椅,供游人休憩,是曰湖滨公园。”[14]
一方面,人口大规模的集中需要相应的物理空间作为“容器支撑”,开阔、容量较大、同质性人口集中分布的公共空间是产生政治行动、民众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必要条件。在浙江1919年5月12日的“学生运动”中,宽阔的公众运动场以及湖滨公园为学生群体聚集、开展政治行动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空间条件。
(二)民族主义思潮下公众运动场的出现
换言之,公共空间是政府、社会组织等进行社会动员、向公民群体传递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对公民群体来说,公共生活是一种民主的教育。可以说,省立公众运动场以及在其中举办的一系列公共活动促成了浙江学生群体公共意识的觉醒及现代民主精神的勃发。
公众运动场内设置有各个运动部门,包括普通体操、器械体操、球部体操、弹子运动、技击、游泳等。运动场面向民众免费开放,其中包括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及网球场各一处。足球场兼做田径场,还有爬杆、单杠、双杠等简单的运动器材。[10]至此,在湖滨公园一带又形成了一个宽阔的、适合人群集聚的公共空间。而公众运动场的出现正是民族主义思潮和浙江城市近代化发展的产物,是民族危亡背景之下民族主义空间对传统的封建主义空间的完全颠覆和置换。
四、新社会关系和观念的生产:公众运动场在学生运动中的作用
(一)举办学生运动会:公众运动场的主要功能之一
公众运动场建立之后,便成为杭州市乃至整个浙江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集会的主要场地,其最主要的功能便是用来举办学生运动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便是浙江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运动会。经亨颐在其日记中也多次记载了学生联合运动会的状况,如1918年的第二届联合运动会:“1918年3月28日,阴晴,又集全体学生在操场,施临时训话:关于第二次联合运动会宜如何注意,并全体徒手演习。”[8]
按照《浙江省联合运动会的章程》规定,运动会的持续时间一般为三天,前两天为男子赛,后一天为女子赛。而联合运动会的前身则是省教育会组织的浙省中等学校联合会操。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会具有多方面的益处,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身体素质,而且还以集体性活动的形式培养了一种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
(二)空间基础、新观念与社会关系的生产:公众运动场在浙江学生运动中的作用
从一个封闭式的统治阶层管控的政治空间变成一个具有公众性的、开放式的平民经商、休闲空间,其背后的主导力量是政权力量的变迁。新政权在取代清政府之后,取得了空间生产的权力,对旗营这一象征着清政府在浙江的政权空间的归属、性质、结构、造型等方面进行大规模重组,将其改造成巩固和强化新政权合法性和先进性的政治空间和符号。正如钟靖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的,“这种空间的强制改写源于新政权渴望赋予其新的政治文化含义以满足自身需求,体现了对帝国主义殖民上海时留下的建筑郑重其事的解构……铸造空间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策略性的政治过程”[15]。浙军政府对旗营的改造亦是如此。
总之,在浙江五四运动期间,公众运动场是组织和动员学生参与集体生活,向他们传递群体观念和公民参与意识的主要场地。而对于学生群体而言,在公众运动场中所参与的一系列运动会活动是一种民主教育。
“新市场”西起湖滨路,东至岳王路、惠兴路;北起钱塘路(今庆春路的众安桥至东坡路段),南至兴武路(今开元路的南山路至青年路段)。[13]新政府对区域内的道路进行规划,设计了迎紫路(即现今解放路)、延龄路、平海路、湖滨路四条主道。
通过改进后的使用,解决了原电缆托辊支架存在的上述问题。更换任一托辊,无需拆卸电缆托辊支架,实现了任一托辊可以单独更换。在更换任一水平托辊时,只需拆卸电动铲运机后尾架两侧边板水平托辊固定卡块,然后将水平托辊从卡槽上取出,再更换安装新水平托辊,简化了水平托辊拆卸工序。在更换任一垂直托辊时,只需拆卸该垂直托辊上、下固定卡块,取出垂直托辊,再进行更换安装。
清末民初之时,民族危亡之际,社会各界为兴国强民,便开始重视体育并倡导强壮国民体质。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曾提出“要复兴民族,第一步是设法使大家的身体强健起来……提倡体育是一个改进民族的很好的办法”和“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思想。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1915年《袁君西洛江苏省内设立公共体育场建议书》颁布,出现兴建公共体育场的浪潮。时任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一职的经亨颐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教育。在经亨颐以省教育学会的名义数次呈请彼时浙省都督吕公望和省长齐耀珊兴建公众运动场之后,1916年新政府终于在湖滨第一公园兴建起了一座规格宏大的公众运动场:“此案原定地点,前据省会警察厅呈以工务处迁移为难……将湖滨第一区公园基地,给图送候核办在案,仰即知照。此批。”[16]
五、小结与思考
(一)政治、空间、学生运动与社会变迁
公众运动场出现的背后是新旧政治力量斗争和社会巨大的变迁,是新政府权力建构起来的空间符号,体现的是权力者的意志。可以说,公众运动场的出现是政治运作的过程,映射出了城市政治体制演变的轨迹及其复杂面相。但是,通过在这一公共空间中开展学生运动会等公共活动,学生群体这一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关系以及学生群体的集体意识和公民参与观念被生产和形塑出来。对于浙江的五四运动而言,公众运动场不仅为这场运动提供了物理空间,而且还孕育出了具有革命性的政治群体——学生以及运动所需的意识和观念,助推了浙江尤其是杭州“学生运动”所需要的阶级力量和思想观念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变迁。
中国力量在不同历史阶段包含着众多的阶级和阶层,其涵盖的范围之广足以说明力量之广泛,同时中国力量的主体——劳动人民,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其占据的人数之多、发挥的作用之大,更能凸显出广泛性这一特点。
(二)对网络空间与当下青年思潮走向的思考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以青少年、青年和中年群体为主。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7.9%;10—19岁占比为18.2%。”可以说,在当下社会里网络已经成为集聚青年最多的一种虚拟空间。在这个进入门槛较低的虚拟空间里,当代青年呈现出非常多元的精神风貌:一方面,以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日益强大为心理依托,一些青年在网络中表现出较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小部分青年受不良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表现出了非理性的言行。在总结空间理论及浙江五四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要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治理,加强在网络空间引导青年思想的工作力度,助力于良性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张静,译.长岳麓书社,1991-8.
[2]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1.
[3]钱厚诚.社会理论中空间问题的沉寂与兴起[J].哲学动态,2010(10)27-32.
[4]叶涯剑.空间社会学的缘起及发展——社会研究的一种新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05(5)73-77.
[5]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0.
[6]林密.空间转向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空间化——以列斐伏尔、哈维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17(9)47-53.
[7]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杭五四运动在浙江[M].杭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
[8]经亨颐.经亨颐日记[M].杭浙江古籍出版社,198165-166.
[9]申报.纪浙垣学生团游街情形[N].1919-05-16(07).
[10]葛程思.民国时期杭州湖滨新区研究(1912-1937)[D].杭杭州师范大学,2016.
[11]申报.浙省旗符善后办法[N].1912-02-23.
[12]浙江日报.投票旗营地亩者注意[N].1913-11-07.
[13]姚一哲.杭试论民国前期(1912-1937)浙江“新市场”的土地开发——兼论浙江城市中心区的移动[D].杭浙江大学,2011.
[14]张光钊.浙江市指南浙江[M].杭浙江市指南编辑部,193273.
[15]钟靖.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D].上华东师范大学,2014.
[16]教育周报.齐省长批本会呈请开办省立公众运动场由[J].1916(163)32.
收稿日期:2019-02-26
作者简介:
程德兴(1991—),女,安徽安庆人,浙江省团校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
两组治疗前PFG、2 hP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PFG、2 hPG 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PFG、2 hPG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沈建良(1970—),男,浙江德清人,浙江省团校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蔡宜旦(1974—),女,浙江诸暨人,浙江省团校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语用分析从符号学角度是分析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因此应结合语境、言语者的表达态度进行分析。以往类似“A到VP”格式大多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其作用主要是叙述和描写,而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这一格式。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网络语言交互性、传播性、个性化的影响下,在多样化网络媒体的促进下,“A到VP”格式不再只出现在晦涩的文学作品中,而是更有生命力地走入民众生活。语言的主观性在网络语境中更加明显,网络语言所传递的情感更加丰富,下面我们主要从语气角度分析“A到VP”格式在不同的语境中的表达功能。
中图分类号:K261.1;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19)02-0024-06
(责任编辑:宋 鑫)
标签:浙江论文; 空间论文; 运动场论文; 学生论文; 公众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9年第2期论文; 浙江省团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