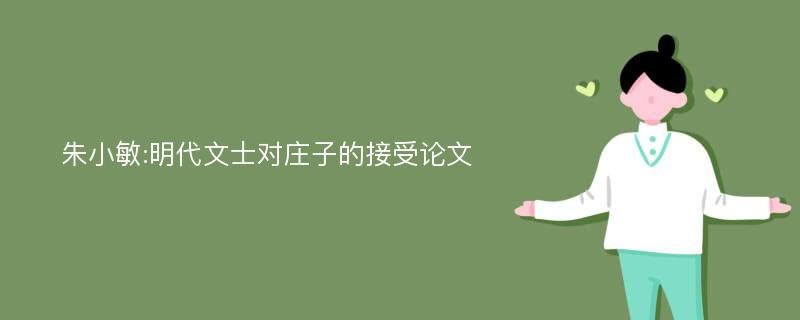
摘要:《庄子》成书于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开放自由的时期,其文汪洋恣肆、潇洒恣意,长期以来以儒家为主的社会传统使得《庄子》在流传过程中处于一种次要的地位,而明代立国以来,对《庄子》的接受也分成了不同的时期,渐渐由排斥到接受,出现了许多关于《庄子》的注书。
关键词:明代;庄子;庄子注
庄子一书,以其汪洋恣肆的文风,朗朗上口的韵语,潇洒自逸的情气,在长久以来,被奉为经典,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儒,通常处于主流之位的也往往是儒学经典。而明朝也不例外,开国之时,便将儒学定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一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教”实行严格的文化专制政策。同时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朱元璋下令全国的府、县都必须设立儒学,以儒学教化民众,而在科举取士方面,明代也制定了一套比宋代更为完备的科举制度即八股文,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且《四书》又专以朱熹注为依据,科举的导向使得广大读书人以儒学经典为主,寒窗十年,吟咏背诵,经典之外更不复览其余。
我们在明初大儒宋濂的话中可以看出明初文坛对于庄子的态度,其对庄子的思想予以猛烈抨击,说其“然所见过高,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盖彷佛所谓‘古之狂者’”,又说“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斁败,卒踣人之家国,不亦悲夫”在宋氏看来,《庄子》一书罪莫大焉。而明代大儒吴与弼亦劝人读儒家经典之书,其在《上严亲书》云:“所读书宜只以小学、《四书》为急,次及诸经本文,其子史杂书切未可轻读。男少有所得,浑在小学、《四书》、《语略》、《近思录》、《言行录》。于此数书,茍无所深得,则他书易坏心术,其害非浅鲜也。”明初建国一切刚刚建立,新的明朝政权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去稳定社会,大乱之下,人心惶惶,更是众口异心,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明初显然不可能接受一个宣扬自由和淡泊的思想的庄子。
而明代对于庄子的接受是在正德、嘉靖时期开始,一方面是明代的最高统治者不理朝政无瑕去继续钳制思想,而放松了对于思想的管控,同时社会上的矛盾也使得明朝有些积重难返,矛盾增多,这些因素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不再是单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的崇拜对象,转而更多的去寻求自身的解脱,在这一方面,儒释道三者之中,后两者便变得更加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时候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的出现,也极大的推动了这种风气的影响,长期以来以朱学为代表的二程之学,一直以来为明代士人所严守,他们注重章句之学,踏实而又保守,有些时候则显得过于迂腐,而阳明心学则致力于突破这一方面走向陆九渊的一路,认为心外无物,从此心学大盛,王氏心学吸收了佛、道的思想,庄子的任性逍遥的主张无疑有了广阔的“市场”。
王守仁之后,其弟子王艮创立了泰州学派,强调“百姓日用是道”,至罗汝芳更是提出了“赤子良心”说,这些学说把人们从理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个性解放的思潮,这为明代中后期庄学的勃兴提供了强大的助力。而在明代中期,经过明初几代皇帝臣子的共同努力之下,社会状况有了很大的发展,明初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形成了一个双向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而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人们思想的活跃,这一切都为庄子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我们也看到伴随着印刷技术的成熟,明代中期后印刷业也飞速发展起来。
明代刻书业,有官家、私家和书坊三种类型,其刻本分别被称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魏隐儒在《中国古籍印刷史》中说:“明代刻书,也是沿袭着宋元习惯,有官刻、私刻和坊刻本三种类型。官刻本着重刻经史典籍;私家刻本以名家诗文为多;坊间刻本,除经史读本和诗文以外,为了满足民间文化生活需要,还大量地刻印了一些小说、戏曲、酬世便览、百科大全之类的民间读物。其中,坊刻尤为繁荣,当时较为有名的坊刻中心有建阳(福建)、南京、苏州、杭州、湖州等地,据统计,闽中书坊有84家、南京有57家、苏州有37家。[1]印刷业的繁荣也为庄子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同时明代中后期科举制度的变化也对这种风气起了促进作用,“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明朝中期后,八股文以追新猎奇为时尚,诸子书走俏,士子们为谋取功名,竞相标新立异,《庄子》“汪洋自恣以适己”、尚奇尚大之文风就成为追求的目标。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八《科场禁约》条中说:“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琦上言:‘自人文向盛,士习寖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鹜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朱、程,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冯琦是站在改革时文之弊的立场上上书皇帝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文风所尚,这个也就极大地促进了庄子的兴盛。种种因素的发展,推动着庄子一书在这一时期的繁盛。
宁夏固原原州区地下水取水井普查成果分析…………………………………………… 牛 赟,南克良(12.53)
从隆庆至崇祯末年,《庄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上至权相重臣、内阁学士,下至县令、教谕,道士、僧人、居士、隐士、书坊商贾,各色人等,讲论、品评,解《庄》、注《庄》,一共留下了二百余种著书,这也形成了明代庄学史上长达数十年的兴盛局面,在这些注书中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儒注庄,上文已经说到,在明代后期,八股文不再严格的遵照朱注来判定高低,而出现尚奇的倾向,往往这时期的注庄多在儒学思想的框架之下,剖析庄子的句法、文法和章法,以此来服务于科举,士大夫亦有以儒解《庄》者,如沈一贯的《庄子通》、叶秉敬的《庄子膏盲》等。沈一贯在《庄子通序》中说:“庄子本渊源孔氏之门,而洸洋自恣于方外者流……余以其五万六千集余参而五之,以畅其说,虽不中庸,远乎哉?第二种便是以佛注庄,在心学发展以后,陈献章等人漫谈心性,在对于本心的阐释中本已经常摇摆于佛老之间,受其他学派的攻讦,而上溯到宋朝,陆九渊等人的思想形成也多少的来源于释家的影响,所以随着心学的发展,晚明时期的李贽、公安三袁有罗汝芳一系而来,强调自我个性,追求生活禅趣,如袁中道在《导庄·自序》中表示,他撰《导庄》的目的即为了揭示《庄子》内篇的“禅髓”,即与佛旨相合的特征。他说:“庄生内篇,为贝叶前茅,暇日取其与西方旨合者,以意笺之。觉此老牙颊自具禅髓,固知南华仙人的是大士分身入流者也,作《导庄》。”而老庄与佛家中思想相通的部分,又为这提供了可能性,典型的方式是以佛典来印证庄子,晚明僧人注《庄》著述还有释性通的《南华发覆》、释如愚的《庄子旦暮解》、释通润的《漆园逸响》、释正诲的《庄子注释》以及憨山德清的《庄子内篇解》。同时与这些高僧交往密切的居士也有大量的《庄子》著述,诸如焦竑的《庄子翼》、李贽的《庄子内篇解》、陶望龄的《庄子解》、袁宏道的《广庄》,袁中道的《导庄》、杨起元的《南华经品节》等等,僧众与居士们多以佛解《庄》,甚至佛化庄子。正是由于佛教对整个晚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晚明注《庄》多参杂佛理。第三种方式是以道解庄,这种做法延续已久,一直以来通俗的说法便是将老庄并举,而更有一种说法将南华经认为是道德经的注解。
明代中后期是明代政治、思想、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时代,先时恪守的赖以维持社会稳定的种种因素都已渐渐崩坏,而这样一个时期之下,庄子一书随着众多其他诸子书一起受到了读书人的重视,人们纷纷在老庄思想的庇佑之下,在心中寻求一个安放自我心性的桃花源地,亦或是厌倦俗世之后的清凉之地。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里,伴随着庄子的广泛传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篇繁盛背后的良莠并存,“商人重利轻别离”在社会的广泛需求的刺激之下,为能得到更多的商业利益,一些书坊主便采取非常手段,或请文人代笔,或托名于状元名士,更有甚者则粗制滥造、偷工减料,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益不捐重价故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随着庄学的日益兴盛的背景下,明人开始自觉地全面品评历代庄学,出现了具有“庄学史”性质的著述。
回顾40年的现代戏创作园地,其次令人瞩目的就是不断成长的现代戏创作队伍。老一代的作家导演杨兰春,音乐家王基笑,演员高洁、王善朴、柳兰芳、魏云、杨华瑞、任宏恩……在改革开放前期仍然耕耘在现代戏园地,后继的作家孟华、齐飞、姚金成、李学庭、王明山、杨林、陈涌泉、贾璐、韩枫,导演李利宏、张平、李杰,演员李金枝、汪荃珍、贾文龙……同样在现代戏的创作中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正是一代接一代的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成就了河南现代戏园地的百花争艳,也正是现代戏园地的一部部作品推出了河南现代戏的创作队伍。
而随着明朝的灭亡,庄学的影响并未突然地也随着政治的覆灭而销声匿迹,相反,承着辉煌的余旭,更因在明代覆灭的这样背景之下士人心态的强烈变化,庄学的研究更存在着一种无声的意义,与其说晚明时期对庄子的接受是在百无聊赖之下对自我心性的寄放,而这时期的接受则是遗民们对于庄子思想的皈依了,庄子本为悲者之书、弱者之书,这时期的移民们,正是这样一种处境,满怀故国之思,在死社稷的强大压力之下,更有无限的悲痛与内心的复杂纠结。
高校的教育目的是为了社会需要培养优秀人才,为了企业需求培养定向型专业人才,随着社会形式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水平的需要也在不断提高。经济管理专业与社会发展、地方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经济管理高校以培养经济管理操作能力与管理理论兼具的经济管理专业型人才为目标,在知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下,大大提高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效果,同时也有利于形成学校和企业双赢的局面。经济管理教学要与当下社会经济环境相融合,有针对的为社会经济需要培养相应经济管理人才。传统的经济管理教学已不能满足现今社会发展速度,校企合作模式是通过企业对人才实际需要的前提下,联合高校共同建立培养企业所需人才的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明代,对于庄子的研究,可以很明显的分为三个阶段,沉寂、辉煌与余旭,同时在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足以在整个庄子的接受时代中有自己的重要地位,正如渊冰始于积水,清代庄学研究的繁盛,不得不说亦受其影响,而对于明代的士人来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注庄解庄的文化氛围中,使得士人的心态在这双向影响中渐渐的显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明代无论是大学士宋濂,如内阁首辅沈一贯,都有专门针对庄子的著述,思想无论如何,总归是多元影响之下,而不是一片皆黄茅白苇、黑白分明。如果是这样,那么文化思想的境界中恐怕就不会显现的如此异彩纷呈,而任何东西也正如庄子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在思想的境界中也正是如此,在历史的脉络中如浪涛,有其高潮迭起,更有其低回深沉。在明代士大夫的政治走向衰败,思想逐渐僵化时,人们逐渐感受到其对于思想的禁锢,而开始求新求变,同时往往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而文人们的思想也多徘徊游离于儒道之间,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明显的将明代士人对庄子的接受分为三个时期,但是我想在这背后每一个时代的士人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点,便是儒释道作为传统文化对传统士人心性品智的长期滋养孕育,恐怕不是这么简单能给予下定义的。
参考文献:
[1]刘海涛,谢谦.明代庄子接受论[N].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1.
[2]张洪兴.论明代中后期庄子学的勃兴及其表现特征[J].兰州学刊,2012 (1):169-174.
[3]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09:1-184.
[4]黄红兵.沈一贯的庄学思想研究[N].江汉大学学报,2010 (1):95-100.
[5][明]宋濂.文宪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1223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明]朱得之.庄子通义[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256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5.
[7][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标签:庄子论文; 明代论文; 思想论文; 现代戏论文; 刻本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道家论文; 《北方文学》2019年第2期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