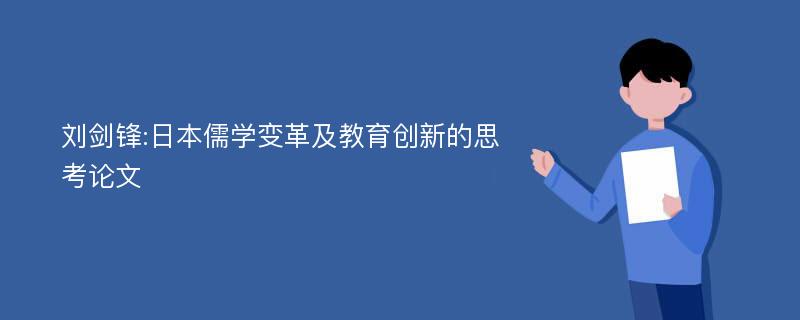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由孔子创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日本是典型的东方文化传统国家,与中国、朝鲜及越南和后来的新加坡统称为儒学文化圈,对传播和发展儒家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为东方文化圈的核心国之一。日本早期系统地引进儒学,全面推行唐化,明治维新后,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同时对儒学进行了相应的改造。日本不仅是第一个批判儒教的民族,也是儒家文化圈中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儒学在日本有三次大的变革演进,其每一次变革,必然要求相应的教育创新,并通过教育创新来实现。研究日本儒学这种来自中国、有异于中国并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的演变过程,对于我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儒学在日本的作用与教育创新
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引进儒学近2000年的过程中,也同时引进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但是,同日本引进儒学并不照搬儒学一样,日本也并不完全照搬中国教育制度,这种独特的学习借鉴形成了今日日本特有的儒学体系和教育制度,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是水资源管理不断加强。《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即将正式颁布施行。首次确立了水资源控制指标体系,各项控制指标已全部分解到各省辖市,2013年年底前将全部分解到各县市区,该项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省、市、县水资源系统平台建设和水资源信息管理软件研究开发工作。突出抓好节水型社会和水生态文明试点建设,试点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1.儒学促进日本民族形成。日本之所以形成大和民族,除了日本原始氏神的图腾文化外,最重要的是中国儒学东传。先进的大陆文化为日本民族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思想基础,从而使日本的奴隶制社会迅速完善成熟。但是,日本当时并未出现如中国东汉的太学等正规教育机构,这应当是一种发展上的差别。尽管可能是发展上的差别,但也表明日本对文化的引进自古以来就并非机械地全盘照搬。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态度,直到二战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时仍始终如一。在古代的大和国中,要创办一所似中国汉代的太学,无论在财力还是人力上都是难以办到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时日本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还不足以供养这大批文化人。但是儒学能促进日本的发展,正是自引进儒学起,就奠定了日本文化发展的根基。从文化发展的本质上,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创新,它开创了一个新文化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确定了引进文化的法则,在移植文化中不必全盘照搬,并对文化或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使之适合本国发展的需要。
2.儒学为日本大化革新开辟了道路。大化时期,日本派出了一批学问僧到唐留学,并多次遣使到唐交流,可以说,这一阶段日本全面地移植了处于盛世的唐文化,促进大化革新的最后成功。革新之后,日本仿唐建立起包括私学在内的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校系统,既有国家设立的大学寮,也有地方管理的国学,还有民间自发创立的私学。这些学校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也是传播中国儒学的场所。但是,日本官学的规模并不像中国那样集中庞大,而且后期还出现衰落,反而地方藩学和私塾发展兴旺。更重要的是,日本并没有移植中国最出名的科举制。
定理 1 设图G是最大度Δ≥7且可嵌入到欧拉示性数非负的曲面图,如果图G中不含相邻的含弦6-圈,则la(G)=「Δ/2⎤。
日本儒学的变革和发展,是一次从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思想体系逐步转向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实践,并得到相应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日本儒学的每一次历史演进和发展,都是通过教育创新来实现的。伴随儒学的发展,教育也从低级向高一级演进。同时,日本儒学的三次变革,拓展了儒教文化新的内涵,对东方文化作出新的时代阐释,推动了东方文化的历史转变,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日本儒学的三次变革演进
“两票制”执行后,药品批发企业需直接从生产企业进货,生产企业为避免资金风险,一般对资金承付要求较为严格,承付期限比以往代理商分销时要短,且不少生产企业要求现款或预付款发货。而药品销售到下游医疗机构后,一般有3至6个月的滞账期,部分情况下甚至更长。在上游垫资负担增大和下游回款延长的双重作用下,药品批发企业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加大,大部分企业现金流非常紧张,特别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如果下游回款出现问题,很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严重时可能导致企业的破产。
第一次是大化革新中皇权统一认同和忠国孝家伦理的形成,对建立大和统一国家起了重要作用。大化革新开始,日本唐化的过程就是儒学化的过程,是日本全面实践儒家的重要开端。但是,即使这样,日本人仍然通过自身实际,对儒学做了符合自身发展的改造,使儒学中的纲常伦理、治国兴邦之仁义礼节与日本原始多神氏族的神话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使这种多氏神崇拜对群体间序列的上下关系有了更加合理和系统严密的阐释。在糅合儒术之下,天皇神道更加具有神明皇道性。日本在幕府时代基本上以儒学为基础,却能根据实际对儒学作相应的取舍,在教育制度上不实行科举制就是一例。
1.强化群体归属意识,维系社会和谐。儒学在日本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群体性,以忠信仁义为特质的文化成为维系社会群体的最重要理念。这种群体性表现为三大原则:一是群体圣化原则,即每个人都重视和维护群体的统一与和谐,群体具有高于个体的意义,个人应无条件地服从群体,按照群体的利益采取统一的行动。这一原则促使每个人都追求同一性,并使个体从中获得归属感,也只有在群体中个体才能得到生存的价值。二是群体序列原则,即每一个体都按有关部门辈分和功名列入相应稳定的序列和位次,这是使群体得以和谐和步调一致的关键。儒学的“三纲五常”提供了有关部门名位、身份、性别的最重要的序列基础。现代日本企业中倡行的“年功序列”,就是以工龄来认同某人对企业贡献而使员工序列化。三是互助共济原则,即以缘结和互帮互助协调群体间人与人关系。获得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报恩性群体情结,使每一个成员在群体间以相互帮助为荣,对别人、上级的施予还报,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的发展。日本儒学成功地把序列与仁义忠信牢固地综合于特定的生产团体和企业运行之中,使日本社会中充满重人际、重情感等人文管理特征。这与欧美等国群体中过于突出个体是不同的。
日本儒学的第三次变革是在战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美军占领全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指令下,从政体到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革,日本儒学也由此出现了重大转型:一是清除了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思想基础和为天皇神道服务的伦理体系,使儒学第一次走出为皇权专制服务的轨道。二是摆脱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突出了人本的新教育观,制定了民主主义的教育基本法等教育法规,实施“六、三、三、四”新学制,重组学校课程体系,建立新的教师教育制度,等等。总之,儒学得到重大整饬,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当皇权从儒学体制中抽去之后,儒学为维护家天下的伦理核心也由此丧失,从而转向与现代管理体制的结合,这是日本儒学走向服务社会实践的新阶段。第三次蜕变使儒学更多地剥离原有的思想体系,使部分原有的伦理原则更贴近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为儒学的发展和历史更新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日本儒学变革的成果及启示
3.儒学促进日本民族的统一。日本儒学发展进程中不断与日本原有的氏神崇拜相结合,也得到教育创新的有力支持。日本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成功地把上下尊卑的等级制与儒学中的三纲五常巧妙地结合起来。大化革新之后,日本走向统一的封建国家,却能统而不一,维系这种政体的正是仁义忠信等儒教伦理。这些儒教伦理与日本民族中氏神伦理的结合,也正是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造后实现的。日本教育中偏重“忠”,讲忠国和孝家的统一,成为全国人的共同精神支柱,如果这点不是日本教育的独特之处,至少也是日本人做得最好、最完善、最彻底的地方。虽然这一点为后来军国主义教育所利用,成为侵略战争的帮凶,但就教育本身而言,是有独特之处的。
日本从吸收引进儒学,到发展儒学,最后以新的儒学体系拓展了东方文化圈,使东方文化圈产生了新的辐射力。日本吸收儒学,都是在日本实际的要求下并在其中加以整合,结合日本社会实践需要予以必要的发展。历史上,儒学在日本有三大变革:
日本儒学的第二次变革是发生在明治维新前后一百多年间。18世纪初,日本与荷兰通商中大量洋学涌入,“兰学”开始盛行,日本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中竟败于南蛮,消息传来,使饱读儒书的日本儒士痛心疾首,随之西方列强炮舰到日逼关,因此对儒学造成了巨大冲击,洋校开始出现。自1861年幕府首次向欧美派出使节开始,洋学兴起,各种西学汹涌而至,日本在向西方列强学习中,逐步实现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和魂汉才”的观点是被日本人奉为“文化之神”的菅原道真首先提出,简单地说就是日本的精神为体,中国的智慧技术为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和魂汉才”中的“和魂”实际仍然是儒学的内容,但是日本人坚持以“和魂汉才”的方式,一方面用以表达一种民族自尊,另一方面表明可以根据日本的实际对汉学进行有目的的选择。正是日本有了对吸收汉学的经验,从而在接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一时期,日本儒学开始走出中国固有的文化模式,通过南蛮学、兰学、洋学的发展融合,不同程度地吸收西方合理主义、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的精神。显然,也由于“和魂”中的许多封建因素的酶化作用,使日本在文明开化中吸收了西方许多负面文化,如扩张侵略等。
大化革新以及后来的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得到全面发展的1200年,这个时期日本通过引进先进的中国教育,使尊重知识、重视教育蔚然成风,各藩以办教为荣,养儒为尚,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儒学流派和大师。日本在这一重大文化移植中,也再次对教育做出有创新意义的变革,使日本儒学朝着符合日本实际的方向发展。没有这种教育创新,儒学在日本就很难得到生存发展。这种创新的原动力,仍然是教育关注和服务于经济、关注和服务于民族生存的实用性特征。这是在中国及韩国儒学发展中所没有的。
2.统一协调与合理竞争。日本儒学现代演变的另一成果是在注重群体统一性中适当地吸收了竞争原则。由于群体统一协调在日本具有至高无上的首要地位,因此市场经济驱动下所发生的竞争,也就成了“日本化”的竞争。结果,竞争不是个体间的行为,而是群体间的相互竞争。在大公司中,分公司之间是相互竞争的,但对大公司整体来讲,其内部又是统一的,只存在着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以此类推,这对整个县、整个国家来讲,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统一协调的。同样,在国内,公司间是竞争的,但面对国外公司,日本企业之间又是协调统一的。因此,竞争是商业行为,在道德上日本民族又是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这种协调与竞争的结合,是今日日本之所以强大的力量所在,也是世界都面临日本人竞争和挑战的儒学根源。正因为这样,资源上一贫如洗的日本却能有力量敛聚了世界上大量的财富。
3.家族纽带与权威特征。这也是战后日本儒学的重要发展。随着现代企业的出现,日本家族式的序列关系被广泛地运用于企业管理中。老板与职员的关系就如家庭中长者与幼者的关系,职员入社就如同成为这大家族的家庭成员,其目标就是“兴家致富”,忠诚、能干、耐劳,显然是得到重用的重要标志。实现这种家族纽带的是权威特征,由于日本文化外来特征分明,且基本上都实行由上至下的领导路线,因此欧美外国人或上级或资深者都成为权威,加以崇拜和捧场。通过对这种权威的认同,日本群体就非常容易获得统一协调。这种文化特征在教育上也有突出表现,其划一性就是一例。
4.“儒”“洋”并举,双重互行。儒学与西方文化有非常鲜明的对照性,但是在日本两者能巧妙结合,双重文化互动同行。这种儒学的发展要求也强烈地表现在教育中。日本儒学在演进中,每一次转变,都祈求教育创新的支撑。自9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掀起多次重大教育改革,特别是要消除过于划一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行为,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儒学的历史更新。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Shapiro-Wilk法作正态性检验,Levene法作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机械中心办公室(党办)副主任)
责任编辑:马黎
标签:日本论文; 儒学论文; 群体论文; 中国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亚洲哲学论文; 亚洲各国哲学论文; 日本哲学论文; 《创造》2019年第7期论文; 国务院国资委机械中心办公室(党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