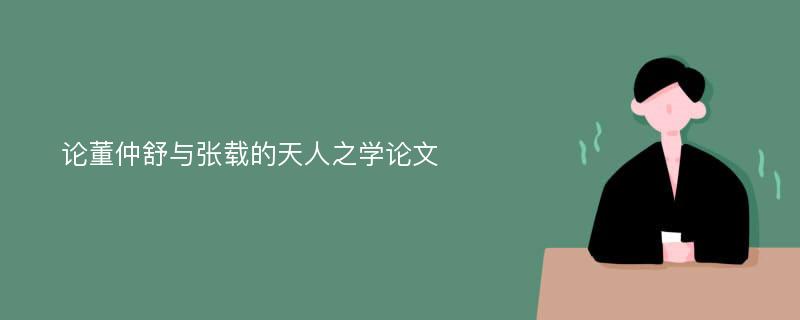
论董仲舒与张载的天人之学
林乐昌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系,陕西 西安710062)
摘 要: 西汉董仲舒与北宋张载是各自时代的儒学代言人。在儒学史上,西汉董仲舒最早提出系统的天人之学,而北宋张载则第一次使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命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建构了“天人合一”的理学体系。天论和天道论,是董、张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探究董、张的天人之学时,有必要分别考察他们二人的天论、天道论及其特色,然后梳理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从董仲舒到张载的演变脉络。
关键词: 董仲舒;张载;天人之学;天论;天道论;天人合一
本文的论题,是对西汉董仲舒(前197-前104年)与北宋张载(1020-1077年)的天人之学进行比较研究。之所以把他们二人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董仲舒与张载二人都高度关注儒家的天人之学。司马迁提出,史学家的职志是“究天人之际”[1-2]。其实,“究天人之际”也是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主题。董仲舒与张载的天人之学各具特色。他们二人站在各自时代的思想制高点,为儒学代言。在儒学史上,西汉董仲舒最早提出系统的天人之学,而北宋张载则第一次使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命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建构了“天人合一”的理学体系。我们需要把董仲舒与张载的天人之学置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他们二人天人之学的特色,并梳理他们二人天人之学的演变趋势。
第二,西汉董仲舒对北宋张载有过某些思想影响,而且张载对董仲舒也做过评价。《西铭》是张载著名的短论。其第一句强调“乾称父,坤称母”[3]62。现代海外新儒家的代表方东美曾指出,这个说法是“根据汉儒董仲舒所讲的‘父天母地’的思想,再追溯到《尚书·周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而来的[4]。无论“乾称父,坤称母”,还是“父天母地”,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董仲舒对张载的天人之学有过一定的影响。此外,张载在比较汉儒扬雄与董仲舒时曾指出:“雄(指扬雄——引者注)所学虽正当,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学差溺于公羊谶纬而已。”[3]251虽然张载评价董仲舒的言论不多,但他认为董仲舒的道德学问“博大”,因而对他是很推崇的。
材料分别为3年生的赞皇枣品种和5年生的木枣品种。其中木枣为当地传统制干品种,赞皇枣为鲜食和制干兼用品种。枣树株行距2米×3米。
第三,董仲舒与张载二人的生平活动都长期依托于关中地域。张载15 岁时,其父张迪病故于四川涪州(今重庆涪陵)。张载与母亲、弟弟扶父亲灵柩经过陕西眉县,将父亲安葬于终南山北麓之后,遂定居于眉县横渠。张载38 岁登进士第,除短暂到外地为官之外,他主要生活和讲学于关中,并创建了关学。清初,关中理学家王心敬编撰《关学续编》,其卷二新增“汉儒二人”,第一人便为“江都董先生”。在叙述董仲舒“凡相两国”之后,王心敬指出: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武帝晚年,以仲舒对问皆有明法,乃赐仲舒第,令居长安。凡朝廷建置兴革,多使使就问,或使廷尉张汤就家问之。年七十余,以寿终长安。
在这段话之后,王心敬加按语说:“仲舒先生原籍广川(今河北衡水——引者注),晚以时应帝问,就家长安,卒也遂葬京兆(今陕西西安——引者注)。今长安城中所传下马陵者即其处。其后子孙乃徙茂陵。则是仲舒老关中,卒关中,并葬关中也。”① 王心敬《关学续编》卷二《汉儒·江都董先生》,见王美凤《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并参见该书第66页)。笔者按:一般认为,董仲舒墓在西安南城墙和平门内以西600 米处的下马陵。另据北宋《太平寰宇记》卷27 记载:“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是武帝刘彻茂陵的陪葬墓。 王心敬把董仲舒纳入关学谱系并不妥当,但他指出董仲舒终老关中并安葬于关中,与关中地域渊源深厚,则是事实。
在1956年之前,科研对于茅台而言几乎是“零进展”,而在1956年,茅台意识到,科学技术实在不能忽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茅台集团的科研团队有了显著的发展,现今茅台集团科研技术团队有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5人、省核心专家2人、省管专家2人、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4人、酿酒大师5人、国酒级品酒委员和特邀品酒委员14人、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7人、中国白酒大师3人、中国白酒工艺大师3人、贵州省省级白酒评委40余人。
一、董仲舒的天论、天道论及其特色
(一)董仲舒的天论及其特色
曾经有学者把古代天人合一的模式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天人合德型:这是儒家的模式。第二种是天人为一型:这是道家的模式。第三种是天人感应型:这是阴阳家及董仲舒以气化之天为主,杂以传统的神性之天乃至世俗的神秘信仰揉而为一[23]。
无论是西汉的董仲舒,还是北宋的张载,他们二人作为各自时代的儒学代言人,天论和天道论都是他们二人宇宙论哲学和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在探究董仲舒与张载的天人之学时,将分别考察他们二人的天论、天道论及其特色,然后梳理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从董仲舒到张载的演变脉络。
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义》)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天”在他的学说体系中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对于董仲舒所论“天”之涵义,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学术界有两种影响比较大的解释:一是徐复观的“天”之“一义”说,二是金春峰的“天”之“三义”说。
张载继承《中庸》和《易传·系辞》的天道论,并兼取阴阳五行家和道家的气论,明确地把阴阳气化纳入儒家的天道理论。张载虽然综合“天”与“气”以说“道”,但他并没有把“天”和“道”都归结为“气”。在张载的话语系统中,“气”只是用以表述宇宙动能、自然元素、生物禀赋、生命活力等意涵的经验性词语,只是在生成之道的表现形式的意义上才加以使用的;“气”并不具有价值意义,更无法作为宇宙本体。清儒皮锡瑞指出:“《汉书·艺文志》‘阴阳’‘五行’分为二家。其后二家皆窜入儒家。”但这只是儒家的别传,而非正传。皮氏强调,孔子儒学与汉儒不同,“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22]18。同理,北宋的张载理学也必不以阴阳五行或阴阳之气为宗旨。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再看金春峰的“天”之“三义”说。金春峰把董仲舒讲天之意义,归结为三个方面:神灵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8]122。其一,“天”是指神灵之天。金春峰认为,这里所谓天,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主宰一切的人格神。这种说法,源自先秦以来的传统天命观。其二,“天”是指支配宇宙的道德原理。金春峰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的话来说明“天”的这一意义:“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8]123但准确地说,董仲舒这句话说的是作为道德价值的“仁”是以天为根源的。其三,“天”是指作为宇宙的总称及自然运行的规律,简称自然之天。董仲舒论自然之天的突出特点是,揭示了天的“十数”。在《天地阴阳》篇中,董仲舒指出:“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最后的“天”,指包括前面十种基本成分在内的宇宙的总称。这样的天,包含万物,广大无极,是万物的总根源。其结构表现为由阴阳、四时、五行相配合而组成的神秘的图式,而这一图式的基础是“气”或“元气”。对于“元”指“元气”,金春峰的看法与徐复观是一致的。金春峰认为,董仲舒所讲的气,是神秘化了的,但其基本性质则仍是一种物质实体。对于董仲舒“天”之三义之间的关系,金春峰指出,三种“天”在原则上是可以统一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矛盾,例如,自然之天既然是由气构成的,那么,它何以会具有道德的属性?[8]129值得注意的是,后来余治平比较重视董仲舒以“天”作为道德价值根源的意义。他引用的董仲舒这方面的言论主要有:“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6]289
综上所述,与徐复观的“天”之“一义”说相比,金春峰的“天”之“三义”说比较全面。徐的说法突出了董仲舒的自然之天,这与孔孟儒学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余治平则强调董仲舒对“天”的道德价值的根源意义。这是对金春峰论说董仲舒道德之“天”的重要补充。
(二)董仲舒的天道论及其特色
张载“理学纲领”的第二句是“由气化,有道之名”。此“由”字,与第一句“由太虚,有天之名”的“由”字一样,也是借用的意思。古今不少学者都把“由气化,有道之名”这句话中“道”的意涵归结为“气”或“气化”。张载对“道”的界定,的确借助了阴阳家和道家的气或气化。问题在于,借用气化的主体是谁?只能是上一句的“天”。《中庸》第20 章曰:“诚者,天之道。”认为“道”是归属于“天”的。《正蒙》的第三篇的篇名为“天道”,也正是此意。认为“天”高于“道”,这是儒家天、道关系理论的传统① 李泽厚认为:“儒道两家的差异在一定意义和范围内表现在‘天’‘道’这两个范畴的高低上。”在道家,“‘道’高于‘天’;儒家则相反,‘天’高于‘道’”。参见李泽厚《荀易庸纪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朱熹解释“由气化,有道之名”说,“道”“虽杂气化,而实不离乎太虚”[10]1430。可见,“道”既不可单独归结为“气”或“气化”,也不可单独归结为“天”或“太虚”,它是“太虚”与“气”的统一体。就张载的“天道”概念看,它具有一本(以天或太虚为本体)、两层(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两个层次)、三合(天或太虚与阴气、阳气三者整合)的特征[12]45。可见,在张载理学纲领“天”“道”“性”“心”四大概念序列中,“气”仅仅是辅助性概念,不宜将其拔高为张载天道论的首要概念。把“气”视作张载哲学体系中的本体概念或最高概念,无法从张载的“理学纲领”或其他理论学说中获得支持。
二、张载的天论、天道论及其特色
有明确的“理学纲领”作为强有力的支持,是张载天论和天道论的重要特色。
在《正蒙·太和篇》中,张载提出:“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3]9可以把这四句话简称作“《太和》四句”。朱熹高度评价“《太和》四句”,指出:“‘由太虚,有天之名’至‘有心之名’,横渠如此议论,极精密。”[10]1432
多年前,笔者曾提出以“《太和》四句”作为张载的“理学纲领”[11-12],但当时尚缺乏支持这一判断的文献依据。随着张载理学新文献的发现及整理,问题得到了解决。北京中华书局版《张载集》外佚著《礼记说》辑本,是张载理学新文献之一。依据《礼记说·中庸第三十一》发现,“《太和》四句”原来是对《中庸》首章前三句的解说[13]。朱熹认为,“读书先须看大纲”,如《中庸》首章前三句,便是“大纲”[10]1480。朱熹所谓“大纲”,与这里所谓“纲领”语义相同。作为解说《中庸》纲领的张载理学新文献《礼记说》,为还原“《太和》四句”的语境提供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文献资料,使“《太和》四句”作为张载“理学纲领”的性质和地位得到确证。同时,“《太和》四句”中所涉及的“天”“道”“性”“心”四大概念排列有序,界定清晰,能够充分展现张载天人之学体系的特征。任何一种学说中的纲领性论述,远比其一般性论述来得重要,因而在研究中应当格外倚重其纲领性论述。
CT诊断和磁共振成像都是当前诊断腰椎间盘突出较为常见的方法,经临床实践证明,两种方法都有较高的诊断准确率。但是从此次研究结果来看,相对而言磁共振成像在诊断准确率上更占优势,但是从具体征象的诊断上来看,二者对不同征象诊断各占优势。
(一)张载的天论及其特色
第二,从“用”的向度考察张载“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特色。广义地看,“知天”也包括“知天道”。张载曾说,他撰写《西铭》的意图,就是“只欲学者心于天道”[3]313。张载批评佛教“不知本天道为用”,主张“得天而未始遗人”。如何“本天道为用”?考察张载的有关论述可知,这需要经由个人修养的实践、社会治理的实践和人类参与自然生成过程的实践等多种途径。
(二)张载的天道论及其特色
在董仲舒之前,儒家绝少讲阴阳五行,绝少讲阴阳之气,也没有把阴阳之气与天道联系在一起。董仲舒是儒家重视讲阴阳五行或阴阳之气的开端,其《春秋繁露》关于阴阳五行的论述是春秋战国以来儒家著述中最为系统、最为详尽的。说董仲舒哲学体系的特点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可能也不为过[6]4,[8]4。就董仲舒的天道论而言,可以说也是以阴阳之气为基础的。董仲舒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1]2502可见,他主要是以阴阳说天道的。徐复观曾对《春秋繁露》各篇的要义做过仔细的分析。他认为,自《离合根》篇第十八起,以下的四十一篇,“皆以天道的阴阳四时五行,做一切问题的解释、判断的依据”[7]192。首先,关于天道与阴阳的关系。董仲舒认为天道与阴阳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包括阴阳对立、阴阳消长、阴阳转化、阴阳中和等四个方面① 陈福滨对天道与阴阳之间四个方面的关系,分析得很细致。参见陈福滨《董仲舒的天道思想与天人关系》(陈福滨《智与思:陈福滨哲学论文自选集》,台北辅大书房2016年版,第250-254页)。 。其次,关于天道与四时、五行的关系。众所周知,孔子最早以四时言天道之运行,但未言及四时与阴阳的配合;《易传》以阴阳言天道之变化及其机制,但未言及阴阳与四时的配合;至邹衍,在其有关阴阳五行的言论中,还看不出阴阳五行与四时的关系。直到《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才开始以四时为中心,并把阴阳、五行与四方配合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董仲舒则综合孔子、《易传》、邹衍、《吕氏春秋》之说,把阴阳、四时、五行与四方构造成更紧密的整体[9]。
第三代路虎发现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中型SUV,4.8米的车身长度配合上仅用直线和直角勾勒出的轮廓,它所具备的阳刚气质让SUV概念重新回归到了原点。
张载综合了儒家之“天”与阴阳五行家、道家、汉儒之“气”,为儒家天道论注入了气论内容。孔子、子思、荀子曾言及自然天道,但却都不曾言及自然生成之气。张载重构儒家天道论,除借鉴道家思想资源之外,所依据的儒家经典资源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庸》所谓“天之道”。张载依照《中庸》“道”归属于“天”的定位,在其理学“四句纲领”中明确将“道”置于“天”之下。二是《易传·系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据此,张载以阴阳及其作用机制说道,并兼以道家和汉儒的“气化”说道,从而提出“由气化,有道之名”。所谓“阴阳”,起于西周晚期,是数术的别名,属后世堪舆地形家之事,其基本涵义是光明和黑暗[17-18]。至战国时期,开始讲求天之气,而不再讲求地之形。这是“阴阳”的另一套说法[19]。汉儒普遍受阴阳家影响,喜用“气”解释一切。傅斯年指出,阴阳之教,五行之论,渊源于战国晚期的齐国,后来这一派在汉代达到极盛[20]。余英时也指出,“‘气’这一概念并非汉代思想家的发明”,但“‘气’的观念在思想史上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则是在汉代”[21]。清儒皮锡瑞针对汉儒指出,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并据此认为,汉儒只是孔子儒学的“别传”,而非“正传”[22]18。从历史脉络看,无论是先秦孔子儒学,还是北宋张载理学,都必不以阴阳五行或阴阳之气为宗旨;其间惟汉儒之学作为孔学的别传则是例外,后来还成为明清气学的理论源头之一。
先看徐复观的“天”之“一义”说。徐复观认为,董仲舒完成了“天”哲学的大系统。他认可《汉书·五行志叙》用“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评价董仲舒。徐复观强调,按照董仲舒的意思,天之端来自《春秋》之元,而元实际是元气之元[7]218-219;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四时之气,认作“天”的具体内容;而且他还认为,阴阳二气是天的基本作用[7]182。
三、天人合一:从董仲舒到张载
(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念
对于天人合一观念,董仲舒曾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说法。虽然他还没有明确使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但天人合一观念在其学说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按照徐复观的分析,董仲舒把历史、人事与天连接在一起,是通过两条线索实现的:一是夸大“元”的观念,二是加强灾异的观念[7]217。在董仲舒那里,实现天人合一的机制是“感应”。有学者正确地指出,董仲舒是感应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其学说中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天人感应系统[6]5。天人以感应相合,其中包括以类相合、人副天数等方式。董仲舒还用“祥瑞”“灾异”作为天人感应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董仲舒天人之学的特点是灾异论的天人感应,或天人感应的灾异论[5]27,80。当然,董仲舒所谓灾异论的天人之学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就是要限制君权,把权力运作纳入正轨。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2498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在与诸侯国王对话时常以“臣”自称,并称对方为“王”,而对于类似称谓词的翻译中,很多译本将“臣”普遍译为I,对“王”的翻译则是利用多重译法。然而,也有大一部分译者将“王”译为you,这样的译文无法体现出君臣间严格的上下等级关系,导致译文没有办法突出原作的真实语境及情感。因此,可以将“臣”译为your subject,将“王”译为Your Majesty,这样的翻译能够充分体现出特殊语境下谈话双方明确的等级关系,弥补英译中称谓词人际功能的缺失。
多数研究汉代儒学的学者都承认,“天”是董仲舒儒学体系的最高原则[5]。甚至有学者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董仲舒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第一次建构出天的本体系统”“天,是董仲舒思想体系运转的轴心所在”“董仲舒之学是天学”[6]3。
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念纳入以上第三种“天人感应型”,大体是不错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天人合一观念就完全没有“天人合德”的内涵。董仲舒说过:“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还说:“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而博,惟人道为可以参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的这些论述,就应当属于“天人合德型”的天人合一观念① 周辅成、余治平都承认,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当中含有道德的天人合一成分。参见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8-99页);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9页。 。
(二)张载的“天人合一”命题及其思想
轴心时期(孔子时代)的天人合一观念开始从王权垄断向个人转型,从而使这一观念向所有追寻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个人开放[2]119,138。与转型期的方向一致,张载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命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对这一命题做了明确的界说。在张载理学纲领中,他首先确定“天”在宇宙中具有至高无上的超越地位,从而为儒家重塑天观;同时,他还为自己的理学纲领引入“心”这一概念,强调人的精神能动作用,从而激活了人体悟“天”这一宇宙最高存在的心灵活动。这就为他所明确提出的“天人合一”和“事天诚身”境界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在《正蒙·乾称篇》中,针对佛教“诚而恶明”的倾向,张载强调指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3]65这一界说,着重从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角度为儒者提出实现“天人合一”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所依据的经典除了《周易》经传之外,显然对《中庸》更加倚重。不难理解,《中庸》对张载的学术生涯曾经产生过特别的影响,也包括对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24]。上引张载所说“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来源于《中庸》21 章“自诚明”“自明诚”的学说。此外,张载依据《中庸》25 章所谓“诚”者“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的表述,将“合内外”确立为实现“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仍与《中庸》有关,张载还从另一角度对“天人合一”思想做了重要的补充说明。他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3]20这表明,张载强烈反对在“用”和“知”这两个向度上使天人关系发生背离。这就启发我们,应当从“用”和“知”这两个向度全面考察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
第一,从“知”的向度考察张载“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特色。《宋史》张载本传说他“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张载在论述天道性命相贯通时指出:“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知人知天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同意。”[3]21,234清初理学家冉觐祖注解“天人异知”说:“知人而不知天,是谓‘天人异知’。”[25]如果人能够“知天”,便意味着天人不再“异知”。在张载看来,“知天”比“知人”更根本。张载批评秦汉以来儒者“不知天”,是指他们对“天”的理解出现了偏误。这表现为,把原本超越的宇宙本体之“天”实然化、经验化了。张载反对“姑指日月星辰处,视以为天”[3]177,他批评说:“‘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苍苍之形也。”[3]12强调不能把“天”理解为苍苍之天,而应当理解为支配自然界的义理之天。他还告诫学者:“气之苍苍,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当以心求天之虚。”[3]326这是说,已少有儒者能“以心求”超越的宇宙本体之天了,更多的情形是以耳目感官把握由气构成的“苍苍”之天。
对于《中庸》首章前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古今学者多看重其中由“性”“道”“教”三个概念组成的序列。而张载却特意把《中庸》首章第一句第一个字“天”纳入其概念序列,并置于首位,将《中庸》由“性”“道”“教”三个概念组成的序列,改造为由“天”“道”“性”“心”四个概念组成的序列。后来,朱熹解读《中庸》首章前三句说:“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其本皆出乎‘天’。”[14]这与张载的思路若合符节。张载以道家“太虚”概念释“天”,是为了纠正秦汉以来儒者“知人而不知天”的“大蔽”[15],重建儒家“天”观。“由太虚,有天之名”句中的“由”字,有“自”“从”“因”等义,其引申义为依据、凭借。在此句中,当以“借用”释“由”字[16]。在张载看来,秦汉以来儒者把原本形而上的超越之“天”有形化、实然化、经验化了;而道家的“太虚”概念则具有非实然性、超验性、无限性等优点,因而有必要借用道家的“太虚”概念以改造被汉儒实然化和经验化了的“苍苍之天”,从而使“天”重返超越和神圣的本体地位② 张载为何以道家“太虚”释“天”,如何诠释“天”或“太虚”的意涵?参见林乐昌《论张载理学对道家思想资源的借鉴和融通——以天道论为中心》(《哲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38-40页)。 。
总之,“天人合一”是张载天人之学体系的总体性命题,既具有道德修养实践意义和精神境界意义,也蕴涵了对社会秩序和自然伦理的诉求,是儒学史上天人之学的重要理论源头。当然,张载所谓“天人合一”,不可能自发地在个人修养、人间社会和自然生态中变为现实。因此,这一观念主要用以昭示人们:只有经由不懈的修为和实践,人类才能够在精神领域、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逐步趋近这一理想境界。
四、结语
董仲舒与张载的天人之学既有共同之处,也各具特色。他们二人思想体系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都使用了“天-人”框架,也都有突出的天人合一观念,并程度不同地坚持了儒家的道德价值。他们二人都使儒学形态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他们的学说称为“新儒学”。虽然二人的学说都可以被称为“新儒学”,但他们二人的儒学思想又的确具有多方面的差异。
第一,董、张二人各自倚重的经典不同。董仲舒倚重的经典是《春秋》,而张载倚重的经典则是《易》《礼》。
在统计综合评价中,权重的大小反映了评价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权重越大则该指标的重要程度越高,对整体的影响就越大。反之权重越小则该指标的重要程度越小,对整体的影响越小。对汾河流域节水灌溉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时,体系中指标的权重直接影响到节水灌溉发展水平评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选择合适的指标权重计算方法至关重要。
忽然看到一个白白净净的馒头放到乞丐的碗里,我抬头一看,原来正是杨公子,他温蔼地对乞丐说,别饿着。乞丐赶紧答谢他。
第二,董、张二人的天论不同。董仲舒的天论,主张“天之数”为十,其天具有复杂的结构。而张载所谓天,是宇宙之间的最高实在,是“至一”[3]325的主导力量。“至一”,亦即唯一。张载之天,作为宇宙间唯一的最高存在,是没有内在结构的。董仲舒的天论,更强调的是天的自然意涵,气的意味比较重;但张载突出的则是天对宇宙的主导作用,以及天是一切道德价值的终极根源。
第三,董、张二人的天道论不同。他们二人的天道论,都重视阴阳之气,但阴阳之气在二人各自的天道当中的地位不同。董仲舒主张“天道之大者在阴阳”,而张载则提出“太虚即气”命题,认为天道是由太虚(天)本体与阴阳二气这三方面构成的统一的宇宙生成力量。与董仲舒不同,张载主张,天道之大者在天,而不在阴阳。
第四,董、张二人的天人合一观念不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强调以“感应”而合。因而,张亨将其归结为“天人感应型”的天人合一。这种“天人感应型”的天人合一主要是政治论的,亦即灾异论和天谴论的,其用意是制约王权。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念除了有其政治性质之外,其实也含有道德的天人合一的成分。董仲舒这种天人合一主要是通过“感应”机制发挥作用的。在天人合一观念上,张载则回避自然“感应”论,强调道德工夫论,主张天与人必须经由主体的诚明工夫才有相合的可能。除了工夫论之外,张载的天人合一观念也涵盖精神境界论以及信仰论和政治论的意涵。张载天人合一的信仰论和政治论的意涵,主要表现为他对“事天爱民”[3]76的诉求。天人之学当中的天论与天道论,是一种宇宙观。对于宇宙观的形成能够起关键性作用的,是掌握抽象知识和思维方式的能力[26]。张载的抽象思维方式,显然超越了汉儒偏于感性的阴阳五行思维方式。
综合前人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可采用Ba、U、TH、Cr、Zr、Sc、La等指标判别。据研究,Ba、As、Sb、Sc元素富集是典型热水成因标志[5、29]。本文硅质岩Ba、As、Sc含量相对于沉积岩丰度[30]亏损,而Sb富集,即不具备典型热水沉积特征[31];另一方面,Ba富存于生物大量繁殖的海域。经对比发现,广西晚古生代单纯生物成因的硅质岩相对该地区热水成因的硅质岩含有较高的Ba[14-15,18]。本文硅质岩Ba含量较高,平均334.07×10-6。结合主量元素分析结果,亦可说明硅质岩符合生物成因的判定。
总之,从西汉的董仲舒到北宋的张载,他们的天人之学都对儒家学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应当看到,他们二人的天人之学之间毕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导致了儒家天人之学的一次大的历史转折。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4]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302.
[5]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
[6]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 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增订第3 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9]陈福滨.智与思:陈福滨哲学论文自选集[M].台北:辅大书房,2016:255-259.
[10]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林乐昌.张载两层结构的宇宙论哲学探微[J].中国哲学史,2008(4):78-86.
[12]林乐昌.论张载理学对道家思想资源的借鉴和融通——以天道论为中心[J].哲学研究,2013(2):38-46,108.
[13]张载.张子全书[M].林乐昌,编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4]朱熹.朱子全书:第6 册[M].黄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6.
[15]脱脱.宋史:第36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724.
[1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75:69.
[17]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83.
[18]李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6.
[19]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85-287.
[20]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史学方法导论·史记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7.
[21]余英时.东汉生死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1.
[22]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23]张亨.思文之际论集:儒道思想的现代诠释[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279-280.
[24]林乐昌.论《中庸》对张载理学建构的特别影响[J].哲学与文化,2018(9):13-39.
[25]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287.
[26]伦纳德·蒙洛迪诺.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M].龚瑞,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48-49.
Dong Zhongshu's and Zhang Zai's Theories of Heaven and Man
LIN Lech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2,China)
Abstract: Dong Zhongshu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Zhang Zai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re the spokesmen of Confucianism in their respective times.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Dong Zhongshu was the first thinker who put forward the systematic theory of Heaven and man,while Zhang Zai first used the phrase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put forward it clearly as an ideological proposition,and then he constructed the Neo-Confucianism system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The concept of Heaven and the principles of Heaven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Dong Zhongshu's and Zhang Zai's theories of Heaven and man.Therefore,in exploring their theories,it is necessary to respectively research their concepts of Heaven and their principles of Heaven as well as their characteristics,and then sort out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from Dong Zhongshu to Zhang Zai.
Key words: Dong Zhongshu;Zhang Zai;theory of Heaven and man;concept of Heaven;principles of Heaven;unity of Heaven and man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9.05.004
作者简介: 林乐昌(1949-),男,山东威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ZX012)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5-0016-07
收稿日期: 2019-07-10
(责任编校: 卫立冬英文校对: 吴秀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