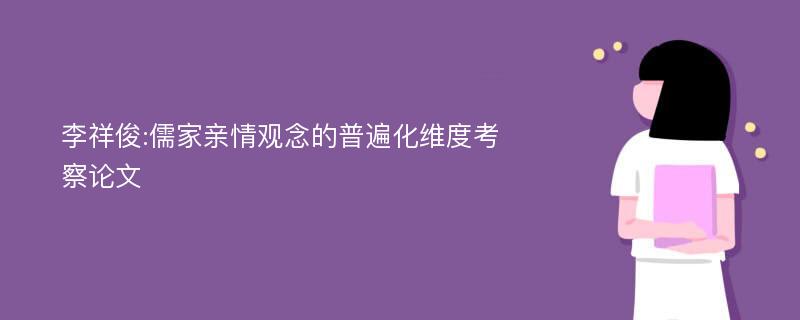
[摘要]儒家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个体与全体、整体的矛盾关系,它以伦理生活、道德实践为基础,追求情感融通的实质普遍性,而不同于侧重理性认知的形式普遍性。儒家以亲情为根本展开其情感普遍化维度,本体意义的情感普遍性是亲情显现的依据,而全体意义的情感普遍性则是亲情显现的结果,共同构成一个本体即全体的融通为一的情感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儒家以亲情为根本建构起了一个情感普遍化的纵贯融通模式,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秩序、理智认知模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亲情观念的普遍化维度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情感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整个生活世界,今天仍然是我们探索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思想前提。
[关键词]儒家;亲情;情感普遍性;纵贯融通模式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人生在世,情感是基本的存在形态,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根本性的地位,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情之义大矣哉!但何谓情?情中以何为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学派也有不同的理解。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的主导思想,它对于情有自身独特的理解方式和价值判断,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对亲情的理解和对亲情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儒家思想是奠基在亲情的大地上的。从个体生命的本源性的情感——亲情出发,走向普遍性的存在,实现人与世界的融通为一,这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理解儒家的亲情观念,反思儒家亲情观念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用、意义,对于理解儒家思想极有意义,对于自觉不自觉浸润在儒家思想传统中的现代中国人理解自我、理解他人、理解社会人生以至理解宇宙万物的存在本真都极有意义。
蒋大伟把车停在宏达公司门口,郑馨突然又变卦了:我不想去了!蒋大伟吃惊地:你不想要钱了?郑馨说:我不想见到那个主管!蒋大伟耐心地:是他们欠你的,你应该理直气壮才是!郑馨犹豫了一下,慢慢腾腾下了车。两人走到传达室门口,门卫问:你们找谁?蒋大伟努努郑馨,郑馨说:我找……组装科主管王运丰。门卫拿起电话:王主管吗?门口有人找你!一个女孩!叫什么名字?郑馨犹豫了一下:郑馨。门卫:她叫郑馨,好好。门卫放下电话:王主管叫你到他办公室去。
一、两种超越路径与儒家亲情论的哲学意义
冯友兰先生在论述宋明道学时,从比较哲学的视阈提出了哲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他说:“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是某一种的个体,它必定有些什么性质。不可能有一个没有任何性质的个体。个体是一个殊相;它的性质就是寓于其中的共相。所以,在每一个体中都有殊相和共相的矛盾,这是一种矛盾。每一个体既然是一个个体,必定认为他自己是主体,别的东西都是客体。这是又一种矛盾,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在哲学中,对于上面所说的那个事实,有三个对待的路子:本体论的路子,认识论的路子和伦理学的路子。”[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三松堂全集》,第10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冯友兰先生提出殊相与共相、主观与客观两对矛盾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两对矛盾关系中,他实际是以殊相与共相的矛盾关系为主导的,因为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关系的解决正是奠基于殊相与共相关系的解决,只有达到共相,才能打破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隔阂,实现主、客的统一。在解决作为殊相与共相、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关系的古今、中外哲学家中,冯友兰先生以柏拉图为本体论路子的代表、康德为认识论路子的代表,而以朱熹等道学家、儒学家为伦理学路子的代表。
冯友兰先生的这个论述是很有意义的,他把哲学看作是具体的个人走向与天地万物的共同性合而为一的过程,而且把伦理学的路子作为中国哲学的特色,这也是很有见地的。但我们对冯友兰先生的上述论述也有异议,这个异议即在于如何看待“共相”与个体,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新理学》等著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个体是指具体的人和事,而他所谓的“共相”是指统摄万事万物的普遍性的理则,他用来作为哲学根本问题的共相与殊相的矛盾关系实际上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了认识论路子上去了。冯友兰先生虽然提出哲学家解决这个问题的三种基本思路,但他所谓的本体论的路子、伦理学的路子其实都是认识论的路子的变形,都可以归结为认识论的路子,认识论是认知其理,本体论是关于概念原理的理则世界,伦理学是认知其理基础上关于伦理秩序、道德实践及其精神境界的论述。
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三个路子,主要是接着西方哲学传统而言的,尤其是接着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一线的西方正统派哲学而言的。用这种殊相与共相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来理解西方传统哲学是较为合适的,但用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根本问题并不在认知意义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关系,而在解决个体与全体、部分与整体的矛盾关系,为人的存在提供安身立命之地。从解决个体与全体、部分与整体的矛盾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出发,则认知的路径固然不可少,但情感的路径更为重要,只有从情感的层面打破个体的局限走向与天地万物的融通一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注]《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页。才算得上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提出两种普遍性的概念,即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形式的普遍性和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实质的普遍性[注]本文关于形式的普遍性、实质的普遍性的划分,在古今、中外哲学家的论述中也有相近似的论述,如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提出“两种真理以及其普遍性之不同”,近现代德国现象学哲学、哲学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斯·舍勒批评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而提出“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他们都看到了认知基础上的形式的普遍性对人的现实的情感生活、道德生活的遮蔽,在注重普遍性的实质内容上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思想启示,但本文注重探讨儒家情感尤其是亲情的普遍化维度,在思想起点和终极关怀上都有自己的思考。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2页;马克斯·舍勒著,倪梁康译:《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34页。。以希腊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所追求的普遍性,它以人对普遍规律、理则的认知为基础,注重解决具体事物与普遍理则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其达到的结果是一种形式的普遍性。而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普遍性,它以人对全体即整体的存在本身的情感感应为基础,注重解决个体的人与作为全体、整体的宇宙大全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其达到的结果是一种实质的普遍性。
软管都取出来了,王姐还不死心,缠着段主任说:您别放弃呀,求您再给试试呗。段主任摇头说:没必要了。王姐说:那总不能让我妹夫这样过一辈子吧?您再给想想别的办法。段主任说:我这是没办法了,你转到胸外科,看看他们有没有好办法吧。王姐说:成,胸外科我也有熟人,您估计他们有什么好办法?段主任说:开胸。
在讨论儒家情感普遍性问题时有必要对儒家的恻隐概念作出辨析,孟子把恻隐等看作是仁本体的发端,而且是人的源初性、基础性的情感,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注]《孟子·公孙丑上》,杨伯峻:《孟子译注》,第79-80页。分析孟子这段话,一方面,从本体的视角看,恻隐和孝悌等亲情一样都是仁体的显现,都是具体的情感;另一方面,从全体的视角看,恻隐和孝悌等亲情都是具体的情感但在表现形态上又有所不同,亲情是最近的、最厚的人与人的情感,而恻隐是最远的、最薄的人与人、人与物的情感。儒家在论述具体情感时,突出人的情感中最厚、最源初的亲情和最薄、最基础的恻隐这两个极端,其他的中间性具体情感就不言自明了,这样就把现实的具体情感表现都包容性地论述了。儒家标志情感普遍性的概念是仁,恻隐不是本体意义上的内在的情感普遍性,也不是全体意义上的外在的情感普遍性,但和亲情、友情、爱情等比较起来,它所涉及的范围最宽,可以把包括陌生人、陌生事物在内的所有人、事都纳入到人的情感生活的领域,但恻隐并不能代替亲情、友情、爱情等,它只是和亲情、友情、爱情等并列的但涵盖范围较宽泛的一种具体的情感而已。亲情、友情、爱情、恻隐等都是具体的情感,而情感的普遍性正是要在这种具体情感之间融通为一,只是这种融通为一的方式应该是建立在类比推理基础上的感应、感通,各种具体情感之间并不能通约,这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可以作形式逻辑推论的形式的普遍性大不相同。中国传统没有形成像西方思想中那样一套形式化的理论系统,其中固然有理论思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所处理的问题不同,所要达到的超越的普遍性不同。
寻求普遍性是哲学的目标,寻求情感的普遍性可以说是儒家哲学的目标,那么儒家思想中的情感普遍性究竟是什么意义?从亲情到情感的普遍性何以实现?我们认为,儒家的情感普遍性可以从本体、全体两个层面加以把握,而亲情的普遍化维度正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弟子有若关于仁、孝关系的论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讨论儒家情感普遍性的意义及亲情在实现情感普遍性上根本地位的基本依托材料。
二、儒家情感普遍化的两重维度与亲情的根本地位
而在儒家学者看来,要实现从具体的特殊的情感达到情感普遍性的目标,则只能是从人的最切身、最本源性的情感入手来走向普遍性,这个最切身、最本源的情感就是以父子之间的孝为中心的亲情。人在世界之中生存,总是有其具体的生存境遇,在儒家看来,亲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道德情感构成了人生最初的“被抛”,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儒家哲学从亲情入手,打通人类情感之间的普遍性,进一步由此打通天地万物的一体感应之情,从而使人的生命在宇宙论、终极存在层面达到永恒,北宋大儒程颐和他的弟子尹焞对此有深刻体会:“鲍若雨、刘安世、刘安节数人自太学谒告来洛,见伊川,问:‘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尧、舜之道,何故止于孝弟?’伊川曰:‘曾见尹焞否?’曰:‘未也。’‘请往问之。’诸公遂来见和靖,以此为问。和靖曰:‘尧、舜之道,止于孝弟。孝弟非尧、舜不能尽。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以至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非尧、舜大圣人,不能尽此。’复以此语白伊川,伊川曰:‘极是。纵使某说,亦不过此。’”[注]《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31页。在程颐、尹焞等儒家学者看来,孝悌等亲情是人生之本,将其扩充就可以上达天德、天道,这和西方主流的认知型哲学传统在目标、路径上都有重要区别,而这正是儒家亲情论的哲学意义所在。
应同时考虑发生滑坡灾害时的间接经济损失,国土资源部[18]统计得出的滑坡灾害间接经济损失为直接经济损失的1.1倍。由此可以确定滑坡灾害损失值为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总和。
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的论述从共时性的当下对亲情等具体情感的产生作出了论述,他曾与学生讨论三年之丧的存在依据问题,“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注]《论语·阳货》,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88页。孔子认为三年之丧的依据在人心、人情,人在为父母守丧期间的这种不甘、不乐、不安的情感是所有有家庭生活的人自然会产生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这就是亲情。孟子则从人类生活的时间性、历史性的角度探索了亲情等具体情感的历时性发生过程,“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蘽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注]《孟子·滕文公上》,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5页。孟子认为,最初人们并没有形成埋葬父母等亲人的习俗,把亲人死后的遗体扔到荒郊野外,但后来看到亲人尸体受到侵害的悲惨状况,内心受到极大冲击,顿然产生出恐惧、怜悯的不忍之情,这就是亲情。而孔子、孟子关于亲情的描述,如不甘、不乐、不安、不忍等都是人的内在的仁的显发,就此而言,亲情即仁,具体即普遍,没有情感普遍性的内在依据就没有包括亲情在内的具体情感可以显现。
北宋大儒程颢在解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时,把孝看作是人类道德情感的基础性概念,而把仁看作是人类道德情感的本体性概念,是包括孝等亲情在内的人类所有道德情感可能发生的内在依据,认为孝不是仁的根本,而是行仁的根本,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注]《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125页。从仁作为本体意义上的情感普遍性而言,它是内在于人心的,可以称为内在的情感普遍性,这种意义上的情感普遍性在时间和逻辑上都是优先于具体的亲情的,但却有待于亲情等具体情感将其实现出来,而在具体情感中尤以孝等亲情最为根本。
人的情感世界是无限丰富的,但在儒家看来,它的起点却是人类最切身、最本源性的亲情,有亲情作为起点,人的情感生活才能真实地展开,形成包括亲情在内的各种情感的总和体,这个总和体不是一团混沌,也不是简单的平列,而是构成一个差异一体的秩序体,孔子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注]《论语·学而》,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5页。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注]《孟子·尽心上》,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22页。我们对其进行分析概括,可以说在这个差异一体的情感总和体中,亲人之间的关系是最近的,情感也是最厚的,而与他人、他物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是疏远的、薄的,近的、厚的是亲情,远的、薄的则是同情、恻隐。从儒家的视角来看,以亲情作为原点划分亲疏远近的圈子,可以对人的情感从总体上概括为两大类:1.奠基于血缘、家庭基础上的亲情系列,最根本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慈、孝之情,其次是夫妻之间的恩爱之情,再次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友、悌之情,最后是扩展到家族、宗族成员之间的友爱感情;2.奠基于非血缘、非家庭基础上的非亲情系列,最根本的是君、臣之间的礼待之情、忠诚之情,其次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友情、同情,再次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恻隐、同情。
(2) 太原地区地层性质更接近软土地层,基坑桩(墙)体水平位移监测,应以管顶为起算点,并将对应墙顶水平位移值代入进行修正。
作为本体的仁是人心内在的情感普遍性,作为全体的仁是人伦、事理外在的情感普遍性,而在儒家有机整体、道德创生的宇宙论视阈中,作为本体的仁就体现在包括亲情在内的具体的道德情感之中,而本体之仁的完满实现就是包括亲情在内的所有具体道德情感的完满显现,从终极层面上说,本体即全体,本体是体,全体是用,即体即用,体用不二。明代大儒王守仁对以亲情为基础的这种本体即全体的情感普遍性及其实现有深刻、细致的论述,对从出于仁本体的亲情出发推扩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仁爱全体的情感普遍性路径作出了细致、深刻的论述,他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注]《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969页。我们把王守仁关于从亲情出发达到情感的普遍性的路径进行梳理,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从孝悌等亲情推扩到对一般人的友爱之情,再推扩到对天地万物的同情,构成了一个差异一体的情感普遍性的全体。外在情感普遍性是以内在情感普遍性为依据展开的,它本身是标志全体性、总和性的概念,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同情等各种具体情感都在“浑然与物同体”的情感普遍性中共同存在,各各相通,又各不相碍,秩序井然,构成一个普遍联系的情感共同体网络。
儒家除了论述亲情系列以外,还有一个关于非亲情系列的情感普遍化存在,这就是政治上的君臣之间,社会政治上的同僚、同事之间,社会上的一般他人之间,人与自然事物之间,这是其中主要的几种情感关系。在儒家思想中,奠基于非血缘、非家庭基础上的非亲情系列深受亲情系列的影响,成为一个泛亲情或者叫拟亲情系列。非亲情系列中最基本的情感关系是君臣之间的礼待之情、忠诚之情,君臣之间的情感关系往往被比附为父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君臣之间就变成了君父与臣子之间,形成一种拟亲情的纵贯情感,由臣向君,由天子向天,将这种拟亲情关系上升到最高存在的层面,“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2、705页。政治上的同僚之间、社会上的同事之间,也模拟亲情中的兄弟姐妹之情,而构成一种横摄的友爱的情感关系,但因为都受制于最高的君权,因此也将这种友爱之情转化为兄友弟悌式的纵贯模式,“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注]《孝经·广扬名》,胡平生:《孝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页。人与陌生他人的关系本来是横摄的恻隐、同情关系,但在差异为本的传统伦理观念主导下也会逐渐差异化,形成一种长幼有序的纵贯模式。至于人与自然物之间本来是一种恻隐、同情关系,但人为万物之灵,因此人与自然物的情感关系也呈现出一种以人统物的纵贯模式。
追求情感普遍性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儒家哲学从一开始就偏重于情感,它的知识学、认识论和意志问题都是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而儒家最关心的,正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情感,并且形成与此相关的宇宙论、本体论哲学。”[注]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第14页。从哲学是解决具体与普遍性之间矛盾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出发,情感论具有不同于认知思维的独特的实现方式,情感对达到普遍性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三种路径都具有统摄性的影响,这与同样具有统摄性的认知的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情感型的哲学解决的具体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具体个体与宇宙全体、整体的关系,它通过具体的特殊的情感的推扩来实现情感的普遍性,达到个体与全体即整体的宇宙大全的统一。情感的普遍性的获得需要通过扩充人的具体的情感体验来达到,这种扩充过程伴随着认知理性,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非侧重概念语言、形式逻辑推理的过程。宋明新儒学中程朱理学侧重“格物致知”、王守仁的心学侧重“致良知”,其所谓的“知”都是情之知、情之达基础上的精神活动,实质都是要在人伦实践中达到情感的普遍性,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融通为一。
三、儒家以亲情为基础的情感普遍化的纵贯融通模式
本体与全体构成儒家情感普遍化的两重维度,儒家的作为宇宙、人生本体的仁并不在现实世界之外,而就在现实世界之中,本体即全体,本体是宇宙内在的大生命,全体是宇宙一切存在的总和,作为本体的宇宙大生命就体现在宇宙万物之中,而宇宙万物的总和正是宇宙大生命的全体大用。从这种本体即全体的视阈看,现实的作为全体的宇宙、人生的情感普遍化才是儒家亲情观念普遍化的真实内涵,这就是儒家亲情在现实世界中的融通方式。儒家以亲情作为现实世界中情感普遍化的根本,这个根本在向全体世界推扩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独特的融通模式,从而使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现实情感世界呈现出内在的脉络,形成儒家情感逻辑下的价值秩序、存在法则,深刻地制约着传统中国人的情感显现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
东汉大儒延笃在解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时,把孝看作是人类道德情感的基础性概念,而把仁看作是包括孝等亲情在内的人类所有道德情感的总体性概念,因而认为孝是仁的根本:“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注]《后汉书》,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4-2105页。从仁作为全体意义上的情感普遍性而言,它是超越具体的人心而体现在所有的人伦、事理之中的,可以称为外在的情感普遍性,这种意义上的情感普遍性在时间和逻辑上都是后于具体的亲情的,它是有待于亲情等具体情感的实现才能够最后达到的结果,而在具体情感中尤以孝等亲情最为根本。
儒家亲情以家庭为基本依托,就秦汉以降家庭本位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社会的基本形态而言,三代以内、六七口之家构成了这种社会形态的最基本的细胞单位[注]一般来说,亲情是亲人之间产生的自然情感,而关于亲人的定义,就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来说,主要指以血缘、婚姻为基础的同居共财的亲属群体,最直接的就是三代以内、六七口之家的家庭成员,本文所谓的亲情主要指的是三代以内家庭成员之间的自然情感,最主要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关于家庭、家族、宗族等的界定,参见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卷首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在这样的家庭形态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构成其最基本的情感关系。其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尤其是父子之间的慈、孝关系构成了亲情中最根本的情感,而母子、父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是依附于父子之间的情感关系的,这种情感关系是纵贯的,由子向父,再由父向祖宗,进一步追溯到祖宗神,而祖宗神与天神的合一,更将这种亲情关系上升到最高存在的层面。夫妻之间本无血缘关系,但因为双方有共同的子女,形成了依托于后代的血缘关系,双方的亲情本来是横摄的,但由于夫为妻纲等约束,夫妻之情从本来的爱情而更多地转化为亲情,且呈现出以夫之忠义之情统摄妻之贞顺之情的纵贯模式。兄弟姐妹之间有共同的血缘关系,自然血缘生成上的先后次序,使其本来具有的横向的友爱之情转化为兄友弟悌的纵贯模式,而姐妹之情在儒家思想中几乎没有论及,它可以比附为兄弟之情的模式。至于有血缘关系但较为疏远的非同居共财的家族、宗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则同样比附父子之情这一主干,但在情感态度上更为淡薄,“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注]《礼记·丧服小记》,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2页。意思是说,以自己为中心的向上的父子、向下的父子,这祖孙三代是最直接的亲属关系,再扩展到五代、九代的血缘亲属,亲属关系愈来愈淡薄,至于九代之外的亲属关系就不在丧礼等的范围内了,也就是说基本不在亲情考虑的范围内了。这样,儒家奠基于血缘、家庭基础上的亲情系列就构成了一个以父子之情为主干的情感普遍化的纵贯融通模式。
当前,视频技术正经历从高清显示向4K、8K等超高清显示演进阶段。巨大的市场,也吸引着中国彩电企业的关注。据悉,海信日本公司在11月13日在日本发布了支持4KBS电视直播的新品A6800。
共建是社会治理系统的建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系统功能发挥的基本前提。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系统构建中,如果说共建是系统治理的基础,那么共治就是实现系统治理的手段,而共享就是系统治理的目的。在复杂条件下实现政府治理与其他多元主体的合作共建,在理念创新上体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就是以系统建构的方式体现在多元主体的社会共识之中,具体化在多元主体合作共建的过程之中。为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儒家在论述现实世界中的情感普遍化时,其基点是亲情,尤其是父子之间的慈、孝之情,随之展开的亲情系列是一个纵贯的情感普遍化系统,与之相应的非亲情系列则比附亲情系列形成一个纵贯的情感普遍化系统,而亲情、非亲情两个系列又共同构成一个以天统人、以父统子、以亲统疏、以君统臣、以人统物的纵贯的情感大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北宋大儒张载的《西铭》论述的就不仅是一个宇宙论的系统,更是一个情感普遍化的系统,“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注]《正蒙·乾称》,《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这个情感普遍化系统从天父地母讲起,由上到下、由亲到疏、由近到远、由人到物,可以说把儒家以亲情为基础的纵贯的情感普遍化维度作出了形象而系统的论述,其受到同代及后世儒家学者的高度认同与赞赏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四、儒家亲情观念普遍化维度的思想特色与现代反思
儒家以亲情观念为基础,通过亲情的推扩实现人的情感普遍性,在现实世界中建构起了一套系统的人的情感普遍化的具体融通模式,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儒家亲情观念的普遍化维度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以至生活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其加以反思,可以看清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和价值信念基础,对于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及其内在局限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为儒家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儒家以亲情为基础追求情感普遍性,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人生超越之路。人生在世,自私自爱出于本性,但越是自私自爱的人,却往往在爱父母、爱子女等亲情上比一般人表现得更加强烈,这是人的情感生活中自然存在的辩证纠结,儒家正是把握到了人性中的这一特点,从而为突破自我走向他人、他物提供了一条最切近、最切实的路径,所谓“立爱自亲始”[注]《礼记·祭义》,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5页。。但儒家在论亲情时,一般都以亲情为善,甚至有意识地以亲情统合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在这一点上,包括王弼等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玄学家也是认同的,他在注解《论语·学而》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时就说:“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注]《论语释疑·学而》,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1页。但亲情中内在蕴含的恶的成分始终未能得到充分揭示,清代大儒戴震对宋明道学的“以理杀人”痛加批判,他说:“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注]《与某书》,《戴震全书》,黄山: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6册,第479页。戴震看到了以法杀人、以理杀人的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以情杀人、以亲情杀人,这一点他也还未及见到,这正是儒家学说尤其是道学家的学说中所欠缺的,而对情感尤其是亲情的考察批判,将会深度推进我们对儒家思想核心精神的真切理解。
儒家以亲情为基础实现情感普遍性,其情感普遍性表现为超越的本体之仁和作为情感全体的“浑然与物同体”的仁两个维度,前者是内在的情感普遍性,后者是外在的情感普遍性。内在的情感普遍性作为依据优先于具体的亲情表现,但这种普遍性从何而来,儒家往往将之推到人性、天道的超越层面,这是儒学本体论的核心内容;外在的情感普遍性作为结果后于具体的亲情表现,这种普遍性需要在后天的伦理生活、道德实践中得以实现,这是儒学工夫论的核心内容。这样的话,内在的情感普遍性——具体的亲情——外在的情感普遍性,三者之间构成一个连续的生成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现实人生来说,只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如果要达到两种普遍性之间、两种普遍性与亲情之间的绝对同一,前提条件是个体的人与有机整体、道德创生的本体即全体的宇宙大全的合一,而这种天人合一正是儒家思想的终极信念。但本体即全体的有机整体宇宙论只是儒家的信念系统,它将个体人格消融于本体即全体的宇宙大全之中,强调由亲情发端的人的情感的自然、自觉的一面,而忽视人的情感的自愿的一面,如何在个体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人与终极存在的内在关联,为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这仍然是中国哲学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解决儒家亲情观念普遍化维度现实可能性需要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在现实的情感普遍化维度中,儒家以亲情为基点,建构起了一个以天统人、以父统子、以亲统疏、以君统臣、以人统物的情感普遍化的纵贯融通模式,这个模式中将本来的横摄的种种人际情感统统收摄到纵贯的系统中去。这种情感普遍化的纵贯系统是儒家作为情感普遍性的本体、全体两个维度的完美结合,它将现实人际情感向血缘脉络上收、向超越的心性与天道上收,将人的情感条理成为一个一以贯之的抒发、感应的良善系统,这个井然有序的情感系统同时也就是现实的伦理关系、政治秩序的精神支撑,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世道人心的安顿、家国天下的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情感的谱系既是伦理政治的谱系,同时也是理智认知的谱系,中国传统哲学中以纵贯性的德性之知统摄横摄的闻见之知,其背后的真正的基础应该是这种情感普遍化的纵贯融通模式[注]牟宗三先生在论述宋明道学尤其是朱熹的认识论系统时,提出纵贯系统与横摄系统的不同,认为本体宇宙论的道德创生是纵贯系统,是第一义,而涵养、致知的认知事物之理是横摄系统,是第二义,应该以第一义统摄第二义,反之,如只有横摄系统则学无根本,他以此判程颐、朱熹的学说系统是正宗儒学的歧出。我们这里关于儒家情感普遍化维度的纵贯、横摄融通模式及其相互关系,正可以与牟宗三先生关于儒家认识论的研究相互补充、印证,而且从根本上说,情感普遍化维度上的纵贯系统统摄横摄系统正是认识论维度上的纵贯系统统摄横摄系统的价值源头和思维模型。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7页。。但我们要认识到,人在世界之中生活,既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子(臣)——父(君)——祖(祖宗神)——天(神)的纵贯的情感普遍化维度,更有己——亲——民——物的横摄的情感普遍化维度,在今天这样一个理性去魅、尊重个体的时代里,对于他者的爱成为人的情感中的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存在形态,亲人之间的亲情与我与他者之间的友爱之情成为人的情感生活的最基本的两种形态,而儒家传统中最为重视的是亲情系列,其他情感多是依附于亲情来论述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横摄的情。突破儒家亲情观念普遍化维度的局限,既保留纵贯的情感普遍化所揭示的超越性道德本体的现实实现,同时更重视横摄的情感普遍化所揭示的具体情感之间的碰撞、协调、妥协,以亲情、友爱之情为两大主轴,建构起纵横交错、丰富多彩的情感普遍性世界,这应该是儒学面对未来、面对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作为人的生存的本源性境遇的家庭也在发生变化,家庭形态日益小型化、多样化,尤其是“家里人”正在走向独立的个人,“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成为社会生活的现实,儒家亲情及其普遍化维度正在经受来自现实生活的考验。就儒家思想的本然而言,它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思考起点,强调人的情感发生的社会生活实践基础,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偏向于侧重情感来源于人的心性本体和超越的宇宙本体,而把人的现实情感生活局限在父子、君臣的视阈中,以亲情为根本的情感普遍化维度日趋固化,本来的精神家园却逐渐变成了人的生存的桎梏。我们应当打破君、父、夫中心主义下的人对人的依附、桎梏关系,尊重不可化约的他者,赋予儒家的亲情观念以个体性、自主性、实践性的品格,保持情感普遍化的开放维度,在人与人的伦理生活、道德实践的基础上重建现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整个生活世界。
ASurveyoftheConfucianConceptofFamilyAffectionfromtheUniversalDimension
LI Xiangjun
(Research Center for Value and Culture,College of Philosophy,BNU,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The fundamentals in Confucian philosophy are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ity,which is based on ethical life and moral practice to seek the essential universality of the emotional integration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formal universality of the rational cognition.Confucianism expanded the universal dimension on the foundation of family affection,and they considered the universality of affection both the basis for and result of the manifestation of affec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aking universality of affection as individual noumenon or collectivity,which constitutes the integral emotional world of integrating an individual noumenon with a collectivity.In the real world,Confucianism constructed a vertically integrated model based on affection,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and political order and rational cognitive model in China.The universal dimension of the Confucian family affection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emotional life,spiritual life and even the entire life wor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eople.It is now still the basic premise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Keywords:Confucianism;family affection;universality of affection;a vertically integrated model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1-0121-08
[收稿日期]2018-0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2016年度重大项目(16JJD72000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转化创新研究”。
(责任编辑胡敏中责任校对胡敏中侯珂)
标签:情感论文; 儒家论文; 亲情论文; 普遍性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2016年度重大项目(16JJD72000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转化创新研究”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论文; 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