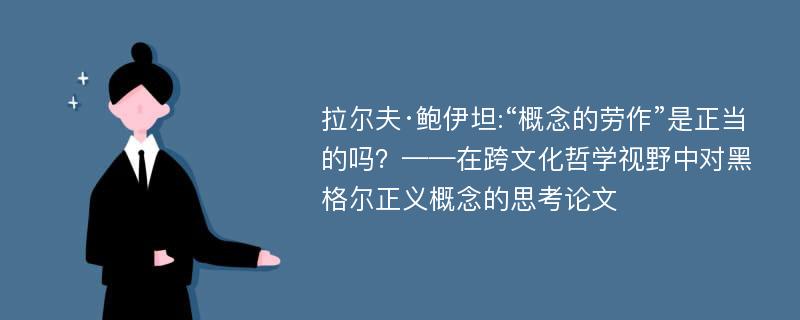
【摘要】本文把“正义”主题与一种非常特殊的实践类型——即概念的实践——关联起来。没有这种概念性—论证性的实践活动,哲学,尤其是欧洲哲学将难以设想。在此需要追问的是,如果说黑格尔哲学宣称通过“概念的劳作”就能把握“真理”,那么它对待其他哲学与(非欧洲的)文明的方式是否“公正”?黑格尔认为,以示范性的方式,系统性的问题应该依据“真理”与“正义”的关系来处理。基于对问题理解的多样性,本文着眼于哲学中“沟通”所发挥的作用,以此论证: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黑格尔哲学本身并非不合理,但是它不能保护我们免受不合理的论断的侵扰。
【关键词】黑格尔,概念的劳作,正义,真理,跨文化哲学
一、 哲学中的正义:真理与正义
“正义”是哲学的核心主题——这一论断是不无道理的。它不仅适用于欧洲哲学的开端——其中包括“睿智”的雅典政治家梭伦(640 B.C.—560 B.C.)那广为流传的洞见,[注]在我看来,东亚哲学传统亦是如此。大家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哲学由于其多样性——并且多样性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本质上是由正义问题所驱动的。这并不能将真理问题排除在外,但也不能简单地被还原成真理问题。甚至也以更显著的方式适用于欧洲和西方哲学传统的另一端(即后现代)——哲学在这里受到彻底怀疑(比如列维纳斯、利奥塔、德里达等)。这在自身中已然是令人吃惊的发现。
因此无须惊讶,在欧洲传统的决定性转向中——这个转向从2000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转变到200多年前开始的现代性动力——即在黑格尔那里,人们无须上下求索便能触碰到正义的主题。毫无疑问,黑格尔的“法哲学”恰好是“正义”问题中的一个关键文本,克劳斯·菲威格(Klaus Vieweg)扎实的“法哲学”研究尤为强调这一点,他把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解释为现代正义理论。(Vieweg, 2012,398)
在古希腊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批判——经济利益诱使公民放弃正确的尺度,并且用不义的方式以他人为代价来使自身获益。在梭伦看来,他们的“自负”(Hybris)挑战了“正义女神”。作为人格化的正义,狄刻(Dike)会向那些被短视私利打破普遍平衡的不义复仇(vergelten),并且重塑被遗忘的真正的秩序。
根据分析的结论,求得上述各市州的农业循环经济效率交叉平均值。因此各个市州的农业循环经济效率值优劣顺序分别为,鄂州(0.97)、武汉(0.91)、宜昌(0.78)、黄石(0.72)、十堰(0.62)、咸宁(0.61)、黄冈(0.55)、孝感(0.54)、襄阳(0.49)、随州(0.46)、荆门(0.41)、荆州(0.38)。
对我们来说有两种思想值得注意:(1)正义的观念在此已经与如何达到某种共同体状态的问题相关联,其中共同体的成员(公民)之间事实性的不平等可以维持在一定程度之内,从而所有“公民”的行动都能产生长远稳定且实际的结果。对梭伦来说,唯有处在一种对普遍尺度的重视之下,或一种“秩序”中,这才是可能的,这种秩序的约束力超越了协议(Vereinbarung)和公约(Konvention),就此而言同时也被视为一种“神的秩序”(这对黑格尔来说也是如此)。在此,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或者说他们的行动将会在同样普遍的尺度中得到衡量;同时他们又是“不平等”的,因为他们所实现的是不同的行动和所有权关系。(2)然而当“不平等”超越了“正当的尺度”,行动仅仅指向短暂的收益,从长远来看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现实性;同时共同体的参与者会受到损害,并最终危及共同体本身。——如果“正当的尺度”被超越,那么参与者必然会通过其(在复仇中的)“苦难”(Leiden)而认识到“被遗忘的秩序”(即整体的本真秩序)。借此,这样的思想就显而易见了(即梭伦关于约束性秩序之过程的“必然性”思想)——正义不是一种状态,而被视为一种发生(Geschehen),即一种真理性的发生(Wahrheitsgeschehen)。(这种思想也在之后黑格尔那里发挥着作用,正如人们在关于“作为世界法庭的世界历史”这种论点所看到的那样。)狄刻是“指引者”,她通过复仇指明了“被遗忘的秩序”。在梭伦看来,正义步入了“真理的中心”。
因此,我们早已能够发现这种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正义在一种通过平等和不平等所标识的共同体中,涉及有关行动(同时也包括经济行动)的普遍性与约束性尺度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表面上对正义的追问与“理论”“真理”这样的核心概念相联结。简言之,自梭伦以来,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人们在欧洲哲学传统中就会发现这种传统的决定性思想:“正义”和“真理”,亦即“实践”和“理论”处在紧密的概念性关联之中。在此可以看到,这种(例如在海德格尔传统与东亚那里)流传很广的观念——即欧洲哲学总体上代表一种片面的理论优先性,后者导致机械论和科学思维模式——遭到了反驳。反过来则是这种情况:古典的形而上学传统并不是“理论性的”(theoretizistisch),而在根本上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实践与理论的联结也是黑格尔哲学那广为人知的特征之一。受费希特影响,黑格尔试图重新弥合在康德那里似乎不可避免的理论与实践的割裂。
然而,那些流行的偏见指出了一个应当进一步讨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首先完全形式地看——人们可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上来阐释“正义”与“真理”之间的关系。(1)要么人们可以以一种强的形式来论证正义与真理的同一性,使两者最终合二为一。[注]简而言之:“正义与真理是互相转化的(Justitia et veritas conventuntur)。”但带来的风险就是抹杀二者的差异性。(2)要么人们可以尝试更多地论证其差异性。但这也会导致这样的风险,即割裂两者概念上的联系,且增强诸如正义概念并不是“真理”概念这种主张。要点(2)是一种可以在后现代哲学语境中找到的理论策略,而要点(1)则是黑格尔部分表达的观念。如果在黑格尔那里,“真理”与“正义”的概念性差异实际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形而上学的真理性要求似乎覆盖了“正义”主题,那么那种偏见(即“理论主义”)虽然绝不是正当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它被当作一个“问题指示器”(Problemindikator)。这种强的(形而上的,而不是以经验为根据的)黑格尔式的真理性要求对正义的实践性追问来说意味着一个问题吗?在此,一般的实践性追问是否应当被归置于理论的优先性之下?我将在下文中试图阐明,问题确实存在。更确切地说,我将关注这个问题:如果理论的“真理性”在“绝对知识”中“逻辑地”展开,那么理论的“正义”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黑格尔本人并没有、可能也无须提出,但我们如今还是要追问。
二、 真理与方法
人们现在可能会论证,一种理论的“正义”问题完全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理论构建的主导性概念并不是“正义”,而是“真理”。我们从理论中要求真的东西,或者说通过理论才认识到什么是真的东西。如果现在人们想要在前文所述的形而上学传统意义上进一步论证,理论的真理优先性绝没有排除“正义”,那么人们可能会在此首先维护一种弱的论点,即在理论之中也关乎“正义”这个理论的对象。例如在黑格尔那里,理论中就包含着一种行动理论。因此,正如人们就可能会论证的那样,只有当我们涉及行动、行动主体和规范性时(而非涉及纯物理实体的行为——例如那些使得某些物理客体落在地球上、某些上升的规律性),对“正义”的追问才有意义。但是人们也可能持有一种更强有力的论点,即一种真的理论意味着它不仅是合法的(即有充足根据的),而且同时还是“正义的”。在此就可能会得出这样的见解,即“认识真理”与“正当行动”意义上的正义处在一种根本性的关联之中。这两种论点在黑格尔那里都发挥着作用,均与理论的真理优先性协调一致。
正交匹配追踪算法(OMP)对目标向量的分解更稀疏且收敛速度较快,因此,文中采用正交匹配追踪算法对稀疏表示系数进行求解。
然而对理论之真理优先性的论证,以及随之而来对追问理论的合法性本身的拒斥,都最终在概念性的范式中发挥作用。根据这种范式,行动要么是理论的一个对象(抑或不是),要么是理论的一种后果(抑或不是),但理论却不同时就是行动本身。在此,假定人们在主张中接受了这样的前提,即正义问题以行动为前提,那么会因此而得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论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阐明:理论并不是偶然地,而是自在地就是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以同样的前提(即“只有行动才是正义的”)就可以用富有意义的方式去追问,是否理论也是正义的。
现在实际的情况是这样,黑格尔式的理论观并没有一种确定的行动模型,也就是说纯粹思维的行动并没有被理解。哲学理论甚至能够且应当对经验的事实行为进行思考,但它在方法论层面并不被要求为有根据性的事例。对黑格尔而言,哲学唯有借助一种先天知识才能确保其科学性。其知识的根据就是“纯粹思维”,后者独立于感性—想象性的表象并独立于经验和非经验(例如“逻辑法则”)的前提,只涉及一种纯粹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的内容仅仅在思维进程中才能把握。在此对黑格尔来说,思维本身纯粹从自身之中发展出来(也就是自由,即自我规定),无关于外在的事例(或权威)或内在直观。思维的自我运动展现为一种概念性的活力(“辩证法”),借此思维的运行就作为一种逻辑性的架构在方法上展开的反思层级中被认识。但其结果,即逻辑性的架构,不应当混淆那些在任何地方“预存的”东西和思维(例如在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中)“给定的”东西;相反,这个逻辑性的架构仅仅是通过纯然思维的自我规定活动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逻辑性的架构和“思维的行动”才会产生并被认识。逻辑性架构的存在—认识根据——即“逻格斯”或“世界的句法”——也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后者唯有通过自我运作在纯粹思维中才能经验到,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天然反思性规定过程(自我规定)的现实化。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思维行动并不被理解为经验性主体的表达或活动,而是作为纯粹思维的运作,后者出自绝对的有效性并独立于经验的主观性和情景性的条件。这可能就是黑格尔言说的“决定,纯粹地思维”背后所假定的东西。
因此,在黑格尔哲学的视域中,我们的确发现一种理论模型,它容许思想可以作为背景性的思想,即作为处于历史具体关联中的思想,后者借此也可以被判定为某种思想行为。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的理论试图这样对待其他理论:它将后者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观察,并以此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但对黑格尔来说,这种使其他理论被承认的方式,在单纯历史背景性的思想中并没有被穷尽。相反,对黑格尔来说,认可其他的理论(哲学的)同时就蕴含着这样的要求,即真理,或者说理论标准的真理性要素必须得到认识。换言之,其他理论变得正当,意味着它的真理得到了认识(而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理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个人之间的关系,“承认”(Anerkennen)同时就意味着“认识”(Erkennen)。从我们一开始对正义问题的追求来看,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在黑格尔那里,正义(在与理论的相互关联中)意味着真理(也就是通过对其他理论的真理性认识而获得的承认)。
一方面,纯粹思维的实践独立于主观性的心理状态和生活世界的利益,另一方面,“逻辑学架构”的绝对有效性(“客观性”)在于他的方法—概念性的关联,后者出现在黑格尔称之为“概念的劳作”的表述中。“劳作”这个术语不仅指出了行动的方面,而且也强调“方法性学说”的特征,这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技术性”特质,消除了“主观性的碎语”,严谨地重视思维内容中纯粹的概念性要素(正如黑格尔也知道,有时这很令人头疼)。“概念”这个表达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不同于现今习以为常的语言使用——不仅是一种稳固的“逻辑性”(即概念性的,而非直观性的),而且也是“客观性”,即形而上学层面的含义。“概念的劳作”以逻辑—方法的方式展示了世界的句法,或者说存在与思维的基本架构。因此“概念的劳作”绝不与个体的或者共同体的“各方面概念的到处运作”混为一谈。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明确表示,“真理”完全是这样展开的,即自身作为纯粹思维的方法进程处在发展之中。“真理”并不独立或外在于“概念的劳作”而实存,而是更多地存在于所有概念要素的充分展开之中——它是其活动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概念规定的逻辑系统。正如黑格尔那句为人熟知的话“真理即是整体”。对黑格尔来说,一个整体(一个大全,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必须是一种概念性的关联,后者纯然产生于概念的自我规定。无概念就无整体(其中没有“存在”,没有“世界”,没有“生命”,没有“对象”……最终一无所有)。
为什么一种通过方法—概念性程序来宣称认识真理的理论,会陷入那种施事性的矛盾之中?(难道只能突出“真理”与“正义”天然关联的假设这个矛盾才能得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特殊的黑格尔式的方法这种基本形态(“辩证法”),而在于更早以前就已经揭示出来的东西。这个问题最终与欧洲哲学的一种基本特质相关,即哲学思考在此(可能从一开始)依赖于对方法理解性反思步骤的解释效力。人们甚至可能会说,欧洲传统已经发明了一种特定形式的方法反思步骤(借助并超越不同的抽象层级),唯有通过这种方法,其理论性的概念才会产生出来或被发现。无论如何:这种在方法学说思维的结果,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追问真理固然非常值得期待,会有不可或缺的影响,但同时也会产生消极效果,真理的闪光与其说使人睿智,不如说更容易让人迷惑。
显然,在其他理论立场的规则中——比如儒学或康德主义的理论,会趋向于否认一种历史观——个人的立场在哲学历史内部看起来是一种不充分且次要的立场。这个与黑格尔相对的敌对阵营至少与黑格尔处理过的哲学一样持久。甚至更持久的是:比倾向于一种逻辑的次要立场还要糟的是,某些人在阵营中被认为完全没有立场。最近就可以听到这样的判断——也可以理解——黑格尔不仅是“不真的”,而且更糟的是“不合理的”,因为他无视整个哲学传统。这样就回到核心问题:“概念的劳作”是否是正当的?
三、 对“方法问题”的附加说明
黑格尔的真理观依然引导了对正义正确或可信的构想(事实上这正是我主张的),并且以黑格尔为根据的一种更为正当的行动形式也是可能的(对此我与菲威格一样,尤其主张政治行动),——但是同时可以思考的是,黑格尔的理论本身带来的一种施事性(perfromativen)的矛盾,也就是说,当这种主张蔓延开来,就不仅仅意味着“真”,而且还暗含着“正当性”(至少在“有权判断”其他立场和传统的意义上,以及在梭伦关于不同立场之间的“真之中心”思想的意义上,这两方面意义都应当在其合理尺度之内根据“普遍的尺度”而被认识)。
黑格尔式体系内部的黑格尔阐释者,会被(在某些要点上)其不寻常的,甚至可能是独特的对“逻辑”“概念”“真理”和“方法论”的理解所说服。至少不得不说,关于“真理”仅仅作为概念的方法展开,简言之:真理只借助“概念的劳作”来展开——这些黑格尔的固有论点至少是十足令人信服的(在此我认为这些论点确实对事实性哲学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且不只限于黑格尔的阐释)。但是,当人们为真理性的概念—方法性的关联(仅仅在思维过程中产生和可见的)这个论点再附加上另一个黑格尔的著名论点——思维规定性的逻辑秩序(例如:存在—无—生成)也在历史的秩序中获得描绘,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困难起来(vgl. W 5, 84和91)。概括而言,对黑格尔来说不仅“真之所是”内在于“逻辑秩序”之中,而且“在历史中的真之所是”(如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的历史)也遵循着“逻辑的秩序”。如果某物在概念—方法性的关联中并无“逻辑位置”,那么它在这个论证关于历史结构的真理性要求就会是糟糕的(一种文化、一种哲学等)。
需要留意的是,啤酒行业目前集中度很高,巨头持续吞并中小啤酒厂的可能性很大,燕京啤酒在中高端市场缺乏竞争力,未来有被并购的预期。
早在高中时期,蒋海峰喜欢的就是紫云,被紫云拒绝,是他一生之痛。一个电话,就把紫云请过来了。这么容易得手,蒋海峰未免有点失落。听说紫云辞了工作,蒋海峰痛心不已:“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然而这种不可视的效果一旦被接受,就首先可以从一种思维的积极效果中得到解释,即决定性地与真理有关。思维的方法—概念性的程序(其“游戏规则”),正如上文所说,是两面性的。这种两面性就在于:它不仅剥离了我们知觉领域的漏洞,而且还剥离了人们口耳相传的“神话”和故事、独裁者的论断、狂野的幻想和狭隘的教条。因而可以概括性地说:它剥离了“神话”而解放了“逻格斯”。这不再适用于人们常说的东西,或以一种压倒性力量所言说的东西,而是处于一种显明的根据关联之中,并且其仅仅来自思维的真理本身不可证明。什么是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首先获得方法性地“构造”——尽管并不是“单纯的构造”(bloße Konstruktion)。举两个例子:无论是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这种真的几何事实,还是“存在”的本体论事实(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存在与无的同一性和非同一性),都不是我们可以在空间—时间性的现实中可以轻易找到的“对象”。它们必须首先在方法性步骤本身中才得以产生。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构造”(konstruiert)中,但还不是“构造物”(Konstrukte),而是对现实性的洞见,正如人们在对三角形的内角和的证明中所看到的那样。
2.2.2 3组小鼠用力呼气时间比较 3组小鼠在6、18、36 h后的用力呼气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b。
不同于数字馆藏较定型的内容储备、传统节庆表演较为固定的时间限制,社区教育能够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目的的灵活选择、批判、更新和创造性应用,更好地发挥非物质文化的交流融会功能,有效促进传统文化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的成果应用。
这种方法性思维的双重剥离性某个方面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被意欲:人们剥离了所有以纯粹偶然的方式断言为真的东西,仅保留在必然推证过程中推导出来的东西,以及完备的非偶然真理的可见之物。与真理图景并不相符的不可见之物,不仅被接受,而且还是方法的特殊目标。在此(根据黑格尔的历史观),那些零散的哲学和哲学传统不仅发挥着次要的作用,而且时常变得不可见,以方法性为优先所获得的真理见解必定不会是消极的。这样就很容易确定,在某物被确立为真的条件下,人们不可能也不一定要思虑一切。人们也可以与黑格尔一道承认,同样在方法性思维的条件下,(a)不同的哲学也都发挥着作用;然而(b)有些(最终是全部)哲学的作用虽然是积极的,但从整个根据性关联的理解而言是次要的;而(c)某些哲学在此则根本就没有经受住完整的批判性(区分性的和评价性的)审视,故而被视为非哲学。即使如上文所论,也可以承认(d)一些哲学不仅被拒斥(但至少还能被认识),而且完全不可见。这种哲学与“不可见的大猩猩”共享着同样的命运:也就是说,对既定“游戏规则”(方法)富有成效的遵循,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无视那些未被强制性视为与“游戏相关”的事件或存在。结果就是,在每一种有效的方法条件下,各种隐藏起来的事物不必再被隐匿起来——如果“不可见的大猩猩”自身拥有更成熟的方法,也同样如此(在“其他哲学”可被预设的情况下)。
四、 背景性的哲学(Situierte Philosophie)
(1) 不同的历史视域能被区分出来,使得思想能被理解为背景性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某种完全依赖于背景的方法性操作(这依然可能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虚构)。(这种核心洞见不仅适用于现象学和诠释学传统,而且也适用于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
假如理论仅仅与“三角形的内角和”这类对象相关,那么的确没有异议。然而,哲学无疑涉及的东西比这更多。正如我所说的,同样是因为哲学从一开始就与“正义”有关。“正义”问题——包括理论的正义问题及其方法论——当它不是着眼于抽象实体的关联方式,而是着眼于更具体的、更生动的(即有活力的)且更有意识(有意识能力的)的关联方式,才会首次出现。同时正义仅仅涉及这样的关系——它与在自然的和历史的世界中可以被思考的具体背景有关。于是首先出现的问题是,在一种具体的、理论能嵌入其中,即处于背景中的历史关联下,一种理论能自身显示成为不正义的。只有一种在世界中背景性的思想,及其在此世中被经验到的、历史的、在背景中的关系和行为模式(例如方法论式的排外)才能在正义问题上被提出。一种背景性的思想也允许这样追问,是否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任何东西更好地被了解——即“更正当”——以至于更能对其他思想进行判断。
为了说明这种负面影响,首先,我想展示一个著名的知觉心理学实验,即所谓的“大猩猩”实验。(为避免错失精准的效果,我建议用YouTube播放器完整播放一次大约两分钟的实验。)简单来说,这个实验表明,我们的注意力在多大程度上被一种特定的“游戏规则”(类似于“方法”)所支配,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盲点”。在此可以将其概括为一种(非黑格尔式的)知觉辩证法,后者产生出一种最大限度的可视化(Visibilisierung)(使之能被看见),同时又会产生出一种不可视化(Invisibilisierung)(使之不能被看见)。这种关联是自然的,并在古老的传统中就被认识到了(比如泰勒斯的水、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等),但是上述实验以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使之直观化和被理解。我们的知觉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可以结构性地与思维进行比较:思维自身“完全”(àcorps perdu)绑定在它的“游戏规则”(方法)中,在缺少方法程序的情况下,那些对所有现象之物的无视(抽象)就不会出现,而是有意或无意地被接受下来(对黑格尔而言可以确定的是,他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也不会对“逻辑”的抽象保持沉默)。
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关键的论点。最近我们必须重视并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合理的判断。黑格尔很少为人承认的伟大哲学贡献就在于,不仅个体及其行动、社会和政治的形式及其规范性基础,而且哲学理论也都是处在历史背景之中的。上述提到的历史观并不源自于一种理论的自负,这种理论想要将历史世界的混乱美化为一种逻辑的世界秩序。相反,这种历史论点更多地代表了一种现代的基本论点,其中每一种思想以及有关普遍真理的形而上学思维,都承载着一个时间索引(Zeitindex),即:总是同时是一种历史背景中的思想,这种思想承载着其时代的标志。因此正是黑格尔,前无古人地试图为背景性的思想,以及在不同历史视域意义上的哲学多样性进行讨论,却并没有为相对主义进行辩护!“在思想中把握其时代”对黑格尔来说,恰好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认识普遍真理。
现在对“概念的劳作”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通过这种“劳作”在与其他理论的关联中所实现的真理导致的一种理论的不正义,这种怀疑又意味着什么?在黑格尔的理论视角内部,这个历史论点恰好不能被理解为必然导向不正义的论点,以至于其他哲学被安排和隶属于一个目的论的关联中(或者甚至变得不可见)。方法论—概念式秩序(“概念的劳作”)与历史论点的联结,更确切地被视为一种对哲学非相对性真理主张的现代尝试,这种阐释不需要将其他理论及其真理主张作为完全不真的东西而排除在外。换句话说,历史论点并不处在其时代之中,而是更多地处在与其他理论关联中涉及正义。黑格尔完全不同于他的哲学前辈(在德国观念论和其他),他承认在过去的历史视域中可以认识到理论的真理,尽管这看起来与他自己的论点相矛盾。这进一步表明,黑格尔的历史观在三个方面依然引领了现代世界的理解:
我们现在可以更为切近地界定理论的施事性矛盾的问题,这种理论试图认识真理与正义,并且通过其自身理论建构的实践(比如“概念的劳作”)独自展现出一种非正义的形式。(比如无视),这种想要脱离暂时性和语境条件来保证真理观的有效性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使情景不可见化,换言之,制造一种自主的根据性关联,这种方法试图通过分离所有可能的语境和似是而非的信念而获得其真理理论相对于依赖语境的解释力的优势。通俗地说,真理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知的。从人们通常所期待和接受的论点和信念来看,从中意欲抽象出来的真理应当被称为“方法的无知”(methodische Ignoranz)。因为对于“真理的方法”而言,在最终裁决中既没有既定真理假设的事实,也没有其语境合理性的一种根据性理论的相关性。
(2) 进一步说,在不放弃真理论点的情况下,这种历史背景性的论点也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可以假定,一种历史背景性的思想是真实而有效的。这种有效性条件的历史界限并不意味着真理的任务,而是用作对真理认识的澄清。
(3) 同时,黑格尔的历史观能解决那些发生着的真理观之间的冲突问题,在此无须非此,或者完全(怀疑)所有真理观,将其判定为单纯的谬误。知识(或真理)之历史性的真理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在此考虑并认识到真理观的多样性,而不将非矛盾律有效性的力量排除在外。因为在一种历史视域中,“真”并不“同时”就是“不真”。某些东西(一种理论、一种原则)同时为“真”和“不真”的矛盾,将借助历史性中的共时性(“同时”)得到解决。一种时间性的序列涉及的是“同时”的立场。这样就可以无矛盾地论证,即使存在哲学的多样性,但真理始终只有一个。
2015年运营指南在2005年的基础上更明确了各地区标准、学校标准和教师标准的运营指南。同时各领域内容囊括了达成基准及说明、学习要素、教学与学习方法及注意事项、评价方法及注意事项。使课程标准更容易被理解和实践,对学校课程的教育及教师课程的设置有直接的影响,并对教育课程的改革有积极推动作用。
五、 真理与正义:融合抑或分离?
对现代范式方法而言,黑格尔的历史观包含了一种背景性思想的论点。在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并没有放弃一种对最终普遍真理的要求——这种对真理的要求与这样的论点相互兼容,即个人的理论在其他理论和真理观念中也能变得正当。这种将真理与正义紧密相连的做法多么吸引人——如果人们进一步讨论背景性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也会被考虑在内。
目前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必须阐明一种背景性的思想如何处于历史序列的条件之下,而且还必须阐明在共时性的条件下应当如何行动。这个问题最终是开放性的。为澄清这个问题,可以做如此升华:黑格尔式的对真理与正义的融合(即一种思想的理论)所涉及的是历史序列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情境性的思想存在于一种直接的交换之中,或者说存在于会被忽视的理论沟通之间。[注]不论是黑格尔本身还是其理论,都不能说交流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其在理论的逻辑—历史秩序意义上确实是作为一种过去的、“被扬弃”的交流形式被看待的,因此才没有被重点关注。但是,一种背景性的思想确实不仅与过去的理论(和过去的交流)相联系,而且还与其他当代的理论相联系。这种在共时性层面上的思想的背景性,在其中思想面对着其他同时的思想形式以及其他方法论标准,甚至部分面对着其他传统——此种背景性带来的是对思想中沟通的特殊关注。但正是这种沟通的情况使问题变得尖锐,即真理与正义如何能够相互支持。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基于黑格尔的融合论,理论之间的冲突可以分布于历史的坐标轴上,而且无权要求同时性的效果。但是这恰好属于沟通这种情况。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似乎现在必须在两种不那么吸引人的选择中做出抉择:(1)要么我们独断地维持着我们的真理性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会强迫其他理论臣服于我们所设置的方法标准,如果它还想提出一种有效的真理要求的话),并且最终破坏正义,即破坏对其他思想形态所进行的正当判断;(2)要么我们无条件地意欲其他思想形态变得正当(也就是说,我们使自己臣服于其他方法标准),考虑到理论的多样性,放弃我们的真理性要求而助力于那种无底线的相对主义。简言之:黑格尔式对真理与正义的融合似乎不再可能。真理与正义彼此互相侵犯。这个图景就不再是融合,而是分离。
我想在结尾处就我的中心论题进行概要解释:当人们将正义与真理——不同于黑格尔——归入沟通情境条件之下进行判定时,二者是如何组成一种哲学理论?我的论点是,即使处在沟通情境条件之下,真理与正义也不是相互分离的,相反,它们的组建方式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说,20世纪的欧洲哲学是把沟通主题作为一个核心的哲学论题来澄清的。从类型学(typologisch)的角度出发,我将简短地呈现出特定的根本立场,从而能对我的论题进行阐明和比较。
(1) 第一个立场可以从一种“普世语言”和“科学性”的流行观念出发来解读。这种观念完全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而延续的,即遵循以科学性来确保真理观之正义(这里可以以卡尔纳普和波普尔为例)。无一例外的是,在这种传统路线中,几乎或者完全没有更老的传统,而且也没有其他传统,如亚洲传统被提及。这种“方法的无知”可以在(并不是黑格尔那里)其最极端的形式中找到。
(2) 第二个立场在20世纪欧洲哲学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这种立场持有更为清楚的反思性和自我批判性。正如在古典和形而上学以普遍真理为优先的传统(直到黑格尔)被部分或全部放弃掉了,这就导致一种决定性的转向。现在理解背景性思维的模式不再沿着“证伪”(Falsifikation)和“证成”(Verifikation)的系列进行科学性进展(正如要点1那样),而是具体生活世界的沟通情境。在此也出现了指示性的思想,后者对沟通情境来说,不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真理,而是为正义所决定和奠基。正义的优先性和真理的边缘化成为现代和后现代思想的主要趋势(这里主要是指列维纳斯、德里达和利奥塔),其后果就是真理不仅是次要的,而且还受到怀疑。黑格尔的融合论在这种情境中看起来如同一种挑衅。正义与真理的分离变成了主导性的观念。
(3) 第三个立场(如哈贝马斯)企图在此将真理收容进来,但并不接受现代科学主义,也不放弃对沟通性情境正义问题的敏感性(正如要点2)。在此可以发现一种——至少理想化——沟通伙伴彼此之间的公正关系,其中每个人在原则上的同等权利都能得到承认。最终以正义为前提,一种可能的沟通进程应当发现一种共识性的真理,这种真理不仅适用于所有人,而且也被视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共同尺度。然而这种立场持有的依然还是正义优先于真理的立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普遍预设了一种共同的传统关联,从而使得标识一种理解真理的乐观图景变得相对容易。但是我们在理智的视角中不能预设沟通成员享有共同的传统关联这个前提,因此,要实现在哈贝马斯构想中的那种共识性的真理,还需作进一步的推动。)
最后基于这些类型的比照,我可以具体说明我的观点:每一种理论的联结,其中个人在沟通情境中对一种思想的反思,在我看来从正义优先性的角度来说都是正确的。因为不像在科学主义的世界图景(1)中那样,环境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我们不仅能有不同的真理信念,而且也能有不同的方法范式,而不只是单纯依靠证成/证伪的游戏。我们首先必须悬置我们自己方法性带来的真理观,容纳其他对真理和方法的看法。我们至少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即对我们来说至少不可理解的事物包含着一种真的思想。这些“使自身可以为他者所规定”或者“以他者作为自我思考的标准”都可以较好地在正义概念之下被把握,但对还不知道已经处在有效的普遍之中并包含可被认识的真理的人那里才是可能的。然而不同于那些理论(要点2和3),我还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即真理既不会被正义优先性所侵蚀或放弃(要点2),也不需要局限于共识性的真理(要点3)。人们也可以从黑格尔进一步示例的历史性思想中认识到,一种来自立场冲突的真理有效形式可以退场,认识到这不是共识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事后的(posthoc)复杂的概念形式。换句话说,即使有人不同于黑格尔,强调的是思想的沟通背景并因此给出了另一种先于真理的正义概念,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去假设真理必须被抛弃或者被限制。如果人们像前述那些现代立场(2和3)那样有效地给出正义的优先性,那么可能会更加期望思想的多重性不仅能汇聚成一种共识的一致性,而且思想还会转变为一种被改变的且更为复杂的概念标准。这是沟通和建构性的正义优先性,而不是意见一致(意见一致在某种程度上是范导性的,对真理概念形式的洞见来说并不施展建构功能;它并不给出单一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后者对任何时代来说都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思想家们的共识)。
关于黑格尔原初的途径,我对真理与正义的理论联结的结论性思考总结如下:
色谱柱 YMC-C30:4.6×250mm,5μm;检测波长:445nm;柱温:35℃;流动相:甲醇∶水=95∶5,等梯度洗脱;流速:0.8mL/min;进样量:20μL。
我们都熟悉黑格尔的历史思想:“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起飞”,其飞行最终与真理有关并带来奠基性的正义的洞见。然而,“正义(Justitia)在黎明破晓之时已持有天平”,但是绝不像现代和后现代想要坚信的立场那样,与黄昏的飞行背道而驰。
根据慢性鼻-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2年,昆明)[1],小剂量(常规剂量的 1/2)、长期(疗程不少于 12 周)口服 MA 是 CRS 的推荐治疗方案。
Is the “Work of the Concept” Just? Reflections on Hegel’s Concept of Justi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Ralf Beuthan
【Abstract】The paper will relate the theme of “justice” to a very specific type of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concepts”, i.e., that kind of conceptual-argumentative activity, without which philosophy, especially in Europe, is hard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Hegelian philosophy, which claims to grasp the “truth”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concept”, does “justice” to other philosophies and foreign (non-European) cultures. In an exemplary way, Hegel will figure out a systematic problem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and “justice”. Starting from a more differenti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with regard to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philosophy, it should be argued for the theme that Hegel’s philosophy in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is not unfair perse, yet it cannot protect us from unfair judgments.
【Keywords】Hegel, Work of the Concept, Justice, Truth,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①作者简介:[德]拉尔夫·鲍伊坦(Ralf Beuthan),韩国明济大学教授。
②译校者简介:吴怡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专业硕士生。朱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生。
标签:黑格尔论文; 真理论文; 正义论文; 理论论文; 哲学论文; 《伦理学术》2019年第1期论文; 韩国明济大学论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