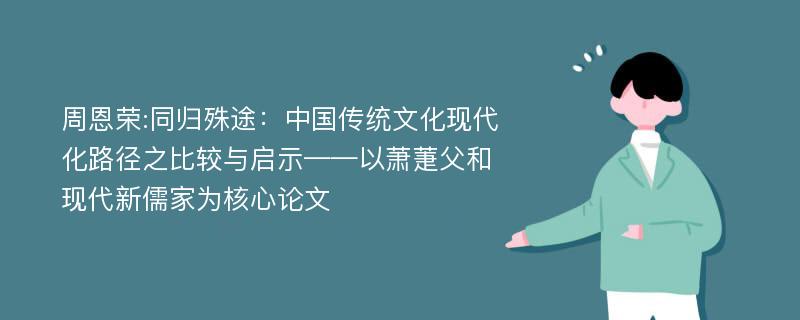
摘要:萧先生根本的学术追求,是通过掘发船山哲学所代表的中国哲学早期启蒙的现代价值,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其船山哲学研究依此方得其恰切理解。萧先生促进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现代化的努力,与现代新儒家经由“返本开新”以焕发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从而在新的时代担负其新的使命,二者可谓殊途同归。比较萧先生与现代新儒家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具体途径的不同看法,反思其中的异同和所以异同的根据,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事业颇有启发,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同归殊途;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路径比较;萧萐父;现代新儒家
萧萐父先生可能会赞赏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现代化的努力,但不大可能会同意他们的具体观点和主张。而现代新儒家是否会同意“中国早期哲学启蒙”的提法,也可存疑和讨论。尽管如此,无论萧先生、还是现代新儒家都赞同中国哲学与文化需要现代转型。而既然要有现代转型,就需要寻找到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或萧先生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国化”的具体途径与方式。比较萧萐父先生与现代新儒家促进中国哲学与文化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反思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研究今天中国哲学和文化,当不无启示。
一、 推故致新:萧萐父先生的学术追求
一般认为,萧萐父先生是船山哲学专家。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因为萧先生确实发表了不少有关船山哲学思想的论著。早在20世纪60年代,萧先生就以其“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受到海内外学人的瞩目,代表了当时船山学研究的水平”[1]248;到80年代,萧先生陆续发表《王夫之的人类史观》《王夫之的自然史观》《王夫之的认识辩证法》《王夫之矛盾观的几个环节》《王夫之年表》等论著,并主编《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等,“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王夫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体系”。这些成果不仅数量多,并且质量上乘,为萧先生赢得了世界性船山学研究专家的声誉,让他受邀为罗马尼亚Luclan Boia教授主编的《国际史学家》辞典中“王夫之”条的撰写人[1]249。2002年,萧先生与许苏民教授合著的《王夫之评传》,被收入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由萧先生规划、定调,许苏民教授执笔的巨著,是萧先生船山学研究的系统总结。
但是,倘若我们仅以船山学研究专家来定位萧先生,那将会忽略萧先生思想更丰富的维度。事实上,萧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而非止船山学专家。他熟悉儒家典籍,对儒学发展史有恰如其分的揭示;他对道家与道教、佛教哲学、周易等均有非常精到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萧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有巨大贡献。萧先生在接受田文军教授采访时,曾介绍了他在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开展学科建设的经验:“我们以研读‘两典’(马列经典著作和中国古典文献)为基石,以清理‘藤瓜’(哲学发展的线索及重点)、探索‘两源’(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为起点,来规划组织中国哲学史教学”,并据此“编印了近百万字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和“一套《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注》”;重视研究生“哲学史方法论的学习”,与陈修斋先生一起合编《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一书[1]254。以上所述,显示了萧先生中国哲学史家全面、深厚的学养,并非一个“船山学专家”所能概括的。
尽管萧先生是学养深厚、视野全面的中国哲学史家,但是,其标志性学术成就却是他围绕船山哲学而提出的“中国哲学早期启蒙”的思想。萧先生的船山学研究,须放在中国哲学启蒙坎坷历程的叙事之中才能得到真正、合理的理解①。因为,在王夫之所处的明清之际,“中国传统社会母体孕育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萌芽、挫折和复苏的曲折过程,一方面是新的关系要突破旧的关系的束缚,另一方面,旧的社会势力又竭力阻止新生事物的发展”,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则是新旧杂陈,方生方死,新观念往往借助旧范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或以复归原典的方式来表达新的时代诉求”,造就了“传统的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社会开始了自我批判但尚未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2]3,王夫之作为这一时代的“思想巨人”,其思想确实打上了“新旧杂陈,方生方死”、新思想或“借助旧范式”“表达自己的理想”“或以复归原典的方式来表达新的时代诉求”等时代烙印。不仅如此,萧先生“对船山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理解,体现了我们的学术目标和追求”[1]255。萧先生的学术追求、其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泛化哲学史研究、注意哲学—文化问题时,具体地展现了出来。他“自觉地有选择地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最新成果,在中西文化对比中,超越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现代价值生长点”,尤其“重视明清时期反理学的启蒙思潮”,以正确地理解中国文化必须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根据[1]256。依此,萧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标和追求,就是通过清理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在根据,找到中国文化固有的现代价值生长点,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从而为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现代化奠下坚实的基础。在萧先生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转型与世界先进文化中国化的综合统一。
二是国家税务总局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提出降低社保费率等建议,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缴费人以前年度欠费,一律不得自行组织开展集中清缴。
综上所述,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哲学研究应放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先生的船山哲学研究是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和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的生长点的一种尝试。在萧先生的理解中,船山先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推故而别致其新”,故“既是宋明道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和先驱者”[2]604-604;船山哲学思想在各个方面所开创的新局面,经谭嗣同、章太炎、杨昌济、梁启超等先生的比较与弘扬,已显示出“主导的和创造性的方面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2]648,值得总结并进一步继承,并进而发展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和中国文化现代价值的生长点。
二、 返本开新:现代新儒家的理想诉求
所谓“现代新儒家”,其涵义与所指均未有定论。由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所引发的现代新儒家的界定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争论不休。人们对“现代新儒家”可能包括哪些人物、其学术认同的范式究竟是什么等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近来,学界通过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大体接受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蒋国保教授即主张广义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是一群“认同儒家的基本原典和基本精神,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对其加以创造性发展”思想家。而刘述先先生则以“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学”进行区分。他指出,作为大陆学者偏爱的术语,现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的所指十分宽泛,包括了“五四”以来信守儒家价值的三代四个群体的学者的工作,即第一代第一个群体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第一代第二群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共15人;而当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是一个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学者中比较流行的概念,其所指相对较窄,主要是指由熊十力开启而由其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继承和发展的哲学运动[3]24-25②。
本文依据刘述先先生的区分,把“现代新儒家”理解为由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以及唐、牟、徐等先生的学生)构成的学术共同体。此种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由多位极具个性的哲学家构成。他们在学术思想和实践上共享的、使其成为学派的基本纲领、理想诉求或“范式”,集中体现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1958年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简称《宣言》)中。《宣言》申明,“当代新儒家肯定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并以由孔孟至宋明心性之学为儒学的主流。此一儒学主流,立基于性善论,做为道德实践之基础,形成一由道德实践而证成的形上学”,依据这一“形上学”,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之本心(仁、良知)即宇宙之心、乾坤之基[4]5-6,亦即是生生之德、创造之本;人的道德实践、修养工夫,乃至政治建构等,都以此为调整和轨约原则。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的思想格局,或者说“返本(内圣)开新(外王)”的理想诉求。
所谓“返本”,一般认为是“返回儒家旧有的内圣之道(即老内圣)”。此说固然不差,但相比现代新儒家的工作,却嫌笼统。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应当是去“发明”作为生生之德、创造之本的人之本心。尽管现代新儒家内部对如何理解人之本心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强调“本心”作为意志—精神具有创造和进化的能力。因此,“返本”实即强调人上承生生之易道、挺立人能动创生的主体性,为人的修养工夫、道德践履乃至政治建构奠下基础。这就是说,“内圣”可理解为人之成就自己、追求自我实现③。以此,“返本”虽可被理解为“返回儒家的内圣之道”,但所“返”之“本”,绝非一般所谓的“老内圣”。
首先,萧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需要一场破除传统专制主义所塑造的“神文主义”“伦文主义”等“伦理异化”的哲学启蒙运动。现代新儒家却认为不必如此。依现代新儒家,儒学传统本身就与专制主义和为其服务的“神文主义”“伦文主义”相对立,而为人文主义传统主流,因而,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化无需“哲学启蒙”,而只需将其以格言形式表达的原创智慧予以系统化,便可完成其现代化。虽然萧先生与现代新儒家群体之间有如此的分歧,但是,他们却共享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
不过,萧先生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他在批判被专制主义利用的“神文主义”或“伦文主义”时可能混淆了儒家的不同面相——人文主义的儒家和甘为专制服务的儒家。而现代新儒家面临的更大挑战是,作为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儒学传统,其中为何出现了“神文主义”“伦文主义”的异化?这是否意味着儒学内部某些成素与“神文主义”“伦文主义”有着亲和性?如何剔除儒学传统中的那些配合专制的成素?
三、 儒学或人文: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不同路径之比较
尽管萧先生与现代新儒家均以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为追求目标,尽管他们都着力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都努力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中国化,但是,在具体的实现路径方面,他们之间却存在着重要分歧。
其次,萧先生主张,儒家之为儒家乃在其“以人伦为中心,各有侧重而又互补地完成了‘修己治人’的‘仁义’之学的建构”[6]142;除此之外,儒家“夙以杂见称”,儒学内部“名实颇多龃龉”。而现代新儒家则认为,儒家内部虽存在分歧,但其主流仍是作为“内圣之学、成德之教”的“心性儒学”,儒学在政治等领域的实践,要以“心性儒学”为根据。以此,儒学之为儒学,其根本在那能上接“天道”的“心性”本体,儒者对这一能上接“天道”的“心性”本体的“呼应”(或“重获”)便构成了儒学的“道统”。因此,萧先生与现代新儒家对“儒学之为儒学”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尽管他们都接受儒学在整体上是“内圣外王之道”,但各自又对儒学之为儒学有不同的主张和侧重点。
萧先生的“早期启蒙”之说,曾引起过争议。包遵信和杜维明分别从相互对立的视角,否认此说。包遵信认为,“17世纪中国并未出现过‘启蒙思潮’,顾、黄、王等人对‘王学末流’的批判乃是儒家思想的振兴或自我调整,‘五四’以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什么思想启蒙或文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靠自我批判达到自我更新,在传统文化中去寻觅近代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生长点,无异于缘木求鱼’”[6]67。杜维明则把儒家传统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把17世纪的‘启蒙运动’与宋明理学当作对立面是犯了‘范畴错置的谬误’,因为‘启蒙运动的健将无一不是儒家传统的成员:晚明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不待说,躬行实践的颜元及其弟子李塨和痛斥“以理杀人”的戴震也不例外’”[6]66。对这两种反对意见,萧先生回应说,他非常重视包先生对明清之际社会思潮转折的分析和对封建传统内在惰性的剖判,并大体同意其关于儒家传统不可能成为科学与民主的价值生长点的论断,但很难认同其“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有自我更新以实现现代化的可能”;相反,中国文化代谢发展的杠杆在17世纪已然形成,后来的历史教训也表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到内在根芽,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基于相似理由,萧先生虽然欣赏和赞同杜维明先生关于要在自己民族优秀传统中去找到现代化的“源头活水”的提法,却不赞同杜先生关于民族优秀传统的抉择,也不同意其探寻中国现代化“源头活水”的取向,在萧先生看来,杜维明先生把儒学或儒家传统视为“人文精神”“至大至刚的正气”,乃至“消除封建遗毒的利器”,进而又把“启蒙运动”健将们笼统地归于儒家门下,其方法太过于笼统、抽象和理想化,很难让人信服,因而“分其本合,合其已分,倒容易‘范畴错置’”[6]67-68⑥。
萧先生持此立场,实因他于“启蒙”的独到理解。他说:“所谓‘启蒙’……是指特定条件下封建制度及其统治思想的自我批判,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相适应,只表示(旧制度)旧思想必将崩解的先兆,新思想必将出现的先声。”[6]68而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家们在中国封建社会虽未崩溃但已能自我批判的阶段,发出了反对封建特权、重视质测之学、坚持经世致用的呼声,表现出早期民主主义意识和人文主义启蒙的特征。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中,萧先生和许苏民教授概括早期启蒙学术的三大主题——个性解放的新道德、科学与民主。其中,个性解放的新道德具体体现了萧先生早期启蒙人文主义理想的内涵,而科学与民主则于实践面为这种人文主义理想的实现提供保障。萧、许二先生说:“早期启蒙学者所论述的个性解放的新道德既有理性层面的对于理欲、情理、义利、个体与类之关系的哲学论说,又有感性层面上的对于伦理异化的突出表现……的激烈批判。”[7]5-6在他们看来,早期启蒙学者是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讨论理欲、情理、义利等关系,其人文主义理想包含着浓厚的自然人性论色彩,以及对情、欲、利的合理承认。早期启蒙学者强调“欲出于天、理在欲中”“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甚至赋予“情”以“位育真种子”的崇高地位。与此相应,萧、许二先生人文主义理想中的“人”是感性与理性兼顾、情理兼备的完整的“人”,因而他们对早期启蒙学者“纳情于理或援理入情”“反对‘桎梏人情’”和“强调‘性为情节’的道德要求”倍加赞赏[7]6-7。萧先生认为,这些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
萧先生以自然人性论为据的“人文主义”,强调作为整体的“生命”的意义,有其合理性。但是,若只强调对“欲”“情”“利”的正视,而缺乏对理欲、情理和义利之间如何比较权衡的具体讨论,是否会面临刘宗周所批评的阳明后学中“情识而肆”的疑难?而现代新儒家以“仁”为出发点和核心的人文主义,如果不能对“生命”的有机构成恰当划界,也可能会面临“道德”宰制或“良知傲慢”之讥。
需要指出,萧先生对现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的定位,与学界一般的认识颇为不同。萧先生认为,熊十力、徐复观、唐君毅等先生实际上应该是哲学启蒙的“同调”,而非所谓“现代新儒家”所能尽⑦。在萧先生看来,熊十力、徐复观和唐君毅诸先生“引古筹今”,一方面批判和清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遗毒,另一方面弘扬中国文化传统“尊生主动,自强不息”[9]23的精神,高扬国人在文化创造、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原则和“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9]23,以“殊途百虑”的学术发展观,自觉地由多源头、多根系、多向度的致思路径,于中西文化“察异观同、求其会通”[8]488,而致力于“创建一理想的人文世界”“展示未来人类文化的光辉前景”[8]494。萧先生对熊十力、徐复观和唐君毅等先生的评价和定位,固然有所根据,但不可否认,熊、徐、唐等先生毕竟以儒学,尤其是心性儒学为宗,吸纳其中蕴蓄的“人文主义”精神,而力主“返心性儒学内圣、成德之本,开民主、科学的现代之新”⑧。萧先生之视熊、徐、唐诸先生为启蒙之“同调”,其根据是这些先生坚持“儒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萧先生其实是把“人文主义”视为中国哲学早期启蒙乃至中国哲学与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与源头活水;而现代新儒家则以儒学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现代化的根据,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儒学根本上是“人文主义”的。因此,萧先生与现代新儒家都认同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目标,但他们对启蒙是否现代化之必须、儒学究竟是专制主义的共谋还是抗议精神的源泉、儒家之为儒家以及人文主义的内在结构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
因而,通过深入探查、比较萧先生与现代新儒家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现代化的方案,我们认为有三点结论值得进一步探讨。
所谓“开新”,即是开创新的外王事业,质言之,即开创或实现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外王事业。根据现代新儒家的观念,“新外王”即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对于现代新儒家所倡导的“新外王”事业及其实现方式,学术界多有误解和批评。在诸多误解与批评中,“良知傲慢”论和“中体西用”论较为典型。持此意见者认为,现代新儒家开创“新外王”事业是通过“加添法”,把“其他文化之理想,亦包括于中国文化的理想中”;他们批评现代新儒家:在“民主与科学”是否西方文化之理想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便将其纳入中国文化以为“理想”,不太过冒失吗?然而,这样的批评,实是出于误解。因为,《宣言》仅说:“我们只当指出中国文化依其本身要求应当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之活动的主体’。这亦就是说……中国文化中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但是其所以需要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乃所以使中国人在自觉成为一道德的主体之外,兼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活动的主体。而使中国人之人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完成”。《宣言》更进一步强调,中国文化思想中有民主思想的种子,同时中国文化也并不“反科学”④;其所缺者,一是民主之制度,一是科学之精神。由于中国文化本身固有民主思想的种子,且不“反科学”,所以中国文化之接受西方或世界文化,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不仅如此,中国人在现代化的挑战下,本着追求人格的更高完成和“利用”“厚生”的需要,也会主动要求民主与科学。因此,不能将开创“新外王”的事业简单视为“加添”。牟宗三在《生命的学问》中明确说,西化不西化,不是在“科学”与“民主”等“用”的层面或功能表现上说,而只能从文化生命的形态或根源上说。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中国文化生命的形态或根源,乃中国文化生命一脉相承之“体”(即中体),它包括但不限于传统的道德心性,毋宁说是普遍的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而表现为“民主政治与科学事业”的“新外王”或“用”,虽最先出现于西方,却非西方所能独有,而毋宁是“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展现其自己之本分事”,是“共许”“共法”[5]70-71。就此而言,那种把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视为“中体西用”翻版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民主与科学或许未必是西方的理想,然而,现代新儒家也并未以之为“理想”,它不过是中华文化大动脉中的“现实关心”、中国文化生命展现自己的某些方式而已。至于“良知傲慢”的批评,与人们如何理解“良知”有关。拙文《良知坎陷,如何可能?》和《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再检讨》对此已有讨论⑤,此处不再赘述。
电动机驱动永磁转子以恒定转速nx(单位为r/min)相对于定子绕组顺时针旋转,与定子绕组之间产生相对运动。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定子绕组中会产生感应电动势e,其瞬时值为:
总之,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之说,是针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境遇提出的因应或解决之道,也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的努力和尝试,其具体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萧萐父先生和现代新儒家群体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
在萧萐父先生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就在于中国哲学早期启蒙。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发扬这一肇端于16世纪中叶、于17世纪有其典型表现、而在其后经历了极为坎坷历程的以“反理学”为其特殊表现的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自我批判的思想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体现出来的精神。
最后,尽管萧先生和现代新儒家共享“人文主义”理想,但是他们的“人文主义”却有不同的结构。萧先生的“人文主义”以自然人性论为据,尊重人对“欲、情、利”的追求,强调把人理解为感性与理性兼顾、情理兼备的“完整人格”。而现代新儒家的人文主义则以儒家的“仁”为出发点和核心,他们虽承认人的“气性”和“知性”层面,但强调它们需受人的“仁性”或道德层面的调整与轨约。
在此,现代新儒家面临的挑战是,心性儒学如何“开出”“新外王”的事业?牟宗三以其著名的“良知坎陷说”来解决内圣外王之间的联结,但是,这一说法一直以来都遭到强有力的挑战和反对。这些挑战和反对尽管大都基于误解,但仍然需要回应和澄清。相应地,如果把儒学仅仅理解为以人伦为中心的“仁义”之学、而不去努力澄清其心性论根据,明确其在兼具普遍性与个体性的主体⑨的构成中的作用,那么,所谓“仁义之学”便极有可能徒有其名,而“人伦”也极可能异化为维系专制统治的工具(儒家的“道统”亦因此沦为“治统”的背书)。
6)AR技术为商业提供便捷的销售方式。可口可乐、星巴克、宜家等商家以AR技术做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的广告并拉近消费者的距离,AR技术将颠覆传统广告行业[2]。
尽管萧萐父先生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应主要从我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6]93,但先生亦认同多维考察,故能正视现代新儒家的努力。以此,现代新儒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探讨,实是萧先生的真理“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多维互动”之态势的显现。我们可由此反思中国哲学与文化多维互动可能出现的途径。
总之,萧萐父先生与现代新儒家有着相近的学术追求。他们都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都致力于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都共享“人文主义”的理想。尽管其间存在着一些不同乃至分歧,但这些不同或分歧并非直接对立和冲突的,而是可以互补和互益的。因此,中国哲学启蒙的完成也需要吸纳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贡献。在厘清各自思想之边界的基础上,萧先生的思想与现代新儒家的追求,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其实也与萧先生所倡导的真理“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和多维互动”的态势暗合。
由于采样的频率远远高于电网电压的频率,所以,预测k+1时刻电网电压矢量ek+1可以近似等于k时刻的采样电压ek。电压矢量在空间以角速度ω做周期性的旋转,所以也可以用式(6)计算k+1周期的电压矢量。
今天,当我们地方立法机构及立法工作者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深入思考地方立法如何顺应新时代新要求,履行什么新使命新任务等系列新问题时,确有必要按照栗战书委员长推动地方立法工作与改革同频率的指示要求,通过在地方立法工作中坚持立法与改革发展相适应,突出地方特色,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真正形成工作合力,凝聚各方智慧,从而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能够得以充分发挥。
结语
尽管萧萐父先生与狭义的现代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究竟在何处、中国哲学的早期启蒙是否存在等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但在大方向上,他们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同意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需要在反专制、反奴性的基础上,挺立中国人的主体性和独立健全的人格,并进一步谋求民主建国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们也同意,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中国文化自身的支撑,不可能脱离自身的活水源头,因而都主张要在中国文化内部找到其现代价值的生长点。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这是一个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和多为互动的过程。 这一事业,是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者共同的使命。
注释:
① 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旨,此处不拟介绍萧先生船山学研究的成就,而仅止于提示理解先生船山学研究之意义的线索。
我跟我妈抗议,不能再叫我陈胖子了。她用没有拿铲子的手摸着我的脸,粗糙的掌心磨得我脸生疼,又将我往她怀里带了带,衣服底下她那厚实的脂肪柔软地包裹着我,我扭了扭头,没有挣脱开来,任她的手越来越用力地掐紧我的身体。
② 刘述先教授在《当代新儒家哲学概要》中,其实际用词是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和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亦即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学。本文认为,现(当)代新儒学总是由相应的这些儒家学者所承担的,所以,并未对“现(当)代新儒学”和“现(当)代新儒家”作出严格区分。此外,当代新儒学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哲人身故之后,亦有新的进境,他们的学生,如蔡仁厚、李瑞全、李明辉、卢雪昆、霍韬晦等,都用各自的学术成就,丰富和深化当代新儒学的思想,促进其理想诉求的实现。此外,余英时亦对现代新儒家的用法有所说明。其说见余英时的《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再版,第58-59页。
(1)操作人员必须先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特殊工种应持证上岗。严禁非指定机械操作人员操作机械,严禁违章操作。
罗四强笑了起来,说:“爸爸你也莫太贪心了。我们还得有姆妈,还得有老婆,还得有自己的伢。爸爸你占个角落就蛮好了。”
③ “内圣”之道,即《大学》所谓“明明德”之修身事也。所谓“明明德”即表现或实现个人内在本有的卓越品德,亦即是成就自我或自我实现。
④ 《宣言》说,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因为中国古代之文化,分明是注重实用技术的。这种观点背后的“科学”,应当解释为“工具理性”。中国文化之不“反科学”,实即指中国文化不反对工具理性,而能遵从逻辑和数学的要求;此亦可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之“注重实用技术”。实在说来,一个反对工具理性的文化,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于历史中的。
美方语料使用位移动词和指向动词臆造历史事实,描述中方“窃取美方知识产权,强制转移美方技术成果”的行为(如例[4]),目的是为其发动贸易战的无理行为寻求借口,并用标记影响的行为动词在话语中构建这些臆造事实产生的危害(如例[5]),企图给民众造成恐慌:
⑤ 《良知坎陷,如何可能?》一文载于《哲学评论》第1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再检讨》一文载于《孔子研究》,2014年5期。
⑥ 萧先生说,儒家传统的中坚人物董仲舒、朱熹不可能同意杜维明先生关于儒家传统是“消除封建遗毒的利器”的观点,而顾、黄、王、颜、戴等恐怕也坚决不会同意把自己与熊赐履、李光地等塞在一个门内。
⑦ 遗憾的是,萧先生或因牟宗三先生的“道统意识特强”而对牟宗三哲学存有偏见,将其定为封闭、排他、单维独进的“道统”论者。从表面上看,牟先生的“道统”意识似乎很强,如牟先生以儒学为中华文化之主流与常道、把荀子视为儒学的歧出、以朱熹为“别子为宗”等。但是,牟先生虽以儒学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常道,却亦能正视道家和佛家的地位和作用;他以“为道尊孟子,为学法荀卿”来表达荀子“为学”方面的积极作用;他判定朱熹“别子为宗”,却肯定其能补充儒学“纵贯系统”之不足。此外,牟先生所理解的“道统之道”,正是仁义之道或“能有所成就的创造性能力”,是由乾坤所代表的“始生—终成”原则,凡能感应和把握此“道”者,即是“道统”之承担者(参见拙文《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载《船山学刊》,2011年第1期,第128~131页),他和他的后学并不“垄断”“道的重获”(即道统,the repossession of Tao)。而牟宗三先生亦力图以“会通”中西来实现“返本开新”。因而,如果萧先生能“依义不依语”,也会在大体上引牟宗三先生为同调。
⑧ 若对熊十力、徐复观、唐君毅等先生的上述界说不误,则视牟宗三先生为与其师(熊十力先生)友(徐复观、唐君毅二先生)“同调”,亦为理所必然。
⑨ 关于“兼具普遍性与个体性的个人”,笔者认为这是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努力工作所欲实现的客观理想;如何建构这样的个体,便是牟宗三他们那个时代(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客观问题。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上)探讨了兼具“普遍性与个体性”的意义,在《人文讲习录》解释了客观问题与客观理想的关系问题。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庶几能恰如其分地理解现代新儒家群体的工作及其局限问题。
参考文献:
[1] 田文军.近世中国的儒学与儒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LIU S H.Essentials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M].Praeger Publishers, 2003.
[4] 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第四版.台北:三民书局,2011.
[6] 萧萐父.吹沙集[M]. 成都:巴蜀书社,2007.
[7] 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萧萐父.吹沙二集[M]. 成都:巴蜀书社,2007.
[9] 萧萐父.吹沙三集[M]. 成都:巴蜀书社,2007.
[10]周恩荣.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J]. 船山学刊,2011(1):128-131.
[11]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5:心体与性体(上)[M].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
[12]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28:人文讲习录[M].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
AllRoadsLeadtoRome:ComparisonandEnlightenmentofModernizationPath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TakingXIAOJiefuandModernNewConfucianismastheCore
ZHOU Enrong, FU Juanjuan
(CenterofLocalGovernance,Yangtze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8100,China)
Abstract: XIAO Jiefu’s ultimate academic pursuit is to explore the sourc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exploring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the philosophy of Chuanshan. Based on this, his philosophy of Chuanshan can be properly understood. XIAO’s effort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lead to the same goal as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which, through "turning back to the original and opening up a new world", can radiate the vit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us shoulder its new mission in the new era. Comparing XIAO’s different views on the specific way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with modern neo-Confucianism, and reflecting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m and their basis, it is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and quite enlightening to the cau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All roads lead to Rom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mparison of ways; XIAO Jiefu; contemporary new-Confucians
收稿日期:2019-02-26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科研项目“萧萐父先生‘中国早期启蒙说’研究”(SXJZX 2016-002)
作者简介:周恩荣(1976-),男,贵州普定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9)08-0011-09
〔责任编辑:邵 明,许 洁〕
标签:儒家论文; 儒学论文; 中国论文; 哲学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现代哲学(1919年~)论文; 《宜宾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论文; 2016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科研项目“萧萐父先生‘中国早期启蒙说’研究”(SXJZX 2016-002)论文; 长江师范学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