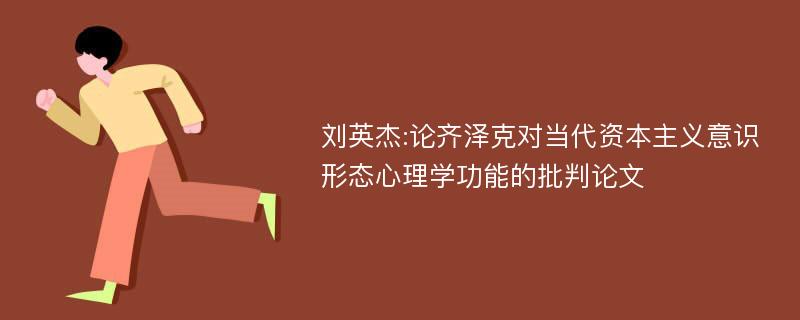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摘 要]意识形态的功能长期被外在化为社会价值导向、合法性辩护、社会控制等方面,实质上,意识形态同样作用于人的心理过程,体现在一种内在心理变化上。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运作机制的深刻揭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功能,即在认知层面,使主体丧失自我决断和批判的维度;在情感层面,激发虚假欲望,制造新的焦虑;在意志和行为层面,使主体在行为中保持与意识形态认同。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主体的内心在意识形态的运作下,似乎是可以治愈的,然而我们却不难发现这种治愈本身也是一种虚假。
[关键词]齐泽克;意识形态;心理学功能;当代资本主义
关于意识形态心理学维度的研究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说,意识形态概念的降生就部分源于心理批判。从柏拉图“洞穴比喻”开始驳斥人类感觉的可靠性,到培根“四假相说”贬斥人类心灵的先入之见,再到法国启蒙学者从感觉主义立场对传统偏见的批判,至特拉西创制意识形态概念作为观念学,企图通过观念向感觉经验还原摒弃传统的、权威的偏见。可以说,意识形态概念的降生离不开对心理的追问。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就有对无产阶级、民主派、农民等各阶层的社会心理的分析。而后,拉布里奥拉、赖希、弗洛姆分别将社会心理、群众性格结构、社会性格与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中介环节进行研究。此后,亦有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弗洛伊德对人类理性骄横的批判、对无意识——本能欲望的揭露,契入意识形态批判研究。但是,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功能却是意识形态研究中一个被长期集体无意识遗忘的领域。毋庸讳言,意识形态作用于人的心理过程,体现在一种内在的心理变化上,但意识形态的功能长期被外在化为社会价值导向、合法性辩护、社会控制等方面。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齐泽克在秉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回到弗洛伊德,发展拉康,深刻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运作机制。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运作机制的深刻揭露,有助于我们依据时代发展和语境变化进一步剖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功能,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为我国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以及更有效地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现实反思以及方法上的借鉴。
一、认知层面:使主体丧失自我决断和批判的维度
通常情况下,提及意识形态认知层面,即指涉认识论意义上对“虚假意识”的相关探讨,而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本身”,意识形态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物——他不强调存在与意识的简单对立,不是将心理作为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中介,而是在心理学视域下探究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齐泽克从人/主体同世界的体验关系出发,探讨意识形态如何直接作用于人/主体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于心理维度而言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主体的生成与发展,这是某种接近卢卡奇关于意识形态本体论的观点,是一种以否定之否定的升华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尝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齐泽克摒弃了马克思的“虚假意识”,他依旧将意识形态界定为虚假的:一方面,他将这种虚假性还原至主体的生成过程,赋予虚假性原初性的地位;另一方面,他揭露出虚假性已逐渐蔓延至社会现实全部的事实。齐泽克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现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渐成为某种无意识的自发形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意图使主体将其建构的生活方式视为理所当然,仿佛私有制或者雇佣劳动是天然的法则、货币是天然的等价物、贪婪或者营利是人的天性,让人们不加决断和反思、想当然地服从和践行。不难发现,这种将资本逻辑下资本主义建构的现实想当然地理解为天然的现实的背后,是对主体的自觉选择和价值判断的操纵,是主体自我决断和批判维度的丧失。
一般意义上,在认知层面,心理学功能或者说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让主体经由自由反思占有其被压抑的内容,使主体成为自由、自主的主体,把主体从无意识的他律支配下解放出来。但是,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功能旨在对主体的无意识加以直接社会化/资本逻辑化,意图使主体被意识形态彻底操纵,使主体丧失自我决断和批判的维度。事实上,对于主体生存境遇的追问由来已久,其间也一直伴随着对于主体精神/心理境遇的“应然”预设和“实然”批驳。这种“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张力是一种必然,二者之间的张力也往往作为一种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依靠主体自我决断和批判维度的发挥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而这种张力自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以来不断扩大,主体甚至在马克思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后,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即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心知肚明但依旧依依不舍、明知故犯的吊诡姿态。齐泽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主体的犬儒姿态的概括说明,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他将这种姿态概括为“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1]25,这意味着在认知层面,主体不愿再追问和反思,只愿沦陷于某种特定的随波逐流的轻松和惬意。
资本主义因其社会存在的对抗性本质和对资本增值、财富积累的无限追求,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掩盖社会对抗,而非解决社会对抗。资本主义最为擅长的掩盖社会对抗的手段即是将矛盾和对抗归因于他者,而归因于他者的谎言迟早会被拆穿,也就是主体自身的一清二楚,但主体为什么明明一清二楚却依旧坦然为之,失去自我决断和批判的维度呢?
据齐泽克所言,一方面,源自主体的自反性服从,即意识形态缝合失败后,主体无法“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继而主体自身回避负担、恐惧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自欺,主体产生某种对服从的依恋;另一方面,源自意识形态不仅作用于“知”,还作用于“行”的事实。
综上所述,在认知层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意图使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双向建构,变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单向度的操纵和支配,使主体失去自我决断和批判的维度,而随着自我意识的消融,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也将被扭曲,主体将沦为意识形态的自动机。
根据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运作机制的分析,意识形态仿佛就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戏剧——虚假的开头和虚假的封闭。从询唤——主体,以虚假的提问和虚假的解答捕获主体,使个体成为主体;到移情——认同,用虚假的欲望使主体与现实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再用对象a(object petit a)[注]对象a(object petit a)即欲望的客体——成因,简单来说,如果欲望的客体是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么欲望的客体——成因就是为什么想要得到这个东西,这与“剩余快感是欲望的客体——成因”并不冲突和矛盾,因为对象a即是剩余快感的具体化。将欲望和快感相结合,产生本身即是多余的剩余快感(surplus-enjoyment)[注]快感(enjoyment)并非快乐(pleasure),快感是某种罪恶之感,是痛苦的快乐,快感并不是一种直接自发的状态,它由超我的训诫控制。所谓剩余(surplus)并非某种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是指额外的、多余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剩余快感(surplus-enjoyment)就是对象a,因为剩余快感无法被具体化,对象a使剩余快感有了一个说辞,在齐泽克看来,剩余快感是被剥削者臣服于意识形态所领取的报酬。,维持欲望的连贯性,使主体成功进入符号秩序;最后疗愈——遗忘,将主体发现的矛盾、社会呈现的征兆用模糊了内在对抗的幻象[注]笔者认为,对象a与主人能指共同占据空洞主体(主体是分裂的主体,同时代表能指网络中的空洞位置)的位置,同时承担着匮乏和剩余的功能,执行着填补空洞的操作。其中,主人能指代表可能性,使符号秩序保持连续,用“缝合”填补空洞,当主人能指/缝合失败时,另一面的对象a/征兆便暴露出来,即当空洞不再能够被一个能指所填补时,填补它的就是一个幽灵般的客体。对象a就是这一客体,是主人能指的对立面,代表不可能性,用“界面”的功能使符号秩序出现“短路”以填补空洞,意识形态这个幻觉依靠主人能指(幻象)和对象a(污点)共同支撑,意识形态是一个悖论式的结构。重新阐释,用主人能指(master-signifier)[注]主人能指(master-signifier)即“没有所指的能指”,它将众多漂浮的能指绑定/缝合在某一确定的固定意义上,使能指进入符号秩序的网络,即赋予空白能指以意义,给予特殊的相关语境。刷新整个社会现实,或转移目标,或延迟冲突,使对抗/矛盾得以掩盖,使主体放弃追问、再度询唤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悖论式关系,这一自导自演的过程会不断上演。那么,在这个一而再、再而三以虚假欲望和剩余快感捕获主体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重复的心理作用,不禁会产生催眠的效果,使主体对意识形态和个体现实体验的不一致习以为常,久而久之主体就放弃了对矛盾的追问和反思。此外,对矛盾的转移和遮蔽,使意识形态仿佛永远停留于符号秩序这一表层,即把意识形态的功能和动因全部外在化,视为一种外在关系,使意识形态主体,甚至意识形态专家们忽视意识形态的心理学视域和功能,使意识形态批判“自觉”忽视内在的向度,这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研究者们长期集体无意识遗忘心理学视域的原因之一。在这种双重作用下,意识形态似乎成为某种无意识,而此时的主体也就真真正正地成为意识形态的自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主动设计/制造焦虑、恐慌和愤怒情绪成为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主旋律,国内教育领域一些自媒体和培训机构的焦虑营销也使得焦虑情绪在学生和家长之间蔓延,可见,对意识形态心理学功能、心理运作机制的反思势在必行。伴随着第三次信息革命出现的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空间的范围不断延展,在其中人们摆脱了实际身体和现实的阻碍,但在这个空间中,欲望设法幸存了下来[4],情绪自然也得以幸免并有无限放大的趋势,在所有信息(书、电影、数据)和行为都被计算机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心理学功能的发挥可使意识形态的进入依旧畅通无阻,甚至悄无声息。
首先,依据齐泽克提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本身”的论断,仿佛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撑,随着大他者(the Other)[注]大他者(the Other)大约相当于符号秩序,我们在其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如名字、种族、家庭等,在某种程度上,大他者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现实”的一个部分。的终结,社会现实的大厦就会顷刻崩塌。实质上,齐泽克这一观点中可能包含着一般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混淆,有将意识形态泛化至整个人类意识/文明的趋势,所以才有了“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本身”的提法。而所谓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撑,社会现实的大厦就将顷刻崩塌,颠覆了意识形态,主体、整个社会都将湮灭,其意义并不是把意识形态定位成整个社会的最高统治力量,仿佛观念一经瓦解,现实社会就将分崩离析,而是强调人/主体同世界的体验关系,强调一种心理的认知过程、情感体验、情绪变化。其次,依据齐泽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运作机制的分析,不难发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学功能最为狡诈的地方在于——看似具有积极功能的虚假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的治愈,对主体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促成,似乎成为其自身必不可少的合法性根据,但其治愈的实质是一种剩余快感的给予,这种治愈是资本主义利用“剩余”收买革命的惯用伎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促成的认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意识形态操纵,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再生产。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的是,主体所回避的负担和恐惧本身就是由资产阶级为获得剩余价值所制造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治愈和必不可少不过是一种让人沉迷的欺瞒。
(1)多点投加方式的优化。在最佳反应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投加方式进行实验,考察多点投加芬顿氧化的最佳投加方式。
二、情感层面:激发虚假欲望 制造新的焦虑
生物陶瓷棒的主要成分是磷酸三钙生物陶瓷骨复合材料,其化学成分与骨中的无机成分较为接近,与人体有着较高的生物相容性,具有力学强度佳、亲水性能好、可降解吸收等特点[9-10],且无致癌性、无毒性、无致敏性,其安全性较高,能够修复股骨头坏死的区域[11]。生物陶瓷棒,其具有较好的细胞亲和性、生物相容性,且其孔隙率较高,可对骨生成诱导,其结构与人体松质骨较为相似,从而可在进行骨诱导时,对坏死区域的再血管化进行促进,更好修复坏死区域[12-13]。
综上所言,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主体的欲望失去了真实性的一面,资本主义依靠设置另一个虚假欲望来解除上一个虚假欲望被识破后给主体所带来的焦虑和恐慌等负面情绪,根植于生物冲动的人的天性的激情、焦虑等情感体验和情绪变化都沦为了资本构造的产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依靠剩余快感的给予,激发虚假欲望,延迟其对主体造成的焦虑,产生看似积极的疗愈,实则是维系其自身再生产的一场自导自演。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欲望的设置出现于询唤的环节。在询唤的过程中,大他者提出问题并解答问题,即告知主体他想要什么,因为解答主体的疑惑才产生对大他者的需要,问题和答案都由大他者提供,这是一个自导自演的过程,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的开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话语的叙述将其内在的对抗性本质描绘成某种主体的匮乏,从而构造主体的欲望,欲望由对象a支撑,并在对象a的作用下与快感相结合,产生剩余快感,以维持主体现实体验的连贯性。但是,这一欲望并不是真实的欲望,而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虚假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设置的欲望。可笑的是,这并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的全部,其在自行回答向主体发出的询唤时,又用“他者”实现主体的虚假的欲望,即由他人替主体完成这一欲望,如“罐头笑声”“罐头眼泪”。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欲望的激发和实现都是虚构的,其设置的欲望只是对自身内在对抗性的永无止境的掩盖。
驱动真实欲望的是人的自主性,齐泽克将人的自主性等同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注]齐泽克认为死亡驱力(death drive)不是一种生理范畴,死亡是符号秩序本身,是像寄生虫一样对生命实体加以殖民的结构,死亡驱力是一种自我破环的冲动,是不能用客观词语来解释的。,死亡驱力不断威胁要打破/颠覆意识形态的象征框架,所以拉康强调“涉及欲望不让步”。因为一旦我们放弃自己真实的欲望,就会陷入一个恶的循环。在笔者看来,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的自主性的支撑下“涉及欲望不让步”与对欲望的激发都是社会现实得以存在并有效存续所必需的内容,是个人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两者共存,生命的实在界才能完成其生成与腐败的循环,意识形态和主体的悖论性结构才能不停运转。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似具有积极功能的虚假性也借此生根发芽,如《恩格斯致弗·梅林》中所言,推动意识形态专家们创造意识形态的是他想象出的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而真正的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或者从他自己的思维中,或者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3]。恩格斯所指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立场,习惯于从思维和观念出发去推演存在的发展,不了解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揭示出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仅仅满足于虚假的动力,沉湎于用观念支配现实的幻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们在这种立场下编造出来的永远都是虚假的意识,设置的永远都是虚假的欲望。再看看资本主义祭出的新的主人能指——自由,如马克思所言,这种自由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自力挣得的自由,一种资本压榨工人的自由,一种狭隘的、私有财产的自由。在这种主人能指的绑定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欲望只能是商业化的、快餐化的、私有制似的欲望,是狭隘的、隔离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目的性很强,根本上都将归结到对财富的快速积累。在这种主人能指绑定下的主体往往不能用辩证的、动态的、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欲望和欲望的实现。
依据齐泽克的逻辑,当真实欲望与虚假欲望产生对抗时,焦虑便随之而来,这同时是一种对危机/创伤的逃避。焦虑的初次登场,是在个体成为主体之时。人由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到具有主体性的人需要抛却自身的陌生性进入符号秩序。也就是说,主体的合法性存在以缺失为根基,个体通过牺牲自身的特殊性成为主体,这种牺牲不是指化为乌有,而是通过牺牲使主体得以成立,如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就是建立在压抑本能这一牺牲上的。继而,按照齐泽克对主体的解读,主体永远不会被主体性所填满,主体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丧失对现实感最基本的支持,经历创伤,产生焦虑。可以说,这种焦虑是原初性的,是先验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焦虑产生于大他者的询唤,复发于虚假欲望的虚假实现,由于欲望自身及其实现都是虚假的,新的焦虑产生,新的焦虑又由大他者虚假的抚平。当大他者迫使主体提出这一绝望的问题时,即著名的“Che vuoi?”(“你想怎么样/你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焦虑就开始产生。因为大他者的提问深藏着关于提问的暴力,其提问针对的是对象a,但对象a位于主体的空洞位置、位于实在界,而实在界永远无法被符号化,大他者将其内在的不可能性转移为主体的无能为力,大他者向主体提出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使主体产生愧疚、羞耻与焦虑。而后,大他者自行“解答问题”,用虚假欲望的虚假实现把主体从不堪忍受的焦虑中解救出来,因为大他者给出的并不是问题的真正答案,这种解救不过是一种焦虑的延迟。当真实欲望与虚假欲望产生对抗时,新的焦虑就会出现,此时,大他者开始重新构造现实,以新的焦虑为代价帮主体遗忘这个旧的焦虑,如此循环往复。
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之间,存在着血浓于水的同源关系”[1]3,即无论是商品的秘密还是梦的秘密都在于其如何运作,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秘密亦在此处。如同梦的无意识欲望并不存在于潜在梦思中,或者说梦的秘密并非释梦后的某些意义,梦的工作(压缩—移置—视象—润饰[2])才是做梦的本质,即梦的无意识欲望藏身于将潜在梦思转换为显在梦文本的伪装性、掩盖性运作之中;商品的秘密同样藏身于商品形式自身的生成中,商品交换行为成为某种无意识的天然思维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奴役在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的外表下被巧妙地伪装起来,即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奴役藏身于商品形式这一绝佳的掩饰和伪装运作方式之下;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秘密同样藏身于其运作方式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就是为了掩盖潜藏于其“不证自明”的表面结构下的结构性不平衡,作用于意识形态主体内心的情感层面则体现为,激发虚假欲望,制造新的焦虑。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其“‘合理性’本质上就是‘合法性’,而‘合法性’本质上就是‘合意志性’”,“合理性乃是意识形态制造的一种幻想”[5]141-142,而合意志性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认同。那么,看似不同的意识形态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实质是一回事,二者都是非理性的产物,需要寻求心理学维度的剖析。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绝对的、非理性的服从,简单来说,就是认同。与此同时,他认为,在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后,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在行为中实现的,意识形态主体呈现出一种一清二楚但依旧坦然为之的状态,这种状态源于意识形态幻觉还处于人的行为一边。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学认同功能既作用于主体的认知层面/情感层面,又作用于主体的行为层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支配思想,支配行为,最终成为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制造的焦虑一方面源于上述的原初性过程,即当意识形态幻象框架崩溃时,主体的意义感、现实感、安全感丧失,主体被剥夺了自我身份,产生焦虑;另一方面来源于对焦虑的不恰当解除,具体而言,或是将创伤和无能为力推给他者,如反犹主义中的犹太人,或是将创伤和无能为力均衡化,如西方鼓吹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此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焦虑的解除看似是积极的心理治愈,实质是对矛盾/对抗的转移或者延迟,企图遮蔽冲突,维系其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些看似积极的心理功能,都让我们对自身的主体性更加困惑。
但是,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人具有自主性,自主性的逻辑能够为主体挣脱现存的范式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诚然,人并不是提线木偶,而是一个自由的存在,自我决断和批判的维度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操纵必然永远无法真正实现。可是,意识形态作为人由自然存在物转入社会存在物的必然升华物,主体之所以由个体发展成为主体又依赖于意识形态。那么,面对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双向建构,难道就要具有颠覆意味的以中性的姿态看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基于齐泽克关于“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本身”的论断,如果颠覆了意识形态,主体、整个社会都将湮灭?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基于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运作机制的分析,不难发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运作的第一步就是对欲望的设置/激发欲望。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激发的并不是源自个体自身需求的真实的欲望,而是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虚假的欲望,其对欲望的激发实质是一种对欲望的设置。对欲望的设置涉及一个关于欲望和匮乏的结构,这一结构可以追述至齐泽克所推崇的拉康的伪主体观,源自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基点——主体的生成悖论。在齐泽克看来,主体合法性存在的背后是天然的匮乏,这种匮乏既是主体生成的可能性又是主体的失败之处,并且这种匮乏是永恒的,这意味着主体永远无法被主体性所填满,这种原初性、永恒的匮乏使无限的欲望成为主体性建构的内容。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主体生成中的匮乏和欲望失去了清白的一面,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狡诈地利用了主体性确立过程中出现的空位,借此植入了自己的意志,使主体的欲望和情绪都沦为了资本构造的产物。
三、意志和行为层面:使主体在行为中保持与意识形态认同
菌种活化和菌悬液的配置:分别挑取菌种在相应的培养基上划线,然后置于恒温培养箱中培养(37℃,36 h)。用接种环挑取少量活化后的菌种接入装有无菌生理盐水的试管内,震荡均匀,制成菌悬液,然后用无菌水进行稀释,使活菌数为107-108cfu/ml,备用。
钾肥价格继续受到强劲需求和供应紧张的支撑。与2017年第三季度相比,主要现货市场的价格上涨了20%-30%,与印度和中国的合约价格分别上涨了50美元/吨和60美元/吨。预测2018年全球钾肥出货量将上调至6600万-6700万吨。
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性在于:首先,其创造并维持着意识形态场域的一致性,把一致性赋予社会实践的多元性;其次,其使主体从某种空无转变为一个在所有意义上都能理解的人,使主体不再孤独,使行动有了意义,使主体间能够相互交流、交往,拥有共同的话语、思维基础。意识形态认同可以说是社会、共同体产生和存续必备的条件之一。然而,依据齐泽克的逻辑,在认知层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与认同的崩溃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亦步亦趋地认同会损害意识形态大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运转要求同它的表现结构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以对它的不认同所产生的快感为支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以不认同为真理。这可以类比于齐泽克对“存在于法律中的这种内在的和构造性的分裂”[6]66的论述,“法律分裂为成文公法和它的阴暗的、‘未成文的’、淫秽的、秘密的法则”,“那些把共同体最深地‘团结在一起’的东西与其说是对那些调整共同体‘正常的’日常流程的法律的认同,不如说是对违反法律、悬置法律的特别形式的认同(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对一种特别的快感的认同)” 。[6]67在齐泽克看来,超我[注]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动的主体”,超我的意识形态保存过去,保存历代相传的风习(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2.)齐泽克认为,超我的这种限制和指令依据的并不是某种实证性理由,而是因为“律令就是律令”,这同时是超我指令的淫荡性所在。在维系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意义上,超我和公共法则是根本一致的,“超我出现在公共法则的失败之处,在这个失败之点上,公共法则被迫在一种非法的享乐中寻求支持”。就是这个秘密法则,它凭借对法律的内在的违反为社群带来一种共享的快感以维持集体的团结。在意识形态领域,或者说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中,符号法则担保的意义同样以超我提供的快感为支撑,即符号法则提供的意义认同以不认同/违反认同为基础。在一般人看来,认同会带来某种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认同带来的是意义和快乐,但快乐并非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快感”,快感是一种罪恶之感,是罪恶的快乐。在弗洛伊德看来,“罪恶之感也即超我压迫自我的一种表示”[7],齐泽克进一步将这种快感逻辑融入了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齐泽克认为,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认同并未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依然停留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并且这种不认同维持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再生产,这种不认同提供的快感——非法的享乐,使主体被意识形态彻底驯服。
依据齐泽克的逻辑,在大他者召唤中的意识形态认知,即询唤,就是一种认同行为。大他者召唤,个人回应召唤,个人由个体变为主体,即达到了某种符号同一性,由对这个召唤的回应开始,认知层面的意识形态认同就产生了。它包括想象性认同和符号性认同,想象性认同维持主体的自我同一性,但必须时刻谨记这种自我同一实质是拉康的“他者欲望”,符号性认同是一种位置认同,使主体能够融入符号秩序。主体往往在想象性认同和符号性认同之间徘徊,因为通过体会和理解之间的不平衡,或者超我的介入,认同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认同总要被击溃。可以设想,如若就此简单地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认同与认同的崩溃理解成为结构性的必然,让其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产生认同与击溃认同的不断循环麻痹了主体的认知,进一步产生催眠的效果,加深主体自我决断和批判维度的丧失,使主体失去自觉意志,渐渐变成无意识的自动机。这一状况与前文所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激发欲望又掩盖欲望、解除焦虑又制造新的焦虑的境况是如出一辙的。与此同时,以虚假欲望为支撑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模式是静止的、功利的,其对财富积累的要求是必须立竿见影的,其认同对象和欲望对象均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阶层制定,并不服务于真实的个体自我。
变频器电源侧常安装三相不可控桥式整流器,中间直流回路产生的电压会随着电网电压升高而升高。如不采取跳闸保护将烧毁变频器。如果变频器安装位置比较接近变压器时,输入端电压将远大于380V,中间直流回路承受电压将会更高。因此,可利用变压器改变绕组分接连接位置的调压装置调至低压档来降低电网电压来控制中间直流回路电压升高。
齐泽克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已“广为人知”的情况下,人们依旧对这种意识形态“依依不舍”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幻觉处于人的行为一边,意识形态认同同样产生于行为层面,非理性认同已经物化于社会场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主体在行为中保持认同,人们的现实、人们的行为早已受到了意识形态幻象的引导。而行为认同奏效的原因在于,经由几个世纪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人们“理解的前结构”和日常生活习惯。可以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主体越过认知认同直接产生了无意识的行为认同,即齐泽克所说的意识形态成为了社会存在本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由心理运作机制达成了无意识行为渗透的目的,实现了使主体在行为中保持与意识形态认同的功能。齐泽克借帕斯卡尔关于“习俗”和“信仰”的解读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律令就是律令”,“摒弃理性的论证,投身于意识形态仪式,通过重复那无意义的姿势使自己变得麻木,假装你已经相信了什么,到那时,你就会真的相信什么。这就是实现意识形态皈依的步骤”[1]38。我们认为,行为认同之所以奏效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维度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人们遗忘了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功能,而对意识形态心理学功能的遗忘让我们放弃追问,无视这种误认/虚假性,产生某种看似自发的习惯或信仰。
【普氏《核子周刊》2018年9月13日刊报道】 2018年9月11日,美国X能源公司(X-energy)高层管理人员在与美国核管会(NRC)工作人员会谈时表示,Xe-100的概念设计目前已完成约50%,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与核管会进行Xe-100设计认证申请提交前的互动,并在2022年或2023年完成这种反应堆的设计。Xe-100是一种200 MWt/75MWe的高温气冷球床反应堆,基于过去50年在高温气冷堆领域的研发和运营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律令就是律令”的阐释中,包含着一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似具有积极功能的虚假性的典型姿态——“为人接受,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1]37依齐泽克所言,只要身处社会现实/象征空间,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这个意识形态的套路——参与日常生活的正常表象只是一个骗局,对欲望的追随、对焦虑的解除、对自我和社会的认同终将被击溃,但意识形态又会不断消除这种麻烦,重新激发欲望、解除焦虑、实现认同,意识形态会不断填补空洞,使主体的空无变成一个丰富的人格。由此看来,意识形态不只是对主体的心理剥削与奴役,它还是一种疗愈,解除了主体内心的恐惧与焦虑,缝合了创伤,抚慰了心灵。但这不是主体牺牲自我、逃避自由、失去批判维度的借口,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具有的积极功能,这只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又一个让人沉沦的剩余快感而已。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统治和奴役依旧如故,它们在物与物的伪装下有恃无恐,又披上了新的种族主义、移民问题的外衣。如同“物质生产中的对立,使一个由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8],主体生成中的“误认”,使一个由欲望构成的认同模式成为必要,但关键的是,并不因为必要,不管作用好坏,就都是可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似具有积极功能的虚假性也体现于此。诚然,“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真正的主体性根植于意识形态之中,但并不因为是主体生成的必要,是内心安慰的渠道,就都是可取的,“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获得自觉的批判意识,个人才有可能找回已经失落的自我,并确立起真实的主体性”[5]3。诚然,对欲望的激发是个人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焦虑的解除是个人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所需,对认同的维系是个人和社会得以存在并有效存续所必需的内容,但并不因为必要,就都是可取的。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功能协同作用于主体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多个层面,使意识形态主体“自觉”舍弃自我,游走于虚假欲望的再生产之中,满足于焦虑的虚假解除,最终在行为中皈依。其中看似积极的功能,实则是对主体的欺瞒。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运作机制看似是一个闭路的循环,但实质上却未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固有矛盾,这一社会在主体自主性的驱动下终将走向灭亡。事实上,无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都必然作用于主体的心理过程,发挥某种心理学功能。这一系列心理学功能必然成为社会价值导向、合法性辩护、社会控制等外在功能得以内化的深层助力。故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功能研究、心理机制建设,要时刻警惕类似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心理学功能虚假积极性的发生,谨防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内涵与实质被抽空,要激发并满足主体的真实欲望,让主体在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发挥下,实现认知认同下的行为认同,要尝试建构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同为旨归的心理运作机制。
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也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乡村振兴中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实践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观念新颖、技术先进、理论要求高。这无疑是地方高校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切合点,是高校人才锻炼和理论知识应用的最好平台和机遇,同时也有利于高校综合办学质量的提高。
[参 考 文 献]
[1]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2]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0-14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2.
[4]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3.
[5]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M].胡大平,余宁平,蒋桂琴,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7]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7.
[8]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M].郭大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09.
[收稿日期]2019-02-1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研究”(18KSB050);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思政课专项“当前大学生认知特点、行为规律与引导对策研究”(SJGSZ2017007);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问题、原因及其对策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GK2220260130)
[作者简介]刘英杰(1964-),女,河北肃宁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6-0013-10
〔责任编辑:杜 娟 杜红艳〕
标签:意识形态论文; 主体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欲望论文; 虚假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哲学论文; 《学术交流》2019年第6期论文; 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研究"; (18KSB050)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思政课专项"; 当前大学生认知特点; 行为规律与引导对策研究"; (SJGSZ2017007)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问题; 原因及其对策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GK2220260130)论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