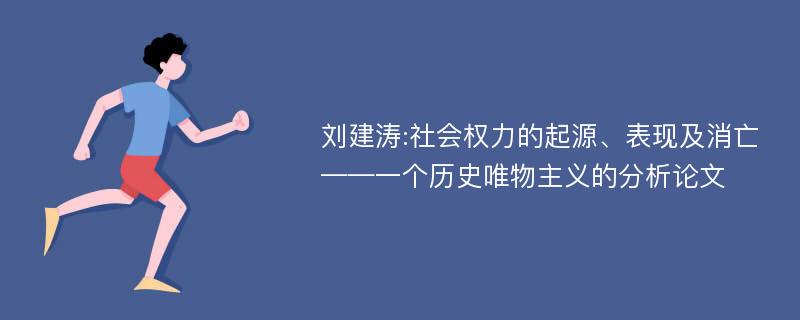
摘要:社会权力是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正确理解社会权力概念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石。社会权力是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非理性的感性力量关系,它起源于自发分工造成的感性活动的异化。社会权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土地私有权,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资本,资本是社会权力与物质财富的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资本发展的最大界限就是资本本身,从它的界限中会生长出否定资本的种种感性力量,从而导致资本权力的消亡,使有个性的人代替偶然性的人。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感性活动;社会权力;土地私有权;资本权力;资本消亡
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历史存在论,抓住社会权力这个核心概念可以避免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误读为近代的用概念、范畴做成的知性理论。经济学家讨论的是用经济范畴做成的经济事实,社会权力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之外,马克思则揭示了经济范畴背后的对抗性的力量即社会权力。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属于历史批判科学,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权力都是社会权力的派生物,不可混淆。目前学界从社会权力的视角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较为少见,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读者可以参考王德峰的《社会权力的性质与起源》、潘乐的《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等。从发表的论文看,主要是研究了社会权力的起源,而对于社会权力在不同阶段的体现,尤其是对社会权力的现代体现即资本权力以及资本的自我否定导致的资本权力的消亡,学界研究得不充分。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较系统地分析马克思社会权力的感性活动异化的起源、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即土地权力与资本权力)、以及社会权力因自身矛盾而导致的消亡。这对于我们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和共产主义渺茫论,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权力起源:感性活动的异化
人在自然界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是感性存在,感性存在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改变自然而形成的人的存在,它具有历史性。人的感性存在不是茹毛饮血的肉体存在,肉体存在不需要创造,它是一个物种的存在,而感性存在需要以属人的方式吃穿住用,需要赢得人对自然界的自由,即创造新的感性自由,这一切都是由人的活动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因此,马克思认为,感性活动就是创造人的感性存在的活动,既是改变自然物的活动,同时又是创建或改变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活动。感性活动所创造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初形式是家庭,“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1](P532)。但是,马克思谈论的家庭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家庭,即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所指向的并不是生物学上的自然联系,而是指向人与人最初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被自觉地意识到就是产生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感性伦理,不是理论化的宗教、道德、哲学。在这种感性伦理中流淌的是生命情感、爱、责任。
在这种家庭关系中,存在着以萌芽的形式隐藏着对抗性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1](P536)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种家庭关系本有的伦理关系、亲情转变为具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属于另外一种更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突破家庭伦理关系的范围而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创造感性存在的活动就同时是创造感性需要的活动,即形成对自然界的感性自由。人之所以需要感性自由是因为人是时间性的存在,倘若一个人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生存而忙碌奔波,没有自己处置的闲暇时间,马克思认为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都不如。所以,对感性自由的强烈需求一定会促使人类去实现它,这种实现同时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感性交往的扩大,而这种感性交往的扩大一定会突破家庭的感性伦理,去创造一种保存物质财富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可见,生产关系的产生是必然的,随着部落与部落之间交往的扩大,即战争和贸易的广泛展开,随着人口增长而产生的新需要,这一切都超越了家庭的范围,走向了家庭伦理的反面,即走向了社会对抗。生产关系从被创造出来的第一天起就具有了社会对抗的性质,它以社会对抗的方式保存社会财富,这种对抗性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社会权力”。
数学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不仅仅是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研究者来说,数学既复杂又有趣,对广大学生们来说,数学是我们从小学起就开始接触的科目.学好数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培养良好的数学解题思维却对学生学习数学的道路有很大的帮助.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生产关系是被生产出来的,这意味着自然界的社会化和历史化,而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是非理性的社会权力,它不是一种观念、范畴,而是一种感性力量关系。这种感性力量具有压迫性,马克思指出:“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1](P614)马克思一开始对作为一种对抗力量的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并不清楚,只是对它的客观性在《莱茵报》时期有所体会,认为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空气一样如影随形,突出表现为物质利益。随后在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真正认清楚了它的本质,马克思指出:“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1](P542)对财产状况的占有恰是所有制的核心内容,从所有制中产生了支配他人的社会权力,因此,起源于生产力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力,私有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就是不同的社会权力。首先,社会权力(social power)指向在人与人的感性交往中形成的人的关系,自然界没有权力关系,狼吃掉羊并不是在行使它的权力,只是一种生物链的关系。其次,社会权力是非理性的非观念性的感性力量,即对抗性的力量,这种对抗性体现在一部分人统治、支配、奴役另一部分人的关系上,社会权力才真正说出了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这种对抗性的权力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表达,即物质利益。当我们用物质利益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抗,因为在未来的真正人类社会不会有物质利益这个问题。最后,社会权力关系的结构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社会的物质利益结构,它的法的政治的表达就是法权、政治(国家)权力(political power),观念的表达就是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用图1简要地表示:
图1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
从图1中可以看到,社会权力上升到法权是经过了意识形态论证的,法权把一个非理性的社会权力变成一个合法的东西。其实法权是社会权力的法的表达,是披上观念、理性外衣的社会权力,是对感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权力的事后追认。而法权的贯彻和落实必须以政治权力为保障和后盾,政治权力则是社会权力的政治表达,正因为这样,政治权力也是一种感性的力量,物化的体现就是军队、警察、监狱等。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存在论理解。如果认为法权决定了社会权力,马克思说这是实践的唯心主义,属于康德的法权学说。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存在论讲的就是社会权力的起源与发展。
社会权力是从感性活动中生长并异化出来的,整个社会就是围绕社会权力来构建与展开的。感性活动中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就是对抗性的关系,社会权力是由于感性活动的异化而产生的。感性活动由于内在的矛盾而发生了自我分裂,从而导致自身的异化,使得从感性活动中形成的类的力量脱离个人、超越个人之上,进而反过来聚合为支配个人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导致感性活动自身异化的因素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把这个异化因素归因于自发分工。分工的英文表达是division of labor,就是劳动的分配,不同的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人,分工并不意味着异化。但是,如果分工不是理性协商的结果,不是自愿的结果,而是自发的,则是自发分工。自发分工是一种强制性的感性交往力量,它脱离所有参与交往的个人,反过来成为支配所有个人的物质力量,只要人们想要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就必须屈从于这种物质力量。迄今为止,自发分工仍然规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生产力越发达,自发分工的体系就越发达,二者相互促进。
式(1)中,S为变电站所属所有10 kV馈线负荷全转移标识的乘积。如变电站任何一条10 kV馈线负荷不能全部转移,即其中任一个SN=0,则变电站全停校验结果为0,不能实施全站停电。由此可知:要使S=1,该变电站所属所有10 kV馈线负荷全转移标识均为1,才能够实现变电站全停下的负荷全转移,即变电站全停通过;当S=0时,该变电站所属10 kV馈线不能够实现变电站全停下的负荷全转移,即变电站全停校验不通过。
二社会权力不同历史时期的体现:土地权力与资本权力
作为人与人之间对抗性关系体现的社会权力是从阶级的财产的占有中产生的,因而社会权力也必然要通过物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权力主要是通过土地的私有权表现出来。马克思认为,耕地、水、森林等等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在封建社会中个人受自然形成的工具的支配。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土地被认为是主要的财富,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若干重要的使用价值的增多自然就成为了财富的主要代表,譬如五谷丰登、良田万顷、牛羊成群,这是具体劳动创造出的感性的社会财富,甚至某些使用价值还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在封建社会中,土地及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土地占有的人格化代表是地主,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等级的占有,农民则是具体劳动的人格化,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就是作为社会生存条件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对具体劳动统治的封建社会形式。而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土地,因为土地是经过了劳动的耕作,加入了农民的劳动,还形成了土地的必要肥力。因此,封建社会的贫困是从阶级的等级压迫中产生的。
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与资本的自我限制交织在一起,即资本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资本自我消亡的过程。一方面,资本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它把生产过程直接变成科学技术的直接应用,以获取最大额度的剩余价值,但这同时也为更高的社会到来创造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也促进了人的社会化和人的多方面能力的空前发展,甚至使个人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与此同时,资本也打开了使用价值生产的广阔的丰富领域,不断探索事物的新属性,并发现事物旧属性的新作用,从而创造并满足了人的不同层次的需要。
而取代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权力也是通过物体现出来的,这种物就是以货币表达的价值的自我生产,即资本。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1](P555)。资本的增值就是价值的增值,就是货币的增值,也就是社会权力的扩大。资本,即自我生产的货币是财富的真正代表,而活劳动则是为货币(资本)的增值服务。故此,在现代社会作为资本的货币君临一切,成为社会的主导原则和绝对命令,具体劳动(活劳动)只有为资本、货币的增值服务的时候才能被确认为有效的劳动,否则只是个人的癖好,资本好像一个牛魔王,它把全世界当作献在它面前的牺牲品。因而作为资本的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反映的是更为深刻的社会生存条件,即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对抗。资本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社会性的物质力量,是现代的社会权力,货币是它的物化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4](P293)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又明确指出:“资本实际是当作‘关系’来说的,不只是当作‘蓄积的资财’,并且是当作一种全然确定的生产关系。”[5](P362)
可见,资本就它作为生产关系来说,不是物,而是以物为中介的一种具有权力性质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指向人与人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并且,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可以量化地计算的,计算的单位是货币,因为货币是可以量化计算的。资本就它作为生产力来说,是通过机器、技术、商品等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的物质财富,目的在于资本的不断增值,只不过凝聚在物质财富上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因而资本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是社会权力和物质财富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表现为支配劳动,限制劳动的权力,表现为与劳动无关的财富。”[5](P233)在现代社会中,拥有或追求超过自己生存需要以外的大量货币,就是在追求社会权力,追求支配别人一部分感性生命或生命时间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我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联系,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6](P316-31)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权力即资本权力的增长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财富不平等分配关系的加深,意味着工人贫困的加深。工人与社会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社会财富的增长反而加深了工人的贫困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悖论。
通过对生产单位产品能耗较高原因的分析,其中蒸汽能耗占白酒生产过程综合能耗的80%以上。许多厂家没有节能工艺与设备,对酿酒生产过程中二次蒸汽利用研究不够深入,不能多次有效地合理利用余热,造成热能利用率不高,酿酒生产汽耗较高。目前国内地方及行业标准中已逐步列入白酒制造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限额指标,针对企业对于白酒生产过程节能降耗的需求,通过已建成的一套酿酒生产节能系统进行实验平台测试,对相关能源消耗数据分析,为企业在白酒生产过程中挖掘回收水、汽资源提供有效的技术途径。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发展的四重界限的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一次的大发展必然会触及它自身的边界,从而从中生长出否定自己的感性力量,因而它是历史的存在,不是永恒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只有)资产阶级的浅陋,认资本主义形态是生产的绝对形态,从而,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7](P306)而资本主义的扬弃不是理性的事情,需要新的感性力量,这种新的感性力量的代表就是由资本产生的作为雇佣劳动人格化的具有扬弃资本原则的新的感性意识的无产阶级。
但是,西方学者霍克海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然而,其社会基础,即资本关系却纹丝不动。”[8](P346)正因为资本的关系即社会权力关系未发生根本改变,所以,工人贫困和资本家财富增长的相反的共生关系在现代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的逆转,反而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以美国为例,收入前10%的家庭在1989—2013年的增长速度远大于收入后50%家庭的增长速度,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不平等进一步加深。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就是社会权力的扩大,而社会权力的扩大,不平等的加重一定会带来感性的冲突,而感性的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带来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是理论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社会斗争解决。因此,工人不仅是为了重新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而生产,同时也是为了重新增大支配自己的资本的权力、货币的权力而生产,而这个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工人贫困化的过程。
大洋钻探的另一大挑战是钻头必须在操作中期更换。海洋的地壳由火成岩组成,这些岩石在钻头达到预期深度之前就会将其磨损。出现这种情况时,钻工将整个钻杆拉出,安装好新钻头后再插入同一个钻孔。这需要引导钻杆进入漏斗状的再入锥。再入锥的宽度不到15英尺,放置在海底的钻孔口。这一过程在1970年首次完成,它就像把一根长长的意大利面放入奥运会游泳池底部宽0.25英寸的漏斗中一样。确认板块构造
而社会权力要成为社会的规范秩序就必须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政治权力是合法的公共暴力,这个合法性需要得到意识形态的论证,通过意识形态的论证获得人们普遍的价值认同。这样一来,社会权力就被表达为法权、政治权力,然后它们再反过来捍卫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进而形成现代政治国家。从对抗性的社会生存条件里产生出来的社会权力,透过意识形态的论证上升为法权、政治权力,而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政治表达,是维护社会权力的感性力量。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权力:一种是在政治层面的权力,即政治权力,另一种是在物质生活关系层面上的由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两者都是感性的力量,但马克思一定要追问政治权力的根源,结论就是政治权力是在社会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权力的派生物。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政权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1](P655)
三社会权力的消亡:资本权力的自我否定
私有制的不同发展阶段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不同的阶级占有,从而从不同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中产生的社会权力也具有不同的历史表现。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阶段,因而社会权力的最高表现就是资本的社会权力。探讨社会权力的消亡也就是探讨资本这种社会权力的消亡。但是,如果把资本、雇佣劳动、价值、利润等清洗感性内容的经济范畴看成是非批判现实的永恒不变的,进而把生产关系看成是对生产关系进行理论抽象而形成的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经济关系,甚至把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价值看成是物质的材料,“价值不是人类活动(劳动)之一定的社会的存在方法,却是由物材构成的,那就是由土地、自然及这种物材的种种变形构成的”[7](P31)。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永恒的非时间性存在,历史就此终结了。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就是聚焦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等经济范畴所形成的经济事实领域,他们不会从资本的运动中发现使得经济事实、经济关系、经济范畴得以成立的社会权力(即异化的感性活动),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要否定资本的权力,而是对其进行细节的修补、完善,以期建立一个永续发展的资本主义,而这只是天真的幻想与骗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12](P592)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即资本的社会权力是必然要消亡的。马克思正是透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范畴全体系的一般的批判”[5](P221),而把存在者还原为存在者之存在,经济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揭示被绝对化非历史化的经济范畴的实践建构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有的对抗性,从而揭示它灭亡的不可避免性。但是,我们若要从存在论的角度深入探讨资本权力的消亡,就必须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实在的三层结构思想,如表1所示:
表1社会实在的三层结构
层级内容上层社会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施、国家中层阶级关系:社会权力(统治与被统治)底层社会生存条件:积累的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
从表1中可以看到,社会实在的底层是社会的生存条件,资本主义社会是自我再生产的,它的再生产是物质财富和资本权力关系的双重再生产,同时也是资本的社会结构以及这个共同体的自我再生产。马克思通过对社会本身生存条件的分析,发现它其实就是积累的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在结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之前,积累的劳动统治活劳动。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量的活的劳动,不能支配等量的对象化劳动;或者说,一定量在商品内的对象化的劳动,会支配一个活劳动量,比商品自身包含的劳动量更大”[7](P105-106)。积累的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土地,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积累的抽象劳动,而活劳动就是当下的雇佣劳动。积累的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之现代表现就是抽象劳动统治具体劳动,正是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才不断地生产出资本主义社会来,这是它生存的基础。但是,社会生存条件是由人来体现的,社会生存条件的人格化存在就是阶级。抽象劳动的体现者就是资产阶级,具体劳动的体现者就是无产阶级,因而生存条件中的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统治的人格化存在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就是社会权力,社会权力体现出了阶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代表着阶级的分化与对立。故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不是像狼对羊的关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1](P728),这种统治力量恰恰是从对抗性的社会生存条件中生长出来的,与人的个性无关。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攫取了现代世界的最高权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力量”[13](P14)。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主要不是道德、伦理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它的生存条件之中展开深入批判。
此外,资本的社会权力作为普照的光还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知识、智力以及科技都具有了权力的性质,都是服务于货币(资本)的增值,异化成了统治人的力量。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9](P358)在现代社会,资本的孪生兄弟科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剩余价值获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统治人的方面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科技实现了双重控制,不仅是对自然界,更是对社会的量化控制,是人与自然界双重的技术设置,甚至于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与《自然与革命》等著作中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控制人的意识形态的工具,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因此,“人在统治自然的过程中统治了人类社会”[10](P51)。法国哲学家福柯则公开承认,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想家分别是马克思和尼采,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权力哲学,突破了知识论,对知识本身进行了存在论批判,在《知识考古学》《疯癫与文明》等系列著作中分析了知识本身中的社会权力或社会权力在知识中的运用。基于文化的权力性质,福柯认为:“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11](P204)培根在《新工具》中也把知识与权力看成是同义的,“知识就是力量”更为准确的翻译即是“知识就是权力”。而表达知识的语言也同样地就具有了权力的性质,霍克海默称之为“语言之社会权力”[8](P61)。对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总之,知识、科学和劳动的分离,是和资本主义生产一道出现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劳动者的富和劳动者的贫,互相对立;这种对立,又唤起一种知识上的对立。知识和劳动,分开来了。前者当作富人的资本或奢侈,而与后者对立”[7](P61)。并且,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为了这种对立性的结果,愿意使这种对立性化为永久性的”[5](P228)。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实在三层结构的划分可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绝不是仅仅止步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当然这是必要的一步。但若是仅仅停留于此,也只是达到了社会实在三层结构中的上层和中层,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大厦的基石,即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人类的大多数还是屈从于抽象劳动,屈从于资本的增殖,即为价值、货币的增殖而奋斗。所以,资本权力的消亡关键就是消解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而资本统治权力的消亡不是靠行政命令就能消除的,而是资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自我否定的感性力量,进而消灭自身。为什么资本蕴含着自我否定的力量,这是因为资本发展的真正限制就是资本本身。资本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即资本不断创造的物质财富总是以社会对抗的形式即对抗性的生产关系进行保存的,而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权力;也就是说,资本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权力的增长是同一个过程,成正比关系。社会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感性冲突和经济危机,这样的冲突和危机的多次反复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K562和KG1a细胞接种于96孔板,细胞密度为1×108/L,每孔100 μL。设对照组、药物组和空白组,每组5个复孔。Rh2-S 均使用DMSO溶解稀释,浓度为20、40、60、80 μmol/L,分别培养24、48、72 h。测量前,每孔加入10 μL CCK-8工作液,震荡混匀,继续正常培养2 h后,酶标仪(工作波长为450 nm)测量吸光度(A)值。计算时去掉复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保留3个有效复孔,计算细胞活力。
在封建社会中,把人聚集在一起的是土地,土地的统治带有伦理的性质,带有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地主与农民是相互熟悉的熟人。因此,马克思指出,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权关系就是一种社会权力,而这种社会权力不是永恒的,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对抗性的社会权力要被取代,只能通过暴力的形式,因为是对抗性的感性力量,所以,必须用另一种对抗性的社会权力取代旧的社会权力。
马克思对这个悖论的实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产生出来。”[1](P124)在现代社会中,劳动的本质就是抽象劳动的主体化,即抽象劳动统治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的物化形式就是货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具体劳动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通过抽象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促使货币的增值,即资本的增值。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抽象劳动的资本“就它们自身考察,它们就是支配他人的劳动的权力,是会自行把价值增加的价值,并且会提供一种权利来占有他人的劳动”[5](P405)。占有他人的劳动本质上就是占有他人的没有经过交换的无报酬的那一部分劳动,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占有的无酬劳动越多,工人越贫困;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以大众的贫困为基础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深刻地指出:“在资本的发展中,在国民财富的发展中,[其增加]会在劳动者境况上发生益益劣的影响,换言之,在财富增加资本蓄积时,或者说,在再生产的规模扩大时,劳动者的境况会依同比例相对的恶劣化。”[5](P286)恩格斯也指出,国民财富在私有制的社会中和政治经济学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并不能消除它自身产生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全面地阐述了资本本身发展的必然界限。第一,必要劳动是工人工资的界限,就是工人的工资一般情况下只能低于而不能高于必要劳动的货币表现,而资本创造出来的财富又需要工人消费。因而工人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与他获得的货币的缩减形成了矛盾,而他们的贫穷和有限的消费力是一切危机的最终根源。第二,剩余价值是生产力发展与剩余劳动实现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的增殖,即获得剩余价值。但是,资本的巨大的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若不能够在市场上实现为剩余价值,那么,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就不能向前发展,因为这是无利可图的,这样就必须把现有的一部分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消灭掉,以重启市场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经济危机中,“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12](P37)。可见,资本生产力的每一次发展一定包含了后来对这种生产力的破坏。第三,货币是生产的界限。现代国家早已突破了这个界限,金本位制已被终结,因而现代人生活在更加动荡不安的金融环境中,每一次的突破都会带来新型的经济危机。第四,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生产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打开了使用价值生产的广阔空间,但交换价值的增殖才是它的目的。为了追求交换价值的增值就必须开发并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这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能源,无限的资本增殖与有限的资源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自然规定了资本增值的界限,而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这个界限。
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一种美丽的谎言,自由的只是资本,资本具有独立性,而作为工人的个人没有自由和独立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劳动者的命运,只当作奴隶制度的变形来把握”[7](P54)。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除了理想化的爱和友情之外,根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关系。而马克思则向人们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根本的关系就是作为感性活动之异化的社会权力关系,其他的一切异化关系都由此而出。并且也从中产生了并持续存在的现代人的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文化的、存在的焦虑与内在的无意义的空虚,正是从这种无意义感的土壤中虚假的信仰得以产生并泛滥。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自发分工中的人的共同活动必然会产生一种社会性的力量,而“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1](P538)。这种强制性的力量既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马克思称之为“物质力量”。感性活动在自发分工的范围内不再是彼此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创造性的感性力量,从感性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变成了一种异化的社会的物质力量,而这种社会物质力量必然脱离个人,必然独立化为社会权力。而自发分工同时也就意味着劳动及其产品在质和量上不平等的分配,意味着私有制的产生,从这种财产状况中就产生了社会权力,即上文所说的“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由此可见,自发分工与私有制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是异化的感性活动的相等表达方式,自发分工是就活动而言,私有制是就活动的结果而言。故此,马克思绝不会把私有制的根源追溯到人的本性中去,而是追溯到人类劳动最初的自发分工阶段的不可避免性。当然,原始社会是由天赋、体力、需要等等所形成的自然分工,还不是真正的自发分工,因而原始社会是公有制而非私有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这一点进行了清楚的阐释。概而言之,社会权力就是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就是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就是生产力即感性活动的异化的社会形式。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权力并不只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它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根本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进步是在对抗中的进步,是以社会对抗的形式来获取并保存物质财富的,因此,社会权力具有非社会的性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2](P188)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也深刻地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P104)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在逻辑上不是一个自洽的体系,资本及其权力的消亡是必然的,这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恰是资本自我否定的结果,而这正是资本自我发展的辩证性质,不管它是采取何种形式,商业的、农业的、工业的、垄断的还是金融的。随着资本权力的消亡,人类的对抗性时期也就结束了,真正的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就到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仍然会有生产关系,但这时的生产关系的私有性、对抗性已经消失了,即生产关系的社会权力性质消失了,人的社会性得以全面展开,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即感性活动的力量在自然界得到了全面的肯定,人也就成为了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有自由个性的人。人本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以社会性的方式存活于自然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人的社会性得到了空前的展现,以至于个人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但是,人的社会性的实现是以货币为中介的,要获得他人的劳动成果必须通过货币,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就变成以价值范畴为基础的等价交换,劳动、人与社会财富都被抽象化了,人被置于形而上学的统治之下,即被超感觉的抽象力量统治。
所以,人的社会性的实现是以社会对抗的方式来实现的。生存条件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与他的个性并不一致,不是个性发展的需要,而是外在压力下谋生的手段,人成为了偶然的个人、阶级的个人,生存条件脱离个人并反过来规定他,故此,在现代社会跳槽也就成了普遍的现象。个人看似自由,实则是处在资本权力之下的选择被雇佣的自由,个人看似独立,实则是种错觉,是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彼此关系冷漠意义上的独立,劳动也成了没有劳动者个性的抽象劳动。
近几年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现代化电教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多媒体计算机正逐渐成为语文教学的一种重要工具。要充分发挥语文课堂教学中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它通过文本、图像、动画、声音等方式,创设情景、激发情趣、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化静为动,发展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学生的能力,打破了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多媒体辅助教学有着明显的优势:有利于个别教学,可以做到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学生的智能发展。让我们的语文课堂能够做到活泼生动、轻松愉快,让学生在多姿多彩的世界里,去学习、去成长。下面就多媒体技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谈谈浅略的看法。
李闺女说,大家都甭理他,看着是好人哩,实际是笑面虎,往大伙身上捅刀子。李六如,你还算是人吗。咱李家庄可都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
资本的权力消亡以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随着人的社会性的全面展开,个人的生活条件与其个性达到了一致。人的个性需要、爱好、情趣注入到了人的生存条件,即职业中去了。职业既是生存的条件,又是个性展开的需要,生命理想的实现,同时就是人所奋斗的事业,只有在这时普遍的敬业精神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从而达至马克思所讲的个性与生存条件的一致。此种状况下,剩余劳动时间就成为了人的自由发展的时间,人对自由时间的支配成为真正的财富,所以,在结束了人类社会对抗性时期的共产主义社会“交换价值废止了,劳动时间也依然是财富的创造的实体,是生产所必要的成本的尺度。……这种劳动时间当作自由时间,……一个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比劳动兽类的劳动时间,有更高得多的品质”[5](P224)。同时,感性活动的异化性质也就消除了,成为了自由自觉的具有吸引人的活动,财产的资本性质也随之消除而成为了丰富和提高人的生活的手段,成为了人的感性的享受对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要消灭财产本身,“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12](P46)。
“完了,我觉得宇晴姐姐是将我们骗到了一个局里。等我们看这两位老爷爷下完棋,爬下树,大概时间就过了一百年,什么黄梁驿,长安,都会变成我不认得的样子,以后鸟窝大师和他的鸟窝孙子们编故事,就会说有四个长安少年,来我们黄梁村,这个美丽的桃花源,躲过了传说中大唐的乱世,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去万花谷,其实就是在大榆树顶上看人家下了半宿的棋,之后回到长安,发现他们孙子的孙子们正在街上玩‘蹴鞠’。”上官星雨有一点担心。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认为,家庭关系和生产关系都属于社会关系,是感性活动展开的社会形式,并且在最初的家庭关系中已经隐藏着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新的需要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而导致的交往必然突破家庭、部落的范围,从而创造了一种保存物质财富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这时在家庭中隐藏的最初的生产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故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能分离开来去理解,没有纯粹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二者就像硬币的正反面一样,同出于生产。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就意味着生产力在其中运动的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即社会权力也同步发展,这种生产关系的对抗性一旦成为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力的阻碍,那么,为了不至丧失新的生产力及创造的物质财富,必然要抛弃生产力在其中运动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这样历史就产生了。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即社会权力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就是资本,这也是马克思重点研究的对象,他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4](P8)
因此,马克思不会像亚当·斯密一样重新撰写一本新的《国富论》,因为马克思洞察到资本的确是现代社会的财富,但资本作为财富在增值的同时就是它作为社会权力的同步扩大,所以,马克思直接写《资本论》,就是研究资本作为财富、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资本这种社会权力如何从中生长出否定自己的感性力量,而资本这种社会权力的自我否定而导致的自我消亡的规律在《资本论》中被表达为剩余价值规律。因此,剩余价值规律不能仅仅视为一种经济规律,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自我消亡的规律。总之,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权力,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指出:“‘社会权力’这一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拱心石。”[15](P23)而要抓住社会权力就必须穿透概念、范畴的屏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资本论》中不断地把范畴做成的经济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以阐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暂时性和非自洽性。因此,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权力的哲学,并且从这种哲学中一定会生长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历史科学,这种历史科学的示范性著作就是《资本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8]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彭子细,刘光斌.物化批判的三个向度与物化的同一性逻辑——阿多诺物化批判理论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11]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刘志洪,王赢.支配现代世界: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澄明[J].湖北社会科学,2016(4).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王德峰.社会权力的性质和起源[J].哲学研究,2008(7).
TheOrigin,ManifestationandExtinctionofSocialPower:anAnalysisofHistoricalMaterialism
LIU Jian-tao1,YANG Jing1,2
(a.School of Marx,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nzhou,Liaoning 121001,China;b.Liaoning Polytechnic Vocational College,Jinzhou,Liaoning 121001,China)
Abstract:Social power is the core concep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power is the cornerstone of understanding the philosophy of Marx.Social power is the emotional strength to control and to be controlled non-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n,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alienation of sensuous activities caused by spontaneous division of labor.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ch as land and capital.Capital is the contemporary of social power.Self-denial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 power,and the replacement of thus the personality of the person instead of accidental person.
Keywords: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social power;sensuous activities;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capital power;capital demise
收稿日期:2018-1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科技与生态互动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17YJC710048)。
作者简介:刘建涛(1983-),男,河北邯郸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杨静(1983-),女,辽宁锦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存在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9)01-0005-09
(责任编辑王能昌)
标签:马克思论文; 权力论文; 社会论文; 资本论文; 生产关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马克思的科技与生态互动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 (17YJC710048)论文; 辽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