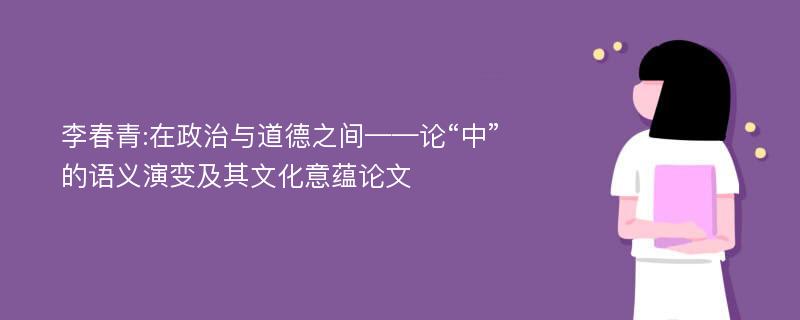
[摘要]“中”是儒学核心范畴之一,集中体现着儒家士人政治诉求和道德理想,也表征着儒学中的哲学之维。作为对君权的要求与约束,它具有政治性;作为儒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它是一种道德境界;作为能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大本”与“达道”,它又具有哲学本体意味。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中”的语义并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在先秦子学时代,“中”既有政治含义,也有伦理道德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在两汉的经学语境中侧重于政治规范意义,到了宋明时期则更多地成为一种道德哲学的概念,而在晚明的何心隐那里又重新成为一种直接指向君主的政治话语。“中”概念的意义演变与儒家士人与君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中庸;时中;理学;心学
宋儒程颐尝言:“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注]①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八·伊川语四》,《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4页。堪称知言之论。在儒家的思想系统中,“中”属于核心范畴,与“仁”“义”“礼”“智”“心”“性”“诚”“敬”等为数不多的概念属于同一层级,而且与这些核心概念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是不大容易说清楚的一个概念。也正因如此,我们通过对其涵义的历史演变以及这种演变所表征的文化意蕴的分析考察,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切入儒家思想体系的内核之中,从而对其丰富的意涵能有更准确的把握和阐发。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代表着儒学的基本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对这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历史演变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按照时代的历史顺序展开对这个概念涵义生成与演变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它们所体现出的诸种文化意义以及在儒学概念网络中的核心位置。
阿花一向都关爱员工。她以女性的细腻,家长的情怀,去体贴员工,嘘寒问暖。那个宫外孕的女孩早就康复了,在检查车间做品检,她从不叫阿花老板,叫花姐。景花厂的女孩几乎都不叫老板,叫花姐显得亲切,暖心。阿花给了我启示,我对新员工格外关心,问他们生活习惯么?吃得好么?休息得怎样?我相信,即使有一天他们的翅膀硬了,高飞了,他们也会念及我们的友谊,至少不会与景花厂为敌。
一、“中”之诸义的发生
“中”这个字很早就有了,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篆书、隶书,直至今天通行的楷书,其字形从来没有太大的变化。《说文解字》对“中”的解释是“内也”。段玉裁的进一步解释是“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说文解字注》)可知这个字的本义是“在里面”,因此也就引申为“心里”或“内心”之义。例如《老子》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之说,这里的“中”就是指内心而言。在先秦典籍中,从《论语》《孟子》《荀子》到《礼记》《易传》,都有大量关于“中”与“中庸”“时中”的论述,都包含着政治、道德和哲学的含义,只是到了两汉的经学时代,这个概念才更多地倾向于政治哲学一面。
《古文尚书·大禹谟》有著名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说,后来被宋代的理学家们奉为“十六字真诀”。《大禹谟》固然是后儒的伪托之作,“人心”“道心”之说也不像是“思孟学派”出现之前的说法,但是“允执厥中”这四个字却应该是有着很早的历史,至少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何以见得呢?在《论语》中记载着尧的话:“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这里的“允执其中”与《大禹谟》的“允执厥中”文、意俱同,可以断定是出自早于《论语》的某个古代文献。所以这个“中”应该视为后来成为儒学话语系统之核心范畴的“中”及其衍生词“中庸”“中和”“中行”“中道”“中正”“大中”“时中”“刚中”等等的渊源。如此看来,宋儒围绕“十六字真诀”大做文章乃是渊源有自,并非无根游谈。
在先秦儒学那里,“中”首先是个道德概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根据上下文意以及历代注释,这里的“中庸”和“中行”都是关于人的行为道德规范。孟子说:“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孟子·离娄下》)这里的“中”是指能“中道而行”之人,同样是从道德修养角度来说的。荀子也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这里的“中正”是指品德高尚正直之人,同样是道德概念。
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与?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皆贵气而迎养之……君子法乎其所贵。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注]②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0、444-446页。
在Citespace中,某个聚类所包含的突发节点越多,那么该领域就越活跃,或是研究的新兴趋势。由此说明Cluster1、Cluster 2、Cluster 3这三个聚类的热点问题“移动阅读终端”“移动阅读推广”“移动图书馆”相对其他热点更为活跃。
但到了《中庸》这里,“中”除了原有的政治含义、道德含义之外,更获得了哲学意义,带上了一种先验本体的意味。《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注]朱熹:《中庸章句》,《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页。根据这段话的逻辑,“中”不再仅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问题了,而成为天地万物存在之依据。“中”与“和”显然是体用关系,也就是说,“中”是本体或本原,“和”乃是“中”的发用或展开。只要能够保证“中”与“和”从“未发”到“已发”的正常展开,天地万物就可以各安其位、繁衍生育了。“中”或者“中和”的这种功能显然超出了政治的和道德的范畴,成为一种哲学玄思了。考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段话的作者受到道家、阴阳家的影响,不满足于传统儒学仅仅限于人世经验而立说,希望把儒学推进到与道家、阴阳家同样的思想深度,以便与之争雄[注]《中庸》一篇在古代通常被认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现代哲学史家如冯友兰等认为其中既有子思的思想,更有战国后期儒者加进去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儒学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需要为其学说找到某种先验的学理依据,以达到用神教设道的目的,其中有着某种必然性。
二、作为政治概念的“中”
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不同,西汉是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儒学也成为经学,从诸子百家中的一种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士人通过经典阐释一方面为汉朝统治寻找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也暗中编织起限制君主权力的“软笼子”。他们对“中”和“中庸”的理解也与这种意识形态建构直接相关,在西汉以大儒董仲舒为代表;在东汉则以作为经学之集大成的《白虎通义》及徐干的《中论》为代表。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政权之后,士人阶层渐渐失去了先秦士人所拥有的“游”的自由,由于失去了择主而事的权利,他们那种“为王者之师”的气概也就大打折扣了。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惟一的选择就是和汉朝统治者合作,成为炎汉王朝中的一名官员。但是即使如此,先秦士人那种制约、引导、匡正君主的动机却丝毫没有消减,那种自认为是“道”的承担者,欲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建立社会价值秩序的努力也从未停歇。在这方面,董仲舒是颇有代表性的。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除了论证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价值以外,还广泛讨论了“天人感应”以及君主如何治理国家等问题。他提出“中适之宜”的说法:“是故君意不比于元,则动而失本;动而失本,则所为不立;所为不立,则不效于原;不效于原,则自委舍;自委舍,则化不行。用权于变,则失中适之宜;失中适之宜,则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则众不亲安;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这段话的主旨是说,如果君主不能按照君主所应该做的那样处理政事,就会偏离正确的原则,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这里的“中适之宜”是指按照正确的政治原则来做事。董仲舒告诫君主,一定要懂得君主的责任与义务,依为君之道行事。董仲舒的“中适之宜”思想无疑是从先秦儒家那里的“中”和“中庸”思想继承下来的,但也明显地带上了时代的色彩,直接成为对于君主的规范了。
何心隐(1517年-1579年),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师从颜钧。思想激进,被视为异端,后得罪当政者,被处死。他有一篇专门讨论“中”的文字,名曰《论中》,立论处处指向现实政治,指向君主,从而把“中”原本就有的政治性推向极致。其云:
对比上述引文,问题就来了:前引《大禹谟》中的“允执厥中”与《尧曰》中的“允执其中”都是指恰当的治国方略而言,无疑属于政治范畴,但到了孔孟荀等儒家这里就变成了道德范畴,原因何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是诸子之学与王官之学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必然结果。盖孔子之前并无个人著述,孔子及其同时代的士人思想家们的学说必定来源于王官之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我们今天无从知晓的某些两周王室传下来的文献。王官之学都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说话的,“中”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被赋予了政治的含义是很自然的事情。孔孟荀所代表的儒家就不同了,他们是布衣之士,是黎民百姓,手里没有权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道德的方式来达到政治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他们把“中”这样一个本来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赋予了道德的意义,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孔子在大力弘扬“周礼”的同时特别凸显了“仁”的意义,孟子在推崇古代“王道”的同时,大讲特讲“仁政”,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万物皆为阴阳二气交感所生,阴气与阳气保持平衡的状态就是“中”,阴阳二气氤氲交融就是“和”,天地的运行从“中”开始又止于“中”,而天地万物都产生于阴阳二气之交融。因此,作为阴阳二气之平衡状态的“中”乃是贯穿于自然宇宙与人世之间的正道;而作为阴阳二气完美融合状态的“和”则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原因。因此一个君主如果按照“中和”的精神来管理天下,就会取得极大的成功;一个生命个体如果按照“中和”的精神来养生,就会长寿。《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之说,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董仲舒从天地自然之间阴阳二气的关系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因为“中”乃是指宇宙之间阴阳二气平衡状态,这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中”为“天下之大本”也就顺理成章了。董仲舒所理解的“中”与“中和”更进一步发展了《中庸》“合外内之道”的思想,并使之更加细密了。与《中庸》明显不同的是,在董仲舒这里匡正、警示君主的意味更加明显了。
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注]②③④ 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70、70、318页。
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注]扬雄:《法言·吾子》,见韩敬译注:《法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页。
这里的“五声”是指音阶,“十二律”是指音高,都是中国古代音乐术语。“雅”是指雅乐,是从西周以降历代相传的官方音乐;“郑”则是指“郑声”或“新声”,是指春秋时期产生于郑国、卫国等地的民间乐曲。同样是由“五声”和“十二律”构成的音乐,为什么会有“雅”“郑”的区别呢?扬雄认为声音“中正”的就是雅乐,声音“多哇”的便是郑声。在这里,“中正”是指音乐表达的情感适度,用《毛诗序》的说法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总之是要求音乐表达情感要有节制,适当,恰到好处。对音乐的这一要求实质上是对人的要求,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品质,“中正”就是正道而行,无所偏倚。作为儒家的根本原则,“中”的表现是无处不在的。在人的行为中,在政治事务中都要求遵守这一原则。用扬雄的话说就是“圣人之道,譬犹日之中矣!不及则未,过则昃。”圣人之道就像中午的太阳一样在天的正中,没有达到正中时就不够明亮,超过正中时就开始偏斜了。无论自然还是人事,“中”都是指那种恰到好处的状态。这也表现在政事中:“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则桀,寡则貊。”(《法言·先知》)只有十税一才是最恰当的,多收了税就近于暴虐的夏桀了,如果收的税比十税一还要少,那就近于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了。
嘉兴项氏家族始祖项晋官至大理寺评事,因护驾而到江南。从项晋到项笃寿,这个家族几乎代代出高官显贵,长辈因子孙荣贵而获赠官职的也有两例。现将项氏家族功名、官职及宦迹列表如表2。
雪莲的叶子上长满了白色的茸毛,又白又细的茸毛交织在一起,在叶片表面“搭建”出许多小小的“房间”。“房间”中的气体很难与外界气体交换,这样一来,雪莲就可以在严寒中保持一定的温度,不至于丧失过多热量。白天,强烈的阳光直晒着高原上的一切,此时,雪莲叶片上的茸毛又能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
三、“中”的含义从政治向道德的转变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以及他之后的几位帝王都极为重视经学,因此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得到空前的发展。然而由于经学传承各有统序,师法、家法互不相属,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以及二者各自内部都出现了关于经义理解上的严重分歧。于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朝廷组织大臣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目的是调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歧,统一经义。由于有皇帝和朝廷重臣的直接参与,这部书就不仅是纯粹的学术讨论,而且是对于稳定和强化既定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的一套完备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当时许多一流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后来,章帝命班固把会议讨论的结果整理出来,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白虎通义》,又称为《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可以说,这是一部融合了君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的文献,是东汉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呈现。因此,这部书对于“中”或者“中和”的理解就更多地带有政治色彩,而大大减少了伦理道德意涵。例如: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马克思关于“物”的深刻洞见。在这个以“物”的庞大堆积表现出来的世界中,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马克思所讲的“物化”?如何才能借助于“物”而不迷失于“物”?如何在与“物”的打交道中来保持和丰富生命的内涵?或许,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从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来给出答案。无论如何,在商品世界中需要有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一种超越性的维度,一种历史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当每个人都在意识上超越了“物”以及“物”的界限,我们才有可能现实地通过“物”而超越“物”的世界。
扬雄是西汉后期著名儒学思想家,有追比圣贤的伟大志向,曾仿效《论语》作《法言》,仿效《易经》作《太玄》。“中”在扬雄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请看下面的对话:
“五帝”是传说中上古时期的君主,还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历来被儒家所推崇。特别是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更被视为中华民族之始祖。在东汉的经学家看来,黄帝之所以称为黄帝乃是因为“黄”是“中和之色”,在“五色”之中最为尊贵。当然人们之所以用“黄”为“五帝之首”的谥号,主要是因为他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有大贡献:
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后世虽圣,莫能与同也。后世德与天同,亦得称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复称黄也。[注]② 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70、70、318页。
为天下初创法度,确立了人伦规范,使人成其为人,真正脱离动物界,这是至高无上的功勋,故而必须以五色中最为尊贵的颜色为之命名。陈立引《通典》注云:“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识也。”[注]③ 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70、70、318页。 可见“中”和“中和”正是万世不易的典章制度、人伦大法的基本特征。这里先是把黄色说成是“中和之色”,继而说黄帝创制的制度即以“中和”为本,故而可以“万世不易”,这无疑是把“中和”阐释为现实政治制度之合法性依据了。在儒家看来,正是由于有了黄帝开创的、夏商周三代继承并完善的典章制度与人伦规范,秉承了中和的精神,中国才成其为中国,而“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注]④ 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70、70、318页。
到了东汉后期,皇帝大都暗弱昏聩,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与士大夫集团矛盾尖锐,导致朝政混乱不堪,经学也出现繁琐考证与神学化两种倾向,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及至汉末,天下大乱,军阀割据,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受到沉重打击,文人士大夫们或者奔走于豪强之门,希望于乱世之中建功立业,或者沉浸于诗词歌赋之中寻求个体精神的满足,或者游心于老庄之学以求精神之慰藉,儒学研究式微了。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有一位儒者却不为时风所染,潜心多年,著成《中论》一书,阐发儒学义理,力图使儒家中正平和精神得以赓续,对于儒学发展而言,可谓厥功甚伟。这位儒者就是在文学上名列“建安七子”之中的徐干(公元179年—217年)。这部书为什么取名《中论》呢?何为而作呢?作者同时代的无名氏为之所作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其统圣人中和之业,蹈贤哲守度之行,渊默难测,诚宝伟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敎、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由此可知,徐干作《中论》一书,一是为了“上求圣人之中”,即继承弘扬孔孟以降历代儒家所遵循的中正平和之道;二是为了“下救流俗之昏者”,即唤醒人们的道德精神,从而扭转世风日下之颓势。所以在徐干这里,“中”的意义主要是强调人应该恪守礼义,在道德上达到正直平和,进而实现政治上的井然有序。他说:“仲尼之没,于今数百年矣,其间圣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迟,人伦之中不定。”[注]② 无名氏:《中论序》,徐干:《中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30、20、47页。这里的“人伦之中”就是指人的行为符合儒家礼义廉耻的标准,是社会政治清明的主要表现。他又说:“……奉圣王之法,治礼义之中,谓之士。”[注]③ 无名氏:《中论序》,徐干:《中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30、20、47页。 这是说,“士”的基本要求除了服务于君主之外,就是能够奉行儒家礼义原则,而“中”或“中和”则是儒家礼仪原则的主要标准:“故恭恪廉让,艺之情也;中和平直,艺之实也。”[注]④ 无名氏:《中论序》,徐干:《中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30、20、47页。这里的“艺”是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言,是古代圣人所创造的文化形式。在徐干看来,“六艺”呈现出来的形态情状应该是“恭恪廉让”,即恭敬、诚恳、谦让的;其内在精神则应该是“中和平直”,即不激不厉、正道直行的。这都是对人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但在君主官僚政体之下,社会的公平合理、政治清明根本上还有赖于君主的作为,所以徐干《中论》的最终目的依然是匡正君主:“故先王明恕以听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节。”[注]⑤ 无名氏:《中论序》,徐干:《中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30、20、47页。这里的“明恕”是聪明宽和的意思,“中”是“公平”“公正”的意思,这是要求君主赏罚分明、恪守中道,可见徐干论“中”同样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
魏晋南北朝的三个多世纪之中,南北对峙,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止。在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疏离于政教伦理的玄学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都居于重要位置,得到极大发展,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落。及至隋朝重新统一天下,儒家士人又激发起重振儒学的志向。在这方面王通具有代表性。
王通(580年?—617年),号文中子,是隋朝的一位有大志向的儒者,以圣人自期,曾模仿儒家经典做《续书》、《续诗》、《元经》、《礼经》、《乐论》、《赞易》等,后均散佚。今存《中说》是王通的弟子模仿《论语》体例编订的。关于这部书何以以“中”命名以及全书的主旨,宋儒阮逸为其所作的序中说得很透彻:“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注]阮逸:《文中子〈中说〉序》,王通:《文中子中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中”的意义太大了!在《易经》中它表现为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等五行;在《春秋》中它表现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在《尚书》中它表现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在《礼记》中,它表现为中庸之道。“中”既不是毫无形迹可寻的虚无,也不是可以用感官把握到的具体存在,它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却又始终合乎人伦大义。这便是“中”的基本精神,也是这部《中说》之主旨所在。阮逸的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中说》处处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政治黑暗、道德沦丧状况的批判,其所表达的正是儒家不激不厉而又能随时恪守原则的中正平和精神。为人则“曲而不谄,直而有礼”(《问易》),进谏君主则“直而不迫,危而不诋”(《礼乐》),论天人关系则以人为主体:“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魏相》)思孟学派那种“中”与“中庸”精神在王通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总体上看,王通主要是把“中”理解为一种道德原则,是人人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
这段对话包含紧密相关的三层意思,一是讲“中”或“中和”并非一个整体,在不同人那里是有大小之别的。“中”就是“性”,人性本善,所以“中”以及相关之“和”也是人人都有的。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在一些具体事件上表现出“中和”来,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得其“全体”,能够“无所不中”,“无所不和”,达到“天下之大本”和“天下之达道”的境界,这当然只有圣人能之。二是说“中”就是“性”也就是“天理”。这是思孟学派的基本思想:人与天地自然本为一体,大道流行,在天而言名曰“理”或“天理”,在人而言名曰“性”,人的任务就是通过存心养性以“合外内之道”,进而实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宏远目标。三是说“天理”为什么又可以称之为“中”呢?因为天理总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是“原本如此”与“应该如此”的完美统一。这也正是“中”的特点。
选用Bengio在工程实践中推荐的batch_size常用值[19];epochs通过网格搜索方式进行参数寻优;如果使用固定学习率进行训练,那么训练速度很容易受到梯度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动量法实现自适应的更新调整,在梯度下降法中加入动量因子ρ,如式(5)所示.
杨头村:以花岗岩类、火山岩类残坡积物为主,母岩风化后一般成粗骨土,土质疏松,砂砾含量大,母岩中微量元素含量均衡,尤其是氮、钾养分元素丰富。
四、“中”作为一种道德境界
及至唐代,“中”“中庸”“中和”等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赞扬人的品行的重要词语,随处可见。然而除了孔颖达《五经正义》能够在学理上对“中”及“中庸”等概念有所涉及之外,专门对其含义与意义进行深入阐发并有新见的可谓渺不可见。受韩愈影响颇大,有志于振兴儒学的李翱作《复性书》,对《中庸》大加赞扬,倡“性善情恶”之说,可惜对“中”与“中庸”的意义也基本上未能论及。
宋代君主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掌权之弊,奉行右文政策,从太祖以降基本上都能做到礼遇士大夫,宽松的政治环境与较为丰厚的物质待遇,激发起文人士大夫一种昂扬向上的主体精神,人人追比圣贤,普遍具有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士大夫这种积极进取的主体精神也使得宋代的儒学大大增加了学理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宋儒极为推重在儒学典籍中比较具有学理深度的《孟子》和《中庸》。程朱理学,从张载、二程到朱熹,都有大量关于“中”与“中庸”的谈论,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庸》展开的,概而言之,其要有二:一是都试图在“合外内之道”的框架内阐释“中”的意义,认为“中”是“天”与“人”所共有的特性,因此强调“中”的价值也就成为沟通天人的有效路径。二是他们重视“中”的原因也都是为其心性之学寻找形而上的本体根据,继承了《中庸》“大本”“达道”的理路。宋儒这种阐释框架到了明代的心学那里才真正被突破。
心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流派,以陆象山、陈白沙、王阳明为代表。心学不满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与人性的二元结构,主张一切均统摄于心,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的观点。在心学看来,“中”与“中庸”也体现为人心的一种状态,并非客观存在之物。在陈宪章和王阳明那里,强调“中”与“中庸”的价值主要是为了张扬“心”统摄一切的主体意义。到了明代后期的“左派王学”那里,由于政治环境日益恶劣,儒者对于“中”的理解就又倾向于政治性的一面,主要是为了规范那些昏聩的君主了。
陈白沙,即陈献章(1428年—1500年),明代中叶大儒。他在一封书信中说:“夫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矣。中无定体,随时处宜,极吾心之安焉耳。”[注]陈献章:《与朱都宪》,《陈献章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5页。由此可知,在陈白沙看来,“中”乃是天地之间最普遍的、最基本的“理”,而这个“理”却并无固定的所指,只是说在任何时候都做到恰到好处即可,而何为恰到好处,其评价标准不能向外寻找,它就在人的心中。换句话说,吾心安处便是“中”。如此,则此“中”已不再有“天之中”那种客观自在性、本然性特征了。
到了王阳明,则更直截明了地将“中”归之于心了。其云:“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中”即是“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浑然心态。它本身并非道德价值,但它却是一切道德价值产生的根本依据,是万善之源。“良知”是王阳明的核心范畴。“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良知”一词出于《孟子》,其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朱熹释云:“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注]朱熹:《孟子集注》,《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05页。也就是说,“良知”乃是人生而有之的道德本能。道德有本能的吗?孟子主张“性善”之说,当然就认为道德是有本能的。王阳明把《中庸》的“未发之中”理解为“良知”,又把“良知”与“性善”联系起来,这样一来,“未发之中”就落到了实处,获得了学理依据,逻辑上是贯通的。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已发之中”与“未发之中”是什么关系?朱熹是用“体用”论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王阳明是否有另外的阐发呢?我们来看他的说法:“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是未尝无动静,而不可以动静分者也。”[注]④ 王阳明:《答陆原静书》,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学生书局授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131页。 这意思是说,“未发”“已发”原是一体两面,“已发”包含着“未发”,但对此只可理解为“未发之中”实现为“已发之中”,二者是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而不可理解为在“已发”之中,尚有某一部分是“未发”。而“已发在未发之中”,只可理解为在“未发”中存有“已发”之可能性(或必然性),而不能理解为“未发”中有一部分“已发”存在。二者不是相互包容的关系,而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它们只能历时性地接续,不能共时性地并存。就是说,二者恰似动与静的关系一样:静中有动之可能性,动中有静之可能性,动是静之动,静是动之静,世上并无纯粹之动或纯粹之静。显然,阳明对“未发”“已发”之关系的辨析在学理上是自洽的。
二程常常让修习遇到障碍的弟子去静坐,陈白沙也认为静坐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希望“于静中养出端倪”来,那么这种无思无虑的“静”的状态是不是就是“未发之中”呢?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问题,阳明弟子也有,请看下面的对话:
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资源,其所面临的土壤安全问题急需解决。对此,贵州开磷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农化中心主任田树刚表示,全球面临着与土壤相关的水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气侯变化、能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等多种问题,而土壤本身也面临着退化、污染等问题。高强度不合理的农用化学品的投入是造成土壤及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合理的肥料添加也为土壤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肥料产业各方的共同努力。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注]王阳明:《传习录》,卷上,《陆澄录》,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39页。
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统一的,即师生应该共同参与,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教学活动,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教学活动的目标是引导学生能够学习体育知识与技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将其培养成为综合素质高,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因此,打造初中体育高效课堂,必须以此为目标设计各种教学活动,并结合实际需求对各种教学活动进行优化,确保达到预期效果。
阳明的回答可以说显示出了心学大师的洞见!对二程与陈献章都是一种突破,从而也从根本上把儒家心性之学与佛禅之学、老庄之学区别开来了。静并不是修身养性的目的,甚至也不是有效的手段,因为在静的状态中只是暂时把各种欲望压制住而已,并没有从意识上解决问题,一旦条件合适,各种欲望还会冒出来。只有在意识中时时存着“去人欲,存天理”的念头,处处尊礼而行,渐渐达到道德自律,才能真正实现“中”的境界。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所谓“去人欲,存天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那么不近人情。按照儒学“中”与“时中”的逻辑,“人欲”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被普遍认为是过分的私利私欲;“天理”则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被普遍认为合情合理的要求。例如,在一个共同体中,每个人一天只能分得一个馒头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下,某人却要求每天有大鱼大肉,那就是“人欲”在作祟了。如果在另一个共同体中,每人每天可以分得一公斤鱼、一公斤肉等食物,则大鱼大肉的要求就是“天理”了。或者说,在父母还没有吃饱饭的情况下,一个人先要求吃饱饭,那就是“人欲”;而当父母都吃饱了的前提下,他吃饱饭的要求就变成“天理”了。可知,“人欲”和“天理”只是说在特定条件下某行为是否合情合理的问题,这是今天依然存在的。由此可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合情合理就是“中”和“中庸”的基本含义。当然,在王阳明的时代,判断是否合情合理的标准只能是儒家伦理。王阳明的观点是透彻的:不要纠缠于“已发”“未发”的辨析,只要时时处处自我提醒、自我戒惧不要放纵欲望、违理而行就是循“天理”,也就达到“中”与“中庸”了。那么,“天理”或者“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我们再看王阳明和弟子徐澄的一段对话:
澄问:“喜怒哀乐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平时无有喜怒之心。至其临时,亦能中节。亦可谓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时之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曰:“天理何以谓之中?”曰:“无所偏倚。”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方见得偏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虽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既谓之有,则亦不可谓无偏倚。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注]王阳明:《传习录》,卷上,《陆澄录》,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61-62页。
从班固的《白虎通义》到徐干的《中论》再到王通之《中说》,“中”的含义呈现出从政治向道德演变的趋势,这一趋势表征着士大夫阶层精神旨趣由外而内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到了北宋时期,随着程朱理学的产生,才真正完成。
其中,Yi表示旅游业下辖的3个核心部门的年度营收,Y表示旅游产业总营收;LPi,t表示旅游产业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LPi,b、LPi,f分别表示初始期与完结期的劳动生产率。基准期美元与2016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6.2[24]6。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中”或者把握到“天理”呢?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颇有不同。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久之自然会把握天理。这是积累的过程。荀子曾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劝学篇》)的说法,朱熹则主张“居敬穷理”,都是讲只有通过积累才能把握到天理,是做加法。王阳明的主张则是“去得人欲,便识天理”,是做减法。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似乎更接近道家之学。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庄子则讲“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之“坐忘”(《庄子·大宗师》),都是做减法。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到各种“人欲”,即私欲,也就是那些在特定条件下不合理的物质需求,那么“天理”就会自然呈现,因为它原本就在人的心里,只是暂时被私欲遮蔽而已。而在老庄看来,“肢体”“聪明”“智慧”之类都是“私欲”的表现,只有彻底消除它们,人才能恢复到自然无为状态,才能“同于大通”,即与天地之大道为一体。由此可知,阳明之学与老庄确实有某种相近之处。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影响巨大,并形成所谓“左派王学”。他们普遍接受了佛学和道家思想影响,对儒家传统思想有较大程度的突破,特别是对现实中士大夫们的虚伪做作有激烈批评,对儒家恪守的“礼教”也颇有微词。尤其是当时日甚一日的黑暗政治激发起他们强烈的政治干预意识,这些在他们对“中”的解读中均有所显现。这里我们仅以何心隐为例来说明“左派王学”语境中关于“中”的新阐释。
五、“中”的含义向政治的回归
董仲舒为了使儒家学说为君主所采纳,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的观点,认为天上的日月星辰、云雨雷电与人间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神秘相互感应的关系,人的行为,主要是君主的行为之善恶都会在天象中有所显现,因此人的行为必须与天地相应而不相悖才行。为政如此,养生同样如此。他又接受了阴阳家的思想,认为阴阳二气乃是贯穿于天地万物与人世间的基本元素,这可以说是天人感应的根本原因。他对“中”的阐释也是在“天人”“阴阳”的框架下展开的。他说: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忧难得人于中而允执也;舜以不得禹为己忧,忧难得人于中而精一也。精于中而执之,必允无杂心也。一于中而执之,必允无二心也。莫非心也,心而主则中心,而贯则道心。人于人则不贯,不贯则比而无所主。既不能主乎人,又不能主于人人也,人亦禽兽也。……人心非有减也,道心非有加也。人聚而道,道散而人,莫非心也。[注]何心隐:《论中》,见《何心隐集》,卷二,容肇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页。
这段话是对《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解释。《大禹谟》虽是战国时期儒者伪托之作,但这并不妨碍它对后世儒家思想的重大影响,上面这段话被视为宋明理学的“十六字真诀”,可见其在宋儒心目中分量之重。从整篇的文义来看,何心隐这段话主要是说给帝王或执政者听的,其中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说尧舜最为忧心的事情是很难找到能够无杂念、无二心地把握“中”的人来接班。这说明在何心隐看来,“中”既是一种道德价值,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品质。二是说人心原本是一样的,“人心”和“道心”的区别主要看是否有“主”和“贯”,“主”就是有所主,“贯”就是有所贯,都是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的意思,也就是在心中树立起一心向善的大原则。有了这个大原则,心便有主宰,有持守,这就是“中心”或“道心”了。“人心”则是没有一心向善之道德主宰的心,心无所主,便会为各种物欲所牵引,如此之人就与禽兽没有根本区别了。“中心”或“道心”不仅可以主宰个人行为,而且可以影响到天下百姓之心,使之成为有道德修养之人。在这里何心隐实际上是在强调作为君主而拥有“道心”或公正之心、无私欲之心,是何等之重要。
然而真正确立“道心”的主宰地位却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人心”是与利益直接相关的,而利益的诱惑是强有力的;“道心”则需要人对欲望的自觉克制,是很难做到的。他说:
心如是危,又如是微,奈之何哉?惟大哉之尧自透其心,见心虽危,而若有主乎其危者,安安在中;见心虽微,而若有主乎其机者,显显在中。中亦心也,心之心也。象身也,身立乎天地之中,中也。中也者,主也。主乎身者,中也,心也。以身主乎人之心者,中也,心也。身以主于人之心者,中也,心也。心乎道以道人,而人乎心者亦自不容不贯而道其心也。心于道,中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既然“人心”危险易成而“道心”微妙难求,如何才能使“道心”呈现,使“人心”遁形呢?只有像尧这样能够自己清楚地了解、掌握自己心灵的人才可以控制危险的人心,彰显微妙的道心,从而使自己的心灵永远处于“中”的状态。这种“中”的状态也就是心的状态,是能够主导人心的那个心,所以“中”就是心,就是能够使人心合于大道的那个心。显然,这里的“中”或者合于道的“心”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自律。这段话依然是说明具有道德自律的领袖人物(例如帝尧)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与他的许多前辈,例如朱熹和王阳明不同,何心隐主要并不是在讨论心性之学的学理逻辑,而是在谈论君主应该如何以身作则,成为道德自律的典范。他的这篇《论中》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规范君主的。在他看来,天下是否太平,关键在于君主是否可以控制自己的私欲,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在何心隐生活的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皇帝昏聩无能,往往是宦官或权臣把持朝政,士大夫阶层普遍心怀不满,希望皇帝能够振作起来,重振朝纲,何心隐正代表了这一普遍诉求。他进而论证道:
尧则允执此中以为君。君者,中也,象心也。心在身之中,中在心之中,故名中。惟中为均,均者,君也。允执乎中者,允执君以道其心也。道乎一己之心,以君主乎亿兆无算之人之心,不惟伏羲之伏其羲而已也。必洗涤乎君以主道而成象于位,位乎上天下地之中,而允执之矣。中而必执,执而必充者。惟忧其或危也,惟忧其或微也。忧之莫解,则不容不旁求透心之人,如己之透,同见乎中之当执,执之当允,以君象中,以位尊君,而共保乎心之不危不微,化乎人,纯乎道而后已也。[注]② 何心隐:《论中》,见《何心隐集》,卷二,容肇祖整理,第31、31-32页。
这里何心隐开始直接以“中”的准则来塑造其心中的君主了:君主之所以是“中”,因为他就像一个人的心灵一样。对一个人来说主宰者是心,对天下人来说,主宰者是君,所以君就是天下人之心。心灵是一个人的中心,“中”又是人心灵的中心,所以才称之为“中”。只有“中”才能保证公平均衡,公平均衡就是“君”的意思。《大禹谟》的所谓“允执厥中”根本上就是要掌控君主的心使之合乎于大道。因为君主之心如果合乎于道,就能够引导天下百姓的心同归于大道,而不是仅仅自己做一个有德之人就行了。君主处于天地之“中”的重要位置,必须中道而行才行,君主的心也有可能会被私欲所牵引,其道心可能被遮蔽,这就需要借助旁人的力量帮助自己能够中道而行。目的是大家一起保证天下能够大道流行,避免成为人欲横流之所在。在这里何心隐是在强调君主“中道而行”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在强调臣民自觉匡正君主的必要性。古代士人阶层从先秦以来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即帝师意识。他们的远大抱负就是塑造出一个像古代的尧舜禹那样的圣人和君主集于一身的人,从而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何心隐在这里也流露了这种帝师意识。
村里的宅门大多是老木头的,门上有铜锁钉,铜锁环,也是老的。门开着,站在门口,听到屋里有说笑声,进屋后又看不见人——原来是电视机开着,屏幕里坐着几位名星,说笑声是他们的。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中”和“中庸”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确实占有重要位置。实际上,“中”与“道”“心”“性”“天理”等核心概念都属于同一层级的范畴,而且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通性。正如在道家思想中,“道”与“自然”“素朴”“混沌”等概念具有相通性一样,所标识的乃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侧面而已。这是中国古代学术话语的基本特征。
儒家士人思想家标举“中”与“中庸”概念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既表征着中国古人思维方式方面的某种必然性,也隐含着儒家士人的政治诉求以及话语策略。因此,对“中”与“中庸”的阐释可以从一个角度切入到儒家思想的深层之中,可以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文化心态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式有更加清楚的把握。“中”与“中庸”思想也体现着中国古人的生存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显现。
入库河道是水、沙、污染物等进入库区水体的重要通道,对库区水文条件、淤积量、水体环境以及生态环境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根据不同入库河道的特点对河道实施生态建设是保护和改善库区生态环境非常重要的措施。
儒家标举“中”,也就是高扬“道”,是为君主或执政者制定行为准则,目的是规范、制约现实的君权。在儒家这里,“中”就是公正、正义、正当的代名词,作为“中”的阐释者和坚守者,儒家就有足够的自信心与合法性去规范君权了。儒家所代表的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流动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因此他们标举“中庸之道”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具有某种同构关系,无论是完全站在统治者位置上还是完全站在黎民百姓的立场上,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选择“中道”而行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所导致的“政治无意识”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与“中庸”实际上乃是士人阶层社会地位与政治立场的话语表征。
BetweenPoliticsandEthics:OntheevolutionoftheinterpretationofZhongandtheculturalessencereflected
LI Chunqing1,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2.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Arts,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in Confucianism, Zhong doesn’t only reflect the political pursuits and ethic ideals, but also signifies the dimension of philosophy in Confucianism. As a requirement and constraint to the monarchy, it embodies 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s; as the personality ideal pursued by Confucian scholars, it belongs to a moral realm; it also has the philosophical ontological meaning when considered as the “source” and “dao”, which “creates a harmonious order prevailing throughout heaven and earth, and makes all things nourished and flourish.” However, its meaning is flexible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oncept Zhong embodied 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s, and reflected the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during the time of Zi-Xue(Scholars’ School) in Pre-Qin Era. In the circumstance of Jing-Xue(Classics School) in Two Han Dynasties, it focused on political regulations, and evolved to an ethical concept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 the horizon of HE Xinyin in Late Ming Dynasty, Zhong returned to a political discourse directly pointing towards the monarchy.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n Zhong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fucian scholars and the monarchy along with their self-recognition.
Keywords: Zhong; Zhong Yong;Shi Zhong; Li-Xue (Neo-Confucianism); Xin-Xue (Philosophy of Mind)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4-0046-10
[收稿日期]2019-06-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学表征研究”(16JJD750008)。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侯珂)
标签:儒家论文; 君主论文; 中庸论文; 天理论文; 政治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学表征研究”(16JJD750008)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