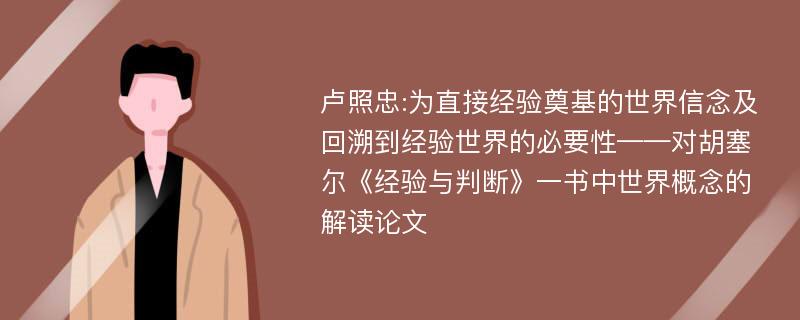
摘要: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一书中试图为传统逻辑学的明证性奠基。在阐明个体对象之明证性的前提下,具有“我为”特征的先验主体被唤醒。这个先验主体自身在把握性的“关注”实行中,发现自身是被吸引到世界中去的,而世界本身乃是预先被给予的。世界视域乃是为直接经验视域奠基的总视域,而经验视域又是有其自身特定结构和特征的。唯有解除科学精密世界对当下生活世界的意义遮蔽,源初生活世界的意义才能得以彰显。
关键词:明证性;经验;视域;世界;先验主体
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中力图澄清谓词判断在原初生活经验中的前谓词经验起源,其核心路径是经由间接判断、直接判断、判断基底、个体性对象等一步步的回溯,最终确立了个体对象明证性的必要性。而“世界信念”则是人的任何实践或认识活动都不可再还原或进一步追溯的最终根基,因为“这一世界信念的无所不包的基础是任何实践、不论是生活实践还是认识的理论实践的前提”[1]。正是由于世界的普遍预先被给予性,胡塞尔才以“世界作为对任何单个对象的经验预先给定的普遍信念基础”[2]这一专题的方式加以凸显。
一、个体对象之明证性经验
对象明证性问题实质上即是如何理解个体明证的被给予性及其方式问题。经验在最初的和最确切的意义上乃是与经过回溯的个体之物有直接关系的经验,同样,经验概念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即是与个体对象的明证性相关的概念;关于个体之物的判断,就是经验判断。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都是现象学前谓词意义上的个体对象、经验与明证性,所以,从“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诉求来说,在对经验概念内涵的把握上,首先要把握的是个体对象在“存在确定性”中的自身被给予性,即让个体对象如其所是所呈现的那样去经验它,并尽可能地排除社会的、心理的、科学的等后发经验的意义沉淀物的影响。另外,这个原始的经验概念还包括存在确定性的模态转化形式,如猜测性、或然性、好像等等。
这种原始的经验概念看似形式化、空洞化、意见化、未规定化,但这种作为原始素朴信念的经验概念却是一切意识形式最初的直截了当性。从发生学角度讲,我们在进行任何主动的认识活动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了‘被以为的对象’,即在信念确定性中素朴地被以为着的对象;直到经验的进一步推进或认识的批判活动动摇了这种信念确定性,将它变成了‘不是这样,而是那样’、‘估计是这样’等等,或者甚至把这被以为的对象也证实为在其确定性中‘现实地这样存在者’或‘真实地存在者’为止。”[3]如在中国流传甚广的“李广射虎”故事中(卢纶《塞下曲》四首之二[4]),在“林暗草惊风”的境域下,李广出猎,忽然看到草丛中有只老虎,然后“将军夜引弓”。此时此地的“老虎”即是在素朴信念确定性中被以为的对象、如它所是的对象、自身被给予性的对象,这种对象的现实存在性是由信念素朴地加以确认的;但在“平明寻白羽”的进一步考察中,在由箭镞“没在石棱中”的直观意义充实中,动摇或者推翻了过去的信念确定性的素朴性,原来不是“老虎”而是真正现实地或真实地存在着的“石头”。
在李广射虎的事例中,我们可以较好地体验个体对象之明证性的意指,它是一种“切身”地“切中”对象的明证性,是意向得以直观地意义充实的明证性;这显然不同于传统逻辑中那种前提和前提之间、前提和结论之间自身融洽意义上的清晰明证性。毋庸置疑,在我们实际性的生活实践中,一种切身的“预先关切”总已经发生着作用了,在其中,对象从来都不是作为单纯的一个孤立物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总是从作为某种境域的场景中,由于某种刺激的诱发作用而涌入我们的意识阈里来的。
二、作为自我主动性之最低阶段的接受性及被唤醒的先验主体
不同于休谟及其后继者所认为的那样——意识白板在原初只有纯粹的被动印象接受性。在胡塞尔看来,质朴意识在外部知觉中使对象得以显现的过程本身已经具有最低限度的自我能动性了。他前期对意向性意识中的本质直观空间侧显式“透视与投影”分析和内时间意识绵延式“原始的在场-记忆-前瞻”结构分析中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1一般资料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我院对脑血栓患者6例进行了研究分析,共有女性患者4例,男性患者2例,最小患者是13岁,最大患者83岁,平均(63.2±2.1)岁,将患者分成了对照组和观察组,均有3例患者,两组的一般性资料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能够进行对比分析。
显然,这种先验主体在“关注”实行中的“我为”(Ich-tun)特征,是不同于经验主体在“表象”实行中的“我思”特征的。
就最基本的外部感觉来说,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也并非如传统心理学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单纯一些孤立材料的汇集,乃至混沌一片,而总是具有一个确定结构的感性场景的,如李广出猎时看到的所谓“老虎”这个“好像是什么”的东西时,既有“某种东西”确实存在的感性信念确定性这种原始的意见,同时又有“林暗草惊风”这个感性场景的在场性运作。这个感性场景是在将林、暗、草、惊、风等作为各项“感性材料”而在意向性构造中融合为一个同质性内在视域的,这个感性场景作为“同一性之统一体”具有自我切身的亲熟性、亲缘性。反过来讲,在具体感性场景中,各感性材料之间作为预先被给予的东西在根源上也是相互亲和、亲融的,即它们是作为属于同一个感性场景内的东西而相互吻合的。借助于“联想化”运作,林、暗、草、惊、风等各感性材料在内时间意识的综合中,质朴意识将具有外在差异性的感性材料,在纯粹内在的关联中,吻合性地综合进同一性的统一体(感性场景)之中。
在整体发展中未能兼顾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一致,没有坚持量水而行、量水发展和以供定需等原则,工业产业全面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建设规模不断膨胀,同时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输配水管网不配套,造成现有水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及严重浪费。用水量的过快增长超过了当地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造成地下水超采、许多河流长期断流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在同质性亲缘性的感性、知觉场景中,经常会出现某种异质性陌生性的东西,这种作为“激”动人心的东西作为“刺激”总会令人产生某种情绪性趋向,诱导着“我”去朝向它,如“鹤立鸡群”,鹤作为显著不同于鸡群的东西,扰动我的心神,引向自我的主动性探查。这时候,不由自主或者情不自禁的素朴反思意识得以萌发,反身指向“自我”的意识开始觉醒,并进入一种自我清醒的状态。
在这个感性场景中,相似、相同性被把握,在此基础上异质性、陌生性的东西才得以凸现出来,并定向于某物(如好像是、应该是“老虎”),在机缘的作用下就有可能和其他具体感性场景融合为一个层次更高的同一性之统一体,如出猎的行为、弓箭、随从、疆场、战事、国家等,从而构建出一个层次更加复杂的“知觉场景”。
在对场景的投入式关注中,自我保持着清醒的状态,但却不是刻意乃至造作地保持清醒那样的强作镇定状态,而是一种原发式的投入式体验,自我沉浸于某物,甚至连自我的念头都不曾生起,就是纯粹地陶醉、沉醉于某物,物我两忘。“当自我关注对象时,自我就在对象那里了。”[5]如晋陶渊明《饮酒·其五》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6]在这种纯粹意境中,物我融为一体。不过,我们的日常自然语言在根本上是难以表达这种意境的,这就如同老子在面临要用语言称呼那个先天地生的寂兮廖兮混成之物时的窘境,只能“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7]。胡塞尔也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在场景中确实存在着主体性,但却不是伴随着我思表象的那种主体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自我性,“而是把一切使这个世界能够形成的这些作用当作可能的作用在自身中承担起来并实现出来”[8]的主体性,即“先验主体性”,“换言之,我们在揭示这些意向性的隐含作用时,在对世界的意义沉淀物询问其从意向性作用中的起源时,是把我们自己理解为先验主体性的。”[9]在原始意向性中起作用的主体,不可能是经验主体,而只能是在措辞上被生硬地表达的先验主体。为了防止误解,胡塞尔马上解释说,这里的先验不能从别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被理解为由笛卡尔所开创的那个原初的动机,即对一切知识形态的最终根源作进一步追问的动机。”[10]也就是说,先验主体并不是指在经验主体之外或之上的另一个特殊主体,而是指那种使经验主体得以可能并成为明确的“我思”意识的先天或先验化运作。
如唐代戴叔伦的词作《转应曲》:“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25]在老卒戍边这个知觉视域下,三个重叠“边草”的意义,并没有随着新的三个重叠“明月”的涌现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边草意象所体现的那种荒凉无依的意义,这种意义在持续着的同时又在新的“山南山北雪晴”意象中朝向更新的预期,最终在胡笳悲悲切切、呜呜咽咽的异乡之音中,被统摄在词眼“愁绝”之中。而这个“愁绝”既可以将以前所有的意象意义统摄起来,同时,又可以以处境对比的方式将视域延展到更新的知觉视域——“不似京华侠少年,清歌妙舞落花前(唐· 戴叔伦《边城曲》)。”[26]但不论是同一视域内不同事物的隐或显、在场或不在场,还是不同视域之间的扩展或更迭,“任何新进入到经验中的实在之物都存在于世界视域之中。”[27]任何具体的视域都逃脱不了世界视域的统摄。
本课题在加拿大里贾纳大学Fatima教授的指导下,把KWL+理论与大学英语读写教学相整合,分析2015级一本学生在使用KWL+模式指导下的语言学习情况。课程研究对象是2015级共379名学生,分别来自成都理工大学四个不同学院的6个理工科专业。授课学时为32个学时,所用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体验英语综合教程》系列教材。
但需要强调的是船舶发生保安事件后立即和船旗国政府主管机关和船公司先联系,不要随意寻求国际援助,一旦发出,可能需要付出高昂费用甚至导致公司破产。
三、作为普遍信念基础的世界
源发境域性的先验主体自身是具有意向性结构的,但“意向性结构”之所以可能并发生作用,又在于先验主体这个“源我”自身先验的“关注”实行的“我为”特征。同样,我们前面所讲的“个体对象”,也不是自然物存在意义上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先验自我在“我性主动性”的关注“实行”中通过意向性作用构建起来的“为我”物,这样,我们也就超出了单纯被动信念确定性的意见领域,才有了关于“对象”的确切概念。“因此对象化总是一种自我的主动作用,一种对被意识到的某物主动相信的觉识(Bewuβthaben);而这个被意识到的某物由于意识连续地延伸而在其绵延中成为一、连续地成为自(Selbes)的。 ”[13]但这“对象”又不能说是纯粹心理物,它是先验自我在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的实行下,在内时间意识的意向性中构建起来的意向对象。这种意向对象已经打穿了自然物和心理物的狭隘边界,或者说,它是有感性场景的“为我物”。
先验主体和意向对象都是在终极性和原始性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固然,我们可以说“真正存在着的对象首先是我们认识活动的产物”[14],但对于认识活动来说,这一真正存在着的对象“毕竟没有表明它从虚无中产生了对象,相反,无论如何,对象总是已经预先给定了的,正如对我们来说一个对象性的周围世界总是已经预先给定了一样”[15]。
作为感性场景和知觉场景的扩展,周围环境或周围世界也是一个预先被给予性领域而与我同在,这是一个任何人注定都要生于斯长于斯的领域。如果对这个周围环境进行进一步拓展的话,那就是整全世界,这个世界作为普遍性的基础,是包括认识行为在内的人的所有活动领域的共同前提,“我们也可以说,在一切认识活动之前,每次都先已存在有一个作为普遍基础的世界;而这首先表明它是无所不包的被动的存在信念的基础,是任何单个认识行动已经作为前提的基础。一切作为存在着的对象而成为认识的目的的东西,都是存在于这个理所当然被视为存在着的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东西。”[16]这个世界是关涉于人的世界,并非仅仅指向自然界,从词源学上讲,世界(Welt)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类学概念,“‘world’这个源自德文的英语语词意指‘人的年岁或生活’(wer+ald,德语welt)。”[17]
世界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领域。我们素朴地确信在我们之外有物存在,世界作为包括自然物和人类在内的存在者整体总是已经预先存在了,我们既被世界所吸进,又素朴地确信世界自身的存在。“这一世界信念的无所不包的基础是任何实践、不论是生活实践还是认识的理论实践的前提。整体世界的存在具有自明性,而这种自明性从未受到过怀疑,并且它本身并不是借助判断活动才获得的,而是已经构成了一切判断的前提。世界意识是处于信念确定性模态中的意识,它并不是通过某种在生活关联中特别提出的存在设定(Seinssetzung)的行为、作为此在着的把握行为、乃至于谓词的实存性判断行为而获得的。这一切都已经是以信念确定性中的世界意识为前提的。”[18]这里的“世界”乃是一个纯粹先在的世界,它是一个在外延上最广而在内涵上最狭的概念,它首先断定的只是世界自身的实存性、先在性,而不是那种“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19]后天追加的意义性,即带着过去经验沉淀物去反思的意义性;简单说来,从发生学角度讲,世界“意义性”处于世界“存在确定性”之后或之外。
合作学习通常采取小组形式,各个成员都需在学习活动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然后糅合彼此的观点,形成最优的学习方案。目前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日益受到重视,甚至被当成一种特殊的教学资源。合作学习可允许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充分展现个性化想法,并与组内其他成员进行交流,实现组内不同思考方法的优化与整合,通过群体智慧来完成共同的任务。由此可见,合作学习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与互助性,其学习意义较大。
所以,世界的存在不是设定的,它就是自在的,“一切刺激着我们的存在物都是这样在世界的基础上发出刺激的……世界作为存在着的世界是一切判断活动、一切加进来的理论兴趣的普遍的被动的预先被给予性。”[22]我们不可能比这追问的更远,既使是指向存在者全体即世界本身的知识,那也是后来追加的事情了。不过,在发生学意义上,同关于世界整体的知识相比,指向单个存在物的经验知识更具有原始性。
四、经验视域的结构和特征以及世界意识的一般结构
在具体的经验开启之前,我们总是已经素朴地预先确定了世界自身以及世界内的万物都是存在着的。
需要澄清的是,在我们说生活世界时,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来说的?理想化及其遮蔽又是如何运作的?解蔽理想化的覆盖作用又有何意义?又应当如何来实行这种解除呢?
“所以,任何有关一个单一物的经验都有其内在视域;而在这里,‘视域’就意味着在每个经验本身中、本质上属于每个经验并与之不可分割的诱导(Induktion)……这种原始的诱导或预期表明,它是原始地发动的认识主动性的一种转化模态,它具有主动性和原始的意向,因而表明它是一种‘意向性’模态,正是这种意向性模态超出了被给予性的核心而向外意指着、预期着。”[23]经验视域的这种向外意指的“诱导”结构表明了经验视域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从而具有“超越”的性质,它既可以超越经验对象的现有规定而预期地意指其他未被证实的规定,也可以超越此物本身而指向只是在背景中尚未被意识到的他物,“这就是说,任何经验物都不只是拥有一个内在视域,而且也拥有一个无限开放的具有共同客体(Mitobjekte)的外在视域。”[24]这些共同客体,虽然我眼下尚未关注它们,但我随时都可以把它们抓取出来。至于这些在预期中可能被关注到的共同客体之间的差异大小,倒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经验视域虽然其在运作中有内在和外在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它们共同来源于作为同一个时空视域的世界。世界是经验视域的基石或前提,经验视域中的存在者在根源上是同一个世界时空视域之中的存在者。
经验视域的“诱导”性结构,既表明视域的“内外超越性”,同时在经验的流动中,又体现着视域的“意义超越性”,已体验过的对事物的统觉意义不会完全消失,它总是可以在“意义储存”的基础上去预期和统觉更多、更新的事物意义。
在我们投入式的场景体验下,意向体验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趋向模态,一种是生动地生活在体验“之中”,忘我地全神贯注于意向对象性;另一种方向相反,“或者说从其中的意向对象出发,产生出一种进向自我的召唤力,一种以各种不同的情绪力量来唤醒自我(这自我在清醒状态下在别的方面已经是能动的)的刺激。”[11]这种由意向对象召唤而被唤醒的自我,即是先验自我或先验主体,胡塞尔后来也称之为“源我”。这种由意向对象的刺激而被唤醒的自我,一方面是接受性的,接受被给予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是生产性的,它的实行方式是“关注”,“这种关注本身具有一种‘我为’的特性,同样,在关注的模态中注意力的视线的游移也是一种‘我为’。”[12]
她看妓女们全穿着素色衣服,脸色也是白里透青,不施粉黛的缘故。赵玉墨穿一袭黑丝绒旗袍,守寡似的。她的行头倒不少,服丧的行头都带来了。书娟很想剜她一眼,又懒得了。妓女们在鬓角戴一朵白绒线小花,是拆掉一件白绒线衣做的。
经验视域的“诱导”性结构,还指示着视域的“未规定的普遍性”特征和“确定的特殊性”特征。所谓未规定的普遍性,是说我们很难一下子把握事物的全部规定,由于具体视域的局限性,事物“普遍”存在着还未被规定的东西,或者说,存在着还未进入视域显明地带的东西,例如一扇门的背面肯定是有颜色的,但具体是什么颜色却是未定的。所谓确定的特殊性,是说虽然事物的具体规定是待定的,但其待定的范围不是任意的,如对那扇门背面的规定是视向颜色的,是有特殊的确定性范围的。
鬼子队长收起军刀,又叽哩呱啦乱叫一气。翻译庄槐冷着脸说:“太君要你把烧窑的师傅请来,他要亲自问话!”停了一下,又说,“把人给我好好的带来,不许碰他一个指头!”
经验视域的“诱导”性结构还有着“普遍固有的相对性”特征,这个特征既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任何视域都普遍具有的内在视域与外在视域的相对性区分。当然,还包括视域中已显明的已知性与隐晦的未知性之间的相对性区分,在这种相对性区分中,一种指向未来的、预先勾画出的、但其意义尚未得以充实的“空视域”得以凸现出来,但这个空又不是纯粹的虚无,它毕竟还有可规定的特征和可能性,犹如面对未来、向理想进发,虽然一路上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又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预知的。
任何具体视域的存在与拓展都是被世界视域所涵盖的,由具体经验视域的基本结构及特征而来,我们实际上已经生活在对世界视域的领会之中了。“所以世界意识的基本结构,或者说打上了世界的相应印记的基本结构,作为一切可经验到的单个实在事物的视域,就是带有其普遍固有的相对性、带有未确定的普遍性和确定的特殊性之间的同样普遍固有的相对区别的已知性和未知性的结构。”[28]因为人本质上是生活在世界之中、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所以必然与世界具有普遍亲切或亲熟的主观性特征,而这,正是我们有意义的源初“生活世界”得以可能的先天或先验性前提。
这就如同《传习录·钱德洪录》[20]中王阳明同友人南镇观岩中花树公案中提到的问题,“岩中花树”在未进入感性场景之前,心物皆寂,但寂毕竟不同于无,只是一切都还处于未规定状态之中而已,此时只有素朴的有物存在意识;唯在岩中花树融入人的感性场景之后,此物才对人来说显现为花,花的意义才得以具体的规定,即“存在先于意义”,或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21]但无论如何,世界自身的存在却是不可再“先验还原”的,如果再要追问世界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不可以不存在,那就只能称之为哲学的玄思,而不是原始的生活经验了。
五、回溯到经验明证性,即回溯到生活世界,消除遮蔽生活世界的理想化
我们本质上就生活在世界的经验之流中,这就是我们的本真世界。回溯到经验的明证性,在导向上即是要回溯到世界本身,将世界视为一切单个经验的无所不包的基础,在世界中经验到的就是经验世界。“回溯到经验世界就是回溯到‘生活世界’,即回溯到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总是已经在生活着,并且它为一切认识和一切科学规定提供了基础。”[29]但是我们现实的当下生活世界由于某种理想化的作用,原始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经验已经被遮蔽,这种原始的生活世界经验,“它对于理想化还一无所知,相反,它却是这些理想化的必要基础。”[30]
如果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的经验,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东西是毫无关联地进入我们的经验体验中的,一物总是关联于另一物,总是有一个具体的感性场景在起着作用的。例如,我们观看某一物时,视线在聚焦这一物的同时,视觉余光也总是起着作用,把某物周围的环境也一并视出来,焦点意识总是伴随着边缘意识的。任何经验都有自己的经验视域,即使在由一个经验过渡到另一个经验时,经验视域也总是存在着,只是视域的域限有所调整而已。而且,处于经验视域中的任何经验总是具有开放性、指向新的可能性,从而将更多的可能事物融合进来,形成一个向新的可能性无限开放的游戏空间(Spielraum)。
胡塞尔认为,带有原发视域结构、带有完全的经验明证性这样的源初生活世界,在由近代以来发端的当代精密实证主义科学理想化模式遮蔽下,是很难被轻而易举地澄清的。
首先,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在其中进行一切认识和判断活动的当今生活世界,并非是由源我或先验自我亲身体验而来的,并非世界自身的被给予,而是外在性地由他人或社会将现成的经验成果或意义沉淀物赋予我们的,我们所接受的东西,实际上是已经被预先规定好了的东西,是丧失了原始经验明证性的东西,“这种预先被给予性的意义是这样被规定的,即同属于这个已预先给予我们的这些当代成年人的世界的,是一切由近代自然科学在存在者的规定上所成就的东西。”[31]这说明,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当今生活世界,是一个遮蔽着本源生活经验的成人世界,是一个已被以科学理念为范式所规定好了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自己的童年和根基的世界。
当代高速公路桥梁的建设缩短了人们的通行时间,打破了地域交通的限制,使得高速公路在地势险要的山区也能纵横交织。
其次,这个成年人的当今生活世界,是被一个理想化理念所统摄的世界,即“一般存在者的无限的全体自身就是一个合理的全体,它可以相应地凭借一种无所不包的科学而毫无保留地被掌握。”[32]这是一个祛魅的世界理念,即凭借精密的方法产出的宇宙理念。它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所谓‘客观地’,就是说‘一劳永逸地’和‘对任何人而言地’。”[33]这种客观性成为了不言而喻或不言自明的东西。
再次,这种“客观性”,产生于僭越的科学理念方法,起源于自欧几里德以来对自然界的数学化理想,以至于伽利略式地将精密的世界概念偷换了我们的经验世界的概念,并延伸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个精密科学用来把握存在者宇宙的宇宙,无非是一件披在直接直观世界和经验世界之上、披在生活世界之上的理念外衣,因而科学的任何一个成果在这种直接经验和经验世界中都有其意义根基且都要返回到这上面来。”[34]
最后,那么,如何解除精密科学这种对直接经验世界的遮蔽呢?胡塞尔认为,一方面要阐明精密科学的理想化是怎样产生和运作的,以及它的根基如何在直接经验世界中有其起源,另一方面,要“对那些属于最终原始的、尚不精密的、尚未从数学—物理上被理想化的明证性领域的意见(Doxa)进行辩护,”[35]并极力阐明:“这个意见的领域并不是一个比认识、判断性的知识及其沉淀物的领域在明证性等级上更差的领域,而恰好是最终原始性的领域,即精密知识按其意义所要回溯到的领域。”[36]而这也正是整个《经验与判断》一书最鲜明的主题。
由于增加了智能分析功能,且可以通过网络继电器远程启/停声光报警器,使得声光报警器日平均工作时间约为零,本次分析将忽略其日平均耗电量。
六、结语
胡塞尔通过逐次的回溯,确立了直接经验的明证性及作为信念基础的世界概念,并对世界视域进行了精心的描述和说明,从而为逻辑学乃至科学本身发掘出了最终的根基,这也是胡塞尔将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本质要求。
在对世界信念问题的具体开展中,胡塞尔区分了直接经验世界、当今生活世界和科学精密世界这三个层次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精密世界对生活世界进行了科学的理想化操作,从而遮蔽了生活世界自身的意义,所以有必要由精密世界回溯到生活世界;而当今生活世界本身又因为受到传统现成的意义沉淀物和精密世界的理想化影响,缺乏源发性的生机和活力,其自身意义已经隐而不显了,所以又有必要由生活世界回溯到源初的具有直接明证性的经验世界。反过来讲,对直接经验世界的阐明,也有助于消除遮蔽在生活世界上的精密世界科学化理念外衣的影响。
参考文献:
[1][2][3][5][8][9][10][11][12][13][14][15][16][18][22][23][24][27][28][29][30][31][32][33][34][35][36][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M].邓晓芒,张廷国, 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46,44,45,99,67,67,67,101,102,80-81,54,54,45-46,46,46,49,49,51,53-54,63,63,59,59-60,60,62,63,63.
[4][清]蘅塘退士,选编.唐诗三百首[M].李炳勋,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40.
[6]张丽丽,编.古诗三百首[M].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5:213.
[7][春秋]老子.道德经[M].北京:华侨出版社,2014:94.
[17][美]郝大维.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7.
[19]田文.世界的模样,取决你凝视它的目光[M].北京:华侨出版社,2015:封面.
[20][明]王守仁.传习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423.
[21]江怡.《逻辑哲学论》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182.
[25]王兆鹏,主编.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42.
[26][清]彭定求,主编.全唐诗:第三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1395.
TheWorldBeliefthatFoundsDirectExperienceandtheNecessityofTracingBacktotheExperienceWorld:InterpretationoftheWorldConceptinHusserl'sExperienceandJudgment
LU Zhao-zhong
(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Sports University, Jinan 250102, China )
Abstract:Husserl trie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of of traditional logic inExperienceandJudgment. On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proof of the individual evidence, the transcendental subjec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Ich-tun" is awakened. The transcendental subject itself finds itself attracted to the world, which itself is given in advance, in the practice of grasping "concern". The world horizon is the general horizon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irect experience horizon, and the experience horizon has its own special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nly by remov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cientific precision world from the current life world ca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riginal life world of intuitive experience be revealed.
Keywords:evidence;experience;horizon;world;transcendental subject
中图分类号:B516.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9)02-0024-06
收稿日期:2018-12-02
作者简介:卢照忠(1978-),男,山东菏泽人,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研究。
(责任编辑:孙书平)
标签:视域论文; 世界论文; 经验论文; 对象论文; 明证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山东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