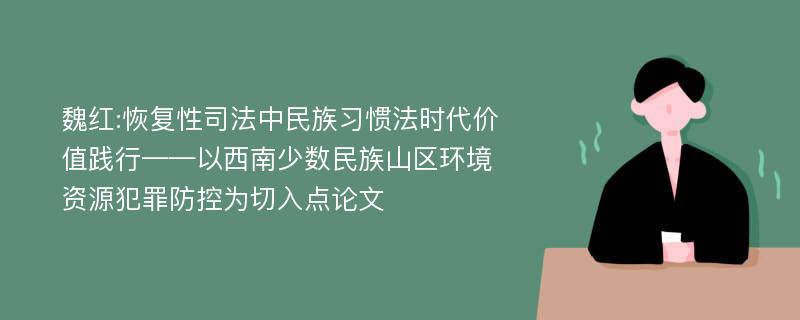
摘 要:生态文明是人类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对未来的共识。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与恢复性司法理念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民族习惯法对于恢复性司法的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具有积极性价值。在西南少数民族山区环境资源犯罪防控中,以新型村规民约为时代背景的民族习惯法的规范载体,通过非正式社会化纠纷解决机制,民族习惯法得以介入环境冲突处理模式,运用补植复绿、恢复原状、增殖放流以及间接修复等非刑罚性处罚措施,践行民族习惯法在恢复性司法中对生态保护、环境修复的价值导向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民族习惯法;西南山区;环境资源犯罪
一、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环境资源犯罪的防控价值取向
(一)恢复性司法理念已成为现代司法的价值追求
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 (2002/12号决议)中提出,恢复性司法是应对犯罪发展变化的对策,希望通过使受害者、罪犯和社区复原以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与平等,建立并促进社会和谐。传统报应性司法过于强调对犯罪者的惩罚,而忽视了对被害者与社会所遭受损害的回应,强调对犯罪者的刑事制裁而忽视对犯罪所造成社会矛盾的解决,因而引发了西方社会“司法危机”[1],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司法的价值与目标,恢复性司法理念应运而生。该理念认为不应求诸刑罚方式进行社会规制,拒绝采用以惩罚痛苦来衡平犯罪伤害的司法手段,其核心观念认为司法重点在于修复犯罪造成损害,尤其是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正是由于恢复性司法理念强调被害人和社区在刑事司法中的回归,弥补了在传统司法中的缺位,强调社会关系的恢复以弥补传统司法在应对犯罪损害上的不足。因此,恢复性司法逐渐在各国推行并展现出司法新趋势,关注重心从对犯罪惩罚逐渐转移到对被害人与社会因犯罪所遭受的损害及其恢复。因此,恢复性司法亦被视为“建立在规制性金字塔底部上的一种优先选择。”[2]
(二)恢复与保护环境成为环境资源犯罪防控目标
由于环境资源犯罪的危害性不仅在于破坏环境资源范围涉及面广,危害后果具有迁延性、叠加性和连锁效应等特点,而且在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破坏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同时,还威胁着动植物生存环境导致生态链断裂,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从对立到融合的转变,最终认识到只有与自然环境友好、和谐相处才是人类幸福、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从生态伦理观出发,认为环境资源犯罪惩治目的并非简单要求犯罪人为其破坏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实施补救与恢复性措施,以消除犯罪对环境资源造成的持续性危害,实现生态保护功能。正是基于此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将恢复与保护环境作为环境资源犯罪防控的重要目的加以定位,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防控犯罪的价值基础。
本书是美国顶级性教育专家黛布拉集三十多年性教育经验的经典之作,为畅销全美20年的性教育“圣经”。本书向父母们讲述了如何对自己的子女进行
(三)西南山区少数民族生态观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相契合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认为,人类是在不断对自然环境改造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影响的不断调适过程中适应成长的,[3]而“文化是一个民族对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4]西南山区少数民族先民大多具有艰辛迁徙史并历经多重生态灾难,尊重与爱护自然已成为民族文化心理与传统,甚至这种文化心理已经上升到与生命平等相待的哲学高度。[5]因此,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人与万物同源、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观念根深蒂固、朴素而深邃。
恢复性司法实质在于采取非对抗方式融解社会矛盾冲突、弥补赔偿加害者对受害方与社会所造成的损害,最大限度地修整与恢复受到损害的社会关系。基于此认识,恢复性司法理念体现在环境资源犯罪防控中,就是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和谐”[6]为践行目标。正是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观与恢复性司法理念具有共同的文化内核与价值追求,因此二者具有契合性,能够在环境资源犯罪防控中并行不悖、共同发挥价值与作用。
二、民族习惯法在环境资源犯罪恢复性司法运用中的价值
(一)立法资源价值
作为民族习惯法现代表现形式之一,新型村规民约是国家对环境习惯法的规范认可并予以确认而成为现代环境立法的组成部分。[11]新型村规民约内容与国家环境法相互衔接,力图让民族习惯法融入制定法的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同时坚守民族习惯法生态伦理传统。在形成过程中保持了民众参与自愿性与广泛性特征,不仅成为连接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桥梁,也积极探求弥补国家环境治理立法单一性的不足与局限性,试图补给并克服环境制定法的非自足性,引入民族习惯法中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观念,在村规民约中规定保护生态环境,严禁任何形式的破坏生态行为。如贵州雷山县郎德上寨有着保护自然环境的历史传统,该村寨森林覆盖率达到80%。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发展乡村旅游、保护村寨生态环境,村民制订相关村规民约,明确划定自然环境保护范围,严禁在保护区内毁林开荒、狩猎打鸟、炸鱼毒鱼、挖山采石、建窑烧炭;而在贵州六枝特区梭戛长期生活的“菁苗”苗族同胞,不仅于1998建立了我国第一座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梭戛生态博物馆,而且2001年梭戛附近的12个自然村寨还推选代表成立“社区民族原生态文化自然保护管理委员会”,制订章程与乡规民约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与环境资源,体现了少数民族群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传统的主体性意识。[12]由于新型乡规民约符合民族习惯与传统,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与乡土气息,在少数民族地区影响广泛、执行效果明显,成为制定法的有效补充。以万物相依、平等共荣朴素生态伦理观为价值基础的新型乡规民约,与恢复性司法中所蕴含“善良、理解、宽恕的人文情怀”[13]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新型乡规民约成为民族习惯法在恢复性司法中规范性体现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不仅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立法多元化,创新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保护规范新形式,而且还催化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中,国家治理与民族地区乡土自治并存的立体化治理模式。
人们对社会规则遵从的内在约束不在于官方制裁的威胁,而在于社会(族群)与个人道德控制交织力量的影响。人们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规范与禁忌(禁令)在人际关系网络中传播共享,内化的代表性规范和道德观念才是制约人们行为举止、遵从秩序的有力禁锢与引导。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于规则遵从度最重要的规范化影响在于人们的认知,由于少数民族群众所遵从的规范和秩序与所信奉的文化伦理观与道德观相一致。因而,对于人际关系和个人道德所产生的遵从力量,民族习惯法既助力其中又驭使其上。梁治平在《社会与国家》中提出:“如果国家的环保制度能够与当地人民的环保理念、环保文化相契合,那么无疑将促进国家法制在当地人心中的内在认同。”[10]因此,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民族习惯法,对于环境资源犯罪惩治与预防具有重要的规范引导与补充作用。一方面,民族习惯法中蕴含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内化为人们秉承着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的理念而参与生产与社会实践活动,唾弃与反对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与犯罪行为。对非法行为的最佳阻却源于社会控制的非正式力量,民族习惯法在发挥“培育社会角色功能”的同时,能够为预防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起着积极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民族习惯法在环境资源犯罪惩治执行中,教育与引导破坏生态环境者认识到自己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能够自觉接受法律惩罚,并愿意最大限度地弥补与修复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恢复因犯罪而破裂的社会关系,为恢复性司法顺利推行提供重要帮助。
(二)司法资源价值
在西南山区,少数民族群众自古以来就有着与自然环境相依共存的生态伦理观念,很早就形成了尊重一切生命、尊重万物的自然道德观。不论是在民族习惯法的历时性维度中以神话传说、民族禁忌甚至象形图记等显性表现上,还是在以村规民约、寨规民俗为载体的共识性维度中,都表现出广大民众自发参与、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认识。而且,少数民族地区对破坏环境资源的责任承担方式与纠纷解决方式也具有多元性特性。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对破坏森林、树木和附随环境等自然要素的行为采取多种罚则形式,既包括罚款、罚物与没收财产等经济惩罚,如贵州黎平县肇兴乡纪堂、登江与从江县洛香乡弄邦、朝洞四个陆姓侗寨,在光绪年间共同订立的《永世芳规》 中规定:“并杉、茶、竹、芦、古树、山林,不准斧斤妄伐而偷……砍伐古树、竹、笋,罚钱三千文”;在侗族山歌中也唱道:“山有山规,寨有寨约,不管谁人,不听规约,大户让他产光,小户让他产落”;[8]还有对毁坏山林者要求采取“补种”“补植”“复绿”等补救行为,如贵州锦屏县侗族村寨严禁砍伐山林、毁坏森林,如有违规者除了罚款、照价赔偿外,规定失火烧毁山林的负责营造成林,发生火灾的必须敲锣喊寨一个月,破坏村寨田间土坎、沟渠的令其修复;[9]还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惩罚违规者同时对全寨村民进行宣传教育,如素有“滇黔锁钥”之称的云南富源县水族村寨,近年来形成一些独具特色的村规民约,对违反护林保土规定、滥砍滥伐的村民处以一定罚款,将罚款全部用于请文化演出队或放映队为村民演出或放电影进行生态保护宣传。[8]在处置破坏环境资源行为的方式上,西南山区民族习惯法相较于制定法更具灵活性与多样性,不论是由苗族“理老”“寨老”主持调解与处分,还是布依族地缘性社会组织“榔团联盟”进行联盟商议、仡佬族传统社会组织由“冬头”召集“会款”对违规行为调处与裁决,都是依据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规约的认可度与惩罚承受能力进行相应惩处与调整,由于具有灵活性与适应性,因而更能凸显生态保护功效。因此,现代社会中,民族习惯法能够弥补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中单一性模式的不足与局限性,为制定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恢复性司法运用提供补充、进行调适,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三)执法资源价值
人们的欲望只能靠他们所尊从的道德来遏制。在先民社会,族群共同信奉的集体情感认识是最初的秩序规范,也成为后世法律规范的渊源。由于道德情感共识具有原发性与内生性,成为制定法的核心价值与灵魂。西南山区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伦理观,由于其蕴含强烈的“民族信仰”内容与道德共识基础而成为环境习惯法核心与亮点,并与现代生态环境保护观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如云南布朗族有着“削木为人”的族源传说,每个布朗村寨都有自己的“龙山”和“龙林”,布朗人对森林与树木都怀有敬畏与尊崇之心,历代布朗族民间都有护林、育林规约;西双版纳基诺族也有“五种林区不伐”“五种树不砍”的民族禁忌,有着尊崇与保护树木、森林资源的习惯;[8]居住于黔南、桂北山区的水族,每年定期举行“封山议榔”,议定“封山榔规”保护山林资源;侗族地区“款约”以及瑶族地区“石牌”所定“料令”等,大多包括封山育林、禁止乱伐、乱猎、乱捕以及保护水源和山地等内容,除了相应奖罚条款外,还包括发生相关纠纷、冲突时的调处原则与方式。
三、民族习惯法在西南山区环境资源犯罪防控中的实现路径
(一)新型村规民约——民族习惯法在恢复性司法中的规范性体现
“法,自其最大之义而言,出于万物自然之理。”[7]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看来,特定自然环境造就了特定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个性。在人类形成与繁衍早期社会中,因自然环境孕育生成并烙下大自然痕迹的环境习惯法很早就诞生,并成为人类社会一体遵循的基本社会规范。环境习惯法是人类社会幼年时期较早形成的规范与规则,也成为后世制定法的重要渊源之一。
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角度划分创业知识接近经典划分,但是在实际运用方面存在操作性不强,掌握困难的情况。根据企业运作的实际情况来划分创业知识,因为不管是隐性创业知识还是隐性创业知识,为促进企业的创立与运营,大学生创业者应该掌握包括创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企业经营管理知识、政策知识、财会知识、公关交际知识等在内的多元知识综合体。因此,根据创业过程中涉及到的事项的内容的不同可以把创业知识分为5个方面,创业政策、法律知识、产品知识、开业知识和经营知识。这5大类知识包涵了创业中可能遇到各种情况与问题的处理原则与对策。还可以进一步展开,形成一个创业知识库或创业知识图谱(见图1)。
(二)非正式社会化纠纷解决机制——环境冲突中民族习惯法介入模式
在对环境资源犯罪的处置方式中,除了通过刑法惩处犯罪实现威慑与预防犯罪功能之外,对部分危害轻微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还可以通过非正式社会化纠纷解决机制,运用民族习惯法进行调解与处理,实现“定纷止争”功能,恢复受损害的生态环境,实现对环境资源的切实保护。有学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发现,当发生砍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行为时,有近70%的少数民族群众选择报告村长、寨老,通过村里(族里)依据乡规民约处置;当发生冲突与纠纷时有80%的群众选择由寨老、族长主持调解解决;[14]由此可见,村、寨等乡土组织和村规民约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高权威性,可以合理运用族长、理老、寨老等民间权威人士影响,并将彝族“家支”、苗族“房族”等纳入非正式社会化纠纷调解机制,组成共议会或调解小组,依据法律、法规与乡规民约调解处理环境矛盾与冲突。如近年来贵州黄平县创建的“多元化调解机制”,以村民调解小组与“个人调解工作室”为初级调解组织,村委会调解委员会为第二级调解组织,乡镇司法所、公安机关与调解委员会组成第三级调解组织,形成“包含正式与非正式、民间与官方、自治与非自治的纠纷调解机制”,[15]民族习惯法通过非正式社会化纠纷解决机制介入到恢复性司法在环境资源犯罪中的运行。
(三)非刑罚性处罚——恢复性司法执行中民族习惯法功能展现
环境资源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犯罪人一般并不是以破坏环境为直接目的,而以获取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为目的,犯罪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往往是模糊不清,且犯罪受害者一般为不特定多数人或具有不特定范围。当前环境资源犯罪刑罚主要为自由刑与罚金刑。前者虽然具有惩罚与改造的一般预防功能,但是无法阻止和减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持续侵害,并弥补破坏行为带来的损害,忽略了广大受害人最殷切期望在于受破坏环境的恢复、良好生态环境的维护。后者虽然对积极性犯罪而言是罚当其罪,并且被认为是惩罚趋利性犯罪的最佳手段,但关键在于环境资源犯罪危害后果具有延展性与蔓延性并难以准确认定,因此很难确定罚金的确切金额。而且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少数民族群众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对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而言数额不大的罚金,也远超过少数民族群众的承受能力。因此,从恢复性司法理念出发,在少数民族地区环境资源犯罪制裁中,应充分发挥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作用,重视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辅助与补充作用。针对犯罪特性以生态修复补偿为核心,借鉴民族习惯法处理环境冲突的方式与措施,采取补植复绿、生态修复等多种非刑罚处罚措施,弥补现有刑罚方法不足,起到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功效。如贵州铜仁江口县法院在2018年审结的毁坏林木案件中,发出多项“植树令”“管护令”,先后要求10名以上被告人进行复植补种树苗;同年,在玉屏县法院审理的失火案中,在判处被告人缓刑后责令缴纳保证金,以督促其对被烧毁山林“补植复绿”。[16]上述法院对破坏环境资源轻微犯罪的被告人,具有认罪、悔罪表现并进行或同意补种、复绿或放养鱼苗等恢复生态活动的,都适用非监禁刑并从宽处罚,通过恢复性司法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文章中我们仅讨论针对共识机制的攻击方式,并不考虑例如双花攻击、日蚀攻击、整数溢出攻击、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等针对区块链其余部分的攻击方式。白帽汇安全学院列举了5种针对共识机制的攻击方式[12],部分攻击方式仅针对部分共识算法。
参考文献:
[1]于改之,崔龙虓.“恢复性司法理论国际研讨会”综述[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4):1 56.
[2](澳)约翰·布雷韦斯特.恢复性司法的功效[J].侯晓焱,译.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4):44.
[3]贾仲益.生存环境与文化适应——怒族社会-文化的生态学解读[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91-92.
[4]郭家骥.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J].民族研究,2003,(1):48.
[5]陈金全.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 62、8.
[6]张霞.生态犯罪案件中恢复性司法应用研究[J].政法论丛,201 6,(2):1 1 4.
[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严复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
[8]何兴亮.中华文明·中国少数民族文明(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 0:874-875,876- 877,878-879.
[9]高其才.变迁中的中国习惯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 7:1 03.
[10]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 996:32.
[11]郭武.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主要“场景”的展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 6:21 1.
[12]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经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 4:275-322.
[13]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
[14]杨爱华,吴位凡.国家林业制度对双柏县彝族地区的影响[J].林业调查规划,201 0,(1):74-75.
[15]甘明.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研究——基于黔东南少数民族纠纷多元化调解司法实践的考察[J].传承,201 5,(1 1):91.
[16]杨军.用“恢复性司法+专业化审判”守护绿水青山[J].人民法治,201 8,(4):63.
The Era Value Practice of Ethnic Customary Law in Restorative Justice:Tak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rime in Southwestern Minority Mountainous Areas as the Breakthrough
WEI Hong
(Guizhou University, Law School, 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uma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he consensus of the future.The simple ecological ethic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philosophy of restorative justice have a common value basis.Ethnic customary law has a positive value of legislation, judicature and law enforcement resourc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crime in southwestern minority mountainous areas, the new-type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taken as the standard carrier of ethnic customary law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Through informal socializ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ethnic customary law intervenes in the settlement mode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dispute.By means of non-penal punishment measures such as replanting, restitution, proliferation and releasing, and indirect restorati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ethnic customary law 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in restorative justice is practiced.
Key words:restorative justice;Ethnic Customary Law;Southwestern Mountainous Areas;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rime
中图分类号:D5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9)01-0019-05
DOI编号: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1.005
收稿日期:2018-11-30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8年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基地课题“西南山区环境犯罪惩治研究——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运用”(项目编号:2018jd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魏红(1969-),女,山东阳谷人,法学博士,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法学、刑事法学。
(责任编辑:卢丽娟)
(责任校对:小 璐)
标签:习惯法论文; 司法论文; 环境论文; 民族论文; 恢复性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调查分析论文; 《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贵州省2018年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基地课题“西南山区环境犯罪惩治研究--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显中的运用”(项目编号:2018jd020)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贵州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