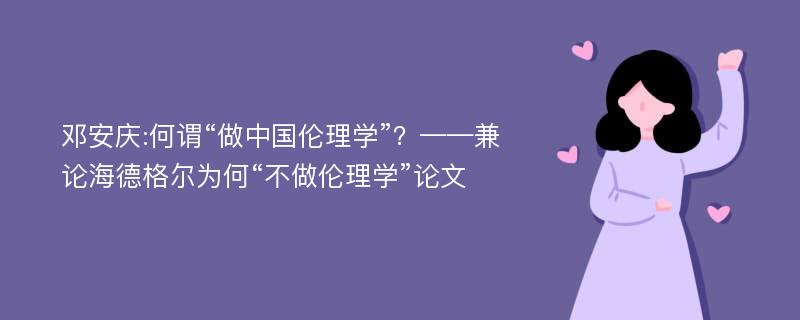
摘要:“做中国哲学”这一提法本身所担忧或反抗的乃是“述而不作”的“哲学史叙事”,即在历史性的知识叙述中迷失普遍的哲学之思。因此,它是一种从超越历史性、地域性知识叙述而向真正哲学性提升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身不是反抗哲学的世界性,相反却是走向世界性。唯其如此,“做中国哲学”才是正当性的吁求。伦理学虽然从属于哲学,但毕竟“伦理”有其地域性,所以“做中国伦理学”没有正当性的疑问。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做“描述伦理学”而是“做哲学伦理学”,我们必须拷问伦理的伦理性,道德的道德性,这就必然上升到了一个纯思的领域,我们就不能单纯地以一时一地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或依据,而是必须为此寻找某种绝对的标准或依据。于是,做中国伦理学与做中国哲学一样,面临相同的本原性问题:如何为存在的正当性辩护?以及存在的家园何在?但是,在西方哲学中只有单纯思辨哲学才是第一哲学,在这种第一哲学中,永远都是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而永远做不到以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来为存在的正当性辩护。但“以伦理本位”的中国哲学不正是蕴含“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之义吗?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在第一哲学层面上证成这一学说,即证成先天的伦理关系具有存在的正义性,那么既证明了中国哲学(伦理学)合法性问题,同时也完成了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成就中国哲学世界化的同时,也同时实现世界哲学的中国化,确实是一项真正的文化伟业。
关键词:做哲学;做中国伦理学;第一哲学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伦理学界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提倡“做中国哲学”或“做中国伦理学”。[注]参见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朱贻庭:《“伦理”与“道德”之辨——关于“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点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高兆明:《伦理学与话语体系——如何再写“中国伦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之所以令人注目,是因为这种提法有两个亮点,一是强调“做”,一是强调做“中国的”哲学或伦理学。这两点对于中国从事哲学、伦理学的人无疑都是非常“切身”的问题。因此,这种“做中国哲学”或“伦理学”的“呼声”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反思。我们必须弄清楚,强调“做哲学”时我们究竟强调的是什么,强调“做中国伦理学”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使命感,当“哲学”或“伦理学”与“中国”相连时,其特质究竟何在?维特根斯坦强调“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区别于“论述哲学史”,是明确提出了“做哲学”的标准的。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述而不作”中抽身出来“做哲学”,还要做出它的中国特色,必须首先确立起哲学之为哲学的标准,即哲学的入门门槛,然后在此“哲学”标准之下,显示出它的“中国哲学特色”。我们非常期待这一创新性成果,即便确实非常难,但这种“难”,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哲学而言的,对于“哲学本身”而言,它就是一大难题。
皖河流域上游山区河床比降大,长河上游河床比降约1/2000,山坡坡度一般为30°~40°,最陡达70°,汇流快,洪水传播速度很快。各支流出山口以上河道洪水过程一般以单峰为主,洪水历时一般1~3天。
一“哲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
“哲学”不是一件“器物”,有一个现成的模板让你把它“做”出来。它不像“做衣服”、“做房子”、“做鞋子”那样具有指认性:“衣服”尽管五花八门,奇装异服有的是,但是不是“做衣服”,我们只需看看它的“材料”和“形式”,便能一眼看出,某人是不是在“做衣服”。“做房屋”、“做鞋子”也同样如此。但“做哲学”决然不同。某人写了一篇带有“哲学”字样的论文或书,他就是在“做哲学”吗?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哪怕就是我们大学里的哲学教授,写了号称是“哲学”的论文或书籍,我们也不能马上指认,这就是在“做哲学”。
时代的改变、科技的发展带来摄影、观影方式的变化。虽然好作品的根本标准是拍出人物灵魂的东西。然而美颜摄影和修图软件、滤镜的一再升级,似乎所谓“灵魂”的东西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在坚持一定的原则、标准之后,并不能摒弃新技术、新事物的诞生和新形式、审美的变化,即便它只是一段时间的流行,也不能排除在外。如果“人像”的风向标可以立意更广阔一些,也许对于时尚的模仿痕迹会淡一些,形式会更加多样和出彩。
之后,赵忠尧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地磁研究所等美国的几个加速器及宇宙线实验室做义务工作,为的是能换取一些零件。他节衣缩食,把有限的经费和生活补贴,都用来向工厂定制加速器零件!
哲学是一项思想的事业,这种思想具有其特有的门槛,只有在门槛之内的思想活动,才能被认可为“哲学思想”。所以,“做哲学”的这个doing,是一个现时态动词,“哲学”于是就要由名词转变为动词,德语把它表达为philosophieren。这个动词要表达的,不是你把别人已经形成了的“哲学”复述一遍,告诉人们黑格尔有哪些哲学,康德有哪些哲学,维特根斯坦有什么哲学,你就是在“做哲学”,而是你本人的所思所想,就是在进行一种所谓的哲学,即在philosophiren。
这种思考本身是要在“所思”对象上,证明自身的“思想”“思入”了“对象”,而非自身主观的想法,因而是以自身独特的个性之思体现为事物本身的客观本性来确认“哲学之思的普遍性”,但这本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自信自身的所思才是真正的“哲学”,别人的,哪怕是被承认的哲学家,都会被自信自己在“做哲学”的人评判为“尚不够那么哲学”!对此,马克斯·舍勒就有很深的体认,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两种不同侧面的区分,实际上只具有相对有限的意义。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哲学之为哲学本身的标准,只要你确定自己思考的就是哲学的普遍性问题,那么,你究竟是用汉语思维,还是英语思维,还是古希腊语思维,这都是次要的问题。如果语言本身是决定哲学之为哲学的东西,那么就不会既有德国哲学,也有中国哲学了。用汉语思维的孔夫子与用古希腊语思维的苏格拉底既然都被承认为世界性的哲学家,就说明,语言只是表达其思想的媒介,而不是决定其思想是否是“哲学”的关键因素。
在口头语体中,因为是面对面交际,修辞语义的表达是通过口耳相传,并在手势、站姿、微笑等态势语以及其他现场语境因素的帮助下来完成的,所以有许多语言成分就会被省略,或者不出现。多使用口语色彩浓的词语,较少适用书面语色彩浓的词语;停顿较多,多使用短句,较少适用错综复杂的长句;多使用平实规范的常规句,较少使用积极修辞格式。这些都为表达简洁明了的修辞语义提供了基本保障。例如:
康德一方面承认,“普通的世俗伦理智慧”具有它的明显优势:
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就在与一般非哲学思维的区别中来确认其思想的哲学性。苏格拉底遇到一个青年人跟他谈哲学,问曰,什么是美?青年人回答,美就是一朵漂亮的花,一个精美的陶罐,一个长相美丽的人时,这显然不是“做哲学”,因为这种回答完全不合苏格拉底的哲学观,而只有当一个青年人被引导超出这些“美的物器”去寻求“美本身”的概念或理念时,他的思考才被带向了“做哲学”。因此,对于苏格拉底而言,“做哲学”就是寻求事物本身的理念,即超越于具体事物的实在形象去把握其一般的“相”。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各门科学开始了分门别类地研究,具有了一般科学(知识)概念,于是“做哲学”就是从它与具体科学(知识)的区别中寻求自身的规定性。亚里士多德说,所谓一般科学(知识)就是关于原因的知识,那么,哲学就不是知道事物一般的原因,而是关于“第一因”的知识,于是,追寻事物第一因的知识成就了哲学之为哲学的门槛,只有寻求事物“第一因”的思想,才能被称之为哲学。“显然,我们应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明知道了这事物。”[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页。“我们正在寻求这门知识,我们必须研究‘智慧’(索菲亚)是那一类原因与原理的知识。……谁能更擅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次之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智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
因为人类理性在道德的事情方面,甚至凭借最普通的知性(Verstand)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高度的正确性和详尽性。[注]甚至在这方面几乎比哲学家本人还更有把握,因为一个哲学家除了拥有普通知性的原则之外,毕竟没有其他的原则,但他的判断倒是容易为一大堆题外的不相干的考虑所缠绕,使之偏离正确方向。[注]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in: Kantsgesammelte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IV, S.391; S.404.
麋鹿小姐紧了紧怀中的酒,仿佛这是她唯一的依靠。红色的围巾让这个圣诞节的夜晚显得更有气氛。出租车里的温度很暖,她陷入了回忆中。记得酒刀先生曾对她讲:“温度过高会使葡萄酒成熟速度太快,变得没那么细腻,还缩短了葡萄酒寿命。温度太低又会让葡萄酒成熟非常缓慢,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她总觉得,酒刀先生说的不止是葡萄酒,还有感情。
在这样的规定下,“做哲学”或者说“哲学之思”是一项最具有普遍性的“思”,它虽然也从思一个具体事物、具体对象入手,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思而超然物外,思入物之为物的物性及其世界,及其“是其所是”的因果关系。因而,是通过一种哲学之思而介入到事物本身的内在生命及其世界。它拒绝对一个事物作外部反思,从而把“主观的思”概括为事物“客观的”本质。“做哲学”就是通过它的思,让物作为物、让存在作为存在“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这样的“哲学之思”不是哪国人、哪个民族的专利,而是人类普遍的“哲思”。
《管子·牧民》中提出“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也就是这样的“普遍”哲思。管子在他实际的治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了,“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的道理。在哲学作为普遍的原因性知识,即第一原因的知识这一点上,虽然中国哲学上没有类似的规定,但“哲学”作为普遍的知识,超越于“见闻知识”,是事物本身之本性的原理,探求“原理”的知识,才是哲学之知的特色,这一点中外哲学之为哲学,应该是一样的。否则,孔夫子不会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样的话,“本”与“道”都是世界的本原性的,即第一性的原理。
于是“哲学”的“哲学性”是以其普遍性,即事物本身的“世界性”为其门槛的,把它降低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或完全“殊相”的知识,如果不是对它的羞辱的话,就必定要承认这种“殊相”知识尚入不了哲学之门。因此,除非在纳粹这样的极权统治下,才会提出“做德意志物理学”这样荒唐的要求,否则没有人会把“科学”挂上一个“国名”,以示其伟大。即便“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最高峰,而当我们说黑格尔是普鲁士(德国)“官方哲学家”时,那是对他哲学的极大贬低而绝非有一丝的褒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会在某种情况下,依然会说有古希腊哲学、古罗马哲学、德国哲学、法国哲学、美国哲学、中国哲学呢?
1.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枫桥经验”是群众工作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集中体现。50年来,“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党政动手、依靠群众”这条生命线,从最早的依靠和发动群众改造“四类分子”,到后来维护农村治安,再到预防化解矛盾,直到现在以群众工作统领社会治理创新,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事实证明,“枫桥经验”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因此,“做中国哲学”这样的说法本身,要“做出中国特色”,脱离哲学史的叙述,根本就做不出来,因为只有在哲学史的叙述中,中国之为中国的“地方特色”才能体现出来。而这根本上与维特根斯坦式的“做哲学”是相反的。而做伦理学与做哲学有一点非常不同,因为“伦理”本身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所以一定是与“国家”相联系的。但“做哲学”,当我们强调它是绝对原创性的思想活动时,鉴于其普遍性要求,一定是超地域、超国家性的。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说自己在“做哲学”时,就不会与“国家”相连,而是与“做形而上学”“做知识论”“做伦理学”等等“哲学”的“分支”相连,因为这样才是从内涵上言说你要做的东西。
更形象一点,在超市里结账时你会选择哪个收银台,这是计算思维中的多服务器模型;当你做饭时怎么安排食物操作的优先顺序,这是计算思维中的在线算法;当你想要找到丢失的物件时会选择原路返回,这是计算思维中回溯的方法;当你今天需要去某个场合时,你会在出门前准备好需要的各类物品,这便是计算思维中的预取和缓冲。因此,计算机思维其实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建立科学的思维模型,从而更高效高质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柏拉图说,我要做“雅典哲学”,孔夫子说,我要“做鲁国哲学”,黑格尔说,我要“做普鲁士哲学”,不仅完全荒谬,而且不可理喻。在此情况下,我们如何理解“做中国哲学”、“做中国伦理学”这样的提法本身呢?
“做哲学”绝对是一种个体性事件,“做”的主体是个人,所做之事——哲学——却是普遍的,无国别、无地域性,只能通向事物本身,思考物之物性、人之人性,领悟宇宙之道、万物之理,因而做出来的“哲学”也只以其“哲学性”本身确认自身的思想价值。
但是,做哲学的人,这个个人是有国籍的、是以其国所通用的语言进行思考的,因此其思想成果是以某种语言来表述的,因而带有这种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民族、国家、时代的文化、价值和情感,因此,我们是以总体的、语言的角度来言说某一时代、某一国家的哲学。所以,当我们注重“哲学”时,基本上是不管这个哲学家究竟是哪国人,究竟是当初是用什么语言表达其思想,我们是把它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来学习和研究的。而当我们注重国别哲学时,我们注重的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历史和地方性经验。
追问哲学的本质之所以困难重重,并不是因为人自身的不足,而是事情本身的缘故。……哲学似乎只有通过追问其本质,才能建构。如果哲学不打算追溯它所寻找的特定形态的哲学本质的学术内涵,亦即不打算追溯某种具体的哲学原理或某个所谓的哲学“体系”,那么它就无法得到类似本质的一切。但这样一来,似乎就陷入了循环,因为要想确定这种学术内涵是否是哲学意义上的学术内涵——不只是搞清它是否真实,是否经得起批判,前提是必须断定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的对象。[注][德]马克斯·舍勒:《哲学与世界观》,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左小龙的脑海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挑战者号”。但他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好像被谁用过,思前想后,出来的都是一些不能让自己满意的名字,诸如“大西洋”,不行,这个就像一个国产摩托的牌子,“所向披靡“也不好,这个“靡”字他不知道怎么写,“暗夜之星”也不好,感觉它是锦江之星的兄弟。
当我们是在“做哲学”,即在思考普遍的哲学问题时,我们既可以参考中国哲学的中国文化和经验,也可以参考古希腊哲学的希腊文化和经验,而且与国籍的关系不大,因为在世界文化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语言可以沟通、相互交流如此频繁的时代,一切思想,都不是单一文明封闭思考的成果,必定是在相同问题背景下相互沟通和融合的一种产物。所以,在同一个国家,做哲学的人,可以是借助于中国哲学资源来做,也可以借助于古希腊的、罗马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等等资源来做。这样一来,做中国哲学,不仅仅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在做,美国人、德国人都可能在做。进而言之,只要我是在中国“做哲学”,哪怕是做美国哲学、德国哲学、希腊哲学,最终都是在“做中国哲学”,因为这些哲学成果,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取自于“西方”的“佛经”,今天不都成为“国学”的“典籍”了吗?世界文化在中国化时,中国文化也在世界化,因而,“哲学”的世界性最终趋向于将地方性的哲学带向人类的普遍性方向上,也在此意义上,世界性的哲学也将被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可见,“做中国哲学”这一提法本身所担忧或反抗的,乃是“述而不作”的“哲学史叙事”,即在历史性的知识叙述中迷失普遍的哲学之思。因此,它是一种从超越历史性、地域性知识叙述而向真正哲学性提升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身不是反抗哲学的世界性,相反却是走向世界性。唯其如此,“做中国哲学”才是正当性的吁求。
二伦理的世俗性与存在家园的本原性
“做中国伦理学”这一要求比“做中国哲学”之要求,更加容易理解,其正当性也更加充分。因为伦理学虽然是哲学,但它作为实践哲学,不是完全思辨的,作为实践的知识,它有其地域性即国家特色。完全思辨的东西,或纯粹形式的学问,如同逻辑学那样,是可以以其完全的普遍性要求忽视其地域性思维的差异的,但伦理学确实不一样,其所研究的伦理本身,常常被理解为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习俗”或“礼俗”之物,而“习俗”或“礼俗”总是与国家、民族、时代相连的东西。这样说来,“做中国伦理学”似乎是个不言而喻正当合理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一般通俗化的话语中而是在“哲学”意义上来讨论伦理学,事情却并不如此简单。哪怕我们把伦理学简单地看作是研究伦理或道德的哲学,那它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描述”一国一地的伦理或道德,作为哲学,它总离不开在描述一国一地的伦理或道德基础上,探求一国一地的伦理所具有的“伦理性”何在,一时一地的“道德”所具有的“道德性”何在?因此,只要我们涉及伦理的伦理性,道德的道德性,这就上升到了一个纯思的领域,就不能单纯地以一时一地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或依据,而是为此寻找某种绝对的标准或依据了。
如此一来,“做中国伦理学”与“做中国哲学”一样,要面对“哲学性”的拷问,只有保证你所“做”的是在哲学的门槛内,所谓“中国”这个地域性定语才是有意义的。当然,要保证你所面对的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不过,“做中国伦理学”与“做中国哲学”所不同的在于,由于“哲学”的“哲学性”只有一个普遍性的标准和尺度,但“伦理”却可以有“世俗”与“纯粹”、“相对”与“绝对”之分,因此,伦理学也就有“世俗伦理智慧”和“纯粹伦理学术”之分。世俗伦理智慧一般是阐明“相对伦理关系”的处世规则,如夫妇、兄弟、朋友关系,我愿意如何对你友善,同时也期待你如何对我友善;你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与尊重,你同时也必须承认和尊重他人。因此,处理这种伦理关系的学问被称之为“世俗伦理智慧”,“幸福生活之指南”。但伦理学除此之外,还有处理“纯粹伦理学术”的,它要阐明的是一种“绝对的伦理关系”,如父子关系、个人与民族关系。儿女不能视父母如何对待他们来采取一种相应的伦理态度或准则对待父母,个人和民族、国家也一样,具有一种绝对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是“先天的”、“绝对的”。所以,真正的哲学家或道德哲学家,当他们说“做伦理学”时,指的是做这种伦理学,只有做这种伦理学,才能超越于一时一地、一国一邦的习俗伦理而能在真正的哲学层面阐明,伦理的伦理性和道德的道德性。
做这样的伦理学就与做哲学处在同样的水平上,所以真正的哲学家都是这种意义上的伦理学家,因此他们都认同柏拉图的如下判断:“习俗之中无哲学。”[注]《理想国》,第10卷:619c-d;同时参见《斐多》,82b-c。因此对于我们如此深深陷入对传统习俗之迷恋中的国人而言,在我们决定要做中国伦理学时,无论是在理论资源还是方法论的思考中,都必须参考大哲学家们对待这两种伦理学的态度。在这里,限于篇幅,只能以康德和海德格尔为例。
但当人试图提供绝对没有任何前提的关于哲学本性的判断时,为了验证自身的正确性,又不得不以哲学史、即已被确认为哲学家的哲学观为前提。所以,想要在哲学史的“叙述”之外“做哲学”,几乎总是陷入一种单纯主观的“自信”,而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以这种“自信”在与“非哲学”的对抗中,确认其思想的哲学性门槛。
三相并网逆变器的MPDPC策略如图3所示,不同的电压矢量产生不同的有功和无功功率变化,因此,存在多种方式去选择合适的开关状态去控制有功和无功功率。采样三相电网电压和电流,分别在8个矢量的作用下计算出下一周期的功率预测值,将预测值代入式(9),根据误差最小化原则,选取最优矢量。p*由直流电压外环PI调节器的输出与直流电压的乘积给定,q*通常设为0,以实现单位功率因数运行。
这些就是我们关于智慧和哲人的诠释。这样,博学的特征必须属之具备最高级普遍知识的人;因为如有一物不明,就不能说是普遍。而最普遍的就是人类所最难知的;因为它们离感觉最远。最精确的学术是那些特重基本原理的学术。[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页。
坚定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四个自信”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出发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13]“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13]树立和坚定人民自信,就是要坚定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这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客观需要,是新时代党的一项战略任务。
尽管如此,康德另一方面依然坚持真正的伦理学必须完成三个过渡:“从普通的伦理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伦理理性知识”,“从通俗的伦理处世智慧过渡到伦理形而上学”,“从伦理形而上学进展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世俗的习俗伦理上,那么就根本不可能从那种先天的绝对伦理之本源来确立我们理性中的实践原理,而世俗的精明的伦理本身,只要缺失了正确评价它们的那个先天原理和至高标准,就必然地总是会遭到各种各样的败坏。
交流式也叫互动式,目的就是为了在体育课堂尾声还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般以小组为单位,学生相互之间启发,谈个人的收获、感想,说说自己对教材的重点、难点、疑点的把握;说说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一起研讨练习的经验。通常这样的交流式,氛围轻松,学生无拘无束,自主性较强,是小学高年级学生比较乐意接受的形式。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他的《存在与时间》明显地具有伦理学意向,而且被认为是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回应[注]参见[意]弗朗柯·伏尔皮:《〈存在与时间〉——〈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改写?》,王宏健译,载于《清华西方哲学研究》第三卷第二期(2017年冬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尤其是文章“四、五”部分,分析“《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为人生存在论:对实践的聚焦和存在论化”,以及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作为人生实存论的分析,第155—172页。,但他始终拒斥“做伦理学”,原因在于,在他眼中,伦理学无非就是“处世智慧”,就是想“提供出一种幸福生活指南”[注][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页。,却根本不去思想“存在的真相”,甚至拒绝和阻止这种思想。所以,当有学生写信问他究竟何时写出一本伦理学著作时,他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申明哲学最为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事,是去思“存在之真相”,同时说“守护存在的家园”就是“本源的伦理学”:
假如现在要合乎(伦理)这个词的本义(Grundbedeutung)来述说伦理学之名称,这就是说,它思人类之居住,那么这里的所思,把作为人类乾元之始的存在之真相作为一种绽出实存(eksisstierenden)来思,本身就已经是‘本原伦理学’(die ursprüngliche Ethik Ethik)了。[注]Martin Heidegger: ÜberdenHumanismus,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1. Auflage 2010, S.48.
之所以能得出这一结论,一方面海德格尔回到了(伦理)的本义:住所、家园;另一方面把“存在”(Sein)阐释为“实存”,把“实存”阐释为“在场”,把“在场”阐释为“居住”。他甚至考察出古德语“存在”,“是”(ist)的含义就是“居住”,“我是什么”,从“我居住在哪里”、“家在哪里”来认定。这样一来,他就完全把近代以来回答“我应该做什么”的关于行为道德的规范伦理学,从属于回答“如何守护存在之真相”这一居住之家园的本原伦理学,而且认为,只有这种本原伦理学才能守护人的“本真存在”。这一“本真存在”之所,才是人类真正的存在家园。
这确实出现了需要分析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可以说有地方性的哲学,它们可以被冠以“国名”来称呼,因为确实有“中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美国哲学”如此等等,但是,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当把“哲学”归于某个“国家”来言说时,并非是就其“哲学”的内涵而言,而是就某种哲学承载的文化信号而言的。我们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说康德和黑格尔是德国哲学时,指的是这样一些非哲学的外部特征:其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属于古希腊人,康德和黑格尔属于德国人;其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用古希腊语思考与写作,康德和黑格尔是用德语来思考和写作。但是,当我们说“做希腊哲学”,“做德国哲学”时,则是另一回事。我不是希腊人,不用古希腊语,也可以说“我做古希腊哲学”,一个德国人、美国人,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可能不懂古汉语,但他们借助于翻译为英文的中国典籍,研究中国哲学,也完全可以说是在“做中国哲学”。所以,当我们说“做哪一个国家的哲学”时,只是一些非哲学的外部特征决定的,指的是“一般的研究”,而且必须依赖于“哲学史的叙述”。脱离了哲学史的叙述,我们很难说是“做一个国家的哲学”。
中国伦理学历来重视家庭,以家庭为核心,返回到这一本原伦理学,无疑要受到我们中国伦理学的重视,虽然在他这里是“无家庭的”“家园”。但存在之家,存在的正当性,只要我们做伦理学,只要我们要为世俗的伦理求索本原的、绝对的伦理性标准或道义,就不得不回到这个“根本”。
三伦理本位的哲学如何能证成伦理学之为第一哲学?
对于西方哲学而言,按照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学科分类,只有以追寻万事万物“第一因”知识的“理论哲学”(纯粹思辨哲学)才是“第一哲学”,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一直未能占有第一哲学之尊位。虽然在希腊化罗马时期,理论哲学已经被伦理学所取代,但没有哪个哲学家能在理论上推翻亚里士多德将第一哲学赋予理论哲学这一定位。虽然近代以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是从其实体论形而上学中推导出伦理学,但依然没有证明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哪怕就是海德格尔提出了“本原伦理学”概念,但他的本原伦理学既非一般的伦理学,也非一般的存在论,“基础存在论”才是他的第一哲学,使得列维纳斯强烈批评他的“此在存在论”具有“存在的暴力”(Tyrannei des Sein)。
之所以说海德格尔的“此在之存在”是一种“存在的暴力”,原因就在于,他把本来并不具有“优先地位”的“向来属我”的“此在之存在”论证为具有绝对“优先地位”的东西:“同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此在具有几层优先地位。第一层是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这种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是通过生存得到规定的。第二层是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由于以生存为其规定性,故就它本身而言就是‘存在论的’。……因而此在的第三层优先地位就在于它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层次上[ontisch-ontologisch]都得以可能的条件。于是此在就摆明它是先于其他一切存在者而从存在论上首须问及的东西了”[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7—18页。。通过这一论证,海德格尔确立了“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 。
但是,列维纳斯恰恰在这里,看出了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暴力”性质:“存在论并不是与他者本身的关系,而是把他者还原为同一。……并不是与他者和平相处,而是对他者的消灭或占有。……作为第一哲学的存在论,是一种强权哲学。”“强权哲学,存在论,作为并不质疑同一的第一哲学,它是一种非正义的哲学。……海德格尔的这种存在论仍处于对匿名者的服从中,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另外一种强权,导致帝国主义式的统治,导致专制。”
列维纳斯的意思是说,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并没有首先证明,你存在“在此”为何是“正当的”,是否没有对他者“侵犯”,你就“先行”存在于此了。“存在”首先具有一种“伦理关系”,此在在世生存,就是与他者的存在论关系,它先于此在对其自身“存在”的“操心”。因此,如果要证明“此在之存在”是正当的,你就得首先证明,我“居住在此”并未造成对“他者”居所的侵占,给出“我”居住在此的正当理由,这样才能克服此在之存在的“专横跋扈”。就此而言,我与他人的关系逻辑上先于“此在之存在”,我们不得不首先考虑我们可能一直未曾谋面的他人的面容(脸)。所以,我的此在之存在与他人先天具有的伦理关系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而是相反,“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这种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其首要课题,不是道德的规范,而是为“存在之正义”(应该存在)作辩护:
存在的危机,并不是由于这个动词的意义可能仍需要在其语义学的秘密中加以理解,仍要求助于存在论,而是因为我已经在质问自己:是否我的存在的正当性得到了辩护?是否我的Dasein(此在)之Da(此)并非已经是对某人的位置的侵占?
……
无论他人是否凝视着我,他都与我有关。正是在这种质疑中,存在与生命被向着人唤醒。因此存在意义的问题——就不是对这个非同寻常的动词进行理解的存在论,而是关于存在之正义的伦理学。不是:为什么有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如何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这才是最高的问题或哲学的问题。[注][法]列维纳斯:《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朱刚译,载于邓安庆主编:《当代哲学经典》,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0—351页。
当然,列维纳斯的这种最高的哲学问题之界定,第一次彻底翻转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但是,将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要能让人真正接受,依然困难重重。因为西方根深蒂固的科学-逻辑优先的思维方式,不会承认康德、费希特发现的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正如舍勒所承认的,要承认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一种道德立场”[注][德]马克斯·舍勒:《哲学与世界观》,第30页。,即要承认人的存在关系要比非人的物理世界的存在关系具有优先地位。
可是,在西方哲学中是很难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人类中心论”越到现代越受到质疑和批判。但是,这对于把存在的意义问题作为哲学之本质问题或核心问题的西方哲学而言,确实又是不得不承认的立场。西方哲学正是在这里走入了死胡同。
然而,道德立场有限,伦理本位优先,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哲学的特色与长项。中国哲学向来没有逻各斯中心论传统,纯粹思辨的哲学一直不发达,更没有雄踞第一哲学之宝座,相反,却正是“伦理本位”的哲学一统天下。因此,在强调“做中国伦理学”的呼声之下,如果能利用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合理地证成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那么不仅回应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是把纯粹思辨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或哲学的本质所造成的),而且回应了“做中国哲学”的质疑,因为正是通过证明伦理学之为第一哲学,使得中国哲学这一地方性知识成功具有了国际性、普遍性,成为一种人类哲学的遗产。
【作者简介】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20043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2ZD122)。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2
(责任编辑付长珍王成峰)
标签:哲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中国论文; 伦理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2ZD122)论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