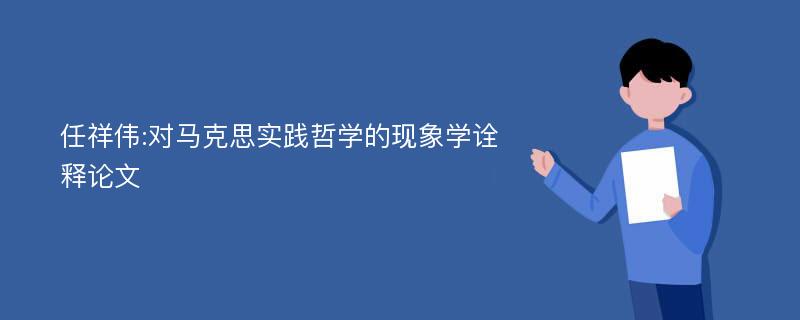
摘 要:马克思实践哲学呈现出浓厚的现象学意蕴,其表现为:在方法原则上,马克思实践哲学展现出“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在人学维度上,马克思实践哲学表现为“此在”式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在形式内容上,马克思实践哲学呈现出现象学内在的“超越性”。这种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象学诠释,一方面,以实践现象学的视角去蔽归澄,合理地诠释了存在问题,走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桎梏,并找到了通向存在澄明之境的智慧之路;另一方面,以实践现象学的视角关注现实,在对象化、具体化的实践活动中人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展现,并在实践中追寻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之路。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哲学;现象学;实践;“面向事物本身”;此在;超越性
在当今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解读日益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由于不同学者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针对马克思的现象学思想,邓晓芒教授将马克思的现象学称为唯物主义性质的“人学现象学”[1](P93),韩庆祥教授和邹诗鹏教授将马克思的现象学方法称作“一种典型的感性的现象学方法”[2](P188),张异宾教授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称为“历史现象学”[3](P20)。然而,从人学、历史和感性等维度出发是否能够做到整体性、涵盖性和周全性的哲学理解,特别是这些概念能否成为理解马克思现象学思想的前提,这是值得怀疑的。相比于马克思哲学的人学、感性或历史等现象学的提法,笔者认为,何中华教授提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4](P1)更为贴切,或者毋宁说这就是实践现象学。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管窥其现象学思想,是符合马克思哲学整体要求的。原因在于:其一,实践范畴具有非常强的理论统摄力,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马克思哲学之中;其二,马克思总是将实践作为存在理解的前提或基础,所以,把实践作为研究的阿基米德点,用实践哲学来诠释马克思的现象学思想是比较恰当的。因此,笔者试图进一步挖掘、表征和确证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象学维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项工作也强化了现象学和马克思实践哲学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
参考时钟的频偏会引入额外的载波多普勒,使得初始搜索在错误的多普勒单元,延长搜索时间;同时还会导致下变频时引起较大频差,导致中心频率两边带内有用信号成分被滤波器滤除,引起载噪比的损失。因此必须保证参考时钟稳定度[19-20]。
一 “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
胡塞尔努力将现象学建构成一个真正探究“本原”的“严格科学”。在《观念》中,他表明了一种“回到事物本身”(zuden sachen selbst)的现象学方法:“每一种原初地给予的直观是认识的正当的源泉,一切在直觉中原初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活生生的呈现中)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都应干脆地接受为自身呈现的东西,而这仅仅是就在它自身呈现的范围内而言。”[5](P316)此后,海德格尔指出:“回到事物本身”就是“让人从显现的对象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6](P41)。由此可见,不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他们所秉持的“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表明,要根据事情自身所显现的方式去说明和认识事物,这俨然和传统哲学所采用的逻辑推论的手段迥然不同。
“回到事物本身”的“事物”并非指现实世界中具有特殊质料、形式和状态的物理存在物,而是胡塞尔意义上的最原初的“直接的给予”或“纯粹现象”。胡塞尔立足“当下”,秉持一种现象学认识论的思路,强调事物本身与先验意向意识的相关性。首先,所谓“现象”是“自明”的,其以事物自身为出发点并展现出自身的全部,让“现象”到场的途径是直观和对理想本质的直觉展示。为确保“回到事物本身”,胡塞尔的方法是进行中止判断,即将相关认识对象和事物的“存在”置于括号内存而不论,继而我们的意识不断地对个别的直观性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清晰地呈现出其共相。海德格尔则注重“未来”,主张一种现象学本体论的路径,强调事物本身与此在的生存性相关联,从而具有本体论阐释学的特色。其次,所谓“现象”是“显现”的。该观点认为,现象只能间接的显现,而并不能直接被把握。与此同时,在显现过程中存在本身被遗忘和遮蔽了,现象学方法就是用来探寻被世俗所隐藏和神秘化的存在领域,以此走向存在的澄明之境。海德格尔让“现象”到场的方法途径是借助语词对复杂语境的解释学理解。对此,哈贝马斯指出:“海德格尔就为一种突出的真理概念作好了准备,并把本质直观现象学的方法论意义转化为它的对立面——生存论意义上的解释学。”[7](P167-168)
那么,马克思有无类似的现象学方法呢?马克思指出:“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8](P76)这就是说,马克思不仅要追根溯源,而且要正本清源,即通过把复杂问题还原为“事物本身”,以此达到对历史的本真性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段论述中,马克思通过其实践理论完成了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很快就没有了。”[8](P77)对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的抽身旁观式的“感性直观”并不能正确认识感性世界和人类历史,这是因为实践构成了现存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原始基础和最初动力,即使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能力也要奠基在实践之上。因此,毋宁说,马克思“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就是回到“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批判唯心主义时,马克思也表现出类似的现象学方法:“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它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8](P73)抽象思辨的意识形态充其量是“主体的想象活动”,与德国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意识形态都要奠基于人类实践之上。这里再次确证了马克思“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态度,即通过回到实践来实现对德国唯心主义的批判。
一般认为,通过借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内核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由此创建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这是一个十分肤浅而片面的认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毋宁说马克思通过“回到实践”完成了对唯心论和旧唯物论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和超越。旧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往往采取直接的、当下的“感性直观”,把感性对象理解为现成的、被给定的。所以,历史就像“一袋马铃薯”一样,不再是“鲜活的”(生成的)而是“僵死的”(完成的),是已然完成之物的堆砌。唯心主义者则主张抽象的精神或自我意识,历史对他们而言仅仅是被悬置于人的头脑中的想象活动,从而远离了人类的现实生活。在对历史的考察方面,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显现出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是因为,以精神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和以物质为基础的旧唯物主义的基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二者都与人的实践相脱离,历史也因此更加外在化、抽象化和虚无化了。
二 “此在”式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
黑格尔诉诸精神现象学,指出:“现象是生成与毁灭的运动,但生成毁灭的运动自身却并不生成毁灭,它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并构成着现实和真理的生命运动。”[9](P30)黑格尔的现象运动是精神和概念的自我运动。与此不同,马克思则扬弃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诉诸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对此,张异宾教授指出:“马克思是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学现象学进一步深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0](P3)马克思把哲学的基础由思辨的绝对精神转变为人的实践,由此展开了“人的存在的现象学”。马克思哲学实践视阈下的“人的存在”就类似于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
诚然,人的实践要遵循外在的客观规律,但实践却具有内在的超越性。这个超越性表现为实践基础上人的存在的超越性。人表现为一种超越性的实践存在者,通过对自然界的索取和改造,人类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在此基础上,人类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寻求更高的安身立命之本,继而诉诸实践来寻求新的超越。实践具有内在的超越性,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内在的超越性的辩证法。遵循着内在超越性的辩证法运动,实践者塑造了螺旋上升的人类历史,这里实践之人构成了大写的人,整个历史过程构成了大写的真理。和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超越性相似,实践的人之存在,其超越性是纯形式的规定,而非内容的规定,毋宁说是纯粹可能性的超越本身。超越性不再是抽象的思辨问题和彼岸的神性问题。这种超越性表明了实践的人的存在向未来敞开的无限可能性,并且在实践过程中领会其自身和体认存在的意义。如果说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视域内的超越性还有“超验性”“先验性”等传统哲学观念的影子,那么,马克思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则开辟了本体论的“实践转向”,以此通往现实生活和人类历史的实践之路。
此外,依据对词源学的考察,海德格尔认为:“(现象)意味着:显示自身(显现)。……等于说:显示着自身的东西,显现者,公开者。”[11](P36)因此,“‘现象’一词的意义就可以确定为,就其自身显现自身者,公开者”[11](P36)。可见“现象”一词的主要内涵就是“自身显现自身”,而海德格尔的“此在”就具备这种“自身显现自身”的特质,“此在”的存在是一个过程,“此在”在存在过程中,其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此在”所揭橥的就是一种动态的展现其自身的过程。由此可见,“此在”对“存在”的把握、领会和体认绝非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一种“抽身旁观”式的感性活动,这种认知方式往往是直观的、抽象的和“完成的”,而且应该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参与体认”式的实践活动,这种认知的手段则是实践的、具体的和“生成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1]。基层农技人员队伍是“三农”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长期扎根基层、切实服务“三农”,是培育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台州科技职业学院作为浙江省九大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之一,承担浙江省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任务。基于往年培训中发现有基层农技人员在培训课间流露对自身职业存在倦怠感的情况,而开始关注我省基层农技人员的职业状态,并着手开展调研,探究其真实职业现状、挖掘倦怠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8](P55)马克思的真理观就在于,基于实践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借助其内在的超越性,真正做到对经验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批判、克服和超越,进而塑造着一幅幅生动的人类历史画卷,这就确保了马克思哲学的勃勃生机和无限可能。对此,何中华教授指出:“马克思的真理观所显示出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之内涵,使哲学真正地广义化了。”[4](P11)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就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这种现象学里同样含有了“自身建构自身、自身显现自身”的现象学旨趣和内在超越性的辩证法,只不过这一切不再是哲学家脑海中的玄想,而是奠基于现实的实践。
如果说海德格尔以“此在”为基础建构了生存论的现象学,那么,马克思则借助人的实践构建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马克思专注人的在场性,在实践基础上的“此在”式的人之存在才是马克思所注重的,相反,脱离了人类实践的先于人类历史和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礁的纯粹自然是无意义的。对马克思来说,人们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8](P147)。维柯也指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12](P145)这是因为,历史进程中的人总是实践的人,他们是塑造历史的主人公,而且这些以实践标榜自身的人之存在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建构和显现自身。马克思的人的存在面向的是未来的可能性,人的期望、理解、价值、意义等都在实践中显现,这和海德格尔的“此在”有相近的旨趣。在这里,实践构成马克思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基础,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得以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人的存在的丰富内涵在实践中得到表征和确证。马克思这种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其显现方式就是人自身的切身参与、实际践行和历史生成。
“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方法、“此在”式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及现象学维度的内在“超越性”等都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实践哲学有着浓厚的现象学意蕴,在这里,马克思的实践成为了“真实践”(2)亚里士多德把“实践”概念引入到哲学,但这种“实践”概念一直发展到康德,都没有摆脱伦理实践的视域和范围。到了阿尔都塞则首次提出“真实践”概念,在《保卫马克思》中分别将实践理解为“论实践”“生产实践”和“政治实践”三种实践形态,并将马克思的实践称为“真实践”,当马克思完全确立自己的“真实践”时,黑格尔的哲学话语就自动“沉默”了(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4页)。如果说阿尔都塞是在认识论上提出“真实践”的概念,那么,笔者认为这里毋宁说是在本体论上的“真实践”概念,是有着浓厚的现象学旨趣的“真实践”概念。。不仅如此,马克思的这种“实践现象学”更是展现出重大的理论意义。
三 现象学的内在“超越性”
和现象学家们的超越性旨趣相同,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存在也呈现出一种现象学视阈内的超越性。应该说,马克思的这种“超越性”得益于对黑格尔真理观念和辩证法思想的吸收。黑格尔指出:“真理不是一个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9](P25)也就是说,真理绝非是处在现成的或完成的状态,而是处于时刻变化的生成性的状态。其实质就在于,“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运动”[9](P11)。在这里,黑格尔的“真理”是按照“自己构成自己、自身显现自身”的现象学模式进行展开、发展和完成自身的完整运动。真理不是静止的、僵死的,而是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这种真理观类似于存在主义哲学的真理观,都是在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提出的,因为只有在本体论的视域内才能把握和理解这样的真理。此外,黑格尔将辩证法视为内在的超越,他说:“人们通常把辩证法看成一种外在的、否定的行动,不属于事情本身。”[16](P38)然而,“辩证法却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并且只有在辩证法里,一般才包含有真实的超出有限,而不只是外在的超出有限”[17](P176)。由此可见,黑格尔把辩证法视为事物本身的内在的超越,只有作为从事物本身出发的内在性超越原则才能超越有限,辩证法内在的超越带动外在的超越和进步,人类历史也随之而螺旋上升。无论是黑格尔的真理观还是辩证法都包含了现象学维度。但是,被表述为“主体”“全体”“过程”的黑格尔的“真理”是用概念来表达的体系,是一种概念的发展过程。同时,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同样是精神和概念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之上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
“超越性”是现象学里的重要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对于“超越性”的理解一般是基于其“意向性”理论之下。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承认自己的理论和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连贯性。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在探讨康德的存在论议题时,指出“意向性”作为生存的一个维度,它只是一种与诸存在者相关的“存在者层次的超越性”(ontic transcendence),它还应该奠基于一种与存在领会相关的“本源的超越性”(primal transcendence)[13](P153),因为对于存在的领会构成了一切意向性本身的可能性条件。海德格尔说:“存在地地道道是transcendens[超越]。此在存在的超越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超越性,因为最激进的个体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就在此在存在的超越性之中,存在这种transcendens的一切展开都是超越的认识。”[11](P36)如果说胡塞尔在意向性中看到本源现象,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则在本源超越性中看到一切存在者层次的超越性的可能性条件[14](P173)。其实,transcendental和ontological几乎可以等同起来,其依据就是海德格尔所阐发的作为“超越性”的“此在”及其“超越性”(1)笔者认为,前期海德格尔似乎想以建构“此在”的“超越性”来撇清与“先验的”或“超验的”等传统观念的关系,但是能否撇得清却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显然,在后期海德格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后期“Kehre”(转向)就是要彻底抛弃“transcendental”。与后期“克服形而上学”不同,《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试图通过一元存在论(metontology)来撇开先验(论)/超越(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以至于有学者称1927年为其“形而上学10年”(参见S.G.Growell.Metaphysics,Metontology,and the End of Being and Time,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60,No.2.Mar.,2000,pp.307-331)。“超越性”并非首先意指主体对于客体的自行相关的活动,毋宁说是“此在”从一个世界出发领会其自身。“此在”以“超越性”为前提和可能性条件,所以,雅斯贝尔斯说:“人在作为可能性存在时,那便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15](P155)。
社会信用体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所有个人、企业或政府的信用状况的总和,社会信用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社会信用体系包含但不限于所列部分)。产品质量信用和企业质量信用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两者均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5-6]。
“此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das in-der-welt-sein),即在世界之中展开其生存活动的动态的人,只有“此在”才能追问“存在”。“此在”是特殊的存在者,即指每刻都在超越自己的人,并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追求着自身的“是其所是”,继而去呈现其生命价值和意义。因此,“此在”总是表现为一种生存论上的可能之在和面向未来的维度。“此在”的本质是通过在世之中“在”(动词性)出来的,而不是事先规定好的,这彰显了“此在”的现象学呈现方式。“此在”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先于其他一切规定性而专注未来的显现和可能性,而不是指现实中已有的具体存在物。“此在”还承担了召唤者的角色,它开启了通向一切其他存在者的窗户。海德格尔认为,只有“此在”才能达成现象学的路标——“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只有通过“此在”才能通达存在的澄明之境和显现事物的本质,具体的方法就是借助“此在”来建构自己的基础本体论。
四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象学诠释之启示
这种在实践视域内对马克思“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解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对“人的存在”的把握由感性直观的传统认识论转变为动态呈现的现象学本体论。“人的存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以往固定的、完成的对象性规定和单纯感性直观的阶段,而应该被视为一种不断超越自身、展现自身、证成自身的实践活动,因而赋予“人的存在”一种无限的、生成的、“活”的意蕴。人的本质、力量、价值等都在实践活动的无限生成和显现中得到表征和确证,这正是一种感性的典型现象学方法。其二,“此在”式的实践者诉诸通向共产主义的现象学呈现之路。在马克思那里,“此在”式的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这样的话,“人的存在”在其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共产主义处在与现存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但是,“此在”式的实践者永远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终极指向的不懈追求,这也正是一种人学本体论的视角。
在马克思这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本体论则被置换为实践现象学,对存在的把握和体认则被放在实践的动态生成和无限敞开中。作为马克思的实践现象学的基础,实践在逻辑上表现为先于主客二分的始源性的整体性范畴,未来人类历史的一切可能性都被包含其内。相反,实践在现实上则展现为某一历史时刻具体的人的经验活动,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因此,实践的这种特性注定了人们无需再执着于去冥想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而是把“存在”与“存在者”在实践的生成和敞开中融合在一起,塑造出此岸世界的以往、现在和将来的人类全部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的遗忘在马克思这里就不成立了,人一直都在动态的实践当中去通向存在的澄明之境,存在及其意义一直都在实践中得到确证和表征,又何来遗忘一说呢。也就是说,对于“存在”的体认和把握要诉诸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要在实践生成的历史中敞显,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在实践中“是其所是”,这是马克思的实践现象学的应有之义。
1.马克思的实践现象学有效地避免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遗忘,在实践中走向存在的澄明之境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没有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18](P4)“存在”不属于传统逻辑发挥作用的领域,而是本体论研究的范围。但是,以往传统哲学的思维方法不仅不能澄明“存在”,而且混淆了存在(being)与存在者(beings)的差别,甚至简单地等同起来,因而导致“存在”被遮蔽,人们一旦谈论存在,存在就已经成为存在者了,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遗忘。传统的经验思维和逻辑论证研究的对象只是“存在者”,而“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个存在者”[18](P6)。因此,这就需要现象学的方法来解释存在本身,海德格尔认为唯独“此在”方可追寻“存在”的意义。
海德格尔一直试图构建一种始源性、超验性的“基础本体论”(或“现象学本体论”),他强调一切经验性的事物都要以这种始源性的东西为根基,并且这个超验性、始源性的基础是不可言说的。但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本体论忽视了这种超验性基础与人的实践生活之间的联系。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的“此在”仍只局限于指代个人,这样的个人不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个人,而是存在论意义上“被抛入世”的个人。海德格尔揭示了“此在”基础上人的烦恼、畏惧和死亡等情绪,认为这是通向存在的办法和途径。可见,存在一直都在个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笼罩下,不能客观地展现存在的本真内涵和意义,海德格尔哲学反而展现出非理性主义、甚至走向神秘主义。后来,海德格尔主张“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只能活在语言的家园中才能“是其所是”。而“此在”不再是核心,而是降身为“存在的看护者”。海德格尔从前期对个人烦恼、畏惧等情绪的研究转向了对“存在”直接昭显的具有本源性的“语言”和“思”,即只有回到人的语言和思想才能具有先于主客分立的始源性而做到对存在的直接呈现和显露,从而去谛听存在的声音。
综上所述,将舒适护理应用在腹腔镜手术的护理工作中,能够有效降低患者在术后发生并发症的情况,同时减少患者住院恢复时间,能够显著提高腹腔镜手术的治疗效果,可被广泛使用[6]。
2.实践构成了人类有待完成的全部历史的可能性和秘密,是真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整体”“大全”和“一”
作为实践现象学的基础,实践的特点就是自我“显现”,实践显现和敞显为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存在。这种自我显现又反过来确证了实践已然成为了始源性的本体论范畴,因为只有这样,这种显现和敞开才是可能的。实践让存在者“出场”“显现”“澄明”“绽放”……,总之让其“在”(动词性)出来。但是,就像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一样,实践作为统摄历史的整体范畴本身确是隐而不显的,呈现给世人的只是具体化、对象化、现实化的实践活动,因此,在这里可称之为“实践的狡计”。总之,实践遵循着“自己展现自己”的现象学逻辑,这不仅印证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象学旨趣,同时也确证了实践成为一个统摄整体的本体论范畴。
海德格尔说:“本体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18](P35),只有诉诸“现象学本体论”的探究模式,人才能澄清被世俗遮蔽的存在及其意义。马克思则诉诸实践现象学,把一切现象还原到实践,存在及其意义则通过实践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显现。毋宁说,实践构成了马克思的现象学路径最原初的起点,是作为现象学的“事物本身”而存在的,在逻辑上是先于主客二元分裂的原初性的本体论范畴,从而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哲学,回归到实践一元论,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实践本身”。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9](P230)在逻辑意义上,实践成为了先于主客二元分裂的原始性的本体论范畴。实践如同一粒种子,主客、心物二分后的种种可能性都将被潜在地包含在实践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在历史意义上,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实践史。换句话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实践由普遍的本体论范畴外化出一切具体的人类活动,由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并且在现实的矛盾道路上自我扬弃、自我超越。这就是实践的“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因此,从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来说,一方面,实践范畴成为了真正本体论意义上统摄全部历史发展的“整体”“大全”和“一”;另一方面,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毋宁说马克思的“实践是存在的家”,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一切存在者都“是其所是”。
根据规范和教科书来看,岩矿石标本电性参数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露头法,二是标本法。露头法测量一般多采用露头小四极法或小极距测深法[2];标本法测量常用的测量方法主要为蜡封法、双盆边架法、标本架法、泥(面)团法[3]。野外生产中多采用标本架法和泥(面)团法。
总而言之,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象学研究可谓意义非凡。然而,邓晓芒教授指出,今天从事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者们正是由于缺乏“现象学的维度”,“最终难免落入旧唯物主义和还原论的窠臼”[20](P13)。相反,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象学考察则强化了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表现为,马克思实践哲学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去探讨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人类关于纯粹哲学、实践哲学及社会哲学提供了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索,即实践的现象学视野,使其在诸多方面具有了与当代哲学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只有当我们真正把握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象学意蕴,马克思哲学体系中一切涉及存在世界的核心阐释不仅都将摆脱传统旧哲学的羁绊,而且还将获得全面的理论深化。当然,要想做好这项工作,还需要现象学和马克思实践哲学之间更深入的交融性研究和更系统的结构性研究、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从而增强马克思的实践现象学研究的理论阐释力。
要想提升企业预算编制结果的合理性,企业应该根据预算编制执行情况,全面落实预算监管和反馈工作,对预算编制执行环节中形成的各个数据进行采集,以此找出预算编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对应的处理对策。此外,企业可以把预算编制结果和职工工作绩效进行结合,从而确保企业各个职工都可以自主的参与到预算编制工作中,在企业职工内部形成良好的监管格局,强化职工自身管理意识,营造规范的预算管理环境,给预算编制和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邓晓芒.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J].江海学刊,1996(3).
[2]韩庆祥,邹诗鹏.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张一兵.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初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2).
[4]何中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之真理观:再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5]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7]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0]张一兵.从精神现象学到人学现象学:析青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1999(1).
[1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2]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3]Heidegger.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M].Heim M,Trans.Indian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1992.
[14]Francoise Dastur.The Ekstatico-horizontal Constitution of Temporality[G]//Christopher Macann.Martin Heidegger:Critical Assessments:Vol.1 London and New York,1992.
[15]考夫曼·W.存在主义[M].陈鼓应,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6]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17]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8]Heidegger·M.Sein und zeit[M].Tue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86.
[19]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0]邓晓芒.马克思论“存在与时间”[J].哲学动态,2000(6).
PhenomenologicalInterpretationsofMarx’sPracticalPhilosophy
REN Xiang-wei
(School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shows strong phenomenological meanings,which are as follows.Firstly,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shows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of “Back to thing itself” in the principle of methodology.Secondly,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manifested as “the phenomenology of human existence” of “Dasein” in the humanistic dimension.Thirdly,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presents the inherent “transcendence” of phenomenology in terms of form and content.These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on the one hand,removes shelte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henomenology,which explains the existing problems reasonably,and is out of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finds a wisdom way to the clarity of being;on the other hand,concentrates on the real lif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henomenology,an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human beings can be displayed in the objectification and concretization of practical activities,and the realistic road to “communism” can be pursued in practice.
Keywords: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phenomenology;practical;“back to thing itself”;dasein;transcendence
收稿日期:2019-04-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1);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项目(2018GF004)。
作者简介:任祥伟(1988-),男,山东滕州人,2016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实践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B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9)05-0014-07
(责任编辑王能昌)
标签:现象学论文; 马克思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论文; 黑格尔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认识论论文; 反映论论文;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1)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项目(2018GF004)论文; 厦门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