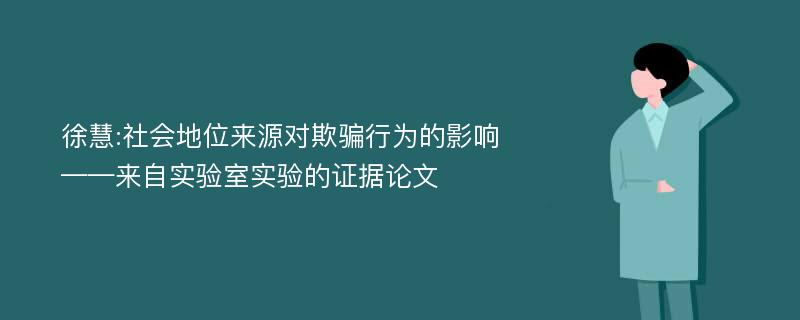
摘要:如何减少欺骗是当前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文章结合社会地位理论和自我概念理论,研究了减少欺骗行为的机制。我们利用实验室实验,区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地位获取方式,用欺骗博弈来检验不同社会地位来源对欺骗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人通过真实劳动获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可以显著减少欺骗行为;由于幸运得到的先赋性社会地位不能减少欺骗行为。同时,非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比赋予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更有效减少欺骗行为,说明物质收益是对市场化自我概念的提醒,从而无助于降低欺骗。研究结果在剔除策略性行为后依然稳健。研究有效验证了Mazar et al.(2008)关于影响欺骗行为的自我概念内在决定机制,并对各类组织提升诚信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欺骗 社会地位 自我概念 实验室实验
一、引言
欺骗行为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社会里(Magnus et al., 2002;Rawwas et al.,2004),例如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事件、1996年日本“住友铜事件”、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等,都与欺诈行为紧密相关。除了在经济、金融领域以外,欺骗在政治领域、学术领域乃至日常生活中都屡见不鲜,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成本(Ederer and Fehr,2007)。
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由于利益驱动,失信、欺骗和造假也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屡禁不止的现象。无论政府部门的贪污腐败、商业领域的财务欺诈,还是医疗与食品行业以及学术领域的造假都对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王小龙,1998;汪昌云、孙艳梅,2010)。在新时期下,国家把诚信建设、减少欺诈也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因此,如何减少欺骗行为,构建一个良好的公平有序的诚信竞争环境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人们在不同环境、不同场景下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欺骗行为,因为个人对自我和环境关系的认知会发生变动(Feravelli, 2014)。但也有研究表明,个人在不同场景下的欺骗行为可能有内在相关性(Dai et al., 2016)。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已从不同角度探究了欺骗行为及其决定机制。Mazar et al.(2008)认为可以将欺骗的决定机制分为外在成本收益(external cost-benefit)以及内在奖励(internal reward)机制。外在成本收益机制主要从物质收益考虑出发,其中以Becker(1968)的经典理论为代表,认为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在诚实行为收益高于欺骗行为收益时才不会欺骗。内在奖励机制认为,除了外在的物质考虑,内在奖励也是个体是否进行欺骗的决定因素,而且可能更重要。与个体价值体系一致的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内在奖励;与个体价值体系相违背的行为会产生负面的内在奖励(Mazar et al.,2008)。当人们开始注意自身的道德标准时,会使得人们减少欺骗。这表明,人们在决定是否进行欺骗的决策时,往往存在两种互相竞争的动机:从欺骗中获得的物质收益以及维持一个积极诚实的自我概念(Aronson 1969; Harris et al., 1976)。
本文中,我们创新地从社会地位角度来验证欺骗行为的内在决定机制。因为社会地位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Frey and Meier, 2004;Eckel and Wilson, 2007; Potters et al., 2005, 2007;Kumru and Vesterlund, 2010;Piff et al., 2012;Gächter et al., 2012;刘凤芹、卢玮静,2013;Chen et al.,2017)。现有研究都肯定社会地位对个体社会偏好(反社会偏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对于影响方向的看法不一致。我们认为,由于社会地位本身有蕴含诸多方面内容,具有截然不同的来源,所以可观察的社会地位与个体行为的关系,可能通过多种决定社会地位的机制共同起作用。基于Mazar et al.(2008)对诚实与内在自我概念维护理论的研究,我们认为以不同方式获取的社会地位会对个体产生不同的关于诚实的自我概念道德标准,从而导致个体维护诚实形象的努力程度差异,最终影响欺骗决定。
本文通过实验室实验,控制了个体社会地位的不同获取方式,区分通过个体努力获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和通过幸运获得的先赋性社会地位,结合欺骗博弈,对以上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不同方式获取的社会地位对个体产生不同的欺骗决定。相比于先赋性方式获得的社会地位,个体以自致性方式获得的社会地位会显著减少不道德的欺骗行为,有效验证了通过努力获得的社会地位可以强化个体公平诚实的自我概念,从而减少欺骗。同时,我们发现与赋予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相比,非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更能有效减少欺骗行为。结果证明,物质收益是对利益最大化自我概念的提醒,从而无助于减少欺骗。
登上古城墙,走一走,望一望,摸一摸墙体,便仿佛触及了宠辱不惊的沉稳豁达,感受到了皇天厚土的苍茫,便有了把酒临风的豪情,体验到了纵横古今的大气,潜移默化地便有了纵览历史的豁达。西安既是一个可以去缅怀汉唐盛世荣耀的城市,更是一个可以排遣眼下烦恼的去处,在西安,似乎没准有资格说“郁闷”。难怪当地人也喜欢到城墙上或城墙边走走,说碰到心烦气躁之事,看到古城墙便能心闲气定。
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文献综述;第三节实验设计和假设;第四节是实验实施和描述性统计;第五节实验结果;第六节稳健性检验;第七节结论。
二、文献综述
2017年12月,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实验室进行了实验。所有被试者都通过学校内外网络平台随机招募,总共380人参与,其中190人在实验中的角色为提议者。其中对照组有48名提议者,实验组1、2、3分别有46、47、49名提议者,每个被试者均只参加其中一场。本次实验使用苏黎世大学开发的z-Tree操作系统(Fischbacher, 2007)。
(一)欺骗的决定机制
欺骗行为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根据Gneezy(2005)的总结,我们将欺骗行为分为四种类型:1.“善意的谎言”(White lies);2.损己利人型欺骗;3.损人损己型欺骗;4.损人利己型欺骗。在本研究中,我们只关注第四类欺骗,即损人利己型的欺骗行为。这类谎言也被称为“黑色谎言”(Black lies)(Erat and Gneezy, 2012),与“善意的谎言”相对。这是在很多经济事件里可以见到的不道德欺骗现象。比如在现实生活中,出租车司机给乘客提供错误的路线信息从而收取更高的价格;销售人员对销售产品问题的隐瞒,从而使得顾客利益受损等。这一类型的欺骗行为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福利损失,因此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大量实验经济学文献对该问题进行研究(Gneezy, 2005; Snchez-Pagés and Vorsatz, 2007; Dreber and Johannesson, 2008; Hurkens and Kartik, 2009;Sutter, 2009;Erat, 2013; Gneezy et al., 2013; Lightle, 2013)。此外,Konrad(2017)最新的实验研究还发现,决策中的时间压力对于欺骗行为有影响。他们发现,个人有更多时间用于思考决策时,欺骗率就有所提高。这个发现表明,欺骗行为可能受到包括时间在内的多种不同机制的相互作用。
Gneezy(2005)的欺骗博弈实验,也叫提议者接受者博弈(sender-receiver game),通过设定不同收益,研究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的欺骗行为。他发现,人们在决定是否欺骗时,不仅依据自己能从欺骗中获利多少,也会考虑受欺骗方需要承担的损失大小。当自己的获益不变,但欺骗会加大对方的损失的时候,个体会倾向于降低欺骗率;但当欺骗能使自己的获益大幅增加时,个体又会增加欺骗率。后续的实验研究发现,欺骗行为与性别有关(Dreber and Johanneson, 2008),与被试的专业有关,甚至与宗教因素相关(Childs, 2012)。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欺骗行为与当地的腐败程度有关(Innes and Mitra, 2013),与提议者与接受者是否可以面对面看见有关(Holm and Kawagoe, 2010; Van Zant and Kray, 2014),是否伴随发送一些私人化的信息有关(Cappelen et al., 2013)。同时,Gneezy(2005)的实验证明,人们普遍存在欺骗厌恶。欺骗厌恶在人群中的普遍性也被其他后续研究所证实(Gneezy et al., 2013; Glatzle-Rutzler and Lergetporer, 2015)。
欺骗行为研究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表现诚实,而有的人不是。Sakamoto et al.(2013)认为,个人在欺骗与诚实行为之间进行决策时,三个维度的因素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一,是否可将欺骗行为正当化;第二,从欺骗行为中获得的收益;第三,诚实行为对于个人效用的影响。经典的外在成本收益理论认为,欺骗是通过比较预期外在收益和成本的有意识行为(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在诚实行为的收益高于欺骗行为的收益时,才不会欺骗。因此个体会在两种情况下选择诚实策略。第一,个人从欺骗行为中获得的物质利益较少;第二,当欺骗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增加并且接受惩罚的代价提高。基于这个结论,政策制定者往往从制定更严格惩罚措施出发,增加欺骗需要付出代价,提升社会总体诚信(Somanathan and Rubin, 2004)。但是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被发觉可能性较低或潜在惩罚程度较轻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选择诚实策略(Lewis et al., 2012)。有研究显示,即使在一个完全匿名,且完全不可能被发觉欺骗的环境下,从始至终保持欺骗也是罕见的(Pascual-Ezama et al., 2013)。同时,外在机制经典模型也无法解释,当个人可能因为不诚实而丧失最大化的金钱收益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多人选择不诚实(Mazar et al., 2008)。
Mazar et al.(2008)给出了解释欺骗行为的另一种内在机制,即自我概念维护理论。他们发现,当个体对道德标准的注意增加时候,个体的诚实度就会增加。他们据此认为,个体决策除了外在物质考虑以外,欺骗行为还取决于个体内在的价值准则。个体不仅在意外在收益,还会在意内在奖励,因为个体希望维护积极的自我概念。另外还有一些直接证据来源于脑科学研究。有研究发现,当个体行为符合社会准则时,会激发大脑中的奖励中心,获得的收益和个体获得的外在收益如金钱、饮料、喜欢的食物、等一样(Knutson et al., 2001; O’Doherty et al., 2002)。因此,目前学界对道德行为的内在机制尤为关注。
(二)社会地位与道德行为相关研究
根据Weiss and Fershtman(1998)的定义,社会地位是指个体根据特征、资产和行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因此社会地位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可以影响判断决策。社会地位根据获得方式可分为两类:先赋性地位(ascribed status)和自致性地位(achieved status)。这两个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在1936年的经典著作《人的研究》中提出(Linton,1936:115)。先赋性地位是指一个人出生后自然获得的社会地位,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家庭背景等,个人没有选择的自主性。而自致性地位主要与个人所受教育、职业、婚姻状况等因素有关,与个人的主动选择有关。社会学主张,两种主要的社会地位来源,继承和代内流动,分别对应于先赋性地位和自致性地位(张翼,2004)。在封闭型社会或者传统型社会,社会地位主要依靠继承得来。而在开放型社会或现代型社会,社会地位则越来越多地依靠自我努力获得,有效实现代内的社会流动。
从理论角度看,Weber(1922:305)最早提出,社会地位是由两种互相交织的奖励系统而形成:诉诸荣誉的地位情境(status situation)和诉诸金钱的市场情境(market situation)。前者可被看作一种被他人认可的尊重和敬佩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后者可被看作一种在社会关系中拥有非对称资源的“社会权利”(Social power)。正是由于社会地位背后代表着一系列与财富、教育等非对等资源相关的因素,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在进行决策时,无疑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包括欺骗决策行为。然而,从理论上来说,到底社会地位如何作用于个体决策,似乎没有一致的定论。如Kafashan et al.(2014)认为社会地位不仅会对利己的、经济的行为决策造成影响,还会对个人的社会偏好、利他主义行为决策造成影响。但涉及具体的影响方向时,Kafashan et al.(2014)认为社会地位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是否具有积极或消息的影响,取决于个人背景以及具体的亲社会行为类型。
许多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即社会地位是决定个体社会偏好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Frey and Meier, 2004;Eckel and Wilson, 2007;Potters et al., 2005, 2007;Kumru and Vesterlund, 2010;Gächter et al., 2012; Piff et al., 2012)。其中Frey and Meier(2004)的田野研究表明,社会地位的差异和比较,对于社会偏好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后续实验研究都表明,领导者以及高社会地位者对促进合作有积极作用(Potters et al., 2005, 2007; Eckel and Wilson, 2007; Kumru and Vesterlund, 2010; Gächter et al., 2012)。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越有可能进行慈善捐赠,同时也会捐赠更多的数额。Ebeling et al.(2012)及Ebeling et al.(2017)分别用实验室和田野实验方法证明了这个命题。刘凤芹、卢玮静(2013)则利用大样本调查数据开展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捐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Chen et al.(2017)用一个田野实验对中国减少交通违章的政策做了研究。他们发现,在提醒车主过去违规次数的同时,将其它高社会地位车主较低的违规次数作为信息告知被提醒的车主,能有效地改变该车主减少交通违章行为。这意味着高社会地位个体的行为对社会上的其他个体行为具有引导作用。以上研究表明,社会地位一般对减少非道德行为有积极作用。然而,也存在与以上研究结论相反的研究。例如Piff et al.(2010)的研究发现,低社会阶层者与高社会阶层者相比,显得更宽容、更慈善、更信任以及更助人。
迄今为止,仅有少数研究涉及社会地位与欺骗行为之间的关系。Piff et al.(2012)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真实的自然环境还是在实验室场景,高等级个体都会比低等级个体表现出更多的非道德行为,比如欺骗、违规等。他们解释为高等级个体更贪婪,而贪婪会减少自我行为对他人影响的考虑,并诱发更多的非道德行为。Dubois et al.(2015)进一步区分利己或利他环境中的非道德行为。他们发现,高等级者会在利己环境中表现出更多的非道德决策,而低等级者会在利他环境中表现出更多的非道德决策。
(三)金钱激励与社会偏好相关研究
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是指人们除了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外,还关注诸如其他社会福利、相互信任、公平分配、公平动机的偏好。Henrich et al.(2001)著名的跨社会研究证明,社会偏好在各种文明水平的社会中普遍存在,这是一类非常基本而又共通的人类偏好。相互信任正是典型的社会偏好,而欺骗则是反社会偏好的行为。同时,Henrich et al.(2001)的研究也揭示,社会偏好与金钱激励无关。他们实验了各种水平的金钱激励,社会偏好水平并不随金钱激励变化而显著变化。
虽然观众可能乐于接受影片中想象性的救赎之路,但这些自我救赎之路却较为“廉价”,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反讽色彩。毕竟身份认同危机源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稳定感,撇开社会转型而谈论解决之道,无异于沙上建塔。就此而言,中国当代都市电影中“想象性的”自我救赎之路,本身就是身份认同危机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实验背景从无金钱激励变成有金钱激励,社会偏好水平则可能发生变化。Bénabou and Tirole(2006)用模型刻画了个人内在激励与社会偏好之间的关系,给出了研究金钱激励与社会偏好的一般框架。Carpenter and Myers(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担任志愿者、慈善捐赠等利他主义社会偏好行为中引入金钱激励,结果无助于提高社会偏好水平,反而会使之降低。他们认为,在这些场景中,引入金钱激励就改变了个人内在动机,从而挤出了社会偏好。
Mellström and Johannesson(2008)对献血行为的研究,用另一个实例得到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对于献血行为给予金钱奖励,会使得个人转而认为献血行为属于市场行为,而非单纯的利他主义行为。行为动机改变,最终表现为总体上减少献血数量,减少利他主义行为。Gneezy and Rustichini(2000)也认为,道德行为与个人所感知的环境有关。如果所处环境更接近市场,那么个人行为也会更接近市场行为。他们发现设定规则对迟到接孩子的父母进行经济惩罚后,反而出现更多的迟到行为,因为父母对迟到行为的意义的认知发生改变。所以,对社会偏好行为附加物质激励,反而会产生腐蚀作用,最终减少社会偏好行为。
总结以上三方面的文献,大多数研究都认为社会地位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着积极关系,这也反映出高等级社会地位背后内化的道德准则有积极作用。高社会地位者会更积极维护自我概念,表现出更积极的道德行为或亲社会行为。为进一步验证这个理论,本研究中,我们区分了自致性和先赋性这两种不同来源的社会地位。我们认为,以不同方式获取的社会地位会形成不同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标准。通过努力获得的社会地位的个体,会认为它与公平诚实的自我概念相联系,而通过幸运获取的地位的个体可能无法有效建立这样的自我概念。因此,人们为了维护不同的自我概念,在非道德行为上会有不同表现。与此同时,我们也进一步研究有无物质激励以及物质激励作用于不同来源社会地位所导致的欺骗行为差异。现实世界里,不同来源的社会地位往往交织在一起,我们很难利用调查数据区分个体的社会地位的获得方式。而且对于社会地位的衡量,现有研究主要以个体主观汇报或个体客观现实地位来衡量,这些都可能存在偏差。本研究中,我们将通过实验室实验的方法设计获取不同社会地位的机制(先赋性或自致性),结合欺骗博弈实验,研究社会地位的不同获得方式对欺骗行为的影响,从而来检验社会地位的不同来源与维护个体自我概念的关系。
三、实验设计和假设
(一)实验设计
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角色分配,第二阶段为欺骗博弈实验。第二阶段的欺骗博弈实验参考了Gneezy(2005)的欺骗博弈。欺骗博弈实验中,设定了提议者和接受者两种角色。我们在分配角色之前引入真实劳动,或者给予物质奖励,从而凸显提议者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通过第一阶段的角色分配环节,第二阶段欺骗博弈实验的提议者、接受者角色得以确定。依据提议者社会地位获得方式的不同,以及是否有物质奖励,实验分为四组,如表1所示。
在对照组中,实验随机分配提议者,并且告知参与者:“恭喜您!由于随机选择,您成为获胜者!您得到提议者角色。”
在实验组1,所有参与者需要先进行真实劳动,依据真实劳动的结果进行角色分配。真实劳动参考改进了Gill(2012)的经典设计,采用“拖动滑条”的劳动任务。这个任务中,每个人需要在60秒规定时间内将20个滑条拖动到屏幕正中位置。拖动位置为正中时得5分,位置越远离正中则得分越低,20个滑条满分总共为100分。在任务中表现为前50%的参与者获得提议者角色,并被告知:“恭喜您!由于您在拖动滑条的任务中表现出色(战胜了至少50%的参与者),成为获胜者!您得到提议者角色。”
表1实验设计
社会地位的获得方式是否有物质奖励对照组随机产生否实验组1真实劳动否实验组2随机产生是实验组3真实劳动是
在实验组2中,和对照组一样,提议者没有进行真实劳动,而是被随机分配角色。但是被任命为提议者的参与者将会得到8元的物质奖励,并被告知:“恭喜您!通过随机选择,您成为获胜者!您得到提议者角色,并获得8元奖金!”
和实验组1一样,在实验组3,所有参与者首先进行真实劳动,在“拖动滑条”任务中表现为前50%的参与者获得提议者角色。与实验组1不同的是,提议者还能得到8元的物质奖励。他们被告知:“恭喜您!由于您在拖动滑动条的任务中表现出色(战胜了至少50%的参与者),成为获胜者!您得到提议者角色,并获得8元奖金!”
角色分配完毕,接着进行第二阶段的欺骗博弈实验。这部分实验将连续进行六轮,已明确的角色在六轮实验中不会改变,然而每轮匹配的接受者不一定相同,防止提议者采用策略。此外,每轮都会出现两个资金分配方案,方案A和方案B,两者次序会随机打乱,即每轮方案A和B的内容会调换,进一步防止提议者采用策略。
方案A:提议者获得15元,接受者获得10元;
方案B:提议者获得10元,接受者获得15元。
“共享经济”根据其参与共享的主体不同,其商业模式分为以下四种:C2C、B2C、C2B、B2B模式。其中B2C模式是我国当前的主导的商业模式,如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等共享平台等,C2B模式的开发潜能非常巨大,B2B商业模式还处于瓶颈期。
只有提议者知道方案的具体内容。提议者需要将以下两种信息之一提供给接受者:
诸暨市在建设大调解体系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延伸与拓展,也为新时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助力。“枫桥式” 大调解体系建设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有如下几点。
结果表明,真实劳动形成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它所带来的对于欺骗的抑制效应有一定时效性,只反映在紧接着的第一轮决策上。在我们的实验设计中,真实劳动只进行一次,社会地位也只凸显一次。在第二阶段的六轮欺骗决策中,被试者不经过凸显社会地位环节而直接进行决策。随着实验的不断进行,由最初的真实劳动形成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带来的影响减弱。从结果来看,社会地位对欺骗行为的抑制效应只能保持一轮。在接下去的几轮决策中,由于没有凸显社会地位,欺骗率并没有显著降低。该结果与Fershtman and Weiss(1998)认为社会地位带来的社会偏好只能持续短暂时间的观点相一致。
信息1:方案A对你更有利;
信息2:方案B对你更有利。
顺德逢简水乡的商户几乎销售同质的农家菜,如鲮鱼肉饼、均安蒸猪、双皮奶等,存在恶性竞争。由于缺乏相关的餐饮行业规范和认证,仅依靠食品的外观和宣传,游客难以判断食品的质量,只能通过网络点评或随大流在最受欢迎的店铺进行消费,对游客满意度造成严重影响。
这是接受者唯一能获得的信息。接受者将根据提议者提供的信息做出决策,选择方案A或者方案B。每对匹配的参与者在每轮实验中的所得将由接受者选出的方案决定。
在电气工程建设中,会涉及到大量信息和数据,是重要的参考标准,通过认真分析可以了解实际状况。在缺乏数据参考下,施工活动是盲目的,严重缺乏科学性,所以要自觉遵循,对实际情况有全面了解。另外参数对工程标准评估也发挥着有效作用,一定要符合规定要求,不能出现太大的偏差。参数制定要根据工程而定,体现出合理性,可以指导其他工作顺利开展。由于数据类型多、内容复杂,所以要进行有效管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方案。在参考的时候,数据信息和实际情况要相适应,看是否达到规定要求,便于对出现问题及时发现和纠正。
(二)实验假设
我们的假设基于Mazar et al.(2008)的自我概念维护理论。首先我们认为,通过不同方式获取的社会地位会对社会地位的认可方式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维护的作用机制发生在实验的第一阶段结束,到第二阶段决策之间,其作用效果会因为第一阶段社会地位来源的不同而不同。相比于通过幸运获得的先赋性社会地位,通过真实劳动的努力赢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对获得的社会地位更为认可。因此自致性社会地位会激发个体公平诚信的内在道德准则,并强化相应的自我概念。根据内在奖励机制(Mazar et al.,2008),个体必然会去维护内在的道德准则和诚信的自我概念。相反,通过幸运获得的先赋性社会地位由于对地位的认可度较低,无法有效建立公平诚信的道德准则和相应的自我概念,因此维护自我诚实概念的努力较小,欺骗的可能性会增加。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1,
假设1: 与先赋性社会地位相比,自致性社会地位将有效降低欺骗率。
Gneezy and Rustichini(2000)认为,道德行为与个人所感知的环境有关。如果所处环境更接近市场,那么个人行为也会更接近市场行为。Aquino et al.(2009)的研究同样显示,与金钱有联系的环境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为自我利益而去欺骗。以上研究都表明道德行为与场景内容相关。我们认为通过物质奖励引入对社会地位的确认的方式,会激发个体内在的对于市场和利益最大化的自我概念的构建。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
生物质吸附剂来源广泛、价格低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物质吸附剂可代替活性炭用于水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目前,生物质吸附剂的实验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关于农业生物质材料的研究应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提议者的平均收益为41.2元。实验组2和实验组3对于提议者有额外金钱奖励,他们的平均收益较高,分别为44.4和44.0元。在对照组和实验组1中,提议者的平均收益分别为38.9和36.6元。
此外,我们认为只要涉及物质奖励的社会地位,它就会诱导倾向于激发个体内在的对于市场和利益最大化的自我概念的构建,即使在自致性社会地位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因此,赋予物质奖励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可能会抵消个体为维护诚信的自我概念的诚实行为。我们把涉及物质奖励的社会地位所导致的欺骗行为,与不涉及物质奖励的社会地位所导致的欺骗行为相比,提出假设3,
假设3:涉及物质奖励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将不再有效降低欺骗率。
四、实验实施与统计性描述
本研究主要与三类文献相关:一是欺骗这类非道德行为的决定机制;二是社会地位与欺骗的相关研究;三是金钱激励与社会偏好相关研究。
我们问卷调查了被试者的年龄、性别、学历、学校、专业、党员身份。我们还调查了被试者对公平感、信任度、幸福度、收入水平的自我测评,这几个主观测评的变量均为1到7的选择范围。1为最低,7为最高。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
参与实验的190名担任提议者的被试者平均年龄为19岁。专业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被试者一共有49名,占总人数26%。被试者的来源省份比较平均,各个省份的人数占比均不超过9%。有16名被试是党员,占总人数的8%。担任提议者的被试者中有37名男生,153名女生,男生占比19%,女生为81%,这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真实性别比有关。我们在之后的回归检验中控制了性别,发现性别对于实验结果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2描述性统计
变量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观测数年龄(年)19.251.5001726190男性(=1)0.1950.39701190经管专业(=1)0.2580.43901190党员(=1)0.0840.27801190公平感(1-7)4.0531.14017190信任度(1-7)3.6631.09517190幸福度(1-7)4.9741.21917190收入水平(1-7)3.6320.97616190
假设2:赋予物质奖励的先赋性社会地位,将无法有效降低欺骗率。
五、实验结果
实验组2与对照组的被试者都是通过随机分配从而获得提议者角色。与对照组不同,实验组2中的提议者可以得到8元的物质奖励。比较这两组提议者的首轮决策,结果如表4所示。实验组2中有28名提议者选择提供真实的信息给对方,19名提议者选择欺骗,平均欺骗率为40.4%。结果与对照组39.6%的欺骗率相比,略有提高,但不存在显著差异。非参数检验中,单边比例检验的p值为0.550,单边Fisher Exact检验的p值为0.533,均不显著。
(一)自致性与先赋性社会地位
首先比较完全由真实劳动成果决定自致性社会地位提议者与完全由幸运决定的先赋性社会地位提议者的欺骗行为差异。我们观察提议者在真实劳动决定社会地位后的第一轮实验中的行为。
表3显示,实验组1的平均欺骗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对照组和实验组1的非参数检验结果的单边Fisher Exact检验p值为0.049,单边比例检验p值为0.031。对照组和实验组1的提议者都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在紧接着的欺骗博弈中实验组1的欺骗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两者差异由于社会地位的获取方式不同导致。对照组的提议者通过随机分配而获得的社会地位,而实验组1是通过真实劳动、自我努力而获得。后者会激发个体公平诚信的内在道德准则,并强化相应的自我概念。为了维护积极的自我概念,个体必然会减少欺骗。该结果与假设1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1:
1.2 研究方法 手术麻醉生效后,使用染料示踪剂亚甲蓝(江苏济川有限公司)定位前哨淋巴结。取亚甲蓝0.5~1 ml在乳晕周围皮内/皮下或活检后的腺体残腔壁周围皮内/皮下注射,沿蓝染淋巴管探寻蓝染淋巴结,若术中触及其它肿大或质硬可疑受侵淋巴结,一并切除送检,此研究中送检淋巴结任意一枚阳性皆视为SLN有转移。
图1 各组平均欺骗率
结论1:与幸运方式获取的先赋性社会地位相比,通过真实劳动获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将有助于减少欺骗。
表3对照组与实验组1的欺骗率
对照组实验组1FisherPrtest真实2936欺骗1910欺骗率0.3960.217p=0.049∗∗p=0.031∗∗
注:Fisher和Prtest分别代表单边Fisher Exact检验和单边比例检验(备择假设是实验组1的欺骗率小于对照组的欺骗率)。***、**、*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
(二)赋予物质奖励的先赋性社会地位
图1显示,各实验组中欺骗率存在差异。在对照组的48名提议者中,有19位选择了提供信息1即选择欺骗,欺骗率为39.6%(标准差为0.494);在实验组1中,有10名提议者选择了欺骗,欺骗率为21.7%(标准差为0.417);实验组2中有19名提议者选择了欺骗,欺骗率为40.4%(标准差为0.496);在实验组3中,19名提议者选择欺骗,欺骗率为38.8%(标准差为0.492)。各组的平均欺骗率和其95%的置信区间如图1所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具体比较各组之间的差异。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因ACS在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行冠脉介入治疗的患者。入选标准:就诊时年龄≥75岁,能配合手术治疗;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30 mL·min-1·1.73 m-2;无出血。排除标准:合并肿瘤等终末期疾病;无法配合术后规则用药。共入选181例患者,其中男性110例、女性71例,年龄75~89岁。其中,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STEMI )60例,肌钙蛋白I(TNI)阳性116例,急诊冠脉介入治疗44例。患者入院时均进行BI评分。
以上结果表明,赋予物质奖励的社会地位无助于降低提议者的欺骗率,反而比对照组欺骗率更高,尽管差异并不显著。该结果与假设2的方向一致。物质奖励,会激发和引导出个体关于市场与利益的自我概念,促使个体为自我利益最大化而选择欺骗,从而对诚实行为起到反作用。实验组2的欺骗率是对照组和所有实验组中最高的(40.4%),与Gneezy(2005)以及 Sutter(2009)发现的提议者的一般欺骗率一致(36%-44%)。因此我们得出:
表4对照组与实验组2的欺骗率
对照组实验组2FisherPrtest真实2928欺骗1919欺骗率0.3960.404p=0.550p=0.533
注:Fisher和Prtest分别代表单边Fisher Exact检验和单边比例检验(备择假设是实验组2的欺骗率大于对照组的欺骗率)。***、**、*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
结论2:赋予物质奖励的先赋性社会地位,无助于降低欺骗率。
(三)赋予物质奖励的自致性社会地位
实验组1和实验组3的被试者在进行欺骗博弈实验之前都进行了真实劳动,拥有获胜者称号的提议者是通过在真实劳动中获胜而得到身份。这两组的不同之处在于,实验组3的提议者不仅拥有获胜者称号,而且得到8元的奖金。被试者在实验组3中不仅通过努力获得了社会地位,同时也获得了对社会地位肯定的物质奖励。我们比较两个实验组在欺骗博弈实验中的决策,结果如表5所示。实验组3中,有30名提议者选择提供真实信息而19名选择了欺骗,欺骗率为38.8%,显著高于实验组1的21.7%。单边Fisher Exact检验的p值为0.057,单边比例检验的p值为0.036,均在统计上显著。
表5实验组1与实验组3的欺骗率
实验组1实验组3FisherPrtest真实3630欺骗1019欺骗率0.2170.388p=0.057∗p=0.036∗∗
注:Fisher和Prtest分别代表单边Fisher Exact检验和单边比例检验(备择假设是实验组3欺骗率大于实验组1的欺骗率)。***、**、*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
实验结果表明,同样是通过在真实劳动中胜出而产生的获胜者,同样拥有自致性社会地位,得到8元物质收益的提议者反而增加了欺骗行为。这与假设3一致。我们认为物质奖励激发了个体对市场与利益的自我概念意识。欺骗获益与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我概念一致。也就是说,在实验组3的情况下,个体既有维护诚实的自我概念,同时存在选择欺骗从而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自我概念。两者动机是互相竞争矛盾的。因此,与实验组1相比,实验组3中的个体欺骗率显著上升。
测量系统在同一速度(stp-20000;spd20)下,对同一单株小麦茎秆,分析3个不同作用点距地高度处测量回弹力T、挠度值a的关系曲线,如图10(a)所示;对同一单株小麦茎秆,同一作用点距地高度(48.2cm处),分析3个不同速度(stp-20000;spd20;stp-20000;spd50;stp-20000;spd70)下测量的回弹力T、挠度值a的关系曲线,如图10(b)所示。
小时候,我读过一本有关大灰熊的书,里面有一幅图是灰熊熊掌前伸、后腿站立着咆哮。艾尔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只见他扑向威尔,死死地抓住他的双手不让他脱身,然后狠狠地朝他的下巴出拳。
我们由此得到结论,
结论3:赋予物质奖励的自致性社会地位,会显著削弱自致性社会地位原本产生的诚实效应,从而无助于减少欺骗。
(四)自致性社会地位的作用时间
我们进一步考察自致性社会地位获得者的欺骗决策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实验组1中提议者在六轮欺骗博弈实验中的具体决策结果如图2所示。决策之前,该组的被试都进行了真实劳动任务,他们的角色分配由真实劳动结果产生。图中可明显看出,紧接着真实劳动的第一轮博弈中,提议者的欺骗率最低,平均欺骗率为21.7%,而在第二轮欺骗率就上升至41.3%,并且在随后四轮中保持这样的高水平,随后四轮的平均欺骗率为39.1%、45.7%、39.1%和39.1%。
图2 实验组1各轮平均欺骗率
将第一轮的欺骗率分别与后面五轮进行比较,发现真实劳动的首轮欺骗率显著较低,符号检验的结果如表6所示。实验组1中的提议者,首轮的欺骗率显著低于其在第二轮的欺欺骗率,符号检验的p值为0.018,Wilcoxon符号秩检验的p值为0.020,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首轮与第三轮至第六轮的欺骗水平之间的差异也都很显著。从第二轮开始,欺骗率都显著高于第一轮。
表6实验组1各轮欺骗率
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欺骗率0.2170.4130.3910.4570.3910.391Signtest-p=0.018∗∗p=0.038∗∗p=0.013∗∗p=0.048∗∗p=0.048∗∗Wilcoxon-p=0.020∗∗p=0.046∗∗p=0.016∗∗p=0.059∗p=0.059∗
注:Signtest和Wilcoxon分别代表单边符号检验和Wilcoxon 符号秩检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是通过1∶5水工水力学模型试验对花园水库竖缝式鱼道池室的流态、池室平面流速分布、竖缝垂向流速分布、单位体积消能率等水力特性进行研究,分析诸多水力特性能否满足洄游鱼类上溯要求。
我们认为被试者在第一轮欺骗实验中的行为表现,时间上最接近社会地位形成,被试者行为受第一阶段的社会地位形成机制的影响。随着实验的进行,社会地位不再被有意凸显,通过努力获得的地位所带来的公平诚信的自我概念会趋于淡化,因此相应的维护自我的内在道德价值的努力也会降低,欺骗行为也逐渐恢复到常态。我们用实验室实验来研究社会地位,只能临时赋予被试者社会地位身份,因此被试者的决策一定会逐步趋于理性。然而第一轮显著降低的欺骗率,充分说明自致性社会地位对于抑制欺骗行为的有效性。与之前的假设相一致[注]作为对比,我们对其余组进行了类似的时间趋势的检验,发现其余各组后5轮和第1轮之间都不存在显著关系,这也进一步说明社会地位对降低欺骗率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由此得出结论4。
在提议者选择发送的信息后,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接受者最终会选择什么?”为确保激励,如果答对将会获得2元人民币的奖金。参与者的最终所得为六轮中随机选择的两轮实验结果,这样确保被试者全程都有激励。他们的收入为随机两轮实验结果,可能的猜测奖金以及10元出场费。
结论4:通过真实劳动获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对于降低欺骗行为具有时效性,并不能长期有效。
六、稳健性检验
(一)剔除策略性选择
以上的分析都基于一个严格假设,提议者的决策行为不包括策略性动机。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在欺骗实验中,不能排除提议者本身存在策略性思考的情况。我们的实验设计可以有效甄别出有策略性动机的样本。在六轮重复欺骗博弈实验中,所有的提议者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接受者最终会选择什么”。依据提议者提供的信息和对与其匹配的接受者行为的预测,可将提议者分成四种类型:普通的诚实、普通的欺骗、策略性欺骗以及善意的谎言。如表7所示。
表7提议者的类型
提议者的类型猜测接受者同意提议猜测接受者否定提议提供真实的信息普通的诚实策略性的诚实提供错误的信息普通的欺骗善意的谎言
如果提议者提供了真实的信息,且预测接受者会同意他的提议,提议者就属于普通的诚实;如果提议者提供了真实的信息,但猜测接受者不会同意他的提议,结果是提议者会得到更高的15元回报,提议者属于策略性的诚实;如果提议者选择提供错误的信息,并且预测接受者会同意,提议者属于普通的欺骗;最后,如果提议者选择提供错误的信息,但预测接受者会选择另外的方案,这样的提议者属于善意的谎言。
考虑到提议者可能的策略性选择,应当在提供错误的样本中补充提供真实信息、猜测接受者会否定的这类“策略性诚实”提议者,同时去除提供错误的信息、也猜测接受者会否定的这类“善意的谎言”提议者。由此我们得到调整后的欺骗者样本:调整后的欺骗者=普通欺骗者+策略性诚实-善意的谎言。实验的四个组中,提议者的首轮调整后的平均欺骗率如图3所示。在对照组的48名提议者中,有20位猜测接受者会选择信息1对应的方案,即选择欺骗,调整后的平均欺骗率为41.7%(标准差为0.498);在实验组1中,有13名提议者猜测接受者会选择信息1对应的方案,调整后的平均欺骗率为28.3%(标准差为0.455);实验组2中有25名提议者,剔除策略选择后选择欺骗接受者,欺骗率为53.2%(标准差为0.504);在实验组3中,23名提议者猜测接受者会选择信息1对应的方案,调整后的欺骗率为46.9%(标准差为0.504)。各组调整后的均欺骗率和其95%的置信区间如图3所示。
图3 调整后各组平均欺骗率
剔除了提议者的策略性选择后,再来考察对照组和实验组1及实验组2调整后的平均欺骗率。实验组1中的提议者需要在真实劳动中获胜而得到提议者角色,而对照组为随机分配。调整后实验组1中提议者的平均欺骗率为28.26%,仍旧显著低于对照组的41.7%。对照组和实验组1的非参数检验结果如表8,单边比例检验的p值为0.087。同样的,比较对照组和实验组2在调整后的平均欺骗率,我们发现实验组2的欺骗率上升较多,达到了0.53。非参数检验表明,给予实验组1中的提议者物质激励无助于降低调整后的欺骗率,单边Fisher Exact检验的p值为0.179,单边比例检验的p值为0.131。
表8调整后欺骗率
对照组实验组1实验组2真实283322欺骗201325欺骗率0.4170.2830.532Fisherp=0.126p=0.179Prtestp=0.087∗p=0.130
注:Fisher和Prtest分别代表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的单边Fisher Exact检验和单边比例检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
该结果表明,考虑到策略性选择,与通过幸运获得的先赋性社会地位的被试相比,通过真实劳动赢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的被试者依然会减少欺骗。同时,研究发现赋予物质奖励的先赋性社会地位不能降低欺骗率,反而使之略有上升,这与调整前的结果完全一致。结论1和结论2是稳健的。
进一步继续考察考虑策略性选择后,自致性社会地位与物质奖励导致的欺骗率的变动。比较被试者在实验组1和实验组3在首轮欺骗博弈实验中的决策,调整后的平均欺骗率如表9所示。实验组3中,有33名提议者猜测接受者会选择真实信息对应的方案,19名猜测决策者会选择对提议者更有利的方案,即欺骗。调整后的欺骗率为46.94%,显著高于实验组1的28.26%。单边Fisher Exact检验的p值为0.048,单边比例检验的p值为0.030。这个结果与调整前的两个实验组之间欺骗率差异一致。结果表明,即便考虑到策略性选择的因素,实验组1和实验组3仍存在显著差异。即通过真实劳动获得自致性社会地位的提议者,获得8元物质奖励之后,反而显著地增加了欺骗行为。因此,结论3即赋予物质奖励会显著削弱真实劳动获得自致性社会地位的诚实效应,这个结果在调整后仍旧是稳健的。
表9调整后欺骗率
实验组1实验组3FisherPrtest真实3326欺骗1323欺骗率0.2830.469p=0.048∗∗p=0.030∗∗
注:Fisher和Prtest分别代表单边Fisher Exact检验和单边比例检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
图4为调整后实验组1中提议者在六轮欺骗博弈实验中的平均欺骗率。图4中可明显看出,紧接着真实劳动的第一轮博弈中,提议者调整后的欺骗率最低,调整后的平均欺骗率为28.3 %,而第二轮欺骗率上升至39.1%,第三轮中继续上升至52.2%,并且在后面三轮中保持这样的高水平,后面三轮的平均欺骗率为41.3%、50.0%、47.8%。
图4 调整后实验组1各轮欺骗率
将第一轮的调整后的欺骗率与后面五轮的平均欺骗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紧接着真实劳动的首轮欺骗率依旧显著较低。实验组1中的提议者,在首轮的调整后的欺骗率显著低于其在后面五轮的平均欺骗率,符号检验的p值为0.01,Wilcoxon符号秩检验的p值为0.008,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如表10所示。
3)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一流能源公司的需要。经过30多年的高速高效发展,中国海油已经初步实现了从纯上游的油气开发生产公司到上下游一体化能源公司的转变。在向着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能源公司迈进的征程中,如何在节能工作中更好的践行集团公司“绿色低碳”核心战略,将节约能源、水资源和生产低碳产品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内在要素,实现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表10调整后欺骗率差异
第一轮第二轮-第五轮平均调整后的欺骗率0.2830.461Signtestp=0.01∗∗∗Wilcoxonp=0.008∗∗∗
注:Signtest和Wilcoxon分别代表单边符号检验和Wilcoxon 符号秩检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
该结果表明,剔除策略性选择之后,通过真实劳动获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的欺骗率降低趋势仍具有时效性,第一轮后不再凸显社会地位时,它对欺骗行为的抑制效应也减弱,该结果也是稳健的。所以,真实劳动形成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对于欺骗的减少必须与决策紧密相连。随着实验的推进和时间的推移,平均欺骗率会逐渐趋于稳定。
总结以上结果,我们认为剔除策略性选择后的结果与之前结果具有一致性,结论1-4都是稳健可靠的。
(二)回归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排除差异结果由于其他个体特征差异所导致的可能性,我们使用Probit模型控制可能的影响因素,对所有实验数据整体进行回归,考察各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因变量是每个个体在首轮实验中是否欺骗(欺骗=1,不欺骗=0)。
模型1将是否为实验组1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对照组和实验组1的差异;模型2将是否为实验组2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对照组和实验组2的差异;模型3将是否为实验组3作为解释变量,但该模型考察的是实验组1和实验组3之间的差异。此外,在模型1-3中,我们控制被试年龄、性别、专业、党员身份以及个体的公平感、信任感、幸福度和收入水平。模型4-6的被解释变量为调整后的首轮实验中是否欺骗(欺骗=1,不欺骗=0),加入前述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结果如下:
表11 Probit回归(边际效应)
(1)(2)(3)(4)(5)(6)首轮欺骗率调整后的首轮欺骗率实验组1-0.203∗∗(0.099)-0.167(0.104)实验组20.007(0.107)0.118(0.110)实验组30.204∗∗(0.098)0.268∗∗(0.106)年龄0.064∗(0.037)0.047(0.042)-0.033(0.038)0.033(0.040)0.133∗∗∗(0.048)-0.094∗(0.048)男性(=1)0.180(0.152)0.283∗(0.157)0.009(0.116)0.262∗(0.149)0.112(0.170)0.217∗(0.129)经管专业(=1)0.109(0.118)-0.058(0.117)0.248∗(0.129)0.090(0.121)0.030(0.121)0.136(0.136)党员(=1)0.008(0.194)-0.221(0.170)0.381∗(0.216)0.211(0.230)-0.431∗∗∗(0.113)0.622∗∗∗(0.119)公平感(1-7)-0.022(0.054)-0.042(0.054)-0.041(0.051)0.009(0.054)0.058(0.056)0.002(0.053)信任感(1-7)-0.079(0.048)-0.092∗(0.053)0.046(0.051)-0.029(0.048)-0.067(0.054)0.057(0.056)幸福感(1-7)0.052(0.049)0.064(0.051)-0.084∗(0.048)0.066(0.052)0.039(0.051)-0.091∗(0.052)收入水平(1-7)-0.018(0.061)-0.058(0.070)0.108∗∗(0.054)-0.020(0.060)-0.088(0.075)0.115∗∗(0.055)观测值94(0.109)95(0.110)95(0.113)94(0.109)95(0.121)95(0.131)
注:括号里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
表11显示,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实验组1中的提议者的首轮欺骗可能性显著低于对照组。模型2中,实验组2和对照组的比较,是否为实验组2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对照组和实验组2的首轮欺骗可能性无差异。模型3表明,相对于实验组1,实验组3的提议者欺骗可能性显著更高。
模型4表明调整后的对照组和实验组1的提议者首轮欺骗行为没有显著差异,但仍旧为负,且p值为0.116,边际显著。模型5的结果说明调整后的首轮欺骗率在对照组和实验组2中没有差异;模型6表明与实验组1相比,实验组3的提议者更有可能进行欺骗。控制被试者的个人特征后,这些结论仍与正文中的实验结果一致,表明这些结论具有稳健性。以上结果也说明我们可以排除样本在性别方面的不平衡对实验结果产生的影响。
七、结论
本文中,我们研究了社会地位通过自我概念机制,对欺骗这种非道德行为产生的影响。我们利用实验室实验,检验不同方式获取的社会地位对降低欺骗率的作用。实验结果发现,不同社会地位来源会对个体决策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通过真实劳动赢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可以显著降低欺骗率。自致性方式赢得的社会地位是在公平竞争环境之下,根据个人能力和努力最后取得的成绩来获得。这种社会地位获取的方式下,个体也会强化诚信的道德准则和自我概念。在紧接着的决策中,个体会以诚实方式或个体认为应该表现出的“合理”方式做出决策, 人们在行为上也会趋于符合一定的内在社会准则(Messick,1999),去维护积极良好的自我概念,从而获得积极的内在回报(Mazar et al.,2008)。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我们只在紧接着的决策中看到欺骗率的显著降低,因为之后几轮决策中,个体没有再进行新的劳动去获取社会地位。
尽管自致性社会地位会引导个体以公平诚实的方式去做决策,但是赋予物质奖励却会诱发个体产生有关交易与利益的自我概念,促使个体为维护这样的自我概念而去最大化个人利益。因此,在自致性社会地位基础上,同时赋予物质奖励,欺骗率显著高于无物质奖励情况下的欺骗率。这有助于解释Piff et al.(2012)提出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地位较高者的精英分子反而会有更多的欺骗行为。原因可能是精英有更多机会接触市场场景,强化个体追求利益的自我概念,削弱维护内在道德准则和诚信自我概念的努力。
本文对Mazar et al.(2008)有关诚实与自我概念维护理论研究作出了有效论证,也是对Becker(1968)等关于欺骗行为成本收益解释理论的补充和延伸。我们的研究表明,个体道德行为决策受到社会地位不同获取方式的影响,只有在公平诚信、自我努力方式下获取的社会地位才会引致个体较高的内在道德准则,促使个体追求诚信的道德行为。
此外,本文对社会、企业、机构等各类组织的诚信管理也都具有启示意义。根据本文研究结论,设计一个与个体努力相应的公平有序竞争机制,能够极大地减少成员之间的欺骗行为,增加组织与社会系统内的诚信,从而降低欺骗以及不信任等带来的低效率和福利损失,最终可能有效提高生产率和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刘凤芹、卢玮静,2013,“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13-120页。
汪昌云、孙艳梅,2010,“代理冲突、公司治理和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研究”,《管理世界》, 第7期,第130-143页。
王小龙,1998,“对商业道德行为的一种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第9期,第70-77页。
张翼,2004,“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社会学研究》,第4期,第76-90页。
Allingham, Michael G. and Agnar Sandmo, 1972, “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11): 323-338.
Aronson, Elliot,1969,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 Current Perspective”,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Leonard Berkowitz, E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34.
Aquino K, Freeman D, Reed A, II, Felps W. and Lim VK., 2009, “Testing a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moral behavior: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situations and moral identity centr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1): 123-141.
Becker, G.S., 1968,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2):169-217.
BénabouR. and Tirole J., 2006, “Incentiv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5): 1652-1678.
Alexander W. Cappelen, Erik. Sørensen and Bertil Tungodden,2013, “When do we li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93(2): 258-265.
Carpenter, J., and Myers, C. K., 2007, “Why volunteer?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altruism, image, and incentiv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4(11): 911-920.
Chen, Yanand Lu, Fangwen and Zhang, Jinan, 2017, “Social comparisons, status and driv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5(C): 11-20.
Childs J., 2012, “Gender differences in lying”, Economics Letters, 114(2), 147-149.
Coie, John D., Kenneth A. Dodge, and Heide Coppotelli, 1982, “Dimensions and types of social status: A cross-age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8(4):557-570.
Dai, Zhixin, F. Galeotti, and M. C. Villeval., 2016, “Cheating in the Lab Predicts Fraud in the Field - An Experiment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s”, Working Papers.
Dubois D, Rucker D. and Galinsky A D.,2015, “Social class, power, and selfishness: when and why upper and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behave unethicall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08(3): 436.
Dreber, A. and Johaanesson, M.,2008,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ception”, Economics Letters, 99(1): 197-199.
Ebeling F, Feldhaus C. and Fendrich J.,2017, “A field experiment on the impact of a prior donor’s social status on subsequent charitable g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61:124-133.
Eckel, C.C. and Wilson, R.K., 2007, “Social learning in coordination games: does status matter?”,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0(3): 317-329.
Ederer, F.,and Fehr, E., 2007, “Deception and incentives: how dishonesty undermines effort provision”,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Erat, S., 2013, “Avoiding lying: The case of delegated dece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93(2): 273-278.
Erat, S.and Gneezy, U.,2012, “White lies”, Management Science, 58(4): 723-733.
Ebeling F, Feldhaus C. and Fendrich J.2012, “Follow the Leader or Follow Anyone -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 Cologne Graduate School Working Paper.
Faravelli, M., Friesen, L., and Gangadharan, L., 2014, “Selection, tournaments, and dishonest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10(1):1-16.
Fershtman C. and Weiss Y., 1998, “Social rewards, externalities and stable preferenc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0(1): 53-73.
Frey,B.S. and Meier, M., 2004, “Social comparison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esting conditional cooperation in a field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5):1717-1722.
Gächter, S., Nosenzo, D., Renner, E. and Sefton, M., 2012, “Who makes a good leader? Cooperativeness, optimism, and leading-by-example”, Economic Inquiry, 50(4): 953-967.
Gill, D., and Prowse, V., 2012,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disappointment aversion in a real effort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1): 469-503.
Glätzle-Ruätzler D. and Lergetporer, P., 2015, “Lying and age: 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46(1):12-25.
Gneezy U. and Rustichini A., 2000, “A Fine Is a Pric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1), 1-17.
Gneezy U., 2005, “Deception: The Role of Consequ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 384-94.
Gneezy, U., Rockenbach, B., and Serra-Garcia, M., 2013, “Measuring lying aver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93(2): 293-300.
Harris, Sandra L., Paul H. Mussen, and Eldred Rutherford,1976, “Some Cognitive, Behavioral, and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Maturity of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28 (1): 123-35.
Holm, H. J., and Kawagoe, T., 2010, “Face-to-face lying-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Sweden and Japa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1(3): 310-321.
Hurkens, S., and Kartik, N., 2009, “Would I lie to you? On social preferences and lying aversion”, Experimental Economics,12(2): 180-192.
Innes, R.,and Mitra, A., 2013, “Is dishonesty contagious?”, Economic Inquiry, 51(1): 722-734.
Henrich J., Boyd, R., Bowles S., 2001,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2): 73-78.
Kafashan, S., Sparks, A., Griskevicius, V., & Barclay, P., 2014, Prosocial Behavior and Social Status: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Status. Springer New York.
Konrad, Kai A., T. Lohse, and S. A. Simon, 2017, “Deception Under Time Pressure: Conscious Decision or a Problem of Aware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146(146): 31-42.
Knutson, Brian, Charles M. Adams, Grace W. Fong, and Daniel Hommer, 2001,“Anticipation of Increasing Monetary Reward Selectively Recruits Nucleus Accumben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1(16):1-5.
Kumru, C.S., Vesterlund, L., 2010, “The effect of status on charitable giv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12(4): 709-735.
Lightle, J. P., 2013, “Harmful lie aversion and lie discovery in noisy expert advice gam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93(2): 347-362.
Linton, R., 1936, “The study of man: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Lewis, A., Bardis, A.,Flint, C., Mason, C., Smith, N. and Tickle, C., 2004, “Drawing the line somewher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moral compromis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5(6): 718-725.
Mazar, N., Amir, O., and Ariely, D., 2008, “The dishonesty of honest people: A theory of self-concept maintena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5(6): 633-644.
Mellström C., and Johannesson M., 2008, “Crowding Out in Blood Donation: Was Titmuss Righ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4): 845-863.
Messick, D.M., 1999, “Alternative logics for Decision Making in Social Sett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9(1):11-28.
Magnus, J.R., Polterovich, V.M., Danilov, D.L. and Savvateev, A.V., 2002, “Tolerance to cheating: an analysis across cul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33(2): 125-135.
Nabanita Datta Gupta and Amaresh Dubey, 2006, “Fertility and the household’s economic status: A 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Indian micro dat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2(1): 110-138.
O’Doherty, John P., Ralf Deichmann, Hugo D. Critchley, and Ray- mond J. Dolan, 2002, “Neural Responses During Anticipation of a Primary Taste Reward”, Neuron, 33 (5): 815-826.
Pascual-Ezama D, Prelec D. and Dunfield D., 2013, “Motivation, money, prestige and chea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93(2): 367-373.
Piff, P. K., Stancato, D. M., Cté, S., Mendozadenton, R., and Keltner, D.,2012,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11): 4086-4091.
Piff, P. K., Kraus, M. W., Cté, S., Cheng, B. H., and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9(5): 771-784.
Potters, J., Sefton, M. and Vesterlund, L., 2007, “Leading-by-example and signaling in voluntary contribution gam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Economic. Theory, 33(1): 169-182.
Rawwas, M.Y.A., Al-Khatib, J.A. and Vitell, S.J., 2004, “Academic dishonesty: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U.S. and Chinese marketing students”, 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 26(26): 89-100.
Sakamoto, Kayo, T. Laine, and I. Farber, 2013, “Deciding whether to deceive: Determinants of the choice between deceptive and honest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93(93): 392-399.
Sánchez-Pagés, S.,and Vorsatz, M., 2007,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ruth-telling in a sender-receiver game”,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61(1): 86-112.
Shils, E., 1968, “Deference”, In: Jackson, A.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omanathan, E. and Rubin, P. H., 2004, “The evolution of honest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54(1): 1-17.
Sutter, M., 2009, “Deception through telling the truth?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dividuals and teams”, Economic Journal, 119(534): 47-60.
Van Zant, A. B.,and Kray, L. J., 2014,“I can’t lie to your face: Minimal face-to-face interaction promotes hones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5:234-238.
Vanberg, C., 2010, “Why do people keep their promise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wo explanations”, Econometrica, 76(6): 1467-1480.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1922,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197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TheImpactsoftheOriginsofSocialStatusonDeception: Evidence from a Lab Experiment
Xu Hui Liang Jie Gui Shan
Abstract: Reducing deception i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faced by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tatus and self-concept in determining the deception behavior. We resort to lab experiment by distinguishing two different origins of social status: “ascribed status” and “achieved status” together with the deception game. Comparing to the proposers with ascribed status, the proposers with achieved status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 of deception rate. Nevertheless, endowing monetary reward to the proposers with achieved status weakens the effects, suggesting that the monetary reward takes as a remind of marketization. All the results are robust afte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strategical behaviors. Our findings provide supportive evidences for the theory of self-concept suggested by Mazar et al. (2008), an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in improving the credibility for various kinds of organizations.
Keywords: Deception; Social status; Self-concept; Lab experiment.
DOI:10.19592/j.cnki.scje.361533
JEL分类号:C91,D01,Z13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9)02-086-22
*徐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E-mail: xuhui@bnu.edu.cn,通讯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编:100875;梁捷(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E-mail:liang.jie@mail.shufe.edu.cn, 通讯地址:上海国定路777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00433;桂姗,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E-mail:17210180046@fudan.edu.cn,通讯地址:上海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数学学院,邮编:200433。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基金信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503022)。
(责任编辑:谢淑娟)
标签:实验组论文; 社会地位论文; 个体论文; 自我论文; 接受者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南方经济》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503022)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论文;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