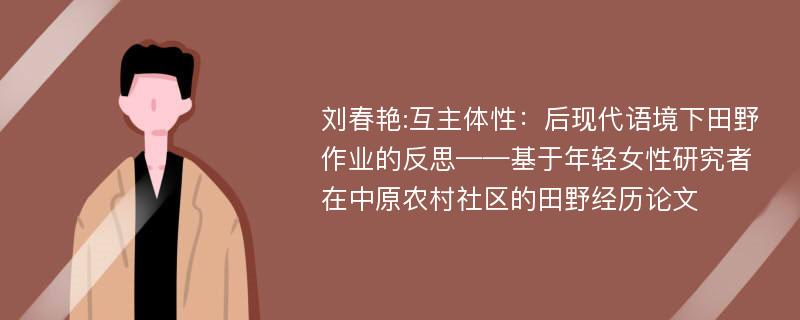
摘 要:基于河南民间高跷表演霸王鞭的田野考察经历,对民俗学人类学田野作业方法进行观照和反思,得出如下认识:官方引介进入研究社区的渠道具有诸多便利,但研究者对其中受到的制约需保持清醒;田野过程复杂多变,研究者需灵活应对、顺势而为;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对世界每个角落的深刻影响,研究者更应自觉用互主体性的视角统摄田野作业;对女性研究者的田野作业而言,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制约和人际交往情感力量的抗衡区隔相比,更经常的状态是二者的交融互动。
关键词:田野作业;反思;互主体性;女性研究者
关于田野研究方法的学理意义,很多学者都有过精辟的阐述,其中最经典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已逝乔健老师的成年礼的生动比喻。他说,“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根本。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是任一专业人类学家的必经之路,是他的成年礼”[1]14。田野作业方法的必需性和不可替代性对于民俗学人类学研究者的成长历程永不过时,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在当今时代,已经没有一个乡村能够不受全球化、现代化的影响,完全与外界文明隔绝。因此新时代的田野作业衍生出许多全新问题,比如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对研究对象的持续影响、城市农村社区的结构性差异引发的不同交往渠道,以及无处不在的田野观下信任关系的构建方式等,使得田野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意味着研究对象不再是想象的、虚构的他者——对外界信息一无所知,而相应地研究者对当地人具有的优势也在逐渐削弱,比如可与之交换的知识资本、信息资本日益成为一种公开的共享资源。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理论屡屡对人类学民俗学民族(民俗)志的歧义性、真实性发出诘难,学术界的质疑和论争敦促我们对田野作业方法不断反思、调适。尤其在21世纪全球化不断加速深化的复杂情势下,研究者对田野经验自觉进行反省,宏观上不仅具有辨析提炼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面向时代拥抱社会的现实意义,具体到微观视域,反思田野作业既是对民族志的重要补充,也是改进田野作业的必然途径。
霸王鞭是流传在河南省叶县境内的一种民间高跷舞蹈表演,现今通常在春节期间表演,一般被认为是表现当地民众过年的欢乐祥和以及丰收的喜悦富足,因为表演时演员需手持一种竹竿制作的道具“霸王鞭”(俗名响杆)而得名。2011年该表演成功申报河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笔者关注到其传承机制在一定范围的代表性,分别于2018年8月、10月进行了短期田野调研。这次田野的经历如果借用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的脉络来勾勒的话,可以由两位女性资讯人结构全篇。一位是当地文化站站长,在我眼中她俨然是地方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另一位是新生代的传承人,她的传艺经历可以概括为民间艺术与乡村政治复杂纠葛的优胜者。与前者的相交始于半正式的引介,文化站长依靠她的社会身份将我带到田野,成为我和研究对象的良好中介,减少了陌生人进入村落社会可能遭遇的抗拒和对调查的干扰。与后者的交往则表现出更多女性之间相知相惜的情感色彩。以这两位女性资讯人为中心展开的调研活动,包括其中发生的更多事件,是我对田野作业方法不断反思的经验基础。
一、进入社区的途径:官方引荐的便利和制约
文化站长的名字,我之前在新闻报道的资料中见到过,和她的交往一开始基本属于官方正式渠道的工作接待和被接待的性质。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亲戚利用工作关系帮我联系上县文化局的办公室主任,由他把我介绍给镇文化站长。所以,虽然有熟人的引介,实际上在我和文化站长之间已经没有熟人社会的那种浓厚的人情关系了。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一早就来到乡政府文化站,出于礼貌还专程买了一些水果作为初次见面、打扰别人的馈赠礼物。虽然有熟人关系的铺垫,但我明显感到一开始文化站长对我的到来还是有一些抵触或者并不很欢迎的情绪。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年轻女性研究者的身份使然。刁统菊博士在她的文章中已经指出类似的情况:“女性研究者常常遭到忽视,不值得信任和尊重。”[2]反观自己的身份,我不仅是女性,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女性,而所在单位又并非全省或全国知名高校。这些身份都让我在对方眼中被视为不具有权威、不值得信任的标志。第二,我的研究成果是否会给她的现有工作带来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这可能是她内心最为关切的,我的造访对她有什么作用,所以我十分理解她的疑虑。第三,我的来访确实占用了她的工作时间。调研期间,脱贫攻坚正在乡间基层热火朝天地进行,乡镇干部工作极为忙碌。为了消除她的顾虑,我一开始就把我的研究内容和将来成果的用途讲解给她,还特意将工作证以及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证拿给她看。我注意到她当时表现得并不在意,言外之意我的这个举动显得外气了,我是通过熟人介绍来的,她信任我。但后来在我和传承人聊天的时候她还是专门拿起来仔细查看,并在确认我的身份之后逐渐转变了态度。第一个资讯人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在和我不断地交往、试探和观察中建立了彼此的田野关系。
当初选择这条进入社区的路径,主要是出于容易被当地社区接受、提高调研工作效率,以及保障自身人身安全的考虑。实际上还是有潜在意识的优越感因素在起作用,但这种自我优越感在和文化站长一开始的接触中便遭遇打击,其实恰好也提醒了自己:研究者在田野研究和书写中应自觉秉持平等、尊重、互信等伦理,不断反思各种权力的影响。具体到我所研究的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频繁的中原农村,应该如何赢得研究对象的信任?首先就要克服自我优越感,这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范可老师说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田野工作,研究者必须克服自己的优越感。你凭什么觉得你比你所研究的人优越?就因为你的教育背景,你的身份,或者你的富有?”[3]放下研究者的架子,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发自真心向他们请教,平等真诚地和他们交流、交往。其次,尽可能地向对方说清楚你的身份、研究内容和研究用途,得到对方最大限度的理解,这一点非常要紧。不管是乡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对外来的陌生人的疑虑和隔阂可能是研究者面临的最大敌人,所以必须尽快克服这个障碍,取得当地人的理解、信任。那么,官方的正式引荐就是很必要、有保障的一个通道。董晓萍老师在谈到地方信息提供者(我称之为“资讯人”)的重要作用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许多田野作业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人类文化集团中的很多群体对外人都是多疑的、提防的、有攻击性的,因此,在地方信息提供者的帮助下,开始良好的接触,对研究者来说,是最基本的一步[4]492。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计划安排还是有效力的,当然也出现了不理想的状况。调研开展到中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条路数的局限和束缚了。很多需深度访谈的话题因为文化站长的在场不便问询,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大家的交流往往止于粗浅外显、不痛不痒的问题,有关态度、思想、观念层面的交流无法涉及或深入。因此,在中午和文化站长共进工作餐后,我就主动暂时中止了这次调研。不过,平心而论,和她的交往确实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首先,她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地方文化宣传者、传播者,她给我讲述当地外出表演或参加赛事的组织运作机制,她对霸王鞭艺术传承的态度和构想,以及她与外界联系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等。她是一个挺坦诚和理想的资讯人,能够将地方文化的传承现状和运作机制等客观清楚地介绍给我。她的身份(既是文化站长,又是该村的扶贫联系干部)顺理成章把我带入田野,并按照我的愿望联络到其他访谈对象,比如代表性传承人、小学校长和教师、村干部等,使我的调查工作能够集中展开、直奔主题。她是一个良好的中间人和桥梁,连接起外来者的我和当地群众,使我在当地被迅速接受,没有遭遇当地人的抗拒和内心的抵触、排斥。
2018年8月12日,我在文化站长的陪同下来到传承人张大爷的家中,这是一座规整的北方庭院式住宅,主体房屋是崭新的两层四间宽的楼房,坐北朝南。老人72岁,身体健朗,精神矍铄,对我们非常热情,给我们展示他获得的诸多荣誉,在气氛热烈的时候,还拿出他的宝贝霸王鞭让我们欣赏,并现场表演了他的绝活抖鞭技术,让我们大开眼界。不足的是,我明显感到老人并不健谈,使得交谈苍白枯燥单调,甚至几度冷场,颇为尴尬,从他那里我并未获取有价值的资料。
二、田野过程:充分准备基础上的灵活调适
田野永远是一个鲜活的世界,是一个多姿灵动的时空。踏入田野、用心感受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乡土社会时,才能切实理解现实的文化与来自书面文本、新闻报道中的被建构的文化之间的落差。田野实践往往并不遵循你的预期,甚至往往会打乱你的计划。这也是田野的开放性、迷人之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先验地把握研究对象,当然并不是否定充分的调查准备和提纲的价值,这是两个维度的议题。在明确研究主题的前提下,调查领域不能过于狭窄,同时根据调研的具体情境灵活调整提纲、计划。范可老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讲到,“带着课题下田野不见得就不会发现其他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你从田野发现的问题可能远比带来的问题更有价值”[5]。邵京老师也讲到“我们去田野是带着问题去的,但问题还可以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不断修订,增补,更换。田野应该是我们提出新鲜问题的地方,而不应当仅仅是验证我们己经形成的想法的场所”[5]。就我的自身感受,还应该添上这个假设成立的前提,即固然有前期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学界相关成果、地方志、官方文件、新闻报道等)对调查对象烂熟于胸的了解,但更重要的是仰赖于平时大量阅读相关著作、消化吸收所构筑的对跨学科多样化理论、研究方法的切实掌握,以及在研究过程的实践运用。否则,发现问题只能成为一种单向的奢望。实际上,很多学者成功的田野研究都得益于此,比如陈泳超对山西洪洞“接姑姑迎娘娘”信仰活动中娘娘身世传说的田野历程,因为他对活动圈内外的尧舜和二妃的所有传说以及细节都了然于胸,那么对传说讲述的些微变化和背后的微妙关系他都能准确地捕捉和感知到,并能够运用长期深厚的学养积累合理地诠释。就我关注的霸王鞭舞的传承现状而言,在代表性传承人、普通民众访谈的过程中,意外洞悉当地流传的关于霸王鞭舞传说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当地传述的复杂情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收获,不仅对我们理解传说的承传、变异和当代功能、传播途径具有助益,更重要的是,传说的讲述、重组、传播对于霸王鞭舞的历史传承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而这一点可谓是对研究主题的深入拓展。于是,在接续的调查中,我就将当地流传的有关传说也作为一个特别的关注点。这样的发现也来自于不断培养的学术敏感。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宪法理论和制度,中国宪法学也由此获得长足发展。宪法学既从改革开放和法治实践中汲取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又运用自身的知识和理论为改革开放和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近年来,浙江省金华市人大常委会探索开展财政专项支出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先后完成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科技创新支出等6个项目的第三方绩效评价,今年又开展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补助等4个项目的第三方绩效评价,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年8月,该项工作获评“浙江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奖”提名奖。
另外,田野中你所遇到的人并不都适合成为你的重要资讯人。拉比诺在他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有类似表述。他认为,麦基(进入村庄后接触到的第一位当地人)很有耐心热情,但不具备成为一个优秀资讯人的能力,即将自身文化采用一系列办法客观清楚地介绍给外来者的能力[6]143。对此,我们需要有独到的辨识眼光和灵活的调适能力。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当地文化精英把我看作对他们文化充满好奇的观察者,他们的表现甚至可理解为“表演”也在应和他们认为我希望看到的景象。按照他们的逻辑,我既然是上级(对于村民而言,文化站长就代表官方、上级)安排来的调研人员,他们就遵照接待外来者的规则对待我。他们按照书面资料上的写定文本给我讲霸王鞭传说,讲家族的历史,讲他们对民间表演的热爱,讲他们的辉煌成果……可是我却看不到民间艺人悲欢离合的从艺经验,也听不到个体的声音和话语,更感受不到他们有温度的内心和情感。更让我感到束缚的是,我的行程很多时候只能按照文化站长的规约进行,接触到的当地人也基本是她替我遴选的“合适”人选。因此,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很可能是他们特意呈现给我这个外来研究人员的,我并没有探寻到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规则的“真实”(假设这个“真实”是存在的)。当然,这个目标并不是短暂粗疏的田野考察能实现的,由此我领悟到,田野作业来不得半点虚,既不是旅游观光者的走马观花,也不是社会实践的浮光掠影,那是一场实实在在、扎根基层的持久战。
课程是学校实现办学目标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学校创建办学特色、提高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的主要载体,更是校长教育领导力的体现。
这种情况并不是特例,在田野中多次发生。在我对另一位男性传承人访谈的时候,向其询问他记忆中的当地相关传说,该传承人只能肯定地回答“有,那咋木有?”,但是却无法讲述具体情节。幸运的是,这个让人遗憾的状况却触动了在场一位女性的记忆,她给大家讲述了童年时期听过的传说,并且她讲述的这个版本和之前当地通行的版本相比出现较大变异,对我的研究非常有价值。
笔者随机在宿舍和同学开启了一场主题谈话:说说自己的择偶观。90后的女同学给我讲了她从上次失败的恋爱经历中得出的教训,再找男朋友一定找:对自己好、一心一意、不要太精明、厚道大度、诚实。我注意了一下,她主要是从品行和情感方面对男性进行认知,没有更多地涉及能力学识,比如他的学历、职业、收入等。那么我就这个变量扩展交流,同学的观念是只要受过正规高等教育都可接受,不一定非得是博士学历,企事业单位管理岗都可以,受过好的本科以上教育的收入应不会太低。就这个问题,我又利用课余和邻宿舍、同班同学交流,得到大体一致的结论。由当代女性的择偶观反观傻女婿故事,可以成为笔者假设的一个有力证据。在这个案例中,同学虽然已经被研究者的“我”对象化,成为我观察研究的客体对象,但是我们的交流是平等的主体间的自觉地讨论、磋商、探究,甚至还就我研究的假设发表各自的看法。
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我一句礼貌的询问,让一直坐在大爷旁边角落里的老伴有了用武之地,大娘性格爽朗、说话直率,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提供了不少宝贵的信息。她把我当成了一个倾听者,甚至是能给她带来物质收益的公家人。大娘给我讲了很多她陪同老伴辗转购买制作道具所需原材料竹竿的曲折故事,以及道具制作的过程。她几次讲到“如果你们学校购买,就和我联系”之类的话,我能够感受到她特别希望我所在学校能够购买道具的朴实愿望。她还讲述了老伴在传承霸王鞭过程中遭遇的一些尴尬事件,对我们理解传承人现实的传承活动经验和个人生活状况,有不少帮助。在原先的计划中,她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访谈对象,但她的积极介入和出色表现使得我们的访谈更为顺利和成功。大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善于利用机会,在这样的场合她既给研究者的我提供了不为别人所知的资料,又侧面向文化站长代表的政府上级显示了她的不满,而她只是一名普通村妇,她不担心会有什么不良影响。我在这个场合就成了她向政府管理部门表达诉求的借口和工具。
三、互主体性:后现代语境中田野作业的突出特征
霸王鞭田野考察中先后经历的数位重要访谈对象都是女性,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冥冥之中的某种规律“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在引导着我的田野。事实上,确实如刁统菊博士所述,我的经验是从女性入手更容易打开局面,更方便深入社区,自身又比较安全。女性研究者的社会性别身份以及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确实导致在受访对象的选择和访谈内容的深入上有偏爱于女性的倾向,但我的感受是进入村落社会之后的调研过程并不完全受社会性别格局的牵绊。比如在访谈的那些老人面前,我通过给他们准备香烟,与他们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他们都将我视作他们的晚辈子女,尽其所知解答我的问题,并没有戒备和刻意隐瞒。
四是考核问责更加严格。这一制度明确要求将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的主要指标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要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负总责,并制定和实施严格的考核和问责制度。
拉比诺的反思如石破天惊,揭开了田野作业的神秘面纱,提出田野作业的一系列问题,引发我们的深思。在田野中,研究对象并不是没有能动性的客体,而研究者更不是一个完全处于支配优势的主体。他不想你知晓的,他会刻意隐藏,甚至误导、抗拒、干扰你的调查。在我就传承人通过学校教育体系进行民间艺术传承的具体开展情况进行了解时,发现非遗法规条例的基层落实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和困难。之前关注到新闻媒体屡次大肆报道当地村落小学传承民间舞蹈的优秀传统,我的资讯人也很确定地告诉我,传承人每周给小学生上一次课。可是当我在村落小学详细询问小学校长、老师、学生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传承人在学校的传授执行走形变样,他对学生的教授指导更多是象征性的、表面化的,实际上相关活动往往由体育老师组织,即使有参加表演的赛事,节目的排练指导更不是传承人力量所能担负的,传承人的在场更多的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表征。最让人惊诧的是村落学校的规模:只开办一、二、三年级,三个年级共计近40名学生。也就是说,在现行乡村学校体系中传承人其实很难在学校真正开展传承活动,民间艺术传承活动仍然是游离于正规教育体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同时意味着民间艺术传承和现行学校教育体系还流于两层皮的情形,二者的对接融合还需较长的探索历程,而这必然牵涉中小学义务教育改革以及城乡经济发展二元对立的社会话题(这需另文专门论述)。因此,资讯人有意无意遮掩的是他不愿让外来者看到的真实,而这个真实可能会削弱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的非遗政绩,进而构成对现有保护成果的威胁,甚至降低民间艺术的广泛影响力。
和张大爷的第一次交流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材料,除了因为他的语言表达不够顺畅之外,我分析还有其他因素的干扰,比如首次见面的陌生紧张、自身代表性传承人的特殊身份以及当时交谈的场合(开放性的,有文化站长、其他村民在场)等,这都使得他在面对我的提问时有顾忌。其实后来我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操之过急、急功近利,在首次接触就想深度访谈,那是达不到的,而且此时可能需要一对一的私下访谈。研究者和访谈对象之间是一种人际交往,而不是一套你问他答的固定程序。访谈对象并不是一个机械的、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有着情感需求、利益诉求,和我们同等的独立主体,他同样有自己的认识、思考和判断。既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彼此相处、观察、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融洽关系的维系更不可能是通过一两次交谈就能实现的。
我所关注的霸王鞭,关于其历史由来,当地文化精英如传承人往往会结合村落最大的宗族张姓家族的迁徙和西楚霸王项羽战争胜利的传说讲述传播,以表明其历史的悠久性和来源的神圣性。文化站长在对外宣传中将家族族谱碑上的“瓦当”图案明确指认为霸王鞭人物脸谱,以此证明张姓家族和霸王鞭舞相伴共生、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有意思的是,我访谈更多的普通百姓,他们则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的霸王鞭舞表演都是在以“二月二”为主的村落庙会上进行的,针对官方的很多说法,我去访谈普通民众,不少都遭到了否定或者不置可否。根据他们描述的艺术形态,我做出初步判断,当地霸王鞭原初很可能是一种类似于河南曲剧早期形态“高跷曲”的地方民间小戏,其形成大约在清朝后期,并没有特别久远的历史。另外,在和一些村民的交谈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霸王鞭现今的发展态势和表演路径颇有微词。但是,他们的声音已经微乎其微,尤其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保护传承模式下,一些学者的碎片化的研究又推波助澜,普通民众的不合时宜的话语可能成为另类、异端,很难有存活的空间。显而易见,我通过文献、观察、比较、访谈后做出的初步判断,则是基于我对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和山西榆社霸王鞭的比较,对河南曲剧、民间小戏样态的熟悉,以及对民间传说发生规律的把握等做出的自觉的学术认识。可见,研究者、地方文化精英、普通民众对文化的经验和理解有着显著的差异。
这让我想到田野中另一个难忘的故事。访谈中,当我向他们了解历史上霸王鞭的代际传承机制、民间有没有团体组织、班头如何产生、逢年过节如何组织活动、有无相关的拜师仪式等情况时,文化站长深受启发,她很认真地反问我是不是以后每年村落应该搞个祭拜仪式,还希望我能给出一些仪式方面的具体指导建议。可见,以研究者为代表的外来人员的介入,让资讯人开始对其文化进行阐述,并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将自己的生活世界逐渐客体化。同时,民间文化的传统有一些确实是应特殊情境或形势的需要,由民俗精英发明或者重建出来的,并没有很久远的历史。研究者对当地的关注、造访、接触不可避免会对当地人的生活和原有的文化构成程度不等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人类学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我在这里不打算就此深入,我想传达的是: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凝固的客体,研究者在把他对象化的过程中,他实际上也在观察、思考你,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者也是研究对象的客体。就像卞之琳的那首小诗《断章》揭示的真谛: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主位观察与客体对象,而是包含各种交流、理解、文化制作的问题。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互为主体和客体,主客体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田野工作是一个交流的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互为主体。所涉及的主体没有共同的假设、经历和传统。他们的建构是公共的过程。”[6]147
上述事例表明,访谈对象与调查人员之间并不仅仅是信息提供者和研究者的关系,访谈对象有自己的主体性,在将自己的生活世界对象化的同时,也在思考与研究者的差异,以及“局外人”如何看待自己文化等问题。现在的田野,研究对象早已不是原始部落的“未开化”民族,访谈对象可以与研究者有较好的沟通,田野作业过程中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因此,随着时代的转变,田野作业也需要从传统的认知范式过渡到一种新的文化理解、互动互渗的知识共建认识论。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场有趣的谈话。最近,我在做傻女婿故事的研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傻女婿会有一个并不傻的贤惠媳妇。我并不满意于一贯的诸如岳父母贪财、媒人巧舌如簧等旧式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泛泛解释。因为制度永远是死板的,而生活是实践的,老百姓是很聪明实际的,往往有自己的策略。基于此,我一直在思考背后隐藏的信息。尤其是在很多故事中,讲述者明确告诉听众,岳父是个员外、富翁,说明家境颇为殷实,往往是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大女婿和二女婿通常是文官、武将、举人、秀才等所谓的中上层统治阶级。由此,我就更加怀疑传统观点的解释力,并有一个大胆的推测。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傻女婿”会不会是三女儿自主择偶的结果,其所体现的憨厚诚实、踏实能干、对老婆专一顺从有没有可能是民间女性择偶观的一种表露。
病理结果 27只大鼠于四氯化碳注射模型制备中死亡,2只大鼠于麻醉时死亡,最终31只大鼠成功完成磁共振检查及病理学检查。其中病理分期为正常的10只、轻度肝纤维化10只、重度肝纤维化11只。HE及Masson染色分别显示汇管区无纤维化(F0),汇管区纤维组织轻度增生(F1),汇管区-中央静脉间桥接纤维间隔形成(F3),早期肝硬化、肝小叶结构紊乱、纤维间隔形成(F4)(图2)。
教师提供了耐热性Taq酶发现、同功酶分子结构特点等材料,帮助学生理解生物如何依赖环境、适应环境,从分子水平上分析进化的本质就是生物大分子物质的演化,帮助学生形成生命基本观念中的“进化观与生态观”。
四、女性研究者和资讯人的对话:社会性别制度与人类情感力量的抗衡
“互主体性”是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提出的,是他反省民族志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传统民族志往往是人类学家自己的一种解释范式,但实际上,“文化即阐释,事实也是如此,事实是被制造出来的。每一种文化事实都可以既被人类学家,也被其持有者,赋予多种解释”。因此,田野作业中人类学家与资讯人对文化的多重解释,展现的是一个经文化调适的世界,是编织的“意义之网”。在这里,人类学事实是跨文化的,资讯人将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世界客体化之后呈现给人类学家,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存在建构不充分,有交流中断、爆发导致断裂的危险。他指出,田野作业需要理解、分析资讯人,因为人类学家与资讯人是平等的实践主体[6]145-146。换句话说,资讯人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与研究者互动的主体。
第二次调研,我直接和第一次见过面但交流不多的霸王鞭新生代传承人赵姐取得联系,准备以她为据点,展开深入调研。这是一位50岁的女性,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娘家婆家都在本村,人脉关系广泛,在村中有一定的威信,热爱文艺活动,是村子的会计兼文化管理委员,是被着重培养的下一代传承人,目前由她主要负责村落霸王鞭表演队的各种活动事宜。虽然她也具有政府人员的性质,但实际上她的日常活动圈主要在村内,她更多地以村落民俗精英的身份与村民、外界交往,所以和前者不能等同。果然,这次的调查因没有上级领导的在场而显得格外轻松随意,我们彼此好像都更加真实、更加亲近。
对于《师说》中“道”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含义的英译相对容易,因为两者皆是一般意义,容易在英语中找到一种甚至多种对应的表达。
自然而然,我们之间的交往有了很多个人层面的沟通,她问我家庭、工作情况,我问她孩子、老公情况,最后共同发出“女人想做点事情要付出更多艰辛”的感叹。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因为同为女性、同为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的妻子,以及同为“公家的人”等多种因素很快拉近,我问她从艺的经历以及进入村落领导群体的前后始末,她陪我访谈70多岁的教书先生、帮我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通过她,我得以接触到村落更深层次的生活和文化、更复杂的基层政治,理解了民间艺术传承的特殊乡村场域,切实感受到村落社会在国家政治话语背景下不断发生的变迁,以及对民间艺术演变传承的渗透。当地民间艺术霸王鞭跌宕起伏的命运就是一副新中国成立、发展、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她身上,我触摸到了一名乡村女性如何通过联姻,又是如何凭借娘家和婆家的影响,以及自己的积极努力成长为村落社会的精英,并凭借民间技艺在与外界广阔领域的交往中不断累积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本。据此,我对民间艺术传承的乡村社会结构和规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当然,我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使我不时清醒地意识到她对我的影响和潜在的羁绊,因此我也在力求摆脱她对我的制约。我利用在田间村头观瞻族谱碑的契机,和村落里对此有兴趣的老人聊天。他们对村落文化的历史有着清晰的记忆,抚今追昔,他们对村落文化的发展有不同的,甚至“刺耳”的声音,这可能是前者并不愿意我听到的,某种程度上,她也把我视为“她”的研究者,她不太愿意我和一些她认为“不懂”的人打交道。事实上,围绕村落传统文化的发展承传,内部似乎存在着至少两股意见并不一致的暗流,虽然后者在很多时候处于被遮蔽、失语的境地,但谁知道什么时候这股力量会不会爆发出来呢?
回顾这次调研的经历,我感到收获颇大,内心最惬意的就是良好融洽田野关系的建立和持续。我把原因归结为女性研究者顺应社会性别制度的主动作为。在女性研究者的田野中,女性的细腻温和、柔弱形象、亲和力本身容易获得访谈对象的信任和好感,特别在面对女性访谈对象的时候,同性相惜,彼此更容易沟通、理解。比如上述我在和女性传承人的多次交往中,坦诚相待,告知她我的身份、研究用途、家庭情况等,并通过礼物馈赠形成了比较融洽的田野关系。她给笔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在交流中她有这样的表述,“(笔者)学历这么高还有家庭孩子,还愿意来我们穷乡僻壤调查,佩服你(笔者),能给你帮上忙就中”。她的认可、接纳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
其实,尽管同性之间易于沟通,但和异性之间的交往也并不总是困难重重。我后来多次和传承人张大爷、李大叔联系,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史非常感兴趣,他们也总是第一时间和我分享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好消息。
总之,和不同性别、年龄、身份的访谈对象田野交往的过程,给我留下一个最为深刻的印象,即和“他者”打交道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与他人交往沟通,抱着真诚、谦虚、和善之心,你也将得到他人的真心。“感情是文化沟通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带着深厚感情进入田野的人类学家一定比例行公事的人类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当地人。因为情感是其文化经验的一部分,可以促进对他者文化的更深理解,并由此促进互主体的沟通。”[7]人类文化的不同并不代表心智的差别,人类学家研究“他者”的文化就是为了实现不同文化的人群无碍畅通地交流沟通,打破狭隘的文化藩篱。在文化认知的基础上,训练有素的研究者通过深入持续的田野作业,以及清醒的反思改进,能够不断揭示和呈现人类基于“互经验”之上的“文化的真实”。
参考文献:
[1]乔健.漂泊中的永恒[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2]刁统菊.女性民俗学者、田野作业与社会性别制度[J].民族文学研究,2017(4):63-70.
[3]范可.自我的他者化: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反思[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6):49-55.
[4]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邵京.田野无界:关于人类学田野方法的思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5):61-64.
[6]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张小军.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概念反思[J].民族研究,2014(4):49-57.
MutualSubjectivity:ReflectionsonFieldWorkinPost-modernContext——Field Experience of Young Female Researchers in Rural Community of Central Plains
LIU Chunyan1,2
(1.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Lanzhou 730030,China;2.Pingdingshan College,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experience of Henan folk stilts performing the bullwhip,this paper reviews and reflects on the field operation methods of folklore anthropology.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hannels for official introduction into the research community are convenient,but researchers need to be sober about the constraints they are facing;the field process is complex and changeable,and researchers need to respond flexibly to the situation;fac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researchers should consciously use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subjectivity to control field work;and women's research should be monitored.For the field work of female researchers,compared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gender system and the counterbalance of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strength,the more frequent state i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Keywords:Field investigation;reflection;mutual subjectivity;female researchers
doi:10.3969/j.issn.1673-6060.2019.07.001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060(2019)07-0001-07
收稿日期:2019-03-27
基金项目:2018年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非遗’保护视域下的河南叶县霸王鞭传承策略研究”(SKL-2018-989),主持人:刘春艳;2018年度河南省社科普及规划项目“叶县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1008),主持人:刘春艳
作者简介:刘春艳(1982―),女,河南叶县人,西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2018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学与文化研究。
标签:田野论文; 霸王鞭论文; 研究者论文; 文化论文; 作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论文; 2018年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非遗’保护视域下的河南叶县霸王鞭传承策略研究”(SKL-2018-989); 主持人:刘春艳2018年度河南省社科普及规划项目“叶县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1008); 主持人:刘春艳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论文; 平顶山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