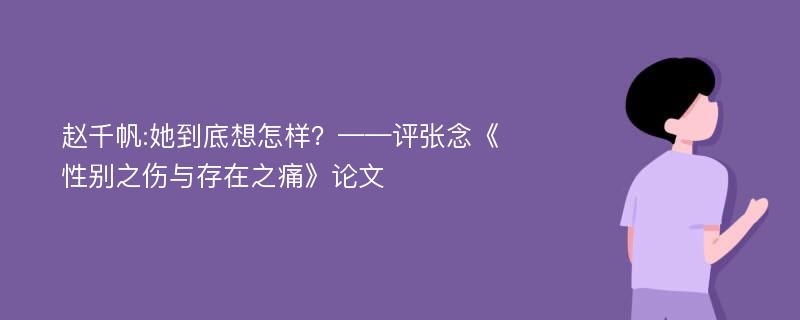
对女人特质的颂扬包藏着对所有秉承这种特质的人们的侮辱。
——阿多诺《最低限度道德》
提防那些令人陶醉和迷离的疼痛……
人们所施加的疼痛,比他们所遭受的疼痛更实在。
——尼采《晚期笔记》
一
“你到底想怎样?”——常规异性恋关系中男女发生争执时常常出现的这个经典疑问句,标示着故作镇定的男人惯用的一个防守姿势。在无法回答诸多具体质疑的时候,男人有时会突然发起对日常关系的形而上学式逆袭,其潜台词是,女方所有外在攻击或质疑,不论巨细,背后无非隐藏着一个指向 “到底”的问题。他以此来拒绝 “表面上”细节的纠缠,在快速揿动按钮抹掉可疑短信的同时,以退为进,试图把问题引向两性关系的终极方向:放过我衣领上的口红,让我们讨论一下这段关系的本质吧!
2.提倡绿色出行,提供创业新思路。节能减排是我国一项重大工程,不少企业为我国绿色出行和节能减排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滴滴出行”、“共享单车”等为我国减少碳排放量做出不小的贡献,也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新思路和新想法。全面健身,绿色出行是我国近年来人民探讨的热门话题,这为大学生提供创业新路径,从绿色出行和全民健身出发,寻找商机的同时,为我国的绿色发展也贡献不小的力量。
用尼采的话说,这是在注射形而上学的麻醉剂,“我们关系的本质”这种抽象命题散发出的思辨荷尔蒙的芳烃味,有时竟能愚蠢地安抚住伦理上的炎症。尼采还说,男人,这时作为一个总是发现自己快编不下去的苦修教士,在发出这样一个形而上学反问时,实质上是虚弱而焦躁的。我现在就明显感到这样的虚弱和焦躁,在我忍不住对这本书的作者发出这般疑问的时候:“她到底想怎样?”
她想要的,难道不就是——或者可以转译成——一个绝望女友的追击吗?
李秀花见他这个样子,嘴里嘟囔着:“你看你,这事有什么想不开的,婚姻是婚姻,爱情是爱情,我总不能永远不找对象吧?”
“使得‘意义王国’中的无权者获得某种概念性形象……”封底的作品简介上写着,“我究竟在这段关系中算什么?……”
“女性主义的哲学气质”开篇的标题说:“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像女权女人那样去思考”,末章的标题发誓:“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的每一个字了!”
我翻到最后,几乎觉得可以断定,这些表述里藏着作者 “到底”还没摆脱的“女性欲望”:她并不是真的着迷于黑格尔留下的“女性迷踪”或拉康“女人不存在”的预判,她想要的无非是——男人们防守反击的一招到这里才图穷匕见:
“没有什么女人,不要拿她说事,你无非是无力构建你自己的生活。”
——以上不只是戏谑之语。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它想测试对一本好书进行极端读解的可能性,如本雅明所说,批评必须尽量尝试摧毁作品。在这篇书评里,我将尝试质疑张念近年高效的学术产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倾向。这个倾向主要就体现在全书主旨—— “对女人问题进行哲学表述”这一不太“哲学”而过于“女人”的表述上。
这种说法把“哲学表述”当作对被表述者——无论是女人问题还是其他的真正严肃的对待(犹如婚姻之于资产阶级妇女):似乎只有通过哲学表述,女人才被提升到真理和存在论的水准,得以“重返本体论现场”;通过哲学表述, “东西方哲学的起源处”的女性元素才得以显现,并在其后的哲学史中草蛇灰线地不绝如缕;通过哲学表述,“性别伤口”被标识为“意义的发生场所”为女权女人提供原动力,鼓励她争取“伴随着差异性而不断生成”的女性自主,“经由无目的的爱去抵临他者”。这是一个方面。
2.3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对照组中有2例出现肝功能损害,3例出现白细胞减少,4例出现甲减,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8.13%;观察组中有1例出现白细胞减少,有1例出现肝功能损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另一方面,经由与女性主义的联姻,哲学似乎也获得了新生。“女性主义在哲学上的回应方式,就是改变提问方式”[1],随着哲学对女人的重新发现/发明,差异和分裂被带入哲学Bachlor的苦修秘室,在这里,女巫与哲学家共同“召唤陌生的真理” “邀约未曾来到的事物”,将洞穴变为朝向未来哲学的子宫,合力造出“激进的现代人”,在末章“余论”中作者为女性主义哲学给出这样的期许:
“当下,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紧急状态,如何能够在被意识形态渗透的地方,重启关乎未来的哲学思想,并重思服从的自由与显示的自由,秩序和变化、安全与恐怖的辩证,避免形而上学的暴力,直视现代性的平庸之恶?欲望革命与女性主义需要探讨的正是:如何成为激进的现代人!”[1]285
(1)分隔土体。可采用土工膜等防渗隔水材料,或者非分散性黏土及改性分散性黏土,将低溶盐水和分散性黏土隔离开来。
这场从相杀走向双赢的联姻构成了本书的出发点:在最基本和关键的哲学层面处理女性问题,同时从女性视角和概念形象出发,重述哲学史上的关键问题,进而构建一个相对于其他与性别相关社会和政治理论更具有根本性和超越性的层面,以重新看待性别差异、平等、身份政治和解放的重大议题。
“不管男性之于身体的体验如何,身体之于女人就是她的第一处境,女性经验奠基于身体经验,在与世界最初相遇的那一刻,之于身体的领悟首先应该表述为身体是我,这样的陈述是前主体的,就是说在没有神性根基或者先验规定的情况下,存在的雏形就是身体,女性意识也就获得了一个不同于意识哲学(男性意识)的逻辑起点,就是说不存在什么抽象的肯定。”[1]109-110
以此观之,在张念这里,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概念化也伴随着对痛苦的刻意品味和提炼,而且跟尼采一样,都走向对生存的美学辩护。在第七章中提到安提戈涅的第二副面孔的时候:
以上是对结构的初步勾勒。作者的语言带有今日罕见的几乎在肉身上可辨识的奇异节奏感,冒着语法支离的危险完成的断句方式很有冲撞力。推论过程中在句法层面都时不时出现让人始料未及的急转或升降,有时让人有不完整和没头绪之感。但在总体上,跟问题意识如影随形的辞气仍然是连贯而有力的,使这些“突转”总会带来“发现”。对安提戈涅命题的穿越式追踪,对尼采和魏宁格的反客为主的援引,对于时新的政治哲学和技术哲学议题的连消带打,说明她在理论搏斗所必需的注意力、距离感和力度把握上都超越了大部分今日的哲学写作者。
在欣赏了这些优点之后,我们还是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在作者本人所要求的那种 “哲学”的、“赤裸”[1]277的层面,以一种“打破僵局”和“爱”的方式提问:
“她‘到底’想怎样?”
神经系统 人体的神经系统包括大脑、脊髓和遍布全身的神经。要是没有了神经系统,我们就看不见、听不到、闻不到、食而无味,也自然感觉不到疼。神经系统由不计其数的细胞构成,这些细胞被称为“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都含有树突和轴突—— 树突相当于一个传感器,而轴突则连通着脊髓。
二
如前所述,作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将性别问题还原为(也可以说是提升到)基本概念或原初动机的层次,并从这些概念和动机在经典哲学家文本中的具体展开方式中找到裂缝或缺失,然后继续进行编织和推衍。在之前的《性别政治与国家》中,作者的理论概括还跟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的历史语境,跟纷繁而沉重的妇女经验保持着联系,在这部书里,一切皆是从概念到概念。作者艺高胆大地以一种跳跃的方式展开她的概念工作,从存在学、知识论到社会理论、政治哲学,从对思想史疑难的再审(安提戈涅问题),对经典文本的重述或阐释(《蒂迈欧篇》或 《精神现象学》),到对特定方法的再检验(存在主义或精神分析),在转换阵地和战法的同时,她并没有觉得需要首先标定自己的论证本身在方法论或基本概念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很先进的哲学写作方法,同时也承担了风险。作者在论述时,不得不自己锻造出一条“到底”的线索,以把不同层面的论述收束到一个可以相互参照勾连的统一框架中来。这个线索,在我看来,就是“女性意识”概念。
“经由弗洛伊德和德勒兹理论的提示,我们就获得了社会抵抗之外的另一种抵抗,就是说基于性别差异之上的女性抵抗,试图直接面对存在之伤,身体之痛。”[1]254
这个论断是错的。胡塞尔就坚持现代科学跟希腊—欧洲的血脉关联[3],海德格尔进而把希腊—德意志的哲学血统铆定为一种特定的语言本质主义。《启蒙辩证法》的作者们则从另一个方向,将犹太人在现代欧洲的命运视为启蒙理性逆转的一个证据。
因此,指责黑格尔为什么会让女性在意识朝向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提前出局,在我看来更好的做法是重新检讨他的“意识”概念本身的缺陷,换言之,一开始就要把性和性别问题放到对自我意识的考察中去,这样才可能引爆意识哲学的根基:意识发展过程中的自性差异问题。尼采和魏宁格关于女性的佯狂般的极端言论的真正标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康德与萨德”命题的外科手术式的解析,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但作者的处理方式却是另起炉灶,提出“女性意识如何成为辩证法中的斗争环节”这个问题。然后,再把尼采和魏宁格当作厌女症——主体理性自我批判失败的产物——的典型代表,顺便把康德也列入共犯之后,作者赞同了《启蒙辩证法》的论断,即遵循合理化法则的思维机器已经无能处理性别问题,所以,女人需要摆脱既有性别模式的“绑架”,在意识的辩证法历程中为自己制造一节“女性意识”专属车厢。[1]86-87
那么,什么是“女性意识”呢?作者先下了个初步的定义:“一般来说,女性对自身经验的反观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女性意识”,然后赋予这种意识以一种“在‘我思’与‘我在’之间” “与人的自异性和平共处”的特殊地位。[87]之后又说,女性意识有一个更原初的 “逻辑起点”[1]109,它 “比自我意识早熟”,“先于那个被对象化的 ‘自我意识’”[1]111。在第三章关于存在主义的部分里,作者把女性意识进一步归结为女性对其特有的身体处境的体认,并冒着陷入一种肉体形而上学的风险说道,这种体认就是一种身体性的经验,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有能力包容一切差异、并在这种包容中实现自身的女性的自我理解,其原型就是Khôra,晃动的子宫,是潮汐起伏的肉身:
全书可以这样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导论到第四章是哲学史重述,虽然多有跳跃穿插,但脉络相对清楚。作者挑选了欧洲思想史上五处出现女性论题的重要节点,它们分别是:①经由德里达解构过的柏拉图在 《蒂迈欧篇》中的Khôra[2]概念;②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中对于女性在伦理的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的探讨;③启蒙辩证法中理性批判与女性奴役命题的复杂关系(同时评论了尼采和魏宁格将理性批判和厌女立场结合起来的激进言论);④波伏娃基于存在主义的处境意识对“第二性”和女性经验中的自异性的揭示;⑤精神分析对女性和 “石祖母亲”(作者表述为“阳具母亲”)所处的既源始又缺失这一悖谬性地位的讨论。
这样,我们被带回到某种意识与肉体合一的境界,只不过,这次不是意识节制了肉体(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之爱节制了情欲),而是相反,肉身统摄一切。黑格尔要女性满足于爱和家庭,把政治留给男人,而作者认为,恰恰是这种带着肉体颤动的意识才能够承担普遍的生命政治主体:
“因此,生命政治在某种层面就是女性主义政治,女人这个词意味着她们几乎反对所有的制度,……反之,女人一词就代表着一个被压抑的由无意识所决定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她们就是艺术,就是图像,就是生命政治的生命体。”[1]279
这里作者用的是跟黑格尔“爱作为伦理的统一体”几乎同类的语汇,只不过“精神无限的泡沫翻涌”换成“血之花的绽放”,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人肉版或女主型的绝对精神。
摘星楼外的空地,方圆数二十余丈,平坦如砥。其时药圣孙思邈、书圣颜真卿、画圣林白轩、琴圣苏雨鸾、棋圣王积薪、乌有先生、子虚道人七位良师益友已按北斗七星的星位立在场地中央,孙思邈在中央占天权位,天枢颜真卿、天璇林白轩、天玑苏雨鸾,为斗魁;玉衡王积薪、开阳乌有先生、摇光子虚道人,是为斗柄。颜真卿持笔,苏雨鸾抱琴,其余皆凝神空掌,平心静气,起手如仪,静候一边已站成一线的袁安、上官星雨、李离三人。三人赤手空拳,袁安在前,据天位,上官星雨在中,据地位,李离断后,据人位,天地人,是为三才。
在兜了一个大圈之后,似乎可以这样说,所谓的女性意识——在男权的意识哲学中失落的女人的身体经验——恰恰是经由作者指控为男权的自我意识的赋型才获得自我理解的,这种自我理解——以弥补缺失的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她本来要指控的那个赋型过程。批判没有推进到跟批评对象的短兵相接,却变成双边立场—— “女性意识”VS男权哲学的“自我意识”——各自的反向强化。用传播理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争论中的“极化”现象。极化的后果是,为了维持住相反的立场,她不自觉地分有了意识哲学本身的本质主义和原始主义倾向,并被对手的立场同化。
2.2 影响因素分析 将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行为问题有关且在统计学上有非常显著意义的因素包括:母亲文化程度、父母关系、管教态度、管教方法、社区环境、父母对子女期望、学习成绩、社区环境共8个因素。见表1。
这里有必要指出张念一个隐蔽的关键操作。她当然知道,传统女性的自然状态是男权的自我理解向外投射的产物,但是,她在拒绝男权意识以赞赏和规范性话语塑造的这种自然的女性理想的同时,却以一种近乎受虐的方式,迫使这些形象在哲学概念中升华,将之施洗命名为女性经验,进而以此为武器去反击,却没有想到,这倒戈一击可能是正中下怀——正如她在美学部分的探讨中也察觉的,对抗可能是“迷狂极乐”的[1]228。意识哲学本来已经耗尽了的本质主义话语,现在凭借这个“血之花”的反哺,重新在某种酒神式狂喜中复活,并变身为一种新的自然形而上学。其核心概念,就是据说女性所特有的“疼痛”和“创伤”。
抽象化的概念必然使其所概括的经验偏狭。一个表现就是,作者把女性问题视为哲学最独特的、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裂隙(这背后是怎样一种阳具母亲的自我想象?),并将之跟种族问题切割开来:
“至少还没有某个学说在显示黑人或者少数族裔与认识论的切近关系,而‘女人’概念却能够被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们所运用。”[1]83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本来就没有“女性意识”的说法,女人、家庭问题只是作为伦理问题才出现和被讨论的,这时自我意识才要发展出自身与原始的“精神本质”的真正差异,性别和国家中所包含的矛盾由此才要获得其客观表达。从另一方面说,男性和国家也只在这个时候才获得其现实性,并马上因为这种现实性的自我矛盾(国家总是建立在以父子兄弟相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少数男性对大多男性的宰制)而毁灭。所以,这时不只女性是主体半成品,男性同样也是。
三
偏狭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把女性经验跟少数族裔的经验切割开来的同时,作者必然会去描述一种在哲学上有独特意义的“受难”经验,只有这种经验才能通向“哲学的紧急状态”,只有在女人痛苦里人才能回到“祼身状态”:
“不正当的私人痛苦,除了单独性地隐蔽地被心理治疗接管之外,现代性作为症状,已经构成了人们心理命运的共同体,在女权主义这里被放进了哲学的紧急状态之中。因此,女权主义所释放的力量正是将人遣返回裸身状态,那被抑制的自然元素与权利正当性的冲突现场,正是女主体的现身之地,而自然正当的安全不正是要穿越危险之境才能善了的吗?”[1]283-284
把“裸身状态”跟 “女主体”并置的做法复制了那种最常见的性凌霸套路,将女人的身体以神圣禁忌的方式切割为供窥淫者争抢的祭余。这跟“心理命运的共同体”的说法完全自相矛盾。“被抑制的自然元素”绝不只是女人,它还包括有或自以为有缺陷的女人,包括一切可能被歧视的族裔和年龄阶段的女人和男人,包括不同性向和身体障碍的人,包括动物,而最为关键的是,最受压抑的自然元素,恰恰就在压迫者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癖好中,在那些“强人”的施虐欲望中,“不正当的私人痛苦”才达到其阈值。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萨德——作为向“她们”施虐的“他们”的代表——的评论中写道:
“她们可以生存,却也可以被灭绝掉;她们的恐惧与软弱,是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亲和性,是赋予其生活的特别因素。这种情形使‘强人’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必须在尽力异化于自然的过程中付出自己的全力,同时也必须经常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他们只有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他们自己不敢发出的死者的呻吟时,才能与自然一致起来。”[4]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拒绝为——萨德笔下那些呻吟的女人们—— “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亲和性”直接加上解放的和声,因为这种亲和性——今日我们可以在无数对Me Too报道的共鸣中感受到——作为施虐者饮鸩止渴的药引,本身就是“强人”主导构建起来并如吸血蝙蝠般赖以为生的,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的不自然:“据称是自然造物的女人就是那个把女人弄得不自然的历史的产物。”[4]132
旅游电子商务的不断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旅游电商企业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但是大多数电商企业的盈利方式不清晰,只是一味的追寻多元化方向发展。一些新进的电商企业为了吸引游客,往往会通过降低价格的方式打开消费者市场,大打价格攻坚战,使得旅游电商市场混乱不堪。即使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旅游电商企业,如携程网,虽然在机票预订和酒店预订这两个方面有着不俗的业绩,相对来说市场定位十分清晰有着自己的发展重点,但由于一些新进入该行业的电商企业利用价格战抢占市场份额,导致其盈利能力不断下降。
对这种可能越是痛苦和耻辱才让人们觉得越自然的经验的一切直接援引,都难以避免沾染着某种施—受虐的潜在淫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会极端地认为:“对女人特质的颂扬包藏着对所有秉承这种特质的人们的侮辱。”[5]换言之,任何对受压迫者的赞美(尼采认为同情即已暗含这种赞美)都在强行赋予他们某种其自身本来可以不是的形象并以此取“乐”;受压迫者对自己形象的反观亦然,而且更多了一层自毁倾向。对痛苦的最前卫的展示可能变为对造成痛苦的最保守话语的迎合。[6]
这种极化现象常常伴随着概念的空洞化和抽象化。作者对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描述,即使用了“迷踪”“暗夜”“血”这样的隐喻,或者援引了痛经、生育等生理现象,指涉着卵巢、子宫和乳房等解剖学对象,因为过于信任语言跟经验的同一性关系,所以仍然是抽象的。
这个话题集中出现在我认为是全书文眼的第五章“性别伤口是意义的发生场所”一节。作者先是引述了齐泽克,指出性别差异可以视为一个事件性的创伤,人类的生物学身体经由性别分化而导致身体稳定性的丧失,进而给人类文化内部留下剧烈冲突的伏笔。然后,作者认为这个冲突在女人身体上才被“更为明显地表征着”[1]164,如同神圣的病人一般,女人因为这种表征而受命成为真理的暗夜守护人。女性主义者,在拒绝了歌德的“永恒女性,引领我向上”的模范表白之后,一转身接受了德勒兹的“女人自身就已然生成为一个秘密”或齐泽克的“只有女人才能体会到大他者的快感”[1]168-169的另类恭维!但这两种对女性形象的指认都是非历史的。
正是依据这种去除了历史语境的女性经验的概念,在第八章谈身份政治时,作者又一次表示不屑于加入族裔、阶层、性取向的 “孩子气的边缘竞赛”[1]248——她因此批评巴特勒仍然只是满足于“向已经存在的被称为常态的合法性系统靠拢”[1]251,女人从自身的自然欲望出发—— “正如女孩欲望的形成与权威—社会无关,其本身就是性的或性别的”[1]254——就可以直接进行抵抗了:
作者把黑格尔视为在现代理性主义传统中 “真正将 ‘女性意识’纳入哲学思辨”的第一人[1]47,但这第一次亮相中女性意识就如头牲之祭般被牺牲掉了。《精神现象学》描述的那个在与他者的斗争中获得自明性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回避了性别差异中包含的他者因素,另一方面,当它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作为“伦理的自我意识”外化为伦理制度(家庭和国家的法权制度体现的“真实的精神”)时,又把女人所代表的“无意识的精神”牺牲掉了。然后,在《法哲学》中,作者引用了第158节谈及“爱是伦理的统一”的著名段落,指出黑格尔强行用爱来化解性别意识的差异,抹杀了爱欲辩证法中 “殊死搏斗”的一面,试图把女人的意识发展永久性地固锁在婚姻关系中。她从这种做法中看到,黑格尔只赋予女人“主体性半成品”的地位。结论是:“可见一位伟大的辩证法大师,其逻辑的力量之于女性问题,显得如此疲弱与荒唐。”[1]56-60
这种对疼痛与创伤的“直接面对”必然带上了上面说的那种自毁倾向,因为它会把具体的、各有来历的苦痛经验离析还原为某种混浊而乖张的心理冲动或身体反应。本书前半部分说到启蒙方案中暗含着“焚毁女人”的用意,而后半部分则以积极的口吻描述女人“焚毁自身”以抵抗,就是这种自毁倾向有意无意的暴露。
这种倾向背后就是尼采提到的那种近乎宗教的嗜痛症。尼采看到,疼痛有一种特殊的 “提升”力量,它比快乐“更实在”,快乐总是倾向于夸张和欺骗,而疼痛则有种令人欲罢不能的清醒性。他提醒我们[7],我们会更加信任自己能够 “施加”的痛苦的实在状态并陶醉于对它的反复确认中。这个“施加”的过程,就是哲学用概念之刀来切割活的经验的时刻。在形而上学的根源,或者张念喜欢说的“本体论现场”,尼采看到的是一种对痛的陶醉和对伤口的维护。犹如通过刺激神经而迫使自体大量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思维迫使我们在抽象思辨中获得自我陶醉。
接下来第五到第九章的线索和议题划分并不清晰,虽然这倒也没有影响作者文采和洞见的发挥。关键词似乎是 “女性意识”和 “差异”。第五章 “思考差异,成为女人”或许可以看作全书的枢纽,尤其是“性别伤口是意义的发生场所”一节有点题之功。然后作者似乎是想从思想史的讨论转移到对具体的理论问题上。第六章应该是基于此前对女性经验和处境的特异性的论证去质疑或“抗辩”传统上一些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立场,攻击范围涵盖了从自由主义传统到阿伦特、斯特劳斯和施密特的广泛谱系,似有神来之笔,比如对施密特的凌空一击—— “……经验的 ‘多’以及哲学之母就被秘密扣留在纯粹性的理论大厦之中,而这个内部的‘敌人’,其政治性又该如何处理呢?”[1]203——就令人拍案。第七章的讨论延伸到历史哲学和美学,“血腥样本”[1]220和 “血之花”[1]228以下的表述或许会帮助读者深化对第五章中提到的“性别伤口”和全书主旨的理解,对安提戈涅的三副面孔的描述可能是全书带来最大阅读快感的部分。跟之前和之后相对具体的共同体、身份政治和解放论题相比,这一部分的论述既尖锐而又有些游离。第八章再回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回应了当前从性别切入身份政治讨论的热点,作者对欧美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有所引述和批评,尤其质疑了比如朱迪·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基于跟权利相捆绑的“身份”而不是跟欲望与爱相关的更富于生产性的“差异”,因此损失了女性主义应有的激进性[1]256。第九章作为最后一章,按惯例推进到未来的向度,在渐渐增强的呼告式语气中谈到“革命”和“解放”,同时接回了此前在谈 “创伤”和 “血祭”时反复出现的身体和爱的动机。解放的范式——如“作为他者去尊重他者”(伊利格瑞语[1]267)——仍然只能止步于抽象的概念。不过意旨大致还是明确的:女性特有的经验中蕴含着保有差异(使二永远不会混同于一)的奇异力量,足以支撑激进民主的游戏空间[1]268,并通过超越既有束缚的先在行动(但行动的主体并不明确)引领解放政治的发生[1]280。
“作为‘血样本’,发挥美的功效,即惊诧以及净化,以便修复人从自然之中诞生或坠落时的伤口,‘美’依然被征用为庇护所;安提戈涅能够‘道成肉身’吗?一个鲜活的面孔,在人之中?在社会秩序之中?”[1]235
智能节点接收到检测模块采集的数据后与节点内存储的值相比较,数据异常会自动发送命令至控制模块,例如在温室大棚中,控制模块控制排风扇、加热器、遮阳网电机、喷淋设备、CO2发生器等设备进行空气温湿度、光照和土壤温湿度的调节,同时上发至监控终端指示环境参数和设备工作状态。
与尼采不同的是,张念使用了发问的口气,她想要的是一种“既是又非的陈述逻辑”,以“释放出语言凹透镜之中被抑制的折射物”,并相信,这种陈述中可以绘制出安提戈涅的第三副面孔:“这张面孔不再神秘,不再沉默,可以按照其自身的方式开口说话。”[1]235这样,问题从美学延伸到了语言哲学。
四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疼痛、表达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醒我们注意,这里隐藏着语言起作用的多种方式,语言并不只以一种唯一的方式传达思想,否则我们一定会面临疼痛既可说又不可说的悖论。疼痛,正如所有感觉,不是某种确切的东西,但也不是“乌有”,而只有在我们觉得无可陈述时,这种“无”倒是作为某种“有”在起作用。但一旦将之说成“有”,陈述就会复制出难以禁绝的伪装,在语法的强制下,增生出难以确定的姿态、言辞、信念。[8]
这一考察或许可以帮我们理解张念其实一开始就给出,但后来并未鲜明贯彻的那种 “是/不是女人”[1]28自反式姿态。这个姿态跟维特根斯坦的见解是相通的,也是一种以语言游戏的方式绕开概念陷阱的尝试,它事实上对我之前指出的她在概念化和抽象化时的用力过度实施了制衡,也暗中抵消了将“女性意识”概念绝对化的倾向。照我的看法,这个自反的姿态实际上可以更连贯地引入更进一步的女性主义哲学的自我批判,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不用某种“概念帝国主义”的方式把痛苦和创伤总体化和抽象化。这里需要的是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的策略—— “对概念祛魅”。不是让无权者获得“概念形象”,或构建适合于“女主体”的新概念,而是反过来,要让已有的概念在那些伤痛面前破裂、变形,从而让主观的感受获得客观的表达:
“让苦难说话,这需求是一切真理的条件。因为苦难就是主体所要担负的客观状态;主体当作最主观的东西来体验的,它的表达,是被客观地中介过才传达出来的。”[9]
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气候讲解的时候,可以对学生进行提问,让学生思考自己所在地区的气候特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降水是怎样变化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可以积极主动的进行问题的思考,能够更好地理解气候特征的相关知识。
如果我对这段广受女性主义者引用的晦涩之语理解正确的话,阿多诺说的是:疼痛和创伤,作为主体最主观的体验,总是经由特定的历史境遇才为我们所知的,并因此成为客观的了:Me Too运动中那些看似空口无凭的指责之所以令人恐慌,就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种经验的客观性。但是这种客观性是被中介过的:所以,哪怕那些呻吟令我们汗毛倒竖,我们也有不将之直接等同于本真的经验的自由,我们也可以拒绝从中提炼出某种马上决定我们命运的政治契机,不用某种概念将它点石成金,变成抽象的口号。我们要做的毋宁说要把这个中介的过程持续下去,把那些痛苦所发生的情境,联结到性别差异以外那些更难以启齿、更触目惊心的中介环节中去,以助成最后社会性的“链式反应”。
在这篇书评完成之前不久,张念、我和两三好友之间有过一场关于Me Too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此。在我看来,女孩们的愤怒必须跟其他类型的社会苦难联结在一起,不然将神秘化为某种无常的怨恨,或竟反过来被加工成给“强人”助兴的药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不要尝试对疼痛做私人指涉,而是要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各种方式参与对痛苦的表达,这样表达和经验才能相互校正,最终,“你随着语言一起学到了‘疼痛’这个概念”[8]384。
要在女性问题上展开这种让概念与经验相互校验的学习进程,熟悉中国妇女解放史和当代妇女境遇的张念大概是最好的开拓者。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把张念这本书读作女性主义在汉语哲学中第一次通过概念“让苦难说话”的尝试。如果尼采的诊断是正确的,那么在我此前的所有质疑之外我必须承认,她的思考和表述所施加的痛苦确实有一种超乎我所能遭遇者之上的实在性,正是这种异质的实在性令我不安和发出那些虚张声势的指控。她所有的用力过度和一意孤行,都是一次辩证法冒险的开始,把我们带入那种陌生的清醒,开启出后续无穷的表达实验和学习进程,正如她在全书结尾所说的——这也是对“她到底想怎样”的最好回答:
“女权主义没有指路的习惯,也不创造什么新世界,并且拒绝历史目的论,拒绝意义象征系统和身体的分隔,穿透这个世界的幻象,她的位置在边缘,而不是可以看见的底层,为解放的任务不断刻写新鲜的标记。”[1]293-294
这样,任何一个学习经历都可以以一点放在图上。例如,传统的演讲(理论式、传授式、教师主导式)会在A箱内,而自我发现学习式的专题研习(实践式、发现式、自我主导式),为另外一个极端,便在B箱内。
注释
[1]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28.
[2]作者将这个词译为“切诺”;一般的译法是“子宫间”(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9页)或 “容器”([法]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A].陈永国译.见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66页注6).
在2004年水库除险加固二期工程建设时,由于自筹资金不到位,原设计的溢洪道安装橡胶坝项目并没有实施。水库设计兴利库容为1 315万m3,但由于橡胶坝未安装,最高蓄水位只能到溢洪道底板高程937 m,达不到正常蓄水位942 m,兴利库容不达标。从2008年除险加固工程完工至今10年来,城市供水基本能得到保证,农田灌溉由于灌区很大一部分还在使用机电井进行灌溉,对库水需求量还未达到设计需水量,所以权且可以维持,但随着地下水位逐渐下降,地表水需求量的加大,兴利用水将不能满足要求。
[3]“新哲学的奠基是近代欧洲人人性的奠基”,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3.
[4] Horkheimer/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ärung,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3,hersg.von Rolf Tiedemann u.a.,Suhrkamp,F.a.M.,1981/2003,S.132.
[5]Adorno,Minima Morailia,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4,hersg.von Rolf Tiedemann u.a.,Suhrkamp,F.a.M.,1951/2003,S.108.
[6]库切在剖析文艺界在恋童癖面前的恐慌时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在色情问题上,女权主义关于前卫运动的其他考虑,却选择了与虔诚的保守派交媾,一切都陷入无法解说的混乱。”库切.凶年纪事[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39—40.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李小树对一个女人表现出如此浓烈的兴趣,尤其是对画稿上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李小树似乎察觉到我在注意着他,他有意无意地咳了两声嗽,便伺机把那瓶马爹利酒攥到胸前。我看到他手背上的青筋开始还隐藏在他手皮子底下,等他的手逐渐用劲,那些青筋就陆续地从皮下蹦出来,像一条条贴在他手背上时不时涌动着的蚯蚓。
[7]Friedrich Nietzsche,Nachgelassene Fragmente 1887-1889,KSA 13,hrsg.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DTV/de Gruyter,1999,11[332],S.143.尼采著作全集(第十三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73.
[8]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1节以后,尤其是304节.
[9]Adorno,Negative Dialketik,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6,hersg.von Rolf Tiedemann u.a.,Suhrkamp,F.a.M.,1970/2003,S.29.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陈琰娇)
标签:女性论文; 哲学论文; 尼采论文; 意识论文; 女人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8期论文;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