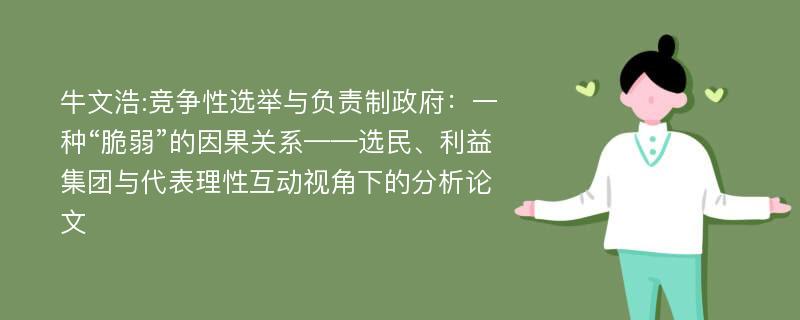
[关键词]竞争性选举;负责制政府;理性无知;有效监督;俘获
[摘 要]许多人相信西式民主制所采取的竞争性选举与一个对选民负责的政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因果关系。这种观念其实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在竞争性选举的制度条件下,选民对代表的决策行为以及代表候选人的竞选信息保持“无知”是合乎理性的选择。前一种无知将直接导致选民难以有效地监督代表,选举也就不能使代表有足够的动机对选民负责。而选民的这两种“理性无知”还会使得代表候选人接受利益集团的“俘获”更有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样,选举政府在许多决策中就会对利益集团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竞争性选举”实现“负责制政府”的条件很难满足,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脆弱”的。
西方社会和学界普遍认为竞争性选举制能够保证政府充分地对选民负责,选举政府能够满足选民的偏好,“将选民的利益放在心中”。这种观念被称作是民主的“佚名理论”(folk theory)。[注]Achen C., Bartels L.,DemocracyforRealists:WhyElectionsdonotProduceResponsiveGovern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1.其背后潜在的推导逻辑是,掌握决策权的代表与总统是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他们自然会关心选民的利益、选民的诉求,对选民负责,否则他们就会在下次选举中失去选民的支持,无法取得连任。[注]Franklin M., Soroka S.and Wlezien C.,“Election”,in Bovens M., Goodin R. and Schillemans T.(eds.),OxfordHandbookofPublicAccountabi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389.持有这种观念的人通常还会认为,相比之下,非经竞争性选举上台的政府就会缺乏对人民负责的动机。[注]广义的政府既包括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也包括由代表构成的立法机关。选举能否使得代表或者总统对人民负责遵循着大致相同的逻辑,所以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仅以“代表”来指称“政府”。但文章里的经验验证仍然涉及到关于总统的数据。福山甚至认为竞争性选举是现代社会实现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注][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5-316页。需要指出的是,福山所说的“负责制政府”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责任政府”,前者的主要含义是包括立法、行政机关在内的决策部门对民众负责。后者则主要是指狭义的政府,即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在“竞争性选举”与“负责制政府”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因果关系。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国内有一部分人也对上述观念及其推论深信不疑,这种信念使得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负责制政府的实现形式的探索是没有必要的,最终还是要走向西式民主。这样的观念不利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不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
事实上,上述信念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这种因果关系赖以成立的许多条件都是很难满足的。选民能够有效地监督代表是“选举使得政府对选民负责”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这一条件是难以满足的。在西式民主的制度条件下,规模庞大的选民群体在监督代表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集体行动困境”,这使得选民选择对代表的决策行为保持“无知”才是合乎理性的。当选民普遍处于这种“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的状态时,代表不回应选民的诉求就不一定会遭到选民的惩罚,而回应也不一定就不被惩罚,选民就难以对代表形成有效的监督,选举也就不足以让理性的代表有足够的动机对选民负责。
“选举使得政府对选民负责”能够成立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在代表候选人与利益集团之间不存在“私下交易”,因为这种交易的存在意味着当选代表在很多决策中会对利益集团负责,而忽视选民的利益。然而这个条件同样是难以满足的。要避免这种交易就要求代表候选人与利益集团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小于他们所投入的成本。但由于选民群体在选举代表时也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而选民个体在确定代表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概率又非常小,这些都会使得多数选民理性地选择对代表候选人的竞选信息保持无知。这种理性无知与选民对于代表决策行为的理性无知一起,又会使利益集团投入的资源能够有效地帮助代表候选人当选,也会导致代表候选人与利益集团的“交易”被选民发现并遭到惩罚的可能性下降,这就使得交易的收益普遍地大于成本。于是,代表候选人在许多决策中与利益集团达成交易就是合乎理性的,对利益集团负责是理性的选择。
本文通过对以上两点的详细分析试图说明,在现实的制度运行中,选民、利益集团与代表之间的理性互动将导致“选举使得代表充分地对选民负责”的条件很难满足,从而使得这个结论也很难成立。在“竞争性选举”与“责任制政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强,而是非常脆弱的。
实验组总体健康、生理功能、社会功能、活力、生理职能、情感职能、躯体疼痛和精神健康方面和对照组实验数据间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且P<0.05,具备统计学分析意义。见表1。
一、选民难以有效地监督代表
在竞争性选举制下,要想让代表对选民负责,选民必须能够有效地监督代表。[注]Guerrero A.,“Against Elections: The Lottocratic Alternative”,Philosophy&PublicAffairs, 2014,42(3): 136-139.所谓有效监督是指,选民能够清楚地知道代表有没有在决策中回应他们的诉求,一旦选民发现代表没有充分回应他们的诉求,就会在下次选举中以让代表下台的方式来惩罚他。可见,有效监督的一个关键是选民要充分地掌握关于代表决策行为的信息。如果选民对代表做了哪些决策或者这些决策是否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并不知情,则即使代表没有回应选民的诉求也不一定会遭到选民的惩罚,监督就会失效。这样,选举就无法保证代表充分地对选民负责。[注]对于那些已达到连任限制的代表而言,“改选”惩罚是不成立的。限于篇幅,这类代表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纪昀笔记故事:一高官死后在阎王那儿控诉门生故吏忘恩负义。阎王斥责:种桃李者得其实,种蒺藜者得其刺。您当年所欣赏的都是依权附势之徒,现在权势倒了,反以道义去责备他们,岂非凿冰求火!当下,许多腐败官员在位时结党营私,被查处时又互相揭短撕咬,读此当如照镜吧。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选民还是更有可能因为面临“集体行动困境”而对代表的行为保持无知,从而难以有效地监督代表。具体来说,选民对于代表的无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行为无知,即对于代表做了哪些事情,选民可能是不清楚的;二是议题无知,即对于哪些是待决的政治议题,选民可能也是不了解的;三是广义的评价无知,即对于在一般意义上代表是否做了一个好的决策,比如促进公共利益的决策,选民可能是没有判断能力的;四是狭义的评价无知,即选民甚至对于代表所做的事是否有利于选民自己也不一定能够确定。[注]Guerrero A.,“Against Elections: The Lottocratic Alternative”,Philosophy&PublicAffairs, 2014,42(3): 145-147,140.相关的调查表明,美国的选民确实是普遍处于上述无知状态的。比如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70%的美国公民都不知道国会已经增加了医疗保险的处方药福利,而这是联邦预算在过去几十年增加幅度最大的新补贴项目。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仅有34%的选民知道“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是由布什政府而非奥巴马政府颁布的。仅有39%的选民知道“防卫支出”是联邦财政中最大的一类可自由裁量的支出。[注]Somin I.,DemocracyandPoliticalIgnorance,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2.又比如,美国人普遍地高估了用于对外援助的财政支出金额,以至于很多人都错误地相信可以通过削减对外援助资金来减少财政赤字。[注]Brennan J.,AgainstDemocr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p.25-26.
航空服务人员需要做好服务,就要将旅客视为家人进行服务,去倾听旅客的诉求。在倾听的过程当中,需要时刻保持自身姿势,并且伴随微笑和认同地点头。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旅客感受到服务人员在用心地倾听。只有服务人员了解旅客的真实想法后,才更好地理解对方,并降低矛盾出现的概率,让服务工作顺利地开展下去。当对旅客需求进行了解后,服务人员需要站在旅客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用关怀来去感动旅客,尽可能地满足旅客,让他们有个舒心的旅程。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集体行动困境是可以被克服的。但其中的很多条件都是选民群体不能满足的,这使得他们难以走出这种困境。例如,针对积极的集体利益生产者的“选择性激励”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因为这种激励增加了个人从事集体利益生产的收益。对选民群体来说,这种激励只能体现为一种社会激励,即对搭便车者予以社会谴责,对努力生产集体利益者予以社会承认。但这种激励仅对熟人社会奏效,在大规模的选民群体中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注][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70-74页。
农户对贷款的风险管控意识不强,对民间借贷过程中隐含的风险意识不到位,对借贷中存在的法律知识认识不清。而且目前我国还缺乏规范农村金融服务的法律法规,现有的只是一些针对银行业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管理规定,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没有可操作性,不具有明显的法律效率。尤其是在农业气候保险、农业担保、依托和租赁等方面,我国还存在明显的法律盲区[4],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农村信贷的发展。
尽管如此,这种观点依然存在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因而同样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对于一项具体议题的有效监督来说,党员身份常常是不充分的。一个人可能因为支持某政党的部分主张而成为该党的成员。例如,一个党员可能在A、B、C、D、E五个议题中只支持该政党在A、B、C三个议题上的主张,而并不支持该政党在D、E两个议题上的主张。对于这样的党员而言,当本党的代表在D、E两个议题上没有做出符合其事先承诺的决策时,他就没有动机去提醒选民,于是选民就会继续对这种情况保持无知。第二,某些集中关注一个特殊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会有助于针对这个问题对代表进行监督,但困难在于当关注同一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很多时,人们就需要考虑哪个组织是更值得信任的。尤其是当需要关注的议题众多时,判断可信赖的组织所要付出的努力丝毫不亚于由选民自己去学习并思考这些问题所要花费的精力。由此就很难确定哪个组织才能成为公民监督代表的真正“帮手”,也就无法改善选民无知的状况。第三,政治积极性高而又有能力实施监督的个人或者非政府组织所关注的议题是有限的,有许多问题可能对于某些利益集团而言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却并不会吸引太多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去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对于这些问题而言,想要借助第三方组织来为无知的选民提供信息也是不可能的。[注]
一种更有希望克服选民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即依靠选民中的“信号发出者”(signals)来实现对代表的有效监督,因为选民群体可以满足这种方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所谓“信号发出者”就是指一些政治积极性比较高的个人或组织,他们会格外关注代表的某些行为,并且会在代表做出了违背选民诉求的决策时提醒选民注意。例如某个政党的党员、非政府组织或者媒体机构,乃至特别关心政治的个人等,都有可能在代表没有做出适当的选择时起到提醒选民注意的作用。这种提醒可以弥补选民无知所导致的“监督空白”,形成对于代表的有效约束。“信号发出者”的行为动机可以完全是自利的,比如他们可能只是想要在自愿承担“发出信号”工作的过程中体验一种自我实现的意义感,这能够增加他们个人的效用。所以群体中有一些这样的行动者是不太难实现的。
根据澳新风险管理标准,在完成风险识别、分析、评价后,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和风险发生时的损失程度是关键落脚点。
合作共赢才能稳步前行,对标看齐就要快追疾行。邯郸永年的张静、河南柘城的张松梅、山东寿光的孙云水、陕西宝鸡的董禄祥、山东淄博的宋清忠、山西芮城的张奇峰、山东德州的张为等等,这些与天脊营销同路、同行、同心、同向、同甘共苦的经销商,已成为携手奋进、筑梦前行的标榜,他们把经销天脊化肥作为“积德成就、行善农民、福报后代”的坚定事业。天脊集团力争在三年内重点培育像上述符合天脊营销转型发展方向的骨干经销商100家。
事实上,在大规模社会中,由于选民普遍处于“理性无知”的状态,[注]“理性无知”这个术语发端于唐斯,但是由戈登·图洛克首次明确提出的,参见[美]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刘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3页。有效监督是很难实现的。奥尔森曾指出,“由于单个人投票改变选举结果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因此,一个普通的公民,不管他是物理学家还是出租车司机,通常对公共事务存在理性上的无知现象。”[注][美]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年,第74页。根据他的集体行动理论,这其实可以被理解成“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体现。有效监督的实现会使所有的选民受益,因而是一种“集体利益”,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种集体利益需要选民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成本才有可能实现。比如选民既要去了解代表做了哪些事情,还要具备相关的知识以评价代表所做工作的好坏。如果选民不掌握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就无法推断出当前糟糕的经济状况是源自本届政府的政策、上一届政府的政策,还是源自独立于任何政府行动的其他因素。这样选民就无法准确地对真正不称职的代表施以惩罚。[注]Somin I.,“When Ignorance Isn’t Bliss: How Political Ignorance Threatens Democracy”,PolicyAnalysis,2004,(525): 12-13.并且,选民还要在代表未能回应他们的诉求时与其他选民协调一致行动,从而达成以改选来“威慑”或是惩罚代表的目的。对于有大量的个人工作和生活琐事需要处理的单个选民而言,“有效监督”的成本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同时,由于选民数量众多,单个选民是否进行这种投入并不会对有效监督的实现以及他本人能够从中得到的好处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投入的收益很小。此时单个选民就会缺少“亲自”去监督代表的动机,而是更有可能选择搭其他选民的“便车”,即自己不去了解相关信息与知识,而是“坐享”其他选民监督代表所带来的好处。这对单个选民而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而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的选民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选民确实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对于代表的所作所为就会普遍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对代表的监督就很有可能会失效。这就是选民在监督代表时所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注]参见奥尔森对“集体行动困境”的一般性说明,[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1995年,第8-14页。
根据“政治无知”问题研究专家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对于美国历次总统选举所做的经验研究,选民的无知的确使得即使在政府决策中存在显而易见的重大失误的情况下,政府依然可能逃脱选民的改选惩罚。例如,虽然胡佛和卡特总统分别因为1932年和1980年的政策失败而在选举中遭受了惩罚,但至少要为这些失败承担同等责任的他们的前任,如柯立芝、尼克松与福特却并未遭到这种惩罚。[注] Somin I.,“When Ignorance Isn’t Bliss: How Political Ignorance Threatens Democracy”,PolicyAnalysis,2004,(525): 3-4,13.这就表明选民对于政府的监督在许多时候确实是失效的,这样政府对选民负责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有人可能会认为利益集团对候选代表的俘获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即使选民没有充分的动机在选举间歇期去关注代表的所作所为,仍然可能会在选举期间特别注重获取候选代表的相关信息。然而事实上,选民更有可能是会对候选代表的竞选信息保持同样的“理性无知”。选民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选出称职的代表也能够使得所有选民获益,所以对于称职代表的选举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而由于单个选民不去努力获取候选代表的信息也不会显著地影响称职代表的选出,不做出这种努力就是理性的。
二、利益集团对现任代表的“俘获”
在选民难以有效监督代表的情况下,利益集团就有了俘获(capture)代表的可能。所谓“俘获”,简单地说就是指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对谋求连任的现任代表或者谋求初次当选的“候选代表”施加影响来使得当选的代表不顾对于选民的承诺而做出有利于该集团利益的决策,其实质是利益集团与代表或候选代表之间的一种“交易”:利益集团帮助候选代表当选,或者帮助代表取得连任,作为回报,当选后的代表则会做出一些有利于利益集团的决策。[注][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81-82、85-86页。由于利益集团的利益与普通选民的利益常常是不一致的,结果是被俘获的代表在许多决策中都会对利益集团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因此,“代表与利益集团之间不存在俘获交易”也是选举能让代表对选民负责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这个条件也是很难满足的。利益集团常常能够成功地俘获代表或候选代表,这将削弱代表对选民负责的动机。
既是交易,交易双方就需要具备可用于交易的资源,代表与候选代表所拥有的“资源”就是他们现在掌握的或者未来即将掌握的决策权,利益集团的“资源”则包括资金、自有媒体等,这些资源有助于在选举中为代表和候选代表做宣传,从而帮助他们当选或是连任。一个利益集团通过“俘获”代表或者候选代表所获得的收益也会使该集团的全体成员受益,所以也是一种“集体利益”,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但与选民群体不同的是,利益集团往往有能力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实现对于这些利益的有效生产。这是由于,一方面,有一些利益集团,例如美国的垄断行业利益集团,规模往往非常小,仅由几家企业组成。在这样的小团体中,每个成员投入的资源都会对集体利益的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他们有充分的动机进行这种投入。同时,由于小团体的组织成本很低,团体成员也比较容易通过达成协议来进行相互约束。所以相关行动者大都会愿意为实现集体利益而努力,而不是“坐享其成”。[注]
另一方面,一些更大的利益集团则可以通过强制入会或者提供非集体性收益等“选择性激励”来促使相关从业者加入他们,进而要求这些从业者为该集团利益的实现贡献金钱等相关资源。比如在美国,很多州都要求每个开业律师必须成为州律师协会的会员,这些会员所缴纳的会费会成为律师协会向代表施加影响的重要资源。又比如,作为医疗行业利益集团代表的美国医学会可以通过为医生提供医疗事故诉讼中的保护性帮助,出版会员所需要的医学杂志等做法来吸引会员入会,并要求他们缴纳活动经费,从而筹集到影响代表所需的资金。这些做法要么是提高了利益集团内的个体成员不去努力生产集体利益的成本,要么是增加了人们从事这项生产所能获得的收益,结果都是使得个人从事这项生产更加符合其理性的要求,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集体行动的难题。[注][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172-178、169-172页。
一旦利益集团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筹集到相关资源,就有了与代表以及候选代表进行俘获交易的能力。就现任代表来说,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向媒体投入资金或者直接利用自有媒体来影响大众对于代表的态度,从而诱使代表按照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来做决策。如果代表不这样做,利益集团就可以运用媒体宣传“抹黑”代表,从而不利于他们再次当选。反之,按照符合利益集团利益的方式做决策则可以使得代表在选举中获得利益集团提供的媒体的正面宣传,从而有助于他们的连任。[注] Guerrero A.,“Against Elections: The Lottocratic Alternative”,Philosophy&PublicAffairs, 2014,42(3): 142,144-145.
鑫两优212是合肥市蜀香种子有限公司利用抗旱性较强的两系不育系蜀鑫1S与抗高温恢复系鑫恢212 2009年配组,2014年通过安徽省审定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审定编号:皖稻2014022),经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2012年抗旱性鉴定,抗旱性达1级,是国内选育的首个杂交籼型旱稻品种[13]。笔者拟利用农业部颁布的行业标准《水稻品种鉴定技术规程SSR标记法》(NY/T 1433—2014)中推荐的48个SSR标记,筛选适合的特异引物用于该杂交种纯度的快速鉴定。
但如果选民能够有效地监督代表,代表与利益集团进行交易的动机就会减弱,交易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能从这种交易中取得的收益都会比较小,成本却很高。选民能够有效地监督代表就表明他们很清楚代表在上一个任期内表现如何,此时与选民所掌握的信息不相符的媒体宣传就难以对选民的判断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此时称职的代表根本不需要借助于媒体资源也能够顺利地取得连任,也不太需要担心利益集团的反面宣传会“抹黑”他们。而不称职的代表也无法指望通过宣传就能很轻易地改变自身的形象。因此,利益集团所投入的资源对不同类型的代表再次当选的帮助都不大,而代表接受这种“帮助”却需要以做出偏向于利益集团的决策作为回报,这就要冒着被选民发现并施以改选惩罚的风险,与利益集团交易的成本太高。因此,理性的代表会倾向于拒绝和利益集团进行交易。理性的利益集团也会由于难以找到交易对象而减少乃至放弃在媒体宣传上的投入。
当选民对代表的行为普遍无知,难以对代表形成有效的监督时,代表与利益集团进行交易的“成本—收益”结构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极大地提高这种交易发生的可能性。一方面,选民难以有效监督代表会增加代表与利益集团交易的收益。当选民对于代表的实际表现理性无知时,他们在做是否让代表连任的决定时就会非常依赖于媒体所提供的关于代表表现的“免费信息”。[注][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第202-205页。因而在媒体宣传上投入的资源多少将对选举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筹集到大量相关资源的利益集团可以使用这些资源与作为候选人的现任代表达成交易,从而促进双方各自利益的实现。选民对于代表的行为越是无知,在选举时所做的决定就会越依赖于媒体信息,利益集团投入到媒体上的资源对于相关代表连任几率的提高就越多,从而代表和利益集团能够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多。其中代表得到的好处就是连任概率的增加。由于利益集团得到的好处体现为通过帮助某些代表连任而可以在这些代表以后的决策中获得“回报”,利益集团资助的代表连任的可能性越大,利益集团得到回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选民监督的缺失越严重,利益集团的资源对于代表当选的帮助就越大,利益集团在与代表进行交易谈判时的“要价”也会越高,从而利益集团能够获得回报的决策范围就会越广,获得回报的数量也会越多。
但如果选民对于候选代表的情况很熟悉,这种交易意向就不容易达成。因为此时媒体宣传对选民挑选候选代表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比较小,候选代表与利益集团通过交易所能获得的收益同样会比较少。具体来说,候选代表能够从利益集团那里得到的媒体宣传对于他们当选概率的提高是有限的。因为利益集团的收益是候选代表当选之后在决策中对他们做出的回报,如果利益集团在媒体宣传上的投入对于候选代表当选概率的提高不多,他们的投入对于得到这种回报的概率也同样不会有太大的提高。因而候选代表与利益集团都会没有充分的动机去进行交易。
因此,在竞争性选举的制度条件下,利益集团俘获代表,以及代表接受这种俘获通常是完全符合二者的理性要求的,这意味着这种交易很有可能发生。而一旦发生这样的交易,代表就会在许多决策中对利益集团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
三、利益集团对候选代表的“俘获”
利益集团的俘获行为还有可能是针对谋求初次当选的“候选代表”的。即使选举过程对于“政治献金”的来源与数目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利益集团还是能够对谁当选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们可以通过控制媒体来影响选民对于政党内部所确定的候选代表及其立场的认识,他们还会事先识别并培养一些与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候选代表。[注]Guerrero A.,“Against Elections: The Lottocratic Alternative”,Philosophy&PublicAffairs, 2014,42(3): 142-144.在这种情况下,候选代表出于当选的需要也可能会主动地寻求与利益集团达成“交易意向”。[注]之所以只是达成交易意向,是因为交易要等到代表当选之后,在做决策时才能最终完成。对于候选代表而言,如果不能成功当选,则交易就无法完成。
另一方面,选民难以有效监督代表还会降低代表与利益集团交易的成本。对于代表来说,如果选民难以有效地监督他们,他们因在决策中对帮助其当选的利益集团做出“回报”而遭到惩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与利益集团进行交易的成本就会下降。对于利益集团来说,如果选民不能有效地监督代表,为了达到影响选民选择的目的所需要投入的资源也会大大减少,从而也会降低利益集团的交易成本。
总之,“选举使得代表对选民负责”的信念所面临的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就是,由于选民对代表行为的“理性无知”而难以保证选民对代表的有效监督。没有这种有效监督,代表就会缺乏对选民负责的动机,“代表会充分地对选民负责”的逻辑也就难以成立。
对此,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因为在选举过程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选民的“目的”其实有两个,除了“选出一个称职的代表”,他们可能还会追求“在选择称职代表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价值主要是实现个人自治,参见Kolodny N.,“Rule Over None I:What Justifies Democracy?”,Philosophy&PublicAffairs, 2014, 42(3):199-200.由于只有当个人认真地考察了候选代表的竞选信息时才有可能选出称职的代表,也才有可能“决定称职代表的当选”,选民的第二种目的会使得他们有动机去获取候选代表的信息,这样选民群体就能够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但这种观念是不成立的。由于个人在对好代表的选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可能很小,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不理性的。只有当其他所有选民的投票形成了平局时一张选票才可能具有决定性,[注]Niko K.,“Rule Over None I:What Justifies Democracy?”,Philosophy&PublicAffairs, 2014,42(3): 199-200.即使乐观地估计,美国选民具有这种决定性的概率也仅有几百万分之一。考虑到选民时间与精力的有限,为了获得对于选举好代表的这种决定性而去了解和学习大量的相关信息与知识是“不划算”的。所以选民在选举时对候选代表的信息保持一种“无知”的状态仍然是符合理性要求的。假设一位亿万富翁向你发出了一份10亿元的要约,只要你完成对微观经济学导论的学习,就可以得到这10亿元,此时你显然有很强的动机去进行这项学习。但如果他要求你完成十门课程的学习,然后只是让你有六千万分之一的机会获得10亿元,仅从获得奖励的角度考虑,你显然会理性地选择不去学习,保持无知。大规模社会的政治选举与第一种情况完全不同,而是与第二种情况相似。为了能够“决定”一名好代表的当选,你需要投入很多精力进行学习,但回馈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一般人都会理性地选择保持无知状态。[注]Jason Brennan,AgainstDemocr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p.30-32.有人可能会质疑集体行动困境为何只会使得选民在无知状态下去投票,而不是直接放弃投票?这其实是混淆了两种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致力于选择称职代表的投票行为与投票本身的成本是不同的,前者需要全面掌握和权衡候选人的信息,后者却只需要花少量的时间把选票填好并投出就可以,这种低成本会使得很多理性无知的选民仍然选择去投票。
储存中的污染和变质。这种情况包括:被有害生物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不合适储存条件、受潮、过期导致的原料变质。
因此,在选举期间,理性的选民也很有可能会选择对候选代表的竞选信息保持无知。而相关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公民在选举期间确实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无知状态,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要选的候选代表都是谁。例如,79%的美国人不能认出本州参议员。即使在选举年,多数公民也根本认不清本选区的国会候选人,并且普遍不知道哪个政党控制着国会。[注]Brennan J.,TheEthicsofVot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163-164.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尽管稍多于50%的美国人知道戈尔比小布什更加偏爱自由派的观点,他们却并不理解“自由派”这个词的含义。尽管57%的美国人知道戈尔比小布什有更高的支出偏好,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知道戈尔更支持堕胎权,更支持福利国家计划,支持对于黑人的更高程度的援助,以及更加支持环境规制。[注]Somin I.,DemocracyandPoliticalIgnorance,p.31.
选民在选举期间关于候选代表信息的理性无知会提高利益集团与候选代表之间进行俘获交易的收益水平,增强双方达成交易意向的动机,从而使得这种交易的发生成为可能。当选民所掌握的候选代表信息有限时,媒体所提供的相关信息也会对他们的选择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此时利益集团对媒体做出的相同投入就能对候选代表的当选起到更大的作用,候选代表当选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这不仅会增加候选代表接受利益集团俘获的收益,对于想从对候选代表的俘获中得到回报的利益集团而言也会增加收益。一方面,候选代表当选可能性的增加就意味着利益集团的投入得到回报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投入的有效性还会提高利益集团在交易中的谈判地位,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更大的决策范围内要求代表做出更多的回报。[注]选民的这种理性无知也会进一步降低现任代表接受利益集团俘获的成本。因为如果选民虽然没有在选举间歇期很好地监督代表,但却在选举期间开始重视对作为候选人的现任代表的了解,就还是有可能发现他们没有回应自己的诉求、对自己负责的情况,从而在选举中对其施以改选的惩罚。选民在选举期间对于所有候选人(包括作为候选人的现任代表)信息的无知使得这种可能性也被降低了。
同时,选民对代表行为的理性无知也会降低候选代表与利益集团达成交易意向的成本。其一,媒体宣传的有效性会降低利益集团在这方面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其二,对于候选代表来说,由于尚未掌握决策权,他们用来与利益集团交易的只能是对于在未来的决策中做出回报的一种承诺,如果当选之后会受到选民的严密监控,他们做出这种承诺的成本就比较高,因为一旦他们在决策中偏袒利益集团的做法被选民发现,就会无法取得连任。选民对代表行为的理性无知降低了这种成本,从而降低了候选代表对于受到改选惩罚的预期,增加了候选代表接受利益集团俘获的可能性。而一旦候选代表接受了利益集团的俘获,他们在当选之后就会倾向于兑现“承诺”,即在一些决策中回应利益集团的诉求。这会使得这类代表在许多决策情境中也是会对利益集团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
利益集团对于代表和候选代表的“俘获”是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真实发生着的事情,这种理论推导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验证。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经过研究发现,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在对选民的回应上存在着明显的倾向性。中高收入者的诉求得到了较好的回应,收入最低的那部分选民则几乎未得到任何回应。对此现象,巴特尔斯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中高收入者贡献了代表竞选资金中的大部分捐款。[注][美]拉里·M·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方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1-286页。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思(Martin Gilens)等人对“多数选举民主”和“多数多元主义”两种认为普通民众对政治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理论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发现普通民众其实对于美国的政治决策并无显著的影响,经济精英和并不代表民众利益的利益集团才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注][美]马丁·季伦思、本杰明·佩奇:《美国政治理论检验:精英、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载本书编写组:《西式民主怎么了Ⅲ》,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213-238页。耶鲁大学教授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等人在研究中提出,美国在过去30年里收入不平等增加的根源就是经济精英对于美国政治的俘获,这些精英拥有在税收政策、公司治理、解除环境管制等方面决定政策结果的能力。[注]Hacker J., Pierson P.,Winner-take-allPolitics:HowWashingtonMadetheRichRicher-AndTurnedItsBackontheMiddleClass,Simon and Schuster,2011.
总而言之,在现实的政治运行过程中,由于“代表与利益集团之间不存在俘获交易”这个条件很难满足,选举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代表充分地对选民负责。
结 语
负责制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构建负责制政府的路径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竞争性选举能够确保政府对选民负责”作为一种观念框架束缚了许多研究者的理论想象力,这不利于探索真正有效的以及适合于中国实际的负责制政府模式。只有突破这种观念框架,才有可能实现理论与制度上的创新,才有可能真正树立起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通过对选民、利益集团与代表之间理性互动的分析可以发现,“选举使得政府充分地对选民负责”所依赖的条件其实都是很难满足的。在竞争性选举的制度条件下,选民难以有效监督代表是普遍存在的,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会有助于候选代表和代表获得当选或者连任也是普遍存在的。代表在很多决策中更有可能回应利益集团的诉求而不是选民的诉求。因此,“竞争性选举”与“负责制政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脆弱”的。那种认为只要采取竞争性选举制就能够有效地保证政府对选民负责的观点是错误的。对负责制政府实现形式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不仅是有余地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一种能够更好地实现负责制政府的“中国方案”将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
CompetitiveElectionandAccountableGovernment:AFragileCasualRelationship——AnalysisinthePerspectiveofRationalInteractionsbetweenVoters,InterestGroupsandRepresentatives
NiuWenh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46)
[Keywords]competitive election; accountable government; rational ignorance; effective supervision; capture
[Abstract]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as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etitive election(which is generally taken by western democracy)and a government accountable to its voters.In fact,this is a belief facing many problems.In the institution of competitive election, it is a rational choice for voters to keep ignorant of representatives’ decision making and representative candidates’ campaign information.The former ignorance will make voters can’t supervise representatives effectively, so the election won’t guarantee representatives have enough incentives to be accountable to voters.Moreover, these two kinds of rational ignorance will also make it a rational choice for representative candidates to accept interest groups’ capture.Consequently, the elected government will be accountable to interest groups,but not to voters in many decision-makings.The conditions of competitive election bringing about accountable government are hard to achieve, the cas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factors is actually very weak.
[作者简介] 牛文浩,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江苏 南京 210046)。
*本文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级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罗尔斯之后的正义理论研究”(项目号:2013PT005)与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发展党内民主与预防权力腐败研究”(项目号:2014LZY02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蔚然]
标签:选民论文; 代表论文; 利益集团论文; 无知论文; 理性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体制论文; 《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6期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级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罗尔斯之后的正义理论研究”(项目号:2013PT005)与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发展党内民主与预防权力腐败研究”(项目号:2014LZY021)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