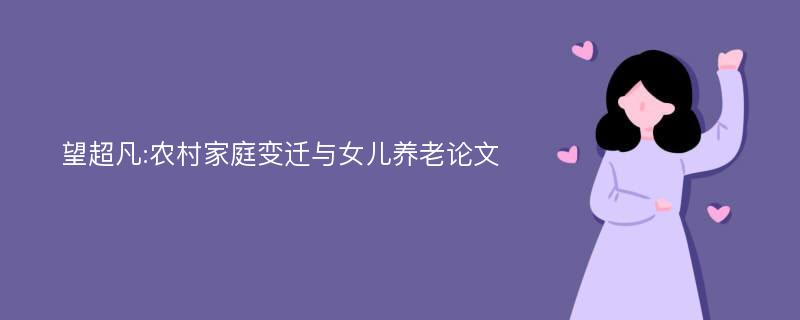
摘要:女儿参与赡养娘家父母已经成为了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通过对强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家庭性质的变迁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家庭的变迁路径是一个宗教性弱化、社会性弱化和生产性改变的过程,这导致家庭逐渐朝向单纯的生活单位转变。家庭性质变迁在形成儿子养老危机的同时,也释放了女儿的养老潜力,从而形成了女儿参与养老过程的新现象。同时,在激烈的变迁中农村家庭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文化韧性,这构成了对传统儿子养老模式的结构性支撑,并给予了行为主体实践能力发挥作用的博弈空间。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儿子和女儿的实践能力对比和行为取向共同发挥作用,一起塑造了当下“共同赡养、儿女分工”的新型家庭养老秩序。
关键词:农村养老;女儿养老;家庭变迁;农村社会
一、农村社会中的女儿养老现象研究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养老的主要场所,儿子是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只有在没有儿子的家庭中,才会以招“上门女婿”的方式来实现养老,但其本质上是对女儿在社会性别上的男性化,依然属于儿子养老的特殊形式[1]。女儿在出嫁前是“替别人家养的”,在出嫁后便是变成了“泼出去的水”[2],在原家庭中没有其结构性位置,因而既没有对娘家财产和宗祧的继承权利,也不负有对娘家父母的养老送终义务。但是近年来的大量经验研究发现,女儿养老在农村社会中不仅已经出现,并变得日渐普遍。如许琪通过对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子女和老人的居住方式以后,农村社会中的女儿在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两个维度上对老人的付出都超过了儿子[3];张翠娥和杨政怡的研究表明,女儿养老作为新观念已经逐渐得到部分农村居民的认同[4]。可以看出,女儿养老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养老秩序的新成分,为缓解农村养老压力,重塑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发挥了重要功能,如何理解女儿养老现象的产生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围绕农村社会中女儿养老现象的产生原因,当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解释路径。一方面,部分学者将女儿养老的产生归因于我国急速的社会结构变迁,聂焱在比较了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女儿养老和儿子养老的差异后发现,打工经济的兴起在弱化了儿子的养老能力和意愿的同时却提高了女儿的养老能力和意愿,进而为女儿参与养老提供了动力[5]。钟涨宝等学者将女儿养老与农民的现代性意识相联系,认为现代性意识在农村社会的广泛传播构成女儿养老得以被接受的观念基础[6],现代性意识的崛起有力地打破了传统社会规范所形成的压力,从而实现了女儿养老潜力的释放[7]。朱安新和高熔通过对老年人的主观意愿进行研究发现,子女的数量及性别结构是导致女儿养老得以形成的人口学背景,进而探讨了计划生育制度对养老模式变迁的影响[8]。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家庭内部,认为家庭结构变迁是女儿养老现象得以形成的现实原因。阎云翔认为随着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同步变迁,其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在于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了纵向的亲子关系成了家庭关系的主轴,进而严重削弱了儿子养老的家庭结构基础[9]。高华对晋东地区的实地研究发现了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家庭地位提高是促使她们能够在自己父母的赡养活动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力量[10]。贺雪峰则敏锐地觉察出了家庭关系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理性化趋势,认为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使得传统的儿子养老越来越不合乎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导致了女儿参与养老逐渐成为了家庭养老得以延续的现实需求[11]。可以看出,当前研究从我国宏观社会变迁和微观家庭结构变迁两个视角共同解释了女儿养老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但是在家庭层面的解释上,学者将目光过于聚焦于家庭形式层面的变迁,进而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家庭规模及其内部关系模式的变迁上[12],对家庭变迁的理解局限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改变,我们可将这一研究范式称之为家庭形态学研究范式。在形态学研究范式指导下的女儿养老机制研究中,研究者更为倾向于从家庭形态的变迁来解释女儿养老的产生机制,而忽视了中国家庭在本质意义上的变迁,其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的研究者已经普遍接受了西方家庭理论中对于家庭含义的预设,将中国传统家庭同样理解为经典家庭理论所定义的“由血缘、婚姻和收养关系联结起来的生活单位”[13],认为探讨家庭的规模与关系变化便可以达到理解家庭变迁的目的。但是中国的家庭内生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与西方的家庭有着巨大的差别,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家庭不是个人的集合,而是诸多社会事务的基本单位,家庭是其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家族的兴旺繁盛与传宗接代对于村民而言才真正具有终极性价值[14]。因而在探讨中国的家庭变迁对女儿养老的影响时,应首先回到我国乡村社会的具体语境中,从家庭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的变迁出发来进行理解。
加强水质监测,建立健全南水北调干线水质安全预警-联动管理制度。水质预警-联动机制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构多级联动检测及管理制度;二是定期开展南水北调干线、尾水导流工程沿线的巡查工作,并加强与相关单位合作,以掌握水质的变化情况;三是深入研究工程运行期的主要风险,分析各风险对水质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好风险预测、风险决策和风险控制工作。制定严格、合理、可行的事故应急预案,以有效预防、实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干线水质安全突发事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切实确保干线水质的安全。
笔者在陕西关中某农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女儿参与养老渐成趋势。一般而言,养老责任被分为三个重要组成方面,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在该村部分村民家庭中,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甚至是超过了儿子的作用,不仅以经济支持的形式分摊和儿子同样的费用,有的女儿甚至还会将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接到自己的家中进行照料。笔者通过对参与娘家父母赡养的女性及其父母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在诸多的推动女儿参与养老的因素中,家庭变迁这一因素显得极为重要。家庭的变迁一方面推动了传统儿子养老模式的瓦解,另一方面形成了吸纳女儿介入养老事务的机制。家庭性质的变迁是当地社会发展推动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的核心动力机制之一。
二、传统家庭制度与儿子养老
1.传统社会中的家庭
从图1可知,该程序设定的脉冲周期为150ms、脉冲输出个数为10个,则输出10个脉冲的时间为1500ms。如果PLC系统接收25个脉冲信号的时间T1小于10个脉冲输出的时间T2(以1500ms为例),也会出现脉冲丢失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上一次的脉冲串(10个脉冲)还没发送完下一次的脉冲串指令就已经下达。因此,输出脉冲串的时间应小于接收脉冲串的时间,即 T1>T2。
西方家庭社会学理论建基于个人主义传统,将家庭定义为个体通过血缘、婚姻和收养关系连结起来的生活单位。中国的传统家庭内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在性质上与西方的家庭有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在性质上并不局限于西方家庭理论所理解的同居共财合炊的生活单位[15],而是一个集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复杂社会单元[16]。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家庭首先是一个生活单位,其次是一个共同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单位,然后是一个参与社会生活的交往单位,最后还是一个进行祖先祭祀的宗教单位。因而传统社会中的家庭是一个兼具了生活性、生产性、社会性和宗教性四重属性的“四位一体”社会单元。
家庭社会属性的变迁让儿子养老失去了规范性保障。传统家庭的嵌入性赋予了村庄社会对家庭内部事物进行规范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社区情理,社区情理以惩罚措施为后盾,以家庭伦理的形式保证了儿子的赡养行为[31]。家庭对村庄的双重脱嵌意味着家庭伦理规范意义的终结,脱嵌的家庭因此得以将自己从村庄社会强加的规范中解脱出来,家庭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家庭的规模与内部关系,对家庭的功能性需求成为家庭成员选择合适家庭结构、安排家庭行为的现实依据。这一方面对老人和儿子而言,都是一种解放,但是另一方面也让儿子养老失去了规范的保证。72岁的访谈对象强去病谈道:
加大对涉农信息技术公司的扶持,有效降低产品价格,并将农业信息设备纳入到农资补贴目录;引导知名电商平台落地建立服务站、帮扶店,支持物流、快递公司分支机构或服务站点入驻乡镇、中心村,推进“互联网+电商”的发展,拓宽销售渠道,增加销售收入。
可以看到,“四位一体”的属性构成了中国传统家庭的基本性质。传统家庭首先是一个生活单位而具有其私人性,然后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农业生产、社会交往和宗教活动的基本单位在村庄社会中存在,内嵌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中。家庭“四位一体”的本质使得家庭的结构、功能和价值取向都受到相应的形塑,并结合其社会背景共同形成了传统家庭制度。
为避免学校直接经营带来的问题,同时又避免独立第三方公司无法满足学校的需求等问题,可以考虑采取由学校将酒店出租给下属经营公司来经营的新型管理模式。
在交换逻辑下,老人生了儿子,所以儿子要养老,“养”是对“生”的回报,而不是出于儿子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在宗教性消退的农村社会中,这成为了人们普遍接受的准则。但是交换逻辑对父代是不公平的,时代的变迁使老人与儿子的交换关系陷入了一种“被动不均衡”的状态:老人对儿子的大量付出可能只表现为“破砖烂瓦”,儿子的赡养行为却能体现为可以变现的劳动力和直接的物质财富。儿子正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堂而皇之地降低甚至是推卸自己对老人的赡养责任。
基于传统家庭制度,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在规模、成员关系以及价值取向都有着清晰的形态偏好,呈现出典型化的特征。家庭形态一方面受到社会结构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则是以社会化的方式深入到家庭成员的人格当中,使之自觉遵守。从养老的角度上而言,传统家庭形态有力地保障了儿子养老的家庭养老秩序。
首先,家庭的宗教性内涵划定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将儿子养老作为对男性性别角色的核心期待施加于男性身上。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构成了宗教活动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宗教活动不在于求得个人的救赎,而是以家族绵延、香火不绝作为其终极价值,家庭成员是将自己放在“从祖宗到子孙”的位置序列中来获取自己的人生意义,因而家庭的继嗣就构成了传统家庭宗教的核心。在父系继嗣制度下,只有男性才能以“嗣”的角色出现,继承家庭的宗祧,完成绵延家族的重任,而女性只能通过婚姻的方式在夫家获取正式社会资格,成为男性继嗣制度的“附带受益者”[20]。在此基础上,传统家庭有着对于儿子和女儿完全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这具体体现在儿子是家庭的继承者,女儿是娘家的客人的这一角色安排上。在传统家庭中,宗祧、财产的继承与祭祀、赡养的责任是彼此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儿子在享受继承宗祧和家庭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祭祀先祖、赡养父母的责任,这一责任负担的过程同样具有对祖宗负责的宗教意义[21]。而女儿在娘家责任义务的缺失则是通过在夫家以“媳妇”身份来实现。于是作为同一父母子女的男女两性,其权力和责任实际上是在两个家庭中分别展开得到平衡。这样一种平衡方式进一步维持了家庭微观领域中的夫权统治和社会宏观领域的男性社会继嗣制度,通过这一过程,社会将儿子定义为年老父母的赡养者,女儿则是以媳妇身份作为丈夫父母的赡养者。
其次,我国传统家庭生产模式有效地保证了老人在家庭中的位置。传统家庭经济模式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阶段性地密切合作,二是生产资料的家户长私有制。前者使得大家庭的结构模式有着重要的功能性意义,后者赋予了作为家户长的老人对于家庭财产的所有权与收入的分配权,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家庭伦理。虽然核心家庭总是最为普遍的家庭形式,但是大家庭的伦理却可以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得以实践和延续[22],家庭的生命周期总是沿着“小家庭—大家庭—小家庭”的模式滚动发展,父代掌握着分家的决定性权力,儿子提出分家则是大逆不道的。因而作为家户长的老人始终是得以将自己包含在有儿子同住的联合家庭或者是直系家庭中,不至于沦落到单独生活、无依无靠的境地。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强村还有所体现,老人强建军向我们介绍:
分地以前分家都是分一次,一般是只剩小儿子没结婚就可以分家了,然后老人就和小儿子一起过,老人帮小儿子结了婚以后便一直跟着小儿子生活,老人是不可能单过的,但是老人生病了就几个儿子一起分担。
这种大家庭和直系家庭的居住方式不仅保障了儿子必须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也极大地方便了老人接受儿子的赡养与照料。
最后,传统家庭对于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使得家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和行为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区情理”的严格规制[23],为儿子养老提供了来自村庄社会的结构性支持。家庭对于村庄社会的嵌入是双重的,家庭一方面嵌入于父系的宗亲团体中,另一方面嵌入于村庄熟人社会中,双重的嵌入性表现为村民在村庄内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对于村民而言不仅具有生产生活中的功能性意涵,还满足着村民的社会性需求,与村民生活的本体性价值相关联,关系网络功能性与价值性使其具备了对村民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进行形塑的能力。因而对于个体家庭而言,其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和行为取向并不仅是家庭成员依照个人喜好与生活便利做出的选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支配与约束。在社会结构的引导下,家庭关系有着必须尊崇的关系模式,如“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家庭行为同样有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如“父慈子孝”等,这些关系模式和行为规范共同组成了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伦理,对家庭成员的行为选择起着规制作用。就养老问题而言,儿子的养老责任既受到家庭伦理的直接规范,又得到伦理规范下家庭的结构形态与关系模式的保证。在访谈中,村民强建民谈起以前是怎么惩罚不孝子的:
老人嘛,有口吃的就可以了,儿子很少会给钱,毕竟年轻人现在压力也大……老人还能动那就还好,他自己还能养活自己、照顾自己,要是不能动了就麻烦了。
传统家庭的嵌入性使得个体家庭对于社会评价极为敏感,村庄社会结构因此具备了对个体村民的行为进行规制的能力。其结果是形成了具体的“一起骂他”的惩罚手段以及“道德法庭”的约束机制。
可以看到,传统家庭的性质为儿子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提供了家庭层面的有力保障。传统家庭不仅是私人生活单位,还兼具了宗教性、生产性和社会性的等多重属性。虽然作为生活单位的家庭有按照其生活便利程度来安排家庭结构与行为的倾向,但是家庭的生产属性使得其在传统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大家庭的规模取向与父代基于土地的权威、家庭的宗教属性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性别角色的规范与禁忌;家庭对父系宗亲与村庄社会的深度嵌入性形成了家庭选择中的伦理压力。这些内容一起参与塑造了传统家庭典型化的家庭结构形态与行为模式,构成了我国传统家庭制度,而儿子养老正是在这一制度基础上成为普遍的养老模式。
三、家庭变迁与女儿养老的形成
1.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家庭变迁
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我国传统家庭制度开始受到各种外来与内生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发生变迁,但是这一变迁真正在广大乡土社会中进入高潮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其变迁原因,既有研究从集体化运动[24]、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打工经济的兴起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阐释[25],这些解释并不冲突,可以想象,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任何对社会整体变迁产生影响的因素都必然会以某种形式作用于家庭,使家庭发生同步变迁。本文无意于探讨导致传统家庭制度变迁的具体原因,而是想要指出在传统家庭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家庭发生的一系列实质性变化。总体而言,家庭的变迁是全方位的,这是一个家庭的生产性、宗教性和社会性或依次,或同步发生变迁的过程。
传统家庭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家庭生产属性的突然转变。传统家庭经济模式受到的第一次冲击出现在集体化运动时期,集体化运动包括了三方面内容:土地集体所有、劳动以集体方式进行、劳动成果以个体劳动力的工分为依据进行分配。在集体化生产模式下,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与生产协作失去了意义。同时,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消灭了家户长对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取消了其对于家庭收入的分配权,工分制让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成果都可以以独立的方式被明确地表现出来,分田到户的过程更使得个体的土地不再是继承于父代,而是从集体分配所得。而后的改革虽然重新实现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包产到户,但是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技术也得到了同步提升,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协作变得不再必要[26]。更为重要的是打工经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生计模式,传统社会中农民赖以为生的农业收入逐渐在农民生计来源中居于次要位置,农村家庭的结构形态逐渐开始围绕打工经济的便利来展开。在这一前后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中,家庭失去了其作为独立社会生产单位的性质,个体成了家庭生计模式的真正落脚点。
其次,与家庭的生产属性同步被削弱的是家庭的宗教属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在“消灭封建迷信”“打倒牛鬼蛇神”的革命话语下,传统的祖先崇拜、家庭祭祀被当作封建糟粕来加以对待,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同时,祖先崇拜、家族延续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观念的广泛传播更进一步打击了传统“香火延续”的宗教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的宗教性被世俗化了,人们不再是在“祖先—子孙”的血脉延续中来理解当前生命的意义,而是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仅仅局限于当下的生活现实[16],家庭的价值也从宗教意义上的神圣价值变成了现实意义上的世俗价值。
最后,家庭实现了对村庄社会结构的双重脱嵌。正如前面所讲,传统家庭对村庄结构存在着双重嵌入。但是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宗族被毛主席划定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27],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基本瓦解。紧接着是随着国家对乡土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农民彻底地实现了从“宗族的族人”到“国家的人民”的角色转变,农民就此实现了对父系宗亲团体的脱嵌。随后,在打工经济下,村民一方面在生产上脱离了村庄社会,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半脱离了村庄社会,村庄对于村民而言从全部的生活世界变成了过年暂时居住的场所与生活空间,家庭因此实现了自己对村庄社会结构的脱嵌。从双重嵌入到双重脱嵌的过程同样是一个家庭社会交往属性变迁的过程,一方面年轻人开始尝试以个人身份在村庄中展开社会交往,另一方面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对于村民而言不再具有绝对性意义,而仅仅是变成家庭或者是个体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可以看到,在这一场家庭的急速变迁中,农村家庭发生的核心变化在于其属性的单一化。家庭的生产性、社会性与宗教性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与弱化,家庭从传统“四位一体”的社会单元变成了以生活性为主的私人生活单位,其结果是家庭结构、关系模式与价值取向发生同步改变,这种改变直接导致社会对家庭的某些功能设定面临挑战。
可以看到,从性质上而言女儿分摊的内容都是属于劳务与经济的分担,在这些事务中,女儿分摊的责任有时甚至比儿子更多,因而女儿毫无疑问具备了养老之“实”。但是女儿的行为却仅仅是分担而不是替代,儿子这一过程中同样分担了实际的养老责任,因而儿子依然是养老责任的有力承担者。儿子的“特权”则体现为仪式性的内容,既包括了老人“跟着谁”的生活仪式,又包括了葬礼的神圣仪式。儿子依然是仪式性内容的唯一合法承担者,通过占据仪式性位置,儿子既表明了自己是养老送终的义务承担者,又保障了自己家庭继承者的地位。所以在老人“养老—送终”这一过程序列中,女儿只是“空有其实,难有其名”,儿子却可以“少有其实,全有其名”,儿子与女儿在养老分担中形成了名与实、权与责上的分离。
在家庭的变迁过程中,农村养老秩序逐渐出现了转型,这种转型首先体现在儿子养老的传统制度安排面临困境。在访谈中,书记强建文对村里的养老状态有这样的叙述:
3)规则3。竖井掘进机偏移为正大,偏移改变量为负大,表示机体虽有很大的偏移,但具有大幅度向设计轴线回归的运动趋势,此时为避免超调,液压缸压力差应取零,防止机体纠偏幅度过大。
当时在村口有两个大石碾子,我们晚上吃完饭就喜欢坐在上面聊天,要是谁家里有儿子不孝顺,我们就一起骂他,这样就没有儿子敢不孝顺了,这就是我们的“道德法庭”。
我们基本上可以用“有饭吃、没钱花、缺乏照料”来概括强村老人的生活状态,但是这绝不单纯是一个“孝道沦丧和伦理性危机”的问题[28],其背后的现实性因素在于由于社会的剧变,中年人的经济压力突然增大。费孝通所描绘的“反馈模式”固然美好,但是其前提是处于家庭核心地位的中年人只需要在家里种地就可以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顺便”照顾好老人,抚育好小孩。而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中,其情形决然不是如此,一方面是老人的寿命得到了空前的延长、赡养成本同步攀升;另一方面是子代的抚育、婚姻成本同样剧烈增长。仅从婚姻成本来看,强村的彩礼标准从2010年的不到一万元迅速增长到了2018年的8~10万元,结婚标准从2014年以前“只需要在村里建新房”变成了2014年以后的“需要在城里买房”。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作为赡养者的儿子是无法再依照传统孝道规范来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只能选择逃避一部分赡养责任来达到自身行为的脆弱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变迁则是为其行为选择提供了支持。
家庭宗教性的消失使得儿子“嗣”的身份世俗化了,儿子养老的制度安排失去了价值基础。在以“香火绵延”为核心价值的传统家庭宗教中,儿子是家族传承的承载者,其行为具有宗教属性,宗教意义和价值理性是其行为选择中的重要支配因素。在香火绵延的世代序列中,老人因为辈分更高而拥有受人尊崇的地位,可以在生前享受儿子的赡养,死后接受儿子的祭祀。儿子则是通过赡养父母、祭祀先祖获得自己在“祖先—子孙”序列中的位置,获取本体性价值。当家庭的宗教性被去除,养老对于儿子的宗教意义也就消失了,儿子的养老行为不再受到价值约束,而成为了代际之间单纯的资源流动。对于儿子而言,养老的动力除了不稳定的情感联系以外,就只能是依靠代际之间物质层面的交换,进而使得儿子养老从价值逻辑向交换逻辑转变[29]。访谈对象强建国谈道:
家庭宗教属性的缺失使得家庭关系迅速世俗化。代际关系的世俗化让养老失去了价值意涵,交换逻辑与情感逻辑由此取代了传统养老秩序的价值逻辑;男女性别角色的世俗化则让传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安排失去意义,儿子和女儿在家庭中逐渐被赋予了更为平等的角色地位。在子女性别角色逐渐缺乏差异的背景下,交换逻辑给予了儿子将女儿纳入到父母养老责任中的最佳理由,情感逻辑则构成女儿主动参与到养老责任中的主要动力。在访谈中,将母亲接到自己家中赡养的妇女权文芳谈到她参与养老的原因:
2.传统家庭制度下的儿子养老
家庭生产属性的改变使得家庭的结构形态和关系模式发生同步变迁,让儿子养老失去了现实条件。传统家庭经济制度形成了大家庭的规模取向,并形成了父权制的经济基础[30]。在父权支配下的大家庭中,儿子的养老责任受到家庭结构与父代权力的有力保证。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宏观社会变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无论是集体化运动还是打工经济的发展,都使得家庭不再能够作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存在,农村的生计获取单位从家庭降级为了个人。这首先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大家庭的生产组织优势,相反的是,在打工经济下,小家庭的管理优势和自主特征是大家庭所无法比拟的。其次,老人再也难以作为家户长享有在家庭内的绝对权威。在这一过程中,老人在儿子家庭中的位置变得岌岌可危,不仅失去了对家庭资源进行分配的权力,还面临着被迫离开儿子家庭的威胁。访谈对象强建斌谈道:
现在与儿子一起过和自己单独过的老人大概是一半一半,和儿子一起过也是单独过,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就在儿子家住一下。
可以看出,在家庭生产属性的变迁过程中,家庭的核心化与“虚拟直系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26],但是其实质绝不仅是家庭形式的变迁,而是父代权力消退,子代权力崛起的过程,子代由此站在了代际关系的高地,儿子养老失去了内部权力关系的保证。不仅如此,在新的生计模式下,老人与儿子的空间距离变得空前遥远,这让儿子即使想要履行自己的养老义务也面临重重困难。
哈希函数是密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一种将任意长度的输入变换为固定长度的输出且不可逆的单向密码体制。哈希函数主要运用于数字签名和消息完整性验证。
陆游在夔州时曾作《风雨中望峡口诸山奇甚戏作短歌》,一度认为“白盐赤甲天下雄,拔地突兀摩苍穹”这样的景致过于雄健而直露,所谓“凛然猛士舞长剑,空有豪健无雍容”,并因此而发出“不令气象少渟滀,常恨天地无全功”的感叹,但在一个风雨大作的日子,他却忽然发现了云遮雨罩中白盐赤甲景象的奇妙:“今朝忽悟始叹息,妙处元在烟雨中”。平时不太美的景致,之所以会在通常令人悲伤的风雨中而变得完美可人,除了上天的帮助外,主要应该是陆游创作时的精神状态在起作用,是他的情绪由身在蛮乡的一贯低沉消极而偶然变得平和愉悦了。
作为生活单位的家庭有着清晰的界限,它包含了同居共财的一群人,成员关系依据血缘、婚姻与收养关系而确立,成员内部的交往具有极强的情感性,与外界社会的交往又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是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经济共同体。农业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家庭既是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单位、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单位,也是劳动产品的分配和交换单位,家庭构成了传统社会中最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作为社会交往单位的家庭对村庄社会具有强烈的嵌入性,一方面小家庭嵌入于大家族,另一方面大家庭嵌入于村庄熟人社会。故此费孝通曾用“小家族”[17]来表述中国的传统家庭,小家庭对于大家族的嵌入既是横向地嵌入在父系血缘群体中,又是纵向地嵌入在超越时空的家族绵延中,横向的扩展与纵向的延展使得传统家庭被牢牢地嵌入在其所属的父系血缘群体中。同时,传统家庭又往往都是存在于一个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以村民之间的“自己人认同”为基础,其现实表现为村民间的人情、面子、信任与规则,村庄内的社会交往不仅关乎了村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便利与否,更关乎了村民的本体性价值。最后,传统家庭还是一个宗教单位,高达观指出,“中国古代普遍的宗教即是家族社会之宗教”[18],家庭正是进行这种宗教活动的基本单位。家庭祭祀的对象以祖先灵魂为主,各种地方神灵为辅,方式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通过仪式对去世的亲人先祖表达追思怀念,对各种神灵表示崇拜敬仰[19]。通过这一系列宗教活动,村民获得的不是个人救赎,而是家庭幸福、香火绵延的生活价值与生命归属。
我们老人只要是能动都不愿意和年轻人住一起,生活不方便,他们要吃硬的,我们要吃软的,他们早上要睡觉,我们睡不着,生活习惯不一样,住在一起就容易发生矛盾,倒不如分开住自在……儿子就算不孝现在没人说,说了也没有用,他反正也听不到,他还告诉你是老人不愿意和他住在一起哩。
当传统家庭伦理不再具有强制性意义,老人和儿子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不用在乎别人的想法。老人将自己从规范中解脱出来可以生活得更加自由,儿子却因此缺乏了养老的动力,在伦理失去了效用的背景下,养老就只是村民的家事了。儿子养老因此失去了其社会性基础。
3.女儿参与养老责任分担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儿子基于代际关系的交换逻辑很自然会想要将女儿纳入到父母的养老责任承担中,同时女儿出于情感逻辑与关系结构变迁也会萌生出参与父母养老的行为冲动与压力,而家庭的变迁则为女儿进入养老责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迅速推动了这一现象的产生。
2017年夏,我们在庐山认识了李汝庆先生。他的祖父李祥卿,曾参与庐山别墅群的修建,他家的“李广记营造厂”比宋子文岳父的“张兴记”还要早得多。20世纪60年代,李汝庆先生还与赫赫有名的王震将军结下不解之缘。已经88岁高龄的李汝庆先生,头脑清醒,思路清晰,记忆力也很好。他告诉我们,他已连续8年从广州来到庐山度夏。在庐山,他领我们去寻访祖父当年留下的遗迹,看合面街他家的旧址,指点“李广记营造厂”当年建造的别墅。在他租住的屋内,李老连续数日讲述了李氏家族起伏跌宕的历史和他奇特的人生际遇。
书记是个大孝子,他母亲瘫痪在床7年,都是他自己照顾,直到去年他实在承担不了了,找到他的两个兄弟,让他们帮忙承担一下,他们不愿意,书记的老婆找上门去,直接问他的两个兄弟:“老人是不是只生了他(书记)一个儿子?”他们就没有话说了,后来决定一个兄弟照顾一个月。
现在是弟弟和妹妹每个月给钱,我负责照顾。这(养老)在以前肯定是弟弟的事,但是弟弟现在也没有办法,城里的房子也住不下,老人又不能自理,总不能放她一个人在家里住……弟弟当时到我们家就问我:“老的是不是就生了儿子?”这话就没办法回答了。
在交换逻辑下,“养”是对“生”的回报,不再是儿子“嗣”这一神圣角色的固有责任。承受老人生养之恩的不仅是儿子,女儿同样如此,这让儿子在向女儿提出分担养老责任的时候,女儿是没有办法回绝的。不仅如此,代际关系的情感化让女儿在出嫁后不再是“泼出去的水”,依然可以保持与娘家父母的密切联系,进而主动参与到娘家父母的养老责任中,以至于相较于儿子而言,女儿的养老行为更具有情感意涵[32]。可以看到,交换逻辑下的被动与情感逻辑下的主动构成了女儿参与养老责任的双重动力。
林书豪的回应滴水不漏:“嘿,兄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发型,这没关系,你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喜欢我的小辫子,正如我喜欢你的中文文身那样……”
要从根本上解决地名检索中的地理空间的层次结构特性和地名表达的模糊性,就必须结合地名描述、地理空间、计算机、网络等相关知识和技术,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构建基于地名本体的语义网实现基于语义的地名检索服务[2]。
在完成钻孔施工作业以后,应立即开展清孔作业[5]。如果钻孔和清孔工作间隔时间较长,孔内底部的位置就会出现沉淀的情况。一旦沉淀厚度较大,还会出现混凝土夹层的现象,直接增加清孔作业难度系数。而在清孔作业阶段,要想规避塌孔与相关问题的发生,就要确保孔内部水头稳定性。
家庭社会属性的转变是一个脱离村庄社会与重新建立社会联系的同步过程。脱嵌的家庭将自己从烦琐的传统家庭伦理中解脱了出来,家庭内部结构、关系模式和行为选择得以相对自由化、情感化。这在导致代际关系下行[33],形成养老危机同时,也让家庭伦理对于女性依附性角色的设定失去了效力,同时伴随着男女平等的时代话语与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作为妻子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迅速提高,与之相伴随的女性在家庭资源的支配和家庭行为的抉择中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这让女儿在分担娘家父母的赡养责任时,有了充分的行为自主性,以至于当我们问道“你丈夫阻止怎么办”的问题时,有女性直接给出“他能把我怎么办”的答案。与家庭对村庄社会逐渐脱嵌相伴随的是女性与娘家关联的逐步增强,这与女儿的角色变迁相关联,也与村庄社会结构的弱化相联系,从而形成了双系亲属网络并重的现象。对于小家庭来说,女性的娘家也有了和父系宗亲团体一样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支持等一系列功能,因而在强村村民需要借钱的时候,娘家一定会是村民的首选对象之一。对于女性而言,娘家的意义显得更为突出。在访谈中,有女性在谈到自己赡养娘家父母的原因时讲到是因为“兄弟威胁着要断绝关系”,而“娘家是自己最后的依靠”。可以看到,家庭社会属性的变迁对养老秩序的影响是双重的,其包含的是一个家庭网络形态转变的过程[34],这一转变不仅提升女性参与养老的能力,也形成了女儿参与养老的压力。
家庭生产属性的变迁形成了女儿养老的必要性。如果说集体化运动破坏了儿子养老的经济基础,那么随后的打工经济则为女儿养老提出了必然要求。在打工经济下,家庭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来配置劳动力,男性在这一配置中往往需要外出务工寻求更高的经济收入,而女性的行为则具有阶段性:当家庭中孩子尚且年幼、老人尚且健康的时候,女性跟随男性一起务工,而当老人需要照料和孩子进入学龄的时候(这两个时期往往是同时出现),妇女就需要回家照顾老人和小孩,这形成了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留守妇女群体。这一劳动力配置模式一方面降低了男性的养老能力与意愿,增加了他们将养老责任推向女性的动力,另一方面则增强了女性的养老能力与选择权利[5]。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女性很容易弱化自己作为儿媳的“孝”责任,倾向于强调自己作为女儿的“情分”,进而弱化儿子养老的传统秩序,强化女儿在养老中的功能。因而老年妇女张桂芳在谈自己的情况时讲道:
我平时就住在儿子家,儿子都在外面打工,除了收麦子的时候孙子会回来,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冬天就去大女儿家里住,她来接我过去,她说家里冷,怕我一个人出事。大女儿也是在家里照顾外孙读书。
对于老人来说,儿子虽然有养老的责任,但是却没有养老的能力;而女儿虽然没有养老的责任,却在家庭结构转型过程中获得了养老的能力,于是作为留守妇女的女儿就成为老人生活照料的重要依靠。可以看到,打工经济从家庭结构的角度否定了传统儿子养老秩序的合理性,并赋予了女儿养老现实可能性。
4.女儿养老的有限性
如前所述,家庭性质的变迁一方面给儿子养老的传统养老方式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却也为女儿参与养老责任的分担形成了条件,进而形成了女儿参与养老的新现象。但是从经验出发可以看到,儿子养老秩序仍然保持了一定的韧性,儿子依然是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女儿只是辅助者,儿子养老和女儿养老呈现出了“前台”与“后台”之分[35]。
强村居民在分担养老责任的过程中,儿子希望将女儿纳入和女儿可以进入的养老责任领域都是有限的。女儿的养老责任包括了:首先是在儿子外出务工期间经常到父母家中看望父母,问候身体健康与否,当父母身体抱恙时及时提醒兄弟回家或者自己送父母去医院;其次是在父母生病期间到医院照料父母并分担医疗花费;然后是当父母生活不能自理,兄弟必须回家照料父母的时候,支付一定的赡养费给兄弟,或者参与分摊请保姆的花费;最后是在平时看望父母时给一定的零花钱,这些钱构成了老人零花钱的主要来源。但是,有两项内容却是女儿绝对不能参与其中的,它们作为儿子的“特权”出现。其一是老人不能住在女儿家里,这是村民所谓的老人“跟着谁”的问题,老人可以独居,也可以跟着儿子,但是绝对不能跟着女儿住。即使是有极个别的老人住在女儿家中,老人的花费也是由儿子全部负担,并且儿子需要向自己的姊妹发工资,表明是雇了她作为保姆。有趣的是一名女性为了让老人生活得更好,不是将老人接回家,而是给自己的兄弟盖了新房子。其二是老人的葬礼只能由儿子来举办,在葬礼中,只有儿子才是丧主,履行着一系列特定的仪式,女儿的仪式虽然特殊,却与儿子截然有别。
2.儿子部分退出养老责任
这种名实之分既来源于我国家庭独特的现代化路径,又来源于村民对规范资源的策略性援引[36]。伴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传统家庭“四位一体”的属性虽然已经发生改变,却并未沿着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示的道路走向单纯的私人生活单位,而是保持了一定的韧性。家庭虽然不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但是在新的生计模式下家庭依然倾向于保持虚拟的大家庭结构,老人虽不能以家户长的名义但是却可以以资源的形式依然保持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家庭对村庄社会虽然已经不再是高度嵌入,但是村庄内的社会关系对于村民依然具有重要价值,传统规范依然保持了对村民行为的基本限制;家庭的宗教性固然已经不复存在,香火观念早被世俗需求所取代,但是“姓氏传承”的需要依然存在,女儿可以平分情感,却始终难以平分儿子的价值。这些因素都让传统的家庭形态、成员关系和责任义务以某种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方式在村庄社会中弥漫着,从而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两套并行的农村家庭规范。基于这一现状,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现实性需求进行援引、论证,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家庭结构模式与关系安排,如界限模糊的虚拟直系家庭。在这一过程中,儿子通过对两种规范力量的灵活引用与重新解释在减少了自己责任的同时又保持了自己权利的延续,而女儿则是出于自己的情感与新的功能需求与儿子产生共谋,进而形成了当前“双系但有别”的农村养老新秩序。
四、家庭变迁下的养老模式之变
1.家庭性质形塑养老模式
公共课和基础课为校内笔答考试方式;校企共同开发的课程由校企双方共同考核;企业单独上的课程完全由企业自行考核。校企共同考核课程根据上课的内容的比例确定双方给出成绩所占的比例。企业考核课程,根据每门课程的内容,制定相应的考核单,实施过程考核,并且把对员工的基本要求纳入考核。
家庭养老嵌入于家庭结构,家庭结构决定于家庭性质,因而养老模式在本质上存在与家庭性质的紧密关联,这形成了理解我国农村社会中的家庭养老模式变迁的重要视角。
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儿子养老”建基于传统家庭性质。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组织与成果分配单位使得大家庭的结构形式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同时也让了父代作为大家长在家庭中享有极高的权威,这保障了父代在子代家庭中的位置与地位。家庭关于“香火绵延”的宗教内涵划定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将儿子确立为父代的继承者,并根据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将儿子养老作为对男性角色的核心期待施加于男性身上,从价值层面保障了儿子对养老义务的承担。家庭对父系宗亲结构与村庄熟人社会的双重嵌入使得个体的行为必然受到社区伦理的制约,从而使得儿子的养老行为可以通过社会规定的方式来被子代内化和进行外在保证。可以看到,儿子养老是传统家庭性质在养老问题上的秩序表达,家庭的宗教性规定了儿子作为养老的主体,生产性为儿子养老提供了家庭结构条件,社会性为儿子养老提供了规范约束的社会条件,生活性为儿子养老提供了具体的养老形式。传统家庭的稳定性形成了稳定的家庭养老模式。
中国农村家庭变迁是一个“形神俱变”的过程,在形式上,农村家庭的变迁表现出了规模上的小型化、关系上的理性化和边界上的模糊化与灵活化等一系列特征,这构成了家庭变迁的表征。但是在这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变迁过程,即农村家庭性质的变迁,农村家庭性质变迁是一个家庭的生产性、社会性和宗教性同步弱化,并逐渐从“四位一体”转变为单纯的私人生活单位的过程。这构成了重塑农村养老模式的核心力量。
家庭生产性的变迁包含了两个过程,集体化运动消解了家庭的生产组织功能与成果分配权力,大家庭的组织形式失去了效率意义,家庭规模出现了核心化的变迁趋势,父代作为大家长的权力再难以得到经济保证;打工经济使得家庭的经济重心向劳动力更为丰富的子代转移,并改变了农村家庭的生活模式。家庭宗教性的消退使得家庭关系日益世俗化,家庭成员的角色行为失去了神圣意涵,儿子和女儿的性别角色不再具有基于宗教意义的划分。家庭对村庄社会的双重脱嵌让家庭结构与成员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社区伦理的制约,呈现出了强烈的实践性色彩。家庭变迁体现为一种朝向私人生活单位进行转变的趋势,在新的家庭性质下,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家庭的内部结构、家庭成员的行为逻辑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变迁。这消解了传统儿子养老模式的家庭结构基础、价值基础和社会基础,进而引发了传统养老模式的危机,但是也为女儿参与娘家父母的养老提供了社会基础与现实条件。打工经济的生计模式让留守妇女成为主要的在村年轻人口,女性成了村庄中主要的养老主体;养老行为的交换逻辑转向让女儿分担养老责任有了合理性;传统伦理的弱化让女性的行为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于是在儿子养老逐渐面临危机的同时,女儿成了分担养老责任的新主体,进而形成了“女儿养老”的新现象。
2.“双系但有别”:农村家庭养老的新秩序
虽然农村家庭性质已经发生剧变,但是其私人生活化趋势并未彻底实现,家庭依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传统样态,宗教性、社会性和生产性依然以若隐若现的形式存在着,因而女儿在养老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领域依然受到儿子养老这一传统模式的制约,其结果是在农村社会的养老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双系赡养、儿女分工”的养老新秩序。
“双系但有别”养老秩序的形成原因在于儿子依然享有了养老模式转变中的主导权。农村家庭的性质变迁是其宗教性、社会性和生产性受到同步削弱的过程,在这一变迁过程的两极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养老模式。其一是当家庭还尚未开始变迁时,家庭养老模式会呈现为传统的儿子养老模式;其二是当家庭完全实现了自身的私人生活化之后,养老模式会呈现为彻底的双系养老模式。两种养老模式以两套行为规范的形式存在于村庄社会中,在家庭正处于变迁之际,两套规范相互冲突但却都具有合理性,于是行为者的主观意愿与行动能力就具有了形塑新型养老秩序的决定性意义。相较于女儿,家庭性质和养老模式的变迁起点决定了儿子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了优势性地位,其结果是儿子掌握了形塑新型养老秩序的主导权。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进城买房和支持子女结婚的经济压力正在日益增大,这些压力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落在了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中年男性身上,其结果是作为儿子的中年男性很难再承受过重的养老负担,同时对代际关系抱有了功利性的期待。在掌控了形塑养老秩序主导权的情况下,儿子一方面希望可以将女儿引入到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中,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女儿分享自己对于父代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的占有权利,这构成了儿子利用主导权来形塑对自己有利的养老秩序的核心动力。于是儿子通过对两套规范的策略性引用和论证,实现了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责任,但是却由儿子单独享有相关权利的新型养老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儿子要求女儿和自己一起承担父母的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心灵慰藉等实质性内容,然后垄断了和父母共同居住、为父母操办丧事的仪式性内容。对于养老实践而言,实质性内容是为了保证老人的生存或者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仪式性的内容则是为了给社会规范一个交代,这些仪式性的内容不仅可以让儿子免受村庄社会舆论的惩罚,也是儿子得以继承父代资源和社会身份的合法性所在。因而这一安排不仅合乎了儿子的功利性和伦理性需求,也满足了女儿的情感性需求,从而形成了新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
不久,果然隐约听到一些传言,说我勾引良家妇女。尤其是镇政府家属院子里的女人,多是半边户,整天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挤在一块扯家常,东家长西家短,扯得最多的偷人养汉。有时我从院子里走过,明显地感觉到有眼光像刺一样扎在我背上,远远地还听到她们放荡的笑声。哎,人言可畏哟。
五、结论
可以看到,家庭养老模式内嵌于家庭结构,家庭结构形式的变迁必然是引发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重要原因,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一方面农村家庭形式的变迁并不是导致家庭养老模式变迁的唯一因素;另一方面家庭形式变迁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层次的家庭性质变迁。家庭性质的改变可能才是在家庭层面对养老模式进行形塑的首要原因,也是对当前普遍出现的“女儿养老”现象最具解释力的变量之一。农村家庭的变迁路径是一个从“四位一体”式家庭逐渐转变为私人生活单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出现了家庭宗教性的弱化、社会性的弱化和生产性的改变。家庭性质的变迁一方面通过消解传统家庭的结构形式弱化了儿子养老模式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直接摧毁了儿子养老的价值与社会基础,从而造成了传统儿子养老模式的结构性危机。所幸的是这一过程在形成儿子养老危机的同时,同步释放了女儿的养老潜力,从而形成了女儿参与养老过程的新现象。家庭变迁的过程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虽然宏观社会的变迁给了家庭变迁以充足的推动力,但是在厚重的传统家庭文化的支配下,农村家庭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文化韧性,这构成了对传统儿子养老模式的结构性支撑,并给予了行为主体实践能力发挥作用的博弈空间。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儿子和女儿的实践能力对比和行为取向共同发挥作用,共同塑造了当下“共同赡养、儿女分工”的新型家庭养老秩序。
参考文献:
[1]田瑞靖.乡土社会中的“女儿养老”:实践机制及其效果——基于鄂中L村的调查[J].南方人口,2013,28(3):46-53,72.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许琪.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J].社会,2015, 35(4):199-219.
[4]张翠娥,杨政怡.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寻乌县的调查数据[J].妇女研究论丛,2013(5):27-33.
[5]聂焱.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女儿养老与儿子养老的比较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8(8):114-118.
[6]钟涨宝,杨威.原生家庭偏好、现代性与农村女儿家庭养老——基于湖北省红安县的实证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7(4):115-125.
[7]吴元清,风笑天.论女儿养老与隔代养老的可能性——来自武汉市的调查[J].人口与经济,2002(5):49-54.
[8]朱安新,高熔.“养儿防老”还是“养女防老”?——中国老年人主观意愿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16(4):36-44.
[9]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0]高华.刍议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新性别差异——对晋东S村的实地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2,18(2):72-81.
[11]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江海学刊,2008(4):108-113,239.
[12]杨菊华,何炤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研究,2014,38 (2):36-51.
[13]郭志刚.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14]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09 (5):84-92.
[15]张佩国.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2(1): 9-18.
[16]王德福.中国农村家庭性质变迁再认识[J].学习与实践,2015(10):85-91.
[17]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8]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19]王善军.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J].世界宗教研究,1999(3):114-124.
[20]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 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1]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22]王天夫.中国传统大家庭数量为何被低估?[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7-25(A08).
[23]狄金华,钟涨宝.社区情理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产——基于鄂东黄村的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2):79-85.
[24]王天夫,王飞,唐有财,等.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5(2):41-60,203.
[25]雷洁琼.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6]王跃生.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5):36-48,95.
[2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申端锋.新农村建设的文化与伦理纬度[J].学习与实践,2007(8):148-151.
[29]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J].中国学术,2001(4):12-23.
[30]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7-16.
[31]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32]高修娟.农村女儿养老问题研究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 2014(5):109-112.
[33]范成杰.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0-95.
[34]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社会学研究,2011,25(2):182-216,246.
[35]高修娟.前台与后台:皖北农村“养老-送终”活动中的性别权力景观[J].妇女研究论丛,2014(2):18-24,33.
[36]沈奕斐.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D].复旦大学,2010.
ChangesofRuralFamiliesandDaughterSupporttheOld
WANG Chao-fan,GAN Ying
(ChineseRuralGovernanceResearchCenter,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4,China)
Abstract: Married daughter participate in supporting their parents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rural society. Field research in Qiang village found the change of family nature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Rural family change is a religious weakening, social weakening and productive process, which has led to the gradual change of families to simple living units. The change poses the crisis of the son’s old-age support,and releases the daughter’s potential, and forms a new phenomenon of the daught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old-age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ierce changes, rural families have maintained considerable cultural resilience, which constitutes a structural support for the traditional son support for the old, and gives the game space for the behaviour agents to play 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is game, practical ability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 of son and daughter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jointly shape the new family support order of “common support,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son and daughter”.
KeyWords: aged supporting in rural areas; daughter support the old; family change; rural society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9)02-0059-12
收稿日期:2018-12-19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9.02.006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0845)
作者简介:望超凡(1993—),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基层治理。E-mail:wcf1993610@163.com
标签:家庭论文; 儿子论文; 女儿论文; 社会论文; 传统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0845)论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