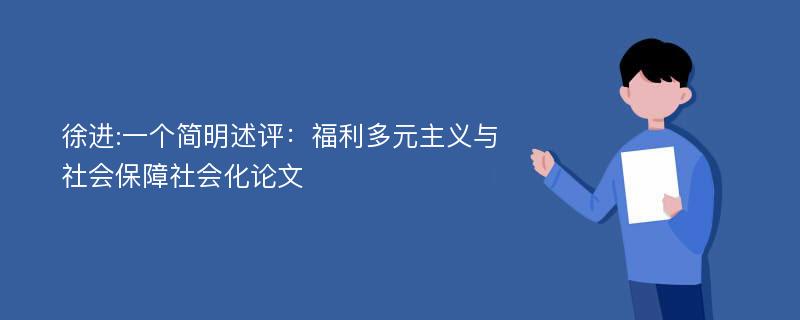
摘 要:西方的社会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和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化理论作为当今世界两大福利供给理论范式,各自历经了多年的理论变迁,已逐渐被世界社会保障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接受。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起源于简单二元论,经历了福利三分法、福利四分法和福利五边形等发展阶段;“社会保障社会化”一词首见于我国的“七五”计划,随后其理论体系逐步被发展和完善。福利多元主义和社会保障社会化理论均主张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但是,福利多元主义因过分专注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而今已失之狭隘;而社会保障社会化以社会共同责任本位为理念基础,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三层社会保障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和全民化为终极奋斗目标,堪为真正意义上的福利治理理论。
关键词:福利供给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社会保障社会化;网络治理;福利治理
引 言
作为一项涉及福利供给的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划分主要取决于福利供给主体体系构成及各主体间如何协同合作以有效提供经济福利的情况,而个人责任的回归以及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改革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力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福利供给的理论范式,主要有两个:一是西方社会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二是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化理论。前者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社会有关“福利来源”问题的讨论浪潮;后者则出现于1986年中国“七五”计划之第五十一章“社会保障事业”关于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
1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福利多元主义,又被称为混合福利经济思想,其理念最早由英国学者蒂特马斯所阐释,他在《The Social Division of Welfare》一文中指出,三种福利,即社会福利、财税福利、职业福利,形成福利体系,它们相互配合,共同维持该体系的运行[1]。因此,蒂特马斯在福利多元主义领域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从福利属性角度来划分社会总体经济福利,即社会福利、财税福利、职业福利;二是提出“福利体系”一词,并主张三种福利相互间的配合协作,以维持该体系运行。但是,蒂特马斯并未直接谈及三种福利具体由谁来负责提供,即“福利从哪里获得”的命题,使得其只能是西方社会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拓荒者而非奠基人。
学术界普遍认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发轫于西方社会对英国学者沃尔芬德在1978年所作的题为《The Futur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报告所引发的有关“福利来源”问题的讨论浪潮,该报告主张“把志愿组织也纳入社会福利提供者行列”。1979年由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zations出版的《Gladstone’s Voluntary Action Organiz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一书,因主张“有效的福利供给应该更多地依赖志愿行动”,将大讨论推向高潮。
英国学者罗斯是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他在《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一书中剖析了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指出福利多元主义存在两个核心内涵:多元化和分散化,即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福利资源配置的非垄断性,进而提出了福利多元组合理论:福利社会应当是混合型的,即混合福利社会,由家庭、市场、国家充当三个不同的福利提供者,社会总福利等于三个部门的福利加总[2]。
在西方社会,对福利多元主义进行的论述主要存在简单二元论(福利二分法)、福利三分法、福利四分法、福利五边形等四种理论形态。其中,简单二元论和福利三分法之基准三角形理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只能算是该理论的雏形范式,由荷兰学者克雷斯·德·纽伯格(以下简称德纽伯格)加以总结;而福利三分法之福利三角形、福利四分法和福利五边形才是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实际范式。
1.1 简单二元论
2.2.2 社会保障学中的涵义
明确划界标准,“依法划界,依据确权”,既要有法可依,又要有策可循,也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既要有利于水利工程的安全管理、设施稳定运行和效益的充分发挥,又要保持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稳定。应参照其他各类工程利用现状,合理界定管理范围。
简单二元论将福利资源配置或福利供给的主体简单地一分为二(如图1所示),即政府和市场,是存在明显局限性的:不仅忽略了“总有一些财富被创造于市场之外,且不存在政府干预”的经济现象,而且回避了市场和政府可能会产生同时失灵的特殊窘境。另外,简单二元论对家庭作为福利供给主体角色的视而不见,暴露了其作为一种有关福利供给的理论形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
周泽赡把小鸡带到一块小方草坪上,小鸡好奇地啄着不同的光影,周泽赡在一旁蹲着守着它。周泽赡腿蹲麻了,起身张望着,镜头随着她的视角,停留在不远处开着花朵的绿化带上,她看了一眼正玩得开心的小鸡,走向那片地带,她脸上掠过一丝不安。小鸡突然大叫起来,周泽赡还在搜索着树枝,她找到树枝的同时,猛地一皱眉,看向小鸡那里,有一只黑猫准备发起攻击。特写周泽赡绝望的脸,她手里拿着棍子,迟疑地站定不动,黑猫迅速扑向小鸡,嘴里衔着猎物跑走了。周泽赡发疯似的奔向黑猫跑过的路,是无生物的过道,灰色的水泥板,画面呈冷色调。
图1 简单二元模型
1.2 福利三分法
福利供给的主体由三方构成,是福利三分法的核心特点。福利三分法主要有基准三角形和福利三角形两种理论论述。
1.2.1 基准三角形
按照德纽伯格的观点,基准三角形理论将福利供给的主体分为三方(如图2所示),即家庭、市场和社会网络。每一方分别占据三角形三个顶点的任意一点,然后用曲线将三个顶点彼此连接,形成福利供给的三角形结构。
基准三角形描述的是社会成员寻求生活资料的三个渠道:家庭、市场和社会网络,由此三个渠道提供生活资料以满足其对基本福利的需求。
德纽伯格认为,在一个缺乏公共慈善事业的社会,社会成员可以通过采取参与市场活动(就业于市场生产部门或服务部门)、转向家庭成员或亲属、动员其有效的社会网络关系三个福利供给渠道,来开展福利寻求活动,以满足自身对生活资料的需求。
图2 基准三角形模型
可见,基准三角形理论并未将国家这一福利供给主体纳入考虑范围,这违背了一个实际,即社会保障实践自古有之,提供社会福利一直是国家职能体系的构成之一。虽然具体到一国或地区社会保障实践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这种职能体系结构所展现出来的效度存在差别,却绝对不能否认这一实际。
还有不少学者从社会保障的社会性、主体社会化、项目社会化、体系层次化、基金运营社会化、服务队伍社会化等多个维度对社会化内涵进行了阐释。可见,从概念内涵上来看,社会保障社会化不仅包括福利多元主义的两个核心内涵,即多元化和分散化,同时涉及社会性和全民性两大内涵属性。因此,社会保障学科中的社会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性概念范畴,社会性和全民化是其本质属性和终极目标,其运行过程体现了多元化(分散化)特征,涉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保障对象的多元化、保障项目的多元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管理的多元化、服务的多元化、监督的多元化等诸多方面。
罗斯颠覆了福利来源“二分法”的主张,成为首位对社会福利供给主体采用三分法的西方学者。在罗斯的研究基础上,德国学者阿德尔伯特·伊瓦斯在《Shifts in the Welfare Mix:Introducing a New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Transformations in Welfare and Social Policy》一文中将家庭、市场和国家分别设置为福利供给的三角,并在考虑文化、经济、政治的背景下,并从组织属性、运行价值和互动关系三个维度(见表1)对三角中的三方进行了明确论述,建立了福利三角形模型(福利三角理论)[3]。这标志着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形成,伊瓦斯也因之成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福利三角形模型展示了两个互动平衡关系:一是福利供给主体体系所涉三方之间的互为补充平衡关系;二是福利接受者与福利供给者之间的供需平衡互动关系。在福利三角形中,家庭是福利对象最直接的福利供给者;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是基本保障;市场满足福利对象多元化的福利需求。研究者们一致强调了保持以上两个互动平衡关系稳定性的重要性,即:平衡状态一旦被打破,如过分强调国家供给福利的作用,就容易引发社会福利危机。
表1 伊瓦斯的福利三角形模型
市场 正式的 选择与自由 福利对象与市场国家 公共的 平等与保障 福利对象与国家家庭 非正式的/私人的 团结与共享 福利对象与社会
福利三角 组织属性 运行价值 互动关系
另外,从互动关系之家庭与“福利对象与社会”这一角度来看,福利三角理论涉及的福利供给三方中的一方—— 家庭,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非单指血缘关系网络,还应该包括邻里、朋友、同学等社会网络。
福利三角形理论所阐述的福利供给主体,即家庭、市场、国家,是福利供给主体体系的基本构成主体,即使是随后出现的福利四边形、福利五边形理论也不得不遵从此三个主体作为其福利供给体系的主要构成之现实。因此,福利三角形理论不仅是福利供给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也是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后续发展的基本遵循。
当然,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如阿布瑞汉森、德纽伯格、魏干德,在遵从福利三角形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的前提下,从不同侧重点对福利三角理论作了略有不同的表述,在此不作赘述。
1.2.3 社会总福利公式
主张福利三分法的西方学者如罗斯、伊瓦斯、阿布瑞汉森,在肯定国家在福利提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福利供给是全社会的责任,国家并非唯一的责任承担者,家庭、市场、国家都应当是福利供给者。同时,他们认为由家庭、市场、国家提供的福利总和即是社会总福利,用公式表达为:TWS=H+M+S。该公式是对福利三角理论范式的最好表述,其中,TWS表示社会总福利,H是家庭福利,M是市场福利,S是国家福利。
另外,奥尔森在其后期的研究中放弃了福利二分法(简单二元论),在《Social Security in Sweden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Tree Essays》一文中将市场、国家、民间社会(家庭、邻里、志愿组织等)作为福利供给的三个主体,进而对民间社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围绕“福利的分散化与私有化”问题,深入分析了福利供给主体多元组合问题[4],丰富了福利三分法的理论内涵。
1.3 福利四分法
式中:W为螺柱受力(N);DG为垫片中心圆直径(mm);D为螺柱直径(mm);b为垫片有效密封宽度(mm);m为垫片系数;n为连接系统螺柱数量(个);pe为等效压力(MPa)。
英国学者诺曼·约翰逊一贯主张福利四分法,分别在《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和《Mixed E-conomies of Welfare: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两篇文章中,就福利供给主体多元组合问题作了详细阐述,认为福利供给具备非垄断性特征,并在福利三角理论所阐述的三个福利供给主体(家庭、市场、国家)的基础上,增设了志愿部门[5-6]。
为了科学有效地服务农民,云天化还同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的团队合作,成立了云天化植物营养研究院和云天化营养学院。其中,成立植物营养研究院的目的是对不同作物生长所需的营养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为作物提供更加科学、精准的营养配方和解决方案。而植物营养学院成立的目的则是为了培养优秀的农化服务人员,让营销人员、经销商、客户掌握更加科学、全面的农化知识。除此之外,云天化还同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开展科技小院项目,让学院专家以及公司专业的农化服务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实地解决农民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从各个方面提供后端支持,全面落实“产品+服务”的理念。
美国学者尼尔·吉尔伯特和特瑞尔拓展了诺曼·约翰逊的主张,在《Dimension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一书中指出,福利四分结构存在两层含义:一是福利供给主体体系由政府、经济组织、非正式组织和志愿组织四部门构成,社会总福利通过此四部门输送给福利对象;四部门嵌入福利国家市场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虽然各部门在福利供给的过程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却无一避免地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7]。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伊瓦斯转而主张福利四分法,在《Wohlfahrts Pluralismus:Vom Wohlfahrts Staat Zur WohlfahrtsGesellschaft》一文中对福利三角理论范式给予了修正,认为福利供给的主体有四个,即市场、国家、社区和民间社会[8]。其中,社区包括家庭、非正式群体等非正式组织;民间社会,即市民社会,也就是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中的第三部门组织(NGO和NPO)。伊瓦斯非常看重民间社会的存在价值,认为它在市场、政府、社区三者之间各架起了一道桥梁,能够使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一致,换句话说,民间社会提供的福利对社会总福利的整合起到了润滑和助推作用。
伊瓦斯和吉尔伯特的福利四分法主张亦可采用图3诺曼·约翰逊的福利四分模型来描绘,其机理并无不同,差异仅存在于四边形的某一角所代表的福利供给主体略有不同。
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学科中的“社会化”一词,初见于“七五”计划所提出的“社会保障社会化管理”目标,这是我国首次在官方文件中阐述社会保障发展问题。因此,在社会保障实务界,社会化是社会保障的一种管理理念或手段。
可见,主张福利四分法的西方学者,无一例外地扬弃了福利三分法的理论主张,一致认为负责福利资源分配的主体不止于家庭、市场、国家,还应当纳入社区、志愿组织、民间社会等组织或群体,从而丰富了福利供给主体体系。
体育活动时,技术动作自然而然地做出来,用不着去想该怎么做,一旦知道要做什么,就能顺利地表现出来,而且完成的效果往往好于自己的预期。
图3 诺曼·约翰逊的福利四分模型
遗憾的是,不管是福利三分法还是福利四分法,均未就“福利供给主体体系各主体间如何采取相互融通、协同合作以实现有效提供经济福利”这一重要议题进行阐述,致使此两个理论仅仅停留在福利供给主体多元组合的粗浅主张层面。
诺曼·约翰逊、伊瓦斯、尼尔·吉尔伯特三位学者是西方社会主张福利四分法理论的典型代表。
1.4 福利五边形
福利五边形理论模型是福利五分法理论的核心,主张福利五分法的西方学者主要是罗伯特·平克和德纽伯格。
英国学者罗伯特·平克在其《Making Sense of 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一文中首次提出“福利文化”(Welfare Culture)一词,认为福利文化由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两部分构成,在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内涵,具体呈现于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提供的各类福利项目中;同时,他就福利供给主体体系作了拓展式阐述,指出福利供给部门应当包括公共部门、非正式部门、私人部门、志愿部门和互助部门[9]。“福利文化”概念的提出,使得福利供给主体提供经济福利的行为具有了精神层面的依托,丰富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内涵。
德纽伯格的福利五边形思想,集中体现在《The Welfare Pentagon and the Social Management of Risks》一文中。他表示,基准三角形理论分析框架并不完整,不但应将承担一定社会福利分配职责的政府纳入框架,而且还应把会员组织(如工会、商会、相互保险公司、合伙公司等)作为第五个福利供给主体,形成福利五边形(如图4所示)[10],这成为福利五分法的核心理论。
德纽伯格并不否认会员组织存在与市场、社会网络重合的情况,进而强调了将会员组织作为一个必要福利供给主体加以看待的深层意义:与社会网络相比,个人拥有更多加入或退出会员组织的自由选择权;与市场相比,会员组织在应对会员供需行为时,拥有更少地受制于市场机制的优势。
德纽伯格将福利五边形作为分析社会总体经济福利的基本框架,认为福利对象为满足其基本需求,既可以通过福利五边形的某一角得到满足,也可以通过寻求福利五边形各个角的不同有机组合来获得满足。
图4 福利五边形模型
德纽伯格特别指出了福利五边形的社会性本质,即福利五边形的每一角均不是封闭、孤立的福利供给主体,彼此之间是有联系的,相互之间的融通提高了解决福利问题(满足基本需求)的效果,体现了福利供给主体相互间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互惠性,形成新的福利五边形(如图4所示)。如某一福利对象决定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工资报酬这一福利,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另一方依照劳动协议准备雇佣前者并支付其应得薪酬;如果福利对象决定依赖家庭获得生存所需,应当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准备且能够满足其需求,等等。
总之,福利五分法,尤其是福利五边形理论,已经摆脱了福利三分法和福利四分法仅仅停留在福利供给主体多元组合的粗浅主张层面(拓展福利供给主体体系方面),转而强调福利供给主体体系内部主体间存在互惠性联系这一事实,进而指出福利供给主体间的相互融通,可以提高经济福利的整体供给效果,为后来者就“如何实现福利供给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以有效提供经济福利,进而满足福利对象的基本需求”这一命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启发和足够的研究余地。
1.5 福利五角模型
借鉴德纽伯格的福利五边形模型,笔者将新福利五边形,即福利供给主体间相互融通互惠的福利五边形模型,姑且称之为福利五角理论(如图5所示)。实质上,“五”是一个虚数,在一国或地区的福利治理进程中,可能会出现福利供给主体的更多元组合,如福利六边形、福利七边形等。总之,无论福利供给主体体系的构成怎么细化或整合,各主体之间有效开展协同合作,实现极限性的融通与互惠,以极大增进福利对象的福祉,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方是福利治理的应有之义。
图5 福利五角模型
2 社会保障社会化理论
2.1 社会保障社会化的提出
1986年4月12 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七五”计划),首次单独设章(第五十一章)将社会保障事业载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现了我国社会保障国家治理的五个历史性突破:一是提出了“社会保障”一词;二是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阐述了社会保障改革的理念为社会保障社会化;四是要求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隐含“个人责任回归”的现代社会保障原则;五是明确了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军人优抚和互助保障(以家庭保障为主)所构成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理念。
“七五”计划有关社会保障事业五年发展目标与任务的谋划,为我国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指明了方向,即开启社会保障社会化进程。因此,作为一个重要年份,1986年被公认为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元年。
社会化犹如城市化、现代化、网络化,是一个过程概念范畴,在社会学和社会保障学两个学科中呈现出了两类根本不同的涵义。
2.2 社会化的概念界定
自1986年以来,伴随社会保障社会化理念,我国社会保障经历了改革、定型、发展三个重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用下,如何解决我国社会保障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成为实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保障科学发展的重大课题。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障社会化这一福利供给理论略作述评,或许可以为推进我国福利治理进程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2.2.1 社会学上的涵义
在社会学中,社会化是一个揭示人的社会化过程的概念,指的是个人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同郑杭生所提出的社会化概念,即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因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与社会保障毫无关系,是一个单纯地界定人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化这一过程的概念范畴。
简单二元论,亦称福利二分法。自从“市场自动均衡”经济思想最终破灭后,以“国家适当干预经济”为核心理念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盛行。在德纽伯格看来,简单二元论(以瑞典学者奥尔森为代表,后转而主张福利三分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被主张,即多数情况下,市场自身是可以有效率地提供社会福利的,但不排除一些例外情况的发生,如市场失灵或违背公平正义,此时则需要国家出面保障社会福利的供给及其合理分配。
综上所述,该工程地质特点为拟建场地人工填土层厚度较大,为2.40~2.80m,土质杂乱,填垫年限小于10年,不能作为持力层使用。下部④1层黏土土质一般,强度尚可,但厚度较薄,其下分布厚层淤泥质黏土(地层编号⑥2),土质软,压缩性高,为浅基础软弱下卧层,故本工程采用桩承台基础。桩型选用混凝土C80级PHC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桩端持力层为⑨1粉质黏土层,桩长27m。承台埋深为-2.55m,承台高度950mm,承台顶标高为-1.60m。
2)施肥时间不当。部分果农施肥随意性大,追肥时间因个人资金、劳力而定,秋季基肥因果实采收等原因,常常推迟到第2年春季施(或干脆不施),打破了苹果树的“生物钟”,造成肥料利用率低,不利于树体生长。
在我国社会保障理论界,存在对社会化内涵进行阐释的多元主张,主要观点如下:
香港学者黄黎若莲在阐释社会化概念时,强调福利照顾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而是人人有责,福利提供、融资、管理应该采用多层次和多渠道的方式,让大众积极参与[11]。
冯兰瑞指出,社会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特征,理解角度有三:一是社会保障对象的全民化,即全体社会成员都应是社会保障对象,都有平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二是树立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观念,即社会保障不只是政府的责任,应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通过代际收入转移的方式,供全社会调剂使用;三是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即积极促进落实社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逐步过渡到全国统筹,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管理和调剂使用收缴的社会保险统筹基金[12]。
林闽钢认为社会化的实质是采用多元化和多来源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并大胆预测了我国社会保障福利供给的未来发展趋势:从政府转移到民间;从一元变成多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从机构式照顾变成社区与家庭照顾;从单一的提供者与提供方式变成组合式的提供者和提供方式[13]。
郑功成合理阐释了社会化的内涵,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开放性,即以立法为基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并接受其监督与评价;二是筹资的社会化,即社会保障资金的多元化筹集,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用人单位缴费、社会保障对象缴费、社会捐赠、发行福利彩票、减持国有股、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国际援助,等等;三是服务的社会化,即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实践离不开社会各方的支持、参与和推动;四是管理与监督的社会化,即通过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实施“放管服”改革,实现社会保障的管理和监督从政府专责向社会化监管(营利性组织、第三部门组织、国际组织均可参与监管我国社会保障实践)发展[14]。
根据塔里木河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析,当前,各类节水项目工程建设已完成80%以上,工程节增水量已超过23亿m3,而且,各源流近几年天然来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但是,各源流下泄干流水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都在减少,各源流灌区不仅占用了通过塔里木河项目建设实现的节增水量,还占用了原来的河道下输生态水量。2008年,各源流下泄塔里木河干流的水量比治理前还减少了7.77亿m3,距离规划目标还相差18.1亿m3。干流断流长度在逐年增加,时间在延长,究其原因,主要症结在于管理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1.2.2 福利三角形
物资管理作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施工企业管理的一个分支学科。当前,国内施工企业的项目材料管理基本停留在简单的出入库,对于当下动辄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造价的施工项目来说这种管理方式工作效率低,控制难度大,成本费用高,信息反馈不及时,使得本来就有限的流动资金很难满足施工需要。
2.3 社会保障社会化的概念界定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社会保障社会化是一个贯穿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改革和发展全过程,以社会共同责任本位为理念基础的系统性概念,具体是指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依托,改革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机制,鼓励和支持多方力量参与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事业,并为其提供适宜的宏观政治、经济、社会、公共安全等发展环境,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求(经济、服务、精神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和全民化为终极奋斗目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供给理论。
高血压较易发生的合并症为左心室肥厚伴左心衰竭,诱因与心脏左心房变大和心脏血流动力学改变存在相关性,与此同时,增加循环阻力后会致使左心室形成代偿性向心性肥厚,从而提升左心衰竭发生率。据有关统计表明,在高血压疾病中左心室肥厚伴左心衰竭的比例可达0.4%,同时该疾病的病情相对危重,若不能实施治疗会对其生命安全构成危及[4]。由此可见,尽早诊断和尽早治疗对生存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 福利多元主义与社会保障社会化的差异
结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福利多元主义和社会保障社会化均为当今世界涉及福利治理(福利供给取向)的两大重要理论;二是社会保障社会化较之于福利多元主义,不止于阐释多元福利供给主体及其组合的理论,而是具有更丰富内涵和更大发展张力的理论范畴。
比较二者,可以发现福利多元主义与社会保障社会化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同。
3.1 核心概念的外延不同
福利多元主义中的“福利”与社会保障社会化中的“社会保障”两个核心概念,具有根本不同的外延。前者不仅包括广义上的社会福利,即社会保障,还包括一切与民生福祉有关的经济福利(能够用货币来衡量的),如市场就业收入;后者仅指广义上的社会福利,即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狭义上的)、军人保障等基本社会保障项目和员工福利、商业保险、家庭保障、社区服务、企业年金、慈善事业、互助保障、社会服务等补充保障措施。
农机深松整地技术推广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为了促进农机推广工作顺利推进,必须要对推广管理体制进行完善。由于在传统的农机推广过程中对农机深松整地技术的推广工作不够重视,导致一部分推广人员有所懈怠。对此,相关部门必须要明确农机深松整地技术的重要性,加强对农机深松整地技术推广工作的安排,需要在原有的工作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例如要加强对农机深松整地技术人员的考核,将人员的考核与推广工作结合起来,完成推广任务的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员将会受到一定惩罚,以奖罚分明的措施带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其加深对农机推广工作的认识,深入到基层,对群众开展教育和引导。
3.2 福利供给主体的范围不同
依照福利五边形理论,西方社会涉及的福利供给主体不仅包括政府、市场、家庭、互助组织、社会网络,还包括会员组织,如工会、相互保险公司、合伙公司、商会。在我国社会保障社会化过程中,福利供给主体不包括工会、商会、学术团体等非营利性会员组织,仅限于政府、市场(包括商业保险公司)、家庭、慈善组织、互助组织和社会网络。
3.3 福利供给的内容不同
福利多元主义仅从经济保障层面阐释了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构成及其有效协同合作,针对的是福利对象的经济保障。然而,社会保障社会化理论及其实践,不仅限于社会保障对象的经济保障层面,还涉及服务保障和精神保障两个更高层面,三者均为社会保障社会化的应然客体,都依托有效的社会保障社会化管理和服务过程而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
多年来处于贫困地区的学校办学成本较高,例如对寄宿制学校宿舍、学校食堂等生活设施的金投入,其中村小的教学运转较为艰难,也成为了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多年来的薄弱环节。对此,政府不断提出建设工程与计划:
3.4 福利治理的过程不同
福利多元主义和社会保障社会化均主张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也认同各主体之间的融通与互惠价值法则,但是治理过程存在很大差别。前者仅强调多元福利供给主体及其有效组合问题,后者还涉及到了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监督等多方面的社会化问题。因此,社会保障社会化理念涉及了更为丰富和更具发展张力的福利治理理念,更为全面、合理和科学。或者说,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较之于社会保障社会化理论,是较为狭隘的福利治理理论(福利供给取向),而社会保障社会化理论内涵丰富、张力更足,展现了更为明显的网络治理倾向,堪为真正意义上的福利治理理论。
对稍大些的儿童适当的锻炼可以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次数,从而减少喘息的发作,但必须注意保暖,气候骤变要注意适当着装,以防受凉引起喘息发作。
4 结 语
目前,在我国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征程中,我国社会保障社会化依然存在两大实施困境,即理解误区和实践偏差:前者如家庭保障思想淡薄、精神保障观念缺乏、“商业保险不是社会保障”观念、社会网络保障概念不明、绝对的“就业保障非社会保障”观点、“慈善事业是部分人的事”等方面的现象较突出;后者如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且存在实施困境、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偏低、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困难、部分企业逃避缴费责任、社会服务从业人员非专业性明显等方面的问题或多或少地存在,成为有效推进我国社会保障社会化进程的制约性因素。作为当今世界两大福利供给理论范式,福利多元主义和社会保障社会化之理论内涵尚有待更多的研究者加以深入分析和研究。只有聚焦社会保障社会化实施困境,找寻破解难题的路径,才能满足我国新时代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Titmuss R.The social division of welfare.essays on the welfare state[M].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8:34-43.
[2]RoseR.Commongoalsbutdifferentroles:thestate’s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3-39.
[3]Evers A.Shifts in the welfare mix:introducing a new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transformations in welfare and social policy[M].Vienna:Eurosocial,1988:7-30.
[4]Olsson SE.Social security in sweden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tree Essays[J].ESO,1993(4):3-7.
[5]Johnson N.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M].Brighton:Wheatsheaf,1987:20-28.
[6]Johnson N.Mixed Economies of Welfare: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Prentice Hall Europe,1999(3):11-25.
[7]Gillbert N,Terrell P.Dimension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M].Boston:Pearson Allyn and Bacon,2005:10-200.
[8]Evers A.Wohlfahrts pluralismus:vom wohlfahrts staat Zur wohlfahrts gesellschaft[J].Opladen,1996(7):14-23.
[9]Pinker R.Making sense of 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J].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1992(2):20-26.
[10]Neubourg DC.The welfare pentagon and the social management of risks[J].Social Security in the Global Village,2002(9):5-17.
[11]黄黎若莲.“福利国”、“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市场化”[J].中国改革,2000(10):62-63.
[12]冯兰瑞.全面理解 切实实现社会保障社会化[J].中国社会保障,2001(9):9-11.
[13]林闽钢.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J].社会,2002(7):36-37.
[14]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22-23.
A Concise Commentary:Welfare Pluralism and Socializ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Xu J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anzhou Gansu,730070,China
Abstract:Western social welfare pluralism theory and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socialization theory,the two major theoretical paradigms of welfare supply in the world today,have gone through years of evolution and have gradually been accepted b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of social security in the world.Welfare pluralism and social security socialization both advocate pluralistic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welfare and has altered the roles of the state,market,and civil society in welfare provision.While welfare pluralism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rovider of welfare supply,socializ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mm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realize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at covers all citizens,and therefore can be regarded as a more reasonable theory of welfare governance.
Key words:welfare provision theory;welfare pluralism;socialization of social security;network governance;welfare governance
DOI:10.11885/j.issn.1674-5094.2019.03.05.03
文章编号:1674-5094(2019)03-0029-08
中图分类号:C913.7,F840.61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9-03-05
作者简介:徐 进(1982-),男(汉族),山东淄川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2017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七五’计划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及其启示”(YB108);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研究”(13BZZ026)。
徐 进.一个简明述评:福利多元主义与社会保障社会化[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3):29-36.
Xu Jin.A Concise Commentary:Welfare Pluralism and Socialization of Social Security[J].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9,21(3):29-36.
编辑:余少成
编辑部网址:http://sk.swpuxb.com
标签:福利论文; 社会保障论文; 社会论文; 主体论文; 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行政管理论文;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2017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 七五'; 计划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及其启示"; (YB108)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西北民族地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研究"; (13BZZ026)论文; 甘肃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