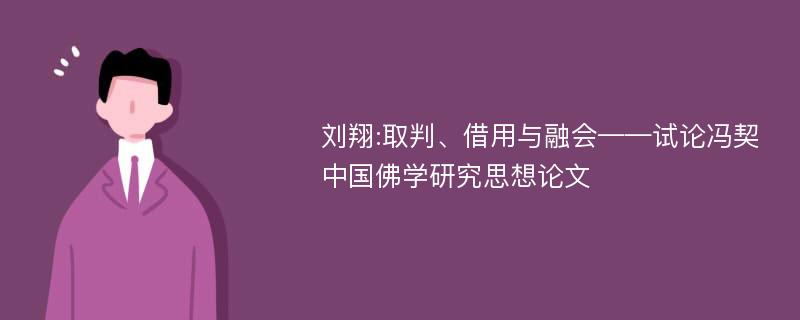
摘 要:冯契先生的中国佛学研究是其哲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或隐或显地反映在其哲学史研究和“智慧说”体系当中。冯先生将中国佛学作为其理论的资源,立足哲学史和比较哲学视域,取其理论的精华,做出客观的评判,并借用若干佛学的概念,融会于其的“智慧”学说当中,创造性地给予自己的解释。对佛学思想的判释和融贯,体现了冯契“会通中西”的哲学态度,也展示了其自成一格的哲学创造,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佛学;转识成智;顿悟;智慧
相比对“认识”和“智慧”的深入考察,冯契先生的中国佛学研究仅仅是其哲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反映在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智慧说”当中。冯先生的佛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而言:对魏晋南北朝、隋唐、近代的佛学思潮,以问题为中心,选取典型的人物、宗派,介绍、分析其理论精髓;从哲学史和比较哲学的视角,对中国佛学作出整体的评判,对“心性”“顿悟”等学说和“对法”、因明等思维方法予以重点关注;借用佛学术语“转识成智”,加以改造和诠释,赋予新的内涵,立足广义认识论的视域,将佛学理论作为思想资源,融会于“智慧说”之中,且特别注意到禅宗“传法”方式和解脱理论对理想人格培养的积极意义。(1)
一、史与思的结合,选取评判比较
对中国佛学的研究,冯先生从哲学史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两个历史时期的总体理论特征、代表人物的思想以及主要宗派的核心教义进行了考察,在对选取人物和宗派的理论分析讨论之后,给予了一定的评判。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就必须使之中国化,佛学概莫能外。冯先生认为:“佛教在印度、西域已经历了长期发展,佛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思辨水平,佛教文化还包括有丰富的艺术、科学等,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很大兴趣。于是,就经历了一个咀嚼、分解、消化的过程,使得这种外来的文化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这也就是佛教文化(包括佛学)的中国化过程。”[1]581具体来说,佛学的中国化是分两步完成的,即玄学化和儒学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化由道安、慧远、僧肇、竺道生等中土学人完成,儒学化则是随着宗派的建立日趋完成的。[1]627
历史地看,玄学化的佛学即般若学,这与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和佛经的传入不无关系,由于对般若的理解不同,产生了六家七宗的学派之分。(2)但“这些学派在哲学上的主要问题也是‘有无(动静)之辩’和‘形神’之辩。不过,自此时起,由于佛学重视主客体关系的讨论,‘心物’关系问题便越来越突出了。”(3)
隋唐时期佛学最盛,冯先生认为:“自大乘佛教空宗、有宗相继传入中国以来,佛教学者便上承玄学,热衷于讨论‘空有’关系问题,并且总是和‘心物(性相)’之辩互相联系着。‘人是否成为圣人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这个老问题,到了佛教徒那里就成了‘人能否成佛以及如何才能成佛’。”[1]635他还指出:“在这以前,中国哲学对精神现象的分析、研究是比较粗略的,而佛学各宗派分别对‘心’的各个侧面作了细致考察,以论证唯心主义,并且使佛学的唯心主义越来越接近儒家的形态。这是隋唐佛学发展的基本趋势。”[1]627
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中国哲学史的认识和总结,在他看来:“哲学家所要探索的根本问题可以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或按中国传统哲学的提法,概括为天与人、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一次次地取得不同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里表现为不同形式的问题,展开不同的论辩。如在中国哲学史上,表现为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形神之辩、力命之辩、性习之辩、有无(动静)之辩、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等等”[2]43。除了考察中国佛学突出的论辩之外,冯先生还注意到不同时期一些哲学家对佛学的批评,如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等,分析其理论的合理和局限。
晚清以降,佛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复兴的局面,当时的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身上都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子。(4)冯先生就中国近代佛学复兴的原因作了分析:“一,佛学不讲天命而讲佛性,禅宗等流派说自心是佛,提倡自尊无畏。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为了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便主张发扬‘心力’,解放个性。他们以为可以从佛学中吸取思想资料。二,从世界思潮来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叔本华哲学,是接受了印度吠檀多、佛教哲学的影响的;也可以说,他在佛教那里找到了东西文化、东西哲学的交接点。而寻找这种交接点,正是近代思想家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三,佛学在近代复兴,最可注意的是唯识宗复兴,这与唯识宗重视因明有关。近代中国人意识到了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因此注意从佛学中去发掘因明学,并拿他同墨辩、西方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3]9-10在提及佛学对哲学家个体的影响,冯先生注意到哲学家身上的唯意志论和虚无主义倾向,认为“中国近代确实形成了唯意志论的传统”。(5)
1)多线程加载数据。为了避免数据反复加载与卸载给场景性能带来的降低,为每一个数据层设置一个单独的线程负责本层数据的加载、卸载及不同LOD模型的加载。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佛学,冯先生对当时重要佛学家和佛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如道安、慧远、鸠摩罗什、支愍度、支遁、竺法汰等均作了简要介绍,而具体考察僧肇和竺道生的思想。僧肇和竺道生同出鸠摩罗什门下,僧肇以“解空第一”闻名于世,竺道生因“孤明先发”饮誉学界。
从“有无”之辩和“动静之辩”的角度,冯先生对僧肇的“非有非无”“即动求静”等命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僧肇实际上是以“虚无”为本体,(6)“借‘缘起’说来论证‘诸法性空’,是大乘空宗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用‘缘起’来说明‘非有非无’,立‘不真空’义,就是僧肇所谓‘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也。’这是僧肇关于‘有无’关系问题的观点。”[1]586冯先生比较了僧肇和郭象在“动静”关系上的不同主张,批评僧肇从“绝对静止的观点否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认为世界的“实相”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空虚和寂静”。还从理想人格的角度,考察了僧肇“般若无知论”,指出僧肇“把对立的‘边见’排除,以启发人去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的虚静,也就是通过相对主义的论辩,以求达到形而上学的绝对。”[1]592他认为这样的论辩方法如同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的辩证法”的一种形式,比郭象《庄子注》的相对主义有更多的形而上学色彩。
从“形神”关系的角度,佛教主张“神不灭”,般若学讲“法身无相”,涅槃学讲“佛性常住”,各有侧重。竺道生结合两家主张,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命题,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受到当时佛教徒的猛烈攻击。冯先生指出:“这个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是相一致的,而与佛教经典相违背。”[1]594但“竺道生的这个观点至少抽象地承认了人在佛性面前是平等的,这就使佛教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对于“顿悟成佛”的观点,冯先生虽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理论,却指出了其合理因素:“竺道生猜测到人的认识过程中有突变,把握整体道结果突变,这却有合理因素。竺道生的‘顿悟’说对后来禅宗有很大影响”[1]595。他认为竺道生关于“佛性”和“顿悟”的学说,是佛学与玄学结合的产物:“经过道安、慧远、僧肇、竺道生等人的努力,佛教大乘空宗的学说实现了玄学化,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1]595。
“转识成智”是唯识宗的一个重要命题,是指通过转变八识达到四智,以至成就佛果的修行理论。唯识宗认为,经过特定的修行,至证得佛果,可以将有漏的八识转化为无漏,得到四种智慧。其中的“识”是指眼、耳、鼻、舌、身、意五识、第六意识、第七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智”是指四种不同的智慧,即大圆境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转识成智”的意思,就是将人的前五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分别转变为大圆境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11)
对天台宗的考察,冯先生十分注意天台宗的“止观”学说,对“定慧双修”的理论从认识论的角度给予解释。(8)在他看来,“止观”就是“在禅定中进行内省或反思的方法而获得的道理”[1]631,这是代表了天台宗在“心物”之辩和“有无”之辩上的哲学主张。天台宗“止观”的核心方法也就是“一心三观”,最终境界是“三谛圆融”,而这也就是天台宗的中心教义。冯先生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其实讲的是一回事,只是分别从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来说。他进一步说明:“‘一心’在同一时间观照得‘空’‘假’‘中’三种实相,相即不离,无有先后,所以说它们‘圆融’;‘三谛’是精神本体的属性,是人们天生就具有的”[1]632,冯先生认为天台宗与三论宗在“有无”之辩上的论点有相似之处,但三论宗是用“破相”的方法、否定的方法来获得“二谛”的境界,而天台宗则主张用“显性”的方法、肯定的方法来说明“三谛”统一与心体。实际上,佛教讲心体与诸法的关系,即心物关系,都主张“缘起”说,但如何“缘起”,却有着不同。天台宗的缘起既不以法性为依持,也区别于依持阿赖耶识的主张,而是认为“一念三千”,即人的一念心的发动而引起的业感缘起的差异。在这一点上,冯先生认为“智顗是有所见的”,“当人们用内心方法来考察自己的精神活动时,确实可以体验到精神(心)与精神现象(心相)是统一的,并没有一个在先或在外的精神实体作为精神现象的依持者”[1]634。所以“用这些内省能见到的精神现象,来揭示思想与客观实在之间的矛盾,是有意义的。”[1]634
与单独对天台宗作了深入分析不同,冯先生将法相宗和华严宗进行对比考察,总的来看:“法相宗从分析法相来论证‘万法唯识’,是经验论的唯心主义;而华严宗则讲‘法界缘起’,以显示理性本体,是唯理论的唯心主义。华严宗也是有宗,但被称为性宗,不同于相宗。相宗与性宗在共同的佛学唯心主义形式下,分别强调了相(现象、感觉经验)和性(本质、理性思维)的环节”[1]639。对法相宗“一切唯识”的中心教义作了详细介绍和分析之后,冯先生注意到其与西方哲学史上的贝克莱、休谟、马赫等人的学说颇为相似。同时,他还列出一节专门介绍法相宗与因明的关系,对因明未能与中国传统相结合,随着法相宗的衰落而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还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更多地注意朴素辩证逻辑,是因明这一思维方法被冷落的根本原因。
(4)梁启超说:“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99页。)
与禅宗注重“自力”解脱,肯定“自心是佛”“顿悟成佛”相类似,冯先生在理想人格的培养中,十分重视德性主体的自身力量,“我自证为德性之主体,亦即具有德性之智”[2]451。“自证,意味着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和情感的自得,所以是知、意、情统一的自由活动”[2]451,具有自明的理性,主体有意识去反省自己去认识“道”,发挥意志的力量,自主地作选择和始终如一地加以贯彻,最后在情感上有所真实的自得,在社会实践中经历磨难,经过情感的升华凝练成真实的德性。这种德性的境界最贴切的“自证”,对身为哲学家的冯先生而言,便是:“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保持独立的德操”[2]454。
冯先生认为禅宗的“顿悟”说,一方面是神学的说教,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主张凭借神秘的直觉可以见性成佛,这在理论上应当加以注意;另一方面,“顿悟”说又有着积极的方面,“那就是反对了烦琐哲学,摆脱了种种名相的束缚;强调了解脱要依靠自力,着重考察了意识主体的能动性。”[1]667具体来说:“第一,它强调了主观能动作用,以为觉悟是自悟、自觉,要依靠自力,不能依赖他力。……第二,悟是顿然的,一刹那间实现的。……第三,……通常所谓‘悟’,就是顿然间把握全体,获得全面性的认识而有豁然贯通之感。”(10)冯先生肯定了在认识的过程中有顿悟所带来飞跃,从而获得一种融会贯通的感觉和意识,但是片面夸大这种意识也是不妥当的。
有研究显示,联合用药治疗抑郁症的疗效优于单一用药[1],本研究收治老年抑郁症患者60例,分别采用氢溴酸西酞普兰联合奥氮平方案和氢溴酸西酞普兰单用方案,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情况,现报告如下。
对中国近代哲学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个案考察,冯先生却采取了与古代哲学不同的方式,更多地考察了近代哲学家在历史观和群己之辩上的理论,这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时代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古今中西”之争成为思想家关切的焦点,从理论上讲,相对于传统哲学,中国哲学也面临着与西方哲学的交涉,佛学在哲学家那里也是作为他们思想的资源加以利用。[3]4-10
二、借用“转识成智”,赋予新的内涵
提及隋唐时期的佛学宗派,冯先生认为三论宗在哲学上着重讲“有无”之辩,把僧肇“不真空”说引向烦琐哲学,基本上还是玄学化的大乘空宗学说,没有多少新的见解,因此没有过多的论述。冯先生着重考察的则是天台宗的“三谛圆融”、法相宗的“一切唯识”、华严宗的“法界缘起”和禅宗的“顿悟”说等佛学宗派的重要主张。(7)
排水管道的安装要点主要在于伸缩节的制作。在伸缩节制作之前,应全面考虑管道结构对伸缩节的影响,安装过程中除特殊要求以外,统一按照4m的间隔距离进行安装,可以保障排水管道的安全及高效运行。另一方面,排水系统所需的管道都需要先进行试验和检验,检验合格以后才能用于排水管道安装。此外,由于排水管道安装位置的特殊性,土方施工是施工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在开挖和支护沟槽时,应对施工区域的地基、地下缆线以及其他管道位置进行检查,以保证排水管道安装的顺利完成。
(2)所谓六家七宗,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界对大乘般若空义进行解释的六个宗派,即心无宗、即色宗、本无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其中本无宗分为本无、本无异两个派别。(具体可参见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131页。)
从知识到智慧的过程有“飞跃”,这个飞跃的具体途径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理性的直觉”,通俗而言即是“领悟”,这种“领悟”是一种直觉,但是在“理性”照耀下,比如在科学、艺术乃至日常德行的领域,因为理性的作用而有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而“在哲学领域,讲理性直觉就要讲如何具体地、生动地把握绝对的、无条件的、无限的东西。绝对的、无条件的、无限的东西是哲学理论思维所探究的东西,在探究中,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顿然之间抓住了,就是‘悟’,就是哲学上的理性直觉”[2]413。二是“辩证的综合”,这个过程可谓是理性的进一步深化,所运用的工具是“概念”与“范畴”,“概念”和“范畴”一方面表达理念,构建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分析运动变化的形态和规律,通过具体与抽象的辩证结合,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三是“德性的自证”,更多强调主体性,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从真诚出发,拒斥异化和虚伪,加以解蔽、去私的修养,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和坚定,这也就是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的过程”[2]445,在“显性弘道和凝道成德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我以德性之智在有限中把握无限、相对中把握绝对”[2]454。德性主体实现理想自明、意志自主和情感自得的统一,获得一种“足乎无待于外”的真诚的充实感。
以“智慧”为主旨,冯契先生指出智慧主要讨论两个方面问题,即:“元学如何可能”与“理想人格如何培养”。(13)第一个问题侧重从认识论出发,追寻对世界和自己的真理性认识,“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它与人的自由发展是内在地联系着的。”[2]65第二个问题,侧重于从实践论出发,探寻自我的成就,“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本体论(关于性与天道的学说)和智慧学说是统一的,哲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认识天道),而且要认识自己(自反以求尽心知性),并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转识成智’和培养自由人格。”[2]66这里冯契先生明确指出了“智慧学说”的根本任务和终极指向。
从表3可见,2010-2016年核心区旅游经济联系密度值整体波动下降,从2010年的0.50下降为2016年的0.44,随着核心区成员增加,尤其是平顶山市、鹤壁市和许昌市作为后发旅游城市进入核心区,它们却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核心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密度,这也说明后发旅游城市的发展动力有待加强。而边缘区旅游经济联系密度值逐年上升,从2010年的0.00上升为2016年的0.09,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旅游发展起步较晚等原因,边缘区城市旅游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边缘区旅游经济联系较弱,远低于核心区旅游经济联系密度。
冯先生认为“认识天道和培养德性,就是哲学的智慧的目标。”[2]415智慧与科学有所不同,科学求真,在于发现事实和条理,智慧求通,力求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对于如何实现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冯先生作了详细的说明:“首先,智慧是关于天道、人道的根本原理的认识,是关于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2]419这样的认识是从具体的、分别的、部分的、阶段性的到整体的、全面的、过程的,其中必然“有飞跃、有豁然贯通的感觉”,如同佛家所言的“顿悟”。“其次,智慧是自得的,是德性的自由的表现,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和个性的自由表现。”[2]419这样一种自得是属于个体的,展现的是个体的内在德性,总是有其“非受之于人,而忽自有之”的东西。“第三,从人性与天道通过感性活动交互作用说,转识成智是一种理性的直觉。”[2]420所以,他认为从知识到智慧是在“理论思维流域中的豁然贯通而体验到无限、绝对的东西”,而且“这种体验是具体的、直觉到的”,但是这种飞跃,不是物极必反的结果,而“通常是保持着与知识经验的联系,在保持动态平衡中实现的转化”[2]420。可见,“转识成智”贯穿冯先生的智慧说之中:从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出发,经过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对“性与天道”的智慧内容获得全面的、整体的认识,并且“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将真理性的认识落实于主体理想人格的培养之中,实现德性的自证。在这里,“转识成智”既是对“智慧”的认识方式,也是德性实践的前提,起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枢纽作用。与唯识宗单纯在意识领域讲“转识成智”相比,唯识宗将人的内心活动分析得近乎极致,但缺少了广义的社会实践的维度,在对天道的认识和理想人格的培养方面略显单薄。
三、会通古今中西,培养理想人格
历史的整体判断和具体个案的考察之外,冯先生还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佛学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中、印、西方三大哲学传统,各有特色。中国人首先是与印度传统相接触,两种哲学传统经过冲撞、比较之后,佛学的中国化是一个“会通、创新的范例”。
不同文化传统相遇,首先表现为冲突。冯先生认为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是在心性论与天道观或智慧学说上的冲突”,其表现就在于“印度佛学以至虚无生为第一原理,用缘起说来解释一切现象为虚假,”这是与儒道两家对生命持以肯定的态度所不同的,另外在终极目标或者最高境界上,“佛家所谓三法印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来说人生皆苦,而以涅槃寂静为解脱了苦的最高境界”[2]24,这样的自由境界是与孟子、庄子等显然有别。冲突之后是了解,冯先生看到佛学在精神现象的考察上可以为中国哲学所采用,“隋唐佛学各派分别对内省、经验、思维、自我意识和顿悟等环节作了深入考察”,在理解和阐释佛学的过程中,学者们开始借鉴和创造同步,印度佛学也日益为中国文化所改造,这样的结果是新的学说不断建立,从而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
对于中国化的佛学,冯先生有着比较精到的总结,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心性论、天道观和智慧学说三个方面。冯先生指出,在心性论上:“把印度佛学讲涅槃寂静的‘性寂’说改造成‘性觉’说,这就接上了中国的传统,特别是孟子的学说。”[2]24-25在天道观上,魏晋时期中国哲学关于体用不二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佛学,改变了印度佛学原有的世界观,而智慧学说,最重要的就是“顿悟”学说的产生。从哲学史发展角度看,中国佛学不仅是印度佛学的新的创造,使印度佛学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为中国哲学注入了新的理论资源,并对后来理学的诞生产生影响。“总之,中国哲学和印度佛学相接触后,结果比较、会通,达到了新的哲学境界和新的思辨水平,最根本地表现在如何转识成智,获得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即智慧学说方面。”[2]26
混凝土浇筑时,应严格测定坍落度,控制其在技术要求范围内;严格执行经审批的专项方案规定的浇筑程序,避免出现施工冷缝。混凝土浇筑时,必须保证各部位振捣充分,避免沉缩裂缝的产生。此外混凝土的养护是本工法确保质量的关键,必须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对混凝土进行实时的养护方法。
由此可见,冯先生的中国佛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心得,或者说从佛学中汲取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便是对“转识成智”的借用和创新,并融会到他对于智慧学说的研究之中,而这一切最终的落脚点便是理想人格的培养。
(3)在“智慧说”三篇中,冯先生也有同样的说法:“在中国的传统哲学里,认识论上的论争,起初与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密切结合。……从佛教传入之后,心物之辩就进一步突出了,许多哲学家着重考察心和物(万法)的关系,到了宋明,心物之辩和知行之辩又密切结合,所以我把它概括为心物、知行之辩。”(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67页。)
所以,冯先生特别提到了禅宗的“传法”方式,并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他认为:“禅宗认真对待这个‘传法’问题,也就是认真做了教育工作,因此也提供了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1]676教育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这与培养人才的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禅宗的著作中,传述下来的诸多的“公案”,多是老师考验学生的事例。对此,冯先生选取典型的案例加以介绍,分析其中的禅机,还对临济宗的“四宾主”“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等禅师接引学人的方式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说“宗密把洪州禅的主张概括为‘触类是道而任心’;认识‘触类是道’,领悟到一切所作所为皆佛性全体的作用,便具有高度自觉;而‘任心’就是任运自在,随处作主,一切皆出于自愿和自然。禅宗不讲宿命论,一个‘触类是道而任心’的领域,一种‘随缘消旧业,任运著衣裳’的生活态度,使人感到(实际是一种幻觉)悠游自得,似乎超脱了命运的束缚。”[1]680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士大夫在政治上不得志时总是‘逃禅’以求安慰的缘故,也是后世许多人以禅说诗、以禅论画的道理。
此外,冯先生注意到佛学的“顿悟”学说在成就理想人格中的积极意义。佛教认为,人可以通过修行的实践,最后达到解脱的涅槃境界,成就理想的人格——佛。佛学与玄学结合产生的顿悟说,对圣和神、顿和渐的关系作了较为妥当的处理,“竺道生把佛、玄两家之说折衷了,认为圣人是可以学的,但是一定要通过顿悟才能把握真理的全体。把握了真理的全体就成为圣人。这个顿悟说后来为禅宗所发挥,为理学所继承,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4]296。而在冯先生“转识成智”的理论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理性的直觉”,在他看来即是顿悟。他说:“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都强调转识成智,以为人的解脱要依靠智慧。隋唐佛教各宗派对精神现象作了很认真的研究。例如天台宗的‘止观’说,提出‘由定发慧’‘以慧照定’,以内省的方法来把握禅定的体验,以理性的光辉来照亮非理性的领域,使之如实地呈现出来,这种方法也就是理性的直觉。禅宗讲精神的本质就是‘灵明觉知’,自我‘灵明觉知’就是佛性,它有整体性,需靠自己的力量,由迷而悟,顿然间把精神所固有的理性唤醒,使之明白起来,这就是‘顿悟’,亦即理性的直觉。”[4]154
至于最为盛行的禅宗,冯先生自然费了不少笔墨,他主要考察了慧能创立的南宗及其“自心是佛”“顿悟成佛”学说。“从中国佛学的演变(以及更一般地从中国哲学的发展)看,禅宗南宗的盛行标志着佛学儒学化的完成。”[1]666尤其在“人是否能够成佛”这一理想人格培养上,与其他宗派相比,禅宗摒弃了累世修行、布施财物、研习经论等等手段,认为要“顿悟”,人人可以成佛。这种简易便捷的成佛途径和比较“平民化”的教益,得到广泛而迅速的流行。“禅宗的‘顿悟’说,把俗世和天国,凡夫与佛统一起来了。”[1]666为了说明禅宗的特征,冯先生对佛学几个宗派进行了比较。(9)为此,冯先生特别考察了禅宗的表达方式——对法,“在唐代,法相、天台、华严各宗的教义都已经烦琐之极,禅宗反对了烦琐的教条,对传统的教义作了革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它用相对主义反对独断论和烦琐哲学,不可能是对佛教学说的真正的批判。它破坏了对旧的权威的信仰,正是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恢复佛教的权威。”
总而言之,对于冯契先生而言,中国佛学作为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选取理论精髓,客观分析评价,借用并改造其传统术语,合理地拓展与创造的解释,本身就是中国佛学在近代中国化的延续和体现。在广义认识论的视域下和对“智慧”的探索和追寻中,自然包含了冯先生对佛学个性的理解和独特的用意。冯契先生会通古今中西,吸取不同哲学传统的理论,在构建自身的体系当中,都能予以准确的评价和合理的定位,这在近现代哲学家中都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如果我们对比同时代的哲学家,如牟宗三、方东美等,都以中国佛学的具体宗派为对象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其视域更多纯粹探求和挖掘宗派佛学的哲学理论,而冯契先生更多地带着眼于中西会通之下的世界哲学,将佛学的思想作为其理论体系构建的资源。
遗传算法中最常用的选择策略是基于适应度的选择策略,这类选择策略首先需要计算个体的适应度,个体的适应度及其分布决定了每个个体的被选概率,然后根据选择方法来选择个体。常用的选择方法有:适应度比例法、排序选择法、最佳个体保存法、截断选择法等。
冯先生虽不完全赞成唯识宗的说法,但认为认识过程中有知识到智慧的转化,所以“借用‘转识成智’这一术语来表示由知识到智慧的转化”(12)。在冯先生那里,“识”是指知识,“智”指智慧,对此他都有详细的说明:“知识所注重的是彼此有分别的领域,是通过区分这个那个、这种那种等等,进而分别地用命题加以陈述的名言之域”。“‘智慧’一语指一种哲理,即有关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2]413他心目中的“智慧”具有更为宽泛的涵义,并非单纯严格意义上所谓的“圣智”“般若”“爱智”等意思,而与此相对照的“知识”,既包括经验世界的事实和条理,也包括名言、概念等理论思维。
在理想人格的培养中,冯先生很重视自觉和自愿原则相结合,在他看来,先秦儒家有着成功的经验,并且形成了传统,但中经汉魏逐渐衰落,直到禅宗才接续起来,“只有到了唐代,禅宗的大师复活了孟子的传统,才又重视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相结合”[1]680。他说:“禅宗讲‘即心即佛’,讲顿悟,认为‘灵明鉴觉’,是每个人固有的,就是佛性。这样激发你的自信心,认识到自性具足一切,相信自己和佛祖没有什么根本差别,成为自由人。在先秦儒家那里,比较重视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禅宗的理论及其教学实践从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中国哲学的传统。”[4]298而且,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佛学才做到了这一点:“佛学本来讲无欲、无我,以为只有把意志作用否定掉才能涅槃。但是中国佛学却讲明心见性,强调自信力,结果达到自觉原则和自愿原则的统一这样一个结论,回到了先秦儒家的观点,柳宗元讲‘明以鉴之,志以取之’,明确地强调两种原则的统一。”[4]298
这天傍晚,大家正在吃晚饭时,桃花突然站起身来,尖叫了一声“方竹”,就摔倒在地上。高木像从梦里窜醒一般,傻呆呆地看着她倒地。凉棚下闹哄哄的,压根儿不知道灵堂里发生的事,直到高木喊,才有人问。桃花随即被送回谷村家中,“老木大”说她是悲伤过度、心力交瘁所致,连忙给她挂盐水,忙到很晚才走;夜里桃花睁开眼睛,看到床前的堂嫂桂花和堂妹巧云,巧云抱着黄方永,她才清醒过来自己是躺在自己家里。桃花默默地流下眼泪。黄方永见母亲哭了,也哇哇直哭,挣扎着要妈妈抱;桃花让巧云把儿子放到床上,黄方永爬到母亲怀里。桃花抱着儿子呜呜地哭。堂嫂桂花和堂妹巧云劝她想开一些,自己的身体要紧。
华严宗用缘起说来解释法界,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普遍联系的。冯先生注意到,华严宗通过“事”与“理”的关系来展开“有无”之辩,“理”是精神本体,具有“无分限”的特征,“事”是指种种的现象,具有“有分限”的特点,理事关系就是空有的关系。冯先生认为:“华严宗对现象的普遍联系以及一和多、整体和部分、同和异、生成和毁坏这些范畴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显然突破了形式逻辑的‘整体是部分的总和’的观点,揭示了辩证法的因素。”[1]657他认为通过形象化的方法说明华严宗的“事事无碍”,“能给人以诗的境界,但不是科学的真理”,华严宗“法界缘起”学说“使人想起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两者都属于唯理论一派,把理性思维所把握的联系抽象化、绝对化。
(5)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24页。冯先生还说道:“西方文化更多地强调了意志自由,近代以来更有个强大的唯意志论传统(佛教在中国并没有促使唯意志论的发展)。佛教传到西方,叔本华深受其影响,大讲唯意志论,这可能是不同的文化土壤使然。”(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378页。)
(6)从本体论来讲,他是把绝对的虚静看作是万物的本体;从认识论来讲,他是把绝对的虚静看作是智慧所要掌握的内容。僧肇以为,真正的圣明就在于体会“非有非无”。可见,他实际上是把虚静作为第一原理。
(7)“冯先生在这一时期八大佛教宗派里仅取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四者进行讨论,略去净土、律宗和密教三者宗教意义浓厚而哲学成分较少的教派,三论宗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这样的取舍固然是出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全书总体思路的需要,同时,也基本符合隋唐佛教宗派主要思想理论的精髓所在。”(夏金华:《冯契中国佛学研究管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2期,36-37。)
建筑工程结算阶段应做好工程的管理工作,编制完善的计划方案,保证在结算期间提升建筑工程造价管控水平,优化整体管理模式。一方面,在结算阶段,应树立正确的造价管理观念,充分意识到造价管控重要性,并编制完善的计划方案,以免出现资金浪费现象。另一方面,在工程管理中,需创建现代化的管控机制,完善整体工作系统。同时,需针对造价管理人员进行阶段性专业知识与先进技能的培训,使其掌握造价管理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并积极参与到造价管控活动中,以免影响工程的经济效益。
(8)“他们认为,正确的途径应是由定发慧,以慧照定。这从认识论来说,无非是在修习禅定的过程中进行内省(观照)的意思。以为凭内省或反思就能获得智慧,这正是天台宗在理论上的特点。”(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631页。)
(9)从哲学来说,佛教宗派在“心物”关系问题上,都主张“心外无物”,一切法都是“心法”。所不同的,它们各自夸大“心”的某个侧面,以论证唯心主义。天台宗讲“止观”“三谛圆融”“一念三千”,用的是内省法。法相宗讲“万法唯识”,用感觉经验来解释一切。华严宗讲“法界缘起”,以为理性思维是唯一实在。禅宗南宗则用自我意识吞没一切,他标榜“自心是佛”,以为自己的灵明鉴觉就是佛性,并强调意识的整体性,把认识过程中确实存在的突变加以绝对化,以为对“自心是佛”“本性是佛”的觉悟是顿然间实现的,所以说“顿悟成佛”。(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669页。)
所述的继电保护装置整机智能测试方案,采用气源作为动力源及气阀作为控制机构,通过对保护装置多维度数据挖掘,充分利用生产过程中的历史大数据智能构建整机闭环测试环境,将繁琐的保护装置人工手动测试变成机器智能测试,并将原有离散的单功能测试行为转变为连续测试过程。这些尝试,对降低企业的测试成本,提高生产整机测试效率,推动工业4.0在智能电网保护装置生产制造领域的深入应用,实现继电保护装置的柔性智能测试做出了有益探索。
①河流冲积主要包括下更新统(下部)浔江组(Q1x)、下更新统(上部)铜鼓岭组(Q1t)、中更新统白沙组(Q2b)、更新统望高组(Q3w)、全新统桂平组(Q4g)。
(10)“从认识过程来讲,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表现在通过人的认识的飞跃而把握全面性的知识和具有融会贯通的意识。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禅宗把这一点夸大了,使之变成了直线,从这里导致唯心主义、神秘的直觉主义。”(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671-672页。)
(1) 当今,在高分子材料的生产和消费中,塑料居首位,其次橡胶。随着消费量的逐年递增,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橡/塑废弃物回收与利用具有积极作用和深远意义:其一,可解决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其二,塑料、橡胶材料的合成主要来自于石油资源,能减轻对石油资源消耗和依赖的压力;最终,使其成为可再生利用的资源。
(11)详细可参见: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月,251-252页;夏金华:《佛学思潮》,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5月,245-249页。对此,冯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解:唯识宗讲“转识成智”,是指由以分别为主、有“我执”“法执”的意识活动,转变为如是理解的无分别、无执着的智慧,这种由染而净、由迷而悟的转变,是以藏识即阿赖耶识而实现的。(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411-412页。)
师:是的,这个图画得还是很准确的.但是光凭画图不能代表证明哟,我们来想想,假如是△AMD∽△DMN那会有什么结论呢?
(12)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411页。关于冯先生的“转识成智”和唯识宗的“转识成智”的关系,有学者作了比较分析,可参见徐东来:《冯契先生佛学研究述评》(《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98-100页)。
(13)智慧的探索起源于人的认识。依冯契之见,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问题,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四个:“感觉能否给与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在这四个问题中,从具体经验领域的知识到关于性与天道的智慧,元学与知识论统一于广义的论识论,具体展开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运动中。对于前两个问题的追问,就是获得智慧的第一阶段:由无知到知;而后两个问题就深化着知,并通过人的认识的努力,达到性与天道的获得。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08(2019)05-0023-07
[收稿日期]2019-04-02
[作者简介]刘 翔(1984-),男,湖北黄山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科学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编辑 张 瑛)
标签:佛学论文; 哲学论文; 中国论文; 佛教论文; 禅宗论文; 宗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晋中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科学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