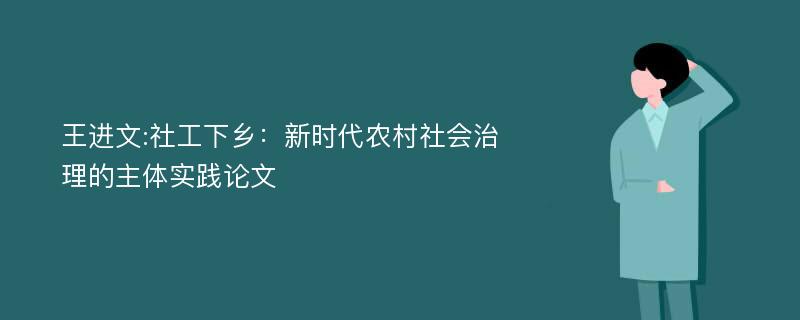
摘 要:“社工下乡”是一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实践,有着较为坚实的理论要求与现实基础。政府社会工作政策向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有序,社会工作方法有机移植,均体现了“社工下乡”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而重归关注底层弱势群体之路,维持社区共同体秩序稳定,秉持保护社会正义的原初本性,更是构成了新时代“社工下乡”的多元实践目标。由于农村生态域情的繁复性和社会工作发展的初级性,“社工下乡”实践的顺利展开必须找准贴合中国乡村文化特质的介入视角,转向合作型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之路,依托基于法治化和契约化的项目制模式等现实进路,促进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和社会工作者主体性建构。
关键词:社工下乡;乡村治理;新时代;主体性建构;社会正义
自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治愿景,到社会工作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进而被纳入到参与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筑和良性有序社会生态创设的政治议程之中,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本土化和实务方法专业化程度均有所提高。进一步说,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领域不断拓展,服务效能稳步提高,实务经验趋向丰富。在政治社会生态和社会工作发展同时处于“稳中向好”之际,关于推动社会工作者“下乡”并使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持性主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由此“社工下乡”这一议题在公共空间中为民众所热议,在学术圈子中为学者所讨论。而这种源于“社会”的呼声更与“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要进入农村社区并为广大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相契合。
长期以来,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者和服务实践者的“首发阵地”是城市社会,其服务与治理的目标对象也大多是接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社区居民,其所能调用与整合的公共政策资源和社会支持网络也是丰富而立体的。与之相比,农村社会工作在理论知识建构和实务经验积累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尚未同步展开和全面推进。那么,新时代政治话语下的“社工下乡”的可行性条件是否业已具备了呢?如果说,“社工下乡”的呼声高涨意味着社会工作“戳中”了理论或现实中的“痛点”,那么,哪些现实要求和理论期待正在日益催促着社会工作者下乡呢?在下乡过程中,以“实践性”和“建设性”为内在品格的社会工作者将会带有何种目标呢?另外,作为一门新兴职业和外借学科(borrowed discipline)的社会工作,我们又该对推进社会工作者顺利下乡并使其大有作为提供何种可资参考的思路呢?恰切地讲,对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深入追问和深层探视,既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发展所应关照的应然之事,也是发挥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组织和队伍在共建服务—治理型社会的“弄潮儿式”角色的题中之义,故而基于该议题的研究是一项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并存的系统性工程。
一、“制度—主体—方法”框架下“社工下乡”的社会基础
自1987年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论证会召开以来,中国社会工作迄今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在时间上,社会工作的理论概念和实务操作总体上历经了“引进—消化—本土化—在地化”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社会工作研究者将其关注视野和研究旨趣从仅限于“城市社会”拓展到“农村地区”;而社会工作实践者也更常态化、更积极地介入并参与到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和目标群体需求满足等之中。社会工作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治国施政观念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向,为社会工作建构服务—治理复合框架,进而使其在服务提供中强化治理效果、在介入治理中丰富服务内容的统一提供了智识支持。目前,社会工作对农村各项议题的积极介入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治理方案,表明社会工作者下乡的现实条件业已走向成熟。故此,基于“制度—主体—方法”这一分析框架,笔者力图对新时代社会工作者下乡的现实基础做一个新的知识梳理。
从宏观制度安排来看,由于中国社会的繁复性和本土域情的多元性,“制度”时常成为党政部门“预防潜在风险—分析问题成因—拟构应对策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推动社会工作学科和职业制度的引介并使之本土化,就是中国政府面对充满风险、复杂流变的内外社会情势所提出的一种制度化设计。从2006年开始,中央政府提出了“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治目标;[1]2009年民政部倡导性地做出了“为民办社会工作提供包括场地和资金在内的政策支持和经济资助”的政治指示;[2]2012年为促进政社关系均衡化和社会工作主体性发展,两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3]2018年中央政府出台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更是为“培育更具服务性、公共性和实践性品格的社会工作”、并使之“走进并服务农村”吹响了新时代号角。[4]客观而言,上述各项利好政策集中体现了中国政府从形式化到实质化、从制度设计到资金注入来全面力推社会工作发展的政治决心,也透视出政府对社会工作职业的合法身份、服务能力和有益贡献的政治承认。最为关键的是,在“制度甚为关键”(institution matters)[5]的中国话语体系和政治语境中,政府对包括农村社会工作机构、农村社区工作者等社会工作重要构件的高度关照,无疑为社会工作者下乡并展开相应的服务—治理实践供给了制度红利。此外,通过爬梳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历程后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工作学科的创设和社会工作职业的培育,抑或是推动行政性社会工作向专业性社会工作转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每一步都或深或浅地烙上了“政治”底蕴和“制度”印记。尤其是在社会工作介入治理领域中,“国家”的“可视性”(visibility)和“在场性”(presence)深刻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实践特性和发展路向。也正如此,新时代话语下政府对社会工作发展所做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关照,为社会工作者以一种更为自主性、独立性和建设性的存在状态来真实有效化解农村发展困境和服务农村居民,留存了充分的政治经济活力和生存发展空间。
从微观人才队伍建设来看,与既往以物化形式存在的“物流下乡”与文化形式的“法律下乡”等下乡活动不同,“社工下乡”是一个旨在通过调用兼具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人及其所属机构,展开整体性、专业化和立体性的服务—治理实践的总体性过程。而社会工作人才梯队建设体系的完善与否,成为社会工作者能否常态化、大规模地下乡,以及多大程度上充当乡村治理效能优化甚至乡村社会再组织化水平提升的重要抓手的关键标尺。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以安徽省为例,全省开设社会工作专业院校有9所,每年培养社会工作专业本专科毕业生及研究生近千人。从笔者调研数据来看,安徽省建立健全了分级培训制度,广泛开展了各类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培训,目前累计培训达38 462人次。近三年来,接受1次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占13%,接受2次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占10%,接受3次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占19%,接受4—6次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占35%,接受7次以上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占23%。另外,在学历层次上,社会工作人员的学历较高,本科以及本科以上的人员有36人,所占比例为61%,大专也占到了32.2%。①从全国范围来看,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与多层级部门的充分重视助推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和培育速度稳步攀升。其中,截至2018年底社工专业人才总数突破百万,持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证书的人数总量更是接近40万。[6]由是观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已初具规模,学科体系已相对完整,专业培训制度也初步建立。这标示着社工下乡有着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队伍接续/继替的社会基础,因而较好地弥补了早期社会工作面临的“人才短缺、学历断层、队伍不全”等先天不足。
就专业服务方法应用而言,受到早期西方社会工作偏向城市地区并服务于市民的潜在影响,中国社会工作虽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也不自觉地因循了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初期的实践逻辑,但在配合政府治理“城市病”和服务城市需求群体的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本土城市社会工作服务范式的多样化,实务应用技巧也日臻成熟。而城市社会工作服务方法多元化和实务经验累积化,为社会工作者借此满足农村目标群体需求和打开乡村治理局面创造了必要的前期基础。具体来说,作为一门以助人自助为核心宗旨的特殊专业和新兴职业,社会工作始终与“社会转型”[7]这一议题密切相关,社会工作者也主要面向并服务于处在剧烈转型阶段中的目标群体。虽然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转型过程尚未彻底结束,但相较于城市地区来说,农村社区遭遇现代性元素的渗透时间较晚,属于典型的“后发转型”这一类别。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和乡土文化仍旧影响人之际,城市社会工作方法虽会因经济发展程度、居民文化水平、面临问题类型等外在性差异而表现出具体实务应用上的一定区别,但也会因城乡群体在文化特质、行动方式和思维认知等“构成性特征”上的相对同一性和贯通性,使其具有相当高的适用性和一致性。故此,面对变动不居和繁杂多样的农村社会这一场域,围绕社工下乡是否可行以及有无作为这一问题,王思斌认为,当政府管理思维向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时,社会工作的角色与地位也会发生明显变化,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会加强。[8]因此,其专业服务方法在场域转移的同时,也能选择性地被有机引介到相应时空之中,并以贴合域情的方式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的是,制度生态良好、人才队伍完善和专业方法移植,为社会工作者顺利下乡并展开科学服务做出了初步的可行性检视,也成了社工能否成为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基本前提。当前,无论学术界还是党政界,关于“社工应该下乡”这一“应然性”论点取得了相对一致的学理共识和话语认可;但对“社工能否下得去”这一“实然性”判断却意见不一,甚至对“社工能否成为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主体”这一观点仍存有疑虑。应该说,这种矛盾心态是因“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而产生的学理焦虑之直观反映,也是对“条件约束下社工实践/行动如何可能”的心理表达。然而同样不容否认也无法忽视如下事实。一方面,实践是检验既有理论、创新治理模式的来源。这意味着社工下乡不仅是一个理论和方法应用的问题,更是一个致力于服务—治理的行动实践。社工下乡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社工也只有在下乡实践中才能锻炼“文化识能”的本领和累积有效的“地方性经验”,才能学会如何在多元共同治理格局中发挥主体价值,更能有效避免陷入“忽视对实践性知识和本土实情的考察,而仅限于‘应该’或‘可能’的思考层面”的困境。[9]另一方面,社工下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遭致“资源不足、条件约束”等挑战,但是“这种挑战大部分都是阶段性的”,[10]因而也是暂时性的,更何况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基础条件在我国农村地区业已具备。[11]另外,立足于本土实践知识而创生的“社工+义工”的双主体合作模式、“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三联动治理格局以及“万载模式、深圳模式、绿寨模式、四川模式”四大地方服务模式,均自觉地将社工视为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动主体,也体认了条件/资源约束下“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农村仍大有作为”[12]这一事实。如此也间接佐证了“社工下乡”这一命题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但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只能是以渐进的、有序的方式方可展开以至完成。
随着基层单位制组织解体和税费改革的全面启动,农村社会进入一种“有权”(村民自治)、 “无财”(全能型保障撤除)、“无人”(城乡推拉力作用)的名实不符的尴尬境遇。在此情势下,包括项目治村、项目扶贫等项目制运作模式及其理念被整体性地提出,并被应用到农村社会诸多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之中。项目制是指“中央对地方或地方对基层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运作和管理方式”。[36]纵然学界对项目制模式的实际成效和功能发挥存在着毁誉参半的争论⑥,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项目制能通过财政上的转移支付,将民生性的公共事业尽可能大的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之中”,[37]藉此有力张扬了人本中心观和社会公正理念。另外还需承认的是,由于农村社会生态的恶化、基层域情的复杂和群体需求的多样,在当前农村社会没有其他可供选择和可资借鉴模式的情况下,依托项目制模式助推“社工下乡”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价值性的。事实上,当前农村基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即是项目制运作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服务时间短期化和需求群体多数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以“短、少、快”为特征的社工购买服务模式既很难达致“根治”问题之成效,也不能满足服务使用者之多重需求。相反,以“长期、高效、稳定”见长的项目制模式能较为有效地化解这一难题。但需警惕的是,为了不让假借助推“社工下乡”之名而行“目标替代”之实的情况发生,必须把社会工作“项目制模式”运作过程“锁定”在法治化和市场化的制度框架之中,并藉由对“项目化、契约化和社会化机制”[38]的创建确保社会工作者下乡服务过程的常态化和服务结果的有效性。只有依托基于法治化和市场化的项目制模式,“社工下乡”才有可持续化和健康化的生态空间;只有适度地推行“去行政化”的项目制模式,社会工作者才能真正实现服务周期的常态化、服务效能的提升化和服务开展的自主化。
二、“社工下乡”的理论期待与现实要求
随着社会制度变革和结构演化步伐持续加快,中国社会工作在吸纳西方社会有益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受到创生本土化和内生化社会工作知识的理论压力,特别是如何实现将城市社会工作理论成果与经验有机移植到乡村地区,并使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抓手。这是城乡统筹发展语境下新时代社会工作势必回答的时代课题。而“社工下乡”观点的提出在浅层回应这一议题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其重要性、可行性与大有可为的肯定。
(一) “社工下乡”是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省思
回顾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的知识脉络,围绕“城市社会”展开的学理探究和经验总结始终是社会工作的主要研究趋向和发展重心。对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集度使农村居民的多重需要或多或少地被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边缘化,[13]有关农村研究的学术议题也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不仅如此,农村社会工作处于隐性滞后发展阶段,社会工作职业也理所当然地被“化约”为只替市民服务的城市职业。在引介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及其实践成果的同时,中国社会也不自觉地遵顺了其有意分割城/乡社会工作,并产生了偏向前者的认知倾向和路径依赖。纵然中国社会工作业已开始进行自反性省思和在地化转换,但由于缺少大众承认、缺乏介入视角、实践方法单一等问题始终存在,农村社会工作无法实现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和减缩其与城市社会工作发展差距的统一。更为关键的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呈现出的研究文献阙如[14]、专业化进程严重滞后、学科门类独立化程度低、人才队伍梯队尚未成型等发展面貌,更是与“三农中国”的基本域情和“农村为本”的发展战略要求不符。近年来,西方社会掀起了重新体认农村社会工作之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反思浪潮,并再度肯定了农村社会工作本身便是为解决人们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不适问题而创设的这一事实。客观地讲,这场反思运动对“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农村人口依旧转移”的中国社会来说具有镜鉴意义,对试图获得政治承认、主体性地位的农村社会工作者而言尤为及时。在这个意义上,社工下乡既是对中国社会工作偏向城市而忽略农村的深层检视与实质回应,也是从实践上找寻化解农村社会发展困境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以及理论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并以“中国为方法”和“内部视角”为方法论基础的新时代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的必由之路。
(二) “社工下乡”是传统救济思想与帮扶运动的当代承继
作为中国政治制度框架中的重要构件,传统救济思想及其制度建设始终被视为统治者“施行仁政”和“达致善治”的重要体现,而这种理念所包纳的有益成分与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与助人自助的专业使命不谋而合,如此能为社工下乡提供适切的文化土壤和制度生态。其中,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始终宣扬“勤爱人、民为本、守相助、互扶持”[15]的互助思想和仁爱情怀;以墨子为先驱的墨家文化也表达了对“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的和谐文化,以及实现“天下兼相爱”[16]目标的高度尊崇;甚至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理念的道家也分别对为政者和富人提出了“爱人利物”和“使财分之”[17]的殷切期待。毫无疑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扶危济困、宽助慈幼”的慈善救济思想延存至今并仍旧影响人,使社会工作者入驻乡土性仍存的农村社会并开展助人服务具备了一定的亲和性(affinity)。近代以来,以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一场利用乡村社会组织使“弱者散者进行一种联合自卫自救,进而应付大家生活的需要和办理公益的事情”[18]的建设运动,其从广义范畴来看已初具助人自助的社会实践性质。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也是一种“公益性事业”和“慈善性工作”。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自建党肇始,中国共产党就特别重视对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予以组织关怀和社会救助,其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探索出的卓有成效的救助理念与帮扶原则,为形成内容完善、覆盖面广、互济度高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搭建了基本框架。由此来看,“社工下乡”既是对传统救济思想的当代实践,又是对既有帮扶运动的自然承续。
两组患者在下肢手术后均给予常规抗生素预防性抗感染、消肿止痛对症支持治疗,其中对照组给予低分子肝素进行治疗,1次/d,5000 u/次,连续服用15天;研究组给予益气通脉汤,具体药方为:黄芪18 g、水蛭8 g、地龙10 g、红花10 g、三七10 g、柴胡10 g、丹参10 g、泽兰10 g等以上各药均为道地药材,200 ml/剂,2次/d,术后6小时后服用一次,早晚分2次于饭后服用,术后连续服用15天。所有的操作、治疗及数据统计均有同一组技术成熟的治疗组医生完成。
(三) “社工下乡”是对当前系列下乡实践活动的必要补充
①本数据来源于笔者参与的“安徽省十三五专业社会工作思路研究”课题,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三、新时代语境中“社工下乡”的多元实践目标
客观而言,以往大部分下乡实践活动均是围绕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具体困境,抑或满足某种实在需求而展开的,其较多地呈现出单一性、目标性甚至实用性的特征。由于学科的指向性和职业的特殊性使然,社会工作者的下乡实践必将带有契合自身发展理念和核心宗旨的多重使命。而这些使命与政府所欲达成地“建设善政乃至善治中国”的政治愿景是一致的,并可从微观层面、中观维度和宏观视角三重面向加以叙述。
(一) 微观层面:重归关注底层弱势群体之路
“社工下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慈善救助实践的自然导向和内在要求。它回应了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政治诉求,也彰显了社会工作者“助人自助”的原初本性;它既是社会工作自身发展的学科或理论需要,也是其主体建构过程中的使命担当或责任使然。更重要的是,“社工下乡”契合了新时代中国政府致力于农村地区脱贫工作,进而带领国民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政治愿景,也为社会工作者创设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本土智慧的发展经验、理论架构和服务模式提供了契机,更是社会工作者及机构不再作为政府的“附庸”,而成为具有职业品格、助人精神、建设意识等特征的支持性主体的恰切入口。正因如此,如何以更为建设性的态度、务实性的作风和立体性的支持来推动社会工作者顺利下乡并助其大有可为,应该成为专家学者和党政干部着重思考的新内容和新方向。
档号是档案的主要标识,5.4规定编制档案时应遵循“唯一性、合理性、稳定性、扩充性、简单性”。五原则是区分档案类别、体现档案排列顺序的要求。唯一性原则,即档号指代单一,一份文件赋予一个档号。合理性原则,指档号结构应与归档文件的整理体系相适应。稳定性原则,档号编制完成后,具有长效性,长期不变,不随意改动。扩充性原则,主要针对档案文件不断增加、扩充这一情况,适当预留一定的递增空间,满足归档文件不断扩充的需要。简单性原则,所有组成要素均由字母、阿拉伯数字标识,简单明了、节省存贮空间。
(二) 中观维度:维持社区共同体秩序稳定
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从“超稳定性”的熟人社会转到“高流动性”的生人社会,叙述内容和分析概念的不同透视出当前乡村基层社会发生的巨大流变。这种变化既消解了原有乡土社会记忆和地方性文化所凝结而成的社区内引力和共识度,也使乡村共同体的稳步解体和社区秩序的益发失衡趋势日渐显化。市场经济观念和理性主义思维促使乡村基层社区生态和交往规则从感性化、非正式化、互助共享往理性化、正式化、精于算计的总体转向。[25]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农村社会工作逐渐超越了社区发展模式而延伸到了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26]社会工作发展理念和服务范式更是经历了从“社区导向”到“社区为本”的知识话语转向。如此,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不再把社区视为一个内含机械意蕴的结构论上的客观单位,而是将其看作兼有使动性、总体性、关系驱动等特征的主体单位。[27]这标示着社区成了社会工作者回应居民诉求和实施专业服务的“立足之地”,而并非只是其创生理论概念抑或完成某项任务的暂时性的实践场所。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只有把维持社区共同体秩序稳定作为自身下乡的基本使命之一,社工才能凭靠社区这一中坚平台顺利进入并融入基层,进而依托社区资源和凝聚社区力量有效地改善社区生态环境和服务多元主体需求。否则社工下乡不仅是毫无活力的“无源之水”,并容易造成“单打独斗”的“单向度”和“弱治理”格局。而且作为局外人和陌生人的社工更可能深陷到“因专业知识阻碍社会工作干预及其效能发挥的‘文化识盲’”③现象的泥淖中。
3.模型的产出。模型的产出主要是一系列计算结果,这些结果基于模型的投入和假设条件,经过相关财务公式计算而来。主要的结果包括:资本支出;削减股本;提取债务;服务费(对于特许经营权项目为车辆通行费);其他运营收入(对于特许经营权项目表现为次级收入,如特许经营权公路相邻的土地开发收入);运营支出;利息;税;偿债;(收入)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现金来源和使用);贷款方的债务偿还能力比率(流动比率,利息偿付比率,债务与股本之间的比率等);投资者的回报;净现值(以便公共主管部门能够对不同投标进行比价)等。
(三) 宏观视角:秉持保护社会的原初本性
纵观西方社会发展历史,市场自由主义经济之手毫无克制地销蚀私人领域和挤压公共空间,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而促动了诸如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平行动等反向保护运动的兴起,而社会工作既可视为社会保护运动的直接产物,也应将之看作是保护社会正义的支持型主体。甚至可以说,“保护社会”和秉持社会正义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原初本性。而这一理念与Barker认为社会工作者需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以解放被压迫者为主旨”[28]的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是契合的。然而,鉴于早期政治制度生态尚未改善和社会工作主体性仍未塑造,社会工作者鲜能尽如人愿地承担其“保护社会”这一历史使命,反而为获致合法地位、经济资源和政治扶持而进行自我矮化,甚至某种程度上充当政府管控“社会”的代言人和执行者。改革开放政策推行40年以降,国家权力开始稳步、有序、适度地退出农村社会场域,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从“总体型”社会迈向“悬浮型”社会④的进程。相较于城市地区而言,农村社会受到政府权力干涉和行政计划捆绑的影响度略小,这为社会工作者在下乡过程中弥补政府退场而产生的组织缺位、重拾保护社会意识和伸张社会正义创造了发展空间和历史契机。一言以蔽之,社会工作者的下乡实践必然是一个自觉地将以“保护社会”作为自身的内在信念,以农村底层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以建设性的态度维持社区秩序的过程。唯有如此,社会工作者才能便易地“走出嵌入性发展的误识,进而回归‘社会导向’和‘社区为本’的传统,社区信任关系才会真正重建”,[29]乡村治理也才可借助新型专业主体的助力而获得实质性发展,社会也才能重新被培育。
四、新时代语境中促动“社工下乡”的现实进路
囿于农村社区生态域情的复杂性和社会工作发展阶段的初级性,社工下乡实践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即时性过程,相反其应该是一个渐进性、动态性、持续性过程。此外,对于任何一种生态系统而言,外生性事物在被引入并应用到该系统之时都将面对着如何与现有的制度架构相协配,如何与底层文化生态相调适的“兼容性”和“拟合度”问题,而社会工作者的下乡过程也必将遭遇这一难题。这意味着,只有寻见与农村社会文化特质、生态结构和交往逻辑相因应的“介入方式、服务关系、依托载体”,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理念与实践目标才能有效达致“知行合一”,农村目标对象的“需求”和“供给”也才会真正实现“供需一致”。
(一) 找准贴合中国乡村文化特质的介入视角
日益流变的乡村社会发生了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未有之巨变”,这种变化使作为局外人和具有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社会工作者时常面临“视角缺乏”和“文化识盲”的双重困境。加之对农村社区生态缺乏过强的敏感性、感知度和觉察力,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常处于“方法生硬化、经验刻板化、知识无能化”的服务状态,而这种状态极大抑制了社会工作效能增进和乡村社会治理效果巩固。因此应该讲,找寻与中国农村社会生态相贴合和地方性知识相适配的社会工作理论视角和实践方法,构成了社会工作突破“文化识盲”困局和推进乡村治理的首要工作和基本前提。近年来,关系理论已显示其有巨大的潜力来支持社工经验实践,而这些实践显然已超越个体心理治疗的范畴。[30]此外,关系为本的视角在西方社会工作中经历了从缺场到复苏、从边缘到主流的回归过程,“关系主义”更是成了当前社会工作认识问题和提供方案的新的思维样式和方法论基础。[31]以关系为本(relationship-based)的西方社会工作论著颇丰,其经验积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发展提供了案例支持和理论基石。至为关键的是,基于综融实践取向的关系视角深度切合中国“关系社会”的情境实践(situated practice),故而其既能成作为社会工作者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的有效“介入工具”,也是社会工作者在提升“文化识能”素质过程中理应主动学习和自觉运用的“默会知识”。[32]具体而言,社会工作者在下乡实践中既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务技巧来应对相关问题,也要在符合地方规范和话语系统的前提下学会如何去调用、维持、建构工作关系和半熟人关系甚至熟人关系;以使自身较为“学院式”和“程式化”的服务方法和操作流程能以“接地气”和“情境化”的方式更精准高效地对接到需求群体,进而完成对个体困扰的“靶向诊断”以及对造成个体困扰背后的结构性制度的“精准把脉”等工作;最终通过并举“帮扶个案”和“改变系统”两种服务方法,来为需求对象提供适切性和实质性的专业化服务。若非如此,“社工下乡”这一实践行动很容易返归到社会工作早先面临的那种内部充满张力的发展状态中。即一方面,社工以一种主持人或调停者的身份来实施干预,以此促动“社会”驶向更具“集体性、我们感(we-ness)、各种观念差异并存”特征的阶段;另一方面,社工又会基于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知识权威身份来强调作为已知者(the knower)和被告知者(the known)、服务者的自我(self)和案主的他者(other)之间的距离。[33]
(二) 转向合作型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之路
注释
(三) 依托基于法治化和契约化的项目制模式
本文所说的“社工下乡”这一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主体实践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通过扎根于农村基层社区,并借助自身专业化知识和其他多元主体力量,以此展开以满足目标群体需求和增进乡村治理能力为目标的服务—治理型实践。依据此种界定,可以从实践主体、实践场域、实践目标、实践属性四大方面对其进行更深入地解析。从实践主体上看,社工应处于“主体地位”而非“主导地位”,也即社工在进入并介入乡村(工作)时始终与其他主体保持着平等地位、主体品格,充当的是“问题传达者”和“服务支持者”等角色,而非异化为对“上(政府)”从属—矮化、对“下(案主)”主导—支配的行动逻辑。另外,社工实践的主体地位也体现在社工不将自己视为“全能型社工”,而是看作一个参与主体,主动促成包括掌握组织资源的社区居委会、拥有强关系网络的社区精英、秉承关爱互助传统的社区居民以及社区外主体的关联,以此建构“社工+”服务模式和形成治理合力。从实践场域来看,社区应作为社工下乡的“立足地”而非“项目地”,也即社工应把社区当作开展服务—治理实践的事业地,用心扎根并融入此地,而并非将之视为“不得不停留的临时之地”,因而也就毫无参与实践的自豪感、积极性和自主性。从实践目标来看,实现改善“微观境遇+宏观系统”的二重目标。社工下乡的实践既要关注微观层面的“事件型案主”,更要体察宏观层面的“系统性生态”,进而发挥“社会工作的想象力”来根治“问题”。从实践属性来看,作为一种主体行动,社工下乡的实践过程将是动态而持续的,服务方法是多元而综融的,面临问题也是复杂而综合的;而这种实践特征反过来也要求“实践主体的立体性、实践场域的在地性、实践目标的二重性”,四者相互关联、彼此促动、互为基础。
在初始阶段,西方社会工作就额外强调对包括儿童、妇女、老人等在内的弱势主体的重视,而“纾解那些生活于我们周边并大多抱以绝望态度之人的痛苦,集中注意力去满足那些易受伤害和处于贫困之中的人们的诸多需要,并在此基础上赋之以权和增能培力,进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与合乎人性的秩序”,[20]更是成为了社会工作者的核心使命和本质任务。然而,对个人主义式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过度信任,使社会工作“丢弃社会服务内容和抛弃贫困者,反而转向承担起抚慰那些焦虑的、孤独的中产阶级的工作,以及据此助其重归有意义性生活的轨道”,[21]而其原因只不过是这些客户能支付起精神治疗费用。一定程度而言,虽然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社会工作避免了西方社会工作的那种病态转向和畸形理念,但由于政社尚未完全分离、第三部门发育迟缓、公民自组织能力弱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加之“政治吸纳服务、行政吸纳治理”的社会情势尚未大为改观,社会工作者也只能选择性地关注某些群体,甚至在偏远贫困地区会出现“因行政系统干预而产生对困境家庭、困境群体支持的整体性忽略”[22]的情况。这显然与社会工作的原初使命和社会治理所要达致的善治目标是相抵牾的。[23]迈向新时代之际,社会工作者既要关注农村议题及其基层治理工作,更要关切处于乡村社区之中的弱势群体和困难对象。因为重归关注底层弱势群体之路,既是社会工作(者)找寻自身存在的人文底蕴和“社会性”真意的基本前提,也是以“政治属性”[24]和“实践本性”为内核的社会工作改善民生福祉和增进社会公平的价值旨归,尤其是在当前全面打响脱贫扶危攻坚战之际。
城西堤线季郎至赵官佐,3m以内均为中粉质壤土,灰黄色,稍湿~湿,可塑,除0.5m耕植层外,以下土层质量较好。
中国社会域情的多样性和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也让本土社会工作呈现出一种“经验丰富、特色不一、模式多元”的异样特征。其中,“嵌入式”发展模式最备受学界关注,并一度被视为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未来走向和应然道路。其原因立基于这一出发点:即考虑到中国政社关系的制度惯性和中西意识形态的话语殊异,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专业社会工作只有以一种“嵌入式发展”姿态来辅助行政性社会工作,[34]方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政治承认。然而,现已有部分学者⑤在开始反思这种“嵌入式”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同时,也尝试性地创设出更具效能和更切本质的“合作式”社会工作发展模式(cooperative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model)。贴切地讲,“合作式”社会工作模式是对当前社会工作者及其机构、政府部门、需求群体三者关系处于扭曲甚至病态状况的自反性省思和内在性超越。具体来说,就社会工作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而言,当前社会工作者(机构)过多承担了来自制度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性事务,甚至有些事实上成了行政部门的附属主体;有些社会工作者(包括机构)还通过话语表达的一致性和治理行动的统一性来置换其自身发展的制度空间和合法地位,反而忘却了自身“保护社会”这一专业志向、社会使命和原初本性,更遑论用一种积极性、建设性和自主性的姿态服务于目标群体。就社会工作与需求群体的关系而言,长久以来,将服务使用者看作病人而把社会工作者视为治疗专家,既是早期西方社会工作者的常态认知,也是先前中国社会工作者的“普遍看法”。然后,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将需求大众“视作一个具备参与对话和协商权利的平等参与者,作为一个能自我负责的自治主体(self-governing),藉而通过搭建基于平等法则的伙伴关系来展开人本中心的案主工作实践(client-work practice),停止继续沿用精神病理学方法上的治疗型实践策略(remedial practice strategy)”[35]等观念尚未内置到社会工作者的内心深处。如此,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间形成的“支配与服从”“能动与受动”的“差等关系”仍旧不断被操演和再生产。而这尤为值得新时代语境中社会工作者去自我省思和检视。由此可说,只有转向“合作式”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道路,并与基层政府和需求群体建立一种基于身份平等、分工殊异、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工下乡”的理念才能为农村基层群体所认可和接纳,社会工作者也才能在因循本性和尊崇使命中有所作为甚至大有可为。
2.1 研究变量与问卷设计 主要选取品牌真实性、网络口碑和顾客价值共创意愿3个变量,在各变量的题项及相关维度的选取方面,笔者在充分考虑杭州龙井茶品牌特点的基础上,参照Napoli等[7]和Morhart等[10]文献以及结合农业品牌的具体特点设计真实量表;依据See-To等[4]所开发的网络口碑量表设计调查问卷题项,在Tajvidi等[28]开发量表的基础上设计顾客价值共创意愿题项。
从近代中国政治演化进程来看,为抑制城乡发展不均衡扩大化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旨在改变基层社会主体间的原子化关联状态,从而构筑以国家记忆与话语、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成了一种政治诉求。一时间,诸如法律下乡、资本下乡、政党下乡等一系列下乡举措成了国家尝试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抓手,并由此开启了自上而下式的城市反哺乡村的下乡运动。在这些下乡的“列表库”中,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下乡活动较多,主体和组织层面的下乡活动较少;单一化的实践方法甚多,基于整体视角和综融取向的服务方法阙如。正因如此,这些下乡活动虽能为农村基层社会提供一定的外在性支持和嵌入性资源,并在促进乡村社会结构转变和治理理念升级之功效上扮演着“辅助型”角色;但从整体实践效果来看,这些以现代性的名义的下乡举措往往既流于形式和浮于农村社会表层,而未能被乡民自觉地加以内化于心并外向于行;更严重低估了乡民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自我改变的能动性,进而简单地将“乡民”这一“能动主体”当作亟待“治理”的“被动客体”,最终超脱于制度设计者的原初本意而使之陷入新的发展泥潭之中。与之不同,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综合系统,社会工作者是支持型社会组织体系的基本构成,其经由提倡积极而有序地参与公共生活,推动公民行动的参与原则从“个体性”迈向“集体性”和“合规范性”,[19]进而拓展乡村社区自组织化的深度、广度和形式。另外,社会工作者较为熟练地掌握了诸如个案方法、小组方法和社区方法等多元实务方法,并积累了大量可“有机移植”和有效推广的服务经验。因此可以说,作为下乡并展开服务—治理实践的主体,社会工作者能够依托基层政府的资源供给而以一种“组织化”“协调性”的方法被编织到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去,进而成为促动乡村社区“自组织化”和“再组织化”②的得力助手。
②提前到来的个体化和原子化社会,击破了既有的农村社区组织结构并使之“松散化”,进而使基层政府治理的行动空间更为逼仄。然而,已有研究证实,作为现代社会管理和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社会工作者在科学化知识和专业化方法的助力下能有效提升社会的“再组织化”程度,甚至能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与优势和综融社区关系等方式化解基层社区的“非组织化”难题(参见徐永祥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的文章《社会的再组织化:现阶段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重要课题》)。
1.2 手术器械与手术方法 采用科医人医疗激光公司的100 W钬激光发生器,配备550 μm激光光纤,配套使用德国Storz公司连续灌洗式前列腺电切镜及直射激光专用操作手件,采用科医人医疗激光公司配套的VersaCut 组织粉碎器械。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身麻醉。
入站操作流程:入站操作流程主要是从外地区货物到达进入本地区,由分拨中心进行卸货,信息采集,分拣,根据顾客目的地放置集货位等待派工出站装车。其中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例如在分拣的过程中存在人力浪费、场地上面的设计不隔离等等。
③张和清认为,这种“文化识盲”现象出现的成因在于,作为一个陌生人和局外者的社会工作内在地限定自身知识内容的使用边界,进而缺乏对当地民情和地方生态的敏感度和认知度(参见张和清等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的文章《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
1.2.2 AFC测定 选择经阴道超声检测AFC,使用西门子公司的SSD3500型超声诊断仪,配有3~5 MHz阴道探头。使探头的扫描面向前,在阴道穹窿部获得卵泡最大切面的信息,使用探头全方位整体性的扫描卵巢,取同一平面上的两条互相垂直的最大径线,对卵泡边缘进行测量,计算在左右卵巢中直径介于2和10 mm之间的总卵泡数,数据纳入AFC计数。测量误差低于5%。
④在制度转型和结构变革的背景下,基层社会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对税费的自收自用,开始变为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在此情况下,基层政府因缺乏控制农村居民的手段和载体,而使其权力范围渐趋收缩、权力效能日益式微,进而使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发生了从紧密的汲取型到松散的悬浮型转向。
⑤以微观社区权力关系演变为切入点,朱健刚、陈安娜指出社会工作的嵌入式模式在具体服务实践中会造成服务行政化、专业社工建制化的政治异化问题(参见朱健刚、陈安娜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的文章《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以街道社区治理为个案研究,陈立周认为社区信任关系的断裂使社会工作的嵌入式治理方式无法获取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支持度,因而也就失去了代表基层群体的合法性地位和社会空间(参见陈立周发表于《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的文章《“找回社会”: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议题》)。
⑥黄宗智、周飞舟、马良灿、龚为纲、冯猛等指出,项目制是“名实不符”的政绩观的反映,是财政目标的异化;而李祖佩、曹龙虎、陈为雷、陈明明等人认为,项目制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一刀切和粗放式服务的做法,是政府整合社会和促进民生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文件资料选编[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16.
[2]民政部. 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EB/OL].(2009-10-12).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zh/2009 10/20091000039649.shtml.
[3]民政部, 财政部. 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EB/OL]. (2012-11-28) [2018-01-20]. http://www.gov.cn/zwgk/2012-11/28/content_2276803.htm.
[4]颜小钗, 黄耀明, 廖晓义, 等.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支持[J]. 中国社会工作, 2018(28): 12-13.
[5]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刘守英,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8.
[6]民政部. 图解: 2019“数”说社会工作发展[EB/OL]. (2019-03-19). http://www.mca.gov.cn/article/gk/tjtb/201903/201903000156 29.shtml.
[7]王思斌.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4.
[8]王思斌.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J]. 社会工作, 2014(1): 3-10.
[9]安秋玲. 实践性知识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建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6): 93-98.
[10]文军.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十大挑战[J]. 社会科学,2009(7): 66-70.
[11]李文详, 高锡林. 社会工作介入与农村社会管理转型[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1): 95-100.
[12]张和清.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J]. 社会科学战线, 2012(8): 175-185.
[13]RICHARD PUGH, BRIAN CHEER. Rural social work: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 Bristol: The Polity Press, 2010: 6.
[14]郭占锋, 李卓. 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及启示意义[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1-11.
[15]孟轲. 孟子[M]. 万丽华, 蓝旭,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05.
[16]墨翟. 墨子全译[M]. 周才珠, 奇瑞端, 译注.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80-125.
[17]庄周. 庄子[M]. 孙通海,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54-67.
[18]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37-245.
[19]方舒. 社会工作促进社会自组织化: 现实路径与道义价值[J].思想战线, 2014(3): 75-78.
[20]KATHERINE VAN WORMER. Our social work imagination: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J]. Journal of teaching in social work, 2008, 22(3): 22-23.
[21]JEANNE MARSH. Book reviews of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J]. 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 1995(2): 125-126.
[22]王思斌.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及其发展——兼论“大农村社会工作”[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5-13.
[23]HARRY SPECHT, MARK E COURTNEY. Unfaithful angels: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85-88.
[24]POWELL F. The politics of social work[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105-110.
[25]王进文, 张军. 乡村社会记忆的提出及其重构[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64-68.
[26]XU BIN. The future for rural social work in China[J]. Rural society, 2009, 19(4): 281-283.
[27]王进文, 张军. “关系”视域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工作生态介入[J]. 社会工作, 2018(1): 71-81.
[28]ROBERT L BARKER. 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M]. Washington: NASW Press, 2003: 75.
[29]陈立周. “找回社会”: 中国社会工作的关键议题[J]. 思想战线,2017(1): 101-107.
[30]ERIN SEGAL. Beyond the pale of psychoanalysis: relational theory and generalist social work practice[J].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2013, 41(4): 376-386.
[31]张军, 王进文.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基于关系为本的实务视角[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6(5): 70-75.
[32]波兰尼. 个人知识: 迈向后批判哲学[M]. 许泽民, 译. 贵阳: 贵阳人民出版社, 2000: 131.
[33]ADRIENNE CHAMBON. Recognizing the other, understanding the other: a brief history of social work and otherness[J]. Nordic social work research, 2013, 3(2): 122-127.
[34]王思斌, 阮曾媛琪.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 2009(5): 128-140.
[35]HELLE CATHRINE HANSEN, SIDSEL NATLAND. The wor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worker and service user in an activation policy context[J]. Nordic social work research, 2017,7(2): 101-114.
[36]折晓叶, 陈婴婴.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4): 126-148.
[37]渠敬东. 项目制: 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 中国社会科学,2012(5): 113-130.
[38]徐选国.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性转向[J]. 社会工作,2017(3): 9-28.
Social Work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e Subject Practice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New Era
WANG Jinw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Social work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s a subject practice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hich has a solid theory and reality basis. The right dire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social work policy, the orderly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talent team and the organic transplantation of social work methods all reflect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work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e original natur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underclass vulnerable groups, maintaining the order and stability of the community, and upholding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justice constitute the multiple practical goals of “social work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 Ow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rural ecological situation and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work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should take the three-dimensional path, that is, identifying the intervention perspective that fit the Chinese rur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turning to the road of cooperative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model, and relying on the project model based on the legalization and contract, thereby promoting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social worker’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ocial work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rural governance; new era;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social justice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9)04-0080-09
■ 收稿日期:2018-04-28
■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互动型’角色转向研究”(15BSH074)。
■ 作者简介:王进文(1993— ),男,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理论。
■ 引文格式:王进文. 社工下乡: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实践[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19(4):80-88.
(文字编辑:徐朝科 责任校对:王香丽)
标签:社会工作论文; 社工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工作者论文; 农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 互动型'; 角色转向研究"; (15BSH074)论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