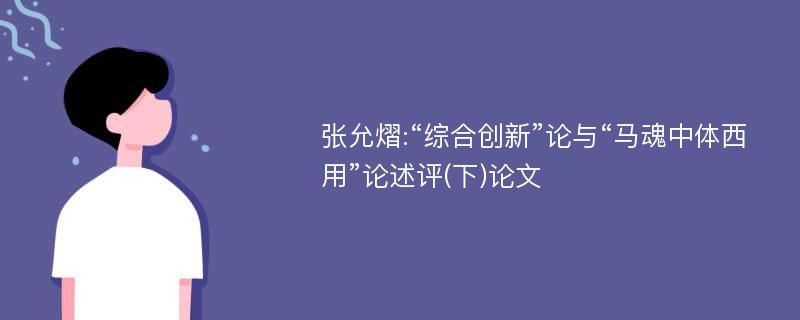
编者按:本刊特约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导张允熠《“综合创新”论与“马魂中体西用”论述评》一文。由于文章较长,本刊考虑到栏目均衡和版面设置,将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已刊登于本刊第2期,本期所登为下篇。
四是竞争性民主选举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特别是在基层,由于基层党政干部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由上级党政部门指派,在群众中缺乏公信力,一旦工作失误伤害群众利益,便可能产生严重的干群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竞争性民主选举是破解这一难题的一剂良药,它从根本上摆正了干群之间的关系,即使干部工作造成伤害群众利益的负面影响,群众可以在制度范围内自我纠正,不会造成社会乱象。因此,与少数人担心的完全相反,民主是实现社会由“乱”而“治”的根本保证。
摘要:文化的“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先生晚年提倡的一种辩证的中西文化观,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砥砺和发展过程。如从明末“中模西材”算起,到“中本西术”的提出,再到“中本西末”和“中体西用”的流行,其思想渊源约有400年的历史。“马魂中体西用”论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方针与“综合创新”论结合起来,采取中国哲学传统的“体用”范畴,开显了新的意境。“马魂中体西用”论与“综合创新”论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那就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兼和中西文化之优长,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魂中体西用”论的三元模式深化和细化了“综合创新”论的内容,在方法上更具“分析”的特点,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进行了创造性应用。
关键词:综合创新;马魂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综合创新”论的意指所归——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谈到“马魂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思想过程时,方克立先生多次表明他的这种提法是以张岱年先生“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思想为基础的,“或者说是接着张岱年先生的思想讲的”[1]。他强调说:“我认为这种‘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观点,是符合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之精神实质的,也是符合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和毛泽东‘古今中外法’之精神实质的。”[2]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没有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早年“三流合一”的思想和张岱年先生1987年提出的“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就不可能有此后方先生把“综合创新”与党的文化方针联系在一起即“16字诀”的提出,也就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借鉴经济学家杨承训的提法形成“马魂中体西用”论①参见杨承训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作者在该书中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方克立先生借用这一“三分法”的模式提出“马魂中体西用”来说明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并在这一模式下阐发了富有新意的自己的文化观。。勿庸置疑,“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的丰富、阐扬和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认同和接受这一思想并对这一思想加以进一步诠释和增益的学者称为“张岱年—方克立学派”。
尽管“综合创新”论与“马魂中体西用”论学出一源、思系一脉,基本思路和建构目标完全一致,但提法的不同还是需要细细琢磨和品味。
(一)“一”与“三”的关系
张岱年先生无论在其提出的“三流合一”还是“三学合一”中,都旨在强调“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三”(即马、中、西)是现状,“一”是目标;“三”是对现状的分析,“一”是对“三”的综合;“三”是事实存在,“一”是价值追求。那么,这个作为价值目标的“一”是什么?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先生就说:“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惟一的出路。”[3]很清楚,这个“一”,就是需要创造出的“新的中国本位文化”。如果说张先生早年对这个新的本位文化的认识还处在朦胧之中,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个“一”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一”既是马,又是中,又是西,是三者的“辩证的综合”和“创造的发展”;但它又是非教条的“马”、非封建的“中”、非西化的“西”。张先生强调这个“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去综合、去创造,但这并不等同说创造出来的新文化是以非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文化,而是“新的中国本位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
至于有人提出“体用难题”“体用困境”“体用陷阱”等说法,认为“体用思维”已经过时,必须彻底抛弃、超越,方先生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体用范畴的含义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就大相径庭。就像“一分为三”原是在“一分为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样,形上、形下统一于“形”的“魂、体、用”三元兼和模式,也是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体用二元模式的基础上变通、发展而来的,应该肯定它们都丰富了中国特色的辩证法。与那种要“彻底抛弃、告别体用思维”之途不同,方先生走出了一条继承和超越民族传统哲学之路,他采取“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慎言体用而不讳言体用、不离体用而又超越体用”的态度,创造性地转换和发展出一种“魂、体、用”三元模式,用来解释和解决当代中国文化“马、中、西”相互关系的难题。
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先生就说:“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必有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为其哲学之根本义,为其系统之中心点,以之应用于各方面,以之统贯部分。这个一贯的大原则却不是可以从别的哲学中取来的,而必须是新创的。”[5]这是说,只有“合”才有可能“新创”,只有“新创”才有可能生出“一”。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一”,就是文化综合创新的结果。因此,张先生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创新意味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人类文化史上高度民主、高度科学的新文化。”[6]“创新”不能凭空而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综合中西文化优长的基础上才能有所新创。这一思路,其实是明末徐光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路径的自然延伸与时代变异。“会通”即为“合”,这是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超胜”而出的“一”就无所生。
应该说,在“会通”“综合”的方向上,张岱年先生与方克立先生是完全一致的。方先生认为,“综合”就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要按照“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思路,“把作为文化资源的中、西、马三‘学’科学合理地整合起来,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辩证统一起来,‘坐集千古之智’”[7],创造具有博大气象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先生认为这就是“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观点,符合张岱年“综合创新”论的精神实质。张岱年先生与方克立先生“合”的价值目的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合一”之“一”的意指所归。“合”起来讲是“一”,但是“分”开来讲,又成了“三”。“马魂中体西用”命题本身就是“三”的排列,三者的功能、结构和定位一眼明了。因此,在方先生的整个论述中,分析方法是其特色。
(二)“综合”与“分析”的方法
上文已经说过,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在路径上是综合的方法,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在路径上是分析的方法。关注“一”必然偏重综合,关注“三”必然偏重分析。
无论在现实场景还是在理论设定中,我们自始就面对着一个逻辑悖论:“三”在不断地汇聚、融合为“一”,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每天都在生长和建构中;但是作为“马、中、西”的“三”也各有自己的源流、体系和逻辑进路,它们同样也与时俱进。“一”与“三”每日都在发展。因此,“一”与“三”甚至与“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将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不会因全球化而消失。换言之,“一”永远在行途中,“三”一直面对着我们。我们努力要把“三”揉和为“一”,而“三”的内在张力却拼命地要离开“一”。这颇有点像行星围绕着太阳转、月亮围绕着地球转——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对冲,只能把他们平衡在固定的轨道上。由此来看,方先生的“三元模式”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和更大的当下价值。
Fe0-PRB技术在含铀废水处理方面得到了研究与应用,但也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制约了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应用的推广.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改进,将会成为Fe0-PRB技术在含铀废水处理方面的研发重点.
在良渚文化中,诸多玉器均有兽面纹或神人兽面纹。兽面纹出现得最多,它的基本形制是两只大眼,有一横梁连接,类似眼镜的横梁,横梁中部连一短柱,类鼻,柱下连一横梁。两横梁夹一柱,类工字。工字下有一横梁,较长。此种造型,大致类似兽面。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合”既是现在进行时,又是未来时,文化思想界“马、中、西”的“三分天下”之“分”主要是过去时和现在时。方先生把握住现在时态之“马中西”的互动现状加以思考,相比张先生富有理想色彩的“综合”观,更具现实性和针对性。鉴于中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马克思主义领导权面临严峻挑战,要对各种学术思想流派进行科学、具体的分析,使马克思主义牢牢掌握当今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导权。这就十分有必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之间的原则界限,避免在一片“西化”与“儒化”热中主流话语销声匿迹。突出“马魂”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指出“马魂”是“主导性之体”,就是要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阵地。否则,辩证的综合就成了无原则的“混合”。在这一点上,方先生目光犀利。有趣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综合创新”派就主张“抛弃二元对立”,结果却搭建了一个“三元模式”,其因就在于从“体”中分殊出了一个“主导性之体”和一个“主体性之体”,一体两立,遂成为“三”。为了更明确地将两“体”区分,突显“主导性之体”的中枢神经地位,故又把“主导性之体”称之为“魂”。方先生指出,这种从“体用二元模式”过渡到“魂、体、用”三元模式的思路,张岱年先生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他还没有对二者作概念上的区分。我们进一步做的工作就是用两个概念来对这两个‘体’分别予以定位。把主导性之‘体’用‘魂’这个概念来标示,借鉴了日本‘和魂洋才’的说法”[8]。
由此可见,“综合”与“分析”都是必要的。正如方先生本人所说:“‘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深化,其主要结论确实是从张岱年先生的有关思考和论述中引申出来的,可以说是‘接着张岱年讲’。”[9]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深化也是对张先生“综合创新”论的重要细化和完善。
(三)“体用之辩”——中国哲学的时代传承
经济犯罪案件现场重建的基点是现场访问和现场勘验。这两个基点不可偏废。在习惯于进行现场访问的侦查实践中,经济犯罪侦查人员尤其应对现场勘验给予充分的重视,将经济犯罪嫌疑人可能遗留在各种空间载体中的痕迹、物品、信息等尽可能地搜集齐全,为在侦查思维中再现经济犯罪过程、重建经济犯罪案件现场打好基础。
“体”“用”范畴是中国哲学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范畴,“体用”关系相当于西方哲学的“本质”与“现象”关系,“体用之辩”就是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高度浓缩的命题,是最有民族传统思辨特点的哲学问题。《周易》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开启了“道体器用”和“形上为体,形下为用”的思辨先河。先秦时期的“天”与“人”,老子《道德经》中“一”与“多”、“道”与“德”、“母”与“子”等诸对范畴之间,也是一种“体用”关系。魏晋玄学明确阐发了“体用之辩”的思想。到了宋明理学时期,“体用之辩”更成为哲学的核心内容。中国哲学中的若干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都具有“体用之辩”的形式和特点,在内涵上也具有双重同构性,除“体用”“道器”“本末”之外,还有“义利”“形神”“理事”“理气”“理欲”“心物”“共殊”“知行”等,这些成对范畴既是对立的,又是“合一”的。用这种既对立又合一的概念来分析、说明事理,便形成了中国哲学普遍的方法论,即“殊相与共相”“个别与一般”的方法论。所谓“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辩证原理,无不是以“体用”之类的“对立法”为思维工具展开的,这是中国哲学的原理,诚如黑格尔所说,它也是中国的“最高科学”。
方克立先生在使用“体用之辩”中,实有不少新颖的创意。首先,他区分了“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进而把“主导性之体”定位为“主体性之体”之“魂”。其次,他把“主体性之体”诠释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实际上,这是把同一个主体即“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析而为三:“生命主体”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华文化生命整体;“创造主体”指作为中华文化生命整体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功能;“接受主体”指中华文化生命整体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德性,其表现为一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为“魂”,另一方面接受西方文化为“他山之石”。再次,将传统二元模式的“体用之辩”转化为“魂、体、用”的三元模式,使之富含深意。本来“体”与“用”概念就是从生物体的形体与功用的具象中抽象出来的哲学范畴,例如人的身体,有体有用,这些都是形下可见的。但是,人的身体和功用都只有在大脑中枢神经支配下才能发挥作用,然而“精神”却是“大道无形”不可见遇的,这就是“魂”。只有“魂”“体”“用”三者齐备,才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生命体。可见,“马魂中体西用”论超越了传统的“体用之辩”,这不仅是对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一种补充和深化,而且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一次创新性运用。
从上文已知,“中体西用”论实际上已经有着长达400年的演变史,在接纳和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中,“中体西用”论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虽然“五四”之后“中体西用”的观点受到了严厉批判,但由于“中学”与“西学”作为一对事实范畴不因情感上的排斥而消失,反因不同时代的需要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体用之辩”作为思维模式是一个没有过时的理性法则,固有的“体”“用”范畴仍然可以阐释出新的时代精神。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体西用”论再次兴起,用“体用之辩”来表达各自的文化观一时成为走俏话题。如李泽厚先生抛出“西体中用”论,张岱年先生提出“马体中用”论,等等,一再引发热议。方先生介入这个话题实际是从评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开始的。2006年他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未究其里就惊诧于他为何重拾晚清的“中体西用”论,有人认为充其量仅是在固有的“中体西用”前面加了个“马魂”而已。他们没有注意到,在方先生那里“中体”的含义发生了质变,“中体”已由彼时的“主导性之体”变为此刻的“主体性之体”了。还有人干脆提出“应当超越过去的体用之争”“必须彻底告别体用范式”“体用之辩应该终结”,等等。应该说,这都是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的误读,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遗产的排斥。
方先生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在他对于“中体”的充满辩证思维的分析中,也包含着这种意向。然而在价值取向上,我们明显感到张先生要抛弃传统的“体用”二元对立,其用力点在“一”上,而方先生同样要抛弃传统的“体用”二元对立,但用力点却是在“三”上,突出表现在“中西”二元之上又加了一元“马魂”,用三元模式取代二元模式。方先生已经意识到了他与张先生的区别,他说:“从体用二元模式过渡到‘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关键,正是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别开来,张岱年先生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他还没有对二者作概念上的区分。”[4]“一”是张先生“合三为一”的价值取向,因此是“综合创新”的重点;而在方先生的构思中,分别对“三”进行论证,明显感到“马魂”是他着力的重点。方先生强调三元模式说明客观世界所具有的普适性,对“一”的理论形态和现实样态则谈得相对较少。本来,“一”在张岱年先生那里也只是作为一个悬置的价值目标。作为后来人,我们要在张先生的基础上努力于“一”的构建,详细地勾画“一”的蓝图。如果仍然把着力点锁定在“一”的解构要素上,那么“一”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拼盘式的,“三”如何“融合”为“一”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当然,方先生在“慎言体用而不讳言体用”时,仍然留给了我们一块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如,“马魂中体西用”论要在三个不同文化实体之间进行功能定位和调适,但又把“魂、体、用”都看成同一个本体或实体的“魂、体、用”,初看起来着实令人费解——“牛之体怎么可以有马之魂”“马之体怎么可以有牛之用”呢?对此,方先生从分析的角度上做出了非常辩证的解释。但是,如从综合的角度来看,“魂”应该是“体”之“魂”,“用”应该是“体”之“用”,“魂”与“用”都应该在一“体”上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马”理解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来说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用”理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精神财富,这一问题似乎就会更加清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有是体就有是用,有是用就有是体,用是体之用,体是用之体,讲“中体”就要言“中用”,讲“西用”就要言“西体”,这应是顺理成章的法则。对于“西用”,我们的理解有点简单化了。如果把“西学”之“用”仅理解为“应事方术”“他山之石”,会留下两个悬疑:一个是“西体”不见了;另一个是“西用”仍然没有褪去“长技”的色彩。
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近代“中体西用”论的局限性。
正如方先生所说,“马魂”不是漂浮无根的“游魂”,它同时也是一个精神性的“指导性之体”,从逻辑上说,这个“体”只能是“马体”而不能是“中体”。同理,“中体”是“中华文化生命整体”即实体,那么,与之对应的“马魂”和“西用”都必须实行中国化——也就是说,它们都要转化为“中魂”“中用”,才能构成“魂体用”三位一体。正如严复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牛之体焉能有马之用?”——这个本来被严复抓住的“中体西用”论的逻辑漏洞,实际上我们今天仍然没能补上,方先生之所以说要“慎言体用”,原因就在这里。“体用”问题虽是理论和逻辑问题,但也是现实问题,不可回避。方先生“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阐发主要不是去解决逻辑问题,而是要解决现实中的文化论争问题。正像“中体西用”论广为流传了数百年一样,“马魂中体西用”论也不失为当下和未来长期处理“马、中、西”三派文化关系的正确方略。
目前,企业在经薪酬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依靠企业本身就可以完美解决的,要求企业具备较好的外部环境。国家以及当地政府因为一些优秀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确保其在自主经营与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开展日常管理活动中,体现其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企业只有在薪酬管理与人力管理方面具备完全自主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调整薪酬结构与薪酬水平,更好的提升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四、结语
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具有展望未来的理想性,方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在一元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尚未定型前,“马魂中体西用”论不仅为各派思想文化留下了互动余地和发展空间,也为将来“三流合一”提供了“兼和”途径和前行方向。未来经过“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而建构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魂,“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体,“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用。换言之,“马”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是伟大复兴的中华文化,“西”将必然被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文明所取代。
参考文献:
[1]方克立等著.谢青松编.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3.
[2][4][7][8][9]张小平,杨俊峰.“马魂中体西用”与文化体用问题纵横谈——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5):18-33.
[3][5]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一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35,239.
[6]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六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52.
收稿日期:2019-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互动与交流”(编号:ZD13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允熠,男,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
标签:中体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论文; 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互动与交流"; (ZD1302)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法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