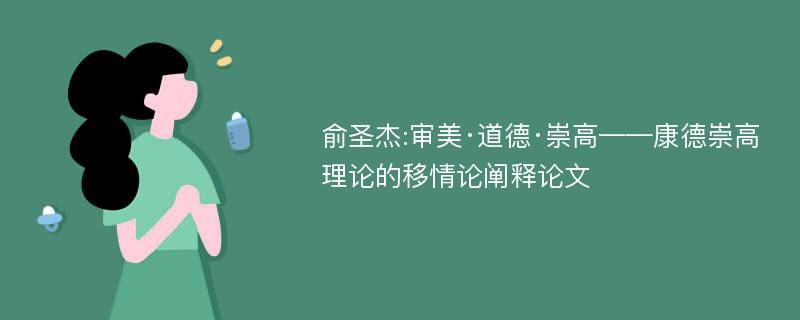
审美·道德·崇高——康德崇高理论的移情论阐释
俞圣杰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康德美学有“崇高”与“美”两个重要的概念。在崇高感产生过程中,康德从情感状态出发,认为崇高与美有着内在的对立,将崇高定义为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感,这就阻塞了崇高感通向美感的道路;但康德提出了一种道德情感来解释崇高感的形成,运用利普斯的移情论美学,将道德情感扩展为一种伦理价值,将移情发展为一种具体的审美机制,既能以人格价值连接起崇高和美,也能够赋予崇高判断普遍可传达性,从而拓宽崇高的内涵。
关键词:康德;崇高;审美;道德;移情
崇高理论是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康德在前人的基础上赋予了崇高新的含义,把崇高升华到了哲学高度,扮演着一种连接自我人格与外界自然的角色,将崇高置于理性力量之上。但在崇高感产生过程方面,康德始终认为崇高与美有着内在的对立,美是主体和客体的无利害的和谐关系,而崇高则是对象与主体对立,崇高感必须经由痛苦向快感的转变过程。康德坚持这一观点大大限制了崇高在美学层面的应用,其原因在于,康德过分强调美与崇高的根源和审美主体情感状态的关联,将崇高定义为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感,这阻塞了崇高感通向美感的内在道路,在这方面,利普斯的移情论美学提供了宝贵的启迪,为深入阐释崇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天气逐渐变冷,真正的冬天来了。每到这个时候,一些与冬天有关的老梗又会沉渣泛起。现在,我们就把它们一网打尽!"
一
要想解释清楚康德美学中崇高感和美感的冲突,就必须弄清楚其来龙去脉。崇高在西方美学上作为一种范畴始于毕达哥拉斯。朗吉驽斯从风格的角度在《论崇高》一文中探讨了崇高,崇高第一次被当做审美范畴来看。之后的柏克明确区分了崇高和美,认为崇高是由痛感带来的快感。而康德对于崇高和美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的研究代表作为1764年发表的《论优美感与崇高感》,将崇高感和美感的区别归因为人性品质、性别差异和民族特性,突出了崇高感和优美感的实践价值。后期的代表作则是其美学集大成之作《判断力批判》,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规定和阐释,奠定了现代美学的理论基础。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是沿着由低至高的认知途径,从优美与崇高相对应的感性经验出发,逐步概括出它们在具体事物之中的不同特性。他将优美感与崇高感的产生归置为实践经验,而人的实践经验的基础是感性经验,优美与崇高依据某种原则,与人的内心活动相结合,可以激发出各种不同的情感形式,“崇高的性质激发人们的尊敬,而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1]6两者的不同在于“崇高的情操要比优美的情操更为强而有力,只不过没有优美情操来替换和伴随,崇高的情操就会使人厌倦而不能长久地感到满足”。[1]7康德在这里明确规定了优美与崇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应不同的感性经验;但这种基于感性层面的区分受到了社会环境和人的主观认识的制约,形式上的崇高感和优美感的探索会随着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而缺乏客观普遍性。康德因而回归到人的内在本质中,由此来规定优美感和崇高感的实践价值。优美与崇高概念的价值,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改善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存在于一切人的心中的爱荣誉——尽管在不同的程度上——也会得到发扬,那必定会对全体造成一种简直是奇迹般的迷人之美”。[1]27总结起来,在这一时期,康德把优美与崇高概念分离开来,展示出它们各自的特性,但其观点受到了柏克等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影响,这种分析始终只是停留在经验性的心理学层面。而《判断力批判》则赋予了美学一种先天原则,将美学脱离了一般的认识论和道德,与此相关,美育崇高的区分也从经验性的区分被提高到了先验层面上。
在《判断力批判》中,崇高与美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可以根据判断的逻辑结构进行四个契机层面的论述:从质上看,二者都是令人愉悦的;从量上看,崇高与美产生的快感是普遍可传达的;从关系和方式上看,二者都不是纯感官的满足,都不涉及明确的目的和逻辑的概念,而且都表现出一种主观的合目的性。用康德自己的观点来说就是:“两者都既不是以感官的规定性判断、也不是以逻辑的规定性判断,而是以反思性的判断为前提的。”[2]82这种反思意味着主体状态的普遍可传达性,意味着主体想象力对无限性的把握以及理性对绝对总体性的要求,而崇高和美的区别正是建立在对二者合目的性的反思之上。
3) 原《办法》仅对四级及以上航道的通航船舶做出规定。因此,根据浙江实际情况,研究界定在四级航道以上。
由此可见,崇高和美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康德也尝试着将崇高和美纳入到同一合目的性的框架中,但在具体的方法层面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展示,美始终是和谐感,崇高始终是冲突感,这在发生机制层面是无法统一的,崇高被限制在了一个狭窄的情感状态之中。尤其是在进入到重要的共通感时,这种分歧更显得突出。审美共通感的概念是知性和想象力协调一致的结果,保证了审美判断的普遍可传达性,作为一个理想的基准它要求每个人对他人的审美判断都表示赞同。但崇高不再是想象力和知性的协调一致,因而与一般知识的主观条件毫无关系,审美共通感在这里是无法派上用场的。所以,我们需要另一种依据,来为想象力和理性的协调一致奠定基础,同时又能与审美判断力发生联系。这种依据只能从道德情感中建立,因为它就是理性对感性的规定性的协调一致,而人的本性中已经具有的这种道德情感就能够为崇高奠基。
正是在合目的性上的差异,崇高和美在形式、情感等方面都体现出了明显的区别。美涉及对象的形式,而崇高却涉及对象的无形式;美直接带有一种促进生命的情感,美感是“想象力的游戏,它能直接促进主体的生命力”。[2]83但崇高因其无形式而无法被我们的感官把握,只能通过某个不确定的理性概念的表现,它不单纯是一个审美判断,还是一个理性概念。作为主体的人在面对崇高的对象时所感到的并不是愉悦,而是先感到恐惧,继而产生痛感,然后在人的理性能力的升华下,恐惧变成崇敬再成为愉快。美给人以积极的愉快,而崇高带来的愉快则是“消极的愉快”,因此,崇高不是主客体之间和谐统一的静态美,而是双方在对立、冲突之中趋向统一的动态美,这样的动态活动展示了人的本质力量,呈现了实践主体努力迫使现实客体与自身趋向相统一的过程。表面上它的对象是自然对象,但实质上却是人自己的能凭理性胜过自然的意识,朱光潜将康德的崇高理解为:“对自然的崇高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使命的崇敬,通过一种‘偷换’的办法,我们把这崇敬移到自然事物上去。”[3]364崇高感彰显着主体的理性精神的伟大,最终指向主体的崇高。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合目的性的反思中,崇高和美已完全进入了主体之中,康德进入到了一个纯粹主观的状态,对崇高和美的理解进入到了先验层面之中。这和早期康德美学想比,它完成了一种主体转向,即不只是将崇高与美与主体之感受相关联,而是要从主体自身去探讨崇高与美得以可能的基础。只有彻底摆脱与外在事物的关联,才能够完全摆脱日常生活的纠缠,将人自身所内涵的可能性展示出来,也就是说,崇高与美首先成为两种不同的情感状态,两种情感再分别指向崇高与美并反映在对象之中,我们因而获得崇高的对象和审美的对象。
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应积极与旅游企业进行联动,鼓励和引导旅游专业师生走进企业,到旅游企业进行考查和调研,以增强学生们对旅游企业发展方面的感知能力。组织教师到旅游企业进行锻炼,以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高职院校还应充分发挥旅游企业的人员优势,适当聘任旅游企业人员作为兼职教师,以有效提高旅游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水平。此外,高职院校还可以采用组织企业讲座、校企学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使旅游专业师生能够对旅游行业的发展状况有充分的了解。
二
利普斯移情说借用伦理价值实现了美学上的圆满,但这只是将这种扩张的道德情感应用于美学层面的阐释,我们需要探索将其运用在崇高判断中的可能性。
首先是非功利性,利普斯的审美情感同现实是没有关系的,甚至还架空了历史观念、科学知识的影响。虽然在我们审视艺术品时,会有一些观念陪伴着我们:作者的创作意图、艺术品的材质、创作的时代背景等,但这些都不会和审美愉悦发生关系,反而推动着我们对艺术品的静观,帮助我们进入审美阶段。就如利普斯在《美学》第一卷里写,“知识和联想的重要性在于帮助审视的运行,但在进入移情阶段后就消失了”。[5]127其次是审美道德化,审美情感最终走向伦理价值,利用抽象的“人格”“人性”来统一美和善。在《悲剧性》一篇中,利普斯运用移情,将人对于悲剧人物遭遇的同情怜悯推向了人对于异己人格的理解上,人类根据自我的结构和本质特征推出了一个异己的我,这是一个“被限定的、客观化的、固定在我以外的世界的某个位置上的自有的我,那么对异己人格的评价就是对自我的评价,对异己人格的价值感就是客观化的自我价值感”。[4]322这种价值感也在我看到别人的灾难时得以增强。达到利普斯自己所说的“全部的美学使命和一部分的伦理学使命”,这样的明显的伦理倾向,正如刘半九所说,是康德“绝对命令”在美学领域的演绎。[4]333综上所述,审美愉悦就是审美主体对一种纯粹伦理意味的人格价值的欣赏。利普斯遵循了康德的意见,认为审美是一种主客之间的和谐统一。他认为,在审美体验中,一旦进入理想的审美愉悦中,主体就置换了对象,“我和你完全一致,我的审美体验变成了对自我精神价值的欣赏。所谓的主客界限消失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对象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对象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4]368在审美过程中,人类借助移情实现了对象和主体的同一化,使得自我人格的伦理价值成为审美体验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协和一致的愉悦感,即美感。
B段音乐反复之后,接着是重复A段的“劳动呼声”。然后进入C段音乐。这一段音乐好像是一位健壮劳动者的“男中音独唱”,左手以壮健、饱满的和声给予衬托:
当我们宣称要对康德的美学命题进行改写时,显然并不是玩一种概念偷换,而是要对道德情感进行新的界定。我们所说的道德情感,并不是狭隘的关乎人实践层面的律令,而是一种带有伦理意味的能与人格价值发生联系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引入利普斯的移情论。所谓移情,即主体首先看到对象的行为状态,然后在自身意识中对这一行为状态进行摹仿,感受自身在这一状态下的情感内容,最后才进行表达,把这一情感内容对外移置到对象身上。这是一种形式论美学,基本沿袭了康德,对于形式的论证较为明确,“在审美观照里,只有审美对象的感性形状才是被注意到的。这感性形状才是审美欣赏的对象”。[4]376就像对大理石雕像进行观照时,大理石只是材料,这个雕像所展示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形式,只有人的生命进入其中以后方能展现出其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审美内容决定了审美活动本身,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我们是因为什么而觉得这件艺术品是美的?
康德认为美是合目的性的自然形式,自然美具备我们的判断力所规定的对象的形式中具有某种合目的性,这种目的性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对象的外在形式与主体的心意状态相适应,与我们先天的某种判断力相契合,从而使得对象与主体之间达到一种无利害的和谐关系,能够让我们从中得到直接的预约情绪,对象因而成为了我们的愉悦的审美对象。而崇高感不同,它表现出的是那种无规则性,那种能够激起人内心的恐惧感的形式与我们的判断力而言是相悖的,是与我们的判断力相违背的,而越是这种违背我们的判断力的、对我们的想象力具有很强暴力的物体,却越被认为是崇高的,“崇高就是那通过自己对感官利害的抵抗而直接令人喜欢的东西”。[2]107当我们面对陡峭的悬崖,带有毁灭力量的火山时,我们只要是站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就会欣然把它们称呼为崇高。这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在此刻提升到了另外的新高度,有一种力量帮助我们超越了自然的威力。康德认为这是一种来自理性观念的力量,这种力量和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和文化修养相关,帮助主体克服着想象力带来的无规则与混乱。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对此进行了论述:“对自然界崇高的判断倒并不恰好由于它需要文化教养,因而它就是首先从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或只是在社会中合乎习俗地被采用的;相反,它是在人的本性中、亦即在人们能够凭借健全知性同时向每个人建议且能够向他自己要求的东西中有根基,也就是说,在趋向于对(实践的)理念的情感即道德情感的素质中有其根基。”[2]105因此,与审美判断中单纯的合目的性(想象力与知性的协调)不同,崇高中的合目的性是间接的,是理性和想象力之间的互动。想象力和理性是对立的,理性是高级的合目的性,而想象力则是无规则、杂乱的以及令人不安的,是不合目的性的。高山、巨浪都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力的合目的性的事物,到了理性这里就变成了更高的合目的性:想象力与理性处于一种严肃和紧张关系之中,想象力不管是在数学的崇高中 ,还是克服对强力的恐惧,向力学的崇高中挺进,都是在为理性服务,作为它的工具,完成它的事务。
三
康德把崇高和美与道德情感关联起来。在康德看来,道德情感是与审美判断力有亲缘关系的,“当一个主体在自身中感觉到感性的障碍,同时却能通过克服这障碍而把自己对这障碍的优越性感觉为自身状态的变相时,它的这种可规定性,即道德情感,毕竟是与感性的[审美的]判断力及其诸形式条件在下述方面有亲缘关系的:它可以用来把出自义务的行动的合规律性同时表现为审美的,也就是变现为崇高的甚至于美的,而不损害道德情感的纯粹性”。[2]307-308也就是说,道德情感虽然属于理性的判断力,但是它在调和理性和想象力层面却能够发挥调和作用,由此产生的和谐感与审美情感能发生一种内在的沟通。但康德显然对这种道德情感充满警惕,就在于它会影响审美的纯粹性,康德认为,“智性的、本身自在地合目的的(道德的)善,从感性上[审美上]来评判,必须不是被表现为美,而是宁可被表现为崇高”。[2]117崇高感和道德感都是理性对感性施加强制力的地方,后者作为前者的工具进行服务。如果崇高是因为道德产生的愉悦感,它就会产生利害感,这样一来,崇高的纯粹性就被破坏了。但康德也指出,崇高并没有被限制在合法的事务下,崇高的判断并不把一个确定的概念作为基础,而是呈现出一种想象力和理性本身的主观游戏的自由和谐。这样,崇高是否是美感这一问题就变成了:崇高的判断是否是自由的、无规定的,还是强制的、被规定的?这也是崇高感是否能与美感形成内在沟通的关键。
在《美学》第一卷中,利普斯将人格引入到了美的范围内,他认为一个观察者只能关注于形式,反之,观察者的人格才是移情的内容。因为这种人格的内容发源于观察者,其受限于观察者自身的心理状况,“譬如小孩容易在移情过程中受到自身限制,因为其道德情感的不成熟”。[5]26在此后的工作中,利普斯不断地将这种审美情感的人格化扩大为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经验。在1912年的《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中,利普斯将移情扩大到了整个人类社会,以此作为社会运行、人类沟通的基础。他将移情分为了实践的移情与审美移情,虽然实践移情才是我们人类产生利人情感、构建社会关系的直接原因,但美学移情的非功利化丰富了人类的情感,帮助我们超越“物的价值”走向“人格价值”。当我们进行审美的时候,会发现:“对象内部的生命活动,感受到对象的人格价值带给我的愉悦,同时,我们有一种精神的自发行为,在移情过程中实现了意愿的满足,对象的内部的生命就是自我的生命,而那个‘我’不是日常现实中的我,而是更纯粹、开阔、更高的自己。一切的美,至少在观照的刹那会使我们成为更善更完整的道德的人。”[6]18综上可以看到,利普斯大大拓展了审美情感的边界,从“自我人格价值”扩展到了“作为人的绝对伦理价值”,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种伦理道德情感的两个特征:
首先需要了解利普斯论著中的“同情”和“移情”两个概念。一般的理解中,同情被理解为“feeling with”“follow-feeling with you”,即与他人共同感受,而移情被定义为“feeling into”,进入他者之中。但在利普斯的观点中,同情感受和如今我们理解的移情意思是一样的。在1897年《空间美学和几何学、视觉的错觉》中,他讲述到主体在石柱中感受到自我的自然行为,这种行为“就是给与了主体快乐。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审美愉悦都是一种同情感受(Sympathiegefühl)”。[4]374他对“模仿—表达”直觉的描述,将这种主体进入对象之中的倾向也称作是同情(Mitfühlen)。在1903年以后,利普斯开始频繁地使用“移情”(Einfühlung),但是奇怪的是,利普斯并没有区分清楚移情和同情这两者。这样的观点出现在《美学》第一卷中:同情看上去像是移情的另一种表达。[5]48“同情”是移情的积极形式,是一种自由的内在参与,与此相对应的还有移情的消极形式,“积极移情是和谐体验,消极移情是不和谐的。我们可以将和谐状态称作是同情(Sympathie),同情是用来联系自我和他者,令不同个体之间相互接纳、理解。这是人类自身欲求同外界他者保持平衡的途径,我们也可以称这种积极移情为‘同情移情’(Sympathetic Einfühlung)”。[5]368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等式:同情感受=积极移情=同情移情。所谓的积极移情,利普斯将其形容为“可以附加到移情体验上去的原初体验”,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完整的移情”,在审美体验中,就意味着我利用移情直觉将自我投射进入到对象之中,从而实现一种同一,达到审美愉悦的状态,那么“不和谐”的消极移情(negative Einfühlung),也就是一般的无法达到我与对象同一化的“移情”是不是就不具有相应的功效呢?首先我们要清楚,利普斯的“消极移情”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他形容其为“移情体验变成我自己的原初的体验行为的趋向不能实现,因为我之中的某个东西反对它。这个东西可能是我的一个瞬间的体验,要么是我的一种人格”。[5]347消极意味着在移情活动中往往会使主体脱离其中,譬如,我看到一个雕塑“高兴的国王”,我在我的内部体验雕塑的那种姿态,却感受到了一种傲慢的情绪,在我的意识中这明明是一个傲慢的过往,这种傲慢强制性地进入了我的体验中,和我内部发生了分歧。那在移情的过程中,我面对雕塑的姿态就会产生一种抵触感,我的人格对其产生了排斥,防止这种傲慢危害到我自己的人格。移情仍会产生,但始终是处于消极状态。
但这种“消极”的移情依然会产生美感,在《悲剧性》一文中,利普斯赋予了“消极移情”另外的美学功能,即悲剧美感。悲剧快感是通过“堵塞法则”和我们的心理状态发生联系的:一个心理变化、一个表象系列,在它的自然发展中,如果遇到遏制、隔断,那么心理运动便被堵塞起来、停滞不前。并且在发生遏制、阻隔的地方,提高了它的程度。此时,我们对对象的感受都是片段式的、局部的,按照一般的法则,我们需要补充,将这种感受补充完整,但事实是,补充以后的感受就不会是原来的感受了,并且会和原有的对象发生抵触,造成消极的移情状态。于是我们的心灵目光就长期停留在了这个片段式的体验上,因为这种凝视,一种新的心理重量产生了,我习惯于一堵挂了画的墙壁,有一天这幅画突然消失了,空荡荡的墙壁在我心中阻碍了我原来的感受方式,我对其进行凝视,从而使其在我心中的心理重量一下子加大了。我的一位朋友突然去世,我与他之前的交往一下子隔断,使得这位亡友在我心中的重量加大。总之,因为表达被阻碍,使得主体发现了原有物体对自己的价值,从而愈发地希望拥有它的现实性。在悲剧中也是如此,只要人还保持着作为人的属性,我就会对其中的恶人遭受灾难也产生同情,“在我身上被灾难所唤醒或增强的价值感,现在连同令人嫌恶的灾难事实本身,一起构成了怜悯”,[4]338使得我感受到自身作为人的价值的可贵,这种因为被我看到的灾难在我身上造成的、对人的价值的感觉,也是一种移情。到这里不难看出,这种对象与主体之间不断发生情感的冲突对立的“消极移情”,就是一种崇高感,而利普斯认为其更接近于人的一种人格价值的表达,它是“是作为那种教导我们从人的崇高性中理解人、理解人性的事物而崇高,是作为那种教导我们更强烈、更深刻地感到自己是人,从而鼓舞了我们的事物而崇高”。[4]345这就可以看到,即使移情处于消极的状态,依然能够转化为悲剧性的人格价值触发人的快感,成为一种崇高感。崇高的快感的来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一种人格价值的放大化,这跟积极移情产生审美愉悦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后者中,审美移情是顺利的、充分的,完全将自我的心理状态移置到对象中,从而造成了一种主体和对象同一化的心理感受。如果我们继续思考,就可以发现移情是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我与对象发生了联系,对象被摄取在我之中。这个对象,与当时的我的精神、和我精神活动中的各要素的关系,如果能够达到和谐一致,就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并最终从对象上获得了快感。但自我人格价值和客体价值往往又是对立的,所以这两种价值是我们感情的并立方向。在我和对象的心理活动中,两种价值感是相互消长的,却又遵照同样的法则成长,决不能把一方归入另一方。这里,客体价值和人格价值的关系论证就讲清楚了之前利普斯的“积极移情”与“消极移情”的机制,无论是积极移情产生的审美快感还是积极移情所触发的崇高感,在其中起作用的都是人的伦理价值,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传达出来。
智能旅游更多是指应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信息处理等技术,达到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框架的契合,最终使得旅游部门和游客都可得到明智的选择。所有游客都可依托大数据所形成的海量数据,形成大数据平台,帮助游客制定个性化旅游、数字化旅游,最终实现无障碍旅游。
这种带有伦理意味的人格价值连接起了崇高和美的内容,而移情机制的存在使得崇高和美发挥着各自的效应,崇高也能够产生审美体验的快感。移情是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能存在,它推动着主体和对象发生关系,进行主体人格价值和对象的双向互动、并立而行,当人类的伦理价值能够通过移情得到合理表达,无论是在对象中以美感的方式涌现,还是因为堵塞而导致的崇高感将自身“人格价值”不断放大,这都能将主体送往美的彼岸。以移情为方法,在崇高的感受中也存在着共通感,崇高判断获得了一种普遍可传达性。而以伦理和人格为内容,审美和崇高不再是狭隘的情感状态,而是进入到了更为广阔的价值层面,审美和崇高得以在这里进行沟通,道德和审美、理性与想象力的争执也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参考文献
[1] 康德.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康德. 判断力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 利普斯. 论移情作用[M]//刘小枫. 德语美学文选: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32-390.
[5] LIPPS T. Ästhetik1: Psychologie des Schönen und der Kunst[M]. Leipzig: Verlag von Leopold Voss, 1903.
[6] 利普斯. 伦理学底根本问题[M]. 北京:中华书局,1936.
Sublime, Morality and Aesthetics: an Empathy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Sublime Theory
YU Sheng-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In Kant’s aesthetics, the sublim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that is in harmony with beauty.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the feelings of sublimity, Kant starts from the emotional state, proposing that the sublimity and the beauty are internally opposite. He also defines the sublimity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which blocks the way of the feeling of sublimity moving to the sense of beauty. But Kant suggests a moral sensibility to explain the sublime. We believe that the use of the empathic aesthetics of Lippes, the expansion of moral emotion into an ethical value,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into a specific aesthetic mechanism, can not only connect the sublime and beauty with the value of personality, but also endow the sublime judgment with universal transmissibility, thus broadening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sublime.
Keywords: Sublime; aesthetic; morality;empathy
收稿日期:2018 -12 - 26
作者简介:俞圣杰(1993-),男,浙江新昌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美学,审美移情说。E-mail: ysj1993.love@163.com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9)03- 0018 - 06
(责任编辑 夏登武)
标签:崇高论文; 康德论文; 对象论文; 价值论文; 主体论文;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浙江大学中文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