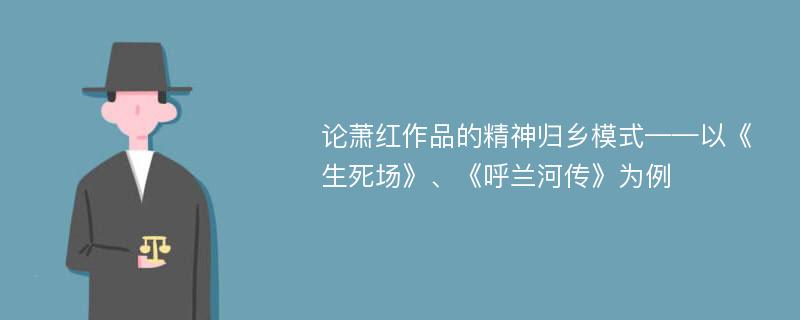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330022)
摘要:回望中国文学的创作历程,有着“归乡”情结书写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鲁迅的《故乡》开启了“归乡模式”的先河,东北女作家萧红在文学史的长河中用31岁的短暂生命惊起了一池波澜,她长期漂泊异地,落脚无根,用沉重的生活痛感体悟世事艰难,她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东北故地的鲜活记忆,在文字走笔间实现了她身为异乡人的精神归乡之旅,本文结合《生死场》、《呼兰河传》两部作品进行深入解析,力图走进作者萧红的灵魂深处,追探生命微光。
关键词:萧红、东北、异乡人、回乡模式
故乡,一直以来都是哺育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源头,中外很多作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将“故乡书写”融入个人的创作之中,东北著名女作家萧红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二十世纪初期最前卫而最有成就的东北农民生活代言人”[1],她少时离家,一生流亡,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她一生创作的众多作品中,对家乡的守望成了文本深处不变的母题。《生死场》、《呼兰河传》是她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分别创作于1934年和1940年,同为书写故乡的力作,风格却迥然有别:《生死场》带给读者的是一种不忍直视,让人几度哽咽无言的生的压抑感与痛感并存的阅读体验;《呼兰河传》中,萧红则一改沉郁笔调,以一种夹杂着淡淡伤感的心态在呼兰河县的小镇上徐徐回望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店,笔到之处,满是深情。两部小说的情节刻画描写中既有对故乡落后的风情民俗的直言批判,也宣泄着作者内心强烈希求“归家”的精神渴望。在对故乡风物的回味、勾勒、描摹中完成了萧红在文本创作意义上的精神情感归乡之旅。
一、探究文史上的“归乡模式”
“有限的结构规律,可以衍生出无限的外部形态”。[2]在文学史上,关于归乡的文学书写作品非常多,在长期以来不断对历史进行回望、反思的过程中,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叙述模式应运而成,即“归乡模式”。如果从归乡方式上对这种叙述模式进行细分,则又可细分为“身体归乡”和“精神归乡”两种。“身体归乡”指的是作品中对于远离家乡后的主人公在回乡的时间、地点等方面是有明确界定的,即强调归乡这一具体行为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代表作品如:鲁迅的《故乡》、《祝福》、废名的《桥》、吴组缃的《箓竹山房》、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张承志的《黑骏马》等等。这些作品中,主人公一般是基于一定原因远离家乡,后重新再回到家乡之际,内心情感世界波澜起伏,对家乡现状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再熟悉的陌生感与重融家乡的不适感,作品结尾多以主人公的再次出走作尾,形成“离去——归乡——再离去”的经典归乡模式;而“精神归乡”指的则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或创作者本身并未真实的返回故乡,但在小说情节描摹和实际创作中紧扣乡情、乡风、乡貌,寄予着一定书写意义和价值的“精神归乡”模式。例如经典之作《狂人日记》,狂人时而癫狂,时而清醒,在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下寻找自己的处世价值,作者鲁迅借狂人之眼冷视故乡的草木人情,在批判中实现了精神世界的寻乡与归乡;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反复书写的“秦岭大地”、还有迟子建倾心打造的“北极村童话”,都无一不是作者借文学书写实现“精神归乡”的例证。“归乡”书写在文学史上始终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论是“身体归乡”还是“精神归乡”,书写者都在力图通过对家乡的寻觅与重构渲泄一份浓郁的“乡愁”情结,鲁迅的开创意义不可小觑,而后来作家的不断继承与发展,也使得这一模式的书写方式更加多元,更加富有生活性和烟火味,萧红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二、萧红“精神归乡”的文学创作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该多么渺茫!而况送走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我的是异乡的风霜!”[3]一段萧红的自述道出了她常年漂泊在外的内心的无限凄凉之感。漂泊往往意指生命个体在生存空间的动态转换中呈现出来的不稳定的状态,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存在状态,它既是对固定居所的游离,又是对固定居所的寻觅,反应了生命实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冲突、不和谐的关系。
“漂泊与流亡”是萧红31年生命里中后期难忘的人生记忆,她一九一一年五月五日正逢端午出生于哈尔滨市呼兰县的一个仕绅家庭,父亲张廷举是呼兰小学的校长,母亲姜玉兰出身书香门第之家,作为家中的长女,萧红自出生就背负着“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的”的乡俗传统习俗,被打上了“不肖子”的符号印记,在家庭中备受冷漠的萧红从外祖父那里收获了亲情与爱,这也对她后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萧红的成长与学习,她不断接触新事物,开阔眼界,面对让人窒息的家庭环境,萧红以决然的心态选择与父亲决裂,出走异地,而这一走,就是十五年,她的人生从漂泊开始,又以漂泊的方式结束。但在萧红的内心深处,始终眷恋着那块有着她和祖父温暖记忆的黑土地,尽管她身处异地,却在精神世界里一直在寻找着归家之路,一个孤独的奇女子,用文学支撑着自己的外在的骄傲与内在的悲悯,《生死场》、《呼兰河传》为她搭起了一座“精神桥梁”,借此帮助她弄清楚长期困扰在心中的疑问:故乡到底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对一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带着惶惑和迷惘,她开始了一场精神归乡,文化寻根旅程。在这个不断寻觅、发现、咀嚼、扬弃的过程中,她批判着夹杂在乡间的民族劣根性,也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宽容的对待着故乡的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静与变。
在小说《生死场》中,萧红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处处充满生死、杀戮、灰暗的乡村世界。在那里“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4]、人们似“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5]村中女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繁殖同时进行,服毒自杀后复活的王婆,被丈夫当成“炸尸”,棒棍相加;曾经恩爱的夫妻在生活的拮据面前坦露人性的丑恶,成业在盛怒之下摔死了自己的孩子;打鱼村最美丽的姑娘月英生病后被丈夫虐待致死,一幕幕惨象在小说《生死场》中遍布横生,像一道道难以去除的伤疤爬满萧红的记忆。如果说《生死场》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冰冷尖刻的萧红,那《呼兰河传》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女人在生命最后流露出的温婉。较之《生死场》的粗犷坦直,《呼兰河传》有更多凄柔的怀念。在呼兰县,童年的“我”整天围在外祖父的身边,感受着乡村的一切,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戏、娘娘庙大会,看大坑、翻储藏室都充斥着“我”的儿时记忆。最让人难忘的还是“我”和祖父的后花园,那些日子里,祖父戴大草帽,“我”戴小草帽,祖父栽花,“我”栽花,祖父“拔草”,“我”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一老一少一起看花开,听雨落,快乐的生活劳作着。在童年萧红的心里祖父成了世上最亲的的亲人。萧红在小说中怀念的是祖父带给她的安宁、和谐、快乐的生活,通过后花园这一载体,萧红宣泄了她对生活中爱的渴望和对故乡绵延不绝的思念。萧红一生走过很多地方,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北京、武汉、重庆、香港,长期的异地飘零生涯让萧红一直在写作中找寻心中的精神家园,实现了“精神归乡”。
三、萧红“归乡”书写的独特性
远离故土的萧红在遥望故乡的视角中因时间距离的拉长,记忆逐渐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这也体现在她的创作里。例如作品《生死场》,她没有像一般的作品那样,完整而缜密地叙述故事,而是选择了片断拼接或场景组合的叙事模式。小说里很少有明确的时间标志、典型环境和清晰的情节线索,也缺乏连贯鲜明的人物,整部作品似蒙太奇的电影镜头的展现:第一章开头写山羊嚼树根,二里半寻羊,王婆的故事等等,如水一般流淌,然后是妇人和孩子在麦场上驱赶老马,打麦子……许多镜头的组合展现给了读者一幅幅形象的画面,具有图像的直观性。这样作品就具有了一种神秘而遥远的距离感,产生了完美的审识效果,这是对传统小说中“归乡”书写的一种重要突破。此外,《生死场》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这种叙事模式不像《故乡》和《祝福》中那样,叙事者“我”和故乡的人有了正面的接触,还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也不像“狂人式”的自我分裂。而是虽然叙事者身在外地,灵魂却一直在故乡徘徊,似一个幽灵飘荡在呼兰河小城的上空,俯视着这里的人、事、物。这是萧红对鲁迅开创的“回乡”模式的继承基础上的一个发展。
“艺术中一切形式均为抽象的形式,他们的内容仅是一种表象,一种纯粹的外观,而这表象,这外观也能使内容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内容的表现会更直率,更完整。”[6]到1940年,萧红对《呼兰河传》的创作更显成熟,对世界的看法更理性,“归乡”书写也更具特点,更能够合理把握艺术的书写形式。像《狂人日记》用“狂人”这样一个特殊角色一样,萧红的回归渴望在《呼兰河传》里寄托给了一个精灵:“七八岁时的自己。”她借助童年时的自己,用一种新奇的第一人称的孩童语气和视角,引领我们走进了呼兰河。离家出走、和父亲断绝关系的萧红意识到自己和故乡已经格格不入,因为在农村人的眼里,这样的女子与“狂人”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儿童的视角终不能掩盖萧红思想的冷峻和尖锐,这种表面的单纯和内里的深刻,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同时也预示着,萧红真实返乡的不可能。所以鲁迅和萧红的“归乡”模式的作品都是灰色调的,回乡的兴奋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伴随着回乡的经历,感觉最多的还是一种莫名的忧伤,因为他们认识到故乡的痼疾所在,却不能真正融入这个坚硬的堡垒,更没有能力彻底地打破它、改变它,只能看着这些乡民的悲剧一代代地继续上演,这背后是一份无奈和悲伤的情绪。
相对于鲁迅而言,萧红更是寂寞的,甚至是苦闷和“消极”的。一个太久没有感受到人间温暖的人,一个太久没有看到朝阳的人内心世界往往是灰暗、冰冷且扭结的。有学者分析说萧红的苦楚来源于感情的不顺利和她没有融进农工劳苦大众中的原因,个人觉得这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侧面。萧红,是一个有着鲁迅般深邃思考力的女人,她和鲁迅一样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质疑和忧虑。在她的文本中我们可以读出她价值观取向的摇摆,对于保持千年的民族传统,对于东北边地人们长期以来的生活状态,是觉醒反抗还是不逾规矩的安静生活,她自身没有准确的答案,对此她持怀疑、保留态度。和鲁迅一样,在面对激进的思想时,她没有盲目追随,而是恪守冷静与客观,以自己独特的叙事空间和书写方式描绘着真实的故乡,真实的中国。怀揣一份深情,在精神世界的探寻中找到一条独特的归乡之路。
参考文献
[1][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84页.
[2]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3]萧红:《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4][5]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Ⅰ)》[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第220、300页.
[6][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作者简介:张晓旭(1991.08-),女,辽宁沈阳人,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