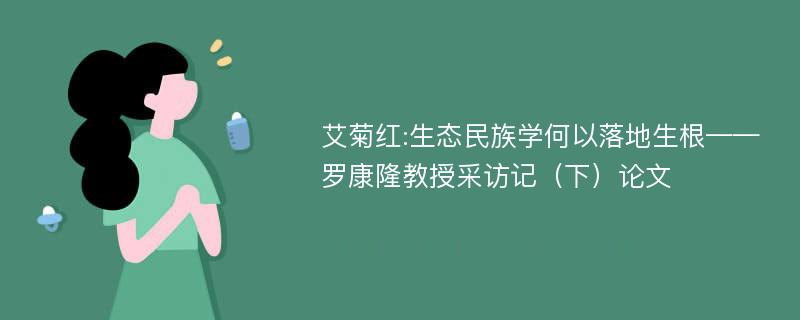
专 家 访 谈
摘 要:罗康隆教授着重讨论了他在研究当中对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理论的应用,以及该理论在解释中国生态问题的不足之处。特别从他对湘、黔、桂地区生态民族学研究的案例,谈到了文化适应理论的解释能力,认为地方性知识是文化与生态的耦合,地方性知识对当下国内和国际所面临的贫困、环境危机、民族冲突等等问题的解决都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归根结底,生态民族学所关注的仍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全球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从民俗社会到国家社会到全球社会的问题;从小传统到大传统到人类“类本质”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生态民族学今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生态民族学;地方性知识;文化与生态耦合
在此次访谈中,罗康隆教授从自己的研究案例出发,对研究当中应用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对国内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和前景进行了展望。
艾菊红(以下简称艾):在您的研究中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理论影响比较大,表现在哪些方面?
罗康隆(以下简称罗):是的,在我的研究中,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理论影响确实比较大。斯图尔德作为生态民族学的奠基人,他提出的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有重大影响。为此,我与我的硕士研究生谭卫华合作翻译出版了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美国的新进化论派的代表人物怀特提出的技术论(或者工艺论),以及技术与环境的产出与投入的比例等等,这些学术思想为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提供了基础。比如说,斯图尔德在新进化论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双重进化模式(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看到人类文化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从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通过阶段性的发展是人类走过的道路;二是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过程而造就的文化发展理论。斯图尔德进一步对文化内核展开探讨,指出在探讨文化变迁的时候,要厘清哪些文化要素容易变迁,哪些文化要素变化缓慢,哪些要素的变迁可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迁等。这对我们理解地方性知识、理解特定环境下的民族文化与所处环境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斯图尔德还提到了从民俗社会到国家社会,从核心家庭到社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对文化的影响;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出发,对大小传统相互间依存的推进,即从核心家庭到民俗社会,再通过国家策略和国家在场导致的国家社会等方面的探讨也是极具价值的分析。这一点也是过去人们在讨论“文化生态学”时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一面,过去人们一提到斯图尔德,就局限在他对生态文化的自然环境分析。实际上斯图尔德除了关注生态环境维度外,还关注社会环境的变化问题,比如他通过对大盆地肖肖泥人的研究以及猎群队伍的大小,来反映民俗社会到国家社会建构历程。斯图尔德的这些研究,对我的生态民族学研究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艾:那么,这个理论在当下你认为对我国目前生态民族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罗:生态民族学理论对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生态扶贫、乡村振兴、民俗旅游、生态产业以及村落保护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今天的精准扶贫、生态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政策制定中,如何与乡村社会传统知识对接、对话,寻找共同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如何纳入国家层面去考虑乡村发展,这也是我们生态民族学必须关注的领域,尤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怎样才能从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文化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引领全球全新的发展道路,这也是我国当前生态民族学学科建设的现实意义所在。
白丽筠握着小银匙,像握着一把匕首,说,那个季经理垂涎于我已经很久了。他是李老板介绍我认识的,可是我一直没有答应他的非分要求,顶多只让他在酒桌下面踩一下脚尖,摸一下大腿什么的。
艾:湘黔地区是您进行研究的主要田野点,而且您也提出这个地区是我国自然过渡地带,因而自然环境和民族特征复杂多样,目前在湘黔进行生态人类学研究,您觉得主要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急需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我咕咚一下跪在了地上。这一下果然管用,听见动静的马兰停下了手,一脸疑惑地望着我。我高高地举起右手说,我对天发誓小兰,我绝对没有动过李金枝,要不然天打五雷轰——
我的田野调查主要聚焦在侗族村落。侗族是一个以家族为主体、集体意识很强的民族,由此所引发出侗族热心公益事业,具有互助、尊老爱幼的精神,这一民族精神很值得去研究,此其一。其二,侗族地区的自律性地方制度体系,比如侗族款约组织、林地契约、老人协会、习俗、交往组织等也需要深入挖掘。其三是侗族的生计体系,如“稻鱼鸭”,“林粮间作”等等。
但我认为眼前最需要去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政策与地方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还是要从人工营林业入手。在1989年中国的大洪水之后,中央政府为了确保江河下游不再受遭受洪灾,开启了“天保林工程”,不允许砍伐江河上游的森林,这就导致成熟的森林不能变换成资本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导致了当地的贫困。可以说,该区域的贫困是来自制度的约束,来自于对江河下游的贡献。
根据我的研究,清水江流域之所以从清代(甚至明代后期)以来,将近300年的时间,经济能够持续发展,老百姓生活富足,完全得力于明清时期的政策支持。在国家的管控下使当地的木材贸易有序进行,极大地调动侗族、苗族民众从事人工营林的热情,并建构出了一套成熟有效的人工营林技术体系,使林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本,实现了该区域几百年的繁荣。这一历史经验很值得去总结,为当今实施精准扶贫提供具体实施思路,为该区域的脱贫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进而也使人类学实现“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使命。
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木材基本上到20年就成材了,之后,树木就停止生长,开始老化。一旦成林,就需要对木材进行砍伐更新,再造新的林木出来,如此循环,那么这个区域的林业发展才有希望。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区域尽管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人工林业区,但是一直没有什么产出,林业未能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只是起到了生态维护而已。通过我的实地田野调查发现,只要借鉴该区域的历史经验与传统的营林技术,政府给当地人以引导,通过市场的作用,按照从培育、幼林到成熟林,有机地进行规划。以100-150亩为一个区域划分出20-25块来,在依次砍伐的同时栽培树木,形成植树、管理、砍伐的良性循环。这个过程当中,25年至30年为一个轮回。这样,一片山林就可以常年处于青山绿水,有植被覆盖,既能保持水土,也能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使森林资源成为区域发展经济的资本。
罗:在通观西方人类学学术发展史的时候,西方人类学的起点大多研究的是单一族群或者社区的发展历程、文化的结构或者功能以及传播,甚至文化符号、象征体系等。但是在中国这样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中,绝对没有哪一个民族不受其他民族的影响,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问题。因此,我们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真正的本土化,要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这一历史基础与现实出发。既要看到西方民族学的发展轨迹,更要看中国的现实,所以说研究民族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之前出版的《族际关系论》(1998年),这本书讨论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它们的类型及方式是怎么形成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加入生态环境维度。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当中,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对生态资源的相互交错利用,形成特定的资源利用链与资源交易圈,由此从资源配置的维度来思考中华民族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些民族在面对共同的生态资源时,如何相互协调,互利共生。尤其是在湘黔桂边区生存的民族,苗瑶、百越汉等各民族生存在同一区域,生态背景基本一致,生计手段也基本类似,他们如何相互协调组织生产,使得在开发这一区域时,不同民族之间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在资源利用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既可代代传承,又高效利用环境资源,这二者的统一,展现出了该区域各民族建构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的大智慧。
据当地人介绍,江底铁索桥是东川铜业鼎盛时期的产物,古名永安桥,屡毁屡修。钢梁桥1944年开工建设,桥头引道要经过仅4米宽的江底街道,行车艰难。1978年,为改善当地交通条件,江底双曲拱桥正式开工建设。从铁索桥到钢梁桥再到双曲拱桥,3座不同时期建设的桥梁下游往上依次跨越牛栏江,常被摄入同一照片里,“江底三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艾:您所提出来的族际文化制衡理论非常有启发性,非常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生计方式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在这种状况下,在湘黔地区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族际文化制衡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2017年暑假我在湖南靖州三锹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三锹乡的每个家庭有森林面积在200亩至500亩不等,甚至更多。按照每亩可种120棵树,每棵树最低售价200元人民币。以平均300亩计,每户拥有林木资产在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不说是国内最富庶的地方,至少不是被“扶贫”的对象。但是,现在的林业政策不允许砍伐树木,也没有开放市场,所以老百姓只能守着金山银山,向国家要资源、要扶贫。因而,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借鉴当地历史上的经验,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对接国家的政策,以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这样既可以调动老百姓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实现林木资源的永续利用,而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又能解决贫困问题,将青山绿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实现该区域的繁荣发展。
今天,尽管这一区域的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只是瞬间。从长远的历史过程来说,这一瞬间并不可怕,族际制衡之下的生态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一定有它的价值意义,甚至可以成为指导民族交融交往交流的基础理论,使不同民族相互之间交融与包容,从而使这些民族依赖共生环境的过程中,真正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文化共同体,相互制衡,彼此约束,这就是文化制衡当中的精髓。当今,世界的格局出现了矛盾、冲突乃至战争,其实就是对族际制衡理论的无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有这种本土理论来解决世界问题,展现大国意识和大国风范。只要人类对自己过往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我坚信人类的未来依然是美好的。
目前,黔东南、湘西南和桂北这些区域各民族历史上所形成的生态文化耦合体,今天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世界市场、跨国公司和国家政策等外界的力量不断作用,使得该区域民族的发展走向处于不定状态,干扰因素叠加,使得这些民族文化的调适时间不充分,调适方向失序,调适内容不确定,因此,目前处于文化的阵痛期。但我相信,民族文化是可具有指导生存延续的法则的,民族文化不可能自掘坟墓,不可能毁灭自己的家园。目前出现文化对环境的偏离,导致出现一些生态问题,包括生态灾变或者蜕变,也包括社会规范失序,甚至贫困等等。但是,我仍然相信,当这种偏离危及到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延续时,文化的回归机制就会启动,就有能力通过文化的回归。通过总结“偏离”环境的经验教训,再度实行民族之间的协调,实现民族之间的共生与共荣。使已经被破坏的环境,又会在文化的影响下重归于好,开启下一轮的文化共同体。
策略:力臂的画法与步骤:(1)找点:在杠杆的示意图上确定支点O;(2)画线:画好动力和阻力的作用线;(3)作垂线段:从支点O向力的作用线画垂线,画出垂足;(4)找出力臂,标明动力臂和阻力臂。
大美新疆(柳京) .........................................................................................................................................11-56
艾:你特别强调文化适应理论,强调文化与环境的耦合,这其中所发生的地方性知识与技术、制度对民族生境格局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您也提出要恢复传统地方性知识,比如南方糯稻种植,发挥南方民族的农业生态蓄水能力,保证南方水资源的生态安全,请你详细谈谈这方面的研究。
罗:关于文化适应理论,文化耦合问题的研究,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十几年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也发表过这方面的论著。关于文化与环境的耦合问题,其实是基于我们的田野调查。为了研究文化适应,我们对国内不同的生态区域都进行了田野调查,如内蒙古的四子王旗、呼伦贝尔、乌审召,青海的玛多,甘肃的黄河地区,新疆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四川的盐源,重庆的秀山,湖北的恩施,贵州麻山地区、黔东南、黔南、铜仁,广西的岭南走廊以及湖南的湘西等。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西方人类学家的“文化适应”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认为文化适应是主动的文化建构过程。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地理空间体系,其地理环境、植被、动物、土壤、水文、气候等构成了特定民族的生存空间。特定的区域系统对稳定特定民族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民族文化在应对其特定环境时,又会建构起独特文化事实体系来。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民族所对应的生态环境都是经过其文化去修饰过的,构成了特定民族的家园。地球上几乎没有被文化所修饰过的自然生态环境。
生态学家提出的地球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或者脆弱环节的理念,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类本位主义思想的表现,因为地球生态系统早于人类存在,也就是说地球生态系统的存在,不只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是为地球上所有生命存在的。有人类与其他物种不一样,人类可以通过特有的文化超越生态系统的限制,使人类成为地球上分布面最广的物种。在地球上,除了南极,人这一物种几乎布满地球的各个角落,不论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无论水域、高山、平地、草原、沙漠,人类以其文化适应环境都能定居生存下去,但其他物种则只能在特定的地域内才能生存。但这也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错位问题,从而导致生态环境和人类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被错误地视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或者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被生态学家称为脆弱生态地带、脆弱环节、脆弱系统。如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地球上确实存在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比如沙漠、草原、湖泊、山地、海洋等,对人类来说,是要靠不同的文化去理解与加以利用的。生态系统对不适应的文化而言就是脆弱的,比如,高寒草甸对于农耕的农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对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高度的藏族有重大的意义。对文化的误用会导致文化对生态的不适应,而这种“误用”的叠加就会导致生态灾变。
世界上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尽管他们会有交叉分布,正如我国的民族分布一样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但总有特定的核心分布区,其文化所适应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民族分布格局的价值所在,只看到目前强大的西方民族及其文化,或者在国内只看到汉族的农耕文化。这些文化看似强大,但是他们也不是适用所有的生态系统。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就会发现今天地球上生态系统的局部退变、灾变,就是由这些强势文化对其不适应的生态系统进行开发导致的后果。
“这是当年你姑父留下来的,陈年好酒。”老太太的脸对着高河说道。一时间,整个饭厅里酒味飘香,果然是好酒。杨年喜根本不打算碰杯,仰起头就喝了一口。
每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的,都有其边界。文化的适应性讲的是特定民族文化对特定生态系统的适应问题,特定的民族都有自己能生存发展延续的生境,这一生境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耦合体,我们也称为“民族生境”。民族的几何分布区也好,核心分布区也罢,每个民族都与特定生态系统相对应,一旦超越这样的生态系统,就会出现文化的不适应性,其生存就需要额外的力量为他提供资源来维持其生存。比如,分布在云贵高原的穿青人、屯堡人、穿蓝人,云南的腾冲人等,这些人群是不同时期从中原汉地移民到云贵高原的古代汉族,由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所适应的环境与云贵高原大不一样,进入云贵高原后他们沿用其原有的文化去应对新迁入的环境,这不仅使他们与原生地的汉族在文化上拉开了差距,而且也没有融入到与之比邻的少数民族中去,因而在云贵高原上形成了一个个“语言孤岛”。如贵州所说的“高山汉,水种家”,由于汉族迁入的晚而只能聚居在高山之地,少数民族却居住在滨水之区,汉族的生活过得比当地少数民族还贫穷。这些汉族移民当年依靠的是国家政治力量、军事力量而移民进入的,如流官制度、羁縻制度、边郡制度等。依靠这些制度维持他们在云贵高原生活下去,但后来这些制度或者被废弃或者被削弱,依靠政府额外的补助日益减少或者终止,于是这些汉族移民有的融入到当地少数民族,有的在不断地调适自己的文化去适应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
二是夯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划定生态环保“责任田”。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明确地方党委政府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市委、市政府与各县(区)党政“一把手”签订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向市直有关部门下达年度环保目标责任书,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责任明晰、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
在这里,我举一个我多年研究的一个个例,那就是侗族的“稻鱼鸭共生生计体系”。2007年我们第一次去黄岗调查时,老百姓问我是要“吃猪饭?还是吃人饭?”时,我感到十分震惊,我回答说,当然是吃人饭。到吃饭时,主人给我的是杂交水稻煮的饭,而主人吃的是糯米饭。我问为什么你给我单独煮杂交水稻的米饭,而你们自己却吃糯米饭。主人解释道:“猪饭”是杂交水稻做成的饭,当地人是不吃的,是拿来喂猪的,所以叫“猪饭”;“人饭”就是糯米饭,当然人只吃本地品种种出来的糯米饭,所以叫“人饭”。为了深入理解当地人的“猪饭”与“人饭”,我开始了自己近10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侗族“稻鱼鸭共生生计体系”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其一,是直接的生计价值。水稻产量可能不高,每亩也就400来斤糯谷,但是田里的鱼和鸭子的收入可观。一亩稻田可以产80斤鱼,12至15只鸭子,一年分三批养鸭(40只左右),这些产出算在一起,其经济价值比起单一的稻谷要高很多。如果就糯米与杂交米按照当地的市场价值(3:1)来折算,其经济价值是接近的。但就总体价值而言,种糯稻是种杂交水稻的二至三倍。其独特生计价值还在于,种植糯稻时其生活之需都可以从稻田获得,除了主食糯饭外,佐食的菜肴诸如酸鱼、酸鸭、咸蛋以及水产的各种动植物等都可以同时获取,不需要另外去市场购买。但种植杂交水稻就不一样,佐食的菜肴需要另外购买。正是侗族种植糯稻能够形成“饭”与“菜”的时空同配,才叫做“人饭”。
将接收机通道按最大增益100 dB设计,经前级低噪声放大器40 dB放大以及功分插损-3 dB后, 射频通道需要最大63 dB最大增益。根据芯片手册的介绍,AD8347芯片最大增益为69.5 dB,因此接收通道留有6.5 dB增益裕量;该裕量可用于补偿滤波器插损以及通道失配造成的增益损失。
其二,为人类保留了珍贵的传统糯稻品种。侗族居住的区域,处于云贵高原的东南缘,属于多雨地带,虽然日照量大,但是雾气也很大,谷物的储存和生长具有特异性。鸟类多,对谷物的伤害也多,老百姓根据这样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点,培育出了很多适应当地环境的稻谷品种。我们在黎平县的黄岗村就收集了27个品种,这些品种中有的芒长20多厘米,鸟吃不下去,还能避雨,避免导致稻子的霉烂。老百姓还培育出适应水温很低的品种,甚至在17度的低水温,日照可能只有3个小时的条件下,都能够结实。这些水稻品种的驯化,是当地老百姓的一种智慧。而现在杂交水稻,对雨量、气温、日照、肥料、农药等相关因素的要求很高,因而很难在这些地区种植。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把推广杂交水稻作为一种政治任务在侗族地区推广时,侗族这一套传统的农耕体系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又有所回归,种植传统糯稻的比例又超过了杂交水稻。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其三,是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侗族地区的“稻鱼鸭共生生计体系”的核心在于传统糯稻种植对水资源的维护与利用。侗族地区稻田种植传统糯稻都是高秆水稻,稻秆可以在水面1米以上,因为要养鱼,水田的储水量也很大,一年四季都是汪汪的水田,不像矮秆水稻需要排水分蘖才能增加产量。高秆水稻的稻田就是一个微型水库,连片的稻田就是一个小型水库,侗族地区无以数计的连片稻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坝。中国的珠江中上游,至今尚有4200多万各民族山区农村人口,此外,在湘黔桂边地沅江、澧水、湘江中上游也居住中1500万各族人口,以我国山区农民人均耕地2-3亩换算,目前实际的稻田耕作面积约9000万亩。这9000万亩稻田若种植传统高秆糯稻,其暴雨季节的储洪能力将高达300亿立方米。其有效储洪能力,接近于另修一个长江三峡水库(三峡水库总库容量393亿m³,但实际不足2/3)。即使在枯水季节,这些稻田还留有5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储备,可以持续补给珠江、长江下游的淡水。
1.PERT指征:临床确诊或疑诊PEI,即可行PERT[1]。可根据患者基础疾病、PEI临床症状、胰腺外分泌功能检测、营养不良的客观证据等进行综合评估。
其四,维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侗族地区的农田、鱼塘、水井、水沟、山塘、溪流等构成一个水域的网络,这是镶嵌在侗族地区的一个个“生态坝”,它是靠泥土、杂草、树枝、岩石等材料累积而成。构成水生动植物的栖息地,也是陆生动物的觅食之处。因此,这样的生态坝既维护了生态多样性的存在,又使得水源得到控制,在天气干旱的时候,可以为江河中下游补充水源,在洪水时节又可以为中下游地区截流洪水。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是侗族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而建构起来的“稻鱼鸭共生生计体系”。
艾:在当下普遍认为要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引进先进技术,这时谈论地方性知识是否有“落后”的嫌疑?您是如何看待地方性知识的?
我觉得斯图尔德的理论也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去反思的内容。刚才所讲的适应性发展构成了斯图尔德的生态文化共同体,从核心家族到民俗社会和国家体系两套路径对今天的生态民族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国内学术界在讨论生态民族学的时候,都以为只是文化与生态的关系问题,忘记了社会环境、国家在场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我们认为在将来的生态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能在理解文化生态共同体核心概念和路径的同时,更多的还要理解国家在场引发的对民俗社会的影响、变迁的维度。当然我们觉得斯图尔德的理论也有一些不足,从文化的概念入手,不论文化生态环境耦合体的存在,还是国家在场都是文化发挥作用。我们把文化的概念理清之后,把文化与文化事实两者间的关系理清,才能理清对文化生态共同体和国家在场下的民族社会的变化。
罗:湘黔地区是我进行田野调查的主要地区,但并不局限于此。该区域有很多世居民族,诸如有侗族、苗族、瑶族、土家族、水族、白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数百年上千年应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建构出来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是值得去关注的内容,这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既有生态知识,技术技艺,也有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宗教观(宗教意识)。就民间信仰而言,有侗族的萨崇拜系统,苗族的巴代系统,土家族的梯玛系统、瑶族的过山榜系统,白族的本主崇拜系统等等,都在这个地方共生,宗教文化的丰富多样成为当地老百姓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文化体系。
罗:对这一问题我们团队也进行过认真的思考与研究。我认为这是一种话语霸权的结果,这是我国近代以来“教科书西化”的结果,知识体系西化的结果。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西方的标准,以西方技术为追求对象,忽略了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智慧,也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民间智慧。如果我们转变一个视角,将这些传统知识进行挖掘、整理,加以精细化的研究整理和提升,可以成为大家能够理解的知识体系,比如云南云大学的朱有勇教授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当选为院士。西方知识体系其实也是从英国开始的,通过殖民活动,建立起世界的工业化体系,这样一来,把一个弱小岛国变成了一个“日不落帝国”,由此使得一个小国的知识体系逐渐的扩大,变成一个世界的知识体系而已。
我认为地方性知识的落后性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学术界仍然抱有那种地方性知识是否有“落后”的嫌疑,主要是很少有真正的学者参与到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中去,没有对地方性知识价值体系进行解剖,而是坐在实验室求数据,更没有对地方性知识的运用性进行升级换代的改造。如此的研究范式,才导致了那种认为地方性知识是落后的、愚昧的,甚至是要被革除的对象。西方国家今天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困惑,甚至是人类的灾难。人类在西方的引导下走入工业化的道路,但今天看来,这条由西方开创的工业文明道路是否可以继续走下去,已经遭到了怀疑,甚至否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我认为生态文明的核心,就是“人-地关系”的和谐,也即是人类利用自身所建构起来的文化,去实现对地球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要实现对地球资源的精心维护,在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中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物种,只有人-地关系和谐了,人类才可以永续发展。在人—地关系的和谐性下,既可以有大的产业,也可以有小的产业,既可以有集中性的生产,也可以有分散性的生产,既可以有资源的集中利用,也可以有资源的分散利用。总之,现代化不再是只有西方工业化道路这一种模式。
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地方性知识去建构人类发展的道路,这仍然需要将整个世界市场作为一个大的背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内,去发掘地方性知识的机制,发现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寻找地方性知识升级换代的路径,重新建立起人类共享的科学思维与技术体系。我认为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乃是人类继生态文明之后的第六大人类文明形态,是中华民族引领人类发展的全新范式。这些都是我们团队当前与日后所关注的主题。
艾:如今民族地区的人口外出务工非常多,因而生计方式的变迁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如何进行?
罗:我也确实看到这一现实问题。民族地区人员大量外出务工,现在留本地的,多是一些老弱病残盲这些弱势群体,有些学者认为乡村出现的“空心化”。但我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是对乡村社会不进行深入调查而得处的错误结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人口在减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并没有像那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了乡村的“空心化”,如果说有“空心”,那也最多只是“季节性空心”。外出务工的百姓在特定的时节都会回到乡村,在劳力不再适应“城市化”时,他们会自觉地回到乡村,因为乡村才是他们的家园。“城市化势不可挡”,由此引发的生计方式变迁也势不可挡,这已经成为了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我通过近30余年的田野调查,依然相信在“城市化”背景之下,乡村未来的发展依然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所幸在2017年国务院提出了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六部委提出了生态扶贫的工作方案,等等。这些都是国家高层看到了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民族学学者如何把这些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来,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利用这些社会环境、社会资源,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去为乡村建设与发展进行思考,也就成为我们当下的重要研究取向。
我认为,人口流动是常态,生计方式变迁也是常态,社会环境改变了,这些都会改变。生态环境也会改变,但其改变的速度十分缓慢,只要生态基础还存在,那么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文化还能存在下去。我们目前面临的困惑乃是十分的浮躁,很难静心下来,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与生计方式变迁的关系展开系统的研究。有些学者只看到了变迁的一面,没有看到民族地区发展根基何在,核心何在。前面所谈的贵州清水江流域的林业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木材流动带来了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生计方式的变迁,在变迁中实现的文化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耦合,由此造就了当地数百年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与文化发展。
目前,国家正在提倡以生态产业振兴乡村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研究领域。比如生态产业如何在振兴乡村中落地生根,产业如何与文化和环境达成耦合性,等等。我们乡村振兴的举措必须从文化与生态环境偶合体这一维度出发,找到问题的症结,发现工业文明的不足与缺陷,看到城市化的问题所在。以人类文化生态共同体的再度形成,去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文化再度在当今的历史背景中调适于正在改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技术环境,这是我们所讨论的文化适应问题。文化变迁就是它已经超越了文化适应环境的原点,走向了另一个文化面对的环境而去加以适应而已。
诚如前面所说,文化面对变化了环境如何做出调试和修正问题,这需要对具体的事项进行研究,也即是民族学强调的“个案研究”。比如前面提到的林业问题,清水江流域的林农面对的自然环境虽然与历史上差异不大,但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明清、民国时期不同。因此,当代清水江流域林业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针对国家的政策和地方性知识的对接,包括现代林业技术与传统民间营林技术的对接。不论如何对接都要从林业发展中的文化与环境的耦合性出发,才能解决当前林业面临的真正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生活在林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会更幸福,就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就不会成为扶贫对象,甚至可能成为支持其他地区发展的对象。因此,要讨论地方性知识的应用问题,需要从特定的一些项目出发,考察特定民族文化与所处环境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协调利用入手,而不会泛泛而谈。
艾:最后一个问题是,请您谈谈如何将国外的相关理论与中国生态民族学的研究具体结合,以及中国生态民族学今后发展的理论性指导。
低情绪稳定性消费者容易冲动购买,价格的敏感程度较高,容易受到促销等营销策略的影响。她们使用化妆品的频率较高、品牌忠诚度较低。因此,企业应该采用顾客导向定价法,并结合促销手段。
罗: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生态民族学研究任重道远,需要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十分迫切。如果要谈国外的相关理论如何与中国生态民族学的研究具体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的话题。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结合问题”,都需要从“个案”入手展开讨论。但若就民族学学科内涵而言,尤其是生态民族学学科而言,我认为要把握好四个领域的关系问题:从生态文化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从地方性生态知识到普同性知识的关系问题;从民俗社会到国家社会到全球社会的问题;从小传统到大传统到人类“类本质”的关系问题。这四组领域涉及到很多新的学术概念需要重新建立,有很多的个案需要积累;其间的学术逻辑关系与解释框架需要重新确立。如果能够完成这样的学术使命,中国的民族学、生态民族学就将作出全人类的贡献,也只有到那个时候,生态民族学的中国话语才能确立起来。这也正是我所期待的。
艾:谢谢罗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所谈到的针对我国民族地区生态与文化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促使我们思考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全球化如何在地方适应地方,而地方性知识在应对全球所共同面临的危机时,能够找到其切入点,从而使地方知识获得全球的普遍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4-0101-07
此次访谈承蒙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春花、田锦筠、杨文娟三位同学整理录音,在此致谢。
作者简介:艾菊红(1971-),女,河南渑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学;罗康隆(1965-),男,贵州天柱人,苗族,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学。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夏 雪
标签:生态论文; 文化论文; 民族学论文; 侗族论文; 民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三峡论坛》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论文;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