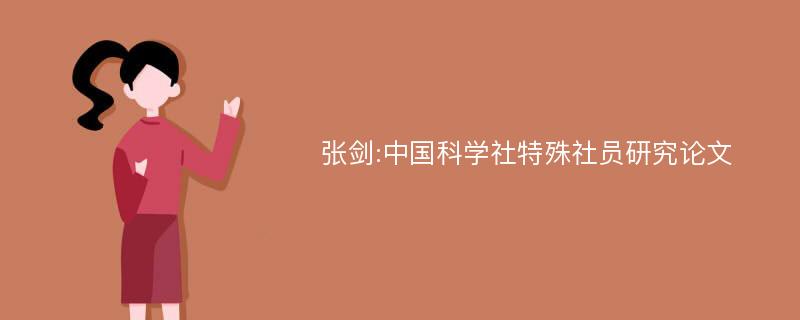
摘 要 除普通社员外,中国科学社还有永久社员、特社员、赞助社员与名誉社员等特殊社员类别。不同类别的特殊社员称号有不同的标准,也担当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对社务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在特社员与个别名誉社员选举时,中国科学社并不完全遵照章程以学术贡献为标准的规定,致使不少本来仅居于赞助角色者当选;在赞助社员的选择上多关注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致使不少完全政治人物当选,这些举措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中国科学社的影响力,但也给中国科学社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科学社的举措在民国学术社团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治在中国社会强大无比的覆盖力,学术独立之路任重道远。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 特殊社员 社会角色 社会影响
1948年6月,有社员探讨中国科学社缺乏凝聚力与活力的原因,制度建设方面,日常工作“机关化”;社员个体方面,社员们“英雄崇拜或名人崇拜的气息太浓”:
看一看赞助社友的名单吧,上自总统,下至汉奸,只要是当时名人红客,科学社就不惜移樽就教,请求他做个赞助社友,而不问这些大亨之流对社的本质,对科学的价值总究知道了多少?名人崇拜的思想在智识分子身上根深蒂固的存在着,科学社的社友也正如此,想做科学社的英雄,做不到英雄也就退避三舍。[1]
对一般社员做不到“科学社的英雄”就退避三舍的批评可能有失偏颇,但对中国科学社赞助社员组成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以学术交流促进学术进步的学术社团,其组成主体、对社务及学术发展影响较大的自然是普通会员,会员的人数与质量也成为衡量学术社团是否兴盛的标志之一。同时,为寻求社务扩展、扩大社团的社会影响及奖励学术成就特出的社员,学术社团往往也会有其他类别会员的设置与征求。1914年创设于美国、1960年在上海黯然退场的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其社员除普通社员外,还有一些特殊社员,包括永久社员、特社员、赞助社员与名誉社员,其中赞助社员与名誉社员不是普通社员,不能参与社务的管理,没有选举与被选举权。不同类别的特殊社员群体在中国科学社中担当着不同社会角色,对社务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也就有不同的地位。
1永久社员
永久社员是为了汇聚维持中国科学社发展经费而设立的。1915年10月通过的章程第9条规定,凡社员一次缴费100元(美金50元,其他国家以汇率照算)为终身社员,不另缴常年费。在美期间虽然有不少社员以特别捐名义向社里捐赠不少款项,如1916年9月前任鸿隽、胡明复、秉志、廖慰慈等捐赠100美元,赵元任、杨铨等也捐赠90美元以上,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要求成为永久社员,而是无偿捐赠。1918年中国科学社搬迁回国后,因经费短缺,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发起5万元基金募捐活动,社长任鸿隽从1918年底开始先后在广州、上海、南通、南京、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历访各界名人,进行募捐,效果却不佳。1919年4月的一次上海社友会上,任鸿隽希望社员们积极行动担任募捐,每人代捐或自捐75元,就可以获得5万元的一半(此时社员已超过400人)。胡明复认为“他救不如自救”,不如提倡社员缴纳100元成为永久社员,这样既增加了基金,可以生利息,又免除了每年缴纳常年费的麻烦[2]。后来董事会开会议决通融办法,凡是社员在一年内按月缴足100元,就得为永久社员。当场就缴足100元成为永久社员的有胡敦复、任鸿隽、胡明复、竺可桢4人,另有李垕身、刘柏棠、杨铨、廖慰慈、胡刚复、李协、过探先、邹秉文、胡先骕、王璇、程时煃、许寿裳、郑寿仁等表示愿意成为永久社员[3]。
可见,中国科学社虽然最初的章程中有永久社员的规定,但在美期间并没有实行。直到从美国搬迁回国后,面临经费严重短缺的窘状,章程的规定才真正开始实施。为了募集资金,在永久社员的资格上曾一再“让步”,最初是一次缴费100元,后来变为一年内缴纳100元。即使如此,到1921年永久社员除上述4人外,仅增加温嗣康、孙洪芬、许肇南、徐乃仁、孙昌克、朱文鑫、刘柏棠、陈宝年、过探先、黄昌榖、黎照寰、关汉光等12人。当初“表示愿意”的李垕身、杨铨、廖慰慈、胡刚复、李协、邹秉文、胡先骕、王璇、程时煃、许寿裳、郑寿仁等人还没有“兑现”。1922年通过的新章程又有规定:“一次或三年内分期缴费至100元者,得为永久社员,不另纳费”。出台了更加“优惠”的政策,缴费之期又从一年扩展到三年,以期调动社员们的积极性,解决经费困难问题。
到1924年,永久社友仅增加金邦正、赵志道、程时煃、陈衡哲、李垕身、侯德榜、朱籙、胡适、周仁、钟心煊、曹惠群、谢家荣、秉志等13人,最初“表示意愿”者绝大多数还是未能践诺。即使允诺成为永久社员者,其费用的缴纳也不理想,大名鼎鼎如胡适,两次仅缴40元,还有60元的欠帐[4]。到1928年共有永久社员58人,除上述29人外,还有谭熙鸿、张轶欧、李协、程耀椿、姜立夫、王琎、胡先骕、熊庆来、张乃燕、胡刚复、杨孝述、杨铨、杨端六、程瀛章、刘梦锡、王徵、何鲁、丁文江、翁文灏、税绍圣、刘惠民、朱经农、徐允中、李孤帆、卢伯、严庄、廖慰慈、邹秉文、万兆芝等29人(1)《中国科学社社员录》(1928年刊行),第5页。。到1930年增加到70人,又有张昭汉、叶云龙、王伯秋、段子燮、庄俊、高君珊、李俨、程志颐、黄伯樵、胡庶华、孙国封、杨振声等12人。到1934年8月,增加到104人,新增顾燮光、田世英、徐宗涑、杨光弼、吴承洛、刘树梅、陈端、王庚、吴宪、盛绍章、姬振铎、郝更生、刘仙洲、周厚枢、蔡堡、涂治、汤震龙、孙继丁、叶善定、卢于道、雷沛鸿、季宗孟、甘绩镛、朱德和、张孝庭、张登三、唐建章、鲁波、程孝刚、陈宗蓥、张延祥、曾瑊益、张树勋、叶企孙等34人(2)《中国科学社社员分股名录》(1934年8月刊行),第134页。值得注意的是,该“名录”所收永久社员中没有“万兆芝”,因此总人数仅有103人。。
吴伟士(C. W. Woodworth,1865—1940),加州大学教授兼农科昆虫主任,对蚊虫、柑橘害虫有深入研究。1918年来华任教金陵大学,1922年任江苏昆虫局局长兼东南大学讲座教授,1924年任满回国。吴伟士来华前在昆虫学上取得大成就,著有《加利福尼亚昆虫》《昆虫的翅脉》等,他1923年当选特社员,可以说名副其实。1969年,美国昆虫学会太平洋分会设立吴伟士奖章以纪念他(9)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W._Woodworth(2018年12月5日)。。
下颌阻生第三磨牙形状多种多样,牙根变异较大,手术视野小,创伤大,操作不方便,拔除手术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风险[1]。临床工作中,针对不同患者,需采用不同的手术方法进行拔除。本研究旨在比较锤凿劈冠法与高速涡轮钻法拔除下颌阻生第三磨牙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科学社经费面临困境,有不少新社员入社时就交足费用,成为永久社员。总社在沪期间,先后有1940年3月入社的孙莲汀,1941年5月入社的郑兰华、寿俊良,同年11月入社的张孟闻,1942年3月入社的杨姮彩、杨臣勋。总社内迁重庆后,永久社员人数大增,1942年12月第一次内迁理事会通过社员中就有刘建康、朱健人、凌敏猷、张孝骞、杨平澜、谭娟杰、濮璚、黄汲清、洪式闾、白季眉、单人骅、燕晓芬、杨明声、戚秉彝、张敬熙、娄执中、刘导丰、简实、邱鸿章、郑子政、张宝堃、卢鋈、胡安定、薛芬、王述纲、黄瑞采、李春昱、曲仲湘、孙雄才、杨衔晋、苗雨膏、倪达书、毛守白、胡福南、谢祚永、姚钟秀、郝景盛、周赞衡、曾世英等人。1943年4月通过社员中也有张昌绍、廖素琴、金大勋、周廷冲、王成发、王进英、林振国等[5]。非常奇怪的是,此后新入社社员不再注明有永久社员,难道与此时脱缰的通货膨胀相较,永久社费实在是微不足道有关?
目前,一些小的钢贸企业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成本控制制度,导致成本控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有一部分钢贸企业建立了成本控制制度,但是没有形成配套的机制,比如监督制度、绩效考核机制等,也就是没有将成本控制和企业员工的利益挂钩,员工不会主动参与到成本控制中去,使得钢贸企业的成本控制制度流于表面,实际发挥作用不是很大。
这个小群体中有不少人是中国近代各门科学的奠基人,如数学方面的胡敦复、姜立夫、熊庆来、何鲁、段子燮、胡明复等,物理学方面的胡刚复、孙国封、叶企孙等,化学方面的王琎、程瀛章、杨光弼、吴承洛、吴宪等,生物学方面的秉志、钟心煊、胡先骕、蔡堡、卢于道,地质学方面的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等,气象学和地理学的竺可桢,农林方面过探先、邹秉文、涂治等,工程科学方面的李厚身、侯德榜、周仁、李协、杨孝述、庄俊、胡庶华、刘仙洲、程孝刚等,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胡适、杨端六、杨振声,教育界的王伯秋、朱经农、张乃燕等。其中竺可桢、侯德榜、胡适、周仁、谢家荣、秉志、姜立夫、胡先骕、翁文灏、吴宪、叶企孙等11人当选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永久社员中也有政界名流,虽然人数不多,如朱籙、谭熙鸿、张轶欧、王徵、黄伯樵、王庚等。当然,有一些人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未能留下可以记载的“丰功伟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学术界社员更应该成为永久社员,毕竟中国科学社是他们自己的“组织”。
到1921年缴费成为永久社员的12人中,孙洪芬、孙昌克、过探先是董事会董事,许肇南是南京社友会会长,黄昌榖、黎照寰也是积极的社务参与者,黄昌榖提交论文连续参加年会。到1924年新增13人中,金邦正、周仁、秉志是创始人,也是理事会理事,李垕身是理事会理事,曹惠群长期担任上海社友会会长,谢家荣不仅常常在《科学》发表文章,而且其著作《普通地质学》是中国科学社购买出版的第一本“科学丛书”书籍,其他赵志道、陈衡哲、侯德榜、胡适、钟心煊等也是社务的积极参与者。后来成为永久社员的李协、王琎、胡先骕、胡刚复、杨孝述、杨铨、丁文江、翁文灏、王伯秋、高君珊、胡庶华、孙国封、杨振声、叶企孙等,或是社长(丁文江、翁文灏、王琎)或是理事会理事或是各地社友会会长。
切片与切段对叠鞘石斛多糖、联苄类化合物及石斛酚提取量的影响研究 …………………………………… 谢 巧等(17):2376
从普通社员转变为永久社员,是热心社务、关心中国科学社发展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永久社员群体可以看作中国科学社社员群体中的核心小群体(虽然他们并没有以永久社员为名结成小团体,造成所谓的“党内有党”的情状)。具体分析1934年8月前永久社员群体,可以发现他们大多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与重要社务推进者,不少人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特出贡献。当回国后募集基金出现困难,中国科学社正式实施“永久社员”这一名号时,胡敦复、任鸿隽、胡明复、竺可桢4人成为第一批永久社员。胡敦复当时在国内教育界已颇有声名,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务所设在他创办的大同学院内,在弟弟胡明复的影响下,对中国科学社社务自然热心,1922年当选为改组后的董事会董事。任鸿隽、胡明复不仅是创始人,也是当时中国科学社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任鸿隽是社长,胡明复是会计。竺可桢虽不是创始人,1916年首届年会上就当选为执掌社务发展的董事会董事,并由此成为最为重要的领导人,曾任书记、社长等。
中国是一个讲究社会关系的国度,除同乡、同学等网络外,夫妻、兄弟、姻亲关系更为重要。考查永久社员的社会关系,可以发现中国科学社的壮大与扩展就颇得益于社员的家庭与亲朋好友这种社会网络。社员中间存在好几个层面的社会关系:社友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亲戚关系等。有些社员是上述多种关系网络的纽接点,通过这个接点,中国科学社可以扩展其关系网络与社会影响,并获得社会资源。例如杨铨与任鸿隽是同学、同事关系,又是朋友关系;杨铨与赵志道是夫妻关系,与赵凤昌是岳婿关系。通过杨铨这一接点,杨铨与他夫人赵志道是永久社员,赵志道的父亲赵凤昌是赞助社员。同样,任鸿隽和夫人陈衡哲同是永久社员;姜立夫娶胡敦复妹妹胡芷华为妻,与胡氏三兄弟同为永久社员。通过胡明复这一层关系,中国科学社回国后将上海社所临时建立在胡敦复创办的大同学院里面。何鲁、段子燮与任鸿隽是同乡关系,他们留法期间已与中国科学社建立联系,成为社友,回国后同在东南大学任教,又成为同事关系;何鲁与段子燮还合作编纂数学教科书《行列式详论》等。
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学术社团,社友之间主要是社友关系和学术关系,其他社会关系本不应占据相当地位,但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简单。当然,如果坚持原则,社员的吸收与社务的扩展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主持者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1923年10月,丁文江当选社长,曾动议除名不缴费社员,胡明复致函杨铨说:“关于社员除名问题,自不便一概以付款为标准。弟意暂取折中办法,其于社事久不热心者不妨去之,其余暂留,若遇事严格人数骤减,反以示弱又寒社员之心也”[6]。这自然也是作为一个模仿西方学术社团而建立起来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是其不断调适以适应中国社会的结果。虽然传统社会关系在扩展社务方面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但也对社团自身的发展及其社会属性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在其领导层理事会和董事会组成上表现得更为突出(3)参阅拙文《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科学社领导层分析》(《史林》2002年第1期)、《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成员社会角色与社会网络研究》,《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23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2特社员
相较永久社员仅需交纳足额费用,就可以自动由普通社员转变而成,表征着社员对社务的热心程度,特社员却需要经理事会推举,年会社员大会的选举,当选标志是学术成就。按照中国科学社章程,凡社员“有科学上特别成绩,经董事会或社员二十人之连署之提出,得常年会到会社员之过半数之选决者,为本社特社员”。1917年第二次年会,选举蔡元培为第一个特社员。此后,1919年杭州年会周达,1920年南京年会胡敦复,1921年北京年会汪精卫,1922年南通年会马相伯,1923年杭州年会吴伟士、马君武、张轶欧,1924年南京年会葛利普,1926年广州年会吴稚晖、孙科、葛雷布等先后被选举为特社员(4)此葛雷布不知是何人。如果是葛利普,但他于两年前已经当选,葛利普当时译名还有葛拉普,没有葛雷布这样的译名。在广州当选,似乎应该是当时在广州的国外人士。他当选为特社员,首先应该是社员,但社员名录中没有此人。具体如何,有待进一步查证与方家指教。。相隔许久之后,1934年庐山年会选举范旭东(5)年会前理事会曾决议选举范旭东为赞助社员,后改为特社员,因为他是中国科学社社员,而且在中国化学工业上有大贡献。《理事会第118次会议记录》(1934年7月21日),《社友》第42期,第1页。。此后,没有再增选。
按照章程规定,蔡元培的当选有一些勉强,因为他在科学上并没有“特别成绩”,他也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也乏善可陈。若从蔡对科学的提倡与对中国科学社的赞助来说,当选为赞助社员倒是“名正言顺”(6)蔡元培对中国科学社的具体赞助与贡献,参阅拙文《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史林》2000年第2期。。可赞助社员是给予那些对中国科学社有一定赞助的社外人士的,而蔡是社员,他的当选主要是基于他在学界的名望。当然,如果从其对北大的整顿及创建中央研究院进而对整个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影响而言,蔡元培又确实对科学有特别贡献,当选特社员也无可厚非。周达(1878-1949)作为中国近代数学发展史上的过渡人物,数学研究兼具传统数学与近代数学,对中国数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如果说有什么特别成绩的话,主要是收集数学书籍,并捐献给中国科学社在明复图书馆设立美权图书室,后来在创建中国数学会上也有大作用,曾当选中国数学会首届董事会董事。无论是蔡元培还是周达,他们对学术界的如许贡献,都是在当选特社员之后。胡敦复作为教育界的名流,康乃尔大学的早期毕业生,清华学堂教务长,大同学院创始人,虽曾任中国数学会首任会长,但在数学研究上并没有特出成绩。与蔡元培、周达一样,他对中国科学社的发展也有大赞助,特别是供给大同学院里的上海事务所,后来曾当选董事会董事兼基金监。与蔡元培一样,神学博士马相伯也是以教育家角色名于世,虽著有《致知浅说》等,但在科学上实在难说有成就。如果说蔡元培、马相伯当选特社员有些勉为其难,周达、胡敦复两人虽在中国近代数学发展史上有其独特位置,但从学术上有特别成绩这一标准来看,也同样有些名不副实。
1921年选举的汪精卫和此后选举的吴稚晖、孙科,都是政坛名流,国民党的大佬,在科学上根本说不上有什么成就。也就是说,他们当选为特社员,完全与中国科学社章程规定相违背。按照他们对中国科学社的贡献,当选为赞助社员倒是恰如其分。这三人后来都曾当选新董事会董事。可见,中国科学社无论是选举他们为特社员还是董事,都是借重于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而非学术成就。此外,马君武虽获得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广州石井兵工厂无烟火药厂总工程师,也翻译达尔文《物种起源》,后来还创建广西大学,在教育文化上有其独特贡献,但他作为国民党元老,主要社会角色还是政治人物,在学术上也没有特出的成就。1923年当选的张轶欧(1881—1938),时任江苏实业厅厅长。他留学比利时获得冶金学硕士学位,曾任北京政府工商部矿务司长、农商部矿政司长,任内与丁文江、翁文灏等创办地质调查所,又纠集人才创设矿冶研究所等。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商业司长、实业部技监等。张轶欧在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上有相当贡献,但在学术上难说有成就。1934年推选范旭东也还是有些勉强,当时对他介绍如是说:“改良华北食盐,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又创办东方最大之永利制碱公司,最近又在组织硫酸铔厂,于发展国内化学工业,厥功甚伟,且对于本社种种事业,素所赞助。”(7)《中国科学社第十九次年会纪事录》,第16页。范旭东对中国近代化学工业有大贡献,但在学术上成就也难说特出。无论如何,蔡元培、周达、马相伯、胡敦复、张轶欧、范旭东相比汪精卫、孙科、吴稚晖等,当选特社员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与他们一样,都不是学术上有“特殊贡献者”。
全场一致通过后,葛利普发言说他应邀来华:
问题是,早期选举如是之多名不副实的特社员,似乎影响到后期中国科学社在相关方面的作为。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出现有特出成就的中国籍社员时,中国科学社却因噎废食,不再选举特社员,致使设立“中国科学社奖章”时提不出候选人。1936年5月28日理事会,时任社长翁文灏提出应该照章选举特社员。在翁文灏看来,特社员可以作为“中国科学社奖章”获得者候选人。理事会议决各理事提出候选人,再全体通信投票通过,提交年会选决。与章程规定不同,理事会这个决议,特社员当选需经三关,首先是理事提出候选人,全体理事投票通过后,再在年会上选决[8]。8月16日理事会上,虽各理事提出了名单,但意见并不统一,伍连德以为“特社员”名称需“另行考虑”,而且应先规定若干合格条件下后再选候选人,“到会者各有意见发表,讨论历半小时。咸谓此事比较重要应从长计议,暂缓提出”[9]。特社员选举于是归于沉寂。
研究组术后出现脑积水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3.33%(1/30);参照组术后出现脑积水3例,颅内感染2例,切口疝2例,癫痫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26.67%(8/30)。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
比较而言,中国科学社选举美国人葛利普和吴伟士为特社员可谓恰如其分,以葛利普最为特出。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特别是古生物学有极大的影响,被尊称为“科学大师”。选举时,翁文灏曾如是介绍:
葛氏掌教美国哥伦比亚及其余各大学,已历十八年之久,著作极富。于前年来华,对于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已多贡献。葛氏近患腿病,行路不便,此次闻中国唯一之科学机关在南京开会,决南下与会。中外友人,咸劝其勿过跋涉,有伤身体,葛君未允,其仰慕中国科学社可谓至矣。
可见,中国科学社无论选举学界与教育界蔡元培、周达、马相伯、胡敦复,还是政坛汪精卫、孙科、吴稚晖、马君武、张轶欧为特社员,都是为了发展社务而借助这些社会名流,而没有完全遵循章程“科学上有特别成绩”的规定。这种视规则为儿戏的行为,在社务得到发展空间的同时,也给社务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可能引起那些真正向学的学者对中国科学社的疏离与不满。中国科学社早期重要领导人、中国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唐钺,1924年致函理事会,要求辞去司选委员职务,其中理由之一是“近来司选委员会已失独立资格”[7]。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科学社选举事务的具体操作与责任者司选委员没有“独立资格”去具体实施包括特社员、理事、董事等的选举,章程所规定的民主程序名存实亡。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状况,在当时不可能选举出真正名副其实的中国籍特社员,后来中国科学社扩大特社员队伍非常谨慎,也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1920年8月在南京社所召开的第五次年会上,选举美国生物学家、韦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格林曼(Milton Jay Greenman,1866—1937)为名誉社员(11)秉志译为“葛霖满”。。格林曼作为世界闻名的生物学研究机构掌舵人,不仅自己有特出的科研成就,而且对研究机构的发展影响甚大,创办有《形态学杂志》《比较神经科学杂志》《美国解剖学杂志》《实验动物学杂志》等专业期刊,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生物学的发展。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格林曼是科学不分国界的“大公无我之精神”的体现者,研究所也弥漫着“唯知学术,不问其他”的“意味”:“凡学人入其中工作者,亦自忘其何国何籍焉”。格林曼一生的努力,“一以促进科学之发展,增加人类之幸福,一以弥漫科学之精神,扫除伪科学家之忌刻,及其种族国籍之隘见”。1937年4月17日,格林曼去世后,曾师从于他的秉志撰文悼念说,中国科学社成立后,他“热心属望其事业之展进,每遇吾国人士,辄表示其爱护希冀之热忱,嗣后凡遇吾国各种事业关于科学者,及科学家之各种企图,恒引以为可喜之事,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成立,至今十余年中,韦斯特所每尽力相助,盖以先生之热心故”。秉志最后总结说:
五是科学技术因素。有利面是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加强,特别是开源节流和保护的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了水资源节约和污染防治。不利面是节水、污水回用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技术创新尚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葛利普在美国时,中国留学生王宠佑、叶良辅、袁复礼等就是他的弟子。1920年应丁文江邀请来华,二十多年如一日,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古生物学者,赵亚曾、杨钟健、裴文中、黄汲清、斯行健、计荣森、孙云铸、王鸿桢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8)除赵亚曾早逝外,杨钟健、黄汲清当选为中研院首届院士,其他人大多于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他自己在学术上也成就卓著,被誉为20世纪重要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家之一[11]。抗战期间受尽日本人的折磨,1946年在北平逝世。他去世后,中国学界给予他极为隆重的纪念,《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和《科学》都曾出版纪念专刊。《科学》纪念刊(第30卷第3期)发表了杨钟健《科学家是怎样长成的?-纪念葛利普先生逝世二周年》、孙云铸《葛利普教授》、寿振黄《古生物学大师葛利普教授年表》等。
按照当初的设想,5万元的基金,若有250人原意成为永久社员,就有2.5万元的基金。到1934年,中国科学社社员人数超过1700人,只要1/7的社员成为永久社员就可以达到这一预期目标。可事态的发展跟5万元的募捐一样,到1934年,永久社员亦刚过百人,考虑到通货膨胀,永久社员刚超过万元的社费收入,相对当日社务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这也许是这一动意的发起人没有料到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不仅当日社会对中国科学社的发展不支持,大部分社员自身对社务也并不是很热心。到1948年6月,中国科学社号称有社员3200余人,“实际有正确通讯处的仅占半数,半数是地址不明,甚至是生死不明。能够通讯联络的社友中,又大都对社漠不关心,有的甚至入社至今连社费也分文没有缴过,或则自己是否社友也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1]
特社员是社会名流与学术界人物的混合体,他们对中国科学社的发展贡献很明显。蔡元培对《科学》的资助、孙科捐助修筑明复图书馆、周达捐献数学书籍、胡敦复在大同大学提供社所等等,都在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史上留下深深印迹。即使如马相伯、吴稚晖等元老,对中国科学社的赞助也是不遗余力,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宣扬科学与呼吁科学研究;汪精卫、孙科、马君武等人与任鸿隽、杨铨等领导人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中国科学社通过他们不仅可以扩大影响,而且还可以获取一些资源。当然,通过中国科学社这个平台,特社员们不仅得到了学界的承认,更扩大了他们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影响。蔡元培利用中国科学社的人才聚集,组建起中央研究院最初的研究团队与研究格局;周达捐建的明复图书馆美权算学室成为中国数学会的会址;胡敦复办理大同大学,也极为看重中国科学社的人力资源;葛利普、吴伟士的学术影响力由此溢出其专业领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学术圈层;即使是汪精卫、孙科、吴稚晖这些政坛名流,也有了赞助学术的好名声,有意无意间会对学术发展产生影响。
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15年6月96例晚期HCC患者,纳入标准:①均符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5-6]的诊断标准,有影像学上可测量的肿瘤病灶,经穿刺病理学明确诊断;②TNM分期Ⅲ~Ⅳ期;③Child-Pugh 分级 A ~B级;④精神正常,体能状况评分(KPS)>60分;⑤预计生存期>3个月;⑥病历资料完整,签署知情同意书。分为对照组45例与研究组51例,对照组男性26例,女性19例,年龄39~68岁,平均年龄(45.47±8.50)岁;研究组男性31例,女性20例,年龄41~67岁,平均年龄(46.05±9.19)岁。两组性别、年龄等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3名誉社员与赞助社员
中国科学社在其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存在期间,只选举了张謇、格林曼和李约瑟三个名誉社员,可见对于这一“徽号”相当重视(10)值得注意的是,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说爱迪生也曾当选名誉社员,并在回答相关人员的问题时说:“选举爱迪生则在《科学》月刊出版后,曾得他的来信表示赞助本社发展科学的意思。他本来只居于赞助社员的地位,但因为他对于应用科学的贡献,故社中同人主张给他较高的荣誉,以作为本社工作的标志。”(周桂发等编注《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书信选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323页)可见,爱迪生对中国科学社仅有赞助作用,“居于赞助社员的地位”,但因其科学发明的成就被提升为“名誉社员”。虽然同属于非社员,名誉社员高于赞助社员。但查遍相关中国科学社的各种记录(特别是年会会议记录,因名誉社员是年会选举通过的)和中国科学社出版的各种社员录,都没有找到爱迪生当选名誉社员的记载,任鸿隽的回忆可能存在偏差。。1917年9月在美国召开的第2次年会选举张謇为名誉社员。按照章程,“凡于科学学问事业上著有特别成绩,经董事会之提出,得常年会到会社员过半数之选决者”,当选为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员。也就是说,名誉社员首先在学术上有特别成绩,张謇当选为特社员似乎违背了这一原则。张謇作为王朝时代的状元,“剑走偏锋”成为“实业救国”代表人物。实业之外,张謇也注重教育文化事业,创办有学校、博物院、图书馆等,当然也是政治运动与政坛的风云人物,但在中国科学社所宣扬的“科学学问事业上”实在难说有特别成绩。有鉴于他对中国科学社赞助甚力,选举他为赞助社员“实至名归”,作为特社员自然“名不副实”。
一因中国为研究自然科学之大猎场,观其地大物博,宝藏尚未大开,诚为将来最有希望之国。二因近代科学应用甚广,因有渐趋于偏重物质应用及谋利方面,失去研究科学之真精神。中国向来注重自然科学,此种正确研究科学之精神,亟宜提倡,定能领袖世界作纯正科学研究之国家。鄙人此次来华,对于家庭安乐,自人幸福不能谓全无牺牲。但鉴于上述种切,觉此次被聘来华以从事于中国科学事业之研究,实为荣幸。今更被举为贵社社员,此后得追随于诸君子之后,为研究开发宝藏以福世利人之一人,更较被举为英国及其他国之会员为荣幸矣。中国科学方在萌芽时代,理应联合同志,亟力提倡。今观诸君热心异常,宗旨纯正,甚为愉快,甚为钦佩,谨为诸君及贵国前途祝福。[10]
总而言之,先生一生即精诚博爱之精神所贯注,乃高尚纯洁、大公无私之科学家,民胞物与,一以学术为依归,其科学精神之真挚,世罕其匹。呜呼!先生以七十一岁逝世,虽已享古稀之年,成久远之伟绩,然凡知先生者,犹悲其不憗。而吾国科学人士,无论与先生习与不习者,乃失一最不易得之良友也![12]
1.3.3 相关知识掌握度评估 采用本院自制的量表进行评估,满分100分,包括热量换算、饮食搭配、禁止食用等,掌握度高:评分在92分以上;掌握度一般:评分在70~92分之间;未掌握度:评分在70分以下。
可见,中国科学社当年选举格林曼为名誉社员,可谓实至名归。
此后二十多年,中国科学社未再增选名誉社员,直到1943年7月,在重庆举行的第23次年会上,选举李约瑟为名誉社员。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来中国并全力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前,已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先后出版著作《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心态发生》,并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3年,他作为英国政府派遣来华担任战时情报和宣传工作的科学家,其任务是 “与中国学者和科学家交换观点,并向中国人解释英国以及英国的生活与文化”[13]。2月24日,李约瑟抵达昆明,访问西南联大、中研院和北平研究院多个研究所。3 月21日,从昆明飞抵重庆,受到陪都各界热烈欢迎。此后,他赴各地考察,迅速与众多一流中国科学家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关系。1943年4月25日,中国科学社召开内迁第2次理事会,提出选举李约瑟为名誉社员的议案,议决提交年会社员大会[14-15]。当选名誉社员的李约瑟也曾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社务,出席在1944年10月25日在湄潭举行的中国科学社湄潭分会年会,11月3日电贺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24次年会暨中国科学社三十周年纪念会。因此,无论是从学术成就还是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来说,李约瑟当选名誉社员实至名归。
三位名誉社员两位是外国科学家,他们的当选除自身特出的科学成就与巨大影响外,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与中国科学社关系密切。与名誉社员选举的谨慎相比,赞助社员的推举就显得太过随意。1915年10月通过的章程规定,“凡捐助本社经费在二百元以上或于他方面赞助本社”,经董事会提出,得年会到会社员过半数同意,得为赞助社员。后来,捐助经费提升为500元,其他条件与程序不变。1917年第二次年会选举伍廷芳、唐绍仪、范源濂、黄炎培为首批赞助社员。此后,相继当选赞助社员有1919年杭州年会黎元洪、徐世昌、傅增湘、熊克武、杨庶堪、赵凤昌、谢蘅牕、凌潜夫、王云五等9人,1920年南京年会阎锡山,1921年北京年会叶恭绰、梁启超、宋汉章、陈嘉庚,1922年南通年会张詧、熊希龄、严修、齐燮元、韩国均、王敬芳、许沅、吴毓麟,1923年杭州年会卢永祥、张载阳、严家炽,1924年南京年会袁希涛,1926年广州年会谭延闿、蒋介石、张静江、宋子文、陈陶遗、傅筱庵、江恒源、张乃燕、张乃骥、王岑等10人,1934年庐山年会杨森、刘湘、甘绩镛,1947年上海年会张群、何北衡、蒋梦麟、钱永铭(12)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8月出版的《中国科学社社员分股名录》所载赞助社员共40人,与上述名单相比,有不少的出入,上述名单到1934年共43人,陈嘉庚、凌潜夫、傅筱菴、张乃燕等4人没有出现“名录”中,“名录”中姚永清不知何时当选。。
可见,先后共有47人当选为赞助社员。1927年前几乎年年选举,人数也较多。自1927年获得国民政府40万元国库券资助后,中国科学社有了相对丰厚与稳定的经费,赞助社员的选举几乎停止。1934年庐山年会选举杨森、刘湘和甘典夔为赞助社员,因当时中国科学社正在募集生物研究所发展基金,前两人各捐款一万元,甘捐款二千元。时隔十多年后,1947年再次选举张群、何北衡、蒋梦麟、钱永铭等4人,与战后中国科学社经费奇缺(战前积累的四十多万基金因通货膨胀形同废纸),发展陷入绝境有关,需要这些强力与实力人物或募集或直接捐助款项。
归一化是一种简化计算的方式,即将有量纲的表达式,经过变换,化为无量纲的表达式,成为纯量。本文实现了一种归一化的算法,其问题与记录的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有些人的当选,与他们是否捐助款项似乎关系不大,而因“他方面赞助”。首批伍廷芳、唐绍仪、黄炎培等,以为《科学》题词当选,并无捐款。不少人的当选与召开年会的地点有极大的关系,大多数当选者都是当地的政界或社会名流。如1922年南通年会选举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均、江苏交涉员兼浚浦局局长许沅、张謇兄弟张詧;1923年杭州年会选举浙江督办卢永祥、省长张载阳和厅长严家炽;1926年在广州召开年会,选举谭延闿、蒋介石、张静江、宋子文、陈陶逸、傅筱菴、江恒源、张乃燕、张乃骥、王岑,这些人都与广州革命政府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有不少确实对中国科学社的发展有大贡献。1924年南京年会选举袁希涛时,胡明复介绍说:“袁先生为当今教育界巨子,其事业道德为社员所共知,且袁先生对于本社极为热心,曾为本社募捐巨款。”[10]值得指出的是,宋子文既是普通社员(社号1001)又是赞助社员,与章程规定不符。
正如本文起首所引文字所言,这些赞助社员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名人红客”,具有呼风唤雨的能量。北洋政府的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国务总理唐绍仪、熊希龄,总长范源濂、叶恭绰、吴毓麟,省长韩国均、张载阳、杨庶堪,地方军阀阎锡山、卢永祥、齐燮元、熊克武、杨森、刘湘,教育界名流黄炎培、袁希涛、傅增湘、严修,金融界人士宋汉章、钱永铭,实业界人物张詧,新兴政权的领导人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宋子文、张群,民国初年南北议和的幕后人物赵凤昌等,真可谓阵容强大。
赞助社员基本上是与科学没有多少关系的社会名流特别是政治、教育与军事方面的人物,他们对中国科学社的了解与理解、对科学的认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自然值得怀疑。他们对中国科学社发展的影响更大程度上体现在经费资助与“政策倾斜”方面,在具体的社务发展上可能影响不大。特社员虽不少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赞助社员一类,他们对社务的发展可以说亦属于赞助层面,但他们多些学术色彩,而且作为社员对社务的发展影响也大于赞助社员,对社务的关心程度也较高。考虑到赞助社员主要是一些政坛名流,他们虽不参与社务活动,但与中国科学社牵扯在一起,可能给外界和学术界留下中国科学社与政治牵连太紧密的印象,这对一个学术性社团来说,可能并非幸事。
无论是特社员中的社会名流还是赞助社员群体这一“名流俱乐部”,他们在中国社会无论是在经济、军事还是教育等多方面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处置和配置的社会资源十分庞大,中国科学社结交他们,正是看重了这一点。通过他们,中国科学社与社会各界关系网并网,扩大了中国科学社的社会网络,自然扩大了其社会影响,这样为中国科学社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资源。同时,这些社会名流也愿意充当以学术为名的社团“保护人”,不仅可以为自己塑造一个支持学术研究的“良好”形象,以获得社会支持;而且中国科学社社员群体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可资利用的地方很多,例如人才与名义等等。
从个税税率表和年终奖计算方法,可以得出税率级差造成了差几块钱,甚至一元钱,税率就上了一个档次,因此,年终奖金发放的时候应避免这种情况,建议提前计算好,有效地避开“多发少得”的情况。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特社员、赞助社员群体中的各式各样人物不可避免地将一些政坛、社会上的负面因素带进中国科学社,使中国科学社的纯学术社团面目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模糊。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人物都有政治立场,他们在历史变迁中的政治选择,不仅与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身家性命与人格尊严密切关联,自然也影响到与他们关联的人事物。赞助社员中不少人后来“落水”做了汉奸,也有不少人被中共确定为“战犯”,他们对中国科学社的发展自然产生了不利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科学社的这些举措在民国学术社团中具有普遍性,因此“民主教授”袁翰青1948年在总结五四以来的科学工作时,曾十分痛心地说,当时科学社团“好几十个”,但“大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或则名存实亡”“或则机关化了”“最坏的官僚化了,一定要部长之流的人物做会长”[16]。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社团,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与政治相勾连,借助于政治强力寻求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政治在中国社会强大无比的影响力,学术独立于政治之路充满了荆棘,可谓任重道远(13)关于抗战胜利后,学术界的学术独立追求的粗浅讨论,参阅拙文《学术独立之梦:战后饶毓泰致函胡适欲在北大筹建学术中心及其影响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14年第4期)。。
本文创新地提出地区电能替代技术优选评估体系,为电能替代精准投资及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支持。随着环境保护观念与能源危机加剧,电能替代成为后续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的评估体系能有效解决电能替代过程中的优先发展次序问题,促进电能替代的发展。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当中国科学社在1927年获得了相对比较稳固的经费基础以后,就基本上停止了这个名流俱乐部的扩展。1947年再次扩展,也是面对当时经费难以为继,需要社外各种有力人物赞助的困难局面的不得已举措。与特社员、赞助社员相校,永久社员是中国科学社社务发展的骨干力量,其中大多数人是著名科学家,他们将中国科学社的发展作为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体。正是在这些社内科学家与社外赞助人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学社才得以蓬勃发展,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综合性学术社团,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王梅卿. 社与社友[J]. 社友, 1948,(85): 2.
2 上海社友之盛会[J]. 科学, 1919, 4(8): 808.
3 永久社员[J]. 科学, 1919, 4(10): 1032.
4 佚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R].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2239-5.
5 佚名. 中国科学社新社员名单[R]. 中国科学社全宗. 上海: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 Q546-1-91.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啼痕: 杨杏佛遗迹录[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244.
7 佚名. 理事会第12次会议记录[R]. 1924年2月15日. 上海: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546-1-63-63.
8 理事会第130次会议记录[J]. 社友, 1936,(55): 1.
9 理事会第132次会议记录[J]. 社友, 1936,(56): 4.
10 佚名.中国科学社第九次年会及成立十周年纪念会记事[R]. 上海: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546-1-228.
11 孙承晟. 葛利普与北京博物学会[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5, 34(2): 182—200.
12 秉志. 悼葛霖满先生[J]. 科学, 1937, 21(8): 605—610.
13 段异兵. 李约瑟赴华工作身份[J]. 中国科技史料, 2004, 25(3): 199—208.
14 佚名.上海档案馆藏中国科学社档案[R]. 上海: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 Q546-1-73-8.
15 竺可桢著, 樊洪业主编. 竺可桢全集(第8卷)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54.
16 袁翰青. 袁翰青文集[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5. 201.
AStudyoftheUnusualMembersoftheScienceSocietyofChina
ZHANG Jian
(InstituteofHistory,ShanghaiAcademyofSocialSciences,Shanghai200235,China)
AbstractIn addition to ordinary members,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SSA) had unusual members, such as permanent members, special members, sponsor members and honorary members. Each of these categories had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played varied social roles, and as a result, exerted different influence on the affairs of the society. When special members and some honorary members were elected, SSA did not fully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its charter, which required that academic contributions be taken as the standard. As a result, a good number of those who were originally only in the sponsorship role were elected. In addition,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social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selection of sponsor members, which led to the election of quite a few purely political figures. Although these measures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SSA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also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More importantly, the measures of SSA were quite universal in the academic socie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llustrates the powerful coverage of politics in Chinese society from one aspect, and shows that academic independence has a long way to go.
Keywords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unusual members, social role, social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N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 1441(2019)02- 0200- 12
收稿日期:2019- 02- 15
作者简介:张剑,1909年生,四川宣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
标签:社员论文; 学社论文; 国科论文; 年会论文; 科学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科学现状及发展论文; 中国论文;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9年第2期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