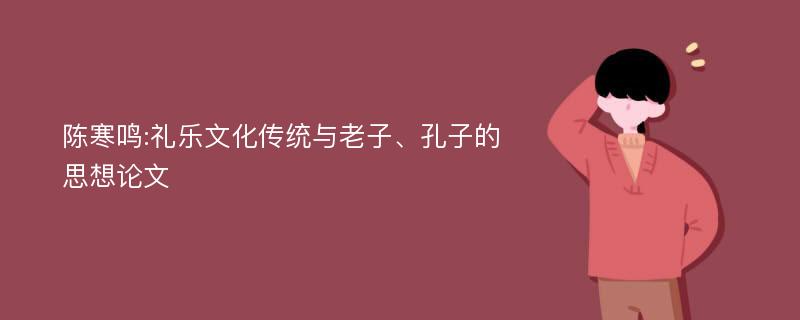
[摘要]老子和孔子大体生活于同一时代,承受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即源于上古巫祝文化的三代,尤其是宗周礼乐文明;遭逢并应对着同时代的社会问题,即在礼崩乐坏的现实条件下怎样重构社会秩序。老子以“道”为核心提出其思想体系而开创了道家学派,孔子以“仁”为核心提出其思想体系而开创了儒家学派,从而把中国思想引领到具有“哲学的突破”之意义的诸子时代。他们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精神素质起了型塑作用,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礼乐文明; 春秋乱世; 老子; 孔子; “哲学的突破”; “轴心时代”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出现过许多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杰出思想家,而就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精神素质起了型塑作用,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生深远影响角度来看,在所有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杰出思想家中,老子和孔子无疑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行为方式等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老子、孔子思想为基础。
一
老子和孔子大体同时代[注]① 张岱年先生序高明所著《帛书老子校注》,谓:“《老子》三十六章有‘报怨以德’之语,《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于‘报怨以德’的批评。足证孔、老同时的传说并非虚构。”,而老子年长于孔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因见周之衰而退隐。《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观周》《庄子》《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子列传》等中都有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或孔子某些关于礼的见解“闻诸老聃”或孔子见老聃并对其颇有称道的记载。孔子见过的这位后来著述了五千言《道德经》的老子,是否如有些论者所说就是太史伯阳[注]② 何新《古本老子〈道德经〉新解》本台湾学者周次吉之说而发挥道:“所谓‘老子’与其认为是一个人,不如认为是一个老氏群体,一个世族,也是一个学派。”“黄老之学传于上古,至晚周主系传于太史伯阳及老聃(聃/鼉通,即龙也。老子又号称李耳,‘李耳’乃是楚方言中老虎之名,龙虎上古本可通名,应即老彭氏世族所宗之图腾)。老氏世传天道而世任商周之史官,传习天道、治国及修身之术。至老聃亦尝任史官及兰台之官,或曾为孔子之师,并传天道于孔子。而太史伯阳(又称伯阳父,父者,老也)处周之末世,知天下将大乱而避世出走,至函公关为关尹喜传讲其家学秘决即今本《道德经》。”,可置不论,但孔子见过老子,向他请教过有关“礼”的问题,并且,这位老子著有《道德经》(目前所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著作传世[注]③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发现有三种《老子》的节抄本,尽管与传世的今本《老子》颇有差异,但可以肯定早在春秋晚期就已有《老子》即《道德经》一书行于世了。张岱年先生在为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所作序中说:“战国时期,秦汉之际,《老子》一书可能已有不同传本。”在流传过程中会有一些后世观念羼入其中,但此乃正常现象,并不足以改变《老子》即《道德经》的基本成书时代。,这应该是事实。诚如董平教授所说:“只不过孔子究竟在何时拜访老子而向他请教,则古史失载,今天已经无法详考了。孔子原以博学多闻而著称,其‘学而不厌’,竟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那么他向曾做过‘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去请教周礼,似应在情理之中。”[1]
由表1可知,在各施工过程中,吊索的索力分布很离散,故施工中根据各根索的就位索力选取千斤顶。第一批吊索的最大就位力为2830.8kN;第二批吊索的最大就位力为2210.5kN;第三批吊索的最大就位力为1636.8kN,施工中选用最大千斤顶为2台250t的千斤顶。
基本同时代的老子和孔子,承受着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就是源于上古巫祝文化的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宗周礼乐文明。大体说来,三代以前是巫祝文化期,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明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就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礼乐文明是从巫祝文化发展而来的。“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据《说文》乃“行礼之器,从豆,象形。”近人王国维孝证,“豊”诚为礼器,然非“从豆”而是“象二玉在器之形”,且“乃会意字而非象形字”。古者行礼以玉,《尚书·盘庚》所谓“具乃贝玉”说的就是以玉礼神。从甲骨卜辞中“囲”(即“豊”)字的结构上看,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于神。王氏《观堂集林》卷六《释礼》据之得出结论:
图6给出了弹丸超高速侵彻中厚靶引起的靶板中的波系作用。反射的稀疏波与入射冲击波相互作用后,靶内出现负压区,随着反射稀疏波向靶的深部传播,负压将会逐渐增大,当负压达到靶的动态拉伸强度时,将会形成层裂片并从靶体向外抛出。根据冲击波强度及靶板厚度的不同,可以形成一块或多块层裂片。如果最终的坑底位置与层裂片位置重合,则被定义为“弹道极限条件”。
盛玉以奉神人之谓之囲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
孔子与老子承受着同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孔子所生长的鲁国保存礼乐文化最为完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观礼于鲁,其所见有周乐,有德康叔、武公之《卫风》,有表太公之《齐》,而闻歌《秦》则听夏声,歌《唐》则思陶唐氏等等,确乎是集宗周礼乐文化之大成了。又,昭公二年,晋韩宣子来聘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曰:“周礼尽在鲁矣”!《庄子天下篇》说:“《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甚至到“春秋末世,中国古代社会正走着它的迂回的路线,政权下移,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氏族单位到地城单位的变革过程,比之希腊社会,显然具备了‘难产性’”[3]138,而宗周礼乐文化传统在鲁存在如故,如据史籍记载:
礼也者,人类一切行为之规范也。有人所以成人之礼,若冠礼是;有人与人相接之礼,若士相见礼是;有人对于宗族家族之礼,若昏礼丧礼是;有宗族与宗族间相接之礼,若乡射饮酒诸礼是;有国与国相接之礼,若朝聘燕享诸礼是;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道以冶人情也。”(原注:《礼记·礼运》)诸礼之中,惟祭尤重。蓋礼之所以能范围群伦,实植本于宗教思想,故祭礼又为诸礼总持焉。
“祭礼”就是历代礼典中的效社宗廟之礼,它以祭祀天神、地祗、人鬼三元系列神为内容,故又统称为“三礼”。《尚书·尧典》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引马融注谓:“三礼,天神、地祗、人鬼之礼。”又郑玄注云:“三礼,天事、地事、人事之礼。”
2.3.1 粒径及Zeta电位 用纳米激光粒度仪对白藜芦醇DPPC脂质体的粒度和Zeta电位进行测定,温度为25 ℃,体积为1 mL,每份样品平行测定3次。结果发现白藜芦醇DPPC脂质体的平均粒径为(191.5±4.5)nm(图1-E),多分散指数(PDI)为0.3±0.1,载药脂质体的Zeta电位为(12.4±1.5)mV(图1-D)。
侯外庐先生依据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古代社会,“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上,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的奴隶社会。但是两者的序列却不一定是亚细亚在前。有时古典列在前面,有时两者平列,作为‘第一种’和‘第二种’看待的。‘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改良的路径。前者便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惟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2]他十分精当地指出:“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末,‘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3]11-12此一论断符合中国古史实际。如西周的宗法制度就是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国家制度,是把国家融合于宗族,或者说是将统治宗族提升为国家的一个典型。而所谓“周礼”,则是由上古氏族习俗提炼、转化、上升而来的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这样一种由氏族而家族而国家,并且国家混合于家族之中,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氏族贵族专政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路径,表明氏族共同体的解体过程就是国家建立的过程,亦即原始巫祝文化衰落、礼乐文明兴起的过程。这样的文明路径,决定了古代礼乐文化具有下列性质与特征:其一,源于宗伯(宗法)和巫祝(宗教)的礼乐文明之兴起与发展,扩大了宗法的范围、缩小了宗教的范围。祭器包容于礼器之中,而礼器(如鼎、尊、爵等)则发展成为权力与氏族等级地位的标识。这样,礼乐便为氏族贵族所专有,并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其二,礼乐“用于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所谓“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史记·乐书》)。礼乐成为社会政治伦理的衡尺。如周武王革殷命时,曾宣布殷纣王三大罪状,即胗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宗廟社稷、尊奉礼乐为由而提出来的,也是后来宗周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依据。其三,宗周政治是氏族贵族的专政,文化也为氏族贵族专有,此即所谓“学在官府”。其四,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从史诗到史书,反映出时代的大转折。《诗》是宗周礼乐文化的代表,而《春秋》则是礼乐崩坏时代的史书。
曾子问曰:“下殤,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涂迩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自贸港金融与当地发展水平和定位紧密关联,为此必须形成总分协同的战略执行体系。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设计必须要求分行之间、业务条线之间的协同合作,整合已有自贸区业务、未来的自贸港业务、离岸业务和境外机构资源。因此,商业银行应加强总行层面的顶层设计,建立专司自贸港业务的领导协同小组,制定整体自贸港金融服务发展规划。同时,在组织架构上建议研究制定自贸区/港分支机构架构管理办法,以减少沟通汇报层级,提升管理效率。
“亲”和“贤”本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分属两个不同角色序列的人物,前者指血缘关系上的人物;作为自然人,表现为家族内部的父母兄弟等等。后者则指有德有才之人。“亲亲”是自然情感,“尊贤”是从“爱人”出发的理智考量,即须选择“德行道艺逾人者”负责公共事务。唯有“尊贤”,即由贤者为社会提供服务,才能把“爱”落到实处,否则徒谈“仁爱”,空而无用。在这里,“道”由“情”生,表现了人类进入文明门槛之初自然与人文的内在连接。尧、舜等古圣先贤“爱亲”而“尊贤”,堪称楷模。孔子把“爱与敬”即既“亲亲”又“尊贤”作为“正(政)之本”,《唐虞之道》的作者则指出六帝之兴“咸由此也”。这样,“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他以“仁”为核心而提出其思想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发展起儒家学派。孔子以来的历代大儒亦无不以“仁”为根本宗旨,把“仁”作为最核心的价值观,视为根本之道,故“孔门之学,以求仁为宗”(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卷一《辨清学脉上》),“仁”成为孔子以来中国儒学传统的精神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儒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仁学史。
曾子问曰:“葬引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变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
老子尝为周守藏室之史,而史官之职本是由“通天以属神”的巫发展而来。他承受着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当然是精通礼乐文明的,所以,在《礼记·曾子问》中可以见到有关老子精于礼的记载:
“我们社区下面,反正书记主任都是我嘛,现在街道是这样,叫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原来比如说消防这块主要是主任做,他现在还要求书记也要负责,就是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你都要负责。 没有像以前那样分,书记主要党务这块,然后安全生产这块是主任去负责,他现在就是说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殯而致事,殷人既丧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众所周知,在孔子之前,许多先哲已将“仁”作为美德来使用了。就目前能够看到的文献而言,《尚书·金滕》曰“予仁若考”,《诗经·齐风·卢令》云“其人美且仁”,春秋时代,人们已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很多优良行为用“仁”来描述或界定,如《左传》中有“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度功而行,仁也”、“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大所以保小,仁也”等记述,《国语》中亦有“畜义丰功谓之仁”、“爱亲之谓仁”、“仁不怨君”、“仁人不党”、“仁者讲功”等观念。前贤都以“仁”作为一种美德。美德与恶德构成矛盾。孔子将“仁”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藉以克服各种恶德。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仁”既是总徳,又是最高的道德人格精神境界。这是孔子对传统“仁”的重大发展,也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作出的卓越贡献之一。在孔子看来,作为一种道德品性的“仁”,贯串、充盈于其它各种德性之中,每一种道德行为都内在地体现着“仁”的精神。这正如其弟子子夏所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孔子从不轻易以“仁”许人,即便他自己亦不敢以仁者自居。但另一方面,“仁”是不是遥远而又高不可及呢?不是的。孔子所讲的“仁”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只要道德主体愿意践行“仁”,它就会同智慧和勇气一同萌发,促成内在品性的变化。“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它建立在人的类别意识的基础之上,而非经济地位和政治特权的差异上。钱穆先生指出:“所谓‘仁’,即是指导各个人在人群中如何做人之大道。而仁则在人心中,与生俱来。故仁即是人之性,而主要乃表现在人情上。一应理智之发展,应有其指导原则,即不能离仁而走向不仁的路上去。仁中有爱,但爱不即是仁。‘仁’与‘爱’之分辨,、违亦为中国儒家所重视。因单讲爱,则易流入‘欲’。欲的分数多了,反易伤其爱。”[8]这是从概念与心理层面来解读孔子的“仁”,有其超越时空的合理性。
精于礼而又亲历了周室之衰的老子,不仅认识到古老的礼制已不适合春秋末年的时势,而且更感知到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礼已徒成虚饰,故而正如其“来自神巫却反对神巫”,他“精于礼而反对礼”[4]1034,以致斥责“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注意到当时社会思潮中已经开始流行的“道”的观念,如“国家之败,失之道也,则祸乱兴”(《左传·昭公五年》)、“川泽纳汙,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天道不滔,不贰其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左传·昭公一年》)、“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等等,但他反对那些将天道神秘化的说法,如“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左传·襄公十八年》)、“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左传·昭公十一年》)之类。老子自觉地将“道”作为其“哲学的中心观念,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开展的”,并且,在以“道”为理论基础和核心观念的前提下,他“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颇具体系的思想。[5]这样,“老子将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原始天人关系改造成富有哲学意义的天人关系,尤其偏重个人(而不是人人之际)的超越,此后道家、道教蔚为与儒家、佛教并驾齐驱的学派或教派,而都奉老子为鼻祖。这位‘古之博大真人’与远古神守之制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其实道家、道教都与原始文化的潜流息息相关,可见神守时代的文化传统生生不息,像奔腾的大海,构成中国文化深厚宽广的底蕴,沾溉每个中国人,儒家也受其影响”[4]1038。
二
“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其渊源于上古巫祝文化当无疑义。关于礼乐文化源自于巫祝文化,文献记载中也有所暗示,如《易经·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礼记·乐记》谓:“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同篇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既然有着如此渊源关系,那末,礼乐文化中非常明显地保留着巫祝文化的残余也就不足为怪了。如《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曾据之发挥道:
齐仲孙湫来省难,……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閔公元年》)
原来,陆叔叔和妻子牟月原本都是蜡像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制作的一家三口的生活场景的蜡像被发到了网络上,一时间成了红人。身为商人的李总感觉这是个商机,就主动找到他们,投资兴建了这两栋小楼。双方签了合同,夫妻二人专心创作,李总负责运营。
此前召开的2018世界钾盐钾肥大会暨格尔木论坛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盐湖资源综合性国际行业大会,也给盐湖股份公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王兴富说,此次大会展示了中国形象,凝聚了行业信心,更为行业开启了新征程。他认为,此次大会通过论坛、展览会、高层访谈等模式,吸引国内外钾盐钾肥企业、技术设备提供商及行业权威专家,汇集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两院院士、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投融资机构、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等多方声音,从国家政策、行业发展、技术创新、农业应用等全方位探讨钾盐钾肥和盐湖资源的产业态势,为国内外钾盐钾肥的发展与盐湖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广泛交流平台。
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虽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叶,但“儒”却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及刘向《七略》均认为儒“出于司徒之官”,而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则以儒为术士之称,“儒”实与初民社会交通人神的巫祝活动有关。“儒”就源自于这巫及与巫有着密切关联的祝史,换言之,上古的巫史文化乃是文明时代儒文化的源头。“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谓巫、尹、史)演化而来的专职监智保存者。”[6]孔子之所以有异于往昔之“儒”而真正成为儒学和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乃是因为他在春秋末叶社会变革时代,不仅传承了巫史以来的传统,而且更把源自上古并存留于当世的社会习俗提取、转化为自觉的思想意识;既依守传统(如其“礼”学),又创发新知(如其“仁”学),更将此二者熔为一炉,建构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文廷式谓:“自有儒术,而巫教仅为斋祝之言,不能如罗马、犹太之祭司动司生杀也。”[7]这既是以巫祝为主体的宗教权力的衰落,亦是人文取代了神文,这是时代的进步,历史的进步。
这样,与精通礼乐文化而又力批礼乐文化的老子不同,孔子依据其“损益”史观,对传统礼乐作了加工改造。《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绎如也,皦如也,绛如也,以成。’‘吾自卫适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兼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正是对《论语·述而》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很好疏证。
可见,古代经典如《易》《诗》《书》、礼、乐便是儒学的本源,而邹鲁缙绅之士则是儒家的先辈。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邹鲁缙绅先生的儒术(《诗》《书》、礼、乐),正是以‘先王为本,今世为用’的过渡思想,正是春秋社会‘私肥于公’的反映。”“孔子是否缙绅先生中人虽不敢强断,但他既生于保存了‘周索’的典章文物的鲁国,则他曾受缙绅学术传统的长期薰陶,并从而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所以《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诗》《书》、礼、乐者甚多,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等。”[3]139,140
从思想文化史角度看,孔子对传统礼乐文明的改造,最重要的表现为其言“礼”论“仁”,更纳“仁”入“礼”,把“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现世的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熔为一体;并且,孔子由“亲”及人,由亲亲而仁民,既肯认既存的等级秩序,又强调某种“博爱”的人道关系。《礼记·哀公问》记孔子之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正之本与!”后来的儒者继承了这种思想,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曰: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让。孝之方,爱天下之民。让之口(缺字),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让,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
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薧,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返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祫祭于祖,则祝近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
如此等等。正因为老子精于礼,好学敏求的孔子才会“适周问礼”,向老子拜访请教(《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其事:“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而据《孔子世家》,孔子将别,“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返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三
在老子和孔子以前,不仅中国的思想自上古巫祝文化以来已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至西周,礼乐文明已发展臻堪称圆熟之境,而且还产生出一些适应新的社会变化需求而有利于宗周思想的新观念,但这些都未及从理论上作系统概括。老子、孔子相继跃登历史舞台,标志着此前思想的终结。他们在旧秩序崩坏的社会现实中,分别以“道”、以“仁”为核心提出各自的思想体系,其后继者又以这两个思想体系为基础发展其学,从而形成发展起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尽管“世之学老子者则絀儒学,儒学亦絀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老子、孔子各以其学把中国思想引领进入到西方学者所谓“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之轴心时代,此即春秋末叶至战国之世,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就此而言,在由远古巫祝文化发展而来的礼乐文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下产生的老子和孔子,既是中国思想史上旧时代的终结者,又是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都具有伟大的理论创造精神。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最早提出“轴心时代”(Axial Age)的说法,认为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这一时期,世界历史上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且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的精神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对雅斯贝尔斯揭示出的这种“轴心时代”的开启,国外有学者把它解释为“哲学的突破”,如余英时陈述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思的观点道:“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9]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具有“哲学的突破”意义的“轴心时代”之开启,乃是由于作为历史存在之主体的人自觉介入了思想文化的运动;“没有那些敏感的生命主体深入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并以其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的独有体验为基础进行历史的反思,就不会有所谓的‘哲学的突破’”[10]。
老子、孔子所以能将中国思想引领进入到“哲学的突破”之轴心时代,就在于他们在礼崩乐坏、社会危机深重的春秋末世,自觉介入了思想文化运动。老子以其亲历周室之衰的生命体验为基础进行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深刻揭露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矛盾与对立,《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七十五章)更试图以其所揭扬的“道”来消解这种矛盾与对立,即“想把‘有之’的社会,回复到‘无之’的社会”[3]261。这当然不能真正解决“拆散”时代的现实问题而重构出一个新的社会,但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
作为道家开山人物的老子,正生当时不仅周室的统治早经瓦解;并且各封建诸侯的统治,亦已开始崩溃;春秋时代所流行的礼的观念与节文,已失掉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作用的时代。这正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当时不仅已出现了平民的知识分子;并且也出现了在《论语》中可以看到的“避世”的知识分子。在这种社会剧烈转变中,使人感到既成的势力、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皆随社会的转变而失其效用。人们以传统的态度,处身涉世,亦无由得到生命的安全。于是要求在剧烈转变之中,如何能找到一个不变的“常”,以作为人生的立足点,因而可以得到个人及社会的安全长久,这是老子思想最基本的动机。[11]289
并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顺着古代宗教坠落的倾向,在人的道德要求、道德自觉的情形之下,天由神的意志的表现,转进而为道德法则的表现。儒家由道德法则性之天,向下落实所形成的人性论,系以孔孟为中心,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由宗教的坠落,而使天成为一自然的存在,这更与人智觉醒后的一般常识相符。在《诗经》《春秋》描述的时代中,已露出了自然之天的端倪。老子思想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对此自然性的天的生成、创造提供了新的、有系统的解释。在这一解释之下,才把古代原始宗教的残渣,涤荡得一干二净;中国才出现了由合理思维所构成的形上学的宇宙论”[11]287。
作为土地管理工作中最基础的环节,土地利用变更意义重大,因需处理大量数据,在具体实践中较为复杂。现阶段,如何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一步提高土地信息变更的效率和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管理信息化建设已然成为各地土地规划与管理的重要问题。
至于孔子,称尧颂舜,寄寓着他希望在现世实行有如上古那样的仁德之政,以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社会理想。他具有强烈的社会情怀,其思想核心“仁”更是批判理论与社会理想的缩写。只有结合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才能深入思考“仁”的社会功用。当时,贵族骄奢淫逸,平民困苦不堪,社会等级森严,列国征战不休,乱象丛生,亟需变革。变革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激烈的革命,有渐进的改革。有人将孔子塑造为革命家,有人将孔子视为改革派,还有人将孔子扭曲为复辟分子。这些都是后人的一孔之见,与孔子本人相去甚远。孔子思想的立足点在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确立“类”的意识,倡导“爱人”,将人类与禽兽区分开来,防止出现统治集团虐待生民、流民冲击社会秩序的恶性事件。从道德的起源到人类意识的确立,再到人类相爱的理想社会,孔子思想的轮廓逐渐清晰,正如张君劢所言:“道德之起也,由于物之各爱其类,飞禽走兽之于子,无有不育哺而卵翼之,其在人类则为慈为孝,由父子兄弟,扩充而为社会,则有分工合作,而相助、相托、相约之关系,由之以生。而信义仁爱、忠恕勇侠之道随之而至,此皆出于人类相爱之心,不可一日离者也。”[12]道德理想一直萦绕在儒者的心头,指引着他们改良世道人心。孔子确立“仁”的崇高地位,成功地使士人摆脱远古宗教观念的束缚,凸显人道的重要性,将天道解释为符合人道的进化秩序。这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注目于中华法系的异彩纷呈,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道理,“由于中国文化,不在宗教方面特别发展,法律自亦随之而不能宗教化矣。中国文化所以不走向宗教途径者,此因华夏民族与其文化,出自多元,而彼此胸襟阔大,对于所会合之各族文化,兼容并收,仍任各族之信仰同存,因而产生多神现象,自然不能形成宗教;法律比较有统一性,自不能将各族的信仰规定于法律之内,且多神并存,亦不成其为宗教矣。”[13]在儒家的理论框架中,人性显得尤为可贵,人性可以拓展为五常之性,它与天道实现吻合。人性是真实不虚,尽管它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为不同的样态,但是有些恒定的道德理念决不会磨灭。我们不能否认人性的真实性和普遍性。“在中国文化史上,由孔子而确实发现了普遍的人间,亦即是打破了一切人与人的不合理的封域,而承认只要是人,便是同类的,便是平等的理念”[11]57。这是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人性觉醒的理性主义呼唤;正是有了孔子的这思想,正是由于有孔学及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才使得中国文化是人学而非神学。
将中国思想引领进入到“哲学的突破”之轴心时代的老子和孔子,都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伟大思想家。如果说老子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其所提出的哲理深邃的“道”论上,那末,孔子的创造性就在于培养士人,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为平民阶层跻身政治领域搭建津梁。在当世社会已发生严重变迁式动乱的背景下,基于对“小人‘疾贫’与君子求富”这样一种现实的肯认,孔子不仅揭橥“有教无类”之旨而对私学及先秦子学思潮的勃兴“尽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首创任务”,而且他还以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光辉命题,“承认了国民参与政事的合理性”,其门下“弟子即以国民阶级占绝对多数(只有南宫适、司马牛二人以贵族来学),而‘问为邦’、‘学干禄’、‘可使南面’、‘可使为宰’、‘可使治赋’者,实繁有徒”。进一步考察,孔子“不但肯定‘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且主张‘仁者爱人’”,“把道德律从氏族贵族的专有形式拉下来,安置在一般人类的心理的要素里,并给以有体系的说明”。[3]133-145尽管“仁”不仅是总德,而且还是本体性的道徳范畴,但它发乎内而著乎外,并不是从外面强加的制度或行为规范,而是人们只要有了自身的自觉便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可以感知可以体现可以达到的。这就使其依据时代精神而创新性提出的“仁”学,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反复强调“仁”的社会功用,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而且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只能是人学而绝非神学。
最后在Synopsys公司的Design Compiler平台采用TSMC 65 nm CMOS工艺库对接收端同步系统进行了综合,得到各方面指标如表2所示。
[参考文献]
[1] 董平.老子研读[M].北京:中华书局,2015:6.
[2]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三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5] 陈鼓应.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M]//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M]//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 文廷式.文廷式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903.
[8] 钱穆.孔子与论语[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25.
[9]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28.
[10] 韩德民.礼:从历史到哲学[J].中国文化研究,1997,春之卷.
[11]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2] 张君劢.义理学十讲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
[13]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1.
TheTraditionofRitualandMusicalCultureandThoughtsofLaoTseandConfucius
CHEN Han-ming
(The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 of Tianjin Trade Union, Tianjin 300380)
Abstract: Lao Tse and Confucius lived in the same period and received the sam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three-generations of ancient sorcery culture, especially the Ritual and Musical Culture inherited from Zhou dynasty. They faced and coped with the same social problems in that period, which was how to reconstruct the social order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ite system. Lao Tse initiated the Taoist school by proposing his ideologies “Tao” as the core concept, while Confucius initiated the Confucius school by proposing his ideologies “Ren”. Both of them led the Chinese thought to the masters’ era with corresponding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s. Their thoughts have shape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xer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 Ritual and musical culture; Turbulent Tim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Destruction of the rite system; Lao Tse; Confucius; Taoism; Confucianism; Breakthrough of philosophy; “The axis age”
[中图分类号]B222.2; 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9)01-0021-07
[收稿日期]2018-07-15
[作者简介]陈寒鸣(1960-),男,江苏镇江人,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儒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
(责任编校:谢光前)
标签:孔子论文; 老子论文; 礼乐论文; 社会论文; 思想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