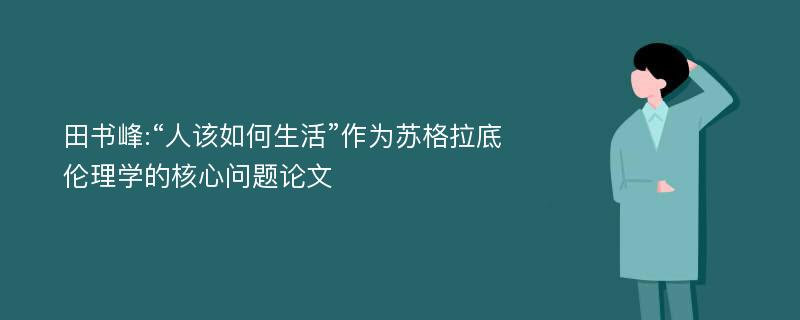
[摘要]“人该如何生活”或“何谓好的生活”是苏格拉底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关切的基本视域。通过与对话者一连串的叩问和对谈、诘难和训诫,苏格拉底所说的“好的生活”的整全面貌也就慢慢呈现出来:第一,“好的生活”必然开始于对德性的追求,这就是“德性转向”,即从对外在的自然事物的关心转向到对内在的灵魂德性的关心;第二,“好的生活”始于对自我的认识,而本真的自我是理性,它不存在于生灭不定的感觉世界(Werden),而是存在于依赖理性的实存世界或本体世界(Sein);第三,苏格拉底对于“好的生活”或德性的理解并不是一种技艺性的知识(technical knowledge),因为技艺都是价值中立的或有两面性,可被用于好的和坏的目的,而有关德性或“好的生活”的知识一定只能被运用到善的目的上,德性绝对会达致善;第四,“好的生活”必然需要实践智慧,因为智慧是对人的所有类型的价值和善的某种整全理解,并且包含运用到所有情境中的能力,但是,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看透所有事物之间的全部的内在联系,所以,苏格拉底至死持守自己的“无知之知”的信条。
[关键词]苏格拉底;德性;好的生活;实践智慧
一、“人该如何生活”作为伦理的基本视域
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是对伦理知识(ethical knowledge)或者道德洞见(moral insights)的追问与寻求,并在此寻根究底的追问与探寻,反思与对谈中发展出一种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1)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352d中这样提问道:“我们现在再来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提出来的那个‘正义者是否比不正义者过得更好更快乐’的问题。根据我们讲过的话,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因为这并不是关乎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而是关乎一个人应该以什么方式来生活的大事(Rep.352d.)。”另外,在《高尔吉亚》472c6ff这样写到:“我们当前争论的问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关乎那知之为最美,不知之为最愚笨的东西,因为,这里的焦点是或者认识或者不认识,谁是幸福的,谁不是幸福的。”。其次,“人该如何生活”与“人如何做一个好人ó)”有着本质上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2)Cf.Sauvé Meyer,S., AncientEthics,ACritical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 2008.pp.1-2.。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唯有追求德性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德性始于对自我的真正认识,德性就是对人的善的整体把握,是一个人内在的实践智慧,不同于以外在产品为目的的技艺。所以,苏格拉底伦理学并不是以寻求“伦理上的应当”(das moralische Soll)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是努力回答“人该如何生活”和“何谓好的生活”的问题(3)Vgl.,Wolf,U.,DieSuchenachdemgutenLeben,PlatonsFrühdialoge,Hamburg: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 H,1996.S.13-14.。对于好生活的追问是苏格拉底的哲学的核心问题,其他所有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核心问题相关联。无论是苏格拉底所使用的“反诘法”,还是他所关心的不同德性的具体定义问题,比如节制、正义、勇敢、虔敬、友谊等,抑或是他与智者和修辞学家在某些问题上所进行的扣人心弦的争论,包括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讲辞,以及他在狱中所发表的临死遗言,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来展开的,如果没有这个核心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对苏格拉底所关心的诸多其他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图景,他的哲学活动也就显得零散杂乱。
这个核心问题可以说是苏格拉底整个实践哲学的基础。虽然,对于善好生活的追问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学的内容,但是,任何一种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会与这个问题相关。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像在解答一道几何题或数学题,求证可以提前被给出的未知数x,而是我们必须亲自去寻找不可以被提前给出的解答,并检验这些答案是否正确。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苏格拉底将“人应当如何生活”设定为自己的哲学关切的基本视域,他对于智慧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于何谓德性与幸福本质的叩问,与对话者所进行的不计其数的提问与回答,抑或反驳与训斥,以及他在自己与传统权威之间所做的区分等都是围绕着“人该如何生活”来进行的,如若苏格拉底的上述行动与这个问题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关联,那么,他所进行的这些活动也便与那些政客、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活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虽然,商人、政客或手工业者的生活也在某种意义上与“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具有关联,他们所追求的善(财富,城邦的兴旺与技艺)也与“人如何过一种善好生活”中的善相关,但是,他们最终并不能在一种整全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提供给我们一种有关不同的善之间的关系图景。
二、“好的生活”与德性
一方面,“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的提出会在苏格拉底的对话者的灵魂里产生震撼,因为这个问题会使人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它打破了人们满足于日常的人云亦云、得过且过的不加思索的寂静状态,它促使人们返回内心,追问自己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而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又具有某种统一或整合的作用,正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生活的各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部分,看似支离破碎的地方才被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个体灵魂中的欲望部分、激情部分和理性部分都能被统一到对好的生活的追求上去,而个体在自己的城邦生活中所从事的各项活动,所进行的各种事业也都是以“好的生活”为目的。
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中国应当尽快出台反制裁政策,减少美国制裁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在此问题上可以参考欧盟的做法。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2018年8月6日,欧盟将1996年《反制裁法案》(Blocking Statute)修订后重启,限制美国域外制裁政策在欧盟的效果,保护欧盟企业的合法权益,要求欧洲公司面对美国制裁不得遵守美国制裁政策,在欧盟管辖范围内不认可任何美国法院或机构的域外管辖制裁的效果,规定因美国域外管辖权实施制裁导致的欧盟受损企业,可以向相关个人或机构要求赔偿(可以直接在欧盟起诉美国政府)[31,32]。
苏格拉底并没有随意地给出一个回答而让听众感到满意,相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苏格拉底与来自当时希腊城邦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对话,比如演说家、诗人、政客、智者、医生、商人等,他们分别代表着希腊社会中流行的对“人如何过一种善好生活”的问题的观点。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苏格拉底总是能够以其睿智的眼光看出其矛盾的地方,并能指出不足,进而提出自己的反驳。尽管,这种对流行的哲学观点的批驳并不一帆风顺,相反,这是一场极具挑战性与危险性的交锋,甚至,苏格拉底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丝毫退让,他在《申辩篇》中将自己比作牛虻,刺激那些陷入昏昏沉沉中的马匹,使它们活跃起来。他有时也将自己的这种工作比喻为神的工作,是对神的命令的服从。他这样做是受神的委托。我们暂且不去追问苏格拉底本人是否经历了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经验,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不管是把自己自喻为牛虻,还是寻求于神明的相助,这都显示出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以及他所使用的诘问法和其他哲学方法具有某种威胁性,至少对于当时那些控告他的人分别所代表的人群具有威胁,这三位控告人应该集中地代表了当时的政治权利与主流文化阶层,比如代表政界的阿尼图斯,代表悲剧诗人(或诗艺)的梅勒托和代表修辞演说家的吕孔。从这三人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来看,这表明苏格拉底与他们三人所代表的有关“何谓人的好的生活”的问题的理解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至于他们不能容忍苏格拉底,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
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466a4-468e2这一演说家与僭主段落(orator-tyrannts-passage)中将当时的政治家和演说家心目中所向往的“好生活”的样式展露无遗地揭示出来。在波鲁斯(Polus)的眼中,“好生活”在于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演说家与偺主就是这种好的生活的代表,因为他们都有权利能够将人们认为最为不幸的事加于那些他们想要惩罚的人身上,剥夺他们的财产,甚至可以将其置于死地。苏格拉底通过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与做自己喜欢或显得好的事情之间进行区分而批驳了这种观点,因为演说家与僭主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或对他们显得好的事情,但他们并不能做他们在意志上真正想做的事情。真正的好生活是正义的生活,一个违反正义的事情虽然可能是令他喜欢的,但并不是真正的善的事情。
雅典人啊,尽管我与你们是朋友,并且热爱你们,但是,我更愿服从神而超过你们,只要我一息尚存,还能做事,就绝不会停止追寻智慧,都会用我一惯的说法向你们提出警告,且向你们证明,无论碰到你们中的任何人:哦,最为卓越的男人,作为来自一个以智慧和力量而著称的最伟大的城邦的雅典人,如果你只渴望尽力获取最多金钱,声名与荣誉,而不追求智慧与真理,也不关心如何使灵魂成为最好的,你难道不会为此而感到羞耻么?如果你们中有人否认这一点,而认为关心这些事,那么,我不会让他离开,我自己也不会离开,而是询问他、考察他、检验他。如果我发现,他并不拥有德性,而说自己有德性,我会给他指出,他将最为重大的事情视作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将较差的事情看作是较高贵的事情。对我遇到的每个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年青人,是异乡人还是本地人,我都会这样做,对你们我更要这么做,因为你们是离我最近的同乡。你们一定要弄明白,是神命令我这样做。我相信,在这个城邦里还没有过比我对神的侍奉更大的善(Apo.29d-30a)。
无论如何,这种第一次航行的隐喻说法所表达的无非是借助于感觉对自然诸物的机械性或技艺性解释并不能让人认识自我,只有借助于思维、假设的命题和语句、理性的推理等才能步入到自我认识的殿堂。苏格拉底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航行所要揭示的也无非是他的这种哲学探寻之路上的转向,即从依赖感觉而来的生灭世界转向于依赖于理性而来的实存世界,从对自然诸物的研究转向到形而上学的研究(7)Frede,D.,Platons“Phaidon”:derTraumvonderUnsterblichkeitderSeele.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9 S.120.。这种转向对于认识自我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借助理性的推理,自我反思的意识才是可能的。
同样的批驳也发生在《理想国》的第一卷,在这里,这个问题显得更为迫切,苏格拉底极力地批驳特拉叙马霍斯的主张:“正义是强者的利益”(Polit.338C-339A)。特拉叙马霍斯将修辞学、智术师和僭主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他的主张“正义是强者的利益”òò代表了权贵阶层对“好生活”的理解,而且他坚持认为这种生活就是正义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强者或统治者与牧人是为了自己的臣民或者羊群的好处,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城邦生活中也是这样,正义者在经营生意时处处吃亏,而不正义者则显得游刃有余,春风得意,所以,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来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于自己有好处,有利益。不正义者既明智又好,而正义者既笨拙又坏。这种逻辑思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不正义被归于道德与明智,而正义反倒被归入愚笨与坏。对此,苏格拉底对这种颠倒黑白的事情愤愤不平。于是,苏格拉底在348b-354A中,先后三次对特拉叙马霍斯的主张进行了反驳(4)Siehe:Friedländer,P.,Platon,Bd.II,DiePlatonischenSchriften,ErstePeriode,Walter de Gruyter,Berlin 1964.S.58-59.。首先,苏格拉底指出特拉叙马霍斯所说的“正义”的本质其实就是“想要更多的欲望(但是,这种对于更多的贪欲将会导致与僭主或强者的利益本身相冲突的后果,即本来他们以为是自己的利益的东西反而成为他们的弊害,所以,正义绝不可以被归入恶,而不正义也绝不可以是善。接下来,苏格拉底批驳特拉叙马霍斯所说的“更为强有力的óτερον)”,按照特拉叙马霍斯的看法,正义的人虽然是更好的和更明智的,但是,不正义的人则是“更强有力的”。苏格拉底认为,完全的不正义将会导致无法行动,因为就连坏人之间也要有某种正义的时刻,否则他们之间无法进行合作。第三个批驳是针对特拉叙马霍斯对于“幸福的理解。因为“幸福”是人生所有行动的最后目的,而这个目的只有通过属于自己的本有德性才能达到,而灵魂的本有德性是正义正义代表着灵魂具有善与知识;不正义则代表恶与无知。如果灵魂是正义的,是善的,那么,它就会完成自己的本有德性,就会生活地好也就是幸福的。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以特拉叙马霍斯为代表的僭主似的生活方式作为“好的生活”或“幸福的生活”的看法遭到苏格拉底的彻底反驳和唾弃,后者将正义置入到善与知识的领域、将正义作为灵魂的力量、而且只有正义才能带来幸福。在这里,“好的生活”与灵魂的德性、知识和善联系起来,而且这是一种必然性的或本质上的联系。基于苏格拉底的这种观点:“好的生活”必然地与德性联系在一起,他才在雅典人民面前发自肺腑地呼吁人们应该放弃对财富、美名与荣誉的欲求,而更多地将自己的灵魂转向对德性的关心上来:
苏格拉底为了能呼吁雅典民众关心灵魂和欲求德性,在这里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因为他会询问、考察和检验任何一位他所遇到的人,如果发现对方声称自己拥有德性,但实际并不拥有德性,那么,他就不会放过他,因为他将最为重大的事情视作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将较差的事情看作是较高贵的事情。苏格拉底的虔敬在这里也显露无遗,因为他认为,是神命令他这样做。苏格拉底自感肩上的使命源自于天授,因此,他更不畏惧权贵的刀剑与巧舌如簧的诡辩。无论如何,苏格拉底指出了雅典的那些政客、能工巧匠与诗人或演说家都基于对自己的技艺的娴熟程度而自认为在那些极为重大的事情上也是拥有智慧的。恰恰是这一错误,遮盖了他们认识到何谓真正的“好的生活”,因为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极为重大的事情”就是指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局限于自己的技艺之内而失去了走向另外一个更高的层面进行哲学反思的机会,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就像精通专门的技艺那样也很精通人应该如何生活或何谓德性的问题,然而这正是雅典人的最大错误:
按照苏格拉底的看法,人们对于何谓“善的生活”的理解是与人对于自身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善的生活”是某种实践的结果,但是,实践出“善的生活”则需要有关它的知识,也就是需要实践智慧。对于“善的生活”的知识或者关于“极为重大的事情”的智慧是以对自我的认识来开始的。阿波罗神庙的神谕“认识自己óν)是一种对于哲学的转向。苏格拉底并不满足于钻研天上星体以及自然物体,研究它们的来龙去脉,生成与毁灭的原因,而是要认识自己:
最为经典的地方就是《申辩》20a-c这一段,这段文本通常被称为技艺类比(Techne-analogy:TA)。苏格拉底问一位叫做卡利亚斯的父亲,谁是他的两位儿子的教化者?如果他的两个儿子是小马驹或者小牛犊,他会找一位驯马师或农夫来做他的两个儿子的教化者,让他们变得优秀或者获得某种特殊本领,因为只有驯马师或者农夫拥有这个训练小马驹或小牛犊的技艺但是,他的儿子们是人,谁具有这种教化人的知识呢?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并不具有这种知识。如果驯马师与马驹的优良相对,那么,X就与人的优良或德性相对。问题是,这种与人的德性相对应的X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呢?这种与人的德性相对应的X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与驯马师的技艺形成类比呢?这种知识X有没有一个确定的、且可以和此种知识的使用者和此种技艺相分离的外在产品呢?它又是不是可教的?也就是说这种类比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借此而勾勒出一种伦理知识(moral knowledge)的模式呢?对此学者们的意见不一,颇有争议。Terence Irwin认为,在TA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一种苏格拉底的伦理理论,其原则就是:德性就是某种技艺知识(Virtue is simply craft-knowledge)(12)Irwin,T.,Plato’sMoralTheory,theEarlyandMiddleDialogu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7.。而Gregory Vlastos则认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TA只能在一种有限制的意义上来被理解,在一些方面就像技艺,但在其他方面则彻底不同(13)Vlastos,G.,“The Virtuous and the Happy,” TLS,23 February 1978,pp.232-233.。Klosko也认为,赋予苏格拉底一种有关德性的技艺理解是缺乏有力的证据的(14)Klosko,G.,“The Technical Conception of Virtue,” JournaloftheHistoryofPhilosophy18(1981):pp.98-106.。David L.Roochnik更是反对Irwin的看法,他认为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多次使用TA,并不是意在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德性或伦理知识的技艺性的理解模式,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主要是用于下述两个辩证性的目的:劝诫与反驳(exhortation and refutation)。根据David L.Roochnik的看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总共出现了675次之多,而大部分是在与TA有关的文本语境中出现的,苏格拉底使用技艺类比用意或在于劝诫对话者去真正地追求这种知识,或在于反驳那些自以为已经知道或者找到自己想要的解答的人。所以,苏格拉底并不是意在使用TA来建立某种伦理知识的技术性模式(technical conception of moral knowledge),而是旨在达到如下的前提,即伦理知识或道德洞见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善(15)Roochnik,L.D.,Socrates’ Use of the Techne-Analogy,in:EssaysonthePhilosophyofSocrates,ed.by Hugh H.Bens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p.185-195.。Roochnik与Irwin对于TA的解读截然对立,前者主张苏格拉底使用TA是为了一种辩证性的用法,而后者则认为TA为我们提供一种有关人的德性的技艺性理解模式。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柏拉图的对话文本本身就会发现,一方面,苏格拉底使用TA并不是意在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关人的德性的技艺性理解模式(technical conception of moral knowledege),但另一方面,他所使用的TA的意义并不终止于劝诫与反驳,或者与人的德性或伦理知识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我们有关人的善好生活的伦理知识应该与TA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若不是这样,那么,苏格拉底就没必要屡次在论述人的德性或伦理知识的时候谈及实际上,对于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关于人的善好生活的知识。在形式上,与显示出同样的结构,也就是说在制作的产品与人的教化方面具有一种类比性,一方面,在Apo.20a-c中,苏格拉底认为驯马师的任务就是将小马驹训练成为一匹出色的战马或优良的坐骑,能够供人骑射。小马驹并不是天生就是一匹出色的战马或优良的坐骑,而是它需要驯马师的技艺来完成。同样地,如果小马驹的优良或出色在于能供人骑射,那么,人的优良或出色在于什么呢?人的卓越、优秀或德性就在于作为人或公民活得好和做得好,就在于善好的生活,而教化者必须知道所有的构成人的善好生活的必备条件。但是,无人能够完全明了这些构成人的善好生活的所有条件,至少不能像一位驯马师那样明了自己的技艺的诸种情况那样。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类比好像忽然断裂,因为教化者本身也是作为人而生活,他的生活对他来说并没有一个外在目的,但是,至少这种类比在形式上,苏格拉底并不否认存在着这种有关人的善好生活或德性的知识,这才是人们应当去追求的。在内容上,苏格拉底承认,有关人的善好生活或德性的知识并不具有一种的形式。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反复地提及他反思自己的生活与活动(Apo.20c5),也检验他所遇到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与活动,他在Apo.20d8中说,他只是具有人的智慧,而没有神的智慧,而前者与后者相比,更是一文不值。无论如何,苏格拉底在这里所要引入的是一个不同于的另外一种知识,即一种有关善好生活或实践的善的知识。这种在内容上的不对称性在《伊翁》和《小希庇亚斯》中显露无疑。在前者,苏格拉底认为,具有在自己所关涉的对象内的整全性(die Ganzheit)和价值中立性(Wertneutralität)。伊翁认为他作为一位吟游诗人拥有一种诠释诗歌的技艺,但只限于诠释荷马的史诗,因为他认为只有荷马才是好的诗人,而其他诗人不是好的。苏格拉底认为,一个好的诗人不能只是理解和诠释好的诗作,而不能理解和诠释糟糕的诗作,所以,他认为,一个好的吟游诗人必须能够吟咏和诠释所有的诗作,好的和差的诗作,因为一种所关涉的领域既是限定的(Begrenztheit),也是整全的或整体性的,就是在它所关涉的受限定的整个领域内的事情(die Ganzheit)。接下来,苏格拉底提出了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特性,那就是价值中立性(Wertneutralität)或两面性(Ambivalenz),即在每一种所关涉的领域中,都存在着它的对立面,每一既可以被应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被应用于坏的目的,这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志。在《小希庇亚斯》中,的这种两面性或双面性被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希庇亚斯认为,《伊利亚特》比《奥德赛》更好,因为阿基琉斯是一个诚实的人,而奥德赛则是一个老奸巨猾的说谎者。但是,如果就说话的技艺来看,它不仅是能说真话,也是能说谎话的一门技艺,而说谎话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结论就是一个只会讲真话或一个只知诚实的人并不比一个既知道真诚又知道说谎的人更好,因为真诚(Wahrhaftigkeit)与说谎本来就属于同一门技艺,如此,阿基琉斯与奥德赛的区别也就自行失效。就言说或说话的技艺来说,一个既能说真话又能说谎言的人要比不能这么做的人更具有这门技艺。但是,希庇亚斯对这个结论显然充满敌意,他所寻求的是一种伦理上的正义行动,一种道义上的善,也就是说他所寻求的不是某种技艺的优良而是人在伦理上的卓越或优良如果说,技艺的优良与人的伦理上的卓越具有同样的结构,那么,结论将会是荒谬而可笑的,因为一方面技艺的能力具有两面性(Ambivalenz),也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人的意愿而被用于好的或恶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存在着关于人的善好生活或人的伦理德性的技艺或知识,那么,这门技艺的对象将会包含一切,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一门技艺被应用于何种目的并非取决于它本身和它制作的产品,而是依赖于人的意愿和决定,所以,需要另外一种有关我们应当选择何种目的、如何管理和在何处运用我们的能力的知识,这就是一种我们应该如何过一种善好生活的知识(16)Vgl.,Wolff 1996.S.63-66.。
三、“好的生活”与自我认识
你们雅典人啊,都会些能工巧匠们在我看来似乎犯了和诗人们同样的错误,因为他对自己的技艺掌握的相当娴熟,于是,每个人意愿自己在那些极为重大的事情上也是最有智慧的。这一错误遮盖了他们拥有的智慧(Apo.22 d)。
在这里,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认识,就去探究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人来说莫过于认识自己。苏格拉底所说的自我认识或自我知识可以在下述两个转向中呈现出来:一是自我认识是一种从对自然诸物的生成与毁灭的原因之探求转向到对超越感性的形而上学的实体的探求,即从生成(Werden)领域转向到实存或实体(Sein)的领域;二是苏格拉底的自我认识是从一种对身体或肉体的关心转向到对灵魂的关心上,因为只有灵魂才是真正的自我,而灵魂凭其智慧与思维(τò而居于统治地位,认识自我就是凭借理性与言辞(λóγο)认识自己的灵魂所本有的德性与功能,或旨趣与本性。
我至今都不能按照德尔斐神谕认识自己,连自己都还不认识就去探究(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对我来说,显得好笑。所以,我把这些东西都搁置一边,人们习惯上是怎么相信这些东西,我就信之若素,而不去探究这些事物,而是探究我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碰巧是个什么怪兽,比百头怪还要曲里拐弯,还要形象可怖,抑或是个更为温顺而且单纯的动物,天性上带有几分神性,而非百头怪(Phdr.229eff.)。
对于第一个转向,苏格拉底实际上并没有一开始就专注于对不可生灭的超越感性的形而上学世界的探究,并没有一开始就以认识自我为终生之旨趣,而是在年轻的时候沉迷于探求自然的智慧,忘情于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而浑然不觉:
我啊,刻贝斯,年轻时候就欲求那种叫做“探求自然的智慧”。毕竟,当时在我看来,这种智慧甚是美妙:知道每一事物的原因,即每一事物何以产生,何以毁灭,何以存在。我不断反复思考,对这样一类问题,困惑不解。就如有些人主张的那样,是否热与冷引起的发酵就会产生出动物的组织?我们是否借助血、空气、或火来进行思考?或者这些都不是,而是大脑给我们提供了听觉、视觉和嗅觉、而记忆与意见就源自于这些感觉,知识则是源于记忆与意见的确定状态?(Phaedo95a-97a)
迪庆供电局启动三级响应,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抢修复电行动当中。为预防触电的次生灾害,迪庆供电局主动停运2条10kV主干线、4条10kV分支线。按应急响应通知单要求,迪庆开发区供电分局在确定辖区内安置点的的数量及具体位置后,分局所有值班人员分成七个小组,每个小组分别由5人组成,主要负责相应安置点的每顶帐篷的布线通电工作。开发区分局设置三个水位观测点,分别为里仁、新仁及开发区水文观测点,每两个小时报告水位情况。
Phaedo,96a-102a这一段文本甚至被Giovanni Reale称为西方形而上学的“Magna Charta”(大宪章),在欧洲的文明史上,这段文本可以被理解为对超越感觉的实存的首次理性上的陈述与呈现(5)Reale,G.,ZueinerneuenInterpretationPlatons.EineAuslegungderMetaphysikdergroßenDialogeimLichtder“ungeschriebenenLehre.” Paderborn:Schöningh 1993,S.140.。这就是有名的被称为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航行)。苏格拉底在青年时代曾沉迷于钻研自然事物,研究它们的生存与毁灭的原因,这种对于自然事物的生成与毁灭的原因的研究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们那里就已经出现了,比如,恩培多克勒就认为思维的基座是血液,而狄奥根尼则认为思维的基座是空气,但是,对于阿克迈翁来说,感觉中枢的基座就是大脑(6)Ebert,T.,Phaidon.Übers.u.Kommentarv.TheodorEbert.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recht 2004(Platon,Werke 1,4),S.340.。苏格拉底认为这种自然的研究方法非常不充足,比如,他认为,单是吸取营养并不能解释身体发育和成长的原因,他在努力寻求另外一种不同的原因。后来,阿那克萨戈拉有关理性)是万有的原因和根据的理论让他甚为惊喜,但是,他发现虽然阿那克萨戈拉这样主张,但是在对事物进行实际的解释时,并没有将理性当作最后的原因和根据来看待,而是举出空气、以太和水的例子来。这让苏格拉底甚为失望,因为阿那克萨戈拉又重新陷入到机械性的世界观里,尽管他认为理性是所有存在中最为纯粹者和最精微者。这种机械性的原因并不能解释实是与生成(Sein und Werden),它只提供了一种原因所赖以发挥作用的物质性条件(Phaedo,98b-c)。这种经验性的解释方式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显得有些荒谬和可笑,比如,他之所以坚持坐在牢狱中而不逃跑,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的骨头是坚硬的,而肌肉是柔软的等等,而是因为他的意志决定,接受雅典人的判决。身体的骨骼和肌肉能够起作用,这只是一种苏格拉底坚持坐于牢中的附属原因,并不能与原本的原因混合在一起。如此,苏格拉底开始了自己在哲学探寻之路上的第二次航行,这是一种隐喻,表示苏格拉底开始发展一种新的完全不同于自然哲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不再以感觉和想象为解释世界的基础,而是以逻各斯或理性为认识世界的最为可靠的工具。这是一种从物理世界转向形而上学的跨越,通过借助而不断地接近那超感觉的世界。在这里,是指思想、语句或假设命题,从这些前提中可以推论出可靠的结论。无论如何,第一次航行借助于东风的力量,扬帆起航,甚为快捷,这象征着自然哲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但是,第二次航行则是奋力划桨,逆风而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表示人如若要发现那超感觉的世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在西方,有这样一个好像是必须的现象,那就是只要抓现当代了,传统的具象水平就自然而然地滑坡了似的。不过就“不同”展而看,我们的具象能力照样强大,对传统研究的势头并未式微。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种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向并不是为了获致关于技艺和其他科学(比如几何学、数学、天文学等)的知识,而是为了获得一种关于自我的知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真正的自我就等同于自我的灵魂,而不是肉体。从对肉体的关心和对属于肉体的那些财富、健康和荣誉等外在善的关心转向到对灵魂的关心以及那属于灵魂的诸种德性的关心是认识自我的至关重要的前提(8)Helmut Kuhn这样描述苏格拉底的“自我认识”所包含的对于人的存在本身之意义的层面:Das von Sokrates erfragte Lebenswissen umfaßt die Einheit des menschlichen Agathon zusammen mit der sich in ihm zur Tauglichkeit vollendenden Seinsgrundlage,dem Sein des Menschen oder zunächst dem Sein,das ich selbst,der Fragende,bin.Siehe:Kuhn,1934.S.37。。苏格拉底在《申辩》中这样呼吁雅典人民不要只关心如何获得更多的钱财、名声与荣誉,而要更多地关心灵魂,以及如何使灵魂变得更好和更卓越(Apo.29d-30a)。苏格拉底的这种灵魂同于真正的自我的命题并不是他本人的发明,而是源于古代希腊的不同传统,比如在秘契或神秘宗教的传统中,灵魂被认为是某种神性的东西,如果生前一个人满全了一些规定的神秘仪式,那么死后他的灵魂还会继续生活;而在伊奥尼亚传统中,灵魂被视为是被封闭在我们身体之中的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某种气或以太(aither),人死后,它就会飞走,重回以太中。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灵魂仍然具有物质性,但是,它仍然被视为与思维的力量相连的某种神性的元素。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与诗人品达在伦理的层面上更强调灵魂要远离不正义的侵害(9)Cf.Guthrie,W.K.C.,148.。只有到了苏格拉底这里,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才被清晰而明确地表达出来,二者的关系就像是制作者与工具、使用者与被使用者。对于他来说,灵魂就是真正的自我,生活着的是灵魂,而肉体只不过是灵魂赖以生活的工具,就像一个制作者只有在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工具时,他才能制作出优秀的产品;同样地,只有当灵魂能够统治身体的时候,或灵魂居于统治地位时人才能活得好。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承继了这种灵魂相对于肉体来说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按照柏拉图的看法,灵魂的理性部分(λογιστικóν)按其本性来说就应该统治与肉体更多地搀和在一起的灵魂的激情部分)与欲望部分óν),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更加清晰地表达出灵魂相对于肉体而言的首要统治地位(Phys.I 2.)。
如果说灵魂就是真正的自我,而自我的本性又在于理性),那么,对于灵魂的关心或提升就在于运用理性与思辨的能力来追求智慧与真理。灵魂所追求的智慧与真理并不是指关于某种以外在的产品为制作目的的各种技艺而是以伦理知识或道德洞见为对象的知识,是关于人的“善好生活”的知识。认识自我与认识何谓伦理德性,即何谓善的生活或何谓人的善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凯米德斯》讨论何谓节制的问题,《拉克斯》主要追问何谓勇敢的德性,而《吕西斯》则就何谓友爱展开对谈,《欧绪弗洛》又论述了何谓对神的虔敬,《理想国I》主要讨论何谓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通过对上述德性的本质的讨论表明,这些不同的德性是构成人的善好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从是否拥有关于这些德性的知识出发也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认识自己。但是,苏格拉底在上述对话中并没有以拥有智慧和对德性的知识而自居,相反,他只是指出了他的对话者们的无知,即他们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知道何谓上述德性,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对话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相信自己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在这些被称为“难题对话”(aporetic dialogues)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在结尾处并没有像一位拥有知识的专家那样教授给他们有关这些德性的最终本质,相反,他只是提出隐含在对话者们的观点中的更为棘手的难题,他依然在寻找德性的本质的路上,而不是自以为已经获得了它(10)苏格拉底之所以能指出对话者们的错误,而又不以拥有这种智慧和知识而自居,原因就在于他对那超越于个人之上的能够揭示出事物本身的逻各斯(λóγο)的敏锐直觉与自愿随从。在《凯米德斯》中,苏格拉底与其对话者就何谓节制的德性展开对话。在苏格拉底与克里迪亚(Kritias-Gespräch)之间的对话中,首先苏格拉底对克里迪亚提出的有关节制的几种定义逐一进行了质疑与反驳,尤其是将节制作为善的行为)和节制作为对自我认识(τòóν)以及其他种类的知识的定义τε苏格拉底提出了更为详细的驳斥。根据Helmut Kuhn的看法,苏格拉底在《凯米德斯》中所说的自我认识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种是反思的或判断的意识(das beurteilende Bewußtsein),这种判断意识在逻各斯、在各种不同言辞的洪流中,在对话的交谈意义的发展中显示出来;自我认识的第二个层面的意义是自我把持(Selbstbesitz),这两个层面的涵义不可分开地交织在一起。这一点不仅在与克里迪亚的对话中显露无遗,而且在苏格拉底与其他所有对话者的提问与被反问的对谈甚或交锋中,他虽然有时表示无言以对的样子,只能沉默、甚或选择逃避,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坚持那能够将事物本身显示出来的逻各斯,而对这种超越个人之上的逻各斯表示一种遵从与敬畏。Siehe:Kuhn,H.,Sokrates,einVersuchüberdenUrsprungderMetaphysik.Berlin 41-44。。
四、“好的生活”与技艺的类比
如果说对于“好的生活”的洞见和认识需要这种建立在自我反思上的自我认识,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自我认识或关于自我的知识如若不是以“好的生活”为指向或目的,那么这种自我认识也就流于空泛。因为这种由自我认识而来的知识不是一种关于某种以制作外在的产品为目的的技艺知识(11)首先,不只是指一种我们今日所说的“技术”(technic),即对于某种工具的操作与运用的技能(比如,开车技能或绘画技能),而更是指一个人借着拥有对于某一领域内的专门的原则知识而能以适宜的方式安排或改变质料的状态,而能借以实现设定的目的。这种意义上的可以被视为实践知识的某种模式(Ein Modell praktischen Wissens)。Sieh:Wolf 1996.S.34.而David L.Roochnik认为,不仅指涉一种以制作外在产品为目的的一种实用的知识,而且它可以包含一种建立于数学之上的理论知识,不以外在产品的制作为目的,而是为了发现事物的真实本性(Eud.290b-c)。我认为,不管只是以制作外在产品为目的的知识,还是也包含认识和事物的真实本性的理论知识,就所关涉的领域来说,一定是具有限定性和整全性(Bestimmtheit und Ganzheit),而就其本性来说一定具有一种双重性或两面性(Ambivalenz)。See:Roochnik 1992.p.186.,对于自我认识的知识来说,它没有一个外在的产品需要来制作,这种知识面对的是自我本身和生活本身,即有关伦理德性或善好生活的知识。但是,苏格拉底很多次使用技艺的类比来阐释人的伦理德性,那么,问题是,技艺的类比与人的伦理知识之间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形成类比?苏格拉底对德性的理解是技艺性的吗?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那些“极为重大的事情”就是指有关何谓正义的和好的生活的问题,这关乎到人的德性以及人在城邦里的教化。苏格拉底对此并没有直言不讳地认为自己具有智慧,认为自己对于这“极为重大的事情”了然于心,他只是确切地认为,僭主、辞令家或演说家、智术师与能工巧匠们所主张的生活方式与他所认为的“好的生活”或“正义的生活”有着本质上的天壤之别。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认为,阿波罗神庙的神谕之所以坚持认为无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是因为只有苏格拉底明白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毫无价值。这种区分是源于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而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
五、“好的生活”与智慧
基于技艺类比,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人的优良或卓越,也就是有关人的伦理德性的知识是一种不同于技艺的知识,有关人的善好生活的知识并不是通过制作外在的产品表达出来的,而更多地在于我们的分辨能力,即决定我们应当选择何种目的以及应当将我们的才能与禀赋运用到何处才能帮助我们过一种苏格拉底所说的“善好生活”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天赋于我,而是需要实践经验与理性的反思。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一方面,他宣称自己并不具有这种知识,也不能教授这种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对那些自以为知道何谓德性或何谓善好生活的对话者无情地加以口诛笔伐,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德性的真实本性,他们只是自以为知道,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有关人的善好生活的知识并不是一种技艺性的知识,而是一种智慧(17)John M.Cooper用非常精炼的语句表达出了这种智慧的特性:“Wisdom,then,is a permanent,deeply settled,complete grasp of the total truth about human values of all sorts,in all their systematic interrelationships,primed for ready application to all situations and circumstances of human life.” See:Cooper,J.M.,PursuitsofWisdom,SixWaysofLifeinAncientPhilosophyfromSocratestoPlotinus.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 2012,p.46.。
2017年是互联网期刊行业面临重大改革的一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将会为互联网期刊行业的信息服务带来巨大的变革:一方面在政策和行业的风口下互联网期刊已经从单纯的资源汇集与提供向知识服务迈进一大步,而且逐渐向智慧型知识服务发展;另一方面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响应用户的潜在需求,能够更加精准的进行知识传播与决策服务。各行业、各类机构目前都对大数据与知识管理有着强烈需求,并针对本行业、本机构的大数据与机构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实际,又衍生出众多个性化需求。
原发性高血压多是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共同导致的,这是一种处于不断进展状态下的心血管综合征,会引发患者心脏血管结构以及功能的改变。关于提高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的护理对策需要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展开综合化的研究与探讨[1]。
没有实践智慧所引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并不能达到“好的生活”。对于“好的生活”预设着有关它的知识或洞见,但是,人们如果想要获得有关“善的生活”的知识和洞见,需要从变化不定的感性世界上升到永恒不变的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中来。这种上升或者这种转变需要智慧。一方面,苏格拉底否定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所拥有的并非真正的智慧,因为智慧是某种对人的所有类型的价值和善的整全把握和理解,并且具有随时能够运用到所有情境中的能力,在苏格拉底看来只有神明配得上拥有这样的智慧,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不能看透所有事物之间的全部的内在关联。所以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智慧,但是,另一方面,他仍然确信无疑的是,追寻德性始终是人能通向“善好生活”的必经之路,是获得人的善的基本条件,所以他才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呼唤人们转向德性。当然,苏格拉底在这里更多地将德性理解为一种对何谓正义、勇敢、节制等德性的伦理知识,基于这种伦理知识或理解,他能够保证他的行动是正确的,并且他的选择或决定就是在每个具体的情境中的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知与行在苏格拉底那里有一种必然的因果性的联结关系,一个人如果真的拥有有关正义的知识,那么他的行动就会是正义的,而不正义的行动更多是出于无知,也就是没有对正义的真知。这种理智主义的解释在柏拉图那里也可以看到,德性根本上是一种对人的善的理智把握(intellectual grasp)(18)但是,这种理智主义的解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遭到批判,因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忽略了欲求能力和非理性欲望的作用,一个人的行动至少包括理性和欲求两个因素,前者是对于善的理论把握,而后者才能提供行动的动力。因此,一个人可以放弃自己的理性而随从欲望,也就是说可以明知而自愿地作恶。这就是(不自制或译为意志软弱)的问题。有关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伦理学的批判详见:EN VII 1-10。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自制是存在的,并且在理论上证明了不自制存在的可能性,这在根本上否定了苏格拉底的无人自愿作恶的主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苏格拉底所说的“好的生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第一,苏格拉底将“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视为自己的伦理学的基本视域或核心问题,一切的哲学关切都是与探寻何谓“好的生活”关联在一起的;第二,苏格拉底反驳了僭主、演说家和诗人对“好的生活”的理解,他不遗余力地呼唤人们转向德性,因为“好的生活”必然是正义的、符合德性的;第三,“好的生活”或德性始于对自我的认识,而本真的自我是理性,所以本真的自我并不存在于生灭不定的感觉世界或生成世界之中(Werden),而是存在于建基于理性之上的实存世界或本体世界中(Sein),换言之,苏格拉底的自我认识是从一种对身体的关心转向到对灵魂的关心,即对德性的关心;第四,苏格拉底对于“好的生活”的理解或者对于德性的知识并不是一种技艺性的(technical),因为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技艺都是价值中立的或是两面性的,即一门技艺根据人的意愿既可以被运用到好的目的也可以被运用到坏的目的上,而有关德性或“好的生活”的知识一定只能被运用到好或善的目的上来,德性一定是好的,因此,对于德性和“好的生活”的知识不是技艺性的。
由于农业生产环境具有较偏僻、温差大、潮湿重、不稳定性多等恶劣因素,给有线信号传输造成很大的使用瓶颈。而无线通讯技术的主要优点有:①对于移动测量或距离很远的野外测量,采用无线方式可以很好地实现并节省大量的费用;②无线传输技术不易受到地域和人为因素的影响;③无线通信的接入方式灵活;④较高的传输带宽,抗干扰能力强,而且功率谱密度低[6]。
“风云莫测”一类的话语,用在内蒙的云上可能最是贴切。例如第四天在曼陀山边达日罕小镇“龙泉宾馆”早起出发时晨晨说“天不好,没云;多半会一路暴晒了”;可此话后不过一个时辰,就无中生有地无意间积聚了甚多的云,开始还是羞答答贴着地平线或地平线一带的平矮低山溜达,尔后随着太阳的高升和气温的提升开始变得越来越登堂入室、越来越肆无忌惮,像往日一般东一抹西一抹地步步拉高,最终是布满湛蓝的天庭。
TheCentralProblemof“HowShouldOneLive”intheSocraticEthics
TIAN Shuf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How should one live”, or “what is a good life”, is the core question in the Socratic Ethics and is the fundamental horizon in Socrates’ philosophical concern. Through a series of asking and answering, elenchus and reprimand,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good life” was gradually clarified. Firstly, “good life” starts from pursuing the virtues,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turn of virtue”, for instance, the turn from the care of the external natural things to the care of internal virtues of the soul. Secondly, “good life” starts with knowing the true self, which is the rationality, and it doesn’t exist in the sensitive world of becoming, but in the world of being or true substances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Thirdly, Socrates doesn’t consider the “good life” and the virtues as technical knowledge, because all techniques or arts are neutral in values and ambivalent, which can be used both for good or bad purposes, but the knowledge of “good life” and virtues can only be applied to good purposes and absolutely lead to the good. Fourthly, “good life” necessitates the practical wisdom, because the wisdom i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r general grasp of all kinds of human values and goods in all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human wisdom is so limited that they cannot obtain complete knowledge on the inner relations of all things; therefore, Socrates persists in the doctrine of “knowing the fact of ignorance”.
Keywords:Socrates; virtue; good life; practical wisdom
[中图分类号]B50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6-0111-10
[收稿日期]2019-06-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希腊罗马伦理学综合研究”(13&ZD065)。
(责任编辑 胡敏中 责任校对 胡敏中 孟大虎)
标签:苏格拉底论文; 德性论文; 知识论文; 技艺论文; 自己的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希腊罗马伦理学综合研究”(13&ZD065)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