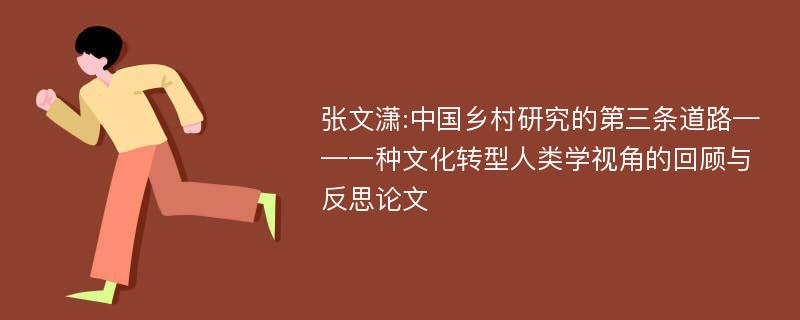
摘 要:乡村是映射中国的一面镜子。在文化转型的当今时代,对乡村社会做出理解变得尤为重要。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和展开,乡村呈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与发展。在追求对它们做出理解的过程中,基于对以往中国乡村研究的方法、对象与立场的回溯与反思,提出要以历史性、开放性与日常性的眼光来看待农民与其生活世界的双向互动。忽略了任何一方的主体性及其所浸润其中的时空维度,都会陷入到或“左”或“右”的选择旋涡,或落入到重复暂时性决断的困境,而这些似乎并不能对乡村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借鉴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不走极端才会良性发展。
关键词:文化转型;反思;理解;乡村研究
文化转型正日益成为一个我们目前亟待做出理解与调适的现实问题,[1]它意味着对自然世界的一种态度转变。[2]71这个过程涵盖三个层次的转变:首先,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上的转变,即从具有包容性的天下观的立场出发转换角色,由从别人影响我们转变到我们去影响他们。其次,是一种价值观念上的转变,随着一些新物质性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曾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支配性的观念正发生着一种重大的转变。最后,由社会连接方式的转变所直接带来的一种主体意识(强调个人价值及其权利表达)的转变。[2]61-62在这类转变的大背景下,尤其伴随着互联网时代乡村社会开放性的日趋加强,我们更需要对以往的乡村社会研究做出理解与反思,以开辟中国乡村研究的新场域。
一、超越村落的中国乡村研究
学术界向来不会否认理解乡村对于理解中国的独特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转型的当下,对乡村社会做出理解变得尤为重要。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最初更多会聚焦在单个的村落空间上。在王斯福看来,一个村落是一个地域归属的界定,村民对地方性和长期性的感受、国家与政府的政治组织和基于亲属制度和朋友关系的民间组织,都会产生出有边界的地方性感受。[3]
庄孔韶将人类学聚焦于村落的研究历程追溯至美国学者葛学溥,在葛学溥看来,乡村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是得到承认的。[4]与葛学溥的中国乡村研究不同的是,布朗采取的是人类学的社区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强调作为研究中国最为基本单元的村落研究的独特价值,如其所言:“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会,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5]
对于村落的关注激发出了一种社区研究的范式,这明显地体现在了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所指导的研究之中,而他在燕大培养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学生,都注重在社区生活的一群人其真实的生活样貌。[6]在李怡婷、赵旭东关于1922-195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统计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此类“目光向下”的学术关怀,统计显示,极大多数的论文是以村落研究或者以乡村为主体的村落研究为主。[7]261-306
一台机器人运作时固然可以做到最短路径的搬货,但是多台同时运作时,因为场地通道有限,所以很难实现全部做到最短路径的搬运。有时就会因为避让另一台机器人而绕远路前行。
尽管聚焦于村落,但学者在村落研究中有意无意地都有一种“透过村落理解中国社会”的想法,即一种“超越村落”的企图,可将之称为一种“自反性研究”。[8]然而,这种企图遭遇了“代表性”的问题。正如利奇对费孝通提出的质疑: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对此,费孝通以“类型比较法”作为回应,即无需把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加以观察,而采用比较的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个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以此逐步接近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9]然而,在乡村时下正经历的文化转型大背景下,一些研究在对一个个乡村展开观察与描述时,呈现都是既有框架的翻版,鲜少见到研究者主体意识之下的社会科学概念的提升。[10]这类研究在我们将村落比较提升至整体认识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尚不明显。
这些研究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观察对象的固化。在我们进入某个村落之时,往往会忽视村庄外部世界的存在,这种存在会由于村落中不断有远去的行者而得到彰显,他们可能是外出任职的官员、到城里的打工者、读书的学生等。[6]赵旭东指出,把研究旨趣限定在乡村,不是“中国社会结构必然的要求”,而是在一种“西方的他者”的范式[注]西方的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作家、记者以及乡村的调查者,这些人对于乡村的描述使得中国的乡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自我观照的他者,他们以其丰富的乡村见闻、细致入微的细节描述以及有着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作为基础的对于描述材料的安排,使这些都成为了一整套的对于中国乡村书写的方法,而还有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才会成为西方乐于去书写的似乎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他者。而中国早期的乡村研究无疑就是在这样一种范式的引领下展开的。拖累下才把我们的目光向下而只看到了乡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描述,从整体来看,臃肿庞杂而缺少深刻彻底的反思,从具体来说,事无巨细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关联。这在某种程度上迫使研究者与读者“仅仅注意到了乡村内部的细节,而从来不会去考虑乡村以外的世界与这个乡村社会之间的关联性”。[6]
患者女性,59岁,因发现左下腹包块1年余来诊。右下腹触及肿块,大小约12cm×8cm×3cm,质硬,活动度差,边界清,无压痛,无腹痛、腹胀、腹泻、便血等症状。病程中包块无明显增大。患者自起病来,精神、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体重无明显减轻。
我们可以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将村落固定为观察对象,但事实上,村落中的人大多是流动而并非是固守在有一定界限的村落中的,这种流动性与费孝通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强调的乡土性(固着性)共同构成了相对整全的村落生活。换言之,乡村本来就是在有限的闭合性和无限的流动性之间不断循环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空间。[11]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对之前唯独从“封闭的村落的视角”出发的既有的乡村研究做出反思。反思,不意味着抛弃所有由单个村落所提供的分析概念,而更意味着基于对村落的开放性的延展而对其重新思考。[11]
在这种远去(无限的流动性)与归来(有限的闭合性)之间构建起关联是“跨越乡土社会的田野民族志方法论”,是“对既有的过度关注孤立的乡村社会的社区方法论的一种矫正”。[6]139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在内外的相互关照中历史地看出乡村社会的共同性之外构成社会核心特征的差异性。“由归来而远去”可具体到两种游走的民族志田野工作,“一种是身体的游走,一种是心灵的游走”,前者是通过身体的移动看社会的多元形态,后者则要求我们具备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而揭示出“更大范围联系”。[6]141-142基于以上超越地方感的乡土研究才可能找出乡土社会得以存在、地方感得以维系的原因。
对于超越村落的解释体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提出集镇社区的解释框架的施坚雅。他认为,对中国农民而言,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是集镇,而非村落。[12]但总体来说,就地方社会变迁而言,目前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已经经历了“村落—区域—整体性的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等几个阶段,但是在这些描述与比较当中,人们更多留意的是地方社会的当下存在形态,而很少注意到在跟外界接触之后社会形态的转化以及这种转化的动力机制。[13]
依循着远去与归来的思考框架,乡村研究在空间范围上得到了拓展和延伸。那么,如何打破时间上的限制?关于这点,社会问题论者与社会结构论者似乎都有意舍弃时间维度,未能耐心观察事物本身的转化和演进,这也是两者均无法理解中国乡村文化内在动力的根本原因。[10]因而,村落代表性问题的一种新的解决途径是在时间向度上展开的。这种解决途径是将一个村落放置在其演进的生命历程轨道上,由此而感受到一个可以微观把握的村落史。[10]这样事件之间相互关联,并且避免了宏观历史学家借助想象力把不同时空场景下的事件做任意拼接。此一过程强调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深入结合,过程和结构的结合将是理解中国乡村当下变革的两个共变量,任何一个的缺失都会造成理解的片面性,而且找寻不到描述乃至历史事实搜集的意义所在。[10]正如黄应贵所指出的,结构关系的形成,必须由历史过程来理解。[14]在这种方法论的考量上,许多学者将历史性纳入考察做出了研究,其中回访研究最为显著。[注]庄孔韶教授是田野回访的先行者,对此可参见于2000年出版的《银翅》一书。关于回访研究,马丹丹、王晟阳在《中国人类学从田野回访中复兴(1984-2003年)》一文中做出了详细梳理。2003年以后,回访研究也并不鲜见,如赵旭东对于华北庙会的重复访问,其弟子王莎莎于2017年出版的《江村八十年——费孝通与一个江南村落的民族志追溯》等。
然而,贺指出,“认知中国”与“改造中国”正在现实的实践中脱节,这也是当前中国乡村研究出现问题的核心所在。从此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为政策部门提供决策的理论依据,但它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是热衷于和西方对话。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重建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以认识中国为“重要甚至是主要目标”,将为缺少对中国农村的系统的理论认识的政策部门提供理论依据作为重大任务,进而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8]这种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认识中国的学术立场与实践逻辑明显可见于这一派对乡土社会的具体研究中。
中国文明在各种转变的影响下也在发生着转型的态势,我们需要告别过去“实验室的隐喻”的民族志,不再把精力完全置于对村落细致入微的观察及对其功能与结构的把握,而应该站在高处去俯瞰并尝试做出深层次理解。其中,对一个文明做出理解的一个基本考察向度就是其内与外的关系,文明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种,即对立排斥、互不交流与圆融共通。[18]具体而言,这种关联性实际上可以由聚焦法之外的另一个社会研究方法——“线索追溯法”来探寻,这种方法不再是静态观察,而是把人与物放置到某个自然或者人造环境的大背景中,循着它们移动的轨迹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去实现一种在点之上的线和面上的整体宏观理解。[19]这种追溯实现了研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展,也实现了真正超越于村落之外的乡村研究。
二、“常态”与“非常态”的转化
乡村问题研究的局限性明显可见于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乡村研究中,人们更多地是希冀在乡村内部找寻问题的症结,希冀获得长远发展。在找寻的过程中,中国乡村研究多集中于乡村社会中“比较热闹的甚至是非常态的事件”,而较少关注它的日常状态(常态)。[8]尤其在村民自治的展开与“三农”问题凸显的背景下,乡村政治的问题,甚至可能简化至如何治理乡村的问题,似乎成为了导致“三农问题”乃至阻碍乡村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20]也成为了乡村研究的重中之重。
结果语步常用词汇:result,findings,find,result in,indicate,predict,occur,show,suggest,provide,present,demonstrate,include等
需要在支护结构强度达到要求以后进行土方开挖,开挖过程中遵循分区、分块、对称原则,采用阶梯式多层放坡开挖方式,软土区域开挖深度不能超过1.0m,在开挖到设计标高24h内,将砼垫层铺设到支护结构边,挖土到位后,及时对垫层浇筑,避免长时间暴露基坑。
何为乡村治理?在社会学者看来,乡村社会治理有两个基本内涵,即乡村社会秩序形成与维持的途径和过程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实现路径和过程。[21]关于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与维持,许多学者出于乡村差异性的考虑试图对村庄类型做出划分。贺雪峰构建了一个讨论乡村治理状况及类型的基本框架,依据实践中的乡村关系、村庄基本秩序的生产能力和村干部的角色定位三大要素区分出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乡村合谋型和无序型四种类型。[22]王斯福区分了造就出的不同的领导类型的“三种制度类型”。[3]赵旭东则根据构成中国乡村社会权力主体四个社会群体或阶层——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和地方拳头势力——在资源禀赋、权力禀赋和权威占有三个维度上的情况,归纳出了中国村庄的三种基本政治类型,即党政独大型、权力制衡型和自由分散型。[23]
谈及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从国家—社会的向度来看,有关如何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也出现了三种声音:刘涛等人认为在历史上国家对乡村治理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强度。即使在提倡村民自治的当今时代,国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国退民进”的思想并不可取,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交锋不可避免。[24]与此相反,陈锋提出,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所导致的结果,国家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25]陆益龙则选取了一个相对折中的看法,认为由于中国乡村的多样化形态与特征,要实现乡村治理创新就不能局限于“顶层设计”,还需要自下而上的中基层实践创新。[21]
乡村政治究竟是如何生成与落地的?于建嵘曾断言,“‘乡村政治’体制是国家民主化取向的结果”。[26]赵旭东指出,这种大致从80年代在国家层面开始接受的民主观念,是经由一批以政治学为依托而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乡村政治的学者带到乡村政治及其后的乡村治理的研究之中的。这些学者有着强烈地改造乡村政治状况的愿望,他们的研究旨趣的转变经历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的三个阶段。[20]其中,陈柏峰、贺雪峰等人将“内卷化”的概念用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中,陈指出由于基层政府依赖于乡村混混进行乡村治理而对后者保持“战略性容忍”,这样,资源下乡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混混的非法占有而激起了农民的反对,进而造成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逐渐消解,即“乡村治理的内卷化”。[27]贺也认为,地方政府为了将更多的地方存量资源变成流量资源,与地方势力结盟为一个相互配合的全新结构,他们吸干了所有用于农村治理的营养,不断侵蚀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最终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28]
理解,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可能。尽管三个立场之间存在着争论与分流,但理解并不意味着对认识的否定,而是倡导研究走上一条深化认识至理解乡村的道路。具体而言,我们要舍弃那些基于看似孤立的、片面的或静止的现象而对乡村所形成的偏见,不把乡村看成是一个整体存在问题的地点,进而深层次、多方位理解农民多元的个性、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等。
需要指出的是,理解并非是否认乡村存在的问题,任何社会都难免遭遇这类困境,但它们都有各自的解决之道。基于此,我们更应舍弃那类围绕中国乡村未来发展所做出的过于确定性的判断或以此为依据而做出进一步的行动,因为当这种暂时性的判断与行动遭遇时空上的无限延展时,便会显得片面和经不起推敲,更毋庸借此去应对无法预料到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或许平心静气地静观其变,通过理解而把握其背后的结构性转变的根本的做法,才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主流。[44]
“乡村治理”研究所关注的往往是乡村社会的“非常态”,并逐渐成为乡村研究的“学术常态”。然而,在这种研究常态之下,许多乡村自身在常态中发展要素却被“消毒”了,比如具有反思能力与行动能力的农民就被“消毒”了。以乡村政治研究为例,赵旭东指出,当前呈现出来的“权力的离散化”与“权威形态的虚拟化”才是许多乡村政治问题的“总根子”,它们是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道路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要化解这种困境,就需要建设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形态,理清和化解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关键问题。这既涉及国家,更关乎民众。[23]以贵州雷山甘吾苗寨“咙当”仪式为例,当地就以“榔规”而非国家法作为其自治的规范(习惯法),后者更多是深藏于苗民心里的对于维持社区有序运行的内在需求,并借助权威力量的保障而得以延续。[31]
由乡村政治扩展来看权力的“支配-抵抗”研究,这也可称为一种学术常态。然而,此类研究多关注于被外力所“组织化”“政治化”和“策略化”的反抗,却多忽略出于抗争者个人认知、情感的“原始抵抗”。[32]基于这种“所作所为”与“所思所说”之间存在的悖逆,卢晖临在“退思——观历史——察人心”中主张使研究进入到“日常生活中行动者的所思、所想、情绪等等方面去”,换言之,即通过长期观察与往返调查透析农民的心态。[8]
从更广的维度上来看,关于日常生活或者仪式生活中反抗形式的研究也并不全面,也就是说,由福柯发展而来的“抵抗的范式”与斯科特提出的“弱者的武器”这类“支配—抵抗”的对立模式都不足以支撑对异文化整体性与多样性的分析。正如赵旭东所指出的,现实比这种直接的对立更具复杂性,在农民群体内部存在着的分化所引发的不仅是“大历史书写”惯常所用的简单的服从与反抗。那类书写是乡土社会的消毒剂,它使其中的文化以及有着自我反思能力的行动者消失了。[20]根据其在华北地区某村落庙会的考察,村落的日常生活与庙会仪式中存在着平权与等级的相互转化,而这种转化机制就不是“支持—反抗”这类模式可以给出解释的。[33]
抵抗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肯定或强化着既有的权力支配,而他提出的“否定的逻辑”则打破了既有的思维模式僵局,后者既关涉了个体的认知层面,也注意到了平权与等级在不同场景下的转化。就其对华北村落的概括而言,“(农民)日常生活中有对于等级的否定性的心理倾向,然后进入到仪式生活中的明显的等级建构,而这真正应该被看作是表面上通过愉悦的表演而对一种等级的否定,这样一种否定,进而一种新的平权的状态可以通过潜在的结构化状态的瓦解性倾向而得以实现,这开始于作为背景的仪式过程的中间阶段,到了最后的阶段,也就是日常生活之中,这背景逐渐凸显而转化成为了一个图形并从隐藏的背景中涌现出来”。[33]基于以上基础,赵旭东结合布洛克对仪式过程“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实践”的论述,对维克特·特纳(Victor Turner)关于仪式过程的“结构—反结构—结构”的平衡模式作出修正,即“结构—反结构—再(新)结构”。[33]跳出民间信仰的场景,“人类心智中共同存在着一种自我否定倾向”[34],这种倾向在汶川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得以再现。[35]
就乡村政治研究而言,有学者提出,研究“农民政治”,要避开偏重于制度结构的研究,从一个更加生活化的角度来理解“农民的政治行为”。与此同理,乡村研究在整体上对日常状态(常态)的关注也亟待加强。关注于“非常态”的研究取向在林聚任对《社会学研究》自1986-2007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的231篇学术文章的分析中得到确证——农村研究总体上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他在“欠缺对农村社会基本问题的研究”中提出,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多是与较为强劲的经济社会变革相关,但缺乏对更基本的农村社会结构性的或更深层次的问题的研究。[8]
若继受取得说成立,依其定义必须从他人处通过让渡取得权利,这里所指的他人,只能是善意取得关系人中的原权利人或无权处分人,权利只能从原权利人或无权处分人处让渡。
客观性,作为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准则,意味着研究者在描述研究对象及其所处境况时所保持的冷静与疏离。然而,这一准则因人类学功能论的主要代表者马林诺夫斯基私人笔记的公开而受到质疑,随后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出版更是引起深层次的反思。这种反思将书写导向了另一极,“人们开始用各种新的书写方式来表达经典民族志所恪守的客观性观察的不可能。这种反思也间接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反思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到中国,从而带动了一批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开始使用一种更加自由而不受学术概念范畴限制的书写形式……”[20]
三、告别西方眼中的“他者”
在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学者围绕中国乡村研究所展开的分流与反思,除了表现在对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选取上,还明显可见于其对研究立场的选取上。进而言之,中国乡村研究在以上三个维度中存在着左与右的分野。左与右,一般用指政治上的激进与保守:右派的政治倾向于现实主义,其基础是遵循实际的客观性原则,左派的政治倾向于理想主义,其基础是尊重理性的合理性原则,前者从现实出发去建构社会,后者从应当(未来的向往)出发去规定现实。尽管二者存在区别,但同样存在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并且在实践中交错混合、互相转换。基于此,吉登斯提出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这是吉登斯基于全球的政治理念的选择所提出的。在他看来,世界纠缠于各类理念的选择中,并为这些选择所有,而在当今社会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吉登斯认为那些极端化的政治理念会逐渐失去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认可,并提出了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以促使社会按其本性(社会的自然)要求发展。[36-38]
另外,经济领域也存在关于“左”(计划)与“右”(自由)的选择讨论。张小军就曾论证,经济改革不应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为方向,也不能回归计划性市场,而应寻找自由市场和计划性市场两端中间的合适平衡态。[39]这显然也是一条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
方法二:在春笋采收后的笋穴内填埋有机肥等上述材料,视笋穴大小填入有机物,并在每个笋穴内施入0.5 kg左右的竹笋配方肥,然后覆土,使笋穴既有肥力,又通气保湿,诱导竹鞭定向出笋,方便鞭笋采收,并提高其产量。
在此,我们暂且将中国乡村研究划归为“左”“右”以及“超越左右”三种取向。“左”意味着带有理想(计划)主义取向的选择与行动,“右”意味着秉持客观(自由)主义的立场与实践,“超越左右”则意味着回归到乡村本身,倡导一切选择要依循其本性与规律。在实践中,“左”与“右”相互区别又互相转换,因而我们将避免果断地对“左派”与“右派”做出界定,而是指出不同的研究派别较多地带有“左”或“右”的倾向。目前,呈现出“左”“右”与“超越左右”的研究倾向的分别是:以改造中国为目的而认识中国的“乡建派”,从理论的角度出发为勾勒中国结构而进行描述与研究的“学院派”和以认识中国为基础进而实现理解中国的“理解派”。
“乡建派”大致可追溯至民国时期,在晏阳初看来,中国乡村的问题在于农民“愚、贫、弱、私”,他及其后迎合民族改造浪潮的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对人的改造来解决农村及农民的诸多问题。这类话语随后影响着更多人的思维;“他们大多都会相信这样的界定,进而会支持对于乡村以及农民的进一步改造。即便是今天,延续这类思考的知识分子还是大有人在”。[10]
现代乡建派主要代表贺雪峰认为,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应该继承的“三大遗产”,他们的共同点是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他们从事理论研究就是要在认识中国的前提下达到改造和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具体而言,“三大遗产”的共同点是“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统一,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造中国社会和建设中国社会,而没有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的目标,认识中国社会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8]
事实上,乡土中国的研究也仅仅是对中国进行认识与理解的一个途径而已。赵旭东、齐钊曾对费孝通乡土中国这条线索以外的山川的关注历程做出了勾勒与论述,进而指出要想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有更加全面而透彻的认识与理解,就要跳出乡土中国的阈限,将视野拓展到山川之灵的独特性与超越性上。[15]这是一种由人到物的翻转——从过度以人为中心的关注翻转到人对诸如江河、山川等自然物以及人造物的关联考察上来,以物观人。[16]田阡就试图论证西南学术研究应该从社区研究转向区域研究,从族群研究转向流域研究。[17]
显然,乡建派所批判的,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学术话语影响的“学院派”。不同于“晏阳初模式”影响下的乡建派,学院派没有“中国乡村存在问题”以及“中国乡村亟待改造”的意识与实践,而是试图在一些既有的西方观念下勾勒出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与乡建派所承担的“社会医生”的角色不同,学院派更像是“摄影师”,强调并追求描述与记录的客观性。[10]
显然,将非常态事件的分析作为研究常态并将之用于整体乡村社会的判断与认识是不够全面的,而以局限在村落内部却缺少关系视角的细致观察来理解中国更是无从谈起,因为,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都是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吴重庆认为,在认识中国的层面上,关注常态的作用并不小于对非常态的关注。[8]换言之,只有兼顾乡村的“常态生活”与“非常态事件”才是理解中国的前提。
尽管具体的书写与表达可能不同,但它们多是通过实地的调查提出乡村的实际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而为“乡建派”提供了更多关于农村“问题”的新材料以及与外部进行对话的凭据。基于此,乡建派学者将关注点放到乡村社会的改造,尤其是人的改造上,这意味着他们是具有“行动主义”倾向的。要认识中国,就要深入社会内部;同理,要认识乡村,就要以大量的农村调查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行动(实用)主义的取向使得他们的认识忽视了学理本身的争论而直接观照他们所看到的现实。
作为研究者,目前我们最需要做的,还是“以先期获得的文化理解来帮助后期当地人社会问题的解决”[20],摆脱无休止的流派争论,寻求在多学科交流合作的基础上,透过对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的表象的认识,抓住其何以可能的发生机制与可能影响,进而为理解乡土社会的现状与走向作出反思和提供依据。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乡建派思想武器的“三大遗产”具体在改造路径与方式的选取上也不尽相同:毛泽东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其依循的是“破坏与建设”的辩证关系;梁漱溟则以传统文化为思想来源,主张用“文化改造”来为“文化失调”的中国寻找一条道路,其依循的是“改良与渐进”的发展模式。[41]不同于梁漱溟的文化改造,费孝通倡导从经济建设出发,通过分散的乡土工业逐步地提高农民实际的生活水准。总体而言,尽管手段不同,毛泽东、梁漱溟都选取了“由外而内”的改造路径,不同于二者,费孝通选取了“由内而外”的改造路径。[42]
项目总投资1.85×106元,其中,除臭风机及生物土壤滤池本体系统约8.5×105元。渗沥液处理站O池生物土壤除臭系统工程具有如下特点:①工程所采用生物土壤除臭系统除臭效果稳定可靠。有效解决了渗沥液处理站恶臭污染,提升了环境空气质量;②运行成本低。除风机电耗、少量水耗及风机皮带更换费用外无其他费用;③系统自动化程度高,可做到无人值守。系统维护工作量小,不会增加运行人员工作强度;④环境美观度好,工程项目设置后,不占用厂区绿化用地;⑤环境友好性好,无二次污染。项目无污染物产生,滤料使用寿命20 a,使用期内无需更换滤料。
目前倡导对社会加以改造的实践者多选取“由外而内”的路径,他们在这一路径中所展开的具体行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以改造中国为目的而认识中国的立场就引起“理解派”的反思与批评。赵旭东指出,它实际上沿用的是医生治疗病人的逻辑,视农民为有“病”的,需要加以诊断和治疗的。[10]事实上,中国近三十年的乡村研究也是笼罩在这种“问题解决”的思考范式之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做了一些关于乡村的调查,以现代城市的眼光去审视传统的乡村。它们延续了自晏阳初以来的对中国乡村的整体看法,把乡村界定为一个问题的乡村,并基于此种判断积极地主张对其进行改造。[20]
对于这一批评,贺雪峰主要针对“乡村是否是有问题的”与“中国学者是否应该干涉与该怎样行动”做出了回应。在他看来,乡村建设者本身未必是乡村研究者,因而若他们不认为乡村有问题,也就没有了开展“乡村建设”的必要,进而更明确指出了乡村是存在问题的,“当前的中国乡村乃至中国当然是成为问题的,不然为何要建设为何要改造?”[8]关于第二个问题,贺指出“为学术而学术”是必要的,但要以在认识农村的基础上为其改造提供理论基础为目的,这也是他所重申的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任务。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改造中国”的目标是有助于“认识中国”的。现在我们要反思对研究产生不利影响的实践关怀,但不意味着要将其取消,甚至更应该从正面的角度考虑它的积极作用。
在围绕“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所展开的讨论中,吴重庆认为,声称“认识中国”是为了“改造中国”是没有必要的,研究者更应该将关注点集中在“认识中国”上,当他们不以“改造中国”为目的时或许更有利于揭示中国的问题。[8]卢晖临也表示,当人们的“改造”愿望过于强烈时,很容易走偏,这就需要在认识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冷却阶段”。[8]文军则更强调学者的角色定位,认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而在当前提“改造中国”并不合适。[8]庄孔韶未直接谈及这两种取向,但指出当面对外部的干预乃至强制所导致的快速的文化变迁所导致的族群—文化主体性的失落之时,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为这些族群争取“文化适应期”。[8]
重回“乡村是否是有问题的”的讨论上来看,乡村何以成为问题?也许,这并非它自身的问题,而是一种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时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的折射,是一种“文明的碰撞”。[20]但这些学者借助书写而将他们所认识到的“乡村问题”固化,农民的生活成了“散漫、混乱、缺乏凝聚力甚至是极端苦难的”,而必须寻求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外力施以援手才能摆脱这种窘境。这样的书写使农民主体丧失了发声的权力转而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更为严重的是,许多问题都是外来者所想象出来的,或者是从农民那里得到的以印证他们先验假设的非核心问题。
这种做法欠缺对农民自身需求和认知的考虑[43],而中国乡村研究不再是“自己看自己”的生活实践,转而采用了一种类似于“西方的他者”这类“遥远的他者”的视角。简言之,这是一种“颠倒的认识论”——把近距离的自己看成他者。[20]在这种意义上,将乡村界定为有问题的、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实际上是从政治层面上迎合了西方对于现代社会模式的想象与界定。
在庄孔韶看来,不管是“诠释性的理解研究”(学术派导向),还是“参与性的社会实践”(乡建派导向),乡村社会研究都与“游猎、游耕、游牧和定居农业上不同族群与文化的传统多样性存在和面临全球化市场经济干预下的变迁及适应问题”紧密相关。为避免中国乡村落入“全盘文化替代的结局”,各个学科应该综合研究和梳理因市场经济推进而使中国农村社会急剧变迁而造成的文化中断现象,找到“应对世界剧变而又获得身心健康发展的途径”。基于此种意义,“积极参与乡村社会的学理分析”和“社会之参与实践”是互渗和互补的。[8]
显然,单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为了勾勒中国结构而有的描述与研究,或者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认知中国,似乎都丢掉了一份社会人类学研究原本应承担的责任——抛开表象,如何理解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着什么?它们对谁更为有益?显然,要承担这份理解中国乡村的责任,乡建派与学院派既不能沉迷于自我封闭与孤芳自赏,也不能汲汲于社会的改造与重建,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可以对接的契合点,并由此展开讨论。这样,或许才能够回到中国问题的根本上去。[10]
(2)水稳定性。当沥青路面中存在水时,在温湿循环及重复车辆荷载作用下,使得集料与胶结料之间的黏结力降低,沥青胶结料本身黏聚力下降[2],在重复车辆荷载作用下,导致路面结构性破坏和使用功能降低,并诱发其他病害。因此,本文通过浸水马歇尔试验评价TPS排水沥青混合料的水稳定性,TPS排水沥青混合料水稳定性试验结果如表5所示。
金玉妍福了一福,又与苏绿筠见了平礼,方腻声道:“妹妹也觉得奇怪,高姐姐一向温柔可人,哪怕从前在潜邸中也和侧福晋置气,却也不至如此。难道一进宫中,人人的脾气都见长了么?”
从乡村社会自身的角度来看,它也存在着一种需要被理解的自然状态,但那显然不合于主流的政治话语。[20]换言之,理解所蕴涵的并非是一种“表达”与“被表达”的非均衡的权力关系。因为那种关系很可能导致乡村沦为亟待现代性拯救、改造、甚至替代的他者,而隐含其中的结构性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终将阻碍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20]
在赵旭东看来,一些学者在接受“治理”“内卷化”这一概念时缺少反思。“内卷化”这个概念是沿着“格尔茨—黄宗智—杜赞奇”的线路传入中国的,追溯其词源意义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争议可见,将其套用到乡村政治的领域中存在很深的“误读性”。[29-30]而他们用“治理”这个“西方自16世纪以来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的统治术的现代形式”分析中国乡村的社会与政治时,取消了“地方自治”的观念。[20]换言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受西方文化传统长期浸润的“治理”一词直接套用在了现实的中国社会,基于现代性观念所塑造的“中国城市文明的他者”的乡村印象,使我们极容易回到把乡村看成是“有问题的乡村”这个范式怪圈,而缺乏对乡土社会的真正理解。[20]
换言之,与学院派相比,乡建派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似乎是一种冲破与摆脱西方思想的影响与束缚的力量。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对“特殊性”的强调使他们闲置甚至抛弃无法直接应用于中国实际的西方理论,由此直接描述中国的“现实”。[40]但这类现实很可能会由于他们预先所带着的偏见而有所局限,即选取某一个发展片段来代表整个连续事件,并将之误读成整个社会。[10]这类“现实”随之成为“乡村存在问题,乡村需要改造”的重要依据。基于此,就问题意识而言,他们更多的是“从政治的层面上迎合西方对于现代社会所应该具有的治理模式的界定”。[20]由上观之,“乡建派”与“学院派”似乎都未从西方观念的牢笼中逃脱。
四、城乡关系:理解乡村的一个面向
跳出聚焦于乡村,乃至乡村非常态事件的研究路径,我们可以将城乡关系展开为理解乡村的一个面向。就中国的乡村及其社会发展所集中凸显的“三农”问题而言,它之所以成为问题,也是因为人们聚焦于乡村自身的问题,尤其是非常态事件,认为它亟待改造,而未能甚至不肯承认隐藏于表象之下的更为深层次的城乡结构关系的断裂,或者是中国所特有的户口制度下形成的本来就无法彻底根除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11]
在每次课结尾部分,我想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补充相应的空中乘务英语的内容,为此我网购了两本空乘英语的课本,以补充课外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这样学生会对我的课更感兴趣,我教起来也更有成就感。
城乡关系的断裂所导致的差距与中国社会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变,包括城乡关系的转变相联系。在这种关系的转变中,城市持续地从乡村社会抽血,长期的后果是造成其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但是一旦结果造成了,想要恢复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实现的。[45]这种抽血的过程是在“极端发展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在经济政策上偏重城市与重工业,积极推动了农业集体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的差价交换及限制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等以农辅工的产业发展政策,利用农业剩余实现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46]
显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它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即解决工业化的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城市化问题。[47]这一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供销体系基本上在最低生活标准的前提下满足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然而代价却是乡村因不断向城市输血而造成自身失血过多,元气大伤,各类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
弗兰克曾提出,阻碍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已开发国家与低度开发国家间的结构性依赖关系造成的。中国的城乡之间似乎也隐含了这样一层关系,这种关系的指向存在双向性。城乡之间在经济层面的落差以供销系统的失衡而愈发凸显,从乡村“销”入到城市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保障生产的农民,这甚至引发了乡村何以可能的现实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在城市牵引力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刺激下,农村呈现出“空心化”和“过疏化”等情况。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在经历了近代急剧的文化和社会转型之后,乡土社会的关系性日渐松散。闫云翔在对下岬村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概念。[48]与之对应的,贺雪峰在新的社会场景下试图对费孝通的“熟人社会”概念进行修正,并提出了“半熟人社会”的概念[49],吴重庆则提出“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50]基于此类判断,许多学者从不同立场出发提出向农村输血的策略。然而,从近三十年的输血来看,中国农村的发展经历了开发式扶贫、可持续发展、城市化道路、参与式发展等各种话语,但仍未脱离西方话语与西方思想的权力支配,它所追寻的仍然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式。[51]
事实上,农民在城乡之间循环往复的运动为我们理解农民与农村提供了一条可供追溯的线索。[52]赵旭东认为,上述研究与判断应该建立在一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即乡村社会原本就一定是非原子化的?非原子化的村落共同体的概念,其实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及其在生活形态的对立之上的,而这种城乡对立的做法早就受到质疑与挑战。因而,原子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尚且缺乏宏观比较,以其为基础而提出的“半熟人社会”更加没有全面看到乡土社会中的“远去”与“归来”。
王铭铭将其阐释为“居“与”游“,赵旭东则将其概括为“远去”与“归来”。[53]远去与归来紧密联系,二者之间的循环构成了人类自农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生存方式,即受土地束缚的人们固着在乡土社会之中,但同时还有多种因素迫使他们离开土地而过着一种类似游民的生活,并以此来补充土地相对贫乏的供给。[6]然而,在“‘荣归故里’的召唤与外乡生活的排挤下,离开土地的人大多并不会割断与故土的联系,而在远去与归来之间保持着一种循环往复的律动”。[54]他们会赚钱养家,也会在打工收入不足的时候以土地来作为基本的生活来源。换而言之,现代中国移民不再是工业代替农业的问题,而是相互补充、共同维系的问题。这种关系是农民在现代情境下对费孝通先生曾论述到的乡村工业与农业关系所作的调试与转型。[55][56]
围绕人口外迁的问题,黄应贵指出,在工业化、都市化与全球化冲击下的农村,因人口外移、当地生计凋落等现象,让我们容易有农村社会没落乃至崩解的印象,但实际上它可能已在形成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型态,而不再是有关农村兴衰的问题。[57]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型态而衍生的新的文化形式,就是“文化再创造”的形式与过程。其中,包括黄应贵称之为“基于两地社会(bilocal society)而来的新文化”,以阿美族人为例,他们同时在台湾大社会的中心大都会与边陲居地建立家园,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57]这种对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或异化,以及都市化吸纳农村大众后所造成人与土地疏离而产生的“去地域化”的否定与反抗,还可见于兴起于1980年代并于199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的会灵山运动。[57]
目前百色学院文传学院、外语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体育学院等相继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民俗学、民间文学、方言研究、民族宗教、民俗文化与表演、壮族原生态音乐、右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民间扎染制作、壮族传统体育文化等课程,有了较好的基础,今后应将把上述课程系统化和常态化,并组织教师撰写校本教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打下人才基础。
金色等同于俗气?NO!其实只要不大面积使用金色就好。比如以金色链背包提气点缀,妆容上再配以正红色口红,复古怀旧,铿锵妩媚,自是胭脂水粉难以匹敌的美丽。
这些案例进一步验证了萨林斯的论述,他曾指出,原住民社会透过循环式移动在大都会的中心得以吸收全球化或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好处,扩展原有的边陲社会之聚落或社会秩序到城市,使两个地区的家园相互弥补,以创造出新的文化。[57]这种文化普遍因过去研究者强调都市与乡村观念上的对立而被忽视。在此种意义上,原子化的趋势(远去)与共同体的周期性的恢复(归来)共同构成了村落生活的全貌。[20]
事实上,黄应贵等人的上述观点都源自于对隐藏于城乡关系背后的乡村文化的关注。正如格尔茨曾指出的,不能忽视根本上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铺平的道路,一些介于经济过程与非经济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其他关系相比更是几乎不变的,我们必须设想存在着与经济合理化相关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真正规律。[58]文化机制作为社会转型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逻辑,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式,是社会转型的本质,而文化转型则以社会转型为动因和表征,实践着文明进程意义上的变迁。[59]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何理解和应对因市场经济推进使中国农村社会急剧变迁而造成的暂时性的“文化中断”?输血要以农村自发的造血机能的恢复为目的。对此,黄应贵所提的“文化再创造”有助于我们摆脱传统与现代这样的两极思维,摆脱掉对工业化、都市化乃至全球化的入侵性与压制性与地方社会的被动性的刻板印象。这种对“文化的再创造”的强调为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经济,乃至整个中国乡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它强调了地方(乡村)社会自身的动力转化机制(不确定性)及确保这种转化成为可能的结构(确定性)。[13]这是“一种来自地方(乡村)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力量”,也即“乡村的创造性转化”。这也就是萨林斯所坚持的文化本身的自主性。[14]218-219在中国的语境中,林毓生曾将之表述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张士闪则突出礼俗互动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提倡“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障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60]在此类表述中,我们均可透视文化的韧性与活力。
乡村文化的韧性与活力,刺激我们重新审视定位。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要想真正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保障“双轨制”两条道路的并行不悖,从“农民的视角”出发,相信他们拥有自身的智慧与转化危机的能力,自下而上地来靠农民自己解决问题。乡村的治理如此,乡村经济的发展亦然。即便在今天,在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大背景有了一种较为清晰化认识的情况下,我们所应该做的,也不是改造农民,而是辅助农民。
五、超越左与右:中国乡村研究取向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乡村研究的“左”“右”以及“超越左右”这三种取向,分别对应以改造中国为目的而认识中国的“乡建派”,从理论的角度出发为勾勒中国结构而进行描述与研究的“学院派”和以认识中国为基础进而实现理解中国的“理解派”。乡建派对应的往往是聚焦于村落的非常态事件、具有行动主义倾向的改造者,学院派对应的则试图基于村落常态生活而勾勒出社会结构的记录者,二者相互区别又互相转换,但不能否认的是,都存在局限。基于此,我们提出超越二者并使其达成合作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思,意味着超越限定在“固化”的村庄之内的分析概念,通过线索追溯将开放性与历史性纳入考量;它也意味着研究者既关注常态研究中的非常态事件,又将目光投射到非常态研究所嵌入的日常生活;它还意味着立场上的转换,从“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哪个为重的争论中跳脱出来,舍弃将乡村视为是“有问题的”这类看法,探寻理解中国的方式与方法。
该次实验经SPSS 21.0统计学软件处理所获取的相关数据,其计量资料表现形式为(±s),二者对比研究以t为标准完成检验;其计数资料表现形式为[n(%)],二者对比研究以χ2为标准完成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基于第三条道路在方法、对象与立场上的展开,我们所探寻的更多是文化转型背景下针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不走极端的另一种可能。理解,是实现这种可能的必要手段。为此,我们要警惕那些在遭遇时空延展时可能会显得片面和经不起推敲的暂时性的判断与行动。具体而言,要舍弃那类围绕中国乡村未来的发展所做出的过于确定性的判断或以此为依据而设定的实践,而选择静观其变以把握其背后的结构性转变。
回溯以往中国乡村研究的对象、立场和方法,我们更加意识到超越左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通过理解,实现超越,达成合作,循环往复。当我们找准定位,超越既有的主流认识,不再将乡村限定为一个孤立的、静止的、片面(有问题)的存在,而是以历史性、开放性与日常性的眼光,在时空的脉络中不带偏见、不怀判断地去理解乡村时,或许才更能走上一条能够真正理解这个转型社会的最优路径。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9.
[2]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M]//人类学高级论坛2012卷: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2012.
[3]王斯福.什么是村落?[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5-32.
[4]庄孔韶.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22.
[5]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M]//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04.
[6]赵旭东.远去与归来——一种跨越乡土社会的田野民族志方法论[J].西北民族研究,2009,(1):131-142.
[7]李怡婷,赵旭东.一个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1922-195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再分析[M]//乡村中国评论(第3辑).青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61-306.
[8]庄孔韶,赵旭东,贺雪峰,等.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J].开放时代,2008(6):5-21.
[9]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J].读书,1990(10):8.
[10]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8(3):110-117.
[11]赵旭东.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解释框架[J].开放时代,2011(12):99-112.
[12]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7.
[13]赵旭东.乡村的创造性转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89-191.
[14]黄应贵.返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5]齐钊,赵旭东.乡土之实与山川之灵——以费孝通为例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两重性的再省思[J].西北民族研究,2014(1):165-174.
[16]赵旭东.中国人类学为什么会远离江河文明?[J].思想战线,2014(1):76.
[17]田阡.重观西南:走向以流域为路径的跨学科区域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2-86.
[18]赵旭东.从文野之别到圆融共通——三种文明互动形式下中国人类学的使命[J].西北民族研究,2015(2):44-61.
[19]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J].民族研究,2015(1):48.
[20]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J].社会科学,2009(2):53-63.
[21]陆益龙.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现实基础、主要问题与实现路径[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101-108.
[22]贺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42-50.
[23]赵旭东,辛允星.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 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J].社会科学,2010(6):63-68.
[24]刘涛,王震.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7(5):57-64.
[25]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95.
[26]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23.
[27]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28]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1(2):86-101.
[29]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5):91-110.
[30]赵旭东.乡村理解的贫困——兼评陈柏峰《乡村江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87-190.
[31]赵旭东,周恩宇.“榔规”运行的文化机制—以贵州雷山甘吾苗寨“咙当”仪式为例[J].民族研究,2014(1):71-77.
[32] 李晨璐,赵旭东.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J].社会,2012(5):179-193.
[33] 赵旭东.否定的逻辑——华北村落庙会中平权与等级的社会认知基础[J].开放时代,2008(4):126-146.
[34] 赵旭东.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243.
[35]赵旭东,辛允星.否定的逻辑:汶川地震灾区民众的情感认知冲突及其转换[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57-164.
[36]赵旭东.结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89-227.
[37]赵旭东.不走极端才会良性发展[N].社会科学报,2016-07-14.
[38]陈华兴.社会的自然——论吉登斯超越左右的政治[J].浙江学刊,2006(6):42-49.
[39]张小军.文化经济学的视野:“私有化”与“市场化”反思——兼论“广义科斯定理”和产权公平[J].江苏社会科学,2011(6):1-12.
[40]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1):210-223.
[41]时广东.梁漱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趋同和差异[J].社会科学研究,1996(6):105-111.
[42]耿达.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33-140.
[43]叶敬忠.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8-156.
[44]赵旭东.从追溯和回顾中理解中国乡村[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1):80-85.
[45]赵旭东.乡村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重新回味费孝通的“双轨制”[J].探索与争鸣,2008(9):43-46.
[46] 赵旭东,朱天谱.反思发展主义:基于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5-11.
[47]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4):37-46.
[48]闫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9]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0]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J].开放时代,2002(2):121-122.
[51]张有春.贫困、发展与文化:一个农村扶贫规划项目的人类学考察[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221.
[52]赵旭东,罗士泂.游离于城乡之间——文化转型视角下作为行动者的中国农民[J].学术界,2006(11):42-54.
[53] 王铭铭.居与游[M]//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4-213.
[54]赵旭东,张文潇.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6-37.
[55]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M]//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56]费孝通.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J].观察,1947(11):8.
[57]黄应贵.农村社会的崩解?当代台湾农村新发展的启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10.
[58]Clifford, G.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143-146.
[59]周大鸣,陈世明.从乡村到城市:文化转型的视角——以广东东莞虎门为例[J].社会发展研究,2016(2):1-16.
[60]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J].民俗研究,2016(6):14-24.
TheThirdWayofChineseRuralStudy:AReviewandRefle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alTransformationandAnthropology
ZHANG Wenxiao1, ZHAO Xudong2, LUO Shijiong2
(1.DepartmentofPublicAdministration,BeijingCity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2.InstituteofAnthropolog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The rural area is a mirror reflects China. In the age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standing rural society becomes especially importan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new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s are arising in rural areas. In the pursuit of understanding them, we propose to view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living world around them from the historical, the open and the gener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etrospection of and reflection on the method, object and position of Chinese rural study. Once we neglect the subjectivity of either of them or the time-space dimension which they embedded in, we would sink into the vortex of choosing “left” or “right”, or falls into the trap of repeating temporary decisions, while neither of them seems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is sense, we should adopt the third way proposed by Giddens, specifically, to avoid extremes can lead a sound development.
Keywords: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reflection; understanding; rural study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2-0095-11
收稿日期:2019-0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乡村社会重建与治理创新研究”(16JJD840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文潇,女,河北承德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乡村研究等。
赵旭东,男,浙江桐庐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与法律人类学、乡村研究、文化人娄学等。
罗士泂,男,江西泰和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社会。
(责任编辑:王勤美)
标签:乡村论文; 中国论文; 社会论文; 村落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乡村社会重建与治理创新研究”(16JJD840015)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部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