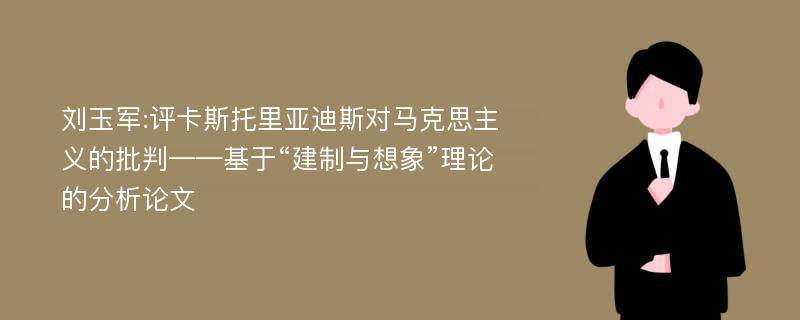
摘要:基于自己的“建制与想象”的理论,卡斯托里亚迪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责为“功能-经济”视角的理论,并据此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结构/上层建筑”结构、关于阶级理论和关于异化理论的批判,这种批判关联着对近代社会功能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科层制的批判。虽然他的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但这种批判建立在原生想象的基础上,最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导致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态度。
关键词:卡斯托里亚迪斯; 想象; 建制; 马克思主义
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作为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同其他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理论家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和重新审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基于他“建制与想象”及其二者的关系的理论而进行的。本文将透过他的“建制与想象”理论来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质疑和逃离的过程,也通过他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质疑和逃离的过程来理解他的“建制与想象”理论,并从这种双重的审视中指出卡斯托里亚迪斯理论的缺陷和他对马克思主义指责的错谬之处,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根据类似工程资料,NM360耐磨性能不低于普通钢板的两倍。其焊接性能与普通钢板类似,但其可切削性能较低,尤其是钻孔比普通钢板略困难。根据笔者调研,在过煤面较大的螺旋溜槽入料段以及刮板输送机槽箱内采用该耐磨衬板效果良好。
一、关于“基础结构/上层建筑”结构的批判
作为后结构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作为一个建构主义者,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自我立足点在于他的“建制与想象”及二者关系的理论。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社会历史的运作是一种想象建制的过程,它始终处于一种由想象或社会想象所产生的建制与被建制的动态张力之中。具体说,这种想象建制的观点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1)卡斯托里亚迪斯假设了一种原生想象(radical imaginary),这种原生想象是从康德的本源性想象那里发展而来,相对于再生想象或者联想而言的,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本源性创造性想象,是一种对于社会历史的“积极的构造”。(2)原生想象构成了符号和实际想象的共同根,引发着社会建制。“建制是一种社会上认可的、符号的网络,在该网络内,一种功能成分和一种想象成分以不定的比例和关系结合在一起。”[1]132这就是说,由原生想象所引发和生成的社会建制或符号化的网络,一方面沿着“功能性的”“集合-同一化的”(ensemblistic-identitary)“逻辑的”的维度展开,构成了社会建制的确定性、限定性和规定性之维,另一方面沿着实际想象(the actual imaginary)、符号意指(signification)维度展开,构成了社会建制的不确定性维度。(3)建制或者符号的功能性或逻辑方面对于一个社会运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建制的象征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功能方面。他认为,人与动物不同,人是有渴求的动物,人的需要总是超出“纯粹的生物需要”,人总是通过自身的原生想象追求象征的意义,追求文化的诗性之维。在这里,建制-符号的展开遵从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结合的“任意性”,表现为“符号的多元决定” (the over-determination of symbols)和“意义的多元符号化”(the over-symbolization of meaning)现象,呈现着社会历史实在的不确定性。基于此,他指责马克思主义者以一种“功能-经济”视角来看待建制。这种视角不仅把建制的实存和它的特征还原为建制所履行的功能,而且把建制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还原为“经济”功能。卡斯托里亚迪斯正是不满意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功能-经济”视角的理论,从而其理论观点充斥着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结构/上层建筑”的批判。
(一)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具有同质性,否定经济结构的“居先性”
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不论人们是有意识地创造一种建制来满足一种特殊功能的必然性,还是 “偶然”涌现的结果使建制得以存在和社会得以生存,或者社会要求满足一种特殊的功能来控制碰巧发生在那儿的事情,抑或上帝、理性、历史逻辑已经组织且继续支配社会及其相应的建制,这些都是一种功能性表现。所谓的功能性,就是“手段与目的或一般层面的原因与结果的不间断的链条,在属于建制的特征与考虑的社会的‘现实’需要之间的严格对应,简而言之,重点在于一种‘现实的’与一种‘合理-功能的’要素之间完整的和不间断的循环”[1]116。这种功能主义的主要主张,往往忽视了象征主义的作用和重要性,只是将象征主义视做一种中性的、表面的覆盖物,视做一种全然足以表达一种先在内容的、社会关系的“真正实质”的工具。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之前就已经构成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或实质就是“基础结构”,建制的象征主义隶属于“上层建筑”,“基础结构”决定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于和表达着“基础结构”,建制的象征主义作为上层建筑,“是一种‘中性的’或‘足够的’功能性表达,即基础社会关系的‘实质’的表达”[1]124。在这里,卡斯托里亚迪斯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上层建筑”视做了“基础结构”的附属物,基于此,他指责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宗教的作用,仅仅把宗教视做一种虚假-结构、或者一种副现象,仅仅是经济的附属物或者中性的覆盖物。
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具有同质性,都是一种想象建制的要素,不存在经济结构的“居先性”。在他看来,对“基础结构/上层建筑”的理解,不能像新康德主义者那样将二者颠倒过来,让“观念”或“意识形态”处于“居先”或者“决定性”的位置,这不是一种一个对另一个的“居先”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要素问题”。正如“基础结构”这个词语所指出的,它本身已经是结构的,本身已经是一种结构、一种建制。他认为,在社会范围内表达的生产关系,“根据事实本身意指一种网络,即现实的和符号的网络,它是自我认可的——因此是一种建制。”[1]124因此,卡斯托里亚迪斯把生产关系或基础结构也作为一种建制,它与上层建筑一样,构成社会历史的要素,具有同质性,在这种情况下,否定“基础结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社会历史演进的矛盾结构和历史规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2.随堂测试成绩比较:LBL+CBL组学员在EUS基础知识、操作要点、胆胰局部解剖学及典型胆胰疾病图的分析、EUS下诊断等方面的平均分数明显高于LBL组和CBL组[(92.3±3.5)分比(85.5±5.6)、(88.2±4.7)分],但在典型图例分析方面,CBL组明显高于LBL+CBL组和LBL组[(94.4±5.2)分比(83.7±3.5)、(82.6±2.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批判,同样也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经济”视角的指责,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了想象的作用。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马克思主义把想象作用视做一种功能性作用,视做“一种‘经济’链条上的‘非经济’环节”。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想象的作用,仅仅强调了经济的基础作用。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还强调人类在历史上经济从史前史到共产主义延伸阶段的暂时匮乏,以及技术的不成熟性,而且这种“匮乏”引起异化,“匮乏是异化的充分必要条件”[1]132。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技术发展或者经济丰富的程度是不能够被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没有它们存在的理由,换句话说,经济上的匮乏和技术的不成熟不能够引起异化。卡斯托里亚迪斯抛弃了经济是异化的根源之后,他把异化的根源归于想象,他认为,想象在历史上是创造的根源,也是异化的根源,因为异化跟创造一样,都预设了赋予其自身所不是的东西的能力。
(二)卡斯托里亚迪斯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而彻底否定“基础结构/上层建筑”结构
本文对比了基于严重拥堵里程比例和基于行程时间比的交通指数计算模型,分析了两种模型在不同区域范围的适用性,确立了小区域更宜采用行程时间比的方法计算交通指数,对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共32个街道进行了典型工作日的交通指数计算. 为分析不同街道的交通运行特征,利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对所有街道的工作日交通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得出了5种典型特征的街道指数模式曲线,从出行特征、交通需求、用地类型等角度,对不同类型街道的模式曲线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交通运行特征. 该研究成果可服务于北京市精细化交通治理工作,在数据条件丰富的情况下,评价范围可从核心区扩展到全市,为不同类型的街道交通管理和拥堵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二、关于阶级理论的批判
第一个图式在于,将阶级本身的实存与经济的一般状态即一种仍然不充分的“剩余”的实存联结在一起。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演进的始端假定了一种“绝对匮乏”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人们不能生产出任何种类的剩余,固然就不会出现剥削群体。他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假定了一种生物的最低限度(biological minimum),由于这个最低限度,人们既不会被饿死,也不会受到剥削;在社会演进的末端,假定了一种“绝对丰富”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剥削也就不会存在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一种“相对匮乏”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足以维持一种剩余,从而维持一种剥削,维持着阶级,而被剥削阶级却在被剥削后只能被还原为“生物的最低限度”。卡斯托里亚迪斯对这个图式给予了质疑,他认为,即便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出现剥削,这种剥削的出现也未必是必然的,或者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即便出现了“剩余”,这种剩余也很可能在增加整体部落福祉过程中被重新吸收,或者可能成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构成部分。如果原始社会“生物的最低限度”存在,那么在这个无阶级的社会里,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力标准就不会进步了。他怀疑“生物的最低限度”是否能够被界定,被剥削阶级是否能够被还原为“生物的最低限度”,如果它被还原为“生物的最低限度”,那么我们就把被剥削阶级仅仅还原为与“它的食物有关的人类集体”,这在历史上是不现实的,因为人类集体除了食物的需要,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需要。总之,卡斯托里亚迪斯对这个图式给予了各种怀疑和否定。第二个图式在于,将每种社会划分的精确形态与一种给定的技术状态联结在一起。马克思曾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142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存在着每个社会的技术为它的阶级划分奠基的情况,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这种奠基是非常困难的,他给予了否认。卡斯托里亚迪斯说,“四千年的埃及历史不可以还原为尼罗河四千个季节的灌溉,也不可还原为用于控制灌溉的不同方式”[1]152,社会关系不能还原为大多数国家基本相同的农业技术,封建领主的实存不能还原成那个时代的生产技术特征,从而对这个图式给予了质疑和否认。
甲亢的发病因素有很多,包括遗传、社会因素、环境、免疫系统等[5-7]。临床上一般使用抗甲状腺药物进行治疗,有经济、方便等特点[8]。甲巯咪唑是常用的甲状腺抑制剂,具有维持时间久、代谢慢、起效快等优点[9,10]。对中度及轻度甲状腺患者非常适用,本文两组患者均使用甲硫咪唑进行治疗,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后效果良好,甲状腺功能得到了一定恢复。但使用单一药物进行治疗的复发率很高,高达55%-64%[11],且抗甲状腺药物具有肝损伤、白细胞减低等副反应。所以,为患者寻找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72,“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2]284。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分析世界和改造世界过去曾经且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阶级理论背后所隐藏的是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当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存在着向“功能-经济”视角的还原时,他也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着向“阶级”的还原。
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异化既不是为历史所固有的,也不是建制的实存本身。然而,异化表现为一种与建制的关系模态(modality),以及通过建制媒介,呈现为与历史的关系的模态”[1]115。异化因想象具有赋予其自身所不是的东西的能力,凭借“建制”的媒介引起异化。有如我们所知,建制是一种符号的网络,在这种网络里,一种功能成分和一种想象成分以不定的比例和关系结合在一起。“当想象要素在建制中成为自治的并占支配地位时,异化就会发生,这导致建制对社会来说成为自治的并占支配地位。建制这种成为自治的或者自治化,以社会生活物质本性的方式来表达和体现,但它总是同时预设,社会在想象的模式中使它的关系与它的建制生存在一起,换句话说,它在建制的想象中没有认识到成为它自身产物的东西。”[1]132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语境中,建制的象征主义因为关联着自然也关联着历史而具有合理性。但在当代社会,原生想象的创造性和生产性趋向停滞,并且在建制的过程中,完全脱离了自然和历史这个社会现实,任由实际想象或想象的要素占据支配地位,这时建制就发生固化、僵化、结晶化和自治化,这种建制的自治化对人类来说,就是一种他治和异化。这种异化现象在当代世界中主要表现为理性的膨胀和官僚制的盛行。
否定了“经济”的基础地位,也就否定了“利益”,自然也就要否定阶级的真实内涵。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阶级”,的确是人类历史社会的诞生与演进的主要事实,但是,他认为这种“阶级”,只是一种想象意指的赋义,主人与奴隶、领主与农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官僚集团与雇佣劳动者的划分只是一种想象的建制,在建制之前,不能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出现,因而不具有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含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的解释中,存在着两个简单的解释“图式”(schemata),并且他对这两个图式给予了质疑和否定。
三、关于异化理论的批判
菌株的持水性与发酵乳的品质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单菌株的持水性越高,酸乳对水的保持性越高,从而乳清的析出也会大大降低,有利于提高酸乳的品质。由表2可知,菌株T9和T16的持水性较高,这两株菌发酵酸奶后乳清析出极少,T1次之,T8持水性最低,有少量的乳清析出现象,与前面感官评价结果一致,实验表明,其持水性较高,发酵酸奶的的品质也较为稠厚,黏度较高,乳清析出较少,适用于制作高黏稠厚质感的酸乳。
有如我们所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73,并且他们阐述了,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是“种种虚假观念”,是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反响”, 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宗教和哲学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部分产生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活动过程之中,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这种理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涉及 “明晰的理论化”或者说建制的合理化,当然这种合理化是一种虚假的合理化,抑或“种种虚假观念”。但是,这种观点又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在虚假的合理化或者明晰的理论化之前,在最为本原的意义上,它不是来源于社会生活或者实践活动,而是来源于人们创造性想象力或者原生想象。他说:“脱离了生产性或创造性想象力(productive or creative imagination),脱离了我们所称做的原生想象(radical imaginary),历史就是不可能的和不可理解的,因为这在历史行动和在意指领域的构造(在任何明晰的合理性之前)上不可分解地被显示。”[1]146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人们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想象力、抑或“原生想象”创造着符号的意指或意义,这种意指规定着人类行动或实践的方向或价值取向,他说:“准确来说,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是这种意义的设定和定义,人类劳动(在最狭隘和最宽泛的意义上)在它一切方面——在它的对象、目的、方式和手段上——指出了把握世界的特定方式,将它自身定义为需要的特定方式,以及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设定它自身的特定方式。”[1]147在这种情况下,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就这样置换了逻辑结构:不是生活“决定”意识,也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意识(从根本上说,是意识背后的先于意识的原生想象)“设定”生活,具体说,是想象的意指“设定”、“定义”社会生活和社会行动。因此,卡斯托里亚迪斯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也就彻底否定唯物史观中“基础结构/上层建筑”的结构。
卡斯托里亚迪斯质疑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和“技术”决定着阶级的划分,而把阶级的产生归结为阶级这个词语的想象意指的突现(emergence),他认为,“不再存在着一种一般的历史解释,而是存在着一种根据历史的历史解释,逐渐地回溯,尝试着解释所有这些要素,但总意外地碰到事实(fact)、‘原始的’(raw)事实”[1]152,这种“原始事实”就是一种新的意指的突现。卡斯托里亚迪斯否认关于阶级的“一般的历史解释”,认为“根据历史的历史解释”进行回溯,就会发现历史就是想象“无中生有”创造的意指的突现。因此,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这种质疑,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否定的基础之上的,当他否定剥削的存在,否定技术(生产工具)决定一个社会阶级的诞生和存在的时候,也就如同前面所述否定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一样,这种否定实则就是对唯物史观的否定,对“一般的历史解释”或“历史规律”的否定,进而也只能把阶级的起源归因于想象的意指的突现,把阶级的存在状态归结于一种建制。
(1)理性膨胀。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建制功能的、集合-同一化的、理性的或逻辑的维度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本来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启蒙以来,近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种理性无限膨胀的世界,这种膨胀的理性本质上运作于一种想象的基础之上,社会中的合理性已经逐渐转化为一种虚假合理性(pseudorationality)。卡斯托里亚迪斯说:“现代世界表面上将它自身呈现为这种世界,它将合理化推向、以及趋于推向它的极限,因为这一点,它让它自身轻视——或者带着恭敬的好奇心考虑——以前社会的奇异习俗、发明和想象表象。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尽管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这种极端的‘合理化’,现代世界的生活正像依赖任何古代的或历史的文化一样依赖于想象。”[1]156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现代社会合理性只是一种形式的问题,是一种三段论的永恒统治,在这种三段论上,大前提从想象中借来了它们的内容,并且三段论本身的盛行、对不关联于其他任何东西的“合理性”的迷恋构成了一种二阶想象。在这种情况之下,现代的合理性实则脱离了历史,也脱离了社会现实,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想象的形式,是一种虚假合理性。卡斯托里亚迪斯说:“现代虚假合理性是想象的历史形式之一,在它的终极目的上,就这些目的自身并没源自于理性而言,它是任意的,并且,当它将自身设定为一种目的,只意图一种形式的和空洞的‘合理化’之时,它是任意的。在它实存的这个方面,现代世界处在一种系统的精神错乱的阵痛之中。这种精神错乱最直接可感知的和最危急威胁的形式在于不受控制的技术发展的自治化,这‘服务’于无明确的目的。”[1]156近代社会以来,伴随着上帝的隐退,“理性统治的无限膨胀”或者“不受控制的技术发展的自治化”已经成为了当代新的虚假的“上帝”。尤其在经济上,从生产到消费的一切层面上都受到了想象的统治,经济上的“需要”具有“任意的”、非自然的和非功能性特征,它超出了一种“基本需要”,变成一种“人造的需要”,化作了一种幻象,隐藏在一种“虚假-实在”的背后。当然,启蒙以来,这种理性的膨胀或技术的自治化,还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过程就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认为的,启蒙的过程原本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3]1,但结果是“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3]5。
(2)科层制领域。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当代世界的异化或者虚假合理性对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主要是通过科层制的社会组织表现出来的,科层领域渗透着想象。他认为,在过去,科层制的运行体现为一种“消极的确定性”,主要表现为越界行为、一种程序的滥用或“错误”;在当代,科层制的运行体现为一种“积极的”想象意指体系,主要表现为它可以基于以下有关的指南提供的碎片和指示而重建:生产的和劳动的组织、这种组织的特殊模式、它为它自身设置的目标、科层制的典型行为,等等。从时间进化上来说,在过去,科层制体系表现为诸如对“惯例”的参考,废除新奇的意愿,统一时间之流的意愿,以及作为一种运行良好的机器组织的幻想;在当代,科层制领域表现为一种未来体系的期待,作为一种自我革新、自我扩展的机器的组织幻想。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虽然与过去相比,科层制体系有了巨大的进化,但这种进步并没有改变科层制的本质特征:“人们,如同信息网络上纯粹的节点,只有涉及他们在等级范围内占有的等级和位置,才会存在并具有价值。世界的本质特性在于这个事实:它可以还原为一种形式规则的体系,包括那些使我们能够‘计算’未来的规则。”[1]158-159这种科层制的“形式规则体系”本质上是虚假合理性的表现,属于一种现代想象,这种想象不具有它自身的血肉,它从某种合理性的要素那里借来它的实质,而这种社会组织的合理性本身脱离了现实,只是一种幻象,它并未涉及根基、整体、目的以及理性与人、理性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科层制世界在本质上存活于符号领域之中,大部分时间,符号既不呈现现实,也不必然地构想它或操纵它。因此,科层制世界使纯粹象征主义的极端自治化实现”[1]159。在这种情况下,科层制领域就发生异化现象。
总体来说,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想象的原因在于经济上的匮乏和技术上的不成熟,并对其进行了否定,从而把他自己的异化理论建构在想象之上。他不承认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就看不到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所以他在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批判时只字未提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毫无疑问,他把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引起异化的原因简单地还原为“经济的匮乏”和“技术的不成熟”,把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的逻辑起点“劳动”置换成了他自己理论中的“想象”,并认为想象才是引起社会异化的原因,表现在现代社会的理性膨胀和科层制领域的异化,这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片面的误识和误读,是一种谬误。
四、结 论
我们从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步步批判和逃离中,认识到卡斯托里亚迪斯把他的批判建立在“建制与想象”及其二者的关系的理论上,有如他曾指出的,这种理论的目的在于张扬主体与建制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活生生的主体,或者是活生生的主体组成的集体,或者是进行建制的社会;另一方面则是作品或者建制。”[4] 180他的这种观点同卡西尔相类似,卡西尔曾说:“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5]36可以说,他们都是张扬人的主体性和非理性要素,同时又要彰显有意义的和诗性的社会实在。就从卡斯托里亚迪斯对主体创造性的强调来说,与拉康和阿尔都塞、齐泽克、巴迪欧和鲍德里亚等“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者”(1)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Lacanian Marxism)为蓝江用语,他把受雅克·拉康理论影响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称作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参见:蓝江:《后马克思主义还是拉康化马克思主义?》,载《福建论坛》2016年第6期。相比,他确实张扬了主体的鲜活性,因为拉康和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把社会历史的实在归结为一种“荒芜的沙漠”那般的逻辑符码,而卡斯托里亚迪斯赋予了其符号的诗性之维度,张扬一种诗性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种发展。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对匿名集体的原生想象的强调,没有为一种主体间性留下空间,“社会实践消失在源于想象维度的新的词语的制度化的匿名的喧嚣之中”[6]330,同时“不能使学习过程加以进行”[6]331;也如霍耐特所指出的,卡斯托里亚迪斯对于集体创生意义的匿名过程的强调,“完全摒弃了作为社会行为的实践特征,而越来越多地具有了非人的事件的特征”[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带来了其主体性理论的困境。
从对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建制与想象”的理解上,我们也看到了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即对“基础结构/上层建制”结构、“阶级”和“异化”理论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初衷如同柯尔施、霍克海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对近代社会功能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科层制或官僚主义的批判,重建革命的实践。但首先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种朝向“功能-经济”或“技术”视角的还原的基础上,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存在着对经济的基础地位的强调,但并不能就此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上层建筑”及其能动反作用等方面的强调,卡斯托里亚迪斯指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向经济“还原”的情况,同其他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指责一样,只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和片面认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批判是建立在无根的“原生想象”之上,社会历史的生成是原生想象“无中生有”的创造,是一种想象的建制,在本体论的层面,“社会就是创造,就是它自身的创造:自我创造”[8]332。这种创造性的社会政治观属于浪漫主义社会政治观,这种社会政治观正是早期马克思曾千方百计地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斗争中挣脱而抛弃的社会政治观。因此,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卡斯托里亚迪斯又重新复活了浪漫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青年黑格尔派将浪漫主义社会政治观建立在“自我意识”原则之上之不同之处在于,卡斯托里亚迪斯将其建立在更为激进,也更为不安定甚至虚幻的“想象”之上,将社会制度视做“建制”或“作品”,否定了“制度”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也否定了制度所规约的“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从而彻底否定唯物史观,完全抛弃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一面,导致了一种主观主义的极端错误态度:历史虚无主义。检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卡斯托里亚迪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地位:卡斯托里亚迪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实践-认识”的逻辑结构颠倒为“想象-行动”,这种转变使理论表面上变得更为激进,实则并没触及事物的根本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不仅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而且显得脆弱无力。
参考文献:
[1]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ImaginaryInstitutionof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法)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论柏拉图的<政治家篇>》,张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6]Jürgen Habermas. 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7](德)阿克塞尔·霍耐特:《用本体论拯救革命:论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
[8]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CastoriadisReader ,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CommentsonCastoriadis’CritiqueofMarxism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Imagine”
LIU Yu-jun, XinyangNormal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his own theory of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imagine”, Castoriadis classified critically Marxism as “the functional-economic point of view”, and hereby criticized his sub-theories such as“infrastructure and superstructure”、“class”and“alienation”of Marxism theory. In this process, he also criticized functionalism, rationalism and bureaucracy of modern society. To some extent, Castoriadis’ critique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but it was based on the radical imaginary,at last negated the scientificity of Marxism, causing the wrong attitude of history nihilism to Marxism.
Keywords: Castoriadis; imaginary; institution; creation; Marxism
作者简介:刘玉军,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KS146);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15CEX009);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
收稿日期:2019-06-20
DOI: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5.11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9)05-0082-06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迪斯论文; 卡斯论文; 里亚论文; 社会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法国哲学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KS146)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15CEX009)信阳师范学院"; 南湖学者奖励计划"; 青年项目论文; 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