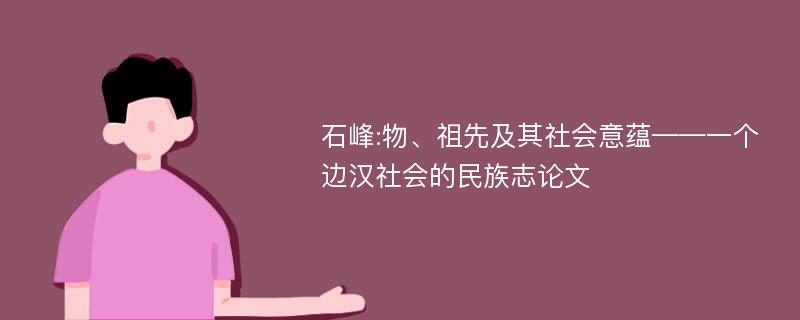
摘要:黔中鲍屯妇女服饰关键构件丝头系腰,在社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多重意义,其编织技艺由鲍氏11世祖鲍大千留传下来,因此鲍大千被编织者尊称为“带子老祖”。从祖先与财产、整合与裂变、祖先与神灵三个方面研究“带子老祖”鲍大千的独特性和学术价值,可以为人类学“物”的研究提供一个跨文化比较的个案。
关键词:边汉社会;丝头系腰;鲍大千;祖先崇拜;物的研究
人类学对“物”的兴趣可追溯到早期的进化论,其以“物”作为人类进化的标尺。而莫斯对“礼物”的研究则开创了该论题的象征起源论。随后的人类学各派理论皆有所涉猎。但在后来的学术进展中,人类学家对“物”的兴趣不再那么高涨,正如黄应贵先生的观察:“因此在结构功能论于四十年代兴起后,物与物质文化的研究便已衰落,几乎只成为博物馆的工作,但很少为人类学者所重视,这情形直到八十年到才有重要改变。”[注]黄应贵:《物与物质文化·导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年,第2页。国际人类学界对“物”的再度热情,显然也感染到了人类学汉语学界。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便是台湾人类学家黄应贵先生主编的论文集《物与物质文化》。黄应贵在文集导论中梳理了“物”研究的大体脉络,相关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有涉及。在此基础上,结合文集各篇论文,在“物”这个大论题下,他提炼出8个次论题:1.物自身;2.交换与社会文化性质;3.物的象征化及其与其他分类的关系;4.物、社会生活与心性;5.物性的表征;6.物性与历史及社会经济条件;7.物的象征化及物在各文化中的特殊位置;8.物与文化。[注]黄应贵:《物与物质文化·导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年,第1~25页。这8个次论题显然有重叠和交错之处,但基本上涵括了“物”研究的多重面相。作为人类学学科标志的“亲属研究”,当然可通过“物”这个媒介做多侧面的探讨。文集中至少有3篇论文具有如此取向。[注]3篇论文分别是:陈文德《衣饰与族群认同:以南王卑南人的织与绣为例》、谭昌国《祖灵屋与头目家阶层地位:以东排湾土坂村Patjalinuk家为例》、胡家瑜《赛夏仪式食物与Tatinii(先灵)记忆:从文化意象和感官经验的关联谈起》,分别载黄应贵主编《物与物质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年,第63~110页、第111~170页、第171~210页。本文正是沿袭了这个思路,将“物”与汉人的“祖先崇拜”进行勾连,进而反思过往的相关研究。
一、秘传的技艺
本文的田野点——鲍屯,位于黔中安顺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屯堡村寨。屯堡文化事项众多,假如要提炼其关键符号,大体有三,即妇女服饰、地戏(跳神)和抬汪公,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便是妇女服饰。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屯堡人放弃传统女装,其作为一个被少数民族包围的地方汉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必将弱化。[注]石 峰:《“边汉社会”及其基本轮廓——以黔中屯堡乡村社会为例》,《安顺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而屯堡妇女传统服饰的关键构件,便是本文所讨论的“物”——丝头系腰(或丝头腰带)。
浅议代扣代缴年金个人所得税………………………………………………………………………………………钱玉香(3.93)
地方文人对丝头系腰的文字记录,通常强调三个要点。其一,汉文化特色。如“屯堡人的服饰可以让我们穿越历史看到最古老的汉族服饰”“屯堡妇女的服饰俗称‘凤阳汉装’。这些服饰从安徽传来,如今当地早已失传,因而这里的服饰已呈活化石”“屯堡妇女腰间的丝头系腰,至今只有鲍屯一地能生产。腰部的装饰物是汉族服饰的重要元素”等等。[注]杨友维等:《鲍家屯》,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51~52页。其二,结构和简要制作过程。如“丝头系腰是由‘带’和‘丝’两部分编成,带长4米许,丝长0.6米。编织时先把棉线放在一块长30厘米、宽4厘米、厚1厘米的铁板上编成通带。通带一般的就只编出方块格或白果花图案,花形特殊的可编织出‘花好月圆’之类的文字和花卉图案。编织成带的成品需要两次煮染成黑色,经过整压梳理才能称为正品。丝线与带的两端相连结,联结的工艺编织技术更为玄妙……”。[注]杨友维等:《鲍家屯》,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53页。其三,美学价值。如“丝头系腰不仅显示女性的三围美,还透露出迷人的妩媚与典雅”“屯堡妇女对丝头系腰的偏爱是令人感动的。成群结队着丝头系腰在乡间路上的屯堡女人,往往会引来屯堡男人的阵阵山歌:老远看你赶路来,丝头腰带甩起来。甩出鱼钩下河去,钩上一条大鱼来”。[注]杨友维等:《鲍家屯》,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49~54页。而在实地访谈中笔者发现,对于丝头系腰的相关问题,村民们关注的着重点与研究者有同也有异,村民们主要强调丝头系腰技艺的秘传性和“带子老祖”鲍大千对丝头系腰技艺知识的贡献。对鲍大千的讨论留给下文。
与中国其他区域的乡村一样,鲍屯的年轻人多外出打工,留守村里的中老年人除了务农,便是从事具有本村特色的丝头系腰编织。一位在家编织腰带的老人介绍说,从事此项工作的中老年人年龄集中在50至70岁,年轻人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加入进来,原因是坐的时间太长,一天要坐5个多小时。但这项工作的经济收入却相当可观。据2018年的调查,如果有人订货,每条售价1 000元左右,如果卖给中间商,每条售价700元左右,1个月能织10条左右。
该研究首席作者、达尔豪斯大学生物学教授阿拉斯泰尔·辛普森说:“它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支,可能已经分离超过十亿年,我们没有任何有关它的信息。它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有助人们了解复杂细胞的进化以及它们的古老起源。”
时值公元2013年4月2号,农历癸巳年二月二十日,鲍氏子孙,大千祖公的徒孙几百余人,谨以酌馐佳果鲜卉之尊,致祭于十一世祖考大千之灵,祝文曰:鲍氏十一世祖考大千,创建农工相辅,技艺财神之祖公祖师,留给子孙徒孙,纺织腰带系腰村,引领百户鲍屯儿女,浓墨重彩,绘就同步小康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创实践超过预期,价钱超过历史,富裕百余家。春暖花开又清明,乾坤宝灵千年好,上坟炊烟万户新,适逢盛世生意新,墓前野祭扫墓真,今天缅怀大千祖,夜以继日纺织忙,真心实意祭我祖,子孙徒孙表真心,乐此不疲富裕臻……
目前关于丝头系腰的记忆可追溯到民国时期。民国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修建贵阳至安顺的公路,途中经今天的带子街村。鲍屯有村民在此地出售丝头系腰,后建房定居,便形成一个自然村落。立于街边的石碑详细介绍了带子街的由来:
带子街位于安顺城东二十公里处,地当滇黔大道。在清朝中期鲍屯棉织手工业发展,从业者多,将所织的各种民国服饰的带子,来此搭棚销售,后建房定居。沿街带子飘舞,由此得名为带子街。从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1765~1770年)为建村时期。在这以后的一百八十多年间,凡经战火劫难,屋疏户稀,到公元一九五零年,建行政村时,始成村寨规模。共四个自然村,上下带子街为汉族,黄坡、黄家庄为苗族。
此段碑文在年代上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清朝和民国混淆不清,但至少可追到民国。人类学家通常认为,中国村庄的裂变与宗族/家族的裂变(分房)相重叠,即宗族/家族人口增加,便通过分房的形式另寻他处居住,随后形成另一个自然村落。但带子街从母村鲍屯分离出来,并非以分房的形式而成,却是因出售丝头系腰而形成的自然村落。
由于场地上全是砂性土,造浆采用膨润土,并适当加入CMC稳定剂及纯碱,膨润土形成泥皮薄而密,具有较高的黏结力。钻进过程中经常测定泥浆浓度,过浓影响钻进速度,过稀不利于护壁、排渣。根据施工经验,比重控制在1.15~1.30之间。泥浆采用高压正循环施工方法。由于泥浆浓度高,含砂量较高,成孔过程中采用泥砂分离振动筛和泥砂分离离心泵两种方法进行过滤,再经多个泥浆池过滤沉淀后循环入造浆池使用,大大地降低了沉渣厚度。
当然,村民们谈论最多的是丝头系腰的秘传技艺。地方文人虽然也记录了丝头系腰的制作过程,但并没揭示其复杂的技术工艺和流程。从上文老人所说,1个月大概只能织10条左右,便知其工艺的复杂程度。丝头系腰的秘传技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传男不传女,这里的女主要指女儿,不包括嫁入村里的外来媳妇。因为女儿会嫁出村外,外来媳妇虽然是女性,但不会把技艺传给村外之人;二是有资格获得技艺之村民,不分姓氏。鲍屯是一个鲍姓独大的多姓村,鲍姓村民占总人口的90%,除鲍姓外,尚有汪、吴、潘、徐、陈等杂姓。作为一姓独大的杂姓村,鲍族之事90%是村庄之事,村庄90%是鲍族之事。在某种程度上,鲍族等于鲍屯。鲍族虽然占据了村庄90%的社会空间,但并非全体占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鲍族又不等于鲍屯。一姓独大的杂姓村内部的这种张力,需要汉人社会最基本的两个组织形式宗族和“会”来舒解。当涉及族内事务时,宗族自行处置。而当涉及包括鲍姓和其他杂姓的全村事务时,则由“会”任之。在这里,宗族和“会”在形式和内容上既重叠又分离。笔者曾将这样的社会构成概括为“族—会”型乡村,以区别于东南和华北汉人乡村社会。[注]石 峰:《“边汉社会”及其基本轮廓——以黔中屯堡乡村社会为例》,《安顺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简言之,村庄作为整体,其利益大于一姓独大的鲍氏宗族。虽然传说丝头系腰技艺是由鲍氏族人11世祖鲍大千从安徽故里学成带来,但其技艺知识却惠及全村村民。在鲍屯,知识传承的基本原则是以村为单位,而不是以族为单位,正如村民所说:“技术不能出村。”
最近几年,有公司曾准备来村里投资建厂,把丝头系腰开发为旅游商品,但最后以失败告终。笔者也向村民询问过具体过程和失败原因,但回答皆语焉不详。笔者估计跟丝头系腰的秘传性相关。因为建厂一定会是规模化机器生产,而且可能会招聘村外工人,这个生产模式当然违背了鲍屯知识传承的基本原则。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最后让步于鲍屯村民围绕丝头系腰而形成的道德经济。
施奈德(Jane Schneider)在一篇服饰人类学的综述中,梳理出了服饰文化在不同社会和族群中所呈现出来的功能和意义多样性。其中服饰能强化和维持社会关系和纽带。[注]Jane Schneider,“The Anthropology of Clot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69,1987,pp.409~448.倘若把鲍屯丝头系腰作跨文化的比较,可凸显其鲜明的文化特色。比如有的族群,母亲会为女儿出嫁准备一些纺织品,女儿在婚后生活中保留母亲的礼物以及继承纺织技术,并照此方式传递给自己的女儿。她们借此强化和维持了女性继承线。但鲍屯妇女结婚时,丝头系腰不是女方准备,而是作为男方聘礼的一部分。因而在屯堡社会丝头系腰促进了联姻。
丝头系腰也表达了鲍屯村民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个认同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强调汉文化的起源和特色,使他们与整个屯堡汉人群体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与周边的非汉族群相区别,建立了一道族群边界;二是通过丝头系腰的秘传技艺,强调鲍屯单个村落的独特性,因而在整个屯堡汉人群体内部,再形成一个次级认同。鲍屯村民借助丝头系腰所具备的这种一级和次级身份认同,体现了多重身份认同的叠合属性。[注]参见杨凤岗《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当然,与本文主题紧密相关的是,丝头系腰与祖先的联结,下面转向对“带子老祖”鲍大千的讨论。
二、“带子老祖”鲍大千
故事情节三:鲍大千进入湖南境内,路过一苗寨,见土匪劫持一女子。鲍大千利用平时练就的鲍家拳救下该女子。
第四个阶段互助提升阶段,该阶段员工除接受组织的安全培训外,能够主动学习和提高安全能力与意识,并主动关注他人与组织层面的不安全隐患,主动给予帮助。
鲍大千墓位于离鲍屯1.2千米处的大西桥镇。该地为鲍氏族人一小墓园,鲍大千墓碑文载:“清乾隆五年庚申(1740年)仲春月吉日立”,碑上的对联为:“腰带学识万里艺,屯堡服饰千古传”。从碑文的公历时间和赞辞来看,鲍大千墓显然是重建的新墓,但旧墓建于乾隆年间应是肯定的。
每年清明节前一周对鲍大千的墓祭,主要是村里丝头系腰的编织者,不分性别和姓氏。祭祀组织仿祭祀始祖鲍福宝的模式,因为人数相对较少,所以规模也没有那么庞大。一般7至8人作为组织者,负责收钱和卖餐票,祭祀者去到坟墓后,先集体磕头,然后“说话”(念咒语:不教外人,如教就“绝子灭孙”),念祭文,最后祭祀者与祖先共餐“一锅香”。2013年的祭文节选如下:
还有老人说,2007年前后,编织腰带的人很多,现在相对有所减少。在之前,村民们是偷偷编织,主要是担心国家政策不允许。村民们的担心是有原因的。改革开放前,编织和买卖腰带被视为投机倒把,但由于有需求,一部分村民们只能躲在厕所、山洞,或去村外亲戚家偷偷做。2007年后,村里挖掘传统文化,村民才公开编织。经过宣传,妇女们对腰带的需求量开始增多。
另外,三维模型的建立有利于材料统计工作的实施。传统项目中的仪表材料用量通常都是估计量加裕量,主要依靠设计人员的经验来确定,材料用量很难准确控制,容易导致施工中出现纠纷,最终的结果就是材料用量超预算采购量。在三维模型中,设计人员可以根据变送器、接线箱、阀门等仪表设备的位置,准确计算电缆、气源管、支架等各类安装材料数量,大幅提高了材料统计的准确性,既有利于成本控制,也能做到有据可查。
陈其南以系谱性宗族/家族批评弗里德曼的功能性宗族理论时认为,功能性宗族只强调了整合维度,而忽视了裂变维度。为此,陈其南特别凸显了“房”在汉人宗族/家族中的社会意义,并将汉人继嗣群体概括为“房—家族”体系。经过反复论证,他将这个体系的原则总结为:
二是全面实施扶贫资金绩效管理。压实资金使用单位的绩效主体责任,督促资金使用单位逐笔逐项编制绩效目标,明确项目的减贫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建立绩效目标执行监控机制和综合评价机制。
故事情节一:清雍正6年(1728年),不满22岁的鲍大千在鲍家拳擂台比武夺魁,并喜添贵子,众宾客前来祝贺。其母萧太君身着系有丝头腰带的服装,引来众宾客的观赏,并询问腰带的来历和技艺。萧太君告知乃鲍家祖传,由始祖“调北征南”时带来,所系腰带为始祖母牛氏传下来已300多年。但制作技艺当时尚未传到鲍屯,只有祖籍地安徽歙县棠越村鲍家人才能制作。
学院积极配合工作,安排班主任负责该班的日常组织和管理工作,为了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开课均选择在晚上。校企双方合作编写《药物临床试验基础课程》作为培训教材,由公司安排高管来校讲授新药临床试验、药物临床试验发展历史及现状、从业人员素质、研究方案基础知识、有效沟通等与行业密切相关的内容,最后进行考核,向优秀学员发放奖学金。
故事情节二:鲍大千当着众人下跪,请求母亲让自己到祖籍地学习丝头腰带的技艺,母亲萧太君允诺。鲍大千离开村子时,回望家乡的山水,大菁山、小菁山、小河、小桥、水碾房……在眼前掠过。
从人类学对“宗族组织”的界定来看,鲍氏在历史上确实是个组织化的宗族,而非礼仪性宗族,因为它具备了组织化宗族的4个基本条件,即共祖、祠堂、公产和族谱。鲍氏始祖为鲍福宝,下分“仁、义、礼、智、信”5房,现已传至21世。鲍大千系11世祖。目前鲍氏宗族的组织性主要体现在每年清明祭祖方面。族人除了集中在鲍屯外,部分还分离出去组建了另一个自然村带子街。另有部分族人散居在各地。清明是祭祖最重要日子。村民们说,祭祖时间一般会持续半月左右,原因是要按照祖先的不同世系来祭祀。清明前一周祭拜的是“带子老祖”鲍大千。清明当天全体族人祭拜始祖鲍福宝,第二天按房祭祖,第三天按支祭祖,第四天以后则按小家祭祖。始祖坟地位于村子后山上,因风水极佳和面积的限制,族人曾规定,六世以后的祖先就不准再葬于此地。因此,这块祖坟地仅有前七世祖的坟茔。其他祖坟则散布各处。另一说法是,族人做官至知府以上才能葬于祖坟地。清明祭始祖无疑是村里和族人的一次盛会,2018年,为了招待各地赶来的族人,曾摆了420多桌宴席,按一桌8人计,则大约有3 000多人。
电加热方法的思路是利用电流互感器线圈自身进行短路加热。由于电路互感器线圈直流电阻相对较大,只需要较小的电流就可以获得较大的温升,同时不需要较高的电压,不会损坏线圈的绝缘。
故事情节四:历时数月,行程数千里,鲍大千终于来到安徽歙县棠越村。但鲍氏族长鲍三立对其身份有些怀疑,鲍大千便出示族谱,并说出鲍氏在黔的世系。族长鲍三立再问其是否会打鲍家拳,鲍大千展示鲍家拳的武艺。至此,鲍大千的家族身份获得认可。
稻瘟病能够大大降低水稻的产量,对水稻生长产生较大的影响。稻瘟病的发病症状为抽穗期稻节处布满小斑点,随着水稻的生长斑点不断扩大蔓延,稻节逐渐发黑以至断裂。出现此疾病的主要原因是缺少阳光照射,湿温环境所致,为此稻瘟病的抗病技术应从根源入手,适当调整水稻植株间距,这在较大程度上能够保证阳光对每个植株都能充分照射。此外,还应严格进行肥料与水分的管理,肥料之间的配合尤为重要,比如化肥与有机肥之间的配合、氮、磷钾之间的配合,能够有效提升水稻抵抗力。除此之外,还能够通过化学方法杀灭病菌,一般使用20%的咪鲜胺兑水实施喷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用量。
故事情节六:回乡后,鲍大千带领乡亲在汪公殿盟誓:“遵照祖训,丝头腰带编织技艺只传本屯鲍、汪、吕三姓,且只传儿子不传女儿。”从此,此门技艺便为鲍屯独有,至今不衰。
这则文人书写的传说与流行在村民中的口头传说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村民说鲍大千两次前往安徽祖籍地学艺,但书面版无此反复曲折的情节。二是口头版情节简单,书面版情节复杂。书面版增添的这些故事情节显然想象的成分居多,尽管如此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其间所透露出的信息和符号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意涵。换言之,内容丰富的书面版,通过叙述鲍大千远赴安徽学艺的过程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或说学艺与身份认同表达这两条线同时展开。
一如上文对丝头系腰的讨论,鲍大千传说的书面版同样表达了鲍氏族人的多重身份认同,且其多重性多于前者。1.祖籍地认同。如故事情节一,叙述萧太君告知宾客丝头系腰乃鲍家祖传,由始祖“调北征南”时带来,但制作技艺当时尚未传到鲍屯,只有祖籍地安徽歙县棠越村鲍家人才能制作。鲍大千远赴安徽歙县棠越村学艺的行为本身,就是寻根追寻自我的过程和表达;2.在地认同。这是移民社会地域空间认同较为常见的文化现象。遥远的祖籍地与当前身处的地域这二重空间,共同塑造了自己的地域身份。所以在故事情节二中,鲍大千离开村子时,回望家乡的山水,大菁山、小菁山、小河、小桥、水碾房……等等自然景观在眼前掠过;3.军人认同。屯堡人作为明朝派遣至西南土司地区的卫所军人之后裔,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强调自己的军事色彩,比如“地戏”所演剧目皆武戏,村庄的布局充满了军事防御功能,而在书面版传说中,则以鲍家拳意象来加以凸显,鲍家拳在文本中总共出现三次。故事情节一,叙述鲍大千在鲍家拳擂台比武夺魁。故事情节三,叙述鲍大千进入湖南境内,利用平时练就的鲍家拳救下被土匪劫持的女子。故事情节四,叙述安徽歙县棠越村鲍氏族长以鲍家拳验证鲍大千的族人身份;4.宗族认同。最显性的例子就是故事情节四,叙述安徽歙县棠越村鲍氏族长以鲍家拳和族谱验证鲍大千的族人身份。鲍大千为何要随身携带族谱千里学艺,文本并未交代其原因,在此故事情节中突然出现族谱,于是便显得有些突兀,但这并不影响文本所反映出来的宗族认同;5.族群认同。故事情节三,叙述鲍大千进入湖南境内,路过一苗寨,见土匪劫持一女子,鲍大千利用平时练就的鲍家拳救下该女子。在所有故事情节中,此情节的刻意虚构性最为明显。虽然所经过的苗寨不在贵州境内,但其族群区隔和歧视的意义并无二致。文本作者把以鲍大千为代表的汉人塑造为正义的化身,苗寨象征了少数民族或土司,同时也象征性地等同于土匪,鲍大千来到此地利用武力解救了被欺压的弱者。故此,鲍大千从土匪(土司)手里解救女子,无疑是明朝卫所军人来到西南非汉地区控制土司的隐喻表达,同时也是汉与非汉的族群身份区隔的隐喻表达;6.村庄认同。故事情节六,叙述鲍大千回乡后带领乡亲在汪公殿盟誓:“遵照祖训,丝头腰带编织技艺只传本屯鲍、汪、吕三姓,且只传儿子不传女儿。”有趣的是,他们盟誓的地点并不在鲍氏祠堂,而是汪公殿。据《鲍氏族谱》载,历史上确存在鲍氏祠堂,1949年以后被毁。鲍屯乃一姓独大的多姓村,其社会结构为“族—会”型村庄,鲍氏族人虽占整个村庄人口的90%,但并不能代表整个村庄。也即是说,鲍氏祠堂发挥不了村庄整合的作用,汪公殿和祭祀组织“汪公会”则能涵括全村的所有姓氏以及男女两性。丝头腰带编织技艺并非鲍氏族人独占,而为全村所有姓氏共享,故而盟誓地点不在鲍氏祠堂,而在作为整个村庄象征的汪公殿。
在鲍大千传说的两个版本中,口头版因故事情节简单而无多大分析价值,书面版的情节丰富多彩,使我们能够分析出以上6个多重身份认同。鲍大千作为祖先的身份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鲍氏族人的11世祖,二是作为全村的“带子老祖”。两个传说都同时表达了他的这两个身份。当然,作为鲍氏族人的11世祖,主要反映在《鲍氏族谱》的系谱记录和清明节的墓祭上。而作为全村的“带子老祖”,则主要体现在清明节受到全村丝头系腰编织者的祭祀。鲍大千作为“一家之祖”上升为“一村之祖”,其连接机制当然是丝头系腰这个物件,而丝头系腰的编织技艺为何不由鲍姓独占,却由全村多姓共享,是什么理念导致了这个共享行为?我们认为,这个理念就是“村庄至上”原则,而不是“宗族/家族至上”原则。“村庄至上”原则的产生,极有可能与历史上屯堡村寨作为一个整体一致对外有莫大的关系。限于篇幅,本文对此暂不作详细讨论。本文关注的是,鲍大千作为“一家之祖”上升为“一村之祖”,其在汉人祖先崇拜的学术话语中有何意义?下面转向此论题。
三、扩大的祖先
汉人祖先崇拜的人类学研究与宗族/家族研究紧密相关。换言之,宗族/家族研究必然要涉及祖先崇拜问题,祖先崇拜是宗族/家族诸多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在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中,祖先崇拜是人类学家热烈讨论的焦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便已撰专文讨论此问题,他从鬼神的概念、拜祖的意义、拜祖的渊源、拜祖的礼仪、祭先礼的变迁和沿革、拜祖与迷信、拜祖的种种影响等方面作了先驱性的研究。[注]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拜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31~258页。在随后的40年代,许烺光更以祖先崇拜为中心撰写了他的代表作《祖荫下》,他将汉人的社会行为皆归结为在“祖荫下”的一切活动:“与其说以贫富间不同的社会行为作出发点,还不如说是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不同,相同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也就不同更为恰当。‘社会行为’在这里指的是以‘祖先荫蔽’为中心内容的一切活动”。[注][美]许烺光:《祖荫下》,王 芃等译,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第7页。另外,汉人祖先崇拜与其他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有何异同,也是人类学家的一个兴趣点。1976年,尼韦尔(W.H.Newell)主编的论文集《祖先》(Ancestors),便从跨文化的角度,将东亚(日本人与汉人)和西非的祖先崇拜作了较为详细的比较。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区域的祖先崇拜进行比较研究,尼韦尔说:“虽然祖先崇拜的行为方式在所有的大陆皆有发现,但东亚和西非有当代的资料可利用(罗马和希腊的祖先崇拜习俗只有历史记载)。而且,这两个区域皆强调单系继嗣;皆有清楚严格的宗教与政治制度,以及皆有优秀的民族志”。[注]W.H.Newell,“Perface”,in W.H.Newell eds.Ancestors,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76,pp.IX~XII.在汉人祖先崇拜研究的诸多问题中,其中有3个问题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紧密相关,因此,本文将“带子老祖”鲍大千置放在这3个问题脉络中进行讨论。
对于新型“被XX”结构中“被”的归属问题各家说法不一,主要有助词/助动词说、否定标记说、类词缀说、副词说。除副词说认为“被”是实词外,其他几种说法都认为“被”是虚化程度较高的成分。
(一)祖先与财产
在《拜祖》其中一节中,林耀华认为,汉人对待祖先的态度是爱恨交加。一方面“视死者为良友”,另一方面“视死者为仇敌”。[注]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拜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33页。庄孔韶在评论这段文字时说道:“林先生提出的祖灵是良友与仇敌之说似乎最早,其后三四十年人类学界才有一个讨论祖灵善恶问题的学术热点。”[注]庄孔韶:《林耀华早期学术作品之思路转换》,载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附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60~261页。
对“祖灵善恶”的争论,成为后来祖先崇拜研究一个主导性的问题之一。同时,也连带产生了其他几个相关议题。李亦园在一篇重要文献中对此作了精彩的回顾和评论。他认为,这段时间人类学汉人家族仪式的宗教崇拜研究有三个争论,一是汉人观念中的祖先是永远地保佑子孙抑或会作祟致祸于子孙;二是祖先牌位的供奉是否一定与财产的继承有关;三是坟墓风水仪式是否有操弄祖先骨骸之嫌。[注]李亦园:《中国家族与其仪式:若干观念的检讨》,载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在李亦园梳理的这三个颇富争议性的问题中,其中以祖先牌位的供奉是否一定与财产的继承有关,对讨论“带子老祖”鲍大千极具启发意义。许烺光认为,汉人供奉祖先牌位是每个人理所当然的行为,与遗产有无无关,但芮马丁(Emily Ahern)却认为,牌位的设立与否和继承权有密切的关系。芮马丁在台湾溪南发现和总结出一个祖先与财产关系的一般原则:1.假如X继承Y的财产,X就应该祭拜Y;2.假如X是Y的直系后裔,X并不一定要祭拜Y;假如X是Y的唯一后裔,X就一定要祭拜Y;假如X是Y最受惠后裔,X就一定要祭拜Y。[注]Emily Ahern,TheCultoftheDeadinaChineseVillag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p.149.这个原则的关键之处,是直系后裔不一定祭拜自己的祖先,而非血缘关系之人却有可能建立祭拜关系。芮马丁在溪南发现了1个典型案例。一位李姓男子在服军役时,认识了1个独身军官,这位军官去世前将自己的财产遗赠他,条件是埋葬其遗体并立牌位当做祖先祭拜。[注]Emily Ahern,TheCultoftheDeadinaChineseVillag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p.139.其他人类学家在台湾也发现了异姓祖先崇拜的案例。如陈祥水对彰化“异姓公妈”的研究,他说:“一个行将倒房的家庭,除了由女儿将祖先牌位陪嫁以在别人家形成异姓祖先崇拜外,也可因招赘而使赘婿将其本家的祖先牌位背过来形成异姓公妈……财产的赠与和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一种互惠的关系。”[注]陈祥水:《“公妈牌”的祭祀:承继财产与祖先地位之确定》,《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36期。反对者认为,这种建立在财产利益基础上的祖先崇拜,违背了中国儒家“慎终追远”的基本伦理和感情,但正如李亦园所说:“Ahern(芮马丁)所看到的现象,虽然为传统的中国人引为震惊,我们仍然不认为这是一种矛盾或冲突,而认为是在特殊环境之下的一种调适与弹性原则运用,也就是说,一种亲族关系成分——着重于权利义务原则的世系关系在这里又被强调了。”[注]李亦园:《中国家族与其仪式:若干观念的检讨》,载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无论是出于陈祥水所说的互惠原则,还是李亦园所说的权利义务原则,异姓祖先崇拜在特殊的汉人社会中,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并被当地人所认可和接受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现象。
鲍大千作为鲍氏族人的11世祖和全村鲍姓与非鲍姓(汪、吕等杂姓)丝头系腰编织者的“带子老祖”,其中包含了汉人祖先崇拜的两个不同的态度,即作为鲍氏族人的11世祖而得到族人的祭拜,反映了非利益性的子孙对其直系祖先的亲缘仪式关系。而作为“带子老祖”得到丝头系腰编织者的祭拜,反映了建立在财产利益基础上的同姓和异姓祖先崇拜。芮马丁总结的祖先与财产关系的一般原则,只能部分解释鲍大千的案例。换言之,只能解释作为“带子老祖”的鲍大千,而不能解释作为鲍氏族人11世祖的鲍大千。鲍大千传下来的丝头系腰编织技艺,虽是一种技艺,但编织者却可以将之商品化以获取物质利益,因此,该技艺通过转换后成为一种财产。鲍屯丝头系腰编织者包含了鲍姓与非鲍姓的村民,鲍姓编织者将鲍大千视为“带子老祖”,符合芮马丁所说的“假如X是Y最受惠后裔,X就一定要祭拜Y”。在这里,X是Y的直系后裔;非鲍姓编织者将鲍大千视为“带子老祖”,符合芮马丁所说的“假如X继承Y的财产,X就应该祭拜Y”,在这里X和Y没有血缘关系。鲍大千将丝头系腰编织技艺惠及全村村民,村民反过来奉鲍大千为祖先进行祭拜,既体现了陈祥水所说的互惠原则,也体现了李亦园所说的权利义务原则。与台湾经验不同之处是,后人并未为鲍大千树立牌位,而是在鲍大千墓进行墓祭。尽管如此,祭祀牌位和墓祭并无本质区别,因为都是将对象作为祖先来祭拜。
矿区内围岩蚀变较强,主要有黄铁矿化、大理岩化和硅化,其他零星可见透闪石化、萤石化等。黄铁矿主要沿裂隙、方解石脉边缘充填或呈浸染状、小团块状分布于围岩中。常伴随有细脉状、浸染状铅锌矿化。大理岩化主要分布于岩体接触带及外围的碳酸盐岩石中,往往伴随着退色化现象。有时可见细脉状、浸染状铅锌矿化。硅化在矿区范围内均有分布,在部分构造发育处,硅化尤为强烈,但铅锌矿化较弱。
(二)整合与裂变
关于鲍大千前往安徽,将丝头系腰技艺带回鲍屯的传说有两个版本。一是口头版,主要流行在普通村民中间,核心内容是说,他两次前往安徽老家学习编织技艺,第一次只学到正面,第二次才学到反面,没有故事情节;二是地方文人书写的较为详细的添加了许多故事情节的书面版。[注]杨友维等:《鲍家屯》,成都:巴蜀出版社,2008年,第147~150页。
任何一个“房”单位,不论其规模和世代的大小,都是从属于一个较高级的“家族”范畴之次级单位……不论成员数量的多寡,这个群集都可以称为“房”,以表示其从属于更高范畴的含义。如果要强调一个家族群集内彼此的分别,人们就可以用“房”这个观念。如果要强调诸“房”之间的整体性,人们就可以用“家族”这个观念。换句话说,一个男系宗祧单位可以同时是个“家族”和“房”。[注]陈其南:《汉人宗族制度的研究:弗里曼宗族理论的批判》,《考古人类学刊》1991年第47期。
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成效显著。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水利行业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水利新闻宣传工作成效突出,水情教育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水利精神文明建设和机关文化建设成果丰硕。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和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得到加强。
故事情节五:在棠越村半月,鲍大千学会了丝头腰带的编织技艺,同时将织机零件尺寸绘成图,记录下编织流程,便踏上返乡之途。
作者在这段话中认为,“家族”的观念代表了整合维度,而“房”的观念则代表了裂变维度。陈其南还从上下不同视角形象地描述了系谱性的“房—家族”体系所包含的整合与裂变两个维度,如果从上往下看,看到的就是“房”所显示的裂变维度,而从下往上看,看到的则是“家族”所显示的整合维度。
陈其南认为,分房的系谱架构主要表现在一些社会生活中,如分家、分户、分财产,以及宗族团体中的其他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上。显然,汉人宗族/家族的裂变过程,即“分房”与分家及连带的分财产和其他权利义务的分配共享一个原则。但导致宗族/家族整合和裂变的根本理念是什么,陈其南并没有做出回答。王崧兴则认为,这个根本理念是汉人父系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所代表的两个相互背离的倾向,即男性原则导致整合倾向,女性原则导致裂变倾向。他认为,卢蕙馨(Margery Wolf)在汉人父系社会中发现的以母亲及其子女为成员的单位“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一开始就孕育了裂变的种子。在未裂变前,“子宫家庭”不包含丈夫,而裂变后,丈夫被涵括进来,这个单位就被称为“房”或葛学溥(D. H.Kulp)所谓的“自然家庭”。尽管裂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整合并没有消失。男性原则发挥了整合的作用,正如王崧兴所说:“家族整合的基础是将男性作为中心的父系继嗣原则。尽管会完全分家,但因为父系继嗣意识形态,家族整合的作用永远存在”。[注]Wang Sung-hsing,“On the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Chinese Society”,in Hsieh Jih-chang and Chuang Ying-chang eds.,The Chinese Family and Its RitualBehavior,Taib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a Sinica,1985,pp.50~60.整合与裂变这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如孔迈隆(Myron L. Cohen)的观察:“汉人家族不断地处于整合与裂变这个矛盾所产生的紧张状态之中。”[注]Myron L.Cohen,HouseUnited,HouseDivided:TheChineseFamilyinTaiw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73.
鲍大千作为“带子老祖”,对丝头系腰编织者这个群体而言,只有整合作用,而无裂变作用。每年清明编织者前往鲍大千墓进行墓祭,仪式性地将全村编织者团结起来,编织者之所以成为一个群体,便是因为他们共享一个共同的祖先鲍大千。在这个群体内部没有出现类似“房”这样的次级单位,这是因为其内部缺乏裂变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类似族谱一样贯通上下的系谱。作为祖先的鲍大千与作为子孙的编织者的传承关系,只有清楚的源而无清楚严格的流,故而未发生裂变。就整合而言,因为编织者包含了非鲍氏村民,所以其整合的范围超越了宗族/家族,故而鲍大千是全村整合的一个符号。导致这个结果的理念是“村庄至上”原则,而非“宗族/家族至上”原则。
(三)祖先与神灵
在中国民间宗教中,许多地方神灵常常为某一家族祖先转换而来。转换的原因多以此人身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或因正统道德及事功得到官府的表彰,死后从仅受到直系后裔祭拜的祖先,上升为受到地方普遍祭拜的神灵。比如,许烺光在大理喜洲记录的,一个身前默默无闻而死后成为城隍的例子。此人苦读诗书,但考试皆榜上无名,知道自己加官晋爵希望渺茫,于是便从事银器生意。别人都以次充好,他的货都货真价实,从不欺骗顾客。68岁时去世。巡游神将他的美德记录下来,并上报给玉皇。玉皇便任命他为某县的城隍。[注][美]许烺光:《祖荫下》,王 芃等译,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第129页。再如,屯堡乡村祭拜的地方神“汪公”也如此。据说“汪公”信仰是明朝屯堡卫所军人从安徽带到黔中地区的。根据常建华的研究,隋末世变,徽州土著汪华起兵平婺源寇,但又有记载,汪华被赐“忠烈”事在南宋,故祭拜汪华的忠烈庙建于宋代。常建华认为,虽然忠烈祠属于名人特庙,而且带有地域神的性质,但是对于汪氏来说,它却是一所祖庙。国家建庙纪念有功于国家的“忠臣烈士”,是一种“专祠”,也是“公祠”。对于被纪念者的家族来说,这种专祠则是一种先祖的祭祀,因此又卜地设置“行祠”,介乎公祠与家礼之间。从形式上看,行祠是作为“公祠”之“专祠”的分祠存在的,实际上行祠除了具有地域性外,主要是作为子孙立祠祭祀始祖或先祖存在的,是一种宗祠。[注]常建华:《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0年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由此可知,在“汪公”信仰早期,作为祭拜神灵的庙宇与作为祭拜祖先的祠堂两者合二为一,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才逐渐分离开来。
“带子老祖”鲍大千尽管具有使丝头系腰编织技艺惠及全村村民的功德,但仍然还停留在祖先身份的阶段,尚未上升为一个地方性的神灵。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无专门供祭拜的庙宇。常建华对“汪公”信仰的研究表明,庙宇与祠堂有可能合二为一,但忠烈祠属于名人特庙,也即是说,忠烈祠仅供奉汪华1人。历史上鲍氏曾有过祠堂,但并非专祭鲍大千1人。目前对鲍大千的祭拜形式就是墓祭而无其他,而且祭拜的模式与祭拜其他祖先并无二致。二是无神异的灵验传说。上文讨论的关于鲍大千远赴故里学艺的两个传说版本,故事情节皆为世俗性行为,没有特别的神圣性。反之,作为村神的“汪公”却有护佑全村的灵验传说。根据田野调查,鲍屯的传说中有这样的故事,清咸同年间,鲍屯村民曾背负汪公神像避战乱于寨旁大箐,及乱兵将至之时而汪公显灵,保全了全村村民。[注]蒋立松:《从汪公等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灵验传说在民间宗教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神灵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
四、结 论
基于以上的讨论,兹将本文的要点总结如下:
其一,作为“边汉社会”类型之一的黔中鲍屯,是一个一姓独大的杂姓村,其社会结构为“族—会”型汉人乡村社会。“村庄至上”原则超越了“宗族/家族至上”原则。
其二,作为一个物件的丝头系腰与人类学的亲属研究连接起来。丝头系腰在村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多重的重要意义,本文仅讨论了其与祖先崇拜的关系,从而为人类学“物”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跨文化比较个案。
其三,鲍氏11世祖鲍大千因丝头系腰而成为全村所有姓氏编织者共同的“带子老祖”。两个关于他远赴故里学艺的传说,描述了他的艰辛历程,同时传说也蕴含和表达了鲍屯村民的多重认同。
其四,从祖先与财产的关系来看,鲍姓编织者将鲍大千视为“带子老祖”,符合芮马丁所说的最受惠后裔一定要祭拜施惠的先人;非鲍姓编织者将鲍大千视为“带子老祖”,符合芮马丁所说的,如果一人继承了另一个无血缘关系之人的财产,就应该将其作为祖先进行祭拜。
其五,从宗族/家族的整合与裂变来看,鲍大千作为“带子老祖”,对丝头系腰编织者这个群体而言,只有整合作用,而无裂变作用,原因是其内部缺乏类似族谱一样的贯通上下的系谱。
其六,从祖先与神灵的关系来看,“带子老祖”鲍大千尽管具有将丝头系腰编织技艺惠及全村村民的功德,但仍然还停留在祖先身份的阶段,尚未上升为一个地方性的神灵。表现有二,一是无专门供祭拜的庙宇,二是无神异的灵验传说。
Things,AncestorsandtheirSocialImplications:EthnographyofaMarginalHanChineseSociety
SHI Feng
Abstract:“Sitoujiyao” or silk belt, an essential accessory on the costumes worn by women of Baotun village in central Guizhou, has multiple meanings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Bao Daqian, the 11th ancestor of the Bao’s, passed down the weaving techniques of the silk belt, so he was honored asthe “Old Ancestor of the Belt”. A study of the uniqueness and academic value of Bao Daqian from the aspects of ancestors and property, integration and fission, and ancestors and gods can provide a case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for the study of anthropological “things”.
Keywords:marginal Han Chinese society,silk belt; Bao Daqian,ancestor worship,study of things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19)01-0028-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黔中屯堡‘族一会’型汉人乡村社会研究”阶段性成果(15BSH098)
作者简介:石 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 贵阳,550001)。
(责任编辑 陈 斌)
标签:大千论文; 祖先论文; 宗族论文; 带子论文; 汉人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黔中屯堡‘族一会’型汉人乡村社会研究”阶段性成果(15BSH098)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