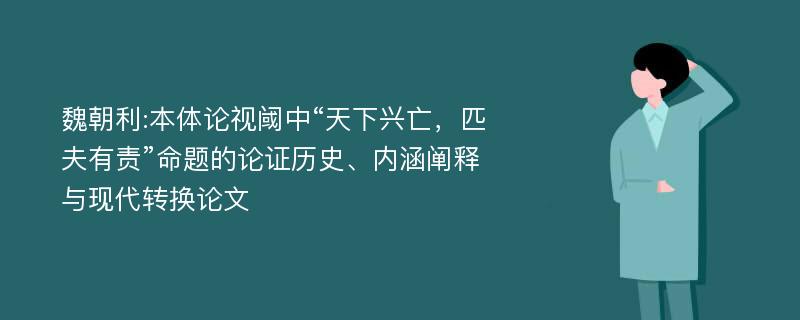
摘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规范性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先后经历了事实论证阶段、天命论证阶段、理学论证阶段与心学论证阶段,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完整表述了这一命题,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等人结合现代政治学概念,转换了这一命题。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内涵,规范了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伦理责任,并且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伦理规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一命题对中国当下社会政治建设与理论建构仍有积极意义,但必须适应现代社会价值,在论证方式与内涵方面实现现代转换。
关键词: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天命 理 心 顾炎武 梁启超
作为命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伦理中的优秀成分。梳理这一命题的发展历史,剖析这一命题的内涵,阐释这一命题的历史价值,对认识传统政治文化是有帮助的。同时,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命题同样面对现代转换的问题,探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命题实现内容与方式的现代转换,或对认识政治思想命题的转换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从事实论证到本体论证: “匹夫有责”命题的论证历史
概念可以根据是否承载价值分为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注]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页。,描述性概念是对事实的描述与解释,规范性概念是对价值、道德伦理等内容的界定、阐释与论证。相应地,命题也可以分为描述性命题和规范性命题。描述性命题是对事实的描述与解释,可以借助对事实的观察检验真假,比如对中国古代政治是否为君主专制政治的判断可以借助史料做判断,而规范性命题则是对伦理与价值的论证与辩护,更多地借助规范性概念、演绎与本体论实现论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命题的完整表述是“天下兴亡,匹夫应有责”,即个人应当对社会共同体的兴亡承担责任。显然,这一命题是规范性命题。通常这一命题被认为是顾炎武或者梁启超提出的思想命题,但是思想史中的命题并非无源之水,这一命题并不起源于顾炎武,早先的思想家为这一命题的提出铺垫了思想资源,这一命题也没有终于顾炎武,后世思想家也为发展这一命题做出了贡献。这一伦理命题的论证过程并不简单。
(一)事实论证阶段
匹夫个体通过个人的言行,对天下或国族等共同体的兴亡承担起责任,作为一种朴素的社会现象自古便有。这可以从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反映出来,比如《诗经·无衣》中“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的记录从侧面反映了秦国百姓为国献身的英勇行为。
原文包含封号、地域等大量文化负载词,译文在处理时补充了公元纪年、地理方位等文化背景信息,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楚国的发展史和疆土变迁。增加这些信息对于跨文化交流是有必要的,然而译文多次用括号加注信息,会打破读者的阅读节奏,不利于读者消化。可以采用尾注的形式在文末体现出来,这样既保证了流畅的阅读体验,又补充了文化内涵。
发展智慧农业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地方政府要积极展开各类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管理和农业科技咨询服务,提升农业竞争力,推动农业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保障产品安全[1]。
孔子、左丘明、《战国策》的作者等史家为什么记载了这些事情呢?在记载史实的同时还有赞扬或讽刺的价值判断要表达吗?在事实与价值尚未被分开的时代,事实论证,即通过描述史例事实,说明与论证伦理命题。《诗经·无衣》等篇章不但是对史实的描述,而且寓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同样,“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删定《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史称“春秋笔法”,一字寓褒贬,将个人的褒贬通过史料表达。《春秋左氏传》与《战国策》等事实的记载也是同样的论证方式,即寓价值伦理于“事实”之中。
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匹夫承担国族兴亡责任的案例更多。比如, 《战国策·魏策四》记载魏国安陵君委任唐雎出使秦国,唐雎与秦王嬴政抗争,言“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不辱使命暂时使得安陵君的封地得以保全。
快速心房纤颤是心脏急症,快速心房纤颤如持续时间过长可引起血流的动力学异常导致心功能下降,增加患者病情,增加住院率及死亡率,和肽素是前精氨酸加压素的羧基肽,克服了精氨酸加压素在临床检测方面的劣势,结果稳定、灵敏度高且保存时间长,最近国内外在临床心衰、心肌梗死中进行了大量研究。本研究对快速房颤患者并结合临床数据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心房纤颤患者血液中和肽素水平与房颤快速房颤心衰的相关性。
事实论证表达了这一伦理观念,同时也是对这一伦理的朴素论证。因为具体的客观第三方,具有超越性,对于言说者和听者都是一定权威的存在,自然带有直观的合理性。将这一伦理的论证诉诸具体第三方,增强了伦理命题的权威性。
但是,事实论证说不得高明,因为事实具有条件性,具体第三方的主张未必适用于言说者与听者。也可以说,事实并不是伦理价值的充分条件,实际现象的论证不能充分论证规范性命题,规范性命题难以用事实充分说明和论证。可以说,叔本华对孔子“没有形而上学作为支撑”的批评是成立的[注]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7页。。伦理说服需要更牢靠的“证据”,古代思想家只能需求另外的论证方式,也就是走向了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论证阶段。
颅内静脉窦血栓属于特殊性的脑静脉系统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包括意识障碍、视乳头水肿以及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等[1]。颅内静脉窦血栓具有发病形势多样、发病原因复杂以及临床症状、体征缺乏特异性等特点,且患者病情进展迅速,增加了误诊以及漏诊率[2-3]。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诊断时间与颅内静脉窦血栓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旨在为颅内静脉窦血栓的早期诊断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二)天命论证阶段
董仲舒也认为匹夫应当对天下承担责任,“君子以天下为忧也”(《春秋繁露·盟会要》)。但是,董仲舒对这一伦理命题的论证摆脱了具体的事实,而是借助于更抽象的第三方——天命或者天理。
“天命”的观念很早就有了,比如《尚书》中的“格知天命”、“受天命”、“服天命”、“逆天命”等。“天命”在《尚书》中已经具有三重属性:其一,“天命不僣”、“天命不易”的绝对属性;其二,“天命有德”的道德属性;其三,“天命殛之”的人格化属性。人类只能“恪谨天命”。这一时期的“天命”被视为人类秩序的本源。具体而言,这一概念多是论证君主受命于天,为君主合法性张目。董仲舒同样将“天命”视为人类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终极原因,不仅承认了“天命”这三种属性,而且将普通人的德性与天命联系起来,以“人副天数”的方式将“天理”视为人之德性的源泉: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天命概念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形而上的支持。对董仲舒而言,首先,“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命具有一定程度的绝对性。其次,“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天命”与“天理”作为抽象第三方对人德性的规定,是至上权威。“以天下为忧”是德性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为了“天命”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天命”概念的引入克服了以具体事实论证伦理命题存在的适用性问题,以更权威的第三方论证了这一命题的合理性。
故而,老子在思维上对统治者进行重塑,使其对“为而不争”有所认识,不执着于外在表现的结果或相对应的形式,只有依道而行,才能在社会整体的平衡和运动中使自身的行动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 从而自然的达到万物自宾、自化的状态,外在有利结果的获得与现实现有威胁的摆脱与需求的满足亦即顺理成章。 例如:
但是这种论证同样存在缺陷。一方面, “天命”、“天理”毕竟还是实体的“天”,实体的“天”则有变化的可能性,因而“天”不在事实上具有绝对性,“天命”、“天理”有变化的可能性,匹夫对天下的责任仍然具有变化的可能性,通过“天命”、“天理”对这一责任作的规范并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天”具有神秘性与不可预测性,因而,这种论证不可避免地带有蒙昧的特点。通过概念来表述这一规范性命题与通过更高层次的本体论论证这一命题是随着理学的发展而实现的。
(三)理学论证阶段
理学家同样认可这一命题,比如程颐言“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三《伊川先生语九》)朱熹注解《中庸》时说到,“反求其本,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推而言之,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中庸章句集注》)更有理学家使用概念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这一主张。比如苏轼曾在多篇文章中论述匹夫与天下的关系,“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注]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90页,第508页。、“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注]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90页,第508页。。这些言论不仅表明苏轼对韩愈等历史人物具体行为的赞扬之情,更表明苏轼试图从义理层面,论证匹夫承担天下兴亡责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此外,还有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文正公文集》卷三《岳阳楼记》)、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剑南诗稿》卷七《病起书怀》)等言论。
理学家的贡献不仅在于表述,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这一命题作出了不同于经学家的论证。理学的本体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哲理化程度的最高阶段,理学家从“天命”、“天道”中提取出“道”、“理”的概念,将“理”或“道”视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原因,从而提升了哲理化程度。 “理”或者“道”具有双重属性:其一,绝对性与最高性,“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其二, “理”是最高的价值原则,具有道德属性,“理便是仁义礼智”(《朱子语类》卷三《鬼神》)。
梁启超等人的贡献重点同样不在于对伦理命题的论证,而在于以现代政治学概念改造了这一命题,从而开启了传统伦理命题的现代转化过程。
科技创新对技术有着很大的要求,科技创新要求企业去运用新的知识创造新的工艺以及制造新的产品,在这基础上,需要企业有新的生产方式,并且要有新的技术管理模式。但是很多企业只是一味的追求新的产品,只追求表面的创新,内里依旧遵循着传统的管理模式,这容易导致企业体系发展不合理,导致企业的科技创新的发展出现问题。同时,很多企业并没有设立内部审计机构,导致审计出现问题没法及时反映给管理部门,使得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甚至是不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决定了企业的发展道路,但企业如果只是一味的对产品的生产或者活动的实施保持着创新态度,那企业的创新道路并不会走远。
但是,“理”是高悬的外在规范,它与人的主体是什么关系?“理”是外在的、合规范性的、被动的。那么,这些特性与人的内在的、目的的、能动的是什么关系呢?人是否只能被动地接受“理”的束缚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由心学来完成的。
他没有得到掌声,甚至反倒对自己一贯在辛娜的面前率先达到终点习以为常了,他再次回到了短跑选手的行列,但他毕竟少了曾经的羞愧或者懊恼。他开始坚信琴瑟和鸣的重要了。不过,在他明白了辛娜选择沙发或许和提升质量有关后,心里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辛娜端正了脸色和姿势,她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每一次的尾随跟进总是在你刚提速的时候比赛就结束了,你能怎么样?
(四)心学论证阶段
陆九渊与王阳明也是认同这一命题的,比如王阳明言:“亲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为一身”[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8页,第19页,第2页,第1482页,第2页,第3页。,“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8页,第19页,第2页,第1482页,第2页,第3页。。
心学家的论证不同于理学家,而是借助“心”与“理”的关系论证这一命题。对心学家而言,“理”仍然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原因与绝对的道德规范。正如陆九渊所言, “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注]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169页,第90页,第149页,第196页。, “义理所在,虽刀锯鼎镬,有所不避。”[注]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169页,第90页,第149页,第196页。然而,外在的“理”与内在的“心”是相同的,“心即理”。陆九渊言“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注]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169页,第90页,第149页,第196页。,王阳明言“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8页,第19页,第2页,第1482页,第2页,第3页。也即将“心”视为人类社会秩序的终极来源与判断标准。
此外,王阳明等人还探讨了“心”的属性。其一, “心”具有同质性,“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注]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169页,第90页,第149页,第196页。,“虽匹夫匹妇之愚,固与圣人无异也”[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8页,第19页,第2页,第1482页,第2页,第3页。,同质性意味着绝对性。其二, “心”具有道德属性,“至善是心之本体”[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8页,第19页,第2页,第1482页,第2页,第3页。,“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8页,第19页,第2页,第1482页,第2页,第3页。。可以说,“心”与“理”具有相同的属性。
因而,借助于“心即理”,心学家实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命题论证由理本体向心本体的转换。在心学家的视野中,这一伦理规范既是外在“理”的要求,也是内在“心”的要求;既是外在规范的要求,也是内在修身良知的要求。心学的论证实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命题合规范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弥合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分歧。
(五)明末清初总结阶段
明末清初时期,思想家顾炎武目睹了异族入主、社会倾颓、伦理崩溃的景象,认为明代的灭亡与君臣士民等各群体没有尽到相应道德伦理责任是有关的,因而,在对明代各社会群体批判的基础之上,相对明确地提出这一命题,抽象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顾炎武的贡献不在于哲理的论证,毕竟顾炎武主张回归到经学阶段,“理学,经学也”,顾炎武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这一命题中的概念和逻辑关系。肉食者、匹夫、国、天下、责等概念被统合到一个命题中,匹夫对天下负有伦理责任这一逻辑关系也被确定。
(六)近代转化阶段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再一次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中。面对严峻的社会危机,梁启超、麦梦华等思想家总结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主张,明确凝练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命题,“斯乃真顾亭林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饮冰室文集》卷三十三《痛定罪言》)此外,梁启超重新组织匹夫、肉食者与国、天下之间的关系,结合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将“天下”替换为“国家”,提出了匹夫应当对“家国之盛衰兴亡”、“国之存亡”承担责任的命题。稍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逐步成为社会规范。
理学家借助于“理”,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伦理命题绝对化。首先, “理”规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样具有绝对性,“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七《孝宗皇帝七》)。其次, “理”规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样是不可挑战的纲常伦理。正如朱熹所言,“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为,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美》) “理”规定了匹夫需要对天下承担仁民爱物等道德责任。
以上六个阶段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过程。比如,早在先秦时期,孟子也有通过概念来表述这一命题,“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南朝刘勰已经直言“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而宋代理学家也在使用“天命”的概念,比如胡安国言,“《春秋》书王必称天者,所章则天命也,所用则天讨也。”(《春秋传·桓公中》)但是整体而言,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随着中国哲学家哲理化程度的提升,思想家逐步超脱出事实论证阶段,对这一伦理命题进行了日益抽象的论证,并经过经学、理学与心学的论证,这一命题成为绝对的伦理规范。
二、单向多层的道德责任:匹夫之责的伦理内涵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政治学、社会学的核心关注议题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命题是儒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通过浮光掠影地梳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演进过程,总结这一命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诉求,可以发现这一命题的内涵。
第一,古代思想家试图探寻这一命题的本体论来源,而不是经验来源。
中国前现代社会,虽然也有思想家试图从社会实践层面解释伦理学命题的产生与流变,但是更多的思想家试图借助本体论对伦理学命题进行论证。借助于本体论中的终极规范,思想家完成了对伦理命题来源的论证。
从分类上看,互对对景、正对对景、侧对对景等类型均有涉猎.互对对景中各景物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等级关系,画面层次感强烈;行政建筑和重大交通建筑以正对对景突出其作为区域核心的地位,表现出较强的秩序感;侧对对景则运用于教堂等文教建筑对景中,突出景物的同时营造出相对自由、轻松的氛围.
同样,西方前现代社会,思想家们也是借助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对伦理学命题作论证,比如泰勒士与赫拉克里特等人主张的元素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基督教方面的上帝、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等概念、康德的绝对道德概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等。思想家们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既是对世界本源追问的结果,也是对伦理秩序来源追问的结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产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力发展,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06年,绍兴市政府通过政校合作率先在全省建设公共实训基地,探索构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区域公共平台,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二,这一命题承认匹夫与天下之间存在关系。这一命题既承认了个人主体能动性的存在,也承认了作为社会共同体天下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承认了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这一命题便与那些认为匹夫与共同体、匹夫与文明之间无涉的学说区别开来。
工分在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社员靠它分配粮食和现金,队干用它组织生产、调节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等。所以辛逸认为:“工分制既是一种分配制度,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劳动的管理制度。”[注]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70-80年代十队的记分方式与全国的其他村落一样,都采取计时和计件两种记分方式。在非农忙季节,一天10分,每天分3节,一节3.3分,每年生产队评1-2次等级。
历代儒家坚持匹夫与天下存在关联,这与道家、佛家以及隐士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道家在古洞仙山中修炼,佛家在名刹古寺中修炼,长沮、桀溺等隐士则主张“辟世”,这三家都是典型的出世主张,不承认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现实合法性。而孔子则主张“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强调了主体作用,表现出积极入世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命题面向社会现实的态度迥异于自然政治观,强调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文化传承的担当需要具体的个体承担,这一命题没有将道德责任归结到家庭、宗族等社会组织,而是将道德责任直接划归具体的个人,体现了儒家对个体主体性的认识。
第三,这一命题认为匹夫对天下的关系是单向责任关系。这一命题强调匹夫对共同体单向地负有责任,甚至这种责任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是无条件的;同时,这一命题不是强调匹夫享有的权利,因而,匹夫对天下的责任关系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特征,以集体或共同体为本位,而不是相反地以个体为本位。
不同于部分极端个人主义者主张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倡导的道德优先性排斥了这种绝对个人主义。即便这一命题不能从伦理学上为伦理体系构建提供标准答案,也能够为我们理解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独特的理论视角。
中医药调节肿瘤转移前微环境虽然已有学者提出[29-30],但关于转移前微环境的形成、功能、动力学等问题迄今尚未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希望利用中药多靶、微效、双向调节等特点,通过对肿瘤功能基因网络的影响,在肿瘤相关生物分子基因表达和组合上发挥整体调节作用。
第四,这一命题强调了匹夫对天下的责任关系是道德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
不同于动物世界,人类社会生活不是完全地遵守丛林法则,人类具有道德与伦理的属性。对于道德伦理的认识与反思,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这一命题以伦理的视角规范社会秩序,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
践行这一伦理命题是道德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这一命题的倡导与惩戒,虽然不排斥法律与强制途径,但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对个人行为的评判主要不是依靠法律规定的奖赏或惩处,而是清议与社会舆论。
再如,孔子删定的《春秋》中记载了齐桓公攻打鲁国的长勺之战,“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左丘明在此注解了曹刿的事迹。 《左传·庄公十年》中记载,曹刿反对鲁国乡人“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主张,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理由请见鲁庄公,进而献策退却齐军。
第一,论证方式的转变。
首先,这种道德责任是在日用生活中,对同胞、同类的具体救助责任。这尤其体现为顾炎武坚持孟子的仁爱思想。顾氏认为,仁义充塞、率兽食人或者同伴相互残害、人将相食的社会现象是不可容忍的,同类之间的互助道德责任是必不可少的。
仿佛涓涓溪流终于汇集成河。“me too”也由此得到中文译名:“我也是”“俺也一样”“米兔”。在“米兔”的鼓励下,那些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受害者冲破了耻感文化的禁锢,勇敢发声。“米兔”最大的意义,就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守望相助、勇于表达的空间。
其次,这种道德责任是匹夫对国族等政治实体的认同责任。顾炎武作为明代遗民坚持华夷之辨,不仕清朝,梁启超多次参与政治运动,这些行为是践行这一层次的表现。以梁启超的政治行为为例,鉴于袁世凯即将签订《二十一条》,梁启超立即作文号召国民抗议袁世凯;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的中国非官方代表,得知北洋政府准备签订合约,立即将这一消息传回国内,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此外,在近代革命史过程中,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章太炎在《革命道德说》等文中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周恩来主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命题对他们领导革命事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这种道德责任较为抽象,即匹夫对道义文明的认同责任。比如,顾炎武对魏晋玄学和明末王学末流的批判源于其认为这些学说的流行是士人对儒家文化缺乏认同,没有承担起繁衍儒家文化的责任。在文化领域,与梁启超同年代的思想家王国维、罗振玉二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期,“以亭林相期”,二人致力于保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延续国脉,便是践行这种责任的行为表现。
三、转换与扩展:传统伦理命题的现代方向
这一伦理命题曾经对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当下的社会政治生活建设与学术理论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时过境迁,这一伦理命题的论证方式与内涵面临现代政治理念的质疑,这一伦理命题继续发挥作用有必要适应现代社会。
第五,这一命题主张匹夫对天下的道德责任关系是多层次的。
诉诸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论证,与其说这是一种论证,不如说是对伦理“教义”的再次确信。以心学家的“心即理”判断为例,“心外无物”的概念界定并不是对“心”和“理”关系的论证,“即”与“不即”之间的更多可能性需要讨论。
在现代社会,淡化规范性命题的倾向突出,但人类不可能是“价值真空”的存在,道德与伦理对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现代社会仍然有较强的规范性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行为逐渐蚕食道德领域,“道德滑坡”逐渐成为社会现实,增强道德共识与文化认同,匹夫之间有条件地承担互助的道德责任,仍然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元素。在这方面,这一伦理命题仍然可以成为社会成员行为的价值原则。
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接受或者拒绝规范性命题的权利交付给个体,公民依据理性,甚至经验、情感等直观因素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公民即便接受这一命题,也不再诉诸本体论论证,而是接受习惯、风俗等已有规范,拒绝也不再需要强有力的本体论反驳,而是直接用经验等因素拒绝。比如,以现代学者的视角看,这一命题前四个阶段的论证难以成立,既不存在“天命”,也不存在“天理”,既不存在“理”,也不存在“心”,对匹夫做这样的伦理要求,这种诉诸本体论的说服工作是没有效用的。
因而,伦理学家不再试图对这一伦理命题做本体论的论证,“拒绝一切不是建立在事实和观察基础之上的、不论多么玄奥或精妙的伦理学体系”[注]休谟:《道德原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页。,而是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转而寻求解释这一命题的产生与流变。
总之,“回到现实”是解释和论证伦理命题的途径,现代社会将伦理视为已有社会现实的反映,伦理命题是借助思想家之口表达出来。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伦理界之通例,非先有学说以为实行道德之标准,实伦理之现象,早流行于社会,而后有学者观察之、研究之、组织之,以成为学说也。”[注]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页。对这一伦理命题的现代论证需要转变以往的本体论论证方式,中国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现实因素需要引入对这一命题的解释与论证中来。
第二,内涵的转变与扩展。
古今时空环境不一样,即便这一命题的表述一仍其旧,即便这一命题仍旧试图为社会生活提供价值规范,但其内涵需要作出转变与扩展以适应现代社会。
首先,这一命题以往是政治学领域的命题,现在面临由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转型的问题。以往,这一命题尤其在国族危亡时机发挥作用。然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当下中国处于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中,匹夫之责的内容与范围可以实现转换,由赢取民族独立转变为文化认同、社会互助等。
其次,匹夫负责的方式,由绝对义务向相对义务的转换。传统社会要求匹夫对天下无条件负责,但是现代社会中公民负责的方式则是有条件的,甚至随着平权运动的发展,公民日益强调天下、国家或者共同体对个体的责任。这时,这一伦理命题不得不面对公民质疑甚至更弦易辙的态度。
第二阶段:通过标准修订及数据更新,将军有民无中的部分非军事特有要素纳入到第一部分中,扩充军民共同表达要素。
最后,这一命题隐含的二分法思维方式需要转换。二分法具有简单明了的分析优势,但是二分法往往对复杂关系的论述不够准确。比如,这一命题隐含了天下——国家、匹夫——肉食者的二分法,肉食者谋政事,匹夫对社会文化、道德伦理负责。这一命题没有论述匹夫对朝廷、公民对政府的关系,结果便是匹夫难以发挥对政治系统的监督与制约作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的时空环境中,匹夫的这种不对政事负责的冷漠态度助长了君主专制的程度。现代政治学核心的问题是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现代政治学不可能再回避这一关系,这一命题如何解释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尚需补充。
四、小 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命题经过历代儒家思想家的论证,成为古代中国的道德伦理规范,并且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实际的作用。诸如此类中国传统伦理命题仍然有激活的必要,因为这些命题不仅仍然对社会生活有着现实影响,而且能够为现代价值体系提供必要的参照,从而成为现代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是这类命题不得不适应现代社会,在论证方式与内涵方面需要现代学人做具体分析。
本文仅对思想家的文本做粗浅的梳理,这一命题的形成与演化以及这一命题与社会政治史实的互动过程则需要更准确的描述与解释。此外,这一命题的现代论证,更需要分析哲学等现代哲学的知识背景,作者力有未逮之处,尚需做进一步的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化的协同推进机制研究”(编号:15BKS020)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03-06
[作者简介]魏朝利,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上海 200020
(责任编辑:赵荣华)
标签:这一论文; 命题论文; 匹夫论文; 伦理论文; 天命论文; 《天府新论》2019年第4期论文;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化的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15BKS020) 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