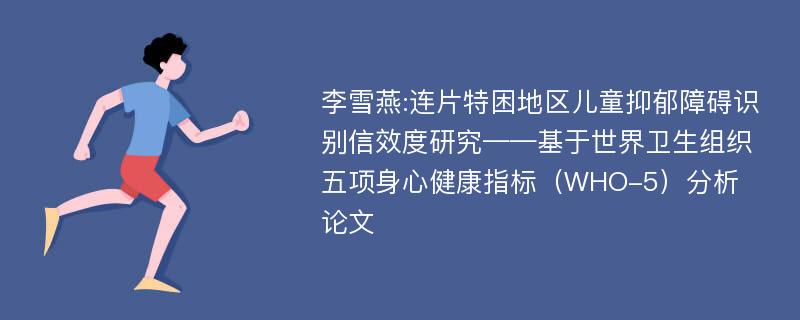
摘 要:考察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ive-item Well-Being Index,WHO-5)在识别连片特困地区儿童抑郁障碍中的信度和效度。用WHO-5对湖北省连片特困地区两个县5所小学、4所初中和3所高中的727名学生施测,随机各取一半样本分别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判定其结构效度;同时以儿童焦虑、社会适应不良和心理弹性作为外在效标,判定其效标效度;计算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发现:WHO-5单因子结构获得验证;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1;WHO-5与儿童焦虑、社会适应不良、心理弹性均呈现显著相关,效标效度得到验证。结果表明:WHO-5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良好的效度;适用于对连片特困地区儿童抑郁障碍的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留守儿童面临严峻的抑郁风险。
关键词: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 WHO-5 信度 效度 连片特困地区
一、前 言
抑郁是儿童青少年面临的主要心理风险之一,也是个体在生命全程中最常发生的心理障碍之一。根据抑郁问题的程度及范围,有学者(Compas,Ey,&Grant,1993)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即抑郁情绪、抑郁症候群(抑郁症状)、抑郁障碍。据西方相关研究估计,6-12岁儿童重性抑郁障碍患病率为2%,13-18岁青少年患病率为4%-8%,约5%-8%的儿童青少年出现重性抑郁的亚综合征症状(Birmaher et al.,2007;Birmaher,Ryan,Williamson,Brent,&Kaufman,1996)。在我国,一项针对2634名中学生的抑郁症状流行病学研究报告中学生抑郁症状发生率达42.3%(冯正直和张大均,2005)。出现抑郁问题的儿童面临严峻的心理社会障碍、自杀风险以及发展为重性抑郁障碍的风险(Fergusson,Horwood,Ridder&Beautrais,2005;González-Tejera et al.,2005)。儿童抑郁发生风险高且影响严重,值得特别重视。
与一般儿童相比,生活于连片特困地区的儿童面临更为严峻的贫困考验。相关研究发现,贫困对儿童造成身体和心理的损害。相对而言,生活于贫困家庭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精神障碍症状、社会功能适应不良;各年龄段的儿童均面临更大的抑郁风险(Bradley&Corwyn,2002;Brooks-Gunn&Dun-can,1997;Joinson,Kounali,&Lewis,2017)。此外,生活于连片特困地区的儿童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留守儿童。他们正处于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长期缺少父母的陪伴、关爱与引导;代养人的文化素质较低、教养方式不当、监管不力,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学校教育对心理健康重视程度不够。相关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经常表现出敏感、孤独、自卑、抑郁、自我封闭、感情脆弱、消极孤僻、缺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林细华、沈敏、王琳、王友洁、2010;刘霞et al.,2013;张帆、刘琴等,2011),种种心理问题的出现可能对儿童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化进程构成损害。连片特困地区的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其抑郁问题更加需要重视。
为对儿童抑郁进行筛查并干预,抑郁的测量问题突显出来。现存的多数儿童抑郁测查工具大多题项多,专业测查程序复杂,且问题表述负面多有侵入性,不利于在儿童减贫及儿童保护框架下的广泛应用。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ive-item Well-Being Index,WHO-5)是评价主观心理健康最常用的工具之一。相对于其他识别儿童抑郁的工具(陈祉妍、杨小冬、李新影,2007)而言,WHO-5题项简短,问卷内容表述积极正向,不会对被试,尤其是抑郁患者产生负面影响。最初的版本有28个题项,后几经删减形成目前的5题项版本。一项针对WHO-5的系统性综述研究(Topp,Østergaard,Søndergaard&Bech,2015)指出,WHO-5应用广泛,具有高临床测量效度,高敏感度和特异性,既可用作抑郁的筛查和诊断工具,也可用作临床干预后的结果测量。虽然WHO-5临床测量特征与心理测量学属性优良,在国际学界应用广泛,但是在我国儿童,特别是以儿童减贫与儿童保护为背景的儿童抑郁筛查干预应用却为数极少(王舟、卞茜,2011)。考虑到连片特困地区儿童可能面临的心理与社会剥夺,罹患抑郁的高风险以及WHO-5呈现出来的优良心理测量学属性,本研究拟在连片特困地区儿童中采用WHO-5考察其信效度,以期考察WHO-5作为筛查儿童抑郁工具的有效性及适用性。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取样。首先在湖北省四个连片特困地区选择大别山片区、武陵山片区各一个县(大别山片区A县,武陵山片区B县);按照高中、初中和小学分别取样。高中取样在A县仅有的两所高中,B县仅有的一所高中进行,实际完成随机取样回收有效问卷包括高一59份,高二61份,高三63份。小学和初中取样首先在A县17个乡镇和B县9个乡镇各随机选取两个乡镇,然后在各乡镇的小学和初中的各年级随机取样。4个乡镇实际随机取样回收有效问卷包括一年级60份,二年级55份,三年级58份,四年级63份,五年级60份,六年级68份,七年级60份,八年级60份,九年级60份。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共完成随机抽样获得有效问卷727份,平均每个年级超过60份。其中男生383人,占52.7%;女生332人,占45.7%;汉族学生458人,占63.0%;少数民族学生绝大部分来自武陵山片区B县,主要包括土家族、侗族和苗族,共265人,占36.5%。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507人,占69.7%,其中填答了外出打工情况的490人中父亲外出占52%、母亲外出9%和父母都外出39%。
(二)研究工具
1.WHO- 5中文版
本研究根据日本铃木清等人编制,周步成修订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周步成,1991),选择学习焦虑(15个题项)和对人焦虑(10个题项)分量表。该量表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除港、澳、台之外)几千所中小学广泛使用后,信度和效度高,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强,是全国最好的心理测量工具之一。本量表采取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1)到“完全符合”(5)。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焦虑感越强。
2.其他用于效标检验的工具
(1)焦虑倾向
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ive-item Well-Being Index,WHO-5)中文版量表取自WHO官方网站提供的免费中文翻译版本,共有5个题项。WHO-5要求被试根据自己最近两周的感觉状态填写问卷,选项包括“所有时间(5)、大部分时间(4)、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3)、少于一半的时间(2)、有时候(1)、从未有过(0)”。将被试每个题项的选项分相加得到总分;总分越高,表示被试抑郁程度越低。WHO-5各题项的具体内容见表2。
(2)孤独倾向
在容量为364的样本2中,采用IBM SPSS Statistic version 20的AMOS模块,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在判断模型拟合的各项指标中,本研究主要报告卡方(Chi-square),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p值(p value),相对卡方值(relative chi-square),RMSEA和CFI。当相对卡方值小于5(Wheaton,Muthén,Alwin,&Summers,1977),RMSEA小于0.08(Maccallum,Browne,&Sugawara,1996),CFI大于0.90(Bentler,1990),模型即被认为拟合优良。
(3)社会适应不良倾向
本研究参考杨彦平、金瑜编制的“中学生社会适应量表”(杨彦平和金瑜,2007)社会交往适应(8个题项)、家庭环境适应(3个题项)和校内人际关系(7个题项)三个分量表。所有题项均为5点反向计分,从“完全不符合”(1)到“完全符合”(5)。分数越高,表示社会适应越不良。
(4)心理弹性
6)潜在替代量:该指标主要考虑区域现有替代对象的存量以及未来发展的增量情况。例如供暖电锅炉在北方区域就较多,而在南方则完全不用考虑。同时,分析各种潜在替代量对后期选择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随后进来的是个胖大警官,一进门就盯住吴邦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站着。吴邦雄愣住,不敢马上坐下,刚才因激动而潮红的脸,这会儿一点点灰白下去。
本研究选取Connor和Davidson编制,于肖楠、张建新修订的“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的坚韧性分量表(Connor&Davidson,2003;Yu&Zhang,2007)。该量表在不同人群中的施测均显示良好的信效度,对于心理弹性的预测效力已得到公认,应用较为广泛。本量表共有13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1)到“完全符合”(5)。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良好。
(三)测试方法
我在文身店游逛,看墙上挂着的艺术品,欣赏这些画面。我突然意识到,唯一有艺术家的是友好派,无私派则把艺术视作不着边际的东西,因为欣赏艺术的时间可以用来帮助他人。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只能在教科书中看到这些艺术品,在现实中却从未踏人艺术展厅。空气中飘散着温馨亲切的气息,我沉浸于其中不能自拔。我用手指轻轻滑过墙壁,一面墙上一幅有鹰的画作闯人我的眼帘,这鹰似曾相识,好像在托莉脖子后面也文着相同的一只。在鹰的下方挂着一幅展翅飞翔的飞鸟素描。
针对高中的取样与测试,由于本研究取样的湖北省四个连片特困地区的两个贫困县,其高中均设在县城所在地,因此县扶贫办协调当地教育局分别提供两个县的高中学校名单。
针对初中和小学的取样和测试,县扶贫办首先提供本县的各乡镇名单,本研究人员利用SPSS软件从中简单随机抽取各两个乡镇。其次,县扶贫办协调教育局提供被抽选乡镇的初中和小学名单,本研究人员利用SPSS软件从中简单随机抽取各两所初中和小学。再次,根据被抽选的初中和小学的学生名单,本研究人员利用SPSS软件分别从各年级学生名单中进行简单随机抽样。计划各县各学校各年级随机抽取15人,实际基本完成计划。对于因部分学校的部分年级规模过小(小于15人),采取到就近学校替补的方法补齐。
在学生名单中标注被抽选学生,请学校相关人员将被抽选学生集中于一个教室。调研员确认每个学生的姓名信息,随后简单介绍调研目的及指导语,强调隐私和保密问题,分发问卷,学生作答。对于被抽选但缺勤的同学,采取现场随机抽样替补的方法补齐。其中,小学一至三年级被抽选学生单独集中于一个教室,由调研员逐题阅读,并加以简单解释,辅助完成。
WHO-5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系数为0.71,各题项分别删除后的信度值在0.65-0.68之间,均低于0.71。折半法Spearman-Brown系数为0.69。这两项系数值均表明WHO-5内部一致性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此外,本研究还对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关(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进行分析(见表4),发现所有5个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关为0.43-0.49,均超过0.40。
(四)统计方法
抑郁常与多种心理问题伴随发生。多项大规模调查显示,抑郁和焦虑多以共病形式出现。美国对1990~1992年间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的年龄为15-54岁的8098例患者研究发现,在年轻人群中,焦虑障碍与抑郁障碍的12个月时点共病率达56.1%(Kessler&Walters,1998);2001-2003年的又一轮调查结果发现,抑郁障碍与焦虑障碍终身共病率和12个月时点共病率分别高达59.2%和57.5%(Kessler et al.,2003)。另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超过75%的抑郁患者共患有不同类型的焦虑障碍(Sartorius,Üstün,Lecrubier,&Wittchen,1996)。针对儿童抑郁与焦虑的研究也支持上述发现,即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鉴于此,本研究选用焦虑作为效标做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儿童WHO-5得分与其学习焦虑得分、对人焦虑得分均呈现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1(p〈0.001)和 -0.14(p〈0.001);即儿童WHO-5得分的越高(即抑郁程度越低),学习焦虑程度就越低,对人焦虑程度就越低。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关于抑郁与焦虑以共病形式出现的结果一致。
三、结 果
(一)结构效度
本研究将总样本(n=727)随机分半,一半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1容量为N=363);另一半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样本2容量为N=364)。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容量为363的样本1中,经检验,WHO-5的5个题项的KMO值为0.78,Bartlett球形检验小于0.001,说明题项之间存在相关,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采用principal component抽取因子,不旋转因子,采用Kaiser方法和Cattell陡阶检验确定选取的因子数目。
依据Kaiser方法(表1),只有因子1的特征值大于1,此因子可解释45.03%的变异(贡献率),因此WHO-5只取1个公因子。依据Cattell陡阶检验碎石图(图1),同样表明WHO-5只适宜取1个公因子,提示WHO-5为单因子结构。因此,综合考虑Kaiser方法和Cattell陡阶检验碎石图结果,数据支持析出1个因子,与原始理论构想一致。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子载荷如表所示(表2),所有因子载荷在0.63-0.70之间,均大于0.60。
表1 WHO-5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因子1 2 3 4 5特征值2.25.77.72.65.61贡献率%45.03 15.44 14.37 13.02 12.14累积贡献率%45.03 60.47 74.84 87.86 100.00
图1 WHO-5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碎石图
表2 WHO-5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因子载荷
编号D1 D3 D5因子载荷.69.69.70题项我感觉快乐、心情舒畅。我感觉充满活力、精力充沛。我每天生活充满了有趣的事情。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选择Asher等(Asher,Hymel,&Renshaw,1984)编制,“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标准化测验”项目组修订的“儿童孤独感量表(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CLS)”。该量表是目前国内外使用和引证最为广泛的针对儿童孤独感的测查问卷,信效度等测量学指标良好。本量表共10个题项,采取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1)到“完全符合”(5)。分数越高,表明被试孤独倾向越强。
在样本2中,假设五个题项均测量同一个潜在概念结构,并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拟合指标见表3。模型的各拟合指标均达到拟合优良的标准。各题项的因子载荷见图2,均显著且大于0.40。基于上述结果,WHO-5的单因子结构得到验证。
其中:γ为上覆岩层的平均容重,KN/m3;p为均布载荷,kPa;y为底板上任意一点的深度;Ka为主动压力系数,Ka=tan2 (45°-φ/2);Kp为被动压力系数,Kp=tan2 (45°+φ/2)。
表3 WHO-5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指标Chi-square df p Relative chi-square RMSEA CFI判定标准〉.05〈5〈.08〉.90模型9.251 5 0.099 1.850 0.048 0.985
图2 WHO-5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1
(二)效标效度
本研究所获得的数据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管理。判定结构效度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的AMOS模块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用Cronbach α系数表示。效标效度采用相关分析。
此外,本研究也考察儿童抑郁与孤独、社会适应不良(社会交往适应不良、家庭环境适应不良、校内人际关系不良)、心理弹性的关系。结果发现儿童WHO-5得分与孤独得分、社会交往适应不良得分、家庭环境适应不良得分、校内人际关系不良得分均呈现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9(p〈0.001),-0.17(p〈0.001),-0.22(p〈0.001)和 -0.31(p〈0.001),与心理弹性得分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4(p〈0.001)。这表明儿童WHO-5得分越高(即抑郁程度越低),孤独程度越低,社会交往适应不良、家庭环境适应不良、校内人际关系不良程度越低,心理弹性程度越高。这一结果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因此本研究以儿童焦虑、孤独、社会适应不良(社会交往适应不良、家庭环境适应不良、校内人际关系不良)、心理弹性作为儿童抑郁的外在效标进行效标效度检验,发现所有效标变量均与抑郁相关,为儿童抑郁的效标效度提供了支持证据。
在进行夹心外保温复合墙的构建上,顾名思义,墙体的中间会进行一层保温材料的加设。在这种墙体的布局规划上,夹层可以是采用一些复合保温材料进行填充,同时也可以采用空心夹层的方式进行布局。具体采取哪种布局方式需要结合地区以及保温性能要求特定进行合理的筛选。
表4 抑郁问题的题项分析(N=688)
?
(三)内部一致性信度
螺虫乙酯分别按照2000倍和3000倍稀释液喷施2次和3次,距末次施药后7 d、14 d、21 d和28 d采样测定,螺虫乙酯在猕猴桃中的含量为 0.06~0.52 mg/kg。
受到索绪尔与雅各布结构研究的影响,格雷马斯认为意义产生于以二元对立思想为基础的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语义要素本身并不能产生意义,语义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才产生出了所谓的意义。在对叙事作品的解读当中,要特别关注其中的对立关系。
四、讨论与结论
(一)儿童抑郁的信效度
本研究在727名连片特困地区儿童中对WHO-5进行信效度检验。在信度方面,WHO-5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0.71),基本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但低于以往研究报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0.91(王舟和卞茜,2011)。这可能与研究所选取的样本群体差异有关。王舟、卞茜(2011)的研究选取上海高一至高三中学生,而本研究选取在连片特困地区的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儿童。以往研究鲜见WHO-5在连片特困地区儿童中的施测与检验。
在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支持WHO-5为单因子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数良好,因子载荷系数达到预期,验证了单因子结构。此外,儿童的WHO-5得分与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社会交往适应不良、家庭环境适应不良、校内人际关系不良得分显著负相关,与心理弹性得分显著正相关,为WHO-5的效标效度提供了证据。总之,在连片特困地区儿童中,WHO-5的信效度均得到检验,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2.3 超声微泡造影剂携RPM对PCNA的mRNA及蛋白表达影响 PCNA 的mRNA 表达产物校正后分析,对照组、RPM组和超声微泡造影剂携RPM组统计结果用±s表示:分别为219.31±7.21,147.32±10.27和97.17±8.79,两两比较RPM组和超声微泡造影剂携RPM组两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同时超声微泡造影剂携RPM组也明显低于RPM组。使用Westernblot检测T24 细胞PCNA蛋白的表达量,结果表明在RPM和超声微泡造影剂携RPM作用细胞24 h后,两组细胞的PCNA蛋白的表达量明显下降(图2)。
(二)连片特困地区儿童的抑郁风险
WHO官方网站提供了两种评分方式,第一,以5题项答案数值总和计算的初始计分,计分范围为0-25,其中0代表最差,25代表最好;第二,以百分制计分,计分范围为0-100,是以初始计分乘以4得到百分制分数,0代表最差,100代表最好。同时WHO网站还提供了对WHO-5初始计分得分的诠释,其中对于被试得分低于13分或者对五项中任何一项答分为0或1的被试,建议进行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重型抑郁症问卷调查。除了WHO网站建议的针对初始计分的界限值(cutoff score),不同学者也针对百分制计分也提出了不同的界限值。基于213篇运用WHO-5的研究的系统性综述,Topp等人(2015)建议采用百分制的50分作为筛查临床抑郁的界限值。百分制的50分相当于原始计分的13分,因此与WHO网站的建议界限值事实上是一致的。因此本研究以原始计分的界限值13分进行讨论。基于此标准,本研究对连片特困地区727名儿童的WHO-5得分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完整作答所有5个题项的688名儿童中,得分〈13分的儿童占51.5%,五项中的任何一项的答分为0或1的儿童占72.1%。以两项标准筛查的儿童抑郁发生率非常高,这表明连片特困地区的儿童面临非常严峻的抑郁风险。
同时,这一结果远高于以往研究报告的结果。冯正直、张大均(2005)报告重庆和四川2634名初一至高三中学生的抑郁症状发生率为42.3%。而将本研究中的初一至高三子样本单独抽取出来,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完整填答5个题项的357名中学生中,得分〈13分占58.3%。这一结果仍然远高于以往研究报告的42.3%。王舟、卞茜(2011)报告上海706名高中生的抑郁障碍发生率为18.3%。进一步将本研究中的高中生子样本单独抽取出来分析发现,在完整填答5个题项的182名高中生中,得分〈13分占57.7%。这一结果远高于以往研究报告的18.3%。
本研究与以往研究报告的抑郁发生率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是因为,(1)样本地区不同。本研究的对象是湖北省连片特困地区的儿童,不同于重庆和四川的非特困地区,更不同于上海的沿海发达地区。在连片特困地区,细分到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子样本一致性地呈现出抑郁高发生率,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连片特困地区儿童的心理剥夺状况,表征了以往在儿童贫困研究中常遭忽视的贫困与剥夺的重要面向(Barajas,Philipsen,&Brooks-Gunn,2007)。此外,湖北省连片特困地区儿童抑郁发生率最高,其次是重庆和四川,再次是上海。儿童抑郁发生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大致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在另一个侧面上反映了儿童面临的心理风险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Birmaher et al.,2007;Brooks-Gunn&Duncan,1997;Joinson,Kounali,&Lewis,2017)。
(2)筛查工具和界限值不同。冯正直、张大均(2005)根据Beck抑郁自评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和Zung氏抑郁量表(Zung Self-Depression Scale,SDS)轻度(BDI:5-13分,SDS:41-47分)、中度(BDI:14-20分,SDS:48-55分)和重度(BDI:≥21分,SDS:≥56分)抑郁症状的判断标准,要求必须满足两个量表的评定标准,即BDI≥5分且SDS≥41分,作为判定抑郁症状阳性的界限值;BDI≥14且SDS≥48的儿童占27.8%。而王舟、卞茜(2011)是采用WHO-5进行初测,同时使用Beck抑郁量表(BDI),BDI≥14分的儿童占18.3%。尽管两项研究采用的判定标准不完全一致,无法将抑郁发生率做严格的比较,但是两者均采用了BDI,大致仍然可以看到前者报告的抑郁发生率明显高于后者。这又从另一个侧面为前述解释即样本地区差异提供了佐证。考虑到王舟、卞茜(2011)的研究虽然使用WHO-5,但并没有报告以WHO-5界限值(初始计分)的抑郁发生率,本研究无法与之进行直接比较。
通常,IEEE802.11p在120公里每小时下,一般可以执行18 Mbps左右的接入速率,以此来计算,已经有足够的冗余,能充分满足车联网需求。
(3)被试群体不同。有研究表明儿童抑郁的发生呈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冯正直和张大均,2005;侯金芹和陈祉妍,2016),11-13岁儿童抑郁患病率比8-10岁高,以14-16岁最高(Simonoff et al.,1997);13-16岁青少年阶段的儿童抑郁发生率高于9-12岁阶段的儿童(Allgaier et al.,2012);也有研究者发现从青少年早期到中期,抑郁随年龄增长(Ge,Natsuaki,&Conger,2006)。本研究的样本覆盖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7岁-17岁儿童,而以往研究或者针对初一至高三(冯正直和张大均,2005)或者针对高一至高三的学生(王舟和卞茜,2011)。被试群体的年龄范围不同可能是抑郁发生率不同的一个原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者认为年幼儿童有限的认知能力和阅读技能可能会影响其填答自我报告的抑郁筛查工具(Achenbach,1991),本研究尽管采用了研究员及教师辅助一到三年级儿童填答的做法,但是这部分儿童的填答仍可能受到影响。
(三)连片特困地区留守儿童的抑郁风险
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留守儿童的单独分析发现,在完整填答5个题项的477名留守儿童中,得分〈13分占50.9%,五项中的任何一项的答分为0或1的占73.3%。这同样比以往研究报告的数字高得多。一项针对重庆4875名7岁到17岁留守儿童的研究(Wang et al.,2015)报告儿童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24.8%。另一项针对湖北590名四到六年级留守儿童的研究(He et al.,2012)报告儿童抑郁症状发生率为15.3%。这两项研究均采用儿童抑郁问卷(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与本研究采用的WHO-5不同。排除可能存在的样本地区差异、筛查工具差异、被试群体差异造成的抑郁发生率差异之外,本研究所报告的连片特困地区留守儿童的高抑郁发生率更可能与其遭遇的更为严重的心理与社会剥夺有关(He et al.,2012)。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抑郁的风险因素包括父母的缺位,亲子沟通的缺乏,以及沟通方式的单一化(Wang et al.,2015)。处于身体与心理成长期的儿童无法就一些重要的成长议题与父母建立稳定有效的沟通,无法及时获得心理社会支持。这些风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儿童抑郁的发生。
不仅是《圣经》还是《佛经》还是谚语,都给红月赋予了灾难的形象。《罪与罚》中没有大量的叙述,仅用了个“红月”就将小说境界全然升华,让所有人都明白阿斯科尔尼科夫的命运,小说以最简练的情景,用几个字传达出了一个贯穿整个小说的线索——阿斯科尔尼科夫正一步步走向灾难。
综上,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WHO-5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良好的效度。(2)适用于对连片特困地区儿童抑郁障碍的识别。(3)连片特困地区留守儿童面临严峻的抑郁风险。
[参考文献]
陈祉妍、杨小冬、李新影,2007,《我国儿童青少年研究中的抑郁自评工具(综述)》,《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6期。
冯正直、张大均,2005,《中学生抑郁症状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第2期。
侯金芹、陈祉妍,2016,《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界定亚群组及其影响因素》,《心理学报》第8期。
林细华、沈敏、王琳、王友洁,2010,《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Meta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第2期。
刘霞、张跃兵、宋爱芹、梁亚军、翟景花、李印龙等,2013,《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Meta分析》,《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第1期。
王舟、卞茜,2011,《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在识别高中生抑郁障碍中的信效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4期。
杨彦平、金瑜,2007,中学生社会适应量表的编制,《心理发展与教育》第4期。
张帆、刘琴、赵勇、孙敏红、王宏,2011,我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的系统评价,《中国循证医学杂志》第8期。周步成,1991,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chenbach,T.M.1991,Manual for the Youth Self-report and 1991 Profile:Department of Psychiatry,University of Vermont Burlington,VT.
Allgaier,A.K.,Pietsch,K.,Frühe,B.,Prast,E.,Sigl-Glöckner,J.,Schulte-Körne,G.2012,.“Depression in pediatric care:is the WHO-Five Well-Being Index a Valid Screening Instrument for CChildren and Adolescents?”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34(3).
Asher,S.R.,Hymel,S.,Renshaw,P.D.1984,“Loneliness in Children”,Child Development55(4).
Barajas,R.G.,Philipsen,N.,Brooks-Gunn,J.2007,Cognitive and Emotion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in Poverty.In C.D.R&H.T(Eds.),Handbook of families and poverty(311-333).Newbury Park,CA:Sage.
Bentler,P.M.1990,“Comparative Fit Indexes in Structural Models”,Psychological Bulletin107(2).
Birmaher,B.,Brent,D.,Bernet,W.,Bukstein,O.,Walter,H.,Benson,R.S.,et al.2007,“Practice Parameter for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Adolescent Psychiatry46(11).
Birmaher,B.,Ryan,N.D.,Williamson,D.E.,Brent,D.A.,Kaufman,J.1996,“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a RReview of the Past 10 Years”,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35(11).
Bradley,R.H.,Corwyn,R.F.2002,“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1(3).
Brooks-Gunn,J.,Duncan,G.J.1997,“The Effects of Poverty on Children”,Future of Children7(2).
Compas,B.E.,Ey,S.,Grant,K.E.1993,“Taxonomy,Assessment,and Diagnosis of Depression During Adolescence”,Psychological Bulletin114(2).
Connor,K.M.,Davidson,J.R.T.2003,“Development of a New Resilience Scale: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Depression and Anxiety 18(2).
Fergusson,D.M.,Horwood,L.J.,Ridder,E.M.,Beautrais,A.L.2005,“Subthreshol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in Adulthood”,Arch Gen Psychiatry62(1).
Ge,X.,Natsuaki,M.N.,Conger,R.D.2006,“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Among Male and Female Adolescents in Divorced and Nondivorced Families”,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18(1).
González-Tejera,G.,Canino,G.,Ramírez,R.,Chávez,L.,Shrout,P.,Bird,H.,et al.2005,“Examining Minor and Major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Psychiatry46(8).
He,B.,Fan,J.,Liu,N.,Li,H.,Wang,Y.,Williams,J.,et al.2012,“Depression Risk of‘Left-behind Children’in Rural China”,Psychiatry Research200(2-3).
Joinson,C.,Kounali,D.,Lewis,G.2017,“Family Socioeconomic Position in Early Life and Onse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Depression: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Social Psychiatry&Psychiatric Epidemiology52(1).
Kessler,R.C.,Berglund,P.,Demler,O.,Jin,R.,Koretz,D.,Merikangas,K.R.,et al.2003,“The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NCS-R)”,Jama289(23).
Kessler,R.C.,Walters,E.E.1998,“Epidemiology of DSM-III-R Major Depression and Minor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Depression&Anxiety7(1).
Maccallum,R.C.,Browne,M.W.,Sugawara,H.M.1996,“Power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Sample Size for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Psychological Methods1(2).
Sartorius,N.,Üstün,T.B.,Lecrubier,Y.,Wittchen,H.U.1996,“Depression Comorbid with Anxiety:Results from the WHO Study on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in Primary Health Care.”.Br J Psychiatry Suppl168(30).
Simonoff,E.,Pickles,A.,Meyer,J.M.,Silberg,J.L.,Maes,H.H.,Loeber,R.,et al.1997,“The Virginia Twin Study of Adolescent Behavioral Development:Influences of Age,Sex,and Impairment on Rates of Disorder”,Arch Gen Psychiatry54(9).
Topp,C.W.,Østergaard,S.D.,Søndergaard,S.,Bech,P.2015,“The WHO-5 Well-Being Index: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Psychotherapy&Psychosomatics84(3).
Wang,L.,Feng,Z.,Yang,G.,Yang,Y.,Dai,Q.,Hu,C.,et al.2015,“The Epidemiological CCharacteristic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f Chongqing in China”,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177.
Wheaton,B.,Muthén,B.,Alwin,D.F.,Summers,G.F.1977,“Assessing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in Panel Models”,Sociological Methodology8(1).
Yu,X.,Zhang,J.2007,“Factor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with Chinese People”,Social Behavior&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35(1).
项目基金:项目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CCNU14A03049,CCNU16A06048)。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9)01-0072-09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9.01.006
李雪燕,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武汉 430079)。
编辑/程渔朗
标签:抑郁论文; 儿童论文; 地区论文; 因子论文; 心理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工作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社会工作》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CCNU14A03049; CCNU16A06048)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