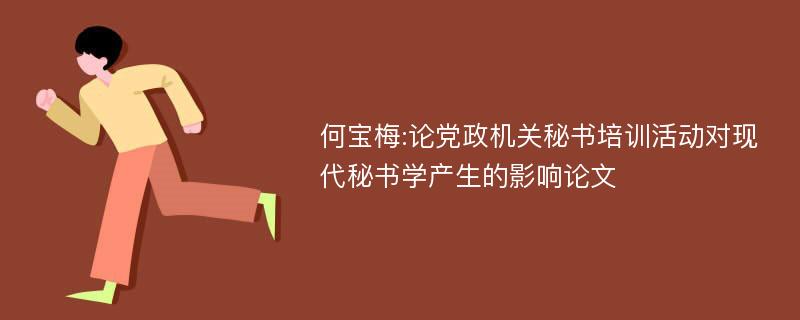
笔者在《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1]一书中指出“1982年2月18日《光明日报》载文提出建设新兴学科‘秘书学’,可以说是秘书学产生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稍后的《秘书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也保留了这一说法。当初笔者的这一说法源自秘书学者的文献[2],并未亲自查证。近来与同行学者聊及此事,王守福教授不顾天气炎热,数次跑图书馆,找到了1982年2月18日的《光明日报》原件,找遍这期报纸的每一个版面,并未发现有文章提出“建设新兴学科‘秘书学’”,却找到了一则《西北建工学院业余文字秘书专业培训班结业》的消息,并指出该培训“为学员学习撰写公文和秘书科学理论打下了基础”。由此笔者推测这则消息应该就是研究者们认为《光明日报》提出建设新兴学科“秘书学”的缘由。若果真如此,仅从一则培训消息推出“提出建设新兴学科‘秘书学’”这样的表述确实有些牵强,笔者在《秘书学导论》第二版中已修正了这一说法。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梳理和认知,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政机关的秘书培训活动对中国现代秘书专业和秘书学科的产生有怎样的影响呢?
一、党政机关的秘书培训活动直接影响了秘书专业的产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领导者对秘书辅助和服务的要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为提高,秘书活动形态发展比较健全的党政机关,首先意识到了加强辅助管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需要一大批新一代秘书人员充实各级军政机关和各类事业单位,原有的秘书人员为了适应新时期领导工作的需要也得进行知识更新;另一方面,原有的师傅带徒弟的秘书培养方式和仅凭经验办事的秘书工作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加强秘书业务培训和秘书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当时党政机关委托高等院校举办秘书培训班的现象在全国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RLSF模型中,运用不可压缩的两相流算法来实现水平集的重新初始化,保证了演化曲线的平滑特性[29],本文算法应用LBF模型的方法,无需重新初始化零水平集,也能保证曲线演化过程中的平滑性。在分割3D腮腺图像时,我们在传统的区域分割方法[30]基础上,根据待分割图像的局部灰度差异以及其空间结构信息,利用FALD算法对区域生长分割结果进行矫正。图2为3D算法的流程图,在step1中,首先从原图中选出种子层及对应的种子点,完成区域生长,得到初步的分割结果,然后在step2中,将其作为三维FALD算法的初始轮廓,最后得到准确的三维分割结果。
从屈干臣先生1985年1月选编的内部资料《秘书学探讨》(全国高等院校秘书学教学经验交流会 中国高等院校秘书教学研究会选辑)中的论文和会议发言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地高校创办秘书学专业大多源自党政机关的秘书培训活动。
成都大学中文系秘书专业始创于1980年,主要以成都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职秘书工作者为培养对象,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成都大学中文系《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加快秘书专业建设》)
学生通过观察可知,在相同的时间内,在竖直方向上只做自由落体的小球和做平抛运动的小球运动的位移相同,即,平抛运动的物体在竖直方向做初速度为零的加速度为g的匀加速运动.做平抛运动的小球水平位移较理论值小,是因为小球运动中受到空气阻力.
1980年,西北建筑工程学院中国语文教研室的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鼓舞下,想在机关干部知识化、专业化中做出贡献,提出创办秘书专业,培训在职秘书。(毛含德《办好成人秘书专业 促进在职秘书专业化》)
青海民族学院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和需要,从1982年开始,在干部训练部增设了秘书专修班。(黄生芳《在少数民族学员中讲授秘书学的体会》)
通过分别检验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境内外利差(DLC)与资本账户跨境资金流出(DLOZB)、证券投资跨境资金流入(DIZQ)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得出:一是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境内外利差(DLC)与资本账户跨境资金流出(DLOZB)之间不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二是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与证券投资跨境资金流入(DIZQ)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境内外利差(DLC)与证券投资跨境资金流入(DIZQ)之间不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教师要求学生从遗传物质的“信息流”角度理解蛋白质与核酸的关系,理解生命历程中基因选择性表达的具体过程:在特定时间DNA分子上特定的基因转录为mRNA,核糖体以mRNA为模板合成肽链,该过程中需要tRNA运载不同的氨基酸,mRNA密码子与tRNA的反密码子相互识别,决定肽链的氨基酸组成及排列顺序。蛋白质结构多样性的根本原因是基因的多样性。
独特的研究方法是学科创立的指标之一。由于大部分高校的秘书学专业缘起于在职培训,经验性研究方法成为秘书学创设初期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录取的学员来自嘉定县各科局,他们原系从事秘书及文书档案工作的。(上海科技大学吴义方《理工科高校也要办应用文科——谈谈我校举办秘书培训班的体会》)
二、为满足培训需要构建了秘书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一)双管齐下,编写培训教材,总结秘书和秘书工作的基本理论
早期有些在职秘书培训所涉及的秘书学理论体系是零星、分散的,如成都大学的秘书培训除了公共课和基础课外,专业课主要有秘书公文学、书法、档案学、新闻学、逻辑学、古代公文选、自然科学和知识概要、法学概论、应用技术训练等。(成都大学中文系《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加快秘书专业建设》)高校的老师们很快认识到了秘书学应该构建独立的核心理论,随着培训中秘书学概论课程的出现,培训者们开始编写教材,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关于秘书和秘书工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如秘书工作者的修养、秘书工作的职责和范围、秘书工作的基本知识,以及秘书制度的历史沿革,出现了一系列秘书学概论的教材。如盐城地委办公室曹晋杰等编写的《秘书工作基本知识》和江苏省委政研室吴镕编写的《秘书工作和机关应用文》讲稿等。前者是江苏盐城地委和行署委托盐城师专举办秘书培训班所使用的讲稿,1981年作为内部教材印了一万册。后者是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开办的秘书培训班所编写的讲稿,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反响较大的是西北建筑工程学院毛含德老师主编的《秘书学概论》。
培训急需教材,最初教材编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由高校老师查阅资料文献编写而成。如毛含德老师接受《秘书学概论》的编写任务后,“走访了西安地区的图书馆,查阅了藏书丰富的陕西省图书馆……在档案阅览室钻了三个月……经过两个多月的经营,得初稿三十七节十二章,使《秘书学概论》初具规模,后打印成讲义,发给学生,一本成型的《秘书学概论》就诞生了”。[3]为了满足各地办秘书培训班的需要,《秘书学概论》数次被油印,“全国使用的单位有15个以上”。另一种是总结实践工作者的经验。“从目前现有的一些秘书专业的使用教材来看,为了教学需要,常常是先到各地政府机关去聘请一些从事秘书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老秘书,由他们来分讲‘秘书学概论’这门课,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整理成文,编印出书。”[4]为了解决培训的燃眉之急,上述两种方式编写出来的教材,总结了秘书和秘书工作的基本理论,填补了秘书学著作的空白。当然,这种应急性产物在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上存在明显的不足。
高校在开设秘书工作培训班的同时,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开始设置秘书专业,并正式出版了一批秘书学教材,如翁世荣编著的《秘书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洪清源等主编的《机关秘书工作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张金安、常崇宜主编的《秘书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王千弓等主编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这些正式出版的教材与早期的培训教材相比,内容涉及面更广,理论知识更系统,影响更为广泛。这些教材的发行量都数以十万计,影响由点及面,把秘书学科推及全国。
(二)培训倒逼教学理论工作者,秘书学启动学科研究
秘书专业和秘书学科的产生是客观的需要,这个客观需要最初对应的是对在职党政秘书的培训,提高在职秘书的水平,继而在高校中培养秘书人才。这个客观需要倒逼教学理论研究者,开始思考秘书学究竟应该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它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这种为各地党政部门代培干部的地方高校出现的新兴专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各地组织部门的重视,从而调动了文科院校办学的积极性。(胡鸿生《试论秘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人才培养是秘书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初步确立的基本动力。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对一门新兴学科来说,构建与否或构建的成熟程度直接体现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前途,秘书学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主要由承担培训任务的高等院校完成。随着高等院校秘书教学的进一步发展,秘书学课程体系的建设日益为各学校所重视,教学者在关注课程设置的同时开始尝试构建秘书学的理论体系,对秘书学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秘书学的分支学科、秘书学知识单元的构成及知识单元的逻辑结构等问题开展初步探索。
在秘书专业培训活动和秘书专业创立后不久,秘书学学科研究的成果也陆续出现。
1.公开出版教材,传播秘书学学科理论。秘书学学科理论即研究秘书学自身的理论,如秘书学的学科对象、逻辑起点、知识体系、相关学科、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历史演进等。1984年出版的秘书学教材大多简要涉及了秘书学的学科理论。如翁世荣编著的《秘书学概论》明确了秘书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这些著作明确了秘书、秘书工作、秘书机构、秘书学等基本概念,对秘书工作的特点、秘书机构的职责、秘书学的对象与性质及研究内容、方法有了最基本的阐述,虽然比较粗糙且有些零星,但毕竟有了独立的学科定义和学术概念,其中的某些理论观念还产生了悠久的学术影响。例如王千弓等主编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对秘书工作特点——五组对立统一矛盾的概括以及对秘书学研究对象和性质的认定就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和科学性,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2.总结教学培训的经验,启动秘书学科的研究。在上海召开的首次全国高等院校秘书学教学经验交流会上,教学者开始探讨秘书学的学科理论,提出了秘书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上海大学文学院楼宇生在《秘书工作与秘书学》中提出“探讨秘书工作的性质和秘书学的科学体系问题至关重要”,他分析了秘书学的领属科学、姐妹科学、交叉科学和边缘科学。镇江师专的胡鸿生在《试论“秘书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提出“如何进一步探讨和建设这一新型学科,研究和发展这一新型学科,无疑是摆在我们高校文科老师面前责无旁贷的一个光荣课题”。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林巍在《试论秘书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中提出“秘书学是研究如何进行辅助性管理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并分析了秘书学与管理科学、新闻学、档案学、文书学、速记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的关系。
为了满足当时秘书业务培训的需要,一些既富有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同志开始系统地总结秘书工作的经验,编写讲稿,走上秘书教学的讲坛。如编写《秘书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版)的李欣同志,编写《秘书学与秘书工作》)的王千弓同志,编写《机关秘书工作概论》的吴镕同志,以及编写《实用秘书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的孙锡钧同志等,均为长期从事机关秘书工作、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秘书部门领导人。他们的著作主要是对秘书工作的经验总结,内容大都涉及起草和办理文件、调查研究、协调工作以及会议组织、信访接待等工作。正是由于这些秘书活动的实践者对秘书工作的直接感受和认识做了系统的总结,才使秘书学的诞生成为可能。李欣同志曾说:“当初,我没从学术角度去想过,只是在搞业务工作总结时才想写书的。”[5]而正是李欣同志这部搞业务总结时所写的《秘书工作》被稍后的研究者们奉为秘书学的开拓之作。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经验性研究便没有秘书学,尤其是在秘书学产生的初期,经验性研究更是秘书学研究的基本形式。
三、培训活动为秘书学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全国高等院校秘书学教学经验交流会于1984年10月27日至31日首次在上海召开,76所高校的教师代表共120余人参加了会议,时任国家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的季啸风亲临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领导同志以及社会科学院、市委研究室、市高教局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从与会代表的交流材料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高校的秘书学教学都是基于对在职秘书(主要是党政秘书)的培训。各地党政部门下单、地方高校接单培训模式的影响甚至直接导致了这个新型专业的产生,这也是秘书专业从地方高校和成人高校中兴起的主要原因。
管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观点:70%的管理问题是沟通。人类除了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外,更重要的需求是被尊重。沟通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重要手段。而对于培训公寓来说,管理者只做好本职事务管理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沟通无论是对员工自身的发展和成长,还是对于共同工作目标的实现都有着重要作用。
(一)秘书专业和秘书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自于经验性研究
通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研究者们对秘书、秘书工作、秘书专业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对秘书学原理的探讨就此起步。1983年上海大学创办的《秘书》、兰州大学创办的 《秘书之友》,成为研究秘书专业教学和学科的重要载体。
桩径>1.6m时:对护筒长度<10m,护筒壁厚采用10mm;对10m≤护筒长度<20m,护筒壁厚采用12mm;对护筒长度≥20m,护筒壁厚采用14mm。
(二)经验性研究的成果增强了学科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性
经验性的东西大都是人们在实践中直接获得的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秘书工作的经验性成果都具有直接感受性、可描述性及可类比性特征。虽然这些经验大多来自党政机关的工作实践,但这些成果对于参加培训的同样来自机关工作一线的学员的需求来说,具有相当高的契合度,对学员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各个学校的秘书培训班都引起了较大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当我们办秘书培训班的消息见诸《文汇报》 《解放日报》 《中国教育报》以后,收到了四面八方的来信来电,有要求参加学习的,有要求购买资料的……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来电更调动我们多办班、办好班的积极性。” [6]
中国的秘书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为适应新形势下秘书工作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对秘书人员实行岗位培训和培养秘书人才的需要。这个直接原因既导致了秘书专业和秘书学的产生,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秘书学科的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笔者在《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等著作和文章中都有所提及,集中表现在:
农村发展和振兴工作既是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有长远的战略规划,脚踏实地抓好每一项工作,落实好每一项举措,为制度改革和农村进步带来显著变革。同时,要找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弊端,充分利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教育上加大资金投入,促进城市农村教育资源共享,用现代化的教育,转变农民认识上的老旧观念,澄清理论理解上的误区,使农民从思想上接受改革,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将农村振兴战略推向更高的阶段。
第一,学科基础理论薄弱。由于秘书学的产生与岗位培训密切相关,秘书学科初步形成基于对秘书工作业务的研究。党政秘书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最初构建秘书学学科体系的核心。如调查研究、文件处理、会议组织、信访工作、保密工作、机关日常事务工作等构成了当时秘书学的主要内容。对秘书工作业务的抽象和概括、总结和研究,直接导致了秘书学的产生,“秘书理论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着秘书学的发展水平。这种弱势在秘书学一产生就表露出来了。正是因为系统化的原理和概念体系的缺失,一直到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人质疑秘书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7]
第二,研究方法单一。经验性研究是秘书学产生之初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它在满足培训者直接需要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大量经验形态的铺陈,代替或掩盖了对秘书本质和秘书工作原理的理论探讨,妨碍了秘书学理论的创造性突破。”[8]“经验性成果替代学科理论体系并广泛加以推广,就很容易造成许多认识上和操作上的误区。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经验性研究成果的局限性。”[9]
第三,研究对象有局限。基于党政机关秘书的培训活动对秘书专业的影响,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大多适用于党政机关的秘书人员。早期的所有秘书学教材都是针对党政秘书的,无论是秘书工作还是秘书人员的研究都是围绕党政秘书展开的,被诸多研究者尊为秘书学开山之作的《秘书工作》也是基于党政秘书的,适用对象的片面性特征不仅表现在秘书学开创之初,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资料显示,从全国来看,大部分高校秘书专业的起步与党政机关秘书的培训活动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政机关秘书的培训活动对秘书专业和秘书学科的产生有着积极甚至关键性影响,随着这些培训活动的信息见诸《光明日报》《文汇报》 《解放日报》 《中国教育报》等权威报刊,现代秘书专业和秘书学科开始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7]何宝梅.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邱惠德.我国当代秘书科学开始走向成熟的门坎[J].秘书,1999(11).文中指出,“自1980年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首建秘书专业,1982年2月18日《光明日报》载文提出建设新兴学科“秘书学”以来,至今快20年了。”
[3]毛含德.办好承认秘书专业 促进在职秘书专业化[M].秘书学探讨(内部资料).广东业余大学,1985.
[4]胡鸿生.试论“秘书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M].秘书学探讨(内部资料).广东业余大学,1985.1.
[5]楼字生.八十年代前期的我国秘书学著作(之二)[J].当代秘书,1997(2).
[6]吴义方.理工科高校也要办应用文科——谈谈我校举办秘书培训班的体会[M].秘书学探讨(内部资料).广东业余大学,1985.
[8]董信泰.加强秘书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几点构想[J].秘书之友,1994(1).
[9]何宝梅.试论经验性研究在秘书学建设中的地位[J].秘书之友,2000(5).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标签:秘书论文; 秘书学论文; 学科论文; 秘书工作论文; 经验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管理技术与方法论文; 《秘书之友》2019年第4期论文;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