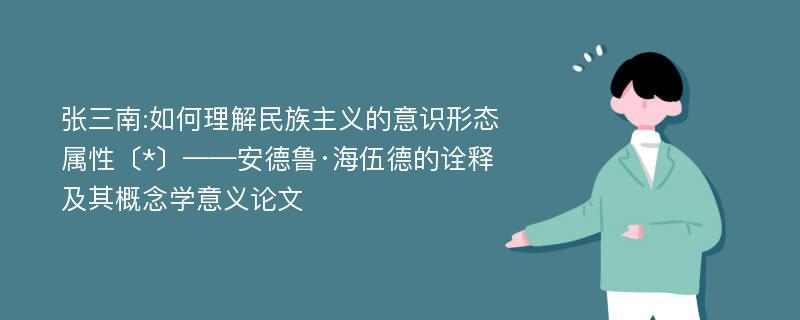
〔摘要〕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常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问题恰恰在于民族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对此学术界长期以来更多是“蜻蜓点水”式的一笔带过。安德鲁·海伍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聚焦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其进行了正面和系统的诠释。他通过“源起与流变→核心要素→主要类型→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的全面剖析,从学理上论证了民族主义是一种与诸多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相伴相生,但却难于独立存在的意识形态。海伍德的诠释有助于人们增进对民族主义意涵的理解,具有概念学上的学理意义。
〔关键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安德鲁·海伍德;概念学
民族主义是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理论与实践议题。在众多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和论述中,除了将民族主义界定为一种思潮、学说或运动之外,学界也常将其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称:“如果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来说是一种具有规范内涵的用以认识世界的一般方法,那么民族主义便是一种意识形态”。〔1〕“族群—象征主义”代表人物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回应人类某些最深层的对安全、公正和认同的迫切要求的意识形态和运动”。〔2〕“现代主义”学者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则承继了本学派著名学者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论,“照惯例”地“将民族主义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3〕我国学界同样普遍如此。有的论著在开篇伊始就将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4〕有的虽未直接提及意识形态一词,但字里行间明显体现出民族主义的某种意识形态化色彩,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就曾将民族主义界定为“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5〕
可见,意识形态和思潮、学说、运动等用语一道,成为了界定民族主义的常用语。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民族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学界对此更多是“蜻蜓点水”和“不证自明”式的一笔带过,鲜见正面、系统的回答,直到英国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
安德鲁·海伍德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学家,长期致力于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曾出版《政治学》(Politics,1997)、《政治学核心概念》(Key Concepts in Politics,2000)、《全球政治学》(Global Politics,2011)等著作,是一位政治学理论畅销书的作者。其著作给读者的基本感受是“地道公允、言简意赅、圆润通畅、清新可读”,〔6〕在全球拥有百万计的读者群,尤其在英语世界影响较大。海伍德所撰写的《政治意识形态导论》(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一书迄今已出版到第6版,其中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了全面诠释,呈现出概念学上的学理意义,有助于人们增进对民族主义这个重要概念的理解。
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源起与流变
民族主义一词何时何地首先出现,学界并无定论,有的最早追溯到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7〕海伍德则认为,“民族主义一词首先出现在1789年反雅各宾派的法国神甫奥古斯丁·巴吕埃尔(Augustin Barruel)的作品中。”〔8〕并据此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年,革命者在卢梭人民主权学说影响下,以人民(people)〔9〕的名义反抗国王路易十六的统治,“法兰西民族”应运而生。相比之前,人们的政治认同在于对统治者或王朝的效忠,大革命使民族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主人,民族主义成为了革命和民主的信条。
几乎同时,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思想家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首创了意识形态一词,认为其是一种新的“观念科学”〔10〕,这恰好成为了能够彰显民族主义属性的贴切用语。于是,在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的推动下,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迅速合二为一,快速扩散,衍生各种流变形式。和许多学者一样,海伍德认为法国大革命激荡出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法国的财富,在随后的200多年间,民族主义被吸纳进了许多成功和引人注目的政治信条之中,影响和重塑了世界历史。拿破仑战争不仅张扬了法国民族主义,也激发了欧陆国家对独立和解放的民族主义渴望。不仅如此,民族主义更是传到拉丁美洲,在其影响下,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最终被推翻。因此,海伍德认为,“到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已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在许多革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1〕尤其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长期分裂和被外族统治的经历使得人们产生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而这种意识承继于法国,却以新的语言形式呈现了民族主义。
和海伍德一样,《意识形态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伊塞克·克拉姆尼克(Issac Kramnick)、弗雷德里克·华特金斯(Frederick M.Watkis)同样认为,民族主义在19世纪确立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地位。他们指出,虽然随着拿破仑帝国在1815年的崩溃,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原则战胜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自由主义,但此后的战争不再是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壁垒分明的斗争,民族主义已成为现代世界中的一股力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地位已难以撼动。〔12〕
当然,海伍德也认识到19世纪的民族主义并非真正的群众运动,仅限于新兴中产阶级。他认为这种状况在19世纪末发生了改变。随着国旗国歌、公共仪式和国家假日的传播和普及,民族主义真正成为了群众运动和大众政治用语,性质也发生了改变。这样的民族主义逐渐演变为沙文主义(chauvinism)和仇外主义(xenophobia)。每个国家都在宣扬自己的独特性和卓越品质,却视其他民族为不值得信任甚至险恶的异族。这种大众民族主义加速了国际竞争与猜疑情绪的弥漫,助推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
一战后的民族主义促使中东欧进行了民族重建。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倡导了民族自决原则,民族主义进一步拥有了理论武器。德、奥、俄、土四大帝国土崩瓦解,众多新的民族国家诞生。当然,世界大战并未缓和一些国家间原有的紧张关系。军事上的败北和对条约的失望留给战败国强烈的失落和不满。民族主义再次成为新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
将现有16级机械设计专业2016学年的成绩总表,与系部上交的2017学年第一学期成绩合并到一起。具体步骤如下:16机械设计成绩总表中新增2017学年第一学期的科目名称顺序与班级上交的成绩表科目顺序一致,在N2单元格中输入“=VLOOKUP(B2,'[16机械设计与制造班.xlsx]16机械设计'!B6:J39,3,0)”即可得到机械设计基础科目的成绩,依次类推,分别可得到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现代企业管理、心理健康教育、电工电子技术和应用文写作的成绩。
保守民族主义也备受批评,为此海伍德总结道:一是其思想总是受到诟病,被视为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精英治理的一种形式。它往往为维护现有统治和治理架构及社会现状合法化而抵制变革。二是它会导致褊狭和固执。它通常与狭隘民族主义相联系,对移民和超国家机构日益增强的影响持抵制态度。为维护文化纯洁和现有传统,它通常将移民和外国人视为威胁,甚至渲染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的情绪。
完成注意力与定向力测试的连线测试(trail making test,TMT)[3],在完成量表前签署知情同意书。连线测试具有完成时间越短,认知功能越好的特点,包括两部分即为TMT-A以及TMT-B,相比较TMT-A,TMT-B难度更大。
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
海伍德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和高度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种族形态,虽然它与各种意识形态均有联系,但其核心要素仍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民族、有机共同体、自决和文化主义。
(一)民族(nation)
他总结了保守民族主义的特点:首先,它本质上是怀旧的、保守的,视传统体制为民族认同的象征。其保守性是通过诉诸传统和历史得以维系,反映了对昔日岁月和荣耀的追忆。譬如,英国保守民族主义就与君主政体有着密切联系,推崇名为《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的国歌。其次,它常被用作应对社会革命的解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就曾通过特殊的技巧把民族主义变成了法国的保守力量,通过推行独立甚至反美的防务和外交政策增强了民族自豪感,重建了社会秩序和权威。再次,它在民族认同受到威胁或面临失去的危险时显得特别地举足轻重。例如,为应对移民问题和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保守民族主义在许多现代国家广为存在。
海伍德强调,民族没有一个客观的蓝本,因为所有的民族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化异质性,它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和传统,尤其是共同语言、宗教和历史,通常情况下包括共同地域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海伍德十分看重语言和宗教的作用。在他看来,语言常被视为民族最鲜明的标志,体现着独特的态度、价值观,是能产生亲近感和归属感的表达方式。例如德国民族主义,建立在文化共同体意识基础上,体现了德语的纯洁和得以幸存的历史。而宗教是构成民族身份的另一要素。在北爱尔兰,常常根据宗教信仰来区分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民:大多数新教徒视自己为联合主义者(unionist),希望维持与联合王国的联系,而许多天主教团体则倾向于爱尔兰的统一。而在北非和中东,伊斯兰教一直是形成民族意识的重要因素。
步骤3:计算综合风险评价云模型。将准则层风险指标的特征值数据结合权重(22)的值,通过式(18)~式(20)计算可得特征值,综合云模型与标准云模型在Matlab中进行比较,风险等级图如图2所示。
此外,海伍德认为,相比较而言,民族通常以文化而非生物学为基础,反映的民族团结可能会基于种族,但更多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信仰。因此,民族往往具有共同的历史和传统,通过追忆昔日荣耀、庆祝国庆、纪念领袖诞辰或重大军事胜利等形式,来维系民族认同。譬如,美国庆祝独立日,法国纪念“巴士底日”(国庆日),英国庆祝休战日。
当然,海伍德也意识到了文化认同因素的复杂性。它一般难以精确界定,反映的是多种文化因素的结合,而非任何精确的准则。因此,民族最终只能通过其成员而非一套外在标准来“主观地”加以界定。从此意义上讲,民族是一个心理政治实体,是将自己视为天然的政治共同体并以共同的忠诚或情感及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来区分彼此。
海伍德还强调,仅从文化和传统角度来界定民族会引发一些难题。即使某种特别的文化特征与民族身份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语言、宗教、族性、历史和传统,仍然不存在任何模板或客观标准能界定一个民族何时何地存在。事实上,民族是主客观因素的结合体,这些因素导致了相互竞争的民族概念的出现。他指出,虽然民族主义者都赞同民族是文化因素和心理政治因素的混合体,但他们都强烈反对在二者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排外型的民族观强调民族团结和共同历史的重要性及共同血缘这一基本特征,但混淆了民族和种族的区别。原生主义者(primordialist)认为,民族具有使人们捆绑在一起的“原生的纽带”,人们对语言、宗教、传统生活方式甚至故土有着强大且貌似与生俱来的情感依恋。保守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不同程度采纳了这种民族观。另一方面,包容型的民族观基于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强调公民意识和爱国忠诚的重要性,倾向于淡化民族与国家及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区别,认为民族可以是多种族、多族群、多宗教的。自由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倾向于这种民族观。
(二)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
海伍德指出,尽管民族主义者有可能不认同民族的一些界定性特征,但他们都一致认为民族是有机的共同体。这就是为什么民族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具有更高忠诚度和更深层政治意义的原因。尽管阶级、性别、宗教和语言等在特定社会中显得很重要,甚至在特定情形下是至关重要的,但有机共同体作为民族核心要素的纽带作用是更为根本的。尽管如此,对这个问题仍存在不同的解释,为此,海伍德介绍了最为重要的原生主义、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看法。〔14〕
原生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认知以历史嵌入的视角来描述民族认同:民族根植于国家成立之前或争取独立之前就已存在的共同文化遗产和语言中,而且是以类似于亲属关系的情感依恋为特征的。从这个意义说,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是原生主义者。安东尼·史密斯通过强调现代民族和前现代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连续性来凸显了原生主义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族性(ethnicity)与民族之间几乎没有区别,现代民族本质上是远古民族共同体的新版本。
相反,现代主义者(modernist)认为民族认同是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应对瞬息万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的挑战。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为此强调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联系。他着重指出,工业社会的出现促进了社会流动、自我奋斗和社会竞争,故需要一种新的文化凝聚的源泉,而这是民族主义能提供的。盖尔纳的理论表明民族联合是为了应对特定的社会情势,恢复前现代社会的忠诚和认同是不可想象的,但它也暗含着民族共同体是根深蒂固和经久不衰的意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将现代民族描述为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他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出现和现代大众传播到来的共同作用,即他所称之“印刷资本主义”的作用。在他看来,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4)淤泥处置不当,造成二次污染。在河道疏浚过程中,由于对河道淤泥进行扰动,底泥中的污染物会释放到河水中,造成二次污染;淤泥脱水过程中,渗滤液若不经过处理,则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在填埋利用和焚烧底泥的过程中,也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清淤的相关单位管理过程中环保意识不强,极易因为淤泥处置不当,引起二次污染事故。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认为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是一种通常为权势群体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结构。此外,海伍德还谈到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连续性和文化纯洁性始终是虚构的,是民族主义自身虚构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族主义是统治阶级在遭到社会革命的威胁时,为确保民族忠诚优先于阶级联合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以此来约束工人阶级顺从已有的权力结构。〔15〕
(三)自决(self-determination)
在海伍德看来,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才正式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出现。可见,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是以人民或民族的自治为基础的。换言之,民族不仅是自然共同体,还是自然的政治共同体。海伍德进而指出,在民族主义传统理念中,民族和国家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认同通常体现在民族自决原则之中。因此,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海伍德总结了实现目标的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统一;二是通过独立。
海伍德强调,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国家是最高级且最令人满意的政治组织形式。民族国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提供文化凝聚和政治统一的前景。而且,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由人民或民族自身来行使,有助于政府权威合法化。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者相信,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世界的动力是自然且不可抵抗的,民族国家是最为可行的政治单位。
海伍德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总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比如,有的民族虽不能拥有国家身份和完全独立的地位,但却可能会满足于一定程度的自治地位。例如英国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就是如此。这说明民族主义并非总是伴随着分离主义(separatism),联邦主义或权力下放也是可替代的方案。不过,权力下放甚或联邦制所建立的自治是否就足以让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却并不是确定的。例如,1999年英国设立苏格兰议会也未能阻止苏格兰民族党(the SNP)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行动。
(四)文化主义(culturalism)
〔7〕参见Anthony D.Smith,“Nationalism,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 Current Sociology,Vol.21,No.3,1973,p.21。
为此,海伍德重点介绍了文化民族主义在德国的源起。和许多人一样,他认为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是位可与“政治民族主义之父”——卢梭相提并论的文化民族主义设计师。赫尔德和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te)、弗里德里希·雅恩(Friedrich Jahn)一道,认为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德国文化与法国革命的理念是相悖的。赫尔德认为每个民族都拥有民族精神(volksgeist),通过歌谣、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展现出来,并为民族提供创造力的源泉。可见,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主义(culturalism)。19世纪的德国,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文化重塑,即民族传统的复兴和神话传说的再现。之后,文化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
海伍德同样意识到,人们对那些将民族首先视为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共同体的观点存有异议。依此看,排外封闭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包容开放的政治民族主义是有区别的,无论是隐性还是显性的文化民族主义,都常常会在骄傲和恐惧情绪激发下对其他民族或少数人群体采取沙文主义或敌对的态度。海伍德最后指出,当文化民族主义演化到追求同化与文化“纯度”时,便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不相容了。
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海伍德大体按时间顺序,诠释了几种主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即自由民族主义、保守民族主义、扩张民族主义及反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
(一)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
自由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融合了人民主权和自由的原则。后经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进一步阐释,自由民族主义融合了在多民族帝国内反抗专制主义压迫的思想。在马志尼看来,意大利的统一意味着要摆脱奥地利的专制统治。自由民族主义不仅传遍了欧洲,还推动了拉美独立运动。一战后,被视为欧洲重建基础的威尔逊“十四点方案”(the Fourteen Points),也是基于自由民族主义的原则。20世纪反殖运动的领袖们同样受到了自由民族主义的影响,譬如中国的孙中山、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等。
在海伍德看来,自由民族主义是一种解放性力量,其基本观点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自由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和个人一样是平等的,应拥有平等的自决权。因而,自由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构建独立民族国家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某一民族的统一或独立。其二,自由民族主义认为,实行民族自决是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自由民族主义是一种在相互尊重国家权利和民族特征基础上推动民族团结和增进民族友爱的力量。从本质上来说,自由主义超越了民族,契合了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意境。
在肯定自由民族主义上述主张的同时,海伍德也批评这些主张有时是单纯的、浪漫的:其一,它意识到了民族主义进步、自由、理性、包容的一面,却忽视了其阴暗面。其二,自由主义者视民族主义为一种普遍原则,却对其情感力量不甚了解。在战争年代,这种情感力量可怂恿人们为他们的祖国去拼杀或牺牲,而不管国家的动机是否正当。其三,自由民族主义低估了民族国家的构建难度。实际上,民族国家往往是由许多语言、宗教、民族或区域群体组成的,政治统一、文化同质的民族国家理想往往难以实现。
〔6〕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影印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封底。
(二)保守民族主义(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海伍德回顾了保守主义者对民族主义态度的转变和二者的结合历程。在19世纪早期,保守主义者曾将民族主义视作激进和危险的力量,是对秩序和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迪斯雷利、俾斯麦、亚历山大三世等保守主义政治家,逐渐与民族主义者产生共鸣,将其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和维护传统体制的天然盟友。到现代,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的信条,保守民族主义已成普遍现象。
在海伍德看来,民族主义理念基于两个核心观点:其一,人类社会被自然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其二,民族是最合适的,也可能是唯一合法的政治统治单位。基于此,古典政治民族主义(classical political nationalism)将国家和民族的边界视为一体,于是认为在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应融为一体。
上述海伍德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源起与流变的分析,更多聚焦于政治民族主义,即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类型的民族主义。而且,海伍德认为,政治民族主义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现象,以晦涩难懂和自相矛盾为特征,而非一系列简单的价值观和目标。比如说,民族主义既是解放的又是压迫的,在带来自治与自由的同时,也导致征服与镇压;既是进步的又是退化的,既向往民族新生,又颂扬昔日辉煌;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一边在倡导有原则的信念,一边又在酝酿各种非理性的冲动与情绪,挑起对旧时恐惧和历史仇恨的回忆。民族主义产自于不同的历史题材,塑造于错综复杂的文化遗产,用于实现不同类型的政治目标和理想。海伍德总结道:民族主义融合和汲取了其他政治理念,创造出系列互竞的民族主义传统,这种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是多种要素的产物。〔13〕
《古今韵会举要》(以下简称《韵会》)引书丰富,据文美华的《〈古今韵会举要〉引例研究》统计《韵会》共引书99部,引书次数13785次,引用诗文450次,但历代学者对此书的重视程度不高,对他的研究也甚少。经笔者统计,《韵会》共引用《说文》6498字,其中释义与大徐本不同的有1846字次,不同率达到28.4%,其与“大徐本”的不同之处能为我们校勘《说文》提供丰富的素材。
(三)扩张民族主义(expansionist nationalism)
海伍德梳理了扩张民族主义的几种表现形式。它们大都为人们所熟知,本身也互有交错。一是沙文主义(chauvinism)。它是与早期自由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的一种扩张民族主义,以法国士兵尼古拉斯·沙文(Nicolas Chauvin)的名字命名,此人曾狂热地崇拜和追随拿破仑一世。19世纪末,英国创造出一个新词——亲国热(jingoism),用以描述当时支持殖民扩张的大众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有时称军国主义(militarism)。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的侵略面孔就已变得尤为显眼,列强以光耀民族、追逐“阳光下地盘”的名义竞相瓜分非洲。此时的扩张民族主义已演变为得到了大众民族主义支持的帝国主义,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这种扩张民族主义再次达到高峰,演变成法西斯政权推行帝国扩张的军国主义,再次引发世界大战。三是泛民族主义(pan-nationalism)。这是一种特别的扩张民族主义,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为代表。泛斯拉夫主义力图实现斯拉夫的统一,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视其为国家使命,这也导致俄奥为争夺巴尔干的冲突。1991年苏联解体后,各种形式的泛斯拉夫主义又开始复活。此外,泛德意志主义(Pan-Germanism)也是一种类似的扩张民族主义。四是种族主义(racialist)。海伍德重点介绍了种族主义在德国的演化。他指出,拿破仑战争时期,传统德国民族主义就已表现出明显的种族优越感,呈现出种族主义的迹象。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这一迹象越发明显,直到后来的纳粹政权公开推行反犹主义(anti-Semitic)政策,将种族主义发展到极致。纳粹党人狂热奉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图实现扩张主义目标,更多是基于生物学而非政治学的语言来说明其所谓的合理性。
扩张民族主义往往源于强烈的感觉,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热情。海伍德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个人作为独立和理性的个体,往往被这种情绪所裹挟。这种民族主义往往伴随着尚武精神,使民众深受绝对忠诚、全身奉献和自我牺牲这些尚武精神的感染。在政治上,这种民族主义常常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得以体现,“非我族类”者往往被其视为展示辉煌或遭受挫折的替罪羊。为此,法国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曾将其称为“完整的民族主义”(integral nationalism)。
Swales认为,“体裁”是交际事件的一种分类,人们在生活中按照特定目的和特定程式运用语言在生活中办事[7](P45-58)。Bhatia根据Swales的观点将“体裁”进一步概括为:“体裁”是一种可辨认的交际事件,内部结构特征鲜明且高度约定俗成[8](P13-16)。以上学者的定义都表明体裁分析注重话语生成过程对于交际目的实现的影响和制约,语篇的内容和程式都受到体裁的制约。元旦社论也是一种内部结构鲜明、可辨认的、高度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有其特殊的交际目的,是一种特定的体裁,具有既定的语步结构。我们运用体裁分析的方法,将元旦社论划分为几个服务于同一交际目的不同语步,并进行了统计(见表2)。
(四)反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anti-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nationalism)
在海伍德看来,欧洲殖民主义通过民族主义的传播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衍生了反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一方面,被殖民统治的经历推动了亚非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增强了民族解放的渴望,衍生了反殖民民族主义。到了20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地理版图因而改变,民族解放运动导致了老牌殖民帝国的陵夷及殖民体系的最终崩塌。这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民族主义常常担当起一种解放的力量,解放全世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并且通过大众的斗争帮助移开某些对世界人民争取更大平等的障碍。”〔16〕
另一方面,许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虽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但却通过各自的民族解放模式与西方政治传统分道扬镳。例如,甘地(Gandhi)提出的政治哲学,融合了深植于印度教并具有非暴力和自我牺牲伦理色彩的印度民族主义。相反,在马提尼克出生的法国革命理论家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则强调了反殖民斗争和暴力的联系,认为只有通过暴力的宣泄才足以强大到能够实现心理—政治上的重生。
海伍德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思想同样对亚非民族主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数亚非反殖民运动领导人,从温和派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受到某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强有力地吸引着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对不平等和剥削问题提供了解析的马克思主义,人们藉此意识到殖民统治是阶级压迫的延伸。
黑龙江省的农作物秸秆总量约为6305万吨,其中玉米秸秆约3610万吨,水稻秸秆约1954万吨,大豆秸秆约741万吨[11]。
海伍德进而总结了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的具体形式:其一,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甫获独立,便跟随苏联模式,将经济资源国有化,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其二,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则建立另一种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istic socialism),在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和安哥拉等地,又被称为“非洲社会主义”(African socialism)。这种社会主义宣称追求的是统一的民族目标和利益。其三是主要传播媒介为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和经济强权的抵制性反应,寻求的是一种反西方的言说形式。
四、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许多关于全球化的争论都集中在它对国家的冲击及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方面。有学者认为,全球化释放了种族政治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全球化力量,意味着“政治的死亡”(death of politics)与国家的过时。〔17〕
海伍德对这一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一方面,他分析了全球化对民族主义的冲击。在他看来,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国家遭到破坏,甚至有的遭到彻底破坏,种族和区域的政治认同正在取代民族认同,民族国家本身逐渐失去权威。全球化对民族主义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且形式各异,经济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作为自主经济体的能力,文化全球化则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文化特殊性。
对此,海伍德提醒人们注意两点。第一,全球互联性的增强(这是全球化的核心),改变了人们的政治共同体意识,扩展了人们的道德敏感性。这使得有些人认为,民族主义正处在被世界主义取代的过程中,仅限于对自己社会内的人民的政治忠诚和道德责任在日益以相互联系和互相依赖为特征的世界上已经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跨境信息与通信的流动,实质性地减弱了人们对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和社会的“陌生感”或“距离感”,世界仿佛“缩小”了。尽管政治上的世界主义(political cosmopolitanism)被广泛认为难于实施且不值得欢迎,某种道德上的世界主义(moral cosmopolitanism)则可能应运而生,人们往往据此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而非某国公民。〔18〕在世界主义者看来,民族间的区隔总是充满无知和武断,人类应有能力超越民族主义。
第二,伴随着国际移民潮的高涨及现代社会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的显著增强,以文化来维系凝聚力的民族国家已成昨日黄花,也就是说民族认同已处在一个被与种族、文化和宗教等紧密相连的竞争性认同所取代的过程之中。近几十年来,国际移民在战争、民族冲突和政治剧变的推动下不断增多,经济全球化浪潮也“拖拽”着人们离开故国,去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反映了民族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变及跨民族共同体(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19〕不断增多的现象,反映出多元文化民族主义(multicultural nationalism)的出现。
海伍德认为,客观地说,殖民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控制和经济统治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也促进了西方思想的传播,民族主义更是成为了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者的武器。1919年,埃及发生民族起义,很快席卷中东。同年阿富汗与英国爆发战争,南亚、东南亚等地相继发生起义。1945年后,殖民帝国在民族解放运动浪潮面前纷纷瓦解,亚非民族纷纷赢得国家独立,再次掀起了民族主义浪潮。海伍德同时认为,反殖民主义运动不仅见证了西方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还衍生了新的民族主义形态。在中国、越南和非洲部分国家,民族主义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则具有反西方色彩,这在宗教民族主义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崛起过程中十分明显。
另一方面,海伍德认为,几乎没有什么经验证据可以说明关于民族主义消亡的预测是接近于实现的。尽管国际组织毫无疑问在全球政治决策中越来越重要,但没有一个国际组织在吸引政治归属或情感忠诚方面的能力可与民族国家媲美。海伍德进而指出,有理由相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复兴而非衰亡,民族主义的复兴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解释。
其一,增强民族自信(national self-assertion)成为了强大国家扩大地位权重的一种战略,尤其是从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流变性质来看。民族主义再次证明了它以意识形态声势(发源于一个关乎力量、团结和自豪的愿景)赋予经济和政治发展以驱动力的能耐。许多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1990年以降,种种文化的尤其是族裔的民族主义形态盛行起来了。这在前南斯拉夫、高加索和非洲大湖地区的一系列民族冲突和战争中得到了体现。这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说:“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许多渴望成功获得独立和主权的族群群体是生死攸关的。一方面,民族主义允许许多大的或较小的群体进入政治竞技场;另一方面,它也常常导致痛苦的和持续的族群冲突,……通过求助于民族主义来动员全体人民保卫祖国。”〔20〕
最后,民族主义或许已作为对全球化及其引起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变革的一种反应而得以复兴。民族主义时常兴起于恐惧、不安和社会混乱的情景之中,其优势在于维护团结和稳定的能力。比如在有些地方,民族主义利用了人们对移民问题的忧虑,通过反对多样性和文化交融的形式得以固化和复兴。近年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的抬头也印证了这一点。
五、海伍德相关诠释的概念学意义
海伍德关于民族主义的上述诠释,承续的思路为:源起与流变→核心要素→主要类型→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这不仅仅是一种全景剖析,还是一种概念学视阈下的诠释,在专业性和通俗性、学术性和清晰性方面的契合程度,不亚于许多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论著,尤其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海伍德看来,民族主义总体上是个争议的政治概念及难于独立存在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在他所著有的《政治学核心概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导论》中,海伍德都将民族主义视为重要的政治概念而专门论述,尤其强调了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在他看来,政治概念是特别令人费解的东西:它们含糊不清,常常成为敌对和争论的主题;它们可能还“荷载”着连其使用者也不甚了然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韵味。〔21〕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民族主义的规范特征向来是难以判定的,因此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个“争议性概念”。当然,其争议性首先来自于民族概念本身的争议性,比如民族到底是划分为“政治的民族”还是“文化的民族”。
进而,海伍德分析了难于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第一,民族主义有时被归为政治学说而不是成熟的意识形态。第二,民族主义有时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通常表现为对本国的忠诚和对他国的厌恶,而不是一种理论体系。第三,民族主义有着“分裂型”的多重政治特征。在不同时期,民族主义时而激进,时而反动;时而民主,时而专制;时而理性,时而非理性;时而左翼,时而右翼。它一直与几乎所有的传统意识形态相互联系,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大概只有无政府主义,由于反对政府存在的鲜明立场,从根本上与民族主义暌离。因此,正如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民族主义难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这应该是海伍德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最为基本的观点。
可以看出,海伍德是一个概念相对主义者、概念多元主义者、概念价值论者或传统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概念拜物教论者,他“一个人能始终如一地探讨和琢磨政治学的基本学问而又能有所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22〕他在诠释核心概念时,无处不在力图给读者展现出一种审慎、公允的立场和态度,彰显政治科学的精神,虽然他本人也承认“完全价值中立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23〕他在论叙中博采了众多学者和流派的观点,接榫之处的手法也很精道,从概念学视阈系统诠释了民族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属性。他并没有尝试一劳永逸地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一个模式化的定义,就像民族主义研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通篇并未给民族主义下明确定义一样。海伍德更大程度上不是一名理论的设计师,更像是一名知识的集成者。他无疑出色地完成了诠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超级术语”的任务,无形中构建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时空和观点“系谱”,而这恰恰是前人的工作中所缺失的。海伍德的诠释更多体现的是学理上的概念学意涵,而不是为了张扬普适性的政治学说,更不是为了推动民族主义成为一些国家和政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虽然它们与民族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他的诠释难以顾全不同时空的各种民族主义形态,但仍不失显见的借鉴意义,至少展现了一幅较为全面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视图”,对我们全面、理性地认识民族主义大有启迪。海伍德的诠释启示我们,最好不要以“对”与“错”的绝对标准来看待民族主义这样的概念。〔24〕毕竟,民族主义仍是当今和未来很长历史阶段挥之不去的现象,许多社会形态仍将与之相伴相生,需要我们直面与之相关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
注释:
〔1〕〔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1页。
〔2〕〔16〕〔20〕〔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中文版前言,第1、2、1-2页。
〔3〕M.Man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European Nationalism”,in J.A.Hall&I.C.Jarvie,eds., Transition to Modernity:Essays on Power,Wealth and Belief,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37.
〔4〕如刘中民等人在其著作中的第一句话就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参见刘中民等:《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页。
〔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编辑委员会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
煤炭传送系统中的自动化技术主要体现在监测传送带的动态运输状况和报警系统的应用。当传送带处于欠饱和运输状态时,监测系统反馈信息至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接收信号后立即对相应的工作人员作出警报,及时增加传送带上煤炭资源输送量;当传送带中的煤炭资源超过传送带的最大承受能力时,监测系统将监测到的数据信息发送至控制中心,并触动相应的警报装置发出警报信号,工作人员及时减少煤炭资源的输送量。传统带装置中通过引入监测系统和警报系统,可以有效提高煤炭传送带的利用率,进而提高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
尽管经典民族主义总是伴随着追求和维护独立民族身份的政治目标,但民族主义大都与民族文化的愿望与需求紧密联系,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海伍德也是如此认为的。
〔8〕〔11〕〔13〕〔15〕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2,pp.168,168,182,177.
〔9〕海伍德这里所使用的people一词,通常翻译为“人民”,但实际上里头蕴含有“民族”的涵义。在欧洲,通常把people作为nation的基础。在阐释nation的源起时,海伍德也是这么表述的:“In the form of natio,it referred to a group of people united by birth or birthplace.In its original usage,nation thus implied a breed of people or a racial group…”,参见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2,p.168。我国学界也注意到people和“民族”的对译关系,参见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王军主编:《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0〕德·特拉西首创的意识形态(idèologie)一词指的是一种新的“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字面意思即“观念学”(ideaology)。有意思的是,当时恰恰也是奥古斯丁·巴吕埃尔首创民族主义一词的时代。
(4)能源矿产与黑色金属矿产工业总产值高。2017年河北省持证矿山企业工业总产值能源矿产较高,达301.64亿元,占矿山企业工业总产值的54.89%,其中煤炭287.33亿元,占能源矿产工业总产值的95.25%;其次是黑色金属矿产195.26亿元(全部为铁矿产值),占矿山企业工业总产值的35.53%。
〔12〕参见罗志平:《民族主义:理论、类型与学者》,台北: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45-46页。
库岸岩层的层厚、上下层序、各层的出露位置及其物质组成和性质,直接控制岸壁坍塌的宽度、速度和型式,还决定着浅滩的形状、宽度和坡角。一般黄土的粉土粒组含量大,孔隙率高,崩解速度快,易形成快速、强烈的坍塌。且水下浅滩坡角小。
〔14〕海伍德所介绍的原生主义、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实际上后两者的界限是较模糊的。我国学界对相关理论范式的区分并不统一。叶江教授概括为“原始主义”(primordialism)、“永存主义”(perennialism)、“现代主义”(modernism)、“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并重点分析了“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王军教授区分为原生论、后设原则论和边界论。我国台湾学者罗志平则区分为原生论、持久论、现代论、后现代论、族裔象征论。参见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王军主编:《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2页;罗志平:《民族主义:理论、类型与学者》,台北: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11-243页。
〔17〕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笔者认为,海伍德在这里引用的观点虽容易引起争议,但确实反映出了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折冲下的诸多国际政治现象,而且随着近年国际上“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的回潮,这一议题更值得关注。
〔18〕在海伍德看来,世界主义字面意思就是关于“大都会”(cosmopolis)或“世界政府”(world state)的一种信仰。道德世界主义基于所有个体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认识,认为世界是由单一的道德共同体构成的,在其中人们对世界上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有(潜在意义上的)义务,而不考虑国籍、宗教、族性等因素。政治世界主义——有时称为“法律”或“制度”世界主义(legal or institutional cosmopolitanism),则认为世界上应该有全球性的政治制度,而且可能的话还应该有一个世界政府。参见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2,p.196。
〔19〕跨民族共同体削弱了政治—文化认同与特定领土或“祖国”之间的联系,从而挑战了民族国家理念。被认为是“非领土化民族”或“全球部落”。参见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2,p.195。
〔21〕〔23〕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63页。
会议邀请了美国Emory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李晓江博士,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彭挺博士分别作了“转基因动物在人类疾病中的应用”和“荧光蛋白标记技术在蛋白质定位、相互作用以及动态追踪研究中的发展和应用”大会专题报告。报告精彩纷呈,大家听的意犹未尽。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内两两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参见吴勇:《对争议性政治概念的独到分析与诠释——〈政治学核心概念〉译序》,〔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24〕海伍德曾在谈论概念拜物教问题时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的看法实际上无形之中契合了辩证法的精神。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2.经费投入不足。工作经费紧缺、溯源设备数量不足。全州共有13个县市,132个乡镇1 203个行政村,要全面开展动物疫病可追溯业务,下拨的工作经费少之又少,现有的溯源设备仅有智能识读器380台、IC卡785、便携式打印机132台,远不能满足业务需要,影响了工作开展面。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2.010
作者简介:张三南,民族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张强,政治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意识形态学视阈下的民族主义及其批判:基于安德鲁·海伍德的诠释”(HB17ZZ012)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洲社会思潮的变化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17JJDGJW01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姝媛〕
标签:民族主义论文; 民族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政治论文; 海伍德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与民族论文; 国家与人民论文; 《学术界》2019年第2期论文; 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意识形态学视阈下的民族主义及其批判:基于安德鲁·海伍德的诠释”(HB17ZZ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洲社会思潮的变化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17JJDGJW010)阶段性成果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论文;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