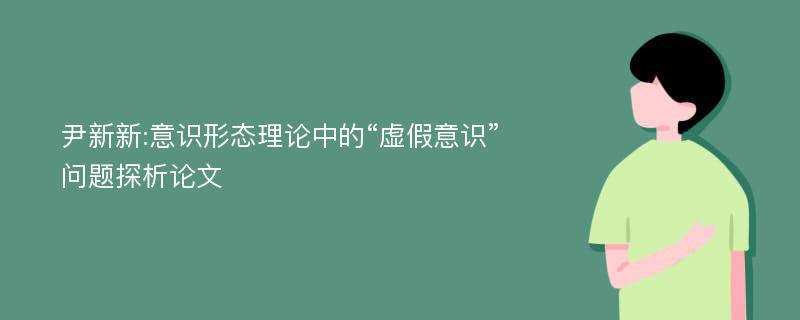
摘要:“虚假意识”产生的根源在于主体从事对象性活动所产生的思维局限,具有现实的物质制约性和历史的存在合理性。寻求“虚假意识”的克服途径是人类思想永恒的主题,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根本旨趣。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影响,使“虚假意识”的问题域与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其观点聚讼纷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文本分析和后继研究者间不同观点的比较分析,是对“虚假意识”进行重新审视并得到一个较为恰切和客观理解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虚假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虚假性;意识形态批判
“虚假意识”问题是意识形态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虚假意识”的不同理解折射出不同的意识形态观。探析意识形态理论中的“虚假意识”问题,也可以认为主要是研究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影响和深刻变革,所以,本文对“虚假意识”的研究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相关争论展开的。“虚假意识”问题蕴含在西方认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中。正如学者所言,“划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确立什么是真正的主观,什么是客观,在我看来,构成了哲学最早(最初)的基本问题”[1]。在承袭西方经验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法国的德·特拉西于1796年创制了“意识形态”概念,其初衷是摆脱“虚假意识”对人认识客观世界的影响和障碍,目的在于“希望建立一种观念的科学并且使之能够分析思想的界限”,并“假设奠基于理性和经验证据之上的‘中性’的观念的科学能够定位,从而改正谬误的、形而上学的推论的源头”[2]。然而,由于这样的立场和方法与拿破仑所维持的政权构成相违,使之成为被迁怒和打压的对象,致使意识形态“它不再只是观念学,而且也开始指观念本身,那就是说,指一批据称是错误的、脱离政治生活实际现实的观念的主体”[3]35,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看法使“虚假性”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随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占据19世纪德国主流的思想观念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并纳入到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体系和范畴之中,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使“虚假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马克思主义的后续发展又使这一争论不断深化。本文即是在挖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文献中对意识形态的阐述和比较分析后继研究者相关问题论争的基础上,对“虚假意识”问题进行的重新审视。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虚假意识”的阐述和理解
直接指明“虚假意识”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源自1893年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所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4]657。恩格斯的表述可以看作是将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说明的最为确切的文本依据,后继阐释者便以此为理论基础,将“虚假意识”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本质性规定的概括,即“虚假意识论”。以最具特征性的“虚假意识”问题为切入点,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述出发,是力图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得到一个客观有效的见解比较稳妥的路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这一段关于“行侠仗义”的探讨,发生在金庸先生所著的《倚天屠龙记》第五章末尾,便是谢逊大闹天鹰教的场子,意图抢夺屠龙刀之时。众所周知,张翠山是武当七侠之一,而谢逊是臭名昭著的金毛狮王,按江湖中的话来说,乃是“正邪不两立”。
1. “虚假意识”的概念群。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的特征描述为“虚假意识”,是其和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关系下存在的诸多现象的特征进行的概括,从而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具有价值上的否定性,而其虚假性的表现则在于人生存状态的实然和应然的“颠倒”。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歪曲”“倒立”“倒置”“幻象”等同“颠倒”具有共同的旨趣,目的主要在于揭示统治阶级思想为了维护统治而通过不同的载体和手段对真实社会关系进行的掩盖和遮蔽,这构成了“虚假意识”的概念群,是“异化”在思想观念上的集中表现。“颠倒”是“虚假意识”产生的直接原因,“虚假意识”则是“颠倒”的理论表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到人与宗教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5]3;针对黑格尔指出的只有“国家”才是解决个体自由与普遍共同体的矛盾和实现理性与现实和解的唯一路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应该受责难的地方,不在于它按现代国家本质现存的样子描述了它,而在于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的本质”[6],这种认为国家共同体对市民社会决定性的颠倒认识,暴露了黑格尔辩证法所具有的独断性和抽象性的形而上学特征;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谈到价格与价值的关系时,恩格斯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在价值学说上的认识误区,认为“经济学中的一切就被本末倒置了: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大家知道,正是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5]66;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人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5]162;在谈到货币敉平人的个性并使之同一化、抽象化时,说道:“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独立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5]247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将“虚假意识”和意识形态相互连接并进行特征描述和批判的主要文本,针对的是“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纯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5]512。马克思恩格斯在开篇便指明了当时资产阶级主流思想所具有的“观念的虚假性”:“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5]509在谈到“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因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时,两位作者认为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了[5]357。特别是针对当时占德意志主流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说道:“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5]525可以看到,上述在资本主义不同领域存在的社会现象均体现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征。
2. “虚假意识”产生的原因。从“虚假意识”产生的思想史的演进逻辑可以看出,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客观世界、自身和对象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偏差、歪曲甚至谬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实践的深入展开,对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是否能够有所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和克服。从人类思想的发展史来看,经历了从盲目性的接受到批判性的反思,从自在性意识到自为性意识的转变。“虚假性”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是意识形态作为被批判对象的主要原因。有学者便指出:“事实上,意识形态是唯心主义的模型或者范式。唯心主义思想是虚假意识,并且虚假意识是精神劳动的专有产品。”[7]49如此理解的“虚假意识”已经超出了上述对虚假意识的一般涵义,赋予了其阶级性和物质性。针对于此,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虚假性的批判便成为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奥秘。”[5]510传统形而上学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具有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它具有思维方式的“同一性”和“内在性”特征,它努力宣扬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为普遍利益,将“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其以意识形态掌控主体的利益诉求为鹄的,将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等等观念赋予独立存在的合法性,以掩盖实际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统治关系,排斥任何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子,从而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合法化和永恒化。马克思主要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的批判,瓦解并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赋予的精神(统治阶级意识)自给自足、自我圆融和永恒在场的内在幻象。但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这种“观念统治着现实”的“虚假意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想存在,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必然产物,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则是其根本原因,而这种分离则被马克思看作是“真正的分工”的产生,认为“于此同时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5]534。“意识形态便是这种哲学或精神劳动,其渴望充分的世俗化,然而却彻底的沉浸在宗教之中,以至于尽管其渴求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却持续的从非物质的领域获得特别的能量。”[7]44这说明意识形态与宗教一样,都是精神异化的产物,其根源在于作为物质生产的劳动的异化。据此,“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存在着两种颠倒----意识中的颠倒和对象化的社会实践的颠倒。前者他视之为意识形态,后者则是异化。意识形态掩盖了异化,构成了对颠倒的现实的颠倒的反映,而这又造成对后一种颠倒的否认”[8]138。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载体,必然在维护资本的剥削性质的同时,极力掩盖以私有财产分化造成的异化劳动所产生的种种不可消解的矛盾。所以在此意义上,“国家是异化了的社会力量,是作为一个异己的存在物凌驾于、对抗并剥削它本应服务的社会”[9]。
2. “虚假意识”的理论属性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描述,后继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称为“虚假意识论”,并随着实践的发展将其纳入整体意识形态之中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的涵义或属性进行的分类和概括在必然包含对“虚假意识”的处理的同时,也体现出研究者对“虚假意识”问题不同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1)曼海姆在对思想进行的知识社会学范式把握的过程中,把意识形态划分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指的是当“意识形态”这一用语“表示对我们的对手提出的观念和陈述有所怀疑时,它所蕴含的就是这一概念的特殊意义”,认为其具有“有意识的伪装”或其“真实认识并不符合他的利益”;而“总体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时代或这一群体的总体性的思想结构的特征和组成成分时,我们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群体(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并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整合起来”[24]。针对于此,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论”和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或世界观(Weltanschauung)”视为一对竞争的概念,认为曼海姆“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秉持的是一种“相对论的方法,根植于科学的实证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力图寻找的是“经验主义方法论的解释以有助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对各种意识形态的调查研究”[13]。(2)拉雷恩通过考察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明确认为存在“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和“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坚决认为马克思创建了“否定性”的意识形态观。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意识形态指的就是有限的物质实践所产生的思想,该思想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错误地表达了社会矛盾”,“所以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由其阶级出身来界定的,而是由掩盖矛盾这一属性来决定的”[8]25-26。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使“意识形态变成了战场但不再是战斗工具了”[8]95,即将意识形态概念从马克思的“否定性”内涵转换成了“肯定性”内涵,这在普列汉诺夫通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扩展初见端倪,而伯恩斯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而使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内涵逐渐消融殆尽,最后通过列宁革命斗争实践和意识形态的“灌输”理论得以正式确立。(3)瑞卡多·卡玛戈(Ricardo Camargo)对以拉雷恩为代表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分类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分类所依据的标准并不明晰,因为“虚假意识”是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分类的重要标准,但“虚假意识”的界定却因是否包含物质基础的考量而有所不同;另外就是作为意识形态合法化标准的支配关系也因为是否只以社会阶层为基础还是同时包括社会团体和性别等因素而产生疑问。卡玛戈试图通过“真理的阿基米德点”来确定意识形态的合理范围和基本范畴,将意识形态的研究分为“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积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消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三种途径。“消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中的“消极”与“轻蔑”和“批判”具有相同意思,来源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以批判理论传统构建的消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超越实证主义所捍卫的严格的合理性概念,从而扩展意识形态现象的特殊内容,以包含诸如非经验主义的信念、态度、愿望等等意图,将其合并成具有更加广泛合理性的解释性框架”,而“积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则忽视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批判属性,集中于生产意识形态而不去对其进行解释[25]。
随着意识形态理论的不断发展,对“虚假意识论”是否能够涵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产生了很大的疑问,这主要表现为三种理论趋向: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针对的是恩格斯以“虚假意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僭越式”的概括;非马克思主义者针对的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虚假性;后现代主义者针对的则是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说,意识形态研究的争议特点是‘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历史产物”[16]。通过对不同学者观点的比较分析,是厘清“虚假意识”相关理论论争,进而得到较为恰切理解的基础,其争论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
1. 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差异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一致性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虚假性”则更加凸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观点上的差异性甚至是冲突,挑起了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上是否存在异质性的诸多争论。持一致性观点的学者认为:“我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相似性,虚假意识可以用来界定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本质。”[17]持异质性的学者则认为:“恩格斯为意识形态专门造出了现在已经是臭名昭著的‘虚假意识’一词,那是马克思不会有意去做的事。”[18]而对恩格斯“虚假意识”的反对可以看作是否定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具有一致性看法的另外一种表达,主要认为“虚假意识”并不足以涵盖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甚至歪曲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并对后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具体而言,产生差异性的原因和内容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1)《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关于“虚假意识”的产生、表现以及克服的主要文本,特别是“费尔巴哈篇”。从文本考据学来看,对恩格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誊写者并不存在大的异议,有别于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著作的核心的传统观点,有学者提升了恩格斯的原创性以及对于马克思的影响[19]。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以恩格斯所总结的意识形态“虚假意识论”不足以涵盖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提供了支撑。另有学者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两种分工论,即马克思的“普遍交往论”和恩格斯的“废除分工论”,从而也形成了两种历史理论,即马克思的“分工展开史论(市民社会论)”和恩格斯的“所有形态史论”[20]。分工产生了异化,而异化是产生“虚假意识”的直接原因,所以对“虚假意识”的认识必然会演绎出以下不同的态度: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较为温和,认为虚假性的存在是通往对其克服的必然路径;恩格斯则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更加轻蔑,认为其应当与私有制一道被消灭。(2)有学者从马克思对意识问题探索的角度,指出了马克思对意识的认识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的认识存在着矛盾,这必然对“虚假意识”的理解产生影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5]499,这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根底上的唯心主义特征。据此,学者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定了一种通过意识而对外部世界的‘被动’的反映,因而回到了马克思刚刚谴责的立场,是很令人震惊的”[12]23-24。从“费尔巴哈篇”文本的考据来看,“恩格斯的笔记里并没有出现‘关系’一词”,恩格斯对意识的理解具有机械性,而只是一种单纯“自然意识”或“绵羊意识”,是恩格斯经过与马克思的讨论之后才添加上去的[21],即“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5]533。(3)认为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观仍然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那么作为其观点核心的“虚假意识”便首当其冲了。如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22]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夫·布洛赫的信中说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4]591据此有学者认为他“陷入了最野蛮的唯物主义决定论”,仍然没有认识到其理论上的缺陷即“不可能将观念从物质领域分离出来”,同时认为“马克思全部著作的要旨在于坚称否定的一方必然决定另一方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错误,这种错误根源于一种观念和物质力量的特殊的历史结构”[23]。
二、“虚假意识”的相关理论论争
3. “虚假意识”的理论定位。对“虚假意识”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中的位置,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1)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分别是认识论上的“虚假的意识”、价值论上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式”[10]。马克思基于认识上的谬误来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德国唯心主义,因为其歪曲了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但正是这种歪曲产生了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社会意识形式。(2)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分为“论战概念”“副现象概念”和“潜在概念”,“虚假意识”是“副现象概念”的典型表现,“它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以幻想的形式代表的阶级关系”。而“揭露一种意识的形式就是表明它是幻想的、错误的或者没有正当理由的;它意味着不但能根据社会----经济条件来加以解释,而且它歪曲了这些条件或者除了经验性地表明它反映地位决定于这些条件的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外并无正当理由”[3]43。(3)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分为“论战----揭露的”、“解释----功能性的”和“批判----哲学的”意识形态三种,但认为三者相互关联只是发挥的作用有所侧重,对“虚假意识”的剖析是“解释----功能性”的,意在回答“怎样,通过什么机制,统治阶级的思想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思想”[11]。针对上述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相对于其严格性的和一致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详细的阐述一种明确和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但并不能据此认为他们以一种武断的方式运用了这一术语,或者认为他们对这一术语的回应缺少理论上的有效性。相反,一旦将他们参与的具体的离散性的论战与其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就会发现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同用法是由隐含的连贯性结合在一起的,并令人惊讶地预示了后来意识形态理论的诸多成就”。该作者从这种理解出发,总结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三种主要向度,即“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PIT)构建”,并认为均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12]21-22。可见,“虚假意识”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应该看到,“意识形态是异化在认知上的反应”,“去异化是意识形态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一种对异化的特殊反应”[13]19-21,这样的理解与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是相符的,也是构建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思想来源,充分说明了意识形态掩盖既有阶级矛盾的功能属性,是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明显展现,所以在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初期,主要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通过对资本阶级意识形态运行规律的揭露,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对真实社会关系的掩盖,具有启蒙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可以认为接近甚至等同于“虚假意识”。但是,马克思“作为抱有激进革命精神的批判家,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时还主要是着眼于否定它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科学的说明它的原因和规律”[14]182,“这些颠倒的概念在现实社会世界中有其基础,这种现实社会世界是如此错误地被构成,以便产生这些补偿性的幻想”[15]152。所以,科学的说明“颠倒的概念”和“补偿性的幻想”产生的根源以及探索破除的方式,便成为摆在马克思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虚假意识”概念群的提出时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人本主义阶段,“由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的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还未制定出来,因而历史运动的最后动力还不是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而是依旧用人类的不变本性和违反这种本性的外部现实之间的冲突来说明”[14]297。而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尚未具备丰厚的知识储备,这就决定了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问题,一方面,着重于从人道主义批判意识形态在“异化”的形式下对人的思想的奴役和摧残,聚焦于种种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预示着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的合理性阐明的需要,这只有在通过不断丰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深入到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找到破除“虚假意识”的科学方法,这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环节。
传统高职课堂以知识传播和技能训练为主的培养模式,学生成为被培养的“物”,丧失能动性与自主性,导致课堂教学气氛机械而沉闷,高职课堂普遍玩手机打瞌睡成为一大风景。针对高职院校学生被动、懈怠的特点,必须让教师摆脱课堂上知识传播者的霸主地位,让学生在课堂上获得充分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学生作为鲜活的、有内涵的生命体。根据高职学生理解能力相对不是很强的特点,多加沟通互动,通过脱离“物化”课堂的压抑感,使学生取得生命发展的主动权。高职课堂的教师,要跳出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传递型定位,要在教育活动中,面向学生生命发展的未来,创设有利于学生出长的环境。
(1)随着对SO2排放限制越来越苛刻,硫磺装置在开停工过程中SO2排放同样有严格限制,仍需要达标排放。在目前情况下,仅仅靠优化工艺、高效催化剂和高效溶剂仍无法实现开停工或紧急情况下的达标排放,需要增加其它手段把关,如后碱洗工艺等,以实现SO2达标排放。
1. 以“整体性”的视野阐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思想。学者指出:“任何将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等同的尝试,都必须依赖于同马克思的后期著作相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5]158,这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既是恩格斯在晚年将意识形态描述为“虚假意识”的主要根据,也是后继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称为“虚假意识论”的根本原因,但也同时指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终点,其实质在于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成熟以及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唯物论阐释。对此,需要我们不拘泥于问题的表面对理解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窠臼,特别是跳出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论”的思维定式,而是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之中,以“整体性”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革命性变革,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特征和阶级属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已经为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这主要体现在针对黑格尔哲学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黑格尔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观念与现实的和解”从而最终达到“绝对精神”,虽然作为人类共同体理性实现形式的国家仍然不能够达到精神的圆满,但却是必须的途径,这鲜明地体现在黑格尔的国家观特别是对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态度上。“黑格尔哲学是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是体现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而又处于无权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益和需要、思想和情绪的表现”[33]。黑格尔哲学体系上的保守掩盖了方法上的革命,导致其对现实的屈从,将资产阶级的诉求寄希望于“观念上的革命”和对封建贵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的改良。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黑格尔对现代国家是理性的最高显现的辩白就只是对问题的意识形态表达;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理论中的对立面的调和只是思想中的调和,而事实上它必定仍然是要实践地解决的”[34]。其次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批判是继承和扬弃的辩证。《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具体地分析了鲍威尔、施蒂纳、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等通过“实体”“自我意识”“类”和“唯一者”等是对黑格尔思想体系的继承,尽管他们自认为是对黑格尔的超越和扬弃,并将之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由于黑格尔的思想在保守的体系中蕴含有革命的因子,所以无论是当时封建贵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均从自身的利益和诉求出发,将黑格尔哲学拿来为自己所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是当时德国哲学的主流和代表,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靶标。《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阐明,实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三个方面的超越:(1)指出德国唯心主义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和“思有同一”是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特征的代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时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2)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的批判,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说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3)在指明意识形态具有的“虚假性”和“颠倒性”的基础上,指出意识形态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预示了对意识形态运行规律和破除方式的进一步思考。最后是《资本论》及相关著述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虚假意识”及其概念群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基本看法的理论先导,并通过对当时德国思想观念的批判塑形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否定性内涵,但其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并非止步于此,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和《资本论》的完成,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态的视野深化了对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的认识,并预示了只有实践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渐破除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消极性。在《资本论》及其相关著作中,马克思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科学地阐明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运行方式和现实意义。伊格尔顿对此便持肯定态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探讨的我们关于意识形态的认知错误不只是扭曲的观念和‘虚假意识’的结果,而是以某种方式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物质结构之中”,“意识形态,对青年马克思是一个幻象和妄想的问题,现在则嵌入在物质世界本身,不是锚定在意识之中,而是锚定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日常运行之中”[27]32-33。这具体表现在对商品、货币和拜物教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得以表征的具体要素或现象的辩证分析当中,揭示出隐藏在物对人的统治之下的人与人的本质关系,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实现了从“物化”到“物象化”的思维范式的跃迁。
三、对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问题的重新审视
随着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虚假意识”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表达:一种指的是对人的真实存在样态的遮蔽,这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为典型代表,具有认识论的特征;另一种则是逐渐发展为对其他意识形态进行驳斥和诋毁的根据,即“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化,具有功能性的作用。本文认为,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和积极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的辩证理解,是对意识形态理论和“虚假意识”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的主线,而这一主线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影响和深刻变革。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3. “虚假意识论”的合理性问题。伊格尔顿是反对将意识形态看作是“虚假意识论”的代表,其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1)“认识论本身在此时是多少有些过时的,并且我们的一些观念‘匹配’或‘符合’事物原来方式而另一些则不是的设想,是有些感觉天真的、有损名誉的知识理论”;(2)“虚假意识可以被认为暗含着明确地正确认识世界的可能,这在今天受到深刻的质疑”;(3)“少数理论家垄断了具有科学根据的社会应当如何的知识,而剩下我们在虚假意识的迷雾中踯躅的观念,不见得能使其受到民主的敏感性的青睐。”[26]可以看出,从对“虚假性”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中,无论是“虚假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还是二者的具体内涵和功能属性,都存在着重大差别,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虚假性”的外延过宽,以至于丧失了强调“虚假性”的意义。伊格尔顿便指出:“如果所有的意识都是虚假意识,那么这个术语覆盖了太多内容,就会从视线消失;这就是后现代为什么很少谈论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27]42麦克里兰则认为,“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自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它几近虚无,既然它无所不包,那么也就毫无意义”[28]2。(2)“虚假性”只是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表征,深刻的现实社会关系是其赖以存在的根源,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齐泽克就断言,“意识形态与‘幻想’毫无联系可言,与其社会内容的错误、扭曲的表征没有任何关系”[29]。伊格尔顿则认为:“那些反对意识形态虚假意识观念的人正确的看到了意识形态并不是无根据的幻象而是具有坚实的真实性,一种活跃的物质力量必然至少具有足够的认知内容来帮助组织人类的现实生活。”[26]26海尔布隆纳也承认:“资本的意识形态问题源自社会中对统治进行详细阐释的需要。”[30](3)“虚假意识”背后透露出的是意识形态主体的诉求和目的,是主体实现其诉求和目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发现或知道真理并不是意识形态的目的”[13]31,“意识形态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实践上运用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加以否认”[31]306,但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必然诉诸“真理”以驳斥对方。所以,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具有相对性,主体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其必然否认己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同时主张对方思想观念的“虚假性”。(4)“虚假性”并不能涵盖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见解是将“照相机比喻”看作是马克思对“虚假意识”的形象表达的传统见解不同,学者认为:“照相机的成像被理解为并不是对‘虚假意识’的比喻说法,而是要理解为阶级社会的‘观念的上层建筑’。”[12]31第二种见解认为要区分“虚假意识”和“意识形态幻象”,其认为:“一种意识形式能够被认为是‘虚假意识’,就如我们的‘意识形态幻象’所认可的,一种意识形式可以是‘虚假的’(至少具有虚假的成分)。但这里对其概念的辩护是,一种意识形式的幻象并不是其本身是‘虚假意识’,再一次重申,它可能被认为虚假意识,并且是虚假的。将意识形式认为是虚假意识是因为忽略了,或者自我欺骗了关于为何如此认为的真实动机。”[32]
2. 用辩证的方法理解意识形态内涵和功能的转换。“摇摆于肯定的和否定的含义之间,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历史的特点。”[28]8可以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的“虚假意识论”的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进路和演化逻辑,是马克思恩格斯始料未及的:其理论和实践属性从轻蔑性、否定性、批判性转换成了积极性、肯定性和建构性,意识形态从斗争的标的经由斗争的工具最后变成了斗争的场所。但如果从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只要不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偏见,教条地咬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意识形态思想的只言片语,那么,意识形态内涵的转换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也是意识形态的功能与实践相符合最为生动的体现。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意识形态等于直接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意识形态否定性和批判性的理解,从而质疑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继承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积极性内涵的认可和建构功能的运用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论。持“违背说”的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针对马克思“最接近”肯定性意识形态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的,“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5]592,学者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上的偏差,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冲突”,特指“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而马克思主义却将其理解为社会关系分为“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两种,“如此二分法容纳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建立了将意识形态沦为观念的理论认识”,“意识形态似乎是一套观念,其中代表着一种‘客观的’阶级利益,它可以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12]55。另一种是将肯定性意识形态转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大缺席”,认为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费尔巴哈章”在俄国出版时间是1924年,在德国则是1926年,所以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概念否定性的支持[8]55。据此,学者进一步总结了意识形态内涵转变所带来的三个后果:(1)失去批判内涵;(2)意识形态和阶级的关系被改变;(3)意识形态和矛盾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并进一步表达了对此问题的看法:“我反对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解读为一种肯定性的概念,但我支持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探讨,并承认他们的理论贡献。”[8]94-97本文认为,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思想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域进行理解和阐释,即使凸显出意识形态的积极性和建构性,也不能得出就此失去批判功能的结论;同时,即使从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出发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也不存在疑问。《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35]30,“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35]66。共产党人的“观点和意图”,不是自恋性的呓语,而在于通过其宣传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相结合,获得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证明,从而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除文本依据之外,以下几点简要说明也能够提供进一步的根据:(1)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和肯定性着眼的问题域和现实条件不同,单纯的直线性平面化比较并没有认识上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2)人类实践的目的之一便是对“虚假意识”的克服,其产生是思维与存在异质性的必然,如果将“虚假意识”概括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属性和特征,那么对意识形态否定性的理解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这与事实相违;(3)意识形态并不是单纯的思想观念之争,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意识形态担负起维护政治统治合法化合理化的重要职能,“这就决定了其实质是阶级意志的思想表达,其作为历史现象所固有的历史合理性和变动性”[36]。所以,只有根据客观实践发展的需要,辩证地理解意识形态属性的转化,才能避免理解上的教条性和机械性。
3. 从“主体性”的维度深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既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理论储备。与单纯从立场上进行反驳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内在性的。这里的内在性批判主要指的是方法论上对黑格尔具有革命因子的辩证法的改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发展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如有学者便指出:“马克思一生至始至终深深的受惠于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并直接地使他了解了一大堆问题的方法论。我的主张之一是,如果离开他在批判资本和资本主义基础上而面向未来的特定视域,就不能充分地抓住和领会马克思的辩证法。”[37]具体来说,内在性批判能够深入到资本主义固有的运行规律之中,揭示出传统形而上学与资本属性诉求的一致性,在内部贯穿资本主义制度非历史性的神话,从而在否定的肯定中预见未来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超越性和辩证性的理论特质。而从“主体性”维度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则是内在性批判最为重要的一环。阿尔都塞率先指明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认为“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但我同时而且立即要补充说,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主体”[31]303。正是因为资本的抽象性和逐利性,使作为“主体”的“具体的个人”“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35]34,资本承袭了传统形而上学“实体即主体”的理路,是传统形而上学在社会关系层面的具体显现。对此,齐泽克敏锐地指出了蕴含其中的宰制个体自由和丰富性的权力欲望:“‘主体’代表现象化、表象、‘幻觉’分裂、有限、知性等非实体的执行者,并且,对绝对的生活而言,认为实体是主体则意味着分裂、现象化等是固有的”,“与实体和主体的思辨的同一形成对照,它们的直接同一的概念包括了主体的加倍,这又一次把真正意义上的主体降为一个实体的绝对的事件(‘载体’),即一个难以‘通过’有限人类主体讲话的他者”[38]。这实质指的便是传统形而上学集大成的“绝对精神”。具体而言,资本的形而上学逻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独断性”:资本增殖的天性是任何存在物存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所有存在者存在的依据和标准都必须由资本来裁决;(2)“同一性”:抽象劳动是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永无止境,必然抹平个人存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3)“绝对性”:资本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必然成为真理唯一的掌控者,对一切异质的声音均持否定态度;(4)“永恒性”:资本对自身的悖论视而不见,否认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此维护自身统治的“千年王国”。资本的这种统治力量在现代社会,以更为精致、更为隐蔽也更为多元的姿态呈现出来,由于物质基础所限,社会主义也仍然超越不了资本在既定条件下所具有的进步功能,差别则在于掌握资本的阶级的阶级属性以及资本配置方式的不同。一般意识形态,虽然基本性质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但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关注的主要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个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和对未来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在当今时代仍具有不可超越的思想价值,资本的统治之网及其作为现实表征的“拜物教”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更加的突出,被资本裹挟下的人类存在境况是当今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指向。诚如马尔库什所言:“拜物教的理解力和概念不仅仅是一种混乱思维的‘幻觉’和谬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对整个历史时期来说还是‘社会有效的,并因此是思想的客观形式’,这些思想也完全包含着这样明确的观点,即哲学思想的形式不仅是由社会产生和决定的,而且事实上是具有实际效用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真实的、正当的和‘正确的’”[11]。所以,可以认为,“资本”是当今凌驾于人类主体之上的最具现实性和影响性的“主体”,“对主体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就是要揭示‘主体’和‘主体性’身上所笼罩的意识形态覆盖物,解构‘主体’和‘主体性’观念所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从而暴露它所包含的独断性与虚幻性”[39],“揭示‘主体’与‘主体性’作为意识形态幻象的实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对人的抽象化理解,推动人们重新认识人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40]。
由表5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板厚32m m和50m m的Q 5 0 0 q E钢板焊接热影响区最高硬度分别为272H V10和264HV10,低于380 HV10,说明Q500qE钢板的焊接性良好。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思想具有从抽象到具体、从表象到本质、从人本主义到科学主义、从局部问题到世界视野的理论特征,通过其意识形态理论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理论和实践、理性和感性、理想和现实既充满矛盾又不得不将之解决的辩证关系。在对包括意识形态虚假性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所具有的独断性、绝对性和非历史性进行彻底批判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出了只有无产阶级实践的不断深入才能逐渐破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这也是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必要条件。聚焦当代中国,狭义上的掩盖统治阶级的统治目的并使其统治合理化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已经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但作为个体的人仍然受到凌驾于其上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和宰制,人的思想观念对其自身存在的认识依然不会完满,广义上的“虚假意识”不可避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在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凸显了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这对加强党的领导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消极因素仍然存在,需要将意识形态的批判作用和建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物质需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等一系列举措,从而有效巩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领导权和管理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提供制度构建的思想支撑。
参考文献
[1] Т.И.奥伊泽尔曼.元哲学[M].高晓惠,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04.
[2] James M.Decker.Ideolog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4:16.
[3]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0.
[7] Ariane Fischer. Philosophical (pre)Occup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Idealism: From Ideology to Marx’s Critique of Mental Labor[J].Doctoral Thesi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oQuest LLC, 2010.
[8] 乔治·拉雷恩.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M].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9] 艾伦·布坎南.马克思与正义[M].林进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6.
[10]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5-16.
[11] 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J].孙建茵,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139-150.
[12] Jan Rehmann. Theories of Ideology[M].Boston:Brill, 2013.
[13] Warren Frederick Morris. Understanding Ideology[M].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10:14.
[14]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5]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M].3版.郑一明,陈喜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6]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郭世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7] Christopher L.Pines. Ideology and False Consciousness: Marx and His Historical Progenitors[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6-7.
[18] 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M].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9.
[19]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8-375.
[20]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M].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2-204.
[21] 岩佐茂,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M].梁海峰,王广,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55.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
[23] David Hawkes. Ideology[M].London:Routledge, 1996:105-106.
[24]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84,104.
[25] Ricardo Camargo. The New Critique of Ideology[M].New York:Routledge, 2013:22-37.
[26] 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M].London:Verso,1991:10-11.
[27] Terry Eagleton (Ed.). Ideology[M].New York:Routledge, 2013:42.
[28] 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2版.孔兆政,蒋龙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
[29] 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30] 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M].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95.
[31]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32] Tommie Shelby.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Moral Ideology[J].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8:18.
[33] 杨祖陶.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32.
[34] 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M].应奇,罗亚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2-63.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 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2):5-13.
[37]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M].Boston:Brill, 2012:4.
[38] 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0.
[39] 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0.
[40]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21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9)01-0009-10
收稿日期:2018-11-20
基金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研究”(2015MZD048)。
作者简介:尹新新(1980-- ),男,吉林德惠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9.01.003
〔责任编辑:朱根〕
标签:意识形态论文; 马克思论文; 虚假论文; 恩格斯论文; 意识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话语权; 管理权研究”(2015MZD048)论文; 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