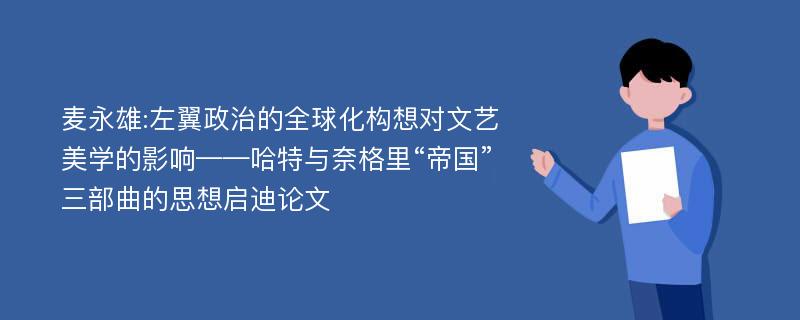
摘要:在当代左翼激进政治领域,美国哈特和意大利奈格里合著的“帝国”三部曲(《帝国》《诸众》和《共同体》)在新千禧年以来引发广泛的关注与反响。《帝国》尤其被视为21世纪文艺理论复兴的标志性著作,它所催生的“帝国研究”刷新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符号学、后殖民批评等思想观念;《诸众》聚焦于抵抗帝国的新主体,对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赛博空间博弈具有特殊意义;《共同体》则构想了一种反抗帝国统治的民主政治。当代左翼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有着丰富复杂的思想赓续或空间对话关系,“帝国”三部曲堪为典型。它们体现出审美乌托邦的力量,启迪人们对当代世界体系和文艺美学新形态进行反思。
关键词:左翼政治;帝国研究;诸众;共同体;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
当代全球化、电子化快速发展的情境,催生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帝国研究”领域,更新与拓展了文学批评与理论的空间。新千禧年伊始,美国左翼理论家米歇尔·哈特和意大利激进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Empire,2000)一书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强烈的反响,享有新世纪共产党宣言之誉。《帝国》及后续的《诸众》(Multitude,2004)、《共同体》(Commonwealth,2009)一道,被称为当代左翼激进政治“帝国”三部曲。它所衍生的“帝国研究”“诸众”和“共同体”等重要理论话语,对于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符号学、后殖民批评理论、赛博空间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启迪意义。
从2006年提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到2012年“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再到2017年“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以及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关注农民的培育与发展问题。“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领域的核心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双创”教育,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双创”能力作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农民职业化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1世纪理论文艺复兴的标志性著作《帝国》
哈特与奈格里的合著迄今已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令人瞩目的现象,几乎可以媲美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学术合作的著名传奇。哈特与奈格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帝国》以左翼政治的构想叩击全球化的脉动,见解独特,面世后被译成20多种语言,引发众多争议与讨论。
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1961- )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1983年在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宾夕法尼亚州索思摩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他对政治和第三世界国家抱有浓厚兴趣,毕业后在中南美非政府组织从事政治与慈善项目工作。20世纪80年代,哈特研究比较文学,获得华盛顿大学硕士(1986)与博士学位(1990)。1993年,哈特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讲授文学与意大利语。哈特早期撰写论奈格里与德勒兹的学位论文,翻译了奈格里《野蛮的异端: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与政治学的力量》(TheSavageAnomaly:ThePowerofSpinoza'sMetaphysicsandPolitics, 1981,英译本1991),由此与奈格里结缘。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 )的生涯交织着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他1956年获帕多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同年任职于该大学法学系并且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两年后获帕多瓦大学法哲学博士学位。1967年奈格里任帕多瓦大学政治学院院长,1979年因参加激进政治活动被捕而终止教授职位,入狱11年,流放14年,但这一切并未阻止其学术生涯和政治承诺。从1983年至1997年,奈格里在巴黎过着流放生活,在巴黎大学任教和著书立说。在此期间,奈格里遇见其著作的译者哈特,两人开始了硕果累累的学术搭档工作。
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与“反理论”之争近年来颇令人瞩目。不同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的基本判断,美国著名文论史家雷奇在《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文艺复兴》(2014)中引人瞩目地提出:一系列21世纪的奠基之作共同提示了一种理论的文艺复兴。他特地遴选了六部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奠基著作,首先就是聚焦于21世纪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性著作——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其他五部标志性著作包括:当代少数族裔身份认同研究最令人瞩目的学术著作——克莱格·沃马克的《红又红:本土美国文学分离主义》;21世纪最尖锐热情的身份认同理论批判——文学批评家迈克尔斯的《多样性的麻烦:我们如何学会热爱身份认同与忽视不平等》;意大利著名哲学家阿甘本的《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抨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巅峰之作——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刻画新自由时代残酷画面的法国畅销书——政治哲学家巴迪欧的《萨科齐的意义》。可以说,哈特与奈格里借鉴马克思、福柯、德勒兹、阿甘本等人的理论资源,揭示了全球化的“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和“逃逸线”的理论形态,以“帝国研究”(Empire Study)范式将资本主义批判、文学理论与反帝国的政治民主构想引入更宏阔的新视野。
二、左翼激进政治的“帝国”论与资本主义批判
总括而言,《帝国》讨论的是政治哲学的经典题域——帝国的兴亡。它面世于新千禧年来临之时,受益于双重语境:一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1980);二是意大利左翼政治。哈特熟悉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观念,奈格里则亲历了意大利激进社会与政治传统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力量”与“工人自主”运动,两人感时论世,出版著述。两人合著的《帝国》论证了旧帝国失效,新帝国崛起的图景。全书分四个部分(共十八章):一是“今日世界的政治构造”;二是“主权的转变”;三是“生产之道”;四是“帝国的衰落”。
20世纪末,美国白宫智囊团成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曾经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引起关于多种文明与不同政治势力能否和谐共存的广泛争议。而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则另辟蹊径,探索一种全球民主政治范式:随着跨国资本不断向外扩张和西方式全球化凸显,是否也会出现一个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全球性秩序,我们能否超出以“主权”为表征的民族国家视野,看到一种全球共同体,一种去中心的、网状形态的全新主权形式——“帝国”。
作为游牧美学图式,光滑空间、条纹空间、多孔空间互相交织缠绕,分别代表了三种基本的哲学力量。譬如,在电子传媒世界里,三者可以并存于虚拟现实的赛博空间:网民在互联网上自由自在地网上冲浪,随心所欲地打开一扇扇网页游牧,进入QQ聊天室私聊,任意组团玩电子网络游戏,进行人肉搜索,心血来潮时写点微博,尽情享受光滑空间;但条纹空间的力量也在起着作用,网管、“斑竹”(版主)随时会把犯规犯忌者踢出局,儿童上网受到成人的限制,网络色情、电子犯罪受到规则、政策、法律的监控或处罚,光滑空间受到公理化的、定居的、条纹的、辖域化式条纹空间的遏制;在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的张力中,多孔空间的利用者有机可乘:人们因不同的利益驱动在赛博空间博弈,黑客或居心叵测的骗子可能钻空子,巨大的利润空间和利益链使得色情网站在扫黄之后很快就死灰复燃。因此,在诸众主体与赛博空间关联域,德勒兹的空间哲学与哈特/奈格里的民主政治思想交叠互渗,启迪人们更深入地认知主观能动性与空间结构之间的纠缠不休、持续生成的博弈特征。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奥匈帝国的国徽双头鹰可以用作当代帝国形式的标识。不同的是,今天它的两个头不再远眺,而是互相对视,互相啄咬。帝国之鹰的第一个头是由生态政治控制机器构造的司法结构与宪制力量,另一个头则是由全球化的生产主体、创造主体构成的大众(诸众),他们既生存于帝国之内,又反抗帝国。《帝国》坚持了欧美左翼思想家立足于社会底层的大众立场。哈特与奈格里认为:“穷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体,是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一切可能的基础。穷人是“永恒的后现代者:穷人的形象代表着一种差异的、流动的主体”。《帝国》最后一章讨论“反对帝国的民众”,为《诸众》的撰写埋下了伏笔。作为新帝国主体的诸众必须在行动中创造一个共同体才有未来。
总括而言,《帝国》主张这个世界没有外部,论述了全球层面上主权的扩张、重构和新功效等方面的趋势;《诸众》认为抵抗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动力,分析了新主体的出现及意义,哈特和奈格里称之为“反帝国”;《共同体》则试图以共同体超越、摧毁和重构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是一种乌托邦色彩的未来政治哲学构想。
(5)矿井直接充水水源。为龙潭组的裂隙水和茅口组碳酸盐岩溶洞水,龙潭组富水性弱,茅口组富水性强,具承压性,25号煤层与茅口组揭露最短距离为55.60 m,岩性为泥岩泥质粉砂岩,起了一定的隔水作用,正常情况下对矿井充水影响不大。但区内断层切割使茅口组强含水层与含煤地层连通,因此对于断层一带的开采有直接影响。在开采深部煤层时尤其要注意。
三、“帝国研究”与西方文论
(一)帝国研究与符号学
国际畅销书《帝国》言说和倡导了一种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中的理论新图式。刘禾在关于哈特和奈格里《帝国》学术话语的访谈中,从“跨文化的帝国符号学”的维度评介了资本主义全球发展和西方“符号学转向”。她认为,欧洲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二元论符号学(Semiology)与美国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Semiotics)是差异明显的两套系统。前者主要影响了结构主义范式,后者则是后结构主义的思想金矿。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符号学家在构想符号学的同时,国际政治也在经历“符号学转向”的过程。各种各样的人造符号,比方说海军使用的旗语、灯语、电报符码、路标、聋哑人的手语、世界语等,都在这时候纷纷出现,使得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次符号系统的大爆炸。当时的主权国家(当然是被列强承认的主权国家,后来也包括日本)在一起开国际会议的时候,除了讨论战争与和平、主权和领土问题,也开始讨论怎样统一度量衡,怎样使用信号和符号,比方说商船和军舰怎样互通信息而不致产生混乱。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专门的国际会议商讨决定各国采用什么信号和符号,如何统一符号系统,而这在当时还是一件新事物。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许多信号和符号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出台继而被承认或被淘汰的。[2]这种高屋建瓴的“跨文化的帝国符号学”视野,为全球化和当代西方文论领域的语言符号学转向展示了宏观背景与社会文化意义。
加大政府宣传力度,电视、新闻、报纸、网络等媒体深入宣传国家粮食政策,报道耐密型玉米增产典型、高产栽培技术和增产潜力。良种补贴向耐密型玉米品种倾斜,适当增加玉米高产创建示范区数量,做好示范观摩,让更多农民亲身体验耐密型玉米的增产实效,从而积极主动地选择耐密型玉米品种,改变种植稀植大穗的老习惯。
(二)帝国研究与后殖民批评
在古希腊,“欧依蔻斯”意为人的家宅、住处或栖息地,在今天则意味着一种政治生态学的“栖居科学”模式。哈特与奈格里的“共同体”憧憬,既赓续了希腊思想传统,又与当代政治生态学遥相呼应。拉图尔在其名著《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中凸显了这种“探索共同世界”的政治生态学题旨。他认为“必须将欧依蔻斯(oikos,栖居)、逻各斯(logos,理性)、菲希斯(phusis,自然)和波利斯(polis,城邦)这四个概念同时运用”,才能解开政治生态学的谜题。[8]4拉图尔提出:政治生态学需要献身于一个细致分诊的可能世界,生命的宇宙蓝图 (the cosmograms)历时常新。[8]365因此,人们要破除柏拉图“洞穴”神话的两院制旧政体,启动包括人类与非人类在内的集体“议题”,运转网络状的“行动者网络”,实施非现代主义的新宪政,落实新分权——考量权、排序权和跟进权,让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道德家等各得其所,通过学习曲线和集体实验,分别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逐步构成共同栖居的“欧依蔻斯”美好世界。
对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理论而言,“帝国研究”标志着文艺美学范式的重要转向。在政治哲学维度,现代主权的世界是一个二元论世界,它分裂为一系列二元对立:自我和他者、白人和黑人、内部和外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从差异政治学维度看,后现代主义思想挑战的正是现代性的这种二分逻辑,它为那些同父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作斗争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后现代主义者坚持差异性与具体性,也挑战着极权主义、统一化话语和权力结构。后现代理论中与文化的混杂性、流动性相关的内容为这些斗争提供了支持:一方面,哈特与奈格里质疑僵硬的种族研究二元论,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殖民地世界从来就没有服从于这种二分式的辩证结构。……我们不能仅仅考虑白人和黑人,至少我们还要考虑混血人群的立场。后者有时同白人联盟,因为他们拥有自由和财产,有时又与黑人联盟,因为他们的肤色还不够白。”[3]153另一方面,他们的“帝国研究”范式又拓展了全球化历史视野,使得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殖民理论呈现出滞后性和局限性。
哈特与奈格里进一步认为:“殖民主义的结束和国家力量的式微,显示了一场由现代主权范式到帝国主权范式的普遍转变已经到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林总总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首先向我们展示了这场转变,但这些理论仍有局限”,因为正如这些理论所带的“后”字所显示的,“它们不知疲倦地批判旧的统治形式,以及旧形式在现在的遗留,从中寻求解放”。但后殖民批评的理论阐释力开始失效:
我们怀疑,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会走入死胡同,因为它们未能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它们认错了敌人。这些理论家花那么大的气力来描述、抗争现代权力形式,可如果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控制我们的社会了,怎么办?……它们模糊而混乱,并没有意识到主权形式变迁所带来的范式飞跃。后殖民主义观点基本上仍在关注殖民主权。这可能会使后殖民主义成为解读历史的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在关于当代全球权力的理论表述方面,它却力不从心。即使爱德华·赛义德这位后殖民主义旗帜下最才华横溢的理论家,也只能做到批判当前的全球权力结构延续了欧洲殖民主义统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残余。可是他忽视了掌控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和逻辑的新颖性。帝国绝不是现在帝国主义的一声微弱的回响,而是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3]166-176
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三部曲”,通过赋予诸如“民主”“共产主义”等政治概念以新的含义,把“爱”“穷人”等概念提高到政治学的高度,探索一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另类政治形式:在“帝国”时代建立在“共同体”之上的“诸众”民主政治。[4]《诸众》努力要回答的是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问题。作为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新主体,诸众有别于构成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人民。人民对内同质化,对外具有排他性;而“诸众”则是阶级斗争新形势的基本模式。它涉及被剥削的劳动力,因而比工人阶级的概念更宽泛、更全面。同时,诸众不是毫无区别的乌合之众,不是民族,而是诸个体构成的网络,是多元异质的大众,包括家庭妇女、农业工人、学生、研究者等等。他们构成了反帝国的主体,具有民族国家所无法统摄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诸众作为很有用却难以操作的政治概念,具有不可测的“可怕”特点,“是今天充满对抗的世界里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理解的核心”。[1]55鉴于资本在全球层面的变化,诸众表达了一种生命政治的活动、民主政治的生产和生命权力的反抗。
四、诸众民主政治与赛博空间博弈
鉴于今天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的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已经不限于第一代的社会文化体验及其文学表达,因此,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只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在一定人群、一定阶段范围内才有效,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在同殖民主义的思想残余作斗争。总括而言,后殖民批评的主要对象只是“帝国”变迁的一个历史阶段。面对世界性散居族裔、移民文学和流散作家的第二代、第三代的繁复嬗变,后殖民批评理论日益显得捉襟见肘,而“帝国”观念在现阶段似乎更适合阐释当代世界。
我们将“帝国”三部曲纳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时空坐标,可以更好地揭示左翼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纵横交错的赓续关系和对话特征,凸显其当代理论价值与思想弱点。
哈特与奈格里的左翼政治三部曲的关键概念“帝国”“诸众”与“共同体”,无疑受到了德勒兹与加塔利等人的影响,并且与当代思想家如福柯、德勒兹、加塔利、韦伯、阿尔都塞、哈拉维等人的话语形成重要的空间对话关系。[5]2615-2619哈特与奈格里将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加以结合,将他们的理论洞见融入政治与民主的致思,描绘了一幅特异的图景:人们所熟悉的传统帝国主义与现代主权国家可能在加速“解辖域化”,一种无疆界、多元化的新“帝国”全球化政治秩序正在出现,但是这种“帝国”又绝非自由狂欢的嘉年华。数字媒介的无形“帝国”或列斐伏尔所言的“技术乌托邦”,隐含着当代赛博空间兼顾雅典式民主嘉年华与罗马式角力斗兽场的博弈。福柯的“生命权力”(biopower)观、德勒兹差异哲学及游牧美学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形态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历史过渡……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之中。”[3]29在他们设想的“全球体制的金字塔”中,顶端是超强权,包含着武力霸权、金融霸权和联合体;中间是跨国资本主义公司的世界网络,覆盖着民族国家;下层是利益团体,是民众的代表。“帝国控制通过三种全球的专制手段来运作:炸弹、金钱和无线电……这种控制手段使我们又想到帝国权力金字塔的三个层次。炸弹是一种君主权,金钱是贵族权,而无线电则是民主权。”[3]394-396在帝国全球治理中,热核武器是炸弹的标志,金融机制是基本手段,无线电则是主要媒介。诸众作为新主体,在数字化媒介的赛博空间尤为活跃,同时,诸众民主政治的复杂境况在电子网络空间得到了典型的体现。在中国,尤其是在新时代反腐败曝光和舆论监督方面,作为诸众的网民在赛博空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诸众似乎可以在赛博空间自由无羁地跟帖灌水,参与娱乐与操控电子终端(如手机、电脑),但是,网络管理者、利益攸关方、权力机构或主流意识形态无不在时时刻刻加以规训与管理,不同的利益力量在进行博弈。
当代左翼激进政治“三部曲”与德勒兹的差异哲学之间蕴含着某种思想赓续与范式互补关系。德勒兹的三重空间论具有特殊的思想力量,它们包括:光滑空间(smooth space)、条纹空间(striated space) 与多孔空间(holey space)。条纹空间是同质的,辖域化的,是科层化、规训的、有固定边界的空间;光滑空间是充满差异、解辖域化、无中心化组织、无高潮、无终点的自由游牧空间;多孔空间是鼠洞式或块茎式的多元空间,四通八达,是暗中连通前面两种空间的“第三空间”和“地下”空间。[6]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经常混杂。游戏、城市、音乐、技术、战争、美学等都是例证。棋艺既有游戏的自由,又必须遵循棋盘游戏的规则,否则无法下棋。一个城市有街道、建筑、地址等条纹空间,可是孩子们在城市公园里玩耍,能够跑这跑那,从而划出他们的光滑空间。因此两种空间是交叠的,它们可大可小,可全球化或本土化,具有视觉或听觉、物质或精神的属性。[7]
马克思的幽灵在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德里达、阿甘本、哈特与奈格里等人的著述中出没。哈特与奈格里认为,讨论趋势的方法是马克思著作的一个特征。2004年,他们造访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把帝国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全球战争联系在一起,其中心假设是:在今天的全球层面上,在帝国主权网络中,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以去中心化的形式出现。帝国不是一个既成事实,而是一种趋势。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工业劳动失势,新的生产形式“非物质劳动”代之而起,占据了统治地位,“情感劳动”成为主要形式,知识、信息、语言和情感关系走向前台。若把这种新的统治形式称为“生命政治劳动”,[1]132-138会更恰当一些。它不仅生产物质产品,也生产各种关系,最终,生产社会生活。帝国研究的生命权力概念受到福柯影响:谈论生命权力就是谈论生命政治。每年世界的统治者聚集在一起,确立统治世界、控制全球剥削进程的游戏规则。瑞士达沃斯变成了帝国构成的图谱,是现今全球权力再现的佳例,也是一种俄罗斯套娃结构:美国主权是外壳,内部是跨国公司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各政治阶层,大众则被警察、催泪瓦斯、雪球阻挡。[1]40而处于行动中的诸众就是反帝国的抵抗力量。奈格里认为,德里达和阿甘本从边缘策动抵抗策略,而福柯和德勒兹则采用以中心为出发点的策略,更有意义也更有效。[1]224-225福柯晚期的伦理学转向侧重个人技术,而哈特与奈格里则从全球化的帝国视野谈论问题。
面板混凝土裂缝,委托专业施工队伍按照处理方案进行了处理,处理完成后,经验收合格。工程未发生质量事故,施工质量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五、共同栖居的“欧依蔻斯”
确定资料的来源与收集方法。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多元化时代,资料的来源是丰富的。可以在图书馆或书店通过书籍、报刊、杂志、文献等来收集,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和数据库等寻找网络和媒体信息。
哈特与奈格里合著的《帝国》堪称将后殖民批评理论拓展到全球化视界的重要著作。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第七章“转变的迹象”被收入雷奇主编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汇编《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2010)。它认为,随着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殖民统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两德统一,1991年苏联和东欧阵营解体,“冷战”终结,海湾石油战争波谲云诡,中国作为经济“巨人”崛起,跨国大公司与电商快速崛起……全球化戏剧性地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一种新的现象——“帝国”——物化了我们的后现代生活。由于出色地描述了“帝国全球政治的新秩序”,《帝国》成为21世纪畅销书。
影响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因素较多,且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主要有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是指水文气象、地形地质和水土类型等;人为因素是指施工人员整体素质的高低,技术能力的强弱,配合能力的好坏等;社会因素是指政治环境、经济、生态安全等背景因素。
毫无疑问,不论是哈特/奈格里的“共同体”,还是拉图尔的“欧依蔻斯”,都具有乌托邦理想蕴涵。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奈格里的演讲集《超越帝国》(2016)的封套设计凸显了这样的宣传文字:如何反抗并超越“帝国”统治下的全球秩序?《帝国》作者奈格里的又一力作,展现了“美丽的新世界”的另一种可能!奈格里并不认可线性历史观,他关注帝国的各种“运动”、多种趋势,以及帝国之中的秩序机制和反抗问题。奈格里曾辩解说,人们对传统的乌托邦常常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予以挖苦和耻笑。但在今天全球化、后现代的帝国政治秩序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外部”世界,因而这种新的乌托邦代表着一种卑微的声音在讨论可能之事,我们可以直面并且实现帝国中的乌托邦抵抗功能。目前正值一个现代结束和后现代开启、民族国家消亡和帝国奠基的“空当”,矛盾丛生,而“文学和美学的前卫性要创造出乌托邦。只有乌托邦竭力去抓住构建现实的集体实践的这种极端可能性,世界的终结才变得越来越有可能”。[1]75
六、“帝国”三部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赓续与对话
《诸众》的副标题是“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它认为只有帝国底层的大众才有足够的创造力来反抗帝国并超越帝国。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颇为有力地说明了这种状况: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差异(商品、人口、文化等差异)宛若无限裂变增生的形态,给任何二元划分的固定边界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在新的自由空间出现的无数差异并没有在全球光滑空间内自由嬉戏,而是被控制在由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结构所组织的全球权力网络之中。联结全球系统的跨国大公司并不像旧式的现代主义模式那样简单地排斥性别、种族的“他者”,而是力求容纳差异性,允许不同种族、性别、性向的人加入,形成多样性、流动性的自由创新工作空间,为利润服务。美国霸权统治是帝国治理的象征,体现了当今全球政治结构的特征。帝国通过更多生活领域的互联,实际上创造了新型民主的可能性,让更多不同的群体组成反抗帝国的新力量——诸众在此意义上类同“芸芸众生”,可以打造不同于现存秩序的一种可选择的民主世界。针对悲观主义的误解,该书认为在“帝国”时代,可以克服恐惧,践行民主之梦。《诸众》以其乐观主义的欣快与深邃的眼光,巩固了哈特与奈格里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哲学家的定位。
左翼政治哲学关注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内部机制,往往将帝国的现实反抗与未来构想联系起来,带有特定的乌托邦色彩。奈格里曾经谈到,帝国的多种趋势使得“建构一个全球化的反帝大众体系的假设成为了可能”,《帝国》和《诸众》“在最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乌托邦式的潜能和表达上的意图”。[1]6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三部曲”之《共同体》论述了一种反抗帝国统治设想的理想社会,试图破除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藩篱,以“共同体”取代西方资本主义财产共和国,把本来属于人民的财产与权力重新归还给他们,创造共享的新世界。这种愿景正是古希腊以降的“欧依蔻斯”(Oikos)传统主题在当代政治生态学的策略性回归。在此意义上,这种“共同体”构想与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自然政治之间蕴含着某种空间对话的韵味。
从历时性的维度看,“帝国”三部曲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脉络上是重要一环。在英美学术视野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可追溯到不同国别的一系列标志性著述,它们包括俄罗斯早期奠基作——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1912,英译本1936)和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1924,英译本1925);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7,英译本1972、2002)和本雅明辞世后出版的论文集《启明》(Illuminations,1968);中国毛泽东的英文版选集《论文学与艺术》(OnLiteratureandArt,1956)。此外,匈牙利卢卡奇著名的《历史小说》(1937,英译本1962)基于黑格尔对欧洲的理解,提出一种社会主义美学。布莱希特则在其论文集《布莱希特论戏剧:一种美学的发展》(1964)反对卢卡奇现实主义美学的理论方法,倡导先锋体验。其他富于意义的著述包括英国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法国阿尔都塞的《列宁与哲学》(1971)、美国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1981)、意大利葛兰西的《狱中札记》(1929-1935)和苏联巴赫金的《对话的想象:四篇论文》(1973,英译本1981)。导论性质的著述包括英国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第二版,2002)和托尼·本内特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第二版,2003)。更为翔实的著述包括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1971)、戴夫·莱恩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DaveLaing,1978)和波林·约翰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PaulineJohnson,1984)。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史著作则有佩里·安德森的《深思西方马克思主义》(1976)等,以及工具书如汤姆·博托莫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TomBottomore,第二版,1991)等。“帝国”三部曲的主要作者奈格里成名较早,曾著有《马克思超越马克思》(1979,英译本1984),它与拉克劳、墨菲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1985,第二版2001)一道,反映了后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哈特/奈格里的《帝国》(2000)“提供了一种富于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的描述”;菲利普·戈尔茨坦《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PhilipGoldstein,2005)则致力于探讨当代经济、政治和女性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5]2676-2678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甚多,不胜枚举。
基准电流源能够产生不随电源电压变化而变化的电流,即为对电源电压变化不敏感。传统的电流源结构也可以运用在亚阈值区域下的电流源设计,电路如图1所示。
从共时性的维度看,左翼政治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有着丰富甚至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帝国”三部曲具有典型意义。
《帝国》作为“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学说。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富有影响的诸众概念、对非物质劳动的阐释和对帝国作为晚近全球霸权的刻画。《帝国》描绘了后殖民、后“冷战”世界的全球化,发展了左翼政治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对新世纪的重塑”。[9]“帝国”赓续了马恩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世界性眼光,形成了与当代世界体系论如沃勒斯坦地缘政治和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全球理论的对话关系。如前所述,《帝国》标志着新世纪文艺美学理论的复兴。它刷新了当代世界文学观,丰富了文艺美学范式。
《诸众》聚焦于抵抗强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新主体,丰富了全球化与数字化背景下阶级论的内涵与外延。诸众是世界性多极集体的命名,具有真实而潜在、团结又散落的形态,被哈特和奈格里用来取代人民、工人阶级或贱民概念。在笔者看来,诸众概念一方面赓续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歌》关于全世界受压迫者团结和抵抗的话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大众立场,从而与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后现代理论形成对话关系,推进了种族、性别与时代研究;但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具有失于笼统的弱点:包括它随意摈弃民族国家主权的取向,简化和泛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复杂问题的特征。
《共同体》凸显了21世纪左翼乌托邦的政治构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的审美维度。奈格里把乌托邦分成三类:一是右翼乌托邦。它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体现为对天堂的怀旧之情和理想国的记忆。从柏拉图到卢梭,例子不胜枚举。二是左翼乌托邦。它带有强烈的未来主义色彩,将乌托邦作为超越的审美经历。从但丁到社会主义,这一直是不断出现的主题。三是潜隐的物质主义乌托邦。从拉伯雷到巴赫金,不乏例子。而今天的乌托邦以未曾预料的形式在劳动的权力中得到重生。谈论帝国,不是在思考乌托邦,而是在思考一种趋势性进程。因此,乌托邦不是一个梦,而是一种可能性。[1]32-36哈特/奈格里的“共同体”和拉图尔的“欧依蔻斯”都有审视当下、破旧立新、建构未来的审美乌托邦韵味和思想启迪意义。同样是资本主义批判的取向,大卫·哈维作为社会科学出身的文化理论家,倚重数据、统计与经验个案研究,比较务实;而哈特和奈格里像阿甘本一样,皆属于欧洲哲学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致力于法律史和政治体制比较研究,难免带上钟爱美好幻象的务虚色彩。当然,这些文化理论家采用不同的方式探讨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霸权过渡的后果,“在此过程中,他们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大陆哲学和新实用论的理论方法,同时也复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1]142“共同体”的审美政治话语,兼具左翼乌托邦的力量与偏于人文想象的弱点。
释意学派认为口译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解、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和表达,其中“脱离源语语言外壳”是口译活动的核心,也是释意理论中意义最为重大的部分,能够帮助译员摆脱原文结构的束缚,更为自然地表达原文意义。在释意理论的指导之下,译员可以采用猜测、解释、概括等策略,力求流畅准确地传达源语信息,使译文符合听众的语言习惯,有效达到交际目的。
七、结语
哈特和奈格里的当代左翼激进政治“三部曲”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良好的外延,本文涉及21世纪文艺理论复兴,资本主义批判,当代西方文论的符号学、后殖民批评思想观念更新,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诸众民主政治与赛博空间博弈,共同栖居社会——“欧依蔻斯”等问题。他们的帝国研究将现实思考与审美乌托邦的力量结合起来,体现出某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赓续,蕴含着与众多领域的空间对话关系,影响了既有的文艺美学范式,启迪人们更深入地对当代世界体系和文艺美学新形态进行反思。
参考文献:
[1] [意]奈格里.超越帝国[M].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黄晓武.帝国研究——刘禾访谈[J].国外理论动态,2003(1):26-31.
[3] [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 迈克尔·哈特,秦兰珺.概念的革命与革命的概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1):1-11.
[5] V B Leitch.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M].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 2010.
[6] Mark Bonta, John Protevi. 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 A Guide and Glossar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95.
[7] R Shields, M Vallee. Demystifying Deleuze[M]. Ottawa: Red Ouill Books Ltd, 2012: 171-172.
[8] [法]布鲁诺·拉图尔.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M].麦永雄,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9] V B Leitch.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Theory Renaissance[M].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4: 133-134.
TheInfluenceofLeft-wingPolitics'ConceptionofGlobalizationonLiteraryAesthetics:EnlightenmentfromHardtandNegri's“Empire”Trilogy
MAI Yong-xiong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4,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left-wing radical politics, the “Empire” trilogy (Empire,MultitudeandCommonwealth) co-authored by Michael Hard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tonio Negri from Italy has arous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s since the new millennium. Empire in particular is deemed as a landmark work of the revival of literary theories renaiss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Empire Study” it spawned has refreshed many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cluding those in semiotics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Multitude, focused on new subjects fighting against the empire,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cyberspace gam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Commonwealth conceives a democratic politics against imperial rule. Contemporary left-wing politics and Marxist literary aesthetics share rich and complicated ideological continuity or interact in spatial dialogues, as is typically exemplified in the “Empire” trilogy. The trilogy embodies the power of aesthetic Utopia and inspires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ystem and new forms of literary aesthetics.
Keywords: left-wing politics; Empire Study; Multitude; Commonwealth; literary aesthetics; Marxism
中图分类号:B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9)06-0097-10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9.06.008
收稿日期:2019-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8ZDA27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XWW003);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基金项目(ZD201608)
作者简介:麦永雄(1955- ),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东方丛刊》主编。研究方向:当代哲学、文艺美学与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魏琼)
标签:帝国论文; 格里论文; 政治论文; 乌托邦论文; 哈特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其他政治理论问题论文;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8ZDA27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XWW003)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基金项目(ZD201608)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