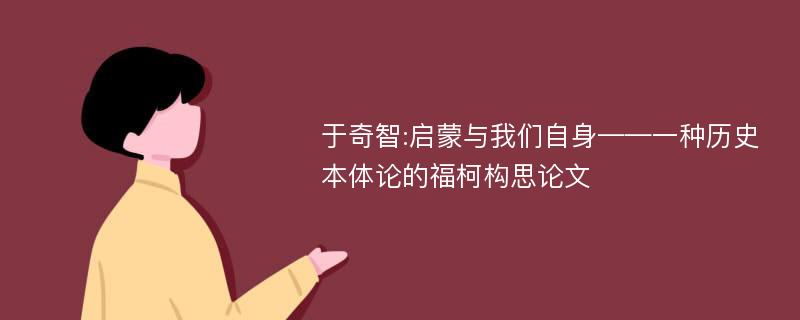
摘要:康德启蒙观无疑成为福柯晚期的重要哲学主题,也是他从现代性探索转向古希腊罗马思想讨论的一个理论契机。在康德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福柯发现了“现在本体论”并对其加以丰富发展,进而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努力建立“启蒙”与“我们自身”的内在关系。康德启蒙观具有奇特的“笛卡尔踪迹”,或者说,是笛卡尔哲学——旨在正确引导理性、寻找真理——的继续;启蒙的历史本体论明确指向“我们自身”,旨在认识其本质,“我们自身”这一概念在对启蒙的沉思中成为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批判主题;启蒙的希望就是我们自身的希望,也意味着自由、独立、理性与现实。作为三维结构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我们自身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就是其存在方式的生成过程,也是其历史本体论的构思过程。
关键词:福柯;启蒙;我们自身;历史本体论
1978年至1984年间,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持续不断地研究康德启蒙观,且总是依据康德的应征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他认为,康德这篇短文阐述了一种关于“现在”(le présent)、现实(l’actualité)或“今日”(l’aujourd’hui)的本体论(什么是今日?今日发生什么事啦?),从而他在康德启蒙观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批判本体论或思想批判史),并且认为我们可以从“启蒙问题”的角度重新评价康德及其三大批判;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柯瓦雷、巴什拉、卡瓦耶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实际上都在努力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一问题,福柯本人也致力于继续回答这个问题并自视为启蒙遗产的继承人[1]100-101。福柯建立了“启蒙”与“我们自身”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其历史本体论内涵。启蒙视域中的“我们自身”意味着处于自己启蒙、自己求知、自己运用理性、自己批判、自己治理等现实的环境中。
福柯明确将“什么是启蒙(运动)”问题看作“什么是现代哲学”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康德那里,“启蒙”作为勇敢求知、摆脱不成熟状态的运动,几乎等同于“现代哲学”,它至少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层面讲,启蒙史就是一部现代哲学史,因为福柯坚持认为,只要回答了启蒙问题就回答了现代哲学问题。而所谓“现代性”只不过是启蒙体现出来的“时代品性”或“批判态度”。康德论启蒙的短文被福柯视为“现代性纲领”,是笛卡尔哲学——旨在正确引导理性、寻找真理——的继续。
一、康德启蒙观的“笛卡尔踪迹”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这篇短文中的“笛卡尔踪迹”非常明显,特别是康德启蒙问题与笛卡尔《谈谈方法》[注]《谈谈方法》的法文完整书名为DiscoursdelaMéthodepourbienconduiresaraison,etchercherlavéritédanslessciences,即《谈谈正确引导自己的理性并在各门学问里寻找真理的方法》(英文题名为DiscourseontheMethodofRightlyConductingOne’sReasonandofSeekingTruthintheSciences),我们也可把其中pour bien conduire sa raison, et chercher la vérité dans les sciences(正确引导自己的理性并在各门学问里寻找真理)视为该书副标题。《第一哲学沉思集》详尽表达了笛卡尔形而上学体系,是《谈谈方法》进一步拓展的结晶。之间具有相似性。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正确引导理性”与“勇敢运用理性”;或者,“正确引导你自己的理性”与“勇敢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知性、悟性)”。这两个方面具有内在联系。笛卡尔的方法就是其著名的哲学论断“我思故我在”,简称“我思”(cogito),这是经得起普遍怀疑的第一确实性与真理。如果说,笛卡尔的“方法”(怀疑、沉思)把“正确引导理性”与“寻找真理”相配,那么,康德的“启蒙”将“勇敢运用理性”与“摆脱不成熟状态”结合起来。人作为存在者,总是与理性、真理、现实、成熟紧密结合。
18世纪启蒙的座右铭首先是古老的贺拉斯格言“勇敢求知”(Sapere aude),然后才是康德自己由此引申出来的祈使句:“勇敢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当然还有判断力、理性)。可见,康德巧妙地实现了双重叠合,即他与贺拉斯的叠合:“勇敢求知”与“勇敢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他与笛卡尔的叠合:“正确引导你自己的理性”与“勇敢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总之,康德通过“启蒙”将贺拉斯的“求知”、笛卡尔的“怀疑”同自己的“批判”结合起来,换而言之,“求知”“怀疑”与“批判”在“启蒙”中产生交会,从而获得“启蒙风格”,这归功于康德的创造性综合。20世纪法国的“五月风暴”的口号或座右铭是“敢想、敢说、敢干”,这是另一种启蒙(或新启蒙),难道不是18世纪融入“贺拉斯格言”与“笛卡尔方法”的“康德启蒙”在20世纪产生的回音吗?
有时她偷偷看他,他没发现还好,若刚好对上他的目光,她都窘得恨不得立刻遁地消失。他在面前,她心跳总是很快,脸也热起来。
福柯晚年系统探究了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中的“直言”(parrêsia)问题。希腊词“parrêsia”是“pan”与“rhema”的合成词,该词缀“pan”恰具“全”“总”“泛”“一切”“大全”等涵义。直言就是说出一切、自由言说,还要正确直言、勇敢直言。此外,福柯特别重视边沁于18世纪末设计的“环视监狱”(panoptique,环视的、环视,可构成动词panotiquer)的学理依据也显现出来。“panoptique”就是看出一切、自由观看、正确观看、勇敢观看、勇敢环视等意。“panoptique”在18世纪这个启蒙时代被视为“一束来自北方的光芒”“最令人担心的启蒙方案”,而福柯把它视为“人类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1983年1月5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了关于康德启蒙观的讲座,我们发现,已经发表的两篇同名文章《什么是启蒙?》脱胎于此次讲座。福柯特别强调启蒙与批判间的严密叠合,将由此展开“治理”之维:治理-统治是构成批判态度史的一种方式。启蒙就是批判(态度),也是治理,他试图将启蒙、批判与治理结合起来,建立它们之间的三功能结构。正如福柯所言:“这三者完完全全以某种方式占有一席之地,当笛卡尔论说显示和表现为真理出现与真相大白之地时,笛卡尔证明将在此发挥作用。”[2]343知道一切,思考一切,采取一切行动,说出一切,看到一切,等等,这些表明我们的行动只有在与一切打交道的漫长过程中才能逐渐获得普遍性,这确实需要决心、勇气和力量,不能懒惰、怯懦和软弱,但是,关键在于必须要求我们自身去实践。自己启蒙是启蒙首先强调的,而“勇敢求知”这个祈使句是对你(你们、我们——听话者——公众)说:它暗示自己求知、自己启蒙(针对启蒙本身而言),还要勇敢启蒙(康德语境)、正确启蒙(笛卡尔语境)。可见,启蒙强调启蒙者必须首先面对自身,要求启蒙者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追问启蒙的本质就是弄清身处启蒙中的启蒙者自身的本质,即我们自身的本质。我们自身是启蒙及其历史的亲历者,置身于时间-启蒙时代之中。这是向成熟迈出的最关键的第一步,而追问我们自身的现在与本质便是历史本体论的核心任务。
笛卡尔的“方法”与康德的“启蒙”之间达到惊人的一致性或同一性:笛卡尔方法旨在正确引导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中寻找真理;康德启蒙意味着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智,摆脱不成熟状态。福柯指出:“当笛卡尔在其《谈谈方法》的开头叙述他自己的旅程与他所做出的、他既为自己又为哲学做出的全部哲学决定时,他完全明确地适当参考某种事物,而此事物可能被视为他自身时代认识、科学、知识制度本身秩序中的历史环境。”[2]13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就一直致力于求真知、寻真理。什么是真理呢?据海德格尔解释,所谓真理是去蔽,即摆脱“遮蔽”,与康德的“摆脱不成熟状态”异曲同工。笛卡尔的“方法”与康德的“启蒙”皆在于自由,即摆脱“蔽”与“不成熟状态”,一句话,摆脱约束、自然、必然、感性世界,就是自由、人的自由、我们自身的自由。“他(指福柯——引者注)注意到,从拒绝知识权威的笛卡尔我思(cogito)到康德的‘勇敢求知(Sapere aude)’,现代哲学的特性完全是重新激活此种直言结构。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第一次架成的桥,在福柯作品里,最终能够向哲学活动的元史学规定性开放:这适合于运用勇敢而自由的言论,勇敢而自由的言论在政治游戏中不断发扬实话的差异和直率,力求打乱与改变主体的存在方式。”[2]361
对地震测量数据的分析还显示,浅水流砂体不仅表现出了强均方根振幅和明显弱相干性的地震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古峡谷水道特征。在这些已知的浅水流砂体物性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内的钻井数据,可以对潜在浅水流砂体的分布进行有效识别和预测。
这次表彰奖励的集体或者个人,有的是在落实“四个最严”“四有两责”上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有的是在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中奋发有为、走在前列,有的是在重大任务或者抗震救灾突发事件中冲锋在前、表现突出,也有的是在执法一线舍生忘死、不懈奋战。他们的先进事迹以及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是全国食品药品监管战线上干部职工攻坚克难、奋发有为的真实写照,生动诠释了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对职责的坚守、对事业的热爱和对崇高使命的不懈追求,值得充分肯定,广泛宣传。
如果说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是人的“出路”,那么,生存美学是我们自身的“未来”,因此,我们自身将成为自由的审美家或爱美者。我们最必要做的事便是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我们自身能如何生存?我们自身该如何生存?我们自身可希望如何生存?我们自身如何生存得更加美好?我们自身如何美化生存?我们自身能是谁?我们自身该是谁?我们自身可希望是谁?对它们的回答构成了福柯所谓的“生存美学”。这些问题及其回答事关我们自身的身份、界限和生存方式,值得深入探索。
二、启蒙的历史本体论指向:“我们自身”
“启蒙”作为“理性运动”和“历史事件”把我们引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认识我们自身之所是,从而建构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福柯指出:“在此意义上,批判不是先验的,不以形而上学成为可能为目的:在其目的性方面是系谱学的,在其方法上是考古学的。在此意义上,批判是考古学的而非先验的,它不会使普遍结构摆脱一切知识或者全部可能性道德行为,而是处理所有论说,论说将我们所思、所说、所做与这么多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批判也将是系谱学的,它不会根据我们是其所是的形式推断我们不能做什么或认识什么;而将从我们是其所是的偶然性中解救出不再是我们所是、做我们所做或者思我们所思的可能性。”[4]574显而易见,先验的形式本体论转向了考古学-系谱学的历史本体论,“我们自身”进入具体的批判领域,诸如牧领权力、自我技术、人口治理、治理术、生命权力、生命政治、我们自身、疯癫、医学、犯罪、惩罚、性欲等,从而开发出了另一种哲学思想领域,也显现出福柯哲学的框架。
福柯在说明系谱学解释的结构时指出:“存在着三个可能的系谱学领域。首先,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与真理相关,真理允许我们将我们自身建构为知识主体;其次,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与权力场相关,在此,我们将我们自身建构为正在影响他人的主体;最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与道德相关,道德允许我们将我们自身建构为伦理代理人。”[5]可见,福柯十分精准地勾画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的三种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的三大必要性,这三大领域表达了主体的知识、行动与道德之三维自我构成观[6],还拓展了主体(即我们自身)的自由而开放的探索领域。这表明我们自身对自由生存的追求。对此,福柯清楚地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必须回答一系列开放问题,必须确定大量调查研究,而这些调查研究如我们所愿,既是多样的,又是明确的;但是它们都涉及如下系统化问题:我们如何构成我们知识的主体?我们如何构成操控或接受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如何构成我们行动的道德主体?”[4]576这三大问题体现了知识、权力与伦理三轴心的同源叠合、三位一体。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福柯哲学的传统归属问题。在康德哲学中,批判哲学与启蒙观互相联系,但代表着两个不可互相归并的哲学传统。批判哲学旨在探求真理与认识真理的可能性条件,而启蒙观研究我们的现实和当下身份;前者是一种“真理的形式本体论”,后者是一种福柯称作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福柯明确将自己的哲学研究归属于后者,划定且多次强调上述三大领域[1]84。
叶秀山在《西方哲学史》第一卷中写道,“在福柯的哲学中,‘同一哲学’,让位于‘异的哲学’”[10]270,努力为“异”留出地盘。进一步讲,福柯围绕着“异”或“异托邦”创立了他自己的差异哲学,即知识考古学、权力系谱学、异托邦学等。可以说,当代法国哲学家要成就的“异”是西方哲学的一次大绽裂。就康德来说,福柯要展示出“我非其所是”的状态,即我不是我,我知道我不能知道的,我做了我不该做的,我希望我不能希望的[10]260;福柯哲学的否定性取向与康德哲学的肯定性向度截然不同,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图景。福柯出于康德又异于康德。
自由的生存就是美的生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美化生存(或美化生活)是人类受灾后重建文明的第二个阶段。法国著名哲学史家、古希腊研究专家让-皮埃尔·韦尔南指出:“在一篇今天已经佚失的对话《论哲学》中,亚里士多德谈到了毁灭人类的周期性灾难,描述了每次灾难后少数幸存者及其后裔为重建文明而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比如,从丢卡利翁(Deucalion)大洪水中逃生的人,首先要重新寻找基本的生存手段,其次是重新发现美化生活的各门艺术……”[7]可见,美化生存及其种种艺术对于人类来说十分重要。康德指出:“在国家公民与公共活动的关系中,在那种有必要时宁肯受损失也要首先用美化自己或自己的事物来竞争的自由问题上(如在节日、婚礼、葬仪等等直到日常交往的良好风度中),简直是不应该用禁止奢侈的法令来羁绊的。”[8]美化我们自身及其生存的艺术应当得到保障和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充分看到,无论思考、启蒙、批判,还是治理,都不能停留于自己-自我-我们自身意识层面,还必须扩展到他者,即从他人角度来理解思考、启蒙、批判、治理等,最后升华到一以贯之的圆融境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40节提出了一般理性的三条基本准则:“1.自我思维;2.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3]这三条基本准则,表达了一种传递、气度、风格与力量,自尊、宽容与通感依次展开,也适合于启蒙、批判、治理等,就是说,它们将化作具体的连锁链条。即思考自我以思考他者,启蒙自我以启蒙他者,批判自我以批判他者,治理自我以治理他者。这三组链条构成行动有序性的双重指向,一切行动皆如此。自我与他者进而获得共同且一致的思考、启蒙、批判、治理等的能力。这便是人类的共通感或共同精神。
“我们自身”置于各种因素交织重叠的“现在”。从人类史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就是从过去史到现在史,亦即从无限史到有限史或从远史到近史。我们必须放弃笼统的人类史、过去史、无限史、远史,才能实现这种变迁。“现在”代表一个特定时代(如柏拉图),它可以在自身中分辨正在来临的事件迹象(如奥古斯丁),它可以是朝向未来新世界的过渡时机(如维柯)。而康德关于启蒙的提问方式与此不同,因为他在寻找差异:比如造成现在与过去之间、今日与昨日之间的差异。康德以几乎完全否定的方式把启蒙界定为“一个出口(Ausgang),一个‘通道’(sortie),一个‘出路’(issue)……在关于启蒙的文本中,问题与纯粹现实性相关。”[4]564这种界定无疑强调了人类的出离方式或浮现形式(向外求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9](我们可称之为“出家成人”“脱颖而出者”),“纯粹现实性”则是一个特定而鲜活的时代特征或事件(时事),处于紧迫的对待-处理-治理之中,意味着当务之急。对此,我们必须批判地对待-处理-治理,因为我们自身切切实实处于此种现实性之中。
本文之所以说吉林销售非油增收“秘笈”不“秘”,一方面是告诉大家,只要在供应体系、服务体系和店面体验等方面做足功课,非油增收就没有秘密可言,谁都能够做到。另一方面,吉林销售把自己增收的经验毫不保留地通过公开媒体传授给了大家,实现了非油增收共享,没有作为独家秘方不外传。在此,也祝吉林销售的非油经营工作更上一层楼!
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思形式,哲学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新闻学,反思的正是身处其中的我们自身的时代即“现在”或“今日”,而“现在”代表一个特定时代,而“我们自身”则是处于“现在”的一个特定主体或特定客体。于是,特定的分析和陈述成为可能,哲学表达总是具有当前性或时代性,保持与时俱进的风格。哲学反思总是当代的、当下的、现在的、活生生的,或如常言道,所谓哲学就是时代精神的反思或镜像。福柯借启蒙反思现代性或异托邦,把哲学扩展到异乡-异邦-异域,从而表明,哲学不仅思考“同”,而且思考“异”,不仅反观“哲学自身”,而且吸纳“非哲学”。这意味着哲学是一种对内反省与向外求援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启蒙”成为福柯晚年最重要的讨论主题之一,它必须勇敢面对人自身造成的不成熟状态,而人要在不断反思这些具体的种种不成熟的漫长过程中走向成熟,成为真正有理性的存在者。
当启蒙成为自指事件时,我们认为,启蒙本身可以成为座右铭:启蒙吧!或者,勇敢启蒙!启蒙意味着“勇敢求知”,“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智”。实际上,“启蒙”首先至少成为福柯自己的座右铭,因为他把康德这篇短文视为“哲学谜语”,将其作为自己的“徽章”或“护符”,他是戴着“康德徽章”的哲人。福柯指出:“他(康德——引者注)使用‘Wahlspruch’一词来指座右铭,即徽章之意。Wahlspruch其实就是准则、训示、下达的命令、对他者对自我的命令,但这也是……通过Wahlspruch达到自身同一且使你们区别于他者的某种东西。因此,作为训示的准则的运用既是命令又是特色。当康德将启蒙作为‘人脱离其不成熟状态’谈论时,这一切,你们知道,都使他所理解的东西变得不很容易,也不清楚。”[2]27-28
启蒙就是一种方法,作为“理论”的“启蒙”变成作为“方法”的“启蒙”,即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智、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方法。这便是“启蒙理论”化作“启蒙方法”。启蒙就是摆脱、脱身之法,摆脱就是方法。方法也是一种启蒙,即正确引导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中寻找真理的启蒙。寻找真理就是消除谬误,摆脱不成熟状态就是走向成熟状态,就是袪除迷信。
福柯在康德哲学基础上力图建立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将“哲学品性”——“关于我们自身的永恒批判”[4]572置于我们所说、所想、所为的批判之中。福柯通过对康德启蒙观的解读划定了他与康德之间的界线:“此种哲学品性可以表现为极限态度(attitude limite)。关键不在于排斥行为。我们应该避免内外抉择,必须置身于边界。批判的确是对极限的分析和反思。但是,如果康德问题是探明知识应该放弃僭越何种极限,那么,我认为,批判问题今日应该转向肯定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给我们提供了诸如普遍、必然、强制的东西,什么是特殊、偶然、因专断强制而造成的东西。总之,关键在于将在必然限制形式上从事的批判转化为可能跨越形式上的实践批判。”[4]574可见,批判展现了必然限制与可能跨越之间的张力。这有助于我们从新的侧面认识我们自身,理解我们自身具有生病、发疯、寻死、违法、犯忌、越位等实情,发现我们自身渴望自由的天性与新的自由方向。“福柯把哲学的注意力正是集中在那‘事物’的‘实际’方面,并且不像康德那样从‘先天性’角度阐述事物之‘理论-现象’方面。而是从‘事物’‘实际’方面揭示这些‘现象’如何‘理论化’,而成为‘界限’。”[10]242总之,这意味着福柯从哲学上开化并彰显了反常事件的实证形态,即事物的另类实际状况。因此,西方哲学出现了一道新的思想地平线或者人类-我们自身的新希望。
三、启蒙与我们自身的自由
启蒙的希望就是我们自身的希望。启蒙意味着我们自身的自由、独立、理性与现实,可以说,它们构成启蒙的核心要件,一句话,启蒙旨在摆脱成见,而最大的成见便是迷信。叶秀山的《启蒙与自由》[注]《启蒙与自由》于201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叶秀山专论康德的一部文集,分为“康德哲学专论”与“哲学史上的康德”两部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康德哲学的独特角度。我们认为,叶秀山建构了“启蒙”“自由”“批判”之间的功能结构,给予“启蒙”以“自由”与“批判”的双重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站在“自由”与“批判”的双轨上审视“启蒙”,同样,我们也完全可以在“启蒙”与“批判”的双重含义上厘清“自由”,在“启蒙”与“自由”的双重含义上解释“批判”。这是一个内在的稳态结构。无论“启蒙”“自由”,还是“批判”,都是西方哲学中非常重要而复杂的主题,它们彼此结合叠加而生成观念或知识的统一。“我们自身”一直在与“它们”及其统一体打交道。
其中,令:fR:U→F(V),u1→fR(Ui)=(ri1,ri2,…rim)∈F(V),rij=R(Ui,Uj),i=1,2,…,n,j=1,2,…m,则fR就是U到V的模糊影射。
我们应当重视“启蒙本身”的探索,因为启蒙本身也是启蒙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便是启蒙的自指事件,或者是关于启蒙的命名问题。为“启蒙”命名,探索启蒙的“本质”,意味着启蒙回到自身,启蒙因而获得反观性、反身性与彻底性。当我们运用“启蒙”分析“启蒙”时,便产生了启蒙的自我指涉,启蒙便上升为一种方法。于是,被分析的“启蒙”成为对象启蒙,而用于分析启蒙的“启蒙”便是“元启蒙”或“纯粹启蒙”。福柯指出:“对于一般的18世纪、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称作启蒙的研究而言,一个有趣的轴心是启蒙本身被称为启蒙这一事实……启蒙是一个时代,即一个自指的时代,一个自身提出其自身座右铭、箴言的时代……启蒙在制度内部善于重新认识自身的历史环境。启蒙,是名词,是箴言,是座右铭。这恰恰是我们将在《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个文本里所看到的东西。”[2]15-16
我们自身只有认真对待、把握与享受“现在”,才能摆脱对过去的过多回忆和对未来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正是我们自身面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应有的启蒙态度。在此意义上,启蒙与批判作为人类日新月异的大事业,完全一致并且持续发展。福柯认为,我们完全有必要把启蒙问题与三大批判结合起来加以思考。“它(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引者注)确实把‘启蒙’描述为人类使用自己的理性而不屈从任何权威的那个时刻;然而,准确地说,‘批判’正是在这一时刻才是最必需的,既然‘批判’的作用是确定合法运用理性的种种条件,以决定我能知道的、该去做的和可希望的东西。”[4]567在这里,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出了启蒙理性与批判哲学所提出的三大问题(形而上学、伦理学、宗教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批判哲学就是启蒙理性的表达,而启蒙时代就是批判或理性的时代。可见,同人类学与三大批判间的内在关系一样,启蒙理性与批判理性归向人类理性,实现了有机连接,以求完整统一性,尽管难乎其难。我们可以通过启蒙观或人类学来理解与重构三大批判。换而言之,批判哲学、人类学与启蒙观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实现了较完美的综合,达成了基本的一致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等同。
为了自由、希望、幸福的生活,勇敢启蒙,勇敢求知,勇敢运用“我们自身”的理智-知性-悟性。启蒙就是要我们自身摆脱不成熟状态:错误、病态、迷信、无知、盲从、困惑、老习惯、旧传统、旧世界等。形形色色的不成熟状态完全是我们自身的懒惰与怯懦所造成的恶果。因此,我们要想得到真正启蒙并走向成熟,就必须自己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我们自身要像笛卡尔那样从干扰、顾虑、造成偏见的书本中解放出来,像门德尔松、康德那样从不成熟、迷信中解放出来,以审视自身的“过去”。启蒙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它要把我们自身从不成熟状态中拯救出来以走向成熟状态或理性状态。这是全新的事业,当然也是陌生的事业。“成熟状态”处于“不成熟状态”之外,走出“不成熟状态”无疑是一种超越-跨界-脱离。“不成熟状态”是我们长久熟悉且习惯的生存空间,也是我们不会轻易从中走出来去迎接一个陌生而毫无把握的异托邦或新世界。然而,启蒙的目的恰恰在于令我们自身搬迁-移居到异托邦,即不成熟状态之“外”:成熟状态、理性状态。作为三维结构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我们自身处于不断成熟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就是其存在方式的生成过程,也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的构思过程。
在贺拉斯名言“勇敢求知”的意义上讲,对于笛卡尔来说,是正确求知,就是正确引导你自己的理性;对于康德来说,是勇敢求知,就是勇敢运用你自己的理性。我们可以为笛卡尔方法给出启蒙视角,为康德启蒙给出方法视角。启蒙成为一种思想方法,我们便获得一种可贵的启蒙式思想,并用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甚或理解哲学本身的历程。这表明贺拉斯、笛卡尔与康德的思想理路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在很大程度上讲,当代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等正是在类似启蒙的启示下摆脱传统哲学(即以“同”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哲学),勇敢走向崭新的哲学世界,创建了丰富多彩的关于“异”的哲学,诸如他者哲学、异托邦学、解构哲学、差异哲学等,从而将法国哲学带往新的“精神王国”,也为世界哲学注入了新元素。总之,通过众多法国哲学家的努力,另一种哲学诞生了。也许,我们可以在“康德启蒙”意义上理解列维纳斯努力要揭示的“异于存在”“不同于存在”“胜于存在”“存在之外”或者“超过本质”“远于本质”“超出本质”“在本质彼岸”“过本质之线”“本质之外”。总之,其实就是摆脱“存在”状态与“本质”状态(此处的“存在”“本质”相当于康德所谓“不成熟状态”),以寻求更原始更可靠的“基础”-“基石”。这是当代法国哲学家试图越过传统哲学划定的“警界线”,在哲学中僭越哲学、违抗哲学;哲学有超越自身的自由,有寻求更远更根本的基础的自由;违抗“禁令”,进入“禁区”,到比存在与本质更远的“地方”去,也就是摆脱同-同的哲学(存在的哲学、本质的哲学),到异-异的哲学中去。如同启蒙作为脱离运动一样,异也是脱离运动,摆脱“同”;哲学要脱离“同”,趋于“异”,在哲学中摆脱哲学;哲学探究的真义就是僭越试验,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远方”。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将管理层能力、技术创新以及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外部治理因素纳入统一研究框架,试图进一步探究管理层能力影响微观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机理;(2)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对比分析治理因素可能存在的影响差异,为明晰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企改革着力点、从管理层能力视角提升企业研发意愿提供理论支持和针对性建议。
批判与启蒙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互相指涉。福柯指出:“批判是不被如此治理的艺术。”[11]可以说,这是关于批判定义的福柯式表达。这是理性的必然诉求,是勇敢运用理性的实际表现。我们自身要勇敢对不符合“理性”的权威说“不”,不盲从权威,摆脱奴役、苛政、残暴等“不成熟状态”。敢于如此说“不”既体现了批判精神,又体现了启蒙抱负,因为批判与启蒙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启蒙时代就是批判时代,也是成熟时代、理性时代,亦是治理时代。在此,我们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同一关系。联系康德启蒙短文,叶秀山说:“康德的‘批判哲学’所针对的也正是‘理性’之‘不成熟’的阶段。‘理性’或者超出‘经验知识’的范围,潜入‘超越’领域,企图在这个领域,也建立一个像在经验领域中那样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或者在‘超越’的‘实践领域’,以‘经验的幸福’代替‘意志自由’。凡此种种,在康德看来,或许都是‘理性’‘不成熟’、‘启蒙’不够的表现。”[10]267
木棉花来源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和东方黎族自治县。采摘新鲜的木棉花,洗净、晾干、置70 ℃通风干燥箱干燥至恒重,粉碎、过200目筛,得褐色干粉备用,10 g新鲜木棉花可制成1 g木棉花干粉,以木棉花干粉作为受试样品进行配制。
依叶秀山看来,“勇敢求知”在于理性、自由与智慧,启蒙也在于理性、自由与智慧。这意味着理性的启蒙只听从理性的律令,也只听从自由的、智慧的律令,那些外在于理性、自由、智慧的所谓“律令”,实际上只不过是具有暴力性的权威,我们自身完全可以不予理会、不用服从。这意味着我们自身有不服从暴力性权威的权利,对僭越理性的权威说“不”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求知、启蒙、理性、自由、智慧具有一致性、协调性、同一性。“勇敢求知”成为“理性启蒙”的箴言,惟有理解与把握这一箴言才能理性地启蒙、自由地启蒙、智慧地启蒙。这便是启蒙的尺度。启蒙、理性、自由有度,批判与治理亦然,一切皆有度。度本身是人的尺度,也是我们自身的尺度。由此可见,启蒙、理性、自由与批判形成相似关系,构成连续系列。叶秀山指出:“‘批判’为‘理性’‘厘定’职能范围。”[10]268“由‘诸自由者’组成的‘社会’,乃是一种‘自由组合’,‘自由的博弈(游戏)’。”[10]271“诸自由者”组成的社会就是自由者联盟,即自由者的“共同体”。所谓诸自由者就是我、你、他,而诸自由者之间构成什么关系呢?这难道不是列维纳斯致力于以“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来回答的问题吗?
诸自由者“我-你-他”结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我们自身”始终置身其中而难以摆脱出来,不成熟状态成为事实,而成熟状态终归是我们自身一直向往并努力接近的理想境界。这意味着启蒙是一场旷日持久、扣人心弦的脱离运动,促使我们自身不断推进、不断尝试。启蒙暗含着不成熟与成熟、或者约束与摆脱这两个极端,终结与出路总是同时存在。而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所用“Ausgang”一词本就具有结束、终结、出口、出路、开端、浮现等意,可见,使用该词便意味着启蒙两端的可能性叠合,或者说,对立的东西既分又合,进与出同时进行,几无时差。很可能,康德借此布下了启蒙的玄机,即不成熟的终结与成熟的出路、逃离与抓住之间的玄机。这玄机大概就是福柯所谓的“哲学谜语”,也是徽章或护符的两面。我们发现,起点与终点总是像齿轮般紧紧咬合着,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构思也许正是在这种紧紧咬合中得以建立。
四、余 论
对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也许会存在着一个可能的批评:所谓“我们自身”难道不属于“人自身”吗?这样的批评也许不无道理。可是,我们应当看到,如果我们自身仍然是人自身,便不再是传统主体哲学意义上的人自身,而是新人,即福柯的考古学人(拥有生命、劳动、语言等经验)或后来的系谱学人(具有犯罪、性欲、微观权力等经验);传统的“人自身”的神秘性与难解性已经造成了自康德哲学以来的巨大困惑;为了解除哲学的人类学重负,福柯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以反思我们曾经对于“人自身”概念的建构并解决由此而造成的难题,因为我们只有在语言层面以第一人称代词“我们自身”即内化自身或第一人称化自身方式表达用于第三人称的自反人称代词“自身”,才能催生出真正属于我们的第一人称自我意识(这里的“我们”不同于笛卡尔的“我”,历史问题——“我们是谁?”也异于非历史问题——“我是谁?”),表达自我的当前性主体地位——正在认识、行动、希望、言说、思考的第一人称主体,因为与“我们”具有远相关的第三人称自身(即外化自身或他化自身)只有获得第一人称性才能与“我们”达成近相关。这种近相关性表明哲学必须思考我们自身及其所处时代的事件,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正确处理今日事件,学习面向“未来”,以历史本体论的眼光审视、批判、反思我们自身的“现在”与“本质”。
正如福柯所言:“在这场自真正的笛卡尔所思的第一人称说明……以来的伟大运动中,你们在此拥有古代世界中哲学直言作用之所是的大重振……康德创作的启蒙文本,对哲学来说,经由启蒙批判,正是在此方面是某种意识到问题的方式,而这些问题,从传统上讲,曾经是古代的直言问题,将如此重新出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并已经意识到启蒙,尤其是康德这个文本中的问题本身。”[2]322古代直言、近代怀疑与现代启蒙遥相呼应、圆融贯通、大象无形。
不过,我们得充分注意康德同代人反对他的声音。连意大利人也惊呼起来:“Anch’io sono tutore(我也是一位监护人)!”[12]151,156即是说,我也是一位代理人或者一位保护人!约翰·格奥尔格·哈曼考察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之后,反对并讽刺道:“宁愿要不成熟的天真,也不愿做监视者唯唯诺诺的或者被收买的仆人[Maul-noch Lohndiener]。但愿如此!”“理性和自由的公共使用只不过是一块餐后甜点,而且还是一块奢侈的甜点。而理性的私人使用则是我们为了理性的公共使用而应该放弃的每日面包。”[12]151难道这不是启蒙给人类甚或我们自身带来的新困惑——摆脱或放弃私人(自我、不成熟)而走向或容纳公共(他者、成熟)吗?难道不是我们自身的“另一种现在”“另一个向度”“另一类生活”“另一大世界”吗?
台湾地区跨文化交际(传播)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是跨文化传播理论是否要“本土化”的理论争鸣。陈国明和汪琪可谓是这一分歧的典型代表,前者明确提倡要建设“中华特色”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后者认为不应该提倡任何地方色彩太浓的理论,应着力建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
参考文献:
[1] FOUCAULT M.Qu’est-ce que la critique ?suivi de La culture de soi[M]. Paris :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2015.
[2] FOUCAULT M.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82-1983[M]. éd. GROS F.Paris:Gallimard/Le Seuil ("Hautes Etudes"), 2008.
[3]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6.
[4] FOUCAULT M.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G]//Dits et écrits (1980-1988). t. IV. Paris : Gallimard, 1994.
[5] FOUCAULT M.A propos de la généalogie de l’éthique: un aperçu du travail en cours[G]// Dits et écrits (1980-1988). t. IV. Paris: Gallimard, 1994:618.
[6] HAN B. Foucault’s critical project : between the transcendantal and the historical[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7-37.
[7] 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M].秦海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57.
[8] 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57.
[9]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2.
[10] 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1] FOUCAULT M. Qu’est-ce que la critique ?[J].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80e Année, №2. Paris : Armand Colin, 1990:35-63.
[12] 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M].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DOI:10.13718/j.cnki.xdsk.2019.03.003
收稿日期:2018-05-16
作者简介:于奇智,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法国哲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9)03-0025-08
责任编辑 高阿蕊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标签:康德论文; 哲学论文; 笛卡尔论文; 本体论论文; 理性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法国哲学论文;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 法国哲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