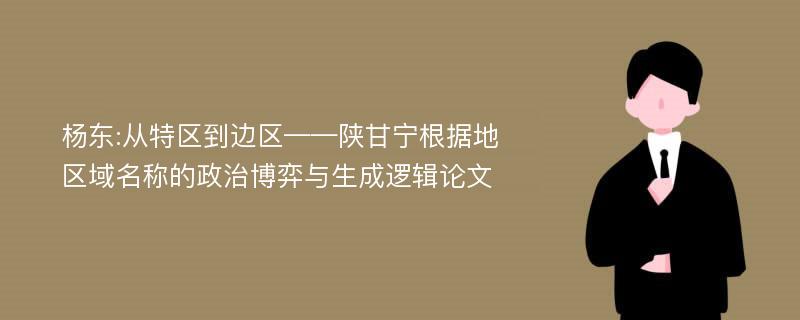
内容提要“特区”与“边区”虽是抗战之前即已存在的区域之称,而“陕甘宁边区”无疑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一种特殊政治行政存在,不过其区域名称则在“特区”与“边区”之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更名互替。个中情由既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博弈,也有中共自身的多重考量,与中共对政治体制的认知也有关系。随着根据地区域范围的不断壮大,陕甘宁边区的名实之争又成为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政治博弈的焦点之争。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生成,自当是中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必然,但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却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中外人士络绎不绝,争相进入陕甘宁边区实地考察之后形成的大量记述,不仅大大拓展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影响,为其继续存在和发展赢得了广阔的舆论空间,同时也为中共的发展壮大赢得了难得的政治空间。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 抗日根据地 国共合作 政治博弈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这个决议时就指出,“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奇事”,这些“小块红色政权之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注]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73页。毛泽东的论述尽人皆知,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革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红色政权的区域称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却各有不同。
中共武装暴动初期,在数省交界区域割据时以“边界”名之,苏维埃时期称其为“苏区”,抗战时期又称之为“边区”,其中“陕甘宁边区”更是为世人所熟知。需要指出的是,陕甘宁边区虽横跨陕、甘、宁三省,但与此前的区域定位相比,它不仅体现为一种政治军事存在,更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一种政治行政存在。特定背景下的政治行政存在,不仅它的政权结构体系有其特殊性,而且它的区域称谓也经历了从“特区”到“边区”多次反复的迁衍变化。
长期以来,学界对陕甘宁边区政权结构体系的阐释颇为常见,[注]相关论著可参见黄正林:《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问题研究——以抗日民主政权和“三三制”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9期;霍雅琴:《陕甘宁边区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但是对于陕甘宁根据地区域称谓的迁衍变革却缺乏详实的寻踪梳理。爬梳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数论著只是将这种称谓变革作为一般性的名称变化加以对待,还有人认为陕甘宁根据地的“特区”与“边区”两种称谓“通用”,只是“从1937年11月10日起统一称为特区政府,边区党委也改称为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注]雷云峰编著:《陕甘宁边区史·抗战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第69页。近年来,有人提出陕甘宁根据地从“特区”到“边区”称谓的变化,体现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的政权之争”。[注]文世芳:《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的政权之争——以陕甘宁地区称谓演变为中心的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1期。这一论述表明学界已然对此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不过仍需追寻的是,中共究竟为何在“特区”与“边区”这一称谓问题上出现了曲折反复的变化,国民党与中共的政治博弈中是如何影响陕甘宁根据地的称谓变化,陕甘宁边区又体现着什么样的生成逻辑。
调查显示,不同评价主体其评分差异较大,评价内容各有侧重,并且体现了不同的关注度。为此,根据调查数据和调查收集的意见,对学生和教师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一、更名互替:陕甘宁根据地曲折反复的名称演变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在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这块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西北革命根据地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2)断路器垂直连杆润滑不足。由于垂直连杆与轴密封垫之间设计采用的是直接接触结构,断路器在长期运行过程中,滑润作用一旦消失,断路器进行分合闸操作时,就会造成垂直连杆与轴密封件之间的直接机械磨擦,影响断路器机械特性。
就在中共中央入陕后不久,“为着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使中国西北各省的苏维埃运动在更巩固的基础上更猛烈的发展起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注]魏建国主编:《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上,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9页。并对西北苏区原有的行政区划进行重新规制,设立了陕北、陕甘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红军西征后又设立“陕甘宁省”)。西北办事处由此成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以革新政治来发动全民抗战,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础,中共中央西北办事处遂着手“更名”和“改制”工作;所谓“更名”,就是将西北办事处改为直属国民政府的一个行政组织,所谓“改制”,就是将工农民主制改为不分阶级的普选的民主制,实行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更名”工作虽从1937年初即已开始,但是及至1938年1月才最终施行固定。
然而就在193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却要求,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要求将“现在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4月5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又指出,“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7、137页。与此同时,西北办事处在此期间成立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特区行政组织法起草委员会、文化建设委员会、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起草委员会等4个专门委员会,经过讨论苏区政权如何转变为特区政府的具体工作后,于5月12日颁布的政府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时,则是以《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之名颁布通过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时已然出现了以“陕甘宁边区”冠名的正式文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边区”“特区”混合使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不断推进。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当是体现中共合作抗日、团结御侮的一篇重要文献。该电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同时“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948页。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篇电文是中共较早提出“特区”这一名称的文献。2月1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在正式谈判之时提出,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苏维埃制度取消,现时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受南京国民政府或西安行营管辖,实施普选制度”。[注]《洛甫、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张冲见顾谈判甲乙两案问题的报告的意见》,《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2期。应该说将“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政府”,是中共着眼于和平、民主与抗日的实际情形,“自动把陕甘宁红色区域改称陕甘宁特区,作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行政区域。”[注]董纯才:《陕甘宁边区简史》,《党史资料》1953年第5期。2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主持筹建政府的更名改制工作。按照刘景范的说法,及至同年3月,即宣布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注]欧阳淞等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1册政治卷上,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相关资料也显示,部分机构确以“特区”冠名。如1937年3月,原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即改为“陕甘宁特区邮政管理局”;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也在这一时期改为“陕甘宁特区工会”。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指责中共“封建割据”的舆论不绝于耳,但是在1937年11月,中共依然再次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甘宁特区”。就此,仅从抗战的角度衡量显然并不能体现其中的意涵,个中情由还当从中共自身的角度加以考量。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办事处的下属机构也相继改组为边区政府的厅和局。这一正式更名既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再次合作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共实现由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在同年9月27日,中共与国民党交涉中要求解决陕甘宁根据地相关问题时,却使用的是“特区”之称。该指示要求国民党速为解决“陕甘宁特别区问题”,要“承认特区的民选制度,特区政府经人民选出可以由南京加委”,确认“特区范围”,解决“特区经费”。[注]宁夏档案局编:《抗战时期的宁夏档案史料汇编》上,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73页。11月10日,边区政府却再次发出通令,要求“陕甘宁特区政府俟后统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不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后“除将特区大会及行政组织纲要依法修改,将来提交特区大会正式通过外,特通令各级政府,自令到之日起,即行统一政府名称为要。”[注]陕西省档案馆等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0~31页。不过这样的通令维持到1938年1月,特区政府又通令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之称。自此之后,陕甘宁边区始更形固定,及至1950年1月陕甘宁边区被撤销。
自中共长征入陕以来,陕甘宁根据地先后经历了苏区、特区、行政区、边区等一系列名称之变。尤其是在“特区”与“边区”之间,更是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更形互替。如此曲折的复杂更替,既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博弈,也有中共自身的多重考量,同时也与中共内部对政治体制的不同认知有关。
汽车完全自动驾驶,车上没有驾驶员,只有使用人或乘客,因无人驾驶汽车或者叫智能网联汽车所需要的软件、算法、地图都处于不断更新中,导致复杂性状况出现,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特区还是边区: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1927-1937年的中国政局可谓此消彼长、波诡云谲。国民党历经10年的发展,及至抗战爆发时逐渐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政治象征,加快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是此时国民党的首要任务。中共则经历艰苦行军长途跋涉最终局促陕北一隅,其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和发展。而日军大举入侵又成为国共两党必须直面的现实危机。
国民党虽未从法律意义上给予边区合法之名,但是中共认为蒋介石在原则上和口头上已然认可。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就这样说道,陕甘宁边区是1936年西安事变以及1937年春夏,蒋介石“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的面亲口承认了的。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党始终没有发表认可命令,“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周恩来也认为,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认为中共抗战后就不需要边区,但是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注]《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462页。随着国民党反共摩擦逐渐加深,陕甘宁边区非但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称为“封建割据”“分裂国家”。即便如此,中共依然通过在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向国民党提出《解决时局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再次要求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但是及至抗战结束,国民党始终没有给予边区“合法之名”。
中共提出将苏维埃改变为“特区”,出于抗战的考量自不待言。在民族危机的严峻时刻,中共认为无论是苏区还是特区,究竟是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要比属于地主还是农民更为重要。对于国民党而言,实际在最初之时并未过多纠缠“特区”之称。
至少在1937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这样说道:“共党应与之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但令其严守范围。”[注]《蒋介石日记》(手抄本),1937年1月5日。在2月10日与张冲的谈判中,国民党也明确提出“将苏区改为特别区,试行社会主义”。[注]《周恩来关于顾祝同谈苏区为特区、红军改国军及蒋杨关系等给中央书记处并告彭任剑英电》,《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2期。随后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进一步确认“苏维埃制度取消,现时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受南京国民政府或西安行营管辖,实施普选制度,区内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5年,第262~263页。及至此时,国民党并未就“特区”称谓问题提出什么异议,而是更多强调对军队的改编。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就是说要将控制军队放在第一位。[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第93、265页。然而就在同时,国民党内却传出了不同的声音。陈诚就指出:“今日赤匪之要求,为目前计,故不能不虚与委蛇,但考其要求之用意,仍非出自诚心,不过假借特区名义,名正言顺,整顿充实,一俟坐大,待机反噬,亦即所谓不战而屈我。阴谋手段,原自高人一等。为中央计,当以八九年来一贯之国策为重,而以苟求一时之表面安定为轻。总之,已崩溃之封建集团,不可曲予保全。而原不够封建领袖之资格者,更无须予以扶植。尤其行之有效之国策,断不可轻易摇动。所谓西北问题,绝非不能了之事。”[注]《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下),“国史馆”,2016年,第421页。
此后蒋介石的态度逐渐强硬。从其日记中可知,自3月以来,日记中已然出现不予设置“特区”的字眼。3月6日的日记中即有“对共匪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的记载;3月1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对赤匪收抚不可迁就之条件”,中共“不能设立总部”,“不能成立特区”。[注]《蒋介石日记》(手抄本),1937年3月6日、1937年3月10日。在此情形之下,国共随后的谈判中对于陕甘宁根据地的名称再次作了调整。
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在与张冲的谈判中提出,“特区政府可改为陕甘宁行政区”,“设长制或政务委员会制,均由民选之识会推举中央政府委任”。这个被称为“三八协议”的谈判结果,应该是国共西安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结果顾祝同、贺衷寒却擅自提出了一个修改案,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分属陕、甘、宁三省的“地方行政区”,并称此为中共代表单方面提出。顾祝同、贺衷寒将陕甘宁根据地一分为三的修改案,随即遭到中共的不满和抵制,认为顾、贺所改各点是“分裂苏区”,完全不能承认,要求谈判须重新作起。3月下旬,周恩来在与蒋介石在杭州谈判时,提出“陕甘宁边区须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65、367页。同时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主制度。”4月5日,中共中央将谈判经过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说明。[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86页。这样以来,“陕甘宁边区”成为随后一段时间相对固定的区域称谓。
这个月,订单居然没有做出来。我说怎么回事?王义山让我去车间看看。我一看,机位有空了。我说,有人辞工了?王义山说,走了十来个,有从大发厂过来的,也有景花厂的老员工,这些人像水平仪里的气泡,漂浮不定,哪儿钱多往哪儿跑。大发厂的课长李霞明确表示了,大发厂老员工愿意回去的,以前的工龄照算。阿花冷静地说,这没什么奇怪的,这就是自由竞争!
从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共两党的博弈情形来看,国民党从最初认可“特区”到随后反对“特区”而以“行政区”或“边区”代之,体现的是一种“编共而不容共”的政治考量。正如蒋介石所说:“考虑大局,决定编共而不容共”是收编共党的基本方针。[注]《总统蒋公大事年谱初稿》卷四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8年,第1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蒋介石甚至要求中共放弃信仰单方面“投降”。但是中共却坚持可以服从三民主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如国民党强迫共产党单方面“投降”,则“只有战争”。共产党保持苏区原有地区,“惟名称可以改变”,[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5年,第267~268页。因为现在“不是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战斗,而是在民主共和国基础上将中国各种形式的现存政权合并起来成立全中国的统一政府,以便统一国力和加强国防。”[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5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6年,第591页。这也是国共博弈下陕甘宁根据地称谓频繁变化的重要原因。
比如,同样是1937年5月颁布通过的选举条例,政权系统以“边区”称之,而5月15日通过党的选举条例则以“特区党选举条例”称之,落款为“中共陕甘宁特区党委”。[注]《特区党选举条例》,《党的工作》1937年第35期。1937年7月17日,《党的工作》刊发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时,是以“陕甘宁特区党委”作为标题,但是信中开篇则以“边区工会”称之;同样在7月刊发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信,是以“陕甘宁特区党委”作为标题,但是文中所列材料则是《怎样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等。[注]《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信》,《党的工作》1937年第36、37期。
对于中共而言,陕甘宁边区是民主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其基本的定位。同时,中共一直强调陕甘宁边区在事实上早已存在,在原则上也是经国民党认可的属于中华民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林伯渠在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边区政府是1937年9月6日正式更名改制,归国民政府领导的一个地方政府,蒋介石在与中共代表历次谈话中“也屡次承认了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屡次答应了发布正式承认边区政府的命令”,国民党行政院“也正式确定了边区为行政院直辖的区域”,尽管中共没有接到国民政府正式责成边区政府成立的命令,“然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8页。
我觉着心里沁凉沁凉的。望着头顶的汽灯,好像在飘动,越升越高。渐渐模糊的汽灯洒下惨白的光影,如六月飞雪,满树槐花,白得晃眼。那一片铺天盖地的槐花哟,我的狼剩儿立在花下,伸出小手,接过我摘下的花串儿。花影重叠,那小人儿又变成了槐生。他提着菜篮,也立在一片白花底下,睁大了眼睛,惊骇地瞄着我。我抬了抬手,对槐生说,娘是回不去了。你将后要听父的话呵……
还在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就指出,“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2月11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指出,“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46~647、654页。1937年5月,林伯渠在谈及苏区更名改制问题时也强调,“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国是革命的前进,不是取消一切”,“苏维埃制度是最民主的。它最能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到政治生活中来,管理自己的政权,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而奋斗”,“现在苏区中的基本任务,是在于转变与创造特区”。[注]《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45页。即便全面抗战爆发,中共在内部决议中依然决定认为“将来还是要搞苏维埃的”。[注]《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40页。
如今,在几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印刷企业要想发展,其决策、运转,都要适合市场需求。沈幸华董事长结合中科印刷发展历程介绍道,“国企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原因,存在历史包袱过重,决策机制过慢,互相推卸等弊端,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发展会受到一些制约。到目前为止,北京书刊印刷企业中市属、央属、军属的企业,以印刷为主营业务的已经相对较少了。经过市场的重新洗牌后,能够真正靠印刷盈利的企业,实在难得。
中共强调使用“特区”之称,不仅在制度结构上要体现自身的优良传统,而且在运行机制上要体现自身的优势特色,更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它是民主模范的“特色之区”,也就是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把自己“在政治上获得领导影响的区域创立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政治与军事准备及动员的模范区域,成为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模范的区域。”[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4页。这样的认识不仅体现在中共的“特区”设计上,也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
2017年,宜章茶叶产量880吨,产值约13亿,上万贫困人口通过茶叶产业受益。据测算,莽山区域每亩茶园可实现年收入8000~10000元,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效果明显。
问题的关键是,国共两党虽已合作抗战,但是军事上合作政治上防范,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状态。就在中共要求改“边区”为“特区”时,蒋介石慨然曰:“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之后即强调要加强“对共党之预防”,要“控制共党,勿使捣乱”。[注]《总统蒋公大事年谱初稿》卷四上册,第1177页;《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30日、1937年12月11日。然而也就在此时,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回国强调“抗日高于一切”,认为在政权问题上,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将这个政权活动统一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样一来中共中央随即提出将“边区”改为“特区”的决定,并于1938年1月重新调整为“陕甘宁边区”之称。不过随着陕甘宁边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国共两党关于陕甘宁边区“非法”与“合法”之争再次开启,边区名实之争则成为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政治博弈的焦点之争。
三、名实之争:抗战中后期的边区定位
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时有段值得注意的对话,蒋明确告知周恩来,“共党应正式宣布取消共党之组织与活动,使名实一致;否则,如不愿取消,或不遵法令,不顾大局,一如过去行动,乃为妨碍抗战,增加敌军势力,此种责任,应由共党负之。我中央决不受人压迫,决不受人欺侮,决不长此坐视也。”[注]《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国史馆”,2011年,第666页。蒋介石提出中共组织要“名实一致”,其中就包括“陕甘宁边区”的区域名称和定位问题。
就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言之,国共走向第二次合作,是以国民党承认中共的合法性为政治基础的。需要指出的是,国民政府虽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承认中共的合法性,也在抗战初期认可陕甘宁边区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组成部分,但是国民政府从未正式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的命令。即在与中共谈判期间,从蒋介石日记中依然窥探出国民党对中共及其名实的态度。1937年5月,蒋日记就记载,对共方“区域宜严,不能使之独立”;“对共问题,如其要公开,则应取消其党名”。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加快,蒋介石虽认为“共党态度渐劣,惟有顺受之。”[注]《蒋介石日记》(手抄本),1937年5月25日、1937年5月29日、1937年8月28日。国民党随后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陕甘宁边区定位问题并没有完全达成协议,没有为之正名,但显然已无法改变陕甘宁边区业已存在这个既成事实。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升降反复,“陕甘宁边区”名实之争势所难免。
在国民党看来,中共虽然把陕甘宁苏区改为国民政府特区,可是边区的政制政策与国民政府迥然不同,除名义变更外,仍然保持苏区时代的一切,边区内部事务,国民政府也无法过问。他们“阳用边区政府之名,阴行苏维埃红军之实”,“自行扩张”搞独立,“擅组机关,自委官吏,紊乱行政系统,破坏国家统一”,“巩固割据局面”。[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5年,第503~504页。这样的边区实际是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的一个特殊区域,甚至被认为是“非法”存在的“伪边区组织”。正如有人撰文指出,从一般层面看,边区就是边僻的区域,但是所谓的“边区”,“并不是简单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是含有浓厚政治意味的一种特殊组织”,如此边区可定义为“边区是共产党的边区,是共产党自成组织、自立政制,自私自利的策源地。”[注]王思诚:《如此边区》,求是出版社,1939年,第2、6页。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据王世杰日记记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组设边区政府,不照中央法令行使政权,近日国民党党部人反对甚力。参政会前后接到反对电不下数十起。”还有人说“共党之边区政府,系国中有国。”[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39年2月19日;《王子壮日记》第5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第396页。于是有关“取消”边区的声音一时甚嚣尘上。他们认为“近代国家在一国中,绝不允许两个对立政府存在,边区政府自成体系,另有法令,另有政策,俨然一小国家,与我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破坏国家统一”;边区政府的存在“影响抗战前途”;中共割据边区“贻祸国家社会”。民国党甘肃方面也呈文中共在边区“擅组特区政府,妄颁法令”,边区各县共党“另立政权,与地方政府发生摩擦,阻碍政治推行,如不早日彻底调整,诚恐遗祸将来”。[注]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707、712页。
将陕甘宁根据地定位为“特别区”,不仅体现在称谓上,也体现在制度建构和运行机制方面。陕甘宁边区虽然是隶属于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但是“要懂得如何在旧形式中灌输新内容,旧躯壳中注入新生命”。[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无论是政府长官的任命,还是选举方式都要体现中共自身的色彩。周恩来在关于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应实行特种选举”。[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438页。在具体选举过程中,中共也明确提出要保持中共革命的优势特色,在陕甘宁边区内虽然“把苏维埃民主制改为普选的民主制,但是仍应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保持共产党对特区政权的领导,保持特区工农既得的权利,保持苏维埃民主制度的长处,而特区政府的组织原则仍应保持民主集中的制度,没有必要完全采用资产阶级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离的议会制度,并且在名称上也决定将各级议会改称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代表大会主席及政府首长统称主席,废除其历史上带有腐朽意味的议会、议员、乡长、区长、县长等名称。特区政府的组织,完全经过民主选举,不用等待外来自委任。”[注]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7页。
传统的液栅型石墨烯场效应器件,因石墨烯直接与待测液接触,使得石墨烯沟道极易被污染,致使器件的稳定性减小,也不能被重复利用。因此,顶栅型石墨烯场效应管pH传感器[19]得到了关注,它以石墨烯材料为沟道并在其表面沉积了绝缘层(如HfO2等),其结构及电学检测示意图如图4所示。
就民国时期行政区划而言,所谓“边区”或“特区”,主要是针对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环境设置的一种特殊区域制度,抑或是为处理特定区域的特定事务而实行的一种特殊制度。国民党确也在一些区域设置了不少边区和特区。但是战时的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人看来显然有悖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之区,而是与边区之名不相符的“特殊政治区域”。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因兵备之扩充、政令之不统一,对于国民党而言显然是不愿意接受的。正如何应钦所说,中共边区纯系“自由破坏地方行政系统之不法组织”,他们坚持陕甘宁边区是“特殊组织,不容中央一切政令实施于该区,体制规章,必欲独为风气”,国民党“虽不认所谓边区之法律地位,固始终为抗战大局而曲予优容,初未尝因该军之侵凌压迫,而有一兵一卒相还击”,而中共军队“则已驰突数省,军政大员被残害者,已不可数计。”[注]何应钦:《为邦百年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718页。于是自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再次就陕甘宁边区问题开启谈判。何应钦提出“关于共党一切不法行为,均有待于‘陕甘宁边区’之解决”。边区问题“照常理,应取消非法名义,回复行政常规,缩小范围”,但为迁就事实,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督察专员区”,隶属陕西省政府。但屡次商谈之结果,叶剑英均要求保持原始之名称,后又提出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暂时隶属行政院。[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5年,第76页。此后又历经多次谈判,1944年国民党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该行政区域内法令制度应呈请中央核准。[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8年,第533页。
国民党一方面从制度上取消“陕甘宁边区”的区域称谓,要求中共“服从中央,遵守法令,彻底取消一切‘特殊化’之行为与组织”,“绝对否认共党所谓‘陕甘宁边区’之组织”,只是将其“认此为地方问题,授意各该省政府恢复管辖权力”,[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1、54页。另一方面国民党又从宣传角度控制“陕甘宁边区”的传播。为此,他们专门设立《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要求将“边区”“特区”“抗日根据地”“陕北圣地”一律改为省名或地名。“如确有必须引用者,需加引号或加‘所谓’二字于其上。”[注]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战时新闻检查局,1941年,第147~149页。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压制管控《新华日报》,禁止出现“陕甘宁边区”字样。1943年4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陕甘宁边区学生电英学生联合会》之大字标题新闻,蒋介石专致国民党宣传部“以后不许有陕甘宁边区字样登载,希即切实注意为要。”针对中共对陕甘宁边区的大力宣传,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认为这是“捏造种种事实”,“欲以争取国人之赞同与拥戴”。[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一),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514、541页。国民党通过舆论管控,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降低陕甘宁边区的影响力,进而取消“陕甘宁边区”之名称。
前已述及,中共从初期提议将“苏区”改称“特区”,就自认为是一大让步。回溯到1937年2月,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这一内容时,有人甚至发言说“宣言还是不说愿意取消苏区和红军名称”。[注]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95、349页。随后与国民党的政治博弈中,陕甘宁根据地名称虽然屡有变动,但是“特”始终是中共强调的内容。及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一直强调“边区”应改称“特区”。1937年10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时依然指出,“我们须坚持各条件,决不让步,并希称特别区。”[注]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95、349页。1937年11月4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这样说,陕甘宁边区的名称须叫“特别区”,“边区”二字对外不好。11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又说,特区政府应坚持实行独立自主原则,过去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改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不好的。陕甘宁边区应称为“特别区”,即“特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页。在中共看来,边区政府虽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但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省级行政区,而是具有中共自身色彩的一个“特别区”,这个“特”,就是要集中体现中共革命的优势特色和优良传统。
陕甘宁边区在事实上早已存在,但是在名义上毕竟尚未有国民政府颁布的正式法令,因此从与国民党正式谈判之日起,争取边区政府的“合法之名”,始终是中共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还在1937年3月国共谈判初期,毛泽东等人就告知周恩来谈判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3月5日再次复电周恩来,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式的公开文件,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训令也一再强调指出:“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注]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30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8~179页。及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唯独关于边区政府的名义没有从法定意义上加以说明。其时,中共代表一再向蒋提议,“蒋诺交孔祥熙院长办理,孔亦当面承认解决。然而一拖三年,上面不否认也不承认”。[注]陕西省档案馆等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161页。及至1944年,毛泽东致电林伯渠依然强调“边区应正名为陕甘宁边区,以符实际”,“边区及敌后各地之民主设施,不能变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3页。
316张护理记录单中,出入量记录错误的护理记录单214张,错误率67.72%,说明出入量记录存在的问题确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共有508例次的错误,其中入量错误167例次,出量错误341例次,具体错误情况为:肠外营养液记录不准确128例次占76.65%,静脉注射漏计量25例次占14.97%,入量计算不准确9例次占5.39%,记录不精确5例次占2.99%,不显性失水未记141例次占41.35%,痰液量未记129例次占37.83%,渗出未记33例次占9.68%,引流漏记37例次占10.85%,呕吐未记1例次占0.29%。
有鉴于此,中共审时度势放弃此前的阶级革命而转向民族革命,愿意在抗日基础上更名改制,与国民党“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948页。于是便有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主动要求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毫无疑问,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旗帜,将其所在区域改称“特区”,从自身的革命逻辑来看的确是一次大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中共认为“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行对日抗战”。[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90页。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也指出,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的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注]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等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89~90页。
国民党之所以没有赋予陕甘宁边区“合法之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认可陕甘宁边区,实际就是认可中共“割据”的合法性。这对于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的国民党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在国民党人看来,“今日之中国,有亟待除之三害:一为军阀,一为土匪,一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未能彻底清除,致有去岁西安之变。赤色土匪假名抗日,到处宣传容共之声。日本帝国主义者,表面故示缓和,实则反较以前为深刻。凡此三者,果属有识之士,当能认识此中真正之危机。一有不当,祸不旋踵。此诚存亡兴废之一大关键也。”[注]《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下),“国史馆”,2016年,第711页。这样的认识应该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人的基本共识。当时陕北23县上书国民党的报告颇具代表性。
该报告指出,那种认为边区政府为中共既成事实,中央似不妨承认其存在的主张“实大谬不然”。中央若退让迁延,陕甘宁边区与冀察晋边区打通一片,“割据西北各省,成立大苏维埃政府,中央又将如何应付”。若论既成事实,“民国以来,岂仅中共割据陕北一隅,试问当日何者之封建局面,非既成事实,中央能一一承认之耶?” 退一步言之,“即使边区人民真正拥护中共,我中央亦不应开此恶例,听其自外生成。边区人民不过数十万,坐视其成立政府,全国人口五万万,将不知成立若干政府矣。”抗战为革命工作,“抗战胜利之唯一保证为统一”,在抗战过程中,“必将军事、政治等之不统一者,调整而统一之”,“盖必统一始可保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一国军队受统帅统一指挥,一国人民受政府统一管辖,为天经地义之真理。”同时,“中央政府制止一切非法政府之存在,非只为巩固统一,争取抗战胜利,应使全世界国家知中国只一个政府,使全中国四万万同胞集中意志拥护一个政府,使边区人民知应受一个政府领导。认识边区政府为非法政府。如不加以制止,无异默许其存在。承认中国可以有两个不同之政府,则边区人民无从认识中央政府,势必至国民思想分歧错杂,力量难以集中,且混淆国际观听,影响抗战前途,诚非浅鲜。”[注]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709~710页。
国民党人对此问题的认识,在中共看来显然站不住脚。中共认为,国民党给予陕甘宁边区“合法之名”,“不仅示全国人以榜样,给各地方以模范,并可以杜绝日寇、汉奸、投降挑拨者诬蔑边区赤化之借口,给全世界民主国家友邦人士以边区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之证明”。至于有人认为“承认边区即是表示分裂中国疆土,承认封建割据”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因为“省区的划分,原是历朝所常有的事”,即在国民党主政以后,“也曾划三特别区及宁青两地为省,划鄂豫皖、湘鄂赣为边区。今兹划区,正有前例可援,盖与分裂中国疆土,丝毫无涉。若之封建割据,则边区所实行者为民权政治,决非封建制度,何能称为割据?”[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2页。而且,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存在是有根据的。尽管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其他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地区有着很大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拿三民主义的尺度来测量我们的边区,那我们就应该大胆的说,我们的特点,即在认真的实现了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战建国的背景下,“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政府,当然是最合法的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难道今天除了依据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与抗战建国纲领的标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测量合法的标准吗?”一言以蔽之,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产生与根据,就在于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与坚决执行者,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彻底实行者,国民政府的组成部分,保卫河防,保卫西北,坚持持久抗战的堡垒”。[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8页。
中共一方面强调陕甘宁边区存在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认为不管“国民党承认与否,也不必急于要求承认”,首先是加强边区各项建设,使其“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以影响全国。同中央政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77页。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国民党高调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中共又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方案,要求共产党员在抗日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主要是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03页。中共设计这样的政权结构模式,一方面是回应国民党一党专政、排斥异己以及“限制异党活动”的种种错误政策,使其在政治上孤立,另一方面则是表明其“愿与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力针,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行为的一贯态度;表明边区人民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卷),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第351页。
《中学数学教学大纲》和《中学数学课程标准》对学生的运算能力、逻辑思维、空间想象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都提出了要求。如何培养中学生数学中的运算能力、逻辑思维、空间想象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呢?我结合新课程改革谈一谈,愿与大家共勉。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陕甘宁边区,中共提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加大对外宣力度,以扩大边区的影响。此次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在自己的报纸和杂志上说明了边区的政治制度”,强调说明“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或惊人的地方。在这个地区正在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18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另一方面邀请中外人士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据统计,仅1938年至1941年四年间,延安交际处就接待中外来客7000多人。[注]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263页。特别是1944年中外记者赴延安考察,更是大大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在国统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外国记者对解放区的友好访问及其报道,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1944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467页。但实际上,“堵门”政策已经不奏效了,随着陕甘宁边区的日益巩固和扩大,“堵门”政策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四、陕甘宁边区:一个革命区域的生成逻辑
回溯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土地革命初期是以“边界”作为革命根据地之称,这些“边界”之区都建立于数省交界的地方,在划省分治的情势下,中共得以生存发展。伴随着中共革命的日益发展,渐次出现了“边区”“特区”之称。如“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川陕边区”“新遂边陲特别区政府”等即是如此。但此时的“边区”之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军事存在”,而且在当时不可能得到国民党的认可。而中共中央长征落脚陕北最终形成的陕甘宁边区,却有其特殊的生成逻辑。
陕甘宁边区地处陕北、甘肃陇东、宁夏东南,从地域位置来看虽可称其为陕甘宁边区,但作为中共中央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陕甘宁边区显然并不只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也就是说,它并不仅仅是此前“几个省接连的边缘地带”,而是有着特定标志的政治行政概念。作为在土地革命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长征的“落脚点”,它的存在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如果不能生存,其他都无从谈起。因为此前刚刚经历过的长征,已经让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红军饱尝了没有根据地的煎熬。故而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中共的基本诉求就是要保证陕甘宁边区在行政区划上的完整性,保持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政策方面的独立性,这是中共的诉求和底线。换言之,陕甘宁边区的存在首先是中共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这个边区,“党中央将无处安身”,如果让党中央在八路军驻扎的地区,“就不能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党中央不在固定的地方,就不能对整个中国的生活发挥影响。最主要的是,如果党中央位于敌后,那就不能对全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施加影响。过去的经验已经教育了我们。位于中央苏区的党中央,不得不放弃一系列工作。”[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18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
当然陕甘宁边区的存在也是中共发展的条件和保障。中共为了实现巩固和发展的目的,主动放弃了此前的苏维埃制度,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中共“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但是让步的限度是“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中共一再强调将陕甘宁根据地作为一个特区,并将其作为一个政治存在,就在于强调它的政治影响。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讨论会上,毛泽民就指出,陕甘宁边区“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它向全中国展现出巨大的政治前景”,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区的青年,“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人是怎样工作的”。边区“在实现民主化方面也做出了榜样”,参观过边区的很多人“都承认我们这里的工作安排得很好,有些方面他们视为榜样”,对于那些过去说我们是土匪,只会搞破坏的人,“现在他们在实践中和在生活中确信,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任弼时也在讨论会上指出,陕甘宁边区有党中央委员会,一系列党的机关、学校、军事学院、文化机构,此外,边区还起着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各省的代表来这里参观络绎不绝,“这个边区在政治上对全国的生活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没有边区,“那我们就没有地方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特别是党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干部。”[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18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26、168、170页。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生存、发展和积极实施抗战的保障,也是中共建立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实验区。特别是随着边区面积的不断扩展,以及中共在此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使得原本就认为国共合作“决非联俄容共,因共党既愿投诚改编”[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5页。的国民党而言,已然将其定位一个不受中央控制的“割据政府”。在国民党看来,所谓“边区”就是一个偏僻区域,陕甘宁边区的存在原本也只是八路军抗战的“募补区”,然而中共却在此自成组织、自立政制,“既非抗日军事政治发号司令的中心所在,也非兵源粮秣接济补充的来源,怎样说得上是抗日的根据地?只能说是共产党人长征之后的流亡聚集地。”[注]王思诚:《如此边区》,求是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6页。甚或有人说,陕甘宁边区“其存在等于割据”,“‘边区政府’此一不详名称之出现,实为中国政治上一大污点。”[注]李一删:《中共割据下之政治》,光明出版社,1943年,第1页。于是取消边区的“特殊化”,反对所谓“封建割据”,对边区包围封锁,成为国民党的基本政策。
然而实际事实并没有朝向国民党既定的目标,反而越是挞伐封锁,越使得陕甘宁边区成为一个极其神秘的区域。诚如毛泽东所说,陕甘宁边区“因未得明令公布,地方官吏常施行无理由之封锁,又禁止外人参观,至使中外人士常惶惑不解。誉之者故神其说,毁之者故甚其词,反致真假难言,是非颠倒,称为西北之谜,此与国家之统一,中外之观听,反而有碍,诚为贵党所不取。”[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2页。结果一方面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涌向边区,另一方面中外记者和一些观察家也源源不断地去探寻这块神秘区域。特别是1944年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团到访陕甘宁边区,更是成为“改变外界关于中共问题的舆论开辟新阶段”。[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这些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团到访期间“常以共产党中国,与国民党中国为对比”,经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救中国,非共产党力量不可。纵对共产主义曾有非议,而对共产党之所作所为,钦佩至极。”[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排印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第220页。即便是一些随行的国民党人,也由于“他们对中国的爱国主义忠诚使他们倾向于承认延安所取得的许多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使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对我们在延安共同看到的一些人和做法,羞怯地,有时用传统的中国礼貌用语表示出明确的民族自豪感。”[注][美]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马飞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88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生成,又何尝不是在中外人士的实地考察之后为其正名的呢!正是由于他们在国共对比的转换中,才形成了“对国民党有颇多批评”而“对共产党则颇多同情”这样的印象。
对于八达岭老虎致害案件,我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角度来对于动物园在此案件中的责任判定问题进行论述。
实际上从这时开始,中共要考虑的显然不是单纯的寻求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而是转向考虑和谋划更为长远的未来。据唐纵日记称,此时的“共产党日见猖狂,不但要求政府承认其私自扩充之部队,近且公然呼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而各党派亦和而应之,以致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注]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62页。曾几何时,“取消边区”还是国共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谈判焦点,但是历史的发展显然超出了国民党的预料。民主人士黄炎培考察陕甘宁边区时认为中共有三弱点——一是物资乏,二是人口少,三是主义不合国情——而“中共之存在与成长,乃国民党不争气使然,今后全看谁得国人信仰,谁得友邦援助,谁生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8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317页。实际上,历史最终走向已然为黄炎培的预判作了结论和注脚。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3-0108-11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01-1949)”(17ZDA198);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课领航学者项目(SZK20170102)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标签:陕甘宁边区论文; 边区论文; 中共论文; 国民党论文; 苏维埃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人文杂志》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01-1949)”(17ZDA198)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课领航学者项目(SZK20170102)论文;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