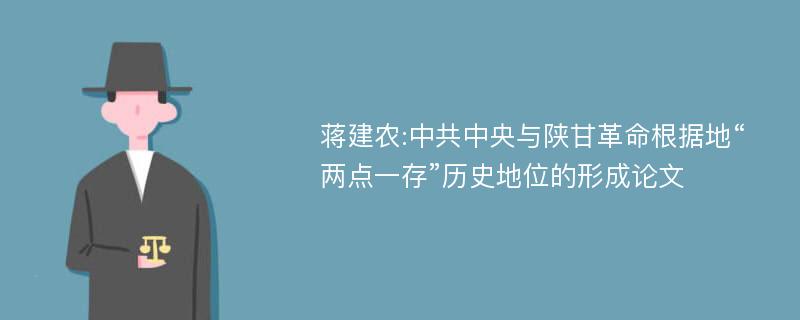
提要:在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转折的历史过程中,作为“硕果仅存”的陕甘苏区,成为南方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走上抗日前线的出发点。这一重要历史地位的形成,首先是陕甘人民长期英勇奋斗的结果;同时,中共中央的领导和中共中央长征到陕甘后的各项举措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讲: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指导开辟了陕甘苏区;陕甘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出独特的斗争经验是其能够“硕果仅存”的内在依据。中共中央根据中国革命中心由南向北转移的历史变迁和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作出奠基陕甘的决策;陕甘苏区的巍然屹立与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为实现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客观可能。陕甘苏区为万里跋涉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栖息地;中共中央贯彻遵义会议以来的正确路线解救了陕甘苏区的危机。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军民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使之成为中国革命长期稳固的大本营,特别是从陕甘苏区生存状态的实际出发,提出并成功实施了以西北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从而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新高潮的伟大历史转折。
关键词:中共中央;陕甘革命根据地;落脚点;出发点;硕果仅存;主导作用
本文所谈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指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其下限到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该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上和学术界,有时以“陕北”为其泛称,也有的称其为“西北根据地”,我们采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称谓。[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在中国南方各路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历史转折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形成“两点一存”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往学术界对此问题已经有许多精辟的阐述,但大多是把陕甘根据地的客观存在(硕果仅存)与其成为“落脚点”与“出发点”简单地划等号,而对陕甘苏区作为“落脚点”与“出发点”的不足与缺憾,却鲜有论及;或是较多地强调陕甘苏区的党组织和军民的作用,对党中央到来之后在最终促成陕甘苏区成为“落脚点”与“出发点”的作为,则语焉不详。本文结合坊间关于究竟是“陕甘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甘”的热议,从中共中央与陕甘根据地相互关系的角度,谈谈对其独特历史地位形成过程的认识。
一、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导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
陕甘地区的中共组织自始就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创立的。早在五四时期,在北京求学的陕西籍青年魏野畴就深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他和当时在北京的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湖南青年,都租住在景山后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8号的一所院落里,时常交流时事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并和杨钟健等人一起创办《秦钟》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他于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经李大钊亲自介绍加入中共,成为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主要创始人。陕甘地区的中共组织在创建之初,就十分注重在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军(冯玉祥西北军)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众所周知,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中心是广东、湖南和湖北地区。事实上,国民军控制的陕甘地区,也是革命高涨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在武汉政府时期的后期,中共领袖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非常倚重冯玉祥的力量,一度有依靠国民军重振旗鼓,打击已经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并坚定日益右倾的武汉政府继续革命决心的设想。中共中央向国民军派去刘伯坚、宣侠父、邓小平、刘志丹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完全由中共所主持。他们在国民军中培养发展了许多中共党员,影响和团结了大批进步官兵,播下了革命火种。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指出:红军的组成、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区,必须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无疑,陕甘地区也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并深受大革命影响的地区。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刚刚结束,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就接见在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陕西省委代表李子洲,向他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对陕西的武装斗争等做了具体指示。[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177页。于是,在中国南方爆发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同一时期,陕甘地区的党组织先是于1927年11月领导发动清涧起义,继而在1928年4月发动渭华起义,以后又领导发动两当兵变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和兵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利用自己在当地深厚的地缘、血缘关系,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努力探索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途径,组织和发展了主力红军,先后开辟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2月形成统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他们在实践中摸索积累出许多独特的经验,当南方各红色根据地在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下一一丧失的情况下,陕甘苏区红旗不倒,成为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这些经验主要是:
其一,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始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陕甘根据地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和中央苏区,在地域上相隔遥远,与中央的联系比南方各苏区更为不易。在八七会议后陕甘地区发动的第一轮武装暴动高潮告一段落之后,以刘志丹为首创建的陕甘苏区和以谢子长为首创建的陕北苏区,分别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北方中央局领导。由于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一度盛行,特别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长期错误统治,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的革命斗争受到严重的干扰,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主要领导人多次受到错误指责,数经撤职、降职,其领导职务互有替代和更迭。根据地和红军也在国民党军的强力进攻下一再遭受挫折和失败。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意见与上级指示的分歧面前,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本着一致对敌的原则,一方面通过组织渠道反映自己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在上级的指示没有更改前,仍然贯彻和执行上级组织的指示,并在行动中尽可能地减轻“左”倾错误的危害,坚定维护革命大局,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其二,加强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之间的协作,自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由于与上级组织的隶属关系不一样,更是由于反动统治势力的分割,在一个时期里,陕甘边和陕北这两个根据地相对独立地平行发展。双方在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方式、方法上不尽相同,在其完全融为一体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受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干扰、危害的情况下,在一部分同志中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但两块根据地都处于少数民族和汉族发达地区中间地带,有着共同地缘和宗亲关系以及共同的生活环境;它们都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开展斗争的;这两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参与者,有着共同的奋斗理想和斗争目标,自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伊始,就是密不可分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陕北根据地的支持与帮助,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陕甘边根据地的帮助与支持。两个根据地在干部、人员方面互有交叉和补充;在发展指向和区域上,既各有侧重,又经常不谋而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双方不仅在战略上互为依托和支撑,而且在战役、战术方面的配合更是一种常态。“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肃反”主要矛头指向了陕甘边根据地的领袖和骨干,但是陕北根据地红二十七军的领导人也一同被撤职、调离,受到打击和歧视,他们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感同身受。总之,自觉地维护红军和根据地之间的团结协作是双方的共识,这种亲密无间、共同奋斗的关系,是其最终能够融为一体,共同组成陕甘根据地的根本条件。这也是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能够顺利纠正“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肃反”的重要历史条件。
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豪迈地宣布:“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他对如何看待长征的胜利做了解释,认为主要是“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并特别强调直罗镇战役“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从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解释看,作为战略大转移的长征,就必然要有一个新的目的地。能否找到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立脚点)是红军能否真正转危为安的关键,也是长征胜利与否的标志。
其四,坚持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团结社会各方面人士,扩大了根据地建设的同盟军。针对陕甘地区沟壑纵横、交通困难和社会经济生活相互隔绝的现实,以及宗亲、会党、绿林与国民党正规军、地方军林立的状况,陕甘根据地区别不同对象的不同利益诉求及其各自的政治倾向,采用“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方式,注重发动组织工农群众,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竭力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使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得以保存和发展。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初步总结了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称赞“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贺龙式”的根据地发展模式。他认为这些“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虽然当年毛泽东无从知晓“刘志丹谢子长式”斗争的具体情况,但是时隔10多年后,毛泽东曾系统地总结了这块根据地的经验,认为“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的许多好的工作作风”[注]《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陕甘革命根据地创造的斗争经验,是其当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尽失时却能够“硕果仅存”的内在依据。
而这时的陕甘根据地却因为“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的严重干扰,正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当时,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气焰正盛,之后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共的进攻,直到1936年6月,国民党军高双城部还趁红军主力西征之机,突袭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匆忙撤离瓦窑堡,被迫进驻保安。可见陕甘根据地的外部生存环境之恶劣、艰险。更为严重是在根据地内仍在顽固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书记,罔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提出了与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背道而驰的进军方向,要求红十五军团向西南发展,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他不知道当时川陕苏区已经因红四方面军的撤离而不复存在);并全面否定刘志丹等在陕甘根据地执行的正确路线,使用残酷的肉刑等逼供手段,开展错误的“肃反”。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汪锋、马文瑞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骨干被抓(有的已经被开除党籍),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的干部和地方党政骨干200多人被错杀。这导致陕甘苏区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被严重削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习仲勋后来回忆:“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文集》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27页。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北,得知这些情况后,果断停止了在陕甘根据地进行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和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习仲勋被安排在关中特委工作,1936年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由于当时“左”倾路线没有得到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并不公正,这批领导骨干能够重新被使用,对于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中共中央对主持错误“肃反”的人员,给与撤职、警告等组织处理,并撤销朱理治任书记的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以聂洪钧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成立陕甘、陕北省委和关中、三边、神府特委,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以陕甘支队组成的红一军团和以陕甘红军、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并设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肃反”造成的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之间的隔阂,党中央要求对从红二十五军和红一军团调到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工作的干部进行一次普遍教育,对陕甘红军“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对陕甘红军干部的“不安与不满进行诚恳的解释”,“使红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01页。。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过程中,当毛泽东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三千多人中,还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结论,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9页。这样,遵义会议以来所确立的正确组织路线在陕甘根据地得到贯彻,从而迅速扭转和稳定了局势,化解了陕甘根据地的危机。这后来被习仲勋喻为“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假设陕甘根据地的“肃反”问题不及时纠正,陕甘苏区自身难保,也就不可能为党中央提供落脚点了。因此,从这个意义讲“中央救了陕甘”也是恰如其分。
二、中共中央确定陕甘地区为战略转移的目的地,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长征的落脚点
其三,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陕甘的共产党人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比如中共中央要求普遍地开展土地革命,但是对于如何开展土地革命,上级组织的要求并不都符合各地的实际。当时中共中央指示在革命暴动发动的同时力行土地革命。实际上在陕甘地区,不仅在武装起义胜负未卜的时刻无法立即贯彻这一指示,而且由于地广人稀和土地占有情况与南方不同,即使建立了工农政权的地方,也不能机械地照搬中央关于土地斗争的具体政策。陕甘苏区开始是以“打土豪,分浮财”为发动群众的主要手段,待政权和根据地相对稳定之后,经过调查研究,在南梁时期才开始大规模地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陕甘苏区也没有盲从和照搬,而是实行“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田、青苗一齐分”等从当地实际出发的具体政策。[注]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姚文琦主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精编(1)》,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抽选我院收治的26例血管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10例,女性患者16例,年龄24~53岁,平均年龄(37.4±2.3)岁。
南方各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力红军出发前后,红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所部会合,以及红二十五军作为“第二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其目的都是调动和牵制“围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根据地的敌军,拯救那里的危机。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派程子华去鄂豫皖根据地组织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并建立新根据地时讲得非常透彻。周恩来说:“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注]《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这三支红军是全国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他们的突围远征和创建新根据地的努力,虽然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局,但是,大大减弱了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进攻势头,为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赢得了时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围剿军”的战术作用。[注]参见拙作:《根据地:长征胜利的彼岸》,《党史博览》2016年第9期。
1.2 病例排除标准 ⑴前次古典式剖宫产 (倒“T”型或“J”型);⑵有子宫破裂史;⑶前次大的子宫手术史或子宫肌瘤剥除史术中穿透子宫内膜者;⑷有阴道分娩禁忌证者;⑸前次剖宫产手术指针再次出现;⑹距上一次剖宫产的时间<1.5年;⑺有2次及以上的剖宫产史;⑻超声检查示子宫下段壁薄(<1.5MM);⑼子宫下段有压痛。
第二阶段是各路红军长征之初,红二、六军团继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并从那里踏上长征路之后,一度在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创建了黔西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创建了川康边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根据敌情变化,先后选择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等地创建新根据地,但是其努力一一落空。这个阶段创建新根据地的区域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并试图与原来的老根据地形成呼应。红二、六军团创建的黔西根据地只存在了一个月,红二十五军的存在了半年,红四方面军实际控制川康边根据地15个月,而中央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尝试则全部未果。这使得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开始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复兴之路等全局性的问题。各路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进入第三阶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陕甘地区(开始时是川陕甘)为长征的战略目的地,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
嘉兴市土地资源极其有限,2013年人均占地面积8.69平方千米/万人,人口密度高达1 149.86人/平方千米。截至2012年,嘉兴市陆地面积3 915平方千米,耕地面积208 036公顷,人均占有耕地0.045 8公顷。从土地利用角度看,就农用地而言,耕地、园地、林地和其他农用地共计282 655公顷,其中耕地是主体,占有75.25%;建设用地方面,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供给78 890公顷;至于未利用地,水域、滩涂沼泽、自然保留地共计39 330公顷,占有土地总面积的9.81%,可利用土地十分有限。
在陕甘地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奋斗目标,不再是且战且走不得已的选择,而是建立在对全国局势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是基于中国革命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预判。因而,中共中央对实现这一目标矢志不移。但是,把持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作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找出各种借口故意延宕。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先后举行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对张国焘及其支持者进行耐心的劝说,并严肃批评其南下主张和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的目标做了微调。在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明确:“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第636页。
其一是确定并实施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对于陕甘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红军将士都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但对如何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根据地的认识并不统一。彭德怀当时就曾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指出,“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的有利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注]彭德怀:《争取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与扩大红军》(1936年1月26日),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毛泽东则主张以发展求巩固。他的主张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这样,继指挥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东征不仅扩红8000余人,筹款和物资50万银元,为日后红军主力全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做了重要的思想发动和战前准备,而且迫使原来盘踞陕北吴堡、义和镇和神木、府谷等地的阎锡山晋绥军的正太护路军司令兼陕北“剿共”总指挥孙楚指挥4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回撤山西,使陕甘根据地“吴、佳、神、府广大区域的恢复与占领,使红军战略后方增加了力量”[注]毛泽东:《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1936年3月1日),《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第125页。。随后红一方面军又发动西征,到1936年7月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开辟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红军的东征和西征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其最重要的成果是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促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完成了中国革命骨干力量由南向北的大转移。此后,中国的各路红军第一次纳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抵御国民党军可能的进犯,应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邀,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红军主力则南下关中,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相互策应,从而使陕甘根据地由陕北一隅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地域扩大为二十余县近13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150多万,成为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长期稳定的大本营。
其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特别是华北事变的发生,造成中华民族空前的生存危机。这实际引起中国革命主要任务的变化,即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变为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企图,由反帝、反封建并重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人民饱受欺辱,国难日益加重。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也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的命题: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果不能立即停止“左”倾教条主义者奉行的“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统战政策,如果只是在远离抗日前线且在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下的南方各根据地一般性地发表救国宣言和号召,是很难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拥护并实现自己的抗日救亡主张的。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因独立自主地依据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它为中共在民族矛盾渐次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适时转变自己的政治路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刚刚从四渡赤水之战杀出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中共中央,从电讯中得知华北事变,毛泽东就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这样,他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如果说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在长征开始时更多地还只是一般性的泛泛号召,那么,到这时已经是红军将士目标明确的实际行动。在陕甘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与奔赴抗日前线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北上抗日化为各路红军鼓舞士气和团结动员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为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再者,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次发展的客观实际,为了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战略依托与支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进军的方向指向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接壤的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设想背靠苏联、外蒙,依托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然后向东发展,实现直接对日作战。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6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页。
首先,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中心发生转移。传统的革命中心——中国南方,自叛变国民革命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蒋介石集团,由于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在与新旧军阀的混战中逐渐胜出,并于1928年12月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其反动统治日渐巩固;而北方旧的反动封建统治势力自辛亥革命起,迭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打击,并在北伐及其以后与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彻底落败,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中国北方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与此相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势力的加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白区的上海、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无法立足,而且在大革命失败之初,利用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间隙,陆续建立的海陆丰、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川陕、黔东,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等,都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成为游击区。这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由南向北,进而向西南、西北不断渗透和拓展,日趋强化。原来的革命中心——中国南方,成为新的反革命势力统治的中心;而传统的封建统治的中心——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策源地。[注]参见拙作:《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党的文献》2013年第3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亲身经历和目睹了红军反“围剿”的失败与各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等地建立根据地的努力落空等痛苦历程,使他们对中国革命中心自南向北转移的历史大趋势,产生了切身的体会。长征结束10年后,毛泽东仍深有感触地指出:“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注]《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必须适时北移,长征在事实上成就了这一历史过程。
张国焘携红四方面军8万之众,一意孤行坚持其南下方针,给党中央造成严峻的挑战。当时经过18000里艰苦转战的中央红军已不足两万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又划归张国焘直接指挥。张国焘不满足于新攫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他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66页。,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坚定北上陕甘的方针不变,率红一军、红三军(即原来的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鉴于北上红军的兵力大为减少,只剩下7000余人,进一步对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进行调整,但仍然将陕甘地区视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计划先在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后,再向陕甘发展。因此,会议决定将单独北上的红一军和红三军以及军委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9月17日,其先头部队一举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北进的通道。但是,对究竟在靠近苏联的哪一块区域建立根据地,尚不明确。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度决定派谢觉哉和毛泽民到新疆去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注]《中央常委会张闻天发言记录》(1935年9月20日),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页。。正在这个举棋不定的关头,毛泽东和党中央意外地从哈达铺邮局得到的报纸上得知,陕北仍然有红军和游击队,仍然有苏区,而且得知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在相邻区域活动,并刚刚取得对国民党军作战的重大胜利。于是,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首先到陕北。[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76页。27日,中共中央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做出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77页。。陆定一当年曾详细记述了28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榜罗镇会议时的讲话内容。毛泽东说:“现在,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注]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13-414页。于是,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从榜罗镇出发又长驱2000余里,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从上述过程可知,确定陕甘地区为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共中央既定的目标,而首先落脚陕北则是必然之中的偶然。各路红军在长征途中重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看似是个行军路线和确定目的地的问题,但实际上与长征时期的历史背景有关,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关,与中国南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力量的变化有关,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其实质是对中国革命任务、路线和前途的规律性认识问题,是关于长征道路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亲身经历党中央与张国焘“北上”与“南下”方针激烈争锋过程的徐向前后来指出: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他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页。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在尚不知道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现状的情况下选择陕甘地区作为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并义无反顾地坚决执行这一战略决策。
踏上长征路的红军,要寻找和开辟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是既定的;在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则是红军由南向北一路转战中用血的代价摸索出的结论;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历史趋势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决定了红军要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薄弱和邻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的大本营;而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巍然屹立,以及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征率先抵达陕北,为党中央和陕甘支队顺利落脚陕北,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三、关于是“陕甘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甘”
中共中央虽已把进军的大方向剑指陕甘,但在长征到达哈达铺之前,对陕甘地区的具体状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对能否在陕甘地区立足忧虑重重。在处于困境最低点召开的俄界会议上,一度曾调整在陕甘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73页。毛泽东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他对那时前途未卜的焦虑印象深刻,以致10年过后仍深有感触地说:“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陕甘根据地后,虽然全体将士革命斗志依然昂扬,但是身体已经是疲惫不堪,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陕甘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阶级亲人,倾其所有帮助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全体将士,体力得到恢复,伤病得到救治,身心得到彻底的休整,摆脱了一年间无根据地作战的痛苦,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以找到新的根据地为标志,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终于取得了胜利,艰苦的万里长征终于结束了,中国革命又揭开了新的一页。从这个意义上讲“陕甘救了中央”并不为过。
另一方面,这时的中共中央已经是经过万里长征洗礼的中共中央。以遵义会议为标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不仅纠正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树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新的军事指挥体系,而且以民主集中制为武器,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端正了党的组织路线和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秩序,并依据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致力于改变党的政治路线。这是一个彻底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的成熟的中共中央。
1.2.2 对照组 采用课堂教育的形式,为PD患者制订有关运动的系列健康教育讲座,主要内容包括PD患者应采取的生活方式、提倡PD患者进行运动锻炼、运动的益处、运动的形式、强度、时间、频率以及注意事项等,如何记录运动日志,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状况等[4]。以上内容共分3次进行讲解,由腹透护士通知患者到肾友俱乐部接受课堂教育,每月1次,每次30~40 min。随后患者每月接受1次电话随访,连续3个月,主要解答患者运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困惑。
四、中共中央立足陕甘促成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出发点
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弥足珍贵,但它当时基本偏于陕北一隅,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合时根据地发展到二十多个县,人口有90余万[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124页。;这里是单一的个体农业经济(少部分区域是农牧结合),几乎没有工业,而且土地贫瘠、交通困难,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更为严重的是它正遭受着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和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高双成、高桂滋,以及宁夏、甘肃军阀武装的20余万大军的包围和“围剿”。这里作为陕甘支队和红二十五军的落脚点已经难以为继,更不足以承载中国革命骨干力量的适时北移和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采取了多方的措施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并以此为基地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这包括:
数据依赖是对程序的数据由于程序结构的关系引用已经被程序处理过的数据而产生的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的抽象。程序变量之间的数据依赖[12]关系可以用程序的数据依赖图(Data Dependence Graph,DDG)来体现。数据依赖图也是由节点和有向边描述的有向图。数据依赖关系有三种:
其二是解决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长征抵达陕甘后,鉴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而导致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精神影响下,于1935年12月中旬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不仅促成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而且对陕甘根据地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说中共中央初到陕北立即停止北方局代表等发动的错误“肃反”是出于组织命令,那么,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后,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不仅过去被错定的“肃反”目标——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成为团结依靠的对象,而且以往确定无疑的革命靶子——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大资产阶级中的英美派也都成为争取团结的对象。这就为彻底纠正和杜绝“肃反”扩大化扫清了理论障碍,为促进陕甘根据地内部各路红军之间的团结与统一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是泛泛地空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是立足陕甘根据地的实际,提出并成功实践了以西北的联合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重要战略。[注]参见拙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2期。比如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向东出师山西而不是南下,既是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也是向“围剿”陕甘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主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示好。在这个问题上,陕甘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中共中央顺利建立与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统一战线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讲:一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数次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交手,歼灭或重创其三个旅,打死打伤和俘虏其旅长各一人。二是他们和陕甘红军及陕甘支队联合,先后粉碎张学良东北军对陕甘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使其损兵折将两个师又一个团。战场上的交锋,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对红军的战斗力有了深切的认识,痛感“剿共”是死路一条,这是三方能够对等谈判的基础。三是陕甘根据地的党组织与杨虎城部(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其中有多位共产党员在杨部担任重要职务或对杨本人有重要影响。而在反“围剿”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如高福源)又成为沟通与张学良及其所部的重要渠道。加之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压迫与歧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前途堪忧;更因为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激起张杨及其所部强烈的民族义愤,对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深恶痛绝。在上述条件下,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先后与张杨达成停战抗日的协议,结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并与陕北地方军阀高桂滋达成合作意向。[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06-507页。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是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抗衡和进行合作谈判的重要砝码,也是与各地方实力派和政治势力洽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强实力基础。于是,有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这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共由此达成合作抗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大本营。
1927年的农村调查,也折射了读书人在村民眼中的尴尬处境:“读书成本太大,出来非但没有官做,即教员位置亦粥少僧多,而况学些空架子,文不象秀才,武不象丁,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不事生产,要吃要用。”[21]
其三是全面开展苏区建设,夯实陕甘宁根据地的物质基础。1935年11月,中共中央为加强陕甘苏区的建设和统一领导,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全面领导苏区建设。发布《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取消一切工商业的捐税;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组织劳动互助社,优待红军家属;开发延长油矿,组织贩运盐池的盐,派部队保护贸易运输和帮助苏区群众开垦荒地;开办各种群众文化福利设施,发展苏区经济文化事业。鉴于宁夏甘肃边界地区回民聚居,党中央加强了民族政策教育,争取回民同胞拥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积极展开对哥老会群众的宣传,使其团结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以调整阶级政策和富农政策为突破口,改变过去把富农与地主、豪绅同样对待、全部没收富农土地财产的政策,“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注]《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页。。以后又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团结爱国乡绅共同抗日。这些举动壮大了红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充实了物质基础,这是陕甘宁根据地能够成为八路军出征抗日的出发点和战略后方,并长期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重要条件。
其四是大力扩红,培养和训练干部,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做好干部和组织准备。中共中央鉴于长征中兵力的锐减,积极扩大红军武装队伍,动员地方游击队担负扩大苏区的任务。1936年初,在新扩红军和收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上,重建了红一军团第一师,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东征中更是扩红8000余人。这些武装力量后来都发展成为抗日的重要力量。此后,为巩固抗日后方,又将苏区划分为5个清剿区,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抽出兵力清剿和肃清土匪,至全国抗战爆发前基本肃清匪患,巩固了苏区内部的稳定安宁。
在“南航”读完学士、硕士,又到“上海交大”读完博士,再到“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一直坚持“计算机软件开发、研究”的梅宏,1999年3月,到美国贝尔实验室作访问科学家。
在长征以来党和部队干部严重减员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应该“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武装力量出发”予以重视。他要求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同时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11页。他在给红军主要将领的电报中曾明确要求:“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00-501页。1936年6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创办,毛泽东亲自为学员们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指出:“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他明确反对照搬苏联内战经验的做法,重申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号召全党和全军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全国抗战爆发前,抗日红军大学共培训军政干部3800余人,输送了大批人才。此外,中革军委还创办了红军摩托学校,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开办了无线电侦察和谍报训练班,三局开办了红军通信学校,总供给部开办了红军供给学校,总卫生部开办了卫生学校,以及各军团和师、团单位主办了多个学兵队。这些专业技术训练班、校,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为迎接全国抗战准备了骨干力量。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会长武涌表示:“智慧建筑应以人为本,注重感知需求,希望通过标准体系建立引导智慧建筑规范发展,降低能耗,引领绿色生活。”
整个滤尘以及除尘系统的风源都由真空源(风机)提供,风机的主要参数一般由风量与风压两个参数确定.风量的计算公式为: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根本改变了陕甘根据地的局面,这是其能够成为各路红军长征落脚点和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出发点的关键。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的是,陕甘苏区的存在,陕甘军民在大革命失败以来,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所开展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及其打下的群众基础,是成就这一历史地位的必要前提条件。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长期稳定的大本营,是中共中央率领各路红军和陕甘军民立足陕甘根据地的实际共同奋斗的结果。毛泽东后来曾饱含深情地指出:“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他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注]《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5页。
TheFormationoftheHistoricalPositionof"TwoPointsandOneExistence"between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PCandtheShaanxi-GansuRevolutionaryBaseArea
JiangJiannong
Abstract:Dur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Agrarian Revolution to Anti-Japanese War, the Shaanxi-Gansu Soviet Area, as "the sole survivor", became the foothold of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in the South and the starting point to the front line for the anti-Japanese armed force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ormation of t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position was the result of the people's long-term heroic struggle in Shaanxi and Gansu. At the same tim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after their arrival in Shaanxi and Gansu played a vital role. Specifically, the guidance of the August 7th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opened up the Shaanxi-Gansu Soviet Area, and the people of Shaanxi-Gansu have found out their unique struggle experience in practice, which was the internal basis for its "sole survivor". Due to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center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the fact th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d become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Chinese societ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s made the decision to develop Shaanxi and Gansu as the base areas. The stand of the Shaanxi-Gansu Soviet Area and the victory of the 25th Red Army's Long March have provided objective possibility for that decision. The Shaanxi-Gansu Soviet Area has provided a habitat for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entral Red Army, which have traveled for thousands of miles. The correct route implement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after the Zunyi Conference has saved the crisis in the Shaanxi-Gansu Soviet Area. The Central Committee led the army and people in Shaanxi and Gansu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Shaanxi-Gansu Soviet Area militarily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so as to make it a long-term and stable base camp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Especially,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Shaanxi-Gansu Soviet Area, the Central Committee has put forward and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the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by the Northwest United Front, thus realizing the grea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low tide to the new high tide.
Keyword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e Shaanxi-Gansu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e foothold; the starting point; the sole survivor; leading role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2.002
作者简介:蒋建农,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31)
责任编辑:魏烈刚
标签:根据地论文; 中共中央论文; 红军论文; 陕北论文; 苏区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