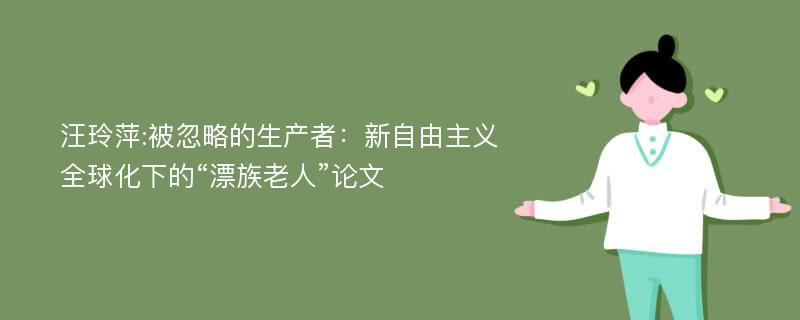
摘 要:有关“漂族老人”的研究都以城市化和家庭主义为视角,将“漂族老人”视为养老服务消费者的角色。将“漂族老人”置于生产语境和全球经济体系中重新分析发现,“漂族老人”承担了低廉劳动力和生产消费者的功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结构因素被遮蔽,导致中国“漂族老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迁入地城市以及家庭中,均成为边缘人群。改善中国“漂族老人”的边缘处境,需要促进整体经济产业升级;需要呼吁迁入地政府重视“漂族老人”的贡献,为促进“漂族老人”的社会适应而制定相应政策,并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需要改善民生,建成适度普惠的福利体系,提升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关键词:“漂族老人”;被忽略的生产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2015年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示,流动老人人数近1 800万。其中,43%的老人是为了照顾晚辈而迁移至子女所在城市[1]。当孙辈长大后,老人们或留居城市,或返回家乡。目前,这类因照顾晚辈而流动的老人还无统一的学术名称,社会大众和媒体常称其为“老漂族”,笔者使用“漂族老人”的名称。
随着规模增加,“漂族老人”的随迁成因、困境及处境改善等问题受到公众和学者的关注。有关 “漂族老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关注群体特征[2]、迁入地适应和融合、精神健康状况、留居意愿等[3],宏观层面则主要探讨异地养老政策[4]。这些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也对改善“漂族老人”的生活状况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存在四个环环相扣的研究误区:第一,单纯将“漂族老人”视为养老者,忽略他们作为家务劳动承担者和儿童照顾者等生产者的角色。第二,由于仅将“漂族老人”视为养老者,研究者只发掘了他们迁移的浅层动因——城市化进程与家庭主义文化的合力[2],而忽略了其作为生产者与当下经济全球化生产体系的联系,从而无法挖掘其迁移的深层原因。第三,对“漂族老人”处境的实质认识不足。快速城市化的浅层归因,使得研究者将“漂族老人”的精神孤独、缺少新的人际交往圈视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不适应[4]。家庭主义文化的浅层归因,则将老人与子女的代际关系紧张视为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碰撞[5]。此外,城市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均等化不足,导致“漂族老人”在享受医疗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障碍[6]。以上认识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却过于表象和零散,未能发现“漂族老人”这些处境背后深层的统一性逻辑:无论是快速城市化还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家庭主义文化,都离不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塑,“漂族老人”处境的本质应是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衍生物。第四,由于存在前三个研究误区,既有研究提出改善“漂族老人”境遇的对策多集中在加强情绪疏导,提高老人交往能力,改变老人传统家庭责任观,倡导子女理解,关爱和孝顺老人,消除医疗、公共福利的户籍分割等[5]。这些建议虽有一定针对性,但是由于没有触及造成“漂族老人”处境的深层结构原因,因此,建议的效用大打折扣。
网络环境下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满足中国网络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满足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烈需求。中小企业需从网络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入手,创新网络财务管理制度,配备相应的高科技人才和过硬的硬件技术,形成新型、良性、高效的企业发展,追求更大的现实利益。
正如米尔斯所言:“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来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7]在全球化发展时代,上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下至一个群体或个体,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漂族老人”的境遇,看似是个体经历,事实上却与全球化发展的社会结构存在着密切联系。对“漂族老人”的研究也只有在全球化视野下进行,才能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
鉴于此,笔者将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野来回答四个问题:为什么“漂族老人”是生产者,其作为生产者的功能是什么?“漂族老人”因何迁移并成为生产者,又何以被遮蔽? “漂族老人”处境的本质是什么?改善“漂族老人”处境的有效途径是什么?
一、作为生产者的“漂族老人”及其功能
1.第一对张力:国际分工中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与消费主义扩张
大多数老人的随迁行为属于责任型和代际互惠型随迁。老人迁移的重要目的是,承担照顾孙辈和子女家庭家务劳动,减轻子女家庭负担,实现子女家庭的“人的生产”。因此,在人的生产语境下,“漂族老人”毋庸置疑地成为社会生产范畴内的生产者。
几十年来,右心前导联高而宽的R波被认为是后壁心肌梗死的征象。但MRI-MDE与心电图相互关系的新证据表明,在排除右心室肥大、完全性右束支阻滞或预激综合征等影响QRS波形态的因素后,在急性冠脉综合征发展过程中,V1导联出现高R波提示侧壁心肌梗死,并且梗死面积通常更大、透壁程度更深。
由于“漂族老人”生产者的角色被遮蔽,其劳动创造不能通过报酬体现,也无法在GDP指标中显现,所以迁入地各级政府不仅忽视“漂族老人”对当地做出的贡献,还常常将之视为负担。“漂族老人”无法享受与迁入地户籍老人同等的公共福利和社会服务,还面临异地就医和异地养老等制度障碍。“漂族老人”成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社会保障“两不靠”的边缘人群。
这首打油诗极为生动地呈现了“漂族老人”精神孤独、家务劳动繁重、代际紧张等生活困境,凸显了他们在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是新家庭主义文化的体现。在新家庭主义文化中,父权制式微。长者不再掌握家庭支配权,即使是男性长者,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家务劳动者大军中。有一定数量的男性“漂族老人”单独或陪同妻子一起来照顾晚辈,承担家务劳动。家庭资源分配实行儿童中心主义原则,呈现从下至上的代际等级,儿童往往在吃、穿、住、玩、教育方面获得了家庭的最优资源,老人则处于资源分配的底端。
第一,“漂族老人”的“人的生产”为全球化经济体系提供低廉劳动力。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积累逻辑由此成为各国生产领域的支配性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利润是工人劳动创造出的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总价值减去劳动力的价值——雇佣工资后的盈余。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意味着要尽可能缩减劳动力价值。工人劳动力价值是劳动者为了维持自身和家属的生活所必需付出的那一部分劳动(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进一步揭示了必要劳动包含社会部分和家庭部分:社会部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工资报酬,用于支付购买劳动力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等;家庭部分表现为家务劳动,包括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被消费前的额外劳动和未来劳动力(婴幼儿的抚育劳动),这部分劳动通常是无报酬的。“漂族老人”所承担的子女家庭的家务劳动和抚育孙辈劳动就属于家庭部分的必要劳动。在必要劳动恒定的情况下,家庭部分的必要劳动越多,“漂族老人”子女家庭需要购买的社会部分的必要劳动越少,则其所需的工资越少。因此,“漂族老人”承担的子女家庭“人的生产”无疑降低了全球资本在中国的用工成本,为其生产出了低廉的劳动力。
“漂族老人”之所以成为生产者,是通过承担抚育孙辈和子女家庭的家务劳动实现的。探究老人何以成为生产者,需要探讨子女家庭何以需要老人前来承担这一任务的原因,也需要结合子女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结构成因来考虑分析。
二、“漂族老人”何以成为被忽略的生产者
大多数“漂族老人”通过承担子女家庭的家务劳动,成为“人的生产”领域的生产者,同时也给全球经济生产体系提供了低廉劳动力和消费至上的消费者,卷入到“物的生产”领域。然而,哪些结构性的力量推动了“漂族老人”背井离乡地成为生产者,同时又是哪些力量忽略了其生产者的角色,导致研究者、政府和经济组织等很少将“漂族老人”视为生产者?
(一)GDP主义
GDP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主要以GDP来衡量,GDP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我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牢不可破的政策意识形态。政府确立一个量化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各地政府,GDP增长同时也是最主要的考核指标。GDP以市场价格来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有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在核算家务劳动时,包括有偿家务劳动和家庭自有住宅服务等,但没有包括抚养儿童、照顾老人、洗衣做饭、清扫房屋等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所以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不被视为生产,承担家务劳动的“漂族老人”也不被看作是生产者,其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也因此被抹杀。
她说:“按我对表哥的了解,你应该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你少管,不捣乱就成。”我说。“那你加油哟!我表哥喜欢有个性的女生。”临别时,她给了我提议。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扩张中的张力
第二,“漂族老人”的“人的生产”为全球化经济体系提供了消费者。20世纪初福特主义兴起,以专业化和标准化为基础的流水线式生产组织形式急速扩张,自动化和机械化带来的批量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大量商品涌现。这些商品必须被消费者购买,资本才能获得利润,因此消费者持续的消费欲望对资本主义生产至关重要。资本主义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后,僵化的生产管理体制和大规模工业生产被更灵活的生产模式(如及时生产和外包制等)所取代。此时的生产早已不仅是商品的生产,而且是消费欲望和消费大众的生产。唯有如此,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商品生产也才有意义。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扩张,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商品数量急剧增长,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数量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对消费者数量的需求,将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转变为消费者十分必要,包括“漂族老人”子女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成为新生消费力量。“漂族老人”的子女迅速将消费主义主导的城市生活方式内化,成为全球化资本所需的消费者,他们的孙辈自出生起就在消费文化中浸润成长,成为天然的消费者,因此“漂族老人”的“人的生产”具有消费者生产的功能。
中国社会正处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这一全球化可以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globalization)。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发端于古典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为英、美等国所推崇[9],其后在多国政治经济实践层面向新自由主义急剧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1)实现稳固的个人财产权、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2)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控制在最小限度;3)国家的角色只是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并提供必要的国防、法律和治安,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和市场的正常运转。因此新自由主义强烈反对二战以后实行的“镶嵌型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10]11政策,而是主张:压缩政府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政府福利开支,重点发展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收入的基础设施和文教卫生行业;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外资限制;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税率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等[11]。其后,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借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将其推行至全球,普遍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也形塑了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格局,这一趋势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正向市场体制转变,恰好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转变交会在一起[10]124-126。虽然中国社会实行的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针,但制度转型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呈现出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特征:严重依赖海外直接投资,跨国资本强势流入;利用人口红利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工厂”;消费主义盛行;高度竞争;农村公社解体及国有企业民营化,国家福利大幅减少。中国建立了新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交叉结合的特殊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以上特征形成了两对张力,促成了“漂族老人”充当被忽视的生产者的结构性力量。
“生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的定义可以视为广义的。他们认为生产既包括“物的生产”,也包括“人的生产”。“物的生产”指生活资料即食物、住房、衣服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人的生产”就是维持和延续人的生命的生产,既包括通过家务等劳动使得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也包括通过生育和抚育使得他人的生命得以产生[8]。狭义的生产,最初特指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和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所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都被视为生产。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为动力,进入后福特主义的企业资本采用弹性生产的后福特制,强调及时生产和外包,实现资本的跨国流动和弹性积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开放东部沿海城市和一些经济开发区,大量吸引外来资本,制造了数量可观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漂族老人”子女前来就业。随着外国资本的强势流入,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劳动条件和劳工待遇“向下竞争”[12],致使“漂族老人”子女的收入相对低廉。跨国企业的外包制在中国沿海地区催生了一大批代工工厂,也造成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在没有国际秩序主导权和缺少技术竞争力的情况下,这些工厂不得不以低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作为优势来参与国际竞争。“漂族老人”的子女迁入到东部沿海地区,虽不一定受雇于外来资本投资的企业和代工工厂,但受到参与国际分工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同类职业相比,工资水平普遍较低。有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平均收入仅为人民币30 197元,“漂族老人”子女集中的东部地区劳动力的人均年总收入也只有人民币34 980元[1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中国社会也全面地遭遇消费主义。五光十色的消费场所、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形式丰富的大众媒体轻而易举地唤起了“漂族老人”的子女的消费欲望,制造出大量的虚假需求。消费更隐蔽地操弄着人们的欲望和情感,成为其幸福的根源。不同的消费方式蕴含着不同的阶层的区隔趣味,更是个人的身份认同和阶层地位的表达。个体依据消费实现了阶层划分,也通过消费模仿力图实现阶层流动。为了在城市能有个体面的身份,“漂族老人”的子女通过购买汽车、看电影、外出就餐和旅游等实现城市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消费主义成为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宰制个体的手段,建构出“新贫困主义”。一旦个体偏离了消费者的标准化生活,就会成为“新穷人”[14]。为了避免陷入“新贫困”,“漂族老人”的子女必须消费,唯有这样才能取得在城市的立足之地。他们通过购买商品房获得当地户籍,进而获得消费公共产品等舒适物(如医疗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等)的资格。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成为“漂族老人”的子女实现城市适应的必要手段。
消费主义扩张导致了“漂族老人”子女的生活成本提高,造成了“漂族老人”子女家庭的生活挤压。为了维持体面的消费生活,“漂族老人”子女家庭既需要女性全面就业,又无力购买昂贵的儿童抚育服务,第一对张力因此形成。
2.第二对张力:“竞争力”逻辑与国家福利大幅缩减
本文构建的机会创新性与资源拼凑模式匹配关系模型,能够指导初创企业的创业行为,帮助初创企业获得较高的创业绩效。同时,能够促使创业者从机会创新性和资源拼凑的双重视角思考创业问题,正确判断机会的创新程度,充分利用手头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最大化创造价值,实现创业成功。但本研究的案例企业仅来自天津、深圳和成都三个城市,缺少其他地区的样本分析,未来会采用大样本统计方法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激烈的竞争环境,资本不断在全球范围寻找更低廉的劳动力来替代现有劳动力,制造劳动者间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劳动者不仅要和同一地区、国家的劳动者竞争,还要同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劳动者竞争,这无疑加重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也逼迫他们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贡献更多的劳动力总价值。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界限逐渐被打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需要投入工作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超时加班成为普遍现象,竞争和自我奋斗也成为主流的工作伦理。近年来,“过劳死”现象频发,“(工作)把女人当成男人用,把男人当成牲口用”等劳动者自我调侃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正是当下激烈竞争社会中劳动者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反映,更是全球资本剥削和异化劳动者的重要表现。面对巨大的在竞争压力,“漂族老人”的子女为了维持日益高涨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得不挤压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的时间和精力来辛勤工作。
改革开放前,国家提供了全方位的福利保障。许多企事业单位开办了食堂、澡堂、理发店、托儿所等福利机构,这些机构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女职工的家务劳动压力。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化进程,国家逐步撤销对个体和家庭全面照料的福利供给结构。最初国家提出“企业不再办社会”,试图取消与生产无关的职工福利和社会保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是将教育(尤其是婴幼儿照顾的幼托院所)、医疗和住房推向市场。至此,包括生育、儿童及老人照料在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为私人化家庭的责任[15]。
高度竞争的逻辑使得“漂族老人”子女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照顾家庭,与国家福利削减造成的育儿等家务劳动家庭化构成了另一对张力。
低收入和高消费的张力下,“漂族老人”子女家庭的年轻女性无法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无力承担有偿的儿童抚育服务。高度竞争和儿童照顾家庭化的张力下,“漂族老人”子女(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需要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需要承担儿童照顾责任。为了应对以上两重困境,“漂族老人”子女让老人们迁移至自己生活的城市,承担家务劳动并照顾孩子。“漂族老人”照顾晚辈成为普遍现象,也因此成为被忽略的生产者。
三、边缘化:“漂族老人”处境的本质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张力作用下,“漂族老人”迁入城市,成为全球资本生产体系中被遮蔽的生产者,也因此陷入了边缘化的处境之中。事实上,前文提及“漂族老人”的诸多困境具有内在统一性,即其边缘化处境。
(一)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位置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根据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和资源的不同流向将不同地区和国家分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空间等级,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地区不平等,敏锐地归纳出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不过,“核心—半边缘—边缘”不平等化等级划分不仅发生在国家和地区间,也发生在不同年龄、性别和阶层的群体间,即便是边缘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群,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也并不相同。“漂族老人”从农村或小城镇进入城市后,虽然从空间维度上看,他们由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区进入了半边缘地区,但却因为年龄因素和子女家庭的需要,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隐性生产者,通过承担子女家庭家务劳动,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劳动力生产和消费者生产提供了无偿劳动,成为该体系中的边缘人群。
(二)成为迁入城市的边缘群体
在狭义生产的范畴中,“漂族老人”还是生产者吗?马克思、恩格斯生产理论同样认为,“人的生产”与“物的生产”存在辩证关系,两者虽然内容不同,却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尤其在当下资本主义生产已进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后,资本几乎将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一切事物商品化和工具化,“人的生产”也被纳入“物的生产”领域。因此,“漂族老人”通过家务劳动而进行的“人的生产”,无法遗世独立于“物的生产”,并在全球经济生产体系中具有以下功能:
这种“GDP主义”的意识形态能解释“漂族老人”生产者角色被忽视的原因,却不能解释“漂族老人”为何成为生产者,也不能解释哪些力量导致“漂族老人”的家务劳动无偿化。回答以上问题,需要从“漂族老人”及其子女所处的社会结构和时代环境入手。
此外,“漂族老人”从原来的人际网络中脱嵌,在迁入地又很难重新建构起新的社会网络,成为“无根的边缘人”。一方面,在城市家庭精细化育儿文化背景下,“漂族老人”不得不花去大量的时间来照顾孙辈,无暇结识新的朋友,难以建构新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的封闭居住空间设计和便利性公共娱乐空间的缺失,也一定程度阻碍了“漂族老人”的交友活动。此外,由于生活方式、气候环境、语言风俗等方面的差异,“漂族老人”很难融入迁入地,加剧了适应障碍,进而导致其无法扎根城市。
(三)成为家庭中的边缘成员
在“漂族老人”中,广为流传一首名为《退休新传——在儿女家看孩子感言》的打油诗:“是主人吧,说了不算;是客人吧,啥活都干;是保姆吧,一分不赚……起早些吧,怕把人家好梦打断;起晩些吧,怕耽误人家吃饭;做多了吧,只怕把东西作践;做少了吧,又怕肚子填不满;菜炒生了,自己咬不烂;菜炒熟了,人家没口感……人家在家,怕脸色难看;人家出门,又感觉孤单;出去串门,全是生面;带娃上街,怕不安全……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累死累活,心甘情愿。唉,左右为难。”
提起丝木棉的名字,让人倍感浪漫、温馨。有人说,它香气氤氲,淬炼时光,只因在寒意袭人的冬季,百花凋零,唯独丝木棉绽放。一片片、一排排的虬枝挂满花瓣,侵袭着大地,在广州大学华软学院校园内摇曳出一地的粉色花海,蔚为壮观。
新家庭主义文化的形成,除了延续传统家庭主义中家庭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事实上,低工资收入和高企的消费水平、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福利的缩减,无疑将家庭放置在风暴之中,任由其应对风险社会的种种不确定性。对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来说,儿童的未来承载着家庭整体利益,因此儿童的发展也是家庭所有成员的责任所在。将资源投入到孙辈身上是家庭应对当下风险社会的最佳策略。如果说传统家庭的秩序是以牺牲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来维系,那么当代中国家庭的稳定则是以牺牲老人利益来实现的。在“漂族老人”家庭,女性不得不就业的现状使得幼儿需要“母职”替代者来照顾;子女收入有限,儿孙的生活质量需要保障,只能将家庭资源的大部分投入到孙辈身上以保障家庭的整体利益[16]。“漂族老人”因此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迁移去照顾后辈,从而成为其家庭的边缘成员。
四、改善“漂族老人”生存处境的对策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构下,“漂族老人”成为被遮蔽的生产者,并在全球资本体系、迁入地城市、家庭中全都被边缘化。改善“漂族老人”处境,提升他们的地位,需要立足全球化背景,从国家、迁入地城市、家庭等不同层面来着手解决。
1102 Down-regulation of grainyhead-like protein 2 promotes drug resistance of tumor cell to gefitinib by inducing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formation
而如果暂态直流偏置磁链和剩磁叠加后使得A相工作磁链正向偏移,则涌流峰值出现的时刻将在合闸后A 相电压的下一个下降沿过零点,该点与初始合闸点的时间差在5~10 ms;若叠加后使得A相工作磁链负向偏移,则涌流峰值出现的时刻将在合闸后A 相电压的下一个上升沿过零点,该点与初始合闸点的时间差在10~15 ms。
民族文化价值:古建筑是民族文化历代相传的载体,同时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生动表现,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文化基础。诸多古建筑物均讲求简朴,但不乏美观,体现了一种不攀比的地域性民族建筑文化。
从国家层面看,首先要抓住信息时代技术革新的机遇,鼓励创新;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升级;减少对外部投资的依赖,鼓励技术创新,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变革对人口红利过分依赖的发展模式。其次,改善民生,加大社会投资,建成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体系,尤其是完善儿童抚育福利体系,减轻“漂族老人”子女家庭的生存压力。
从迁入地城市层面看,劳动力是迁入地城市重要的财富之一,“漂族老人”以无偿家务劳动的形式参与劳动力生产,降低了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城市的竞争力,因而他们不能被视为负担。迁入地城市应正视“漂族老人”的贡献,保障他们能享受当地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权益,从而实现公平正义。首先,迁入地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全国范围异地医疗结算,消除异地养老制度障碍。其次,以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等形式,为“漂族老人”提供精神健康、心理疏导、家庭关系协调和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社会服务,促进“漂族老人”的城市适应。最后,加大社区公共空间和设施的建设力度,使老人能拥有方便易达的活动场所,打破封闭家居环境的限制,扩展其交友空间。
在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塑料打包带(绳)的性能、降低生产成本,通常会根据不同的生产工艺以及不同的用途,添加不同种类和配比的填料,塑料打包带(绳)中常用的填料主要有SiO2、CaCO3、高岭土、滑石粉。不同填料有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将滑石粉作为填料应用在塑料之中,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同时可以改善塑料的物性,扩大塑料的应用范围。采用滑石粉改性的塑料在刚性、拉伸强度、热变形变温度等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可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要[8]。根据所查文献[9]得到塑料打包带(绳)中常用填料的拉曼标准图谱(见图8)与特征峰(见表3),对样品含有填料的种类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地将样品进行分组。
从家庭层面看,各级政府、群团组织也要致力于家庭能力建设,提升“漂族老人”子女家庭的经济能力、照顾能力等,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普惠性服务,促进形成邻里互助,从而提升其家庭风险应对能力。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的号召,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在家庭中形成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等观念,切实改变“漂族老人”家庭边缘地位的现状。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
[2] 孟向京, 姜向群, 宋健, 等. 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J]. 人口研究, 2004, 28(6): 53-59.
[3] 李珊.我国移居老年人的居住意识研究[J].西北人口,2011,32(5):69-72.
[4] 刘庆, 陈世海. 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调查[J]. 中州学刊, 2015(11): 73-77.
[5] 郑佳然.流动老年人口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基于6位“北漂老人”流迁经历的质性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6 (1):112-119.
[6] 周皓.省际人口迁移中的老年人口[J].中国人口科学,2002(2):35-41.
[7]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1.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16.
[9] 萧易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医疗化”的形构[J].社会,2014,34(6):165-195.
[10]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 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1] 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5.
[12] 闻翔,周潇.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7(3):29-39.
[13] 蔡禾.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7.
[14] 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 仇子明,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10.
[15] 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J].开放时代,2012(12):98-112.
[16] 汪玲萍,风笑天,李红芳.老人随迁的多元动力机制与制度逻辑[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3):85-91.
IgnoredProducers:“MigrantElders”intheAgeofNeoliberalGlobalization
Wang Lingping, Li Hongfang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rbanization and familism, “migrant elders” are regarded as consumers of caring service. In the production context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it can be found that “migrant elders” function as the cheap labor force and prosumers. Influenced by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factors, “migrant elders” are marginalized in the global capitalism system, in cities they have moved in and even in their families. To change the marginalized situation of “migrant elders”, the overall economic industry should be upgraded; the governments of immigrant cit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migrant elders”, mak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to promote their social adjustment and provide them with social guarantee and public service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livelihood, establish a moderately inclusive welfare system, enhance the family risk-coping ability and reduce the family’s burden of child-rearing.
Keywords:“migrant elders”; ignored producers;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作者简介:汪玲萍,社会学博士,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红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江苏随迁老人生活地位研究”(2014SJB471)。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9.05.008
(收稿日期:2019-03-06;
责任编辑:沈秀)
标签:老人论文; 家庭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生产者论文; 子女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 江苏随迁老人生活地位研究"; (2014SJB471)论文; 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