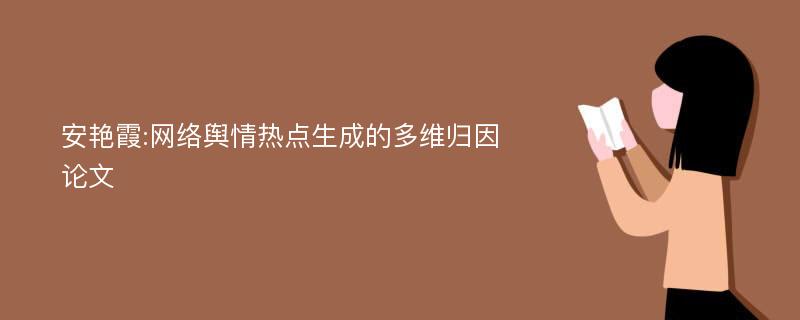
摘要:随着互联网迅速普及、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网络舆论的热度也逐渐上升,其发挥出的强大力量已然改变了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纵观近几年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可以看出社会事件是网络舆情热点产生的导火索,公民意识觉醒是网络舆情热点形成的催化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为网络舆情热点的扩散提供了空间;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网络舆情的产生创造了平台,网络的繁荣为网络舆情提供了规模相当的舆论主体,网络媒体的传播促使个案演变为网络舆论客体;在舆论的传播过程中,社会公共心理是网络舆情扩散的共识要件,作为网络舆论热点制造者、舆论释疑与扩散、舆论引导或干扰的意见领袖又进一步推动了网络舆情的扩散。
关键词:网络舆论;社情民意;公共心理;意见领袖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网络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八次提到了互联网[1]。事实上,网络舆论场已成为人们意见的汇聚之地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网络舆情热点中蕴藏的价值取向对公众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研究其多维成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学术界,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呈不断上升趋势。比如,Brauchler Birgit指出网络中对立矛盾的交锋更容易引发网络舆情。Bob J. Carreil和David L.Sturges 等人提出网络舆情是在公众利益的冲突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引发的[2]。官建文等则重点分析了网民认知框架对议题结构演变的影响[3]。从已有研究来看,关于网络舆情生成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但深入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近年来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发现网络舆论热点发端于现实的社会情境,得益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同时也离不开意见领袖的推动和社会公共心理的作用。
一、社情民意是网络舆情热点产生的现实基础
网络舆情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现实世界这一物质基础。目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期,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4]。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带来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均能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这为网络舆情热点的产生提供了足够多的舆论引爆点。
(一)社会事件是网络舆情热点产生的导火索
网络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是公众意见与网络传播媒介博弈的结果[5]。笔者通过对《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研究报告》及近年来的网络舆情热点进行研读、分析发现,网络舆情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既有国内、国际重大事件,也有突发事件;既有公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有反应社会道德困惑的事件及与弱势群体相关的事件。2016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公共管理仍是舆情高发区[6]; 2017年的舆情事件类型中,社会民生类仍占绝大部分[7]。笔者通过对2018年《网络舆情参考》1-32期的整理、分析发现,社会治理和社会民生类舆情一直占比较多[8]。如“王凤雅事件”、“背受伤学生参加高考、郧西一民警成‘网红’”等。这些网络舆情热点是社会事件在互联网空间的投射;社会事件的发生为网络舆情热点的自发产生提供了足够多的话题和素材,其在网络上的热度丝毫不亚于传统媒体。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消息都可以形成舆情。一则事件、一条消息能否进入公众视野,取决于事件的热度和公众的兴趣,进入公众视野后能否形成网络舆情热点受到多方影响。
(二)公民意识觉醒是网络舆情热点形成的催化剂
公民不同于“臣民”,公民意识需要以主体意识的觉醒作为内在的支撑和动力,具体表现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只有公众积极、主动、自主地参与到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中,他的公民意识才真正觉醒。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体制的日益完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公民意识越来越强。《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2)》指出,公民意识群体性觉醒的时代开始了。比如在国难发生后,多家官媒把自己的微博头像改为黑白色,为逝者哀悼;多家电视台停播综艺节目,悼念逝者。再看近年来的一些网络舆情热点,从“药家鑫案”到微博问政,从两会提案到网络议政,无一不体现着公民维权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的增强。对于网络舆情热点来讲,公民意识是一剂催化剂。当社会事件的发生关系到社会民生、违背主流价值观时,或者发生有违道德、法律、规则的事件时,公民就会利用各种表达渠道发表看法、进行评论,网络因其开放性、草根性等特点,使之自然而然地成为公民的宣泄渠道、言论的“自由市场”、议题不断裂变的“天然温床”。
(三)利益表达机制缺位为网络舆情热点的扩散提供了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9]。网络舆情热点的产生、发展大多都涉及到公众或网民的利益,当公众利益或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时就会引起他们对某一社会事件的关注和持续讨论,最终演化为群体事件。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其利益表达渠道是有限的。在我国,公民或社会团体进行利益表达的途径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制度内利益表达和制度外利益表达[10]。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等都是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游说、集会、游行、静坐和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制造舆论是制度外利益表达渠道。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表达机制还未实现良性运作,存在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制度外利益表达渠道受到法律限制等问题。比如下层市民的诉求需层层上报才可能得以解决。“传统利益表达机制已经滞后于多样化利益诉求的社会现实”[11]。“民意”急需泄洪,互联网顺理成章地成为各阶层畅所欲言的利益表达平台,使得原本处于内隐状态的社会舆论借助互联网之力迅速爆发并蔓延。
二、网络技术的发展是网络舆情热点传播的物质基础
网络舆情的客体是指能够吸引主体眼球,并能引发主体积极参与、讨论的话题,即公共议题。前面我们说过,并不是所有社会事件或者信息都能引起舆论。某一个个案要成为舆论客体,就必须延长它的生命。这既离不开网民的持续关注,更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互联网这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技术区别在于“去中心化”。“互联网从设计之初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一个节点都可以通过任何一个另外的节点,通向一个节点可以有无数路径”[16]。这就决定了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只要掌握互联网这项技术,在任何一个具备上网条件的地方,每一个拥有技术终端的人都可以参与到网络舆论的传播活动中。著名的“克林顿性丑闻”事件就真正印证了“网络传播无国界”。互联网上热点话题丰富,舆情热度高位运行,再加之信息在网络上呈病毒式、蛛网状传播,网络媒体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播频率、传播质量等方面的优势增加了各种社会事件的现场感和冲击力,使得信息呈现更为直接、形象、生动,刺激了网络舆论的大爆炸,为个案演变为网络舆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网络舆情热点的产生创造了平台
2003 年之前,中国的互联网处于 Webl.0 阶段。这个时期,以民意为主导的网络舆情事件在中国并不多见。2003 年以后,互联网进入Web2.0阶段。在这一阶段,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等综合类社交应用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用户可以畅所欲言,甚至可以跨时间、跨地域、跨年龄进行不同形式的互动和交流,信息传播更为便利。纵观网络舆情热点,舆论的首曝直至扩散基本都在互联网上,而且瞬间扩散能力极强。如天津人才新政颁布后,“人民网”、“央视网”等媒体进行相关报道,随后吸引了网民的广泛关注与传播,引发了落户狂潮。“眼癌女童王凤雅去世事件”是微信公众号“有槽”发布了一篇名为《王凤雅小朋友之死》的文章后,使得该事件进入公众视野,进而成为网络舆论热点。据《2017年上半年舆情分析报告》,社交媒体依然是舆情发生的主要信息源及舆情发酵关键渠道[7]。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和社交作为基础应用,规模增长稳健[13]。Web2.0的发展再加之相关技术的使用,使得网络成为人们思想或利益诉求的公共舆论平台,为网络與情热点的形成和兴起提供了载体和技术条件。
(二)网络的繁荣为网络舆情提供了规模相当的舆论主体
装备制造业的决策人员可以对企业发展的情况与当前企业的规模展开数据分析,研制出最适合企业当前发展的ERP系统。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整合要注意与企业实际相结合,切忌生搬硬造。决策人员可以积极参考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分析成功的原因并适当运用。此外,企业的技术人员要及时更新并完善ERP系统,确保信息化与工业化整合度高,防止企业在高新技术上出现落后的情况。
舆论包括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的存在体三个基本要素[14]。网络舆论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主体是指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客体是指人类活动对象的总和[9]。网络舆论主体是在网络这个空间里发表意见、展现态度、抒发感情的人,具体包括网民、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推手等,其中网民是数量最为庞大的网络舆论主体。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到55.8%[13]。规模庞大及逐年攀升的网民数量是网络舆情传播、扩散的有效力量。“六度分离”现象显示,人际网络中的各个节点能够通过网络中若干个节点间接地发生联系,即人际网络是具有明显的小世界特性的[15]。如果说网络是一张巨网,那么网民就是网络中的节点,网民与网民间以节点连接状态呈现,这样的话,网民可以通过这若干个节点传递信息,当一件事情通过成千上万网民的点击,就会产生“蝴蝶效应”,社会对这件事的关注程度会成几何倍数增长。豪不夸张地说,互联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学历等各种社会背景的网民,社会事件会以“亿”为单位传播,这件事在24小时之内传遍“大街小巷”不费吹灰之力。
以羧甲基纤维素钠(CMC)为粘合剂,制备成型秸秆炭,优化了粘结剂的添加量及成型温度,并对样品进行吸附性能测试及结构表征,具体结论如下:
(三)网络媒体的传播促使个案演变为网络舆情客体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正处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1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应用技术也逐步走向多元化。微博、微信、QQ、论坛等技术在现实生活中作用越来越明显,其在传播领域的作用也日渐强大。
三、社会心理是网络舆情热点扩散的共识要件
攻击性较强的儿童往往缺乏解决交往问题的策略,不善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不善于与他人进行交往。这就需要向儿童提供一些正常交往的策略,通过榜样的示范、解释和说明,帮助他们掌握减少人际冲突的策略,从而改善人际关系,减少攻击性行为。
(一)从众心理激发了网络舆情的热度
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最早对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又译为舆论领袖)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意见领袖是指能够影响竞选结果的部分选民,亦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在网络舆论场中,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不同作用。
(二)公众同情延伸了网络舆情的广度
刻板印象,即“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过于简单的印象”[21]。刻板印象伴随着对人、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好恶情感。在网络舆论中,当一个舆论客体出现时,围绕客体产生的种种舆论并不是凭空而起的,公众先入为主的“成见”往往会影响事件和舆论的进展程度。比如,提到城管,我们就会想当然地把“城管”与“打人”、“暴力执法”联系起来,形成对城管的刻板印象,使得城管的形象被贬损甚至“丑化”。有时候即使城管这一群体并没有表现出违反大众价值观的行为,我们也会认为他们在“暴力执法”,出现认知偏差。 在“王凤雅”事件中,微信公众号“有槽”发布了一篇名为《王凤雅小朋友之死》的文章,之后被热传。该文在没有确认事实之前使用了“重男轻女”、“弃女救儿”、“诈捐”等词语吸引公众眼球并刺激着广大读者,促使事件不断扩散、发酵。在舆情风波的初期,这些词语先入为主地进入了公众视野,公众对此口诛笔伐,失去了对事件的真实性的推敲和考量,致使事件发生之初就有大量的社会批判和讨伐直指小凤雅的家人,以致于小凤雅的妈妈发声澄清依旧没能换来大家的理解,反而更加激起了舆论质疑,最终造成澄清困难。公众因刻板印象极易忽略事实,一次次将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德国学者A.E.F.谢富勒首次提出“社会心理”一词。R.B.普列汉诺夫指出:“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17]。公众的社会公共心理在现实中得到共鸣后,情绪会不断被激发,聚积的情绪在某一时刻由量变到质变,最终促使社会事件不断演变、发酵、爆发。
(1)同质化倾向严重,民宿识别度低。庐山现有民宿多为原景区内居民自用房改造,规模较小,客房数量不多,且装修简单,外形上缺乏特色,千篇一律。多数民宿主题设置为“家庭旅馆”,名称及风格都十分雷同,大多以“XX家庭旅馆”为名,缺乏创意。庐山民宿经营者年龄层次也较大,为游客提供的基本是普通的“长辈式”温馨服务,但是目前游客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更追求有个性、多元化的住宿体验,这些民宿就不能够满足年轻游客群体的消费需求,出现了无特色、无创意、低识别度的现象。
(三)刻板印象增加了网络舆情的强度
林郁沁指出,公众同情即国民集体情感,具有批评时弊又容易被操纵的、特殊的社会批判功能[19]。他认为,“公众同情,特别是当它被自发地表达出来时,经常能成功地唤起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力批评”[19]。他强调了“公众同情中情的被高度动员及其政治性”[20]。简而言之,公众同情可以通过影响舆论倾向进而影响事件进展,扩大舆论的影响力。新媒体时代,人类情感表达更加自由和直接,因情而动员的批判力量逐渐显现,并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中进一步放大。以2018年的“眼癌女童王凤雅事件”为例,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初,有很多针对王凤雅家长的负面言论,如“诈捐”、重男轻女等,公众出于对王凤雅的关心和同情,对她的家长进行了各种攻击和批判,甚至通过电话、微信、微博等诅咒她的家人,致使全家都要崩溃。公众在同情心的情感驱使下,失去了对事件的理性观察和思考,加之各种媒体的渲染和传播,舆论一次次被推向顶峰,真相却一直没有浮出水面。“施剑翘案”“王凤雅事件”虽处于不同时代,借助媒介不同,但从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来看,都是公众同情与媒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公众同情的力量加速了舆论的发酵。
四、意见领袖是网络舆论的助力器
从众心理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是个体普遍具有的心理现象。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指出,个体在加入群体后,会产生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与个体心理有着很大差异。他认为,人在孤身一人时,他不会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的诱惑,他也可以抵制诱惑。但成为群体的一员后,他就会意识到人多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烧杀抢掠的念头,并且会屈从于这种诱惑[18]。正如“沉默螺旋理论”所讲,如果一个人的意见属于“少数”,他会因害怕孤立而放弃自己的看法,最后甚至会转变支持方向,与主流观点保持意见一致;当人们认为自己的意见属于“多数”的时候,便倾向于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此反复,便形成主流意见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劣势”意见越来越弱小这样的循环,最后在舆论形成上产生马太效应。网络“极化”现象以及暴力倾向,都与网民的从众心理密不可分。比较典型的就是2011年的抢盐风波。“王凤雅事件”中的网络暴力和网络攻击与网民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有关。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网民存有“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导致独立思考能力缺位,最终盲目从众。
现代个性化的推荐系统所利用的推荐算法主要可以分为4种,在下面,我们将分别来讨论这四种不同的推荐算法的特征。此外,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中,还会涉及到一些非传统的,并不常用的推荐算法,限于篇幅,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暂不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参考文献[1]中的相应章节。
(一)作为网络舆情热点制造者的意见领袖
在舆论的萌芽阶段,意见领袖提供信源功能[22]。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两级传播,其模式如下: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23]。依此来看,意见领袖更接近信息源,可以第一时间接触信息并掌握舆论事件真相,尽管在网络中大家掌握信息的机会是均等的。根据网络舆情事件中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意见领袖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舆情的爆料人,另一种是在其领域内具有专业知识的专业型意见领袖[24]。他们凭借自身知识、威望和影响力,传递的信息往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容易引发公众关注,迅速形成舆论。比如值得我们铭记的“微博打拐”事件就是在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的关注下逐渐露出苗头的;“于欢案”由社会事件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网络舆论热点离不开网易新闻、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等这些意见领袖的推送。“王凤雅事件”能够进入舆论视野也是在大树公益官方微博@小希望之树和微博@作家陈岚发文指责王凤雅家人诈捐后引发的。意见领袖作为最先或者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的人,是舆论热点制造者的一份子。他们利用自己在信息方面的优势或者领域权威来设置议程、引发讨论,进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影响受众讨论的框架和内容,从而控制舆论走向。
(二)作为舆情释疑与扩散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在舆论扩散期,是放大舆论,到了舆论高潮期,则是深化舆论”[25]。在网络舆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意见领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回应公众的疑虑和问题,发挥释疑的作用。在“王凤雅事件”中,当公众对王凤雅的指责和谩骂漫天而来时,“新京报网”、“央视网”等意见领袖集体发声,进行了理性分析,并对事件的不实之处进行了及时梳理,客观呈现了事件原委。另一方面,意见领袖在制造热点和释疑的同时也充当了扩散者的角色。尤其是在2018年5月4日的“北大校长口误事件”中,林建华发表致歉信后,北大未名BBS首先将致歉信进行了传播,之后@北京青年报、@头条新闻、@澎湃新闻等媒体的官方微博也进行了转发,@王思聪、@管鑫Sam、@克里斯托夫-金等知名网络大V也相继针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言论,提出了不同观点,推动了舆论的发展及分化。在舆论扩散过程中,意见领袖或深入挖掘案件细节、或进行评论、或进行转发,展现出舆论扩散的力量。
(三)作为舆情引导或干扰的意见领袖
众所周知,意见领袖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威望,这在放大舆论影响的同时也会影响受众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示范、引导,二是协调或干扰。在“于欢案”中,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虎嗅网、@但斌等意见领袖积极发声,引导公众从对八卦的好奇、警察的批判转向对法制教育、司法判决、民警执法能力的思考。“王凤雅事件”中,“央视网”在《河南“小凤雅”事件真相出来了,谁该反思?反思什么?》一文中极力倡导公众追一追事实,等一等证据,不要“结论先行”;呼吁广大网民在转发和讨伐之前,先让理性“多跑一会儿”,此类报道和文章引导着舆论向理性方向发展。在舆论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给予处于信息传播终端的受众指点和调节,影响这些人说什么、看什么、做什么和想什么,而且还支配他们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做和怎么想。需注意的是,威望程度不同的意见领袖所发挥的引导、支配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总之,意见领袖不仅是舆论的制造者,引导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及其重要性进行判断,还可以利用自身影响力和支配力放大自己的声音,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力量。
综上所述,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基于一定的社会现实,网络舆论也不例外。社情民意是网络舆论热点产成的现实基础,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网络舆论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和物质基础,社会公共心理成为网络舆论发酵、扩散的共识要件,意见领袖的存在成为引爆网络舆论的助力器。
参考文献:
[ 1 ] 人民网-传媒频道.习近平作十九大报告,八次提到互联网[EB/OL].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1018/c120837-29594814.html,2017-10-18.
[ 2 ] 廖永亮.舆论调控学:引导舆论与舆论引导的艺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 3 ] 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与效果评估信息平台建设研究课题组.网络舆论生成与发酵的深层逻辑——网民认知框架对议题结构演变的影响[J].人民论坛,2015(31):62-65.
[ 4 ]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建立完善利益表达机制[N].经济日报,2014-08-05(01).
[ 5 ] 席伟航.网络舆论、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异同[J].新闻与写作,2010:25-26.
[ 6 ] 人民网舆情检测室.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EB/OL].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6/1222/c408999-28969136.html,2016-12-22.
[ 7 ]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7年上半年舆情分析报告[EB/OL].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7/0710/c209043-29395003.html,2017-07-10.
[ 8 ] 新华网.网络舆情参考(周报)[EB/OL].http://www.xinhuanet.com/yuqing/2014/xbyqpx/zhuanti/03.html,2018-09-03.
[ 9 ] 中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7.
[10] 王金情.我国现阶段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06.
[11] 胡夏冰.和谐社会需要多维度利益表达机制[N].检察日报,2006-04-28.
[12] 习近平.“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28536396.html,2015-12-16.
[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7026.htm,2018-01-31.
[14] 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56.
[15] Travers J,Milgram S.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Small World Problem[J].Sociometry,1969(32):425-443.
[16] 李凌凌.网络传播理论与实务[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26.
[17] 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1.272.
[18]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19] 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M]. 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6.
[20] 李文冰.公众同情与“情感”公众:大众传媒时代一种新的社会批判力量——析《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J].中国出版,2014(15):48-50.
[21] Dennis C.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之路[M].郑钢,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781.
[22] 刘元臻.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意见领袖的角色和功能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5,6(2):48-48,87.
[23] Katz, Elihu, Lazarsfeld,Paul F.Personal Influence[M].New York: Free Press,1957.
[24] 佟璐.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的传播与引导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2.
[25] 刘元臻.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意见领袖的角色和功能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 2015,6(2):48-48,87.
AMulti-dimensionalAttributionStudyoftheFormationofInternetPublicOpinionHotspot
ANYanxia1,HeYunfeng2
(1.College of Informatio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0, Shanxi)
Abstract:With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sharp increase of the netizens, the popularity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power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has already chang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public opinion. Through public opinion hotspot event in recent years, it can be seen that social events are the triggers of the Internet public hotspot; civic consciousness is a catalyst for the formation of internet public hotspot; the absence of interest expression mechanism provides space for the proliferation of internet public hotspot.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has created a platform for the crea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he prosperity of the internet provides a fairly large-scale subject for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he spread of online media prompts the case to evolve into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bject.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opinion, social public psychology is the consensus element of the internet public hotspot. The opinion leaders, as a hotspot maker, doubters and proliferators, media guides or disruptors of the internet public hotspot, further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Keywords:internet public opinion; social and public opinion; public psychology; opinion leaders
中图分类号:G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927(2019)01-0006-0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志码(OSID):
DOI号:10.13320/j.cnki.jauhe.2019.0002
收稿日期:2018-09-18
基金项目:2016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面向MPA的《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开放性课程建设研究”(编号:2016JG46);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编号:GH-16015)。
作者简介:安艳霞(1985-),女,山西翼城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
通讯作者:何云峰(1973-)男,山西翼城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编辑:王佳)
标签:舆情论文; 舆论论文; 网络论文; 热点论文; 事件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9年第1期论文; 2016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 面向MPA的《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开放性课程建设研究"; (编号:2016JG46) 山西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 规划2016年度课题:";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 (编号:GH-16015)论文;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论文;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