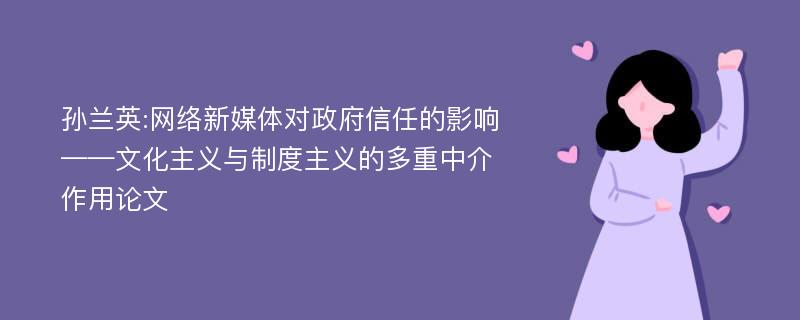
摘 要:新媒体时代的政府信任问题日益引发各界关注。本文基于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研究视角,构建了网络新媒体对政府信任影响的复合多重中介模型,并通过“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众受到网络新媒体的影响程度与其政府信任水平负相关。在两者的负向关系中共存在4条中介路径,即“后物质主义”伦理价值观的特定中介路径、“后物质主义”政治价值观的特定中介路径、政府绩效评价的特定中介路径以及政治价值观与绩效评价相结合的连续多重中介路径。在全部中介路径中,政治价值观的特定中介效应最强,而伦理价值观的特定中介效应最弱。
关键词:政府信任;新媒体;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政府绩效;多重中介
1引言
政府信任指公众对政府或政治系统信赖与支持的态度,它既是政府合法性的逻辑起点,更是政策有效性的心理基础。随着后工业化与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府信任危机:一方面,物质生活满足和文化素养提升,催生了强烈的公民意识觉醒,以监督和质疑政府权威为主要特征的“批判性公民”文化日渐兴起[1];另一方面,更趋“后物质主义”特征的价值取向提升了公众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对政府要求,从而导致人们对政府绩效预期与实际的感知体验之间产生落差[2]。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正处于重要的媒介转型时期: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进一步强化了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网络新媒体颠覆性的信息沟通模式不仅加速了社会价值的转型,更为人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个体与政府关系的机会。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的政治认同与传统时代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而政府信任作为政治认同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与新媒体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机制更应受到足够重视。
鱼排粉总磷含量最小值为3.6%,而部分俄罗斯白鱼粉样本的总磷含量大于3.6%。如果以总磷含量作为小型鱼全鱼鱼粉和鱼排粉的判别依据,则可以发现,俄罗斯白鱼粉中含有部分鱼排粉。进口鱼粉总磷含量与鱼粉总磷含量分布重叠,其总磷含量小于3.0%;国产鱼粉总磷含量也是全部小于3.0%。
近年来有关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热点,其中以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分析视角最为常见[3],但涉及媒介或互联网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聚焦网络新媒体对政府信任影响机制的研究更为罕见。互联网作为崭新的媒介形态,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转变,其对公众政府信任的影响也绝非机械单一的直接作用。首先,就文化主义视角而言,公民价值变迁是政府信任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互联网能够增加受众的民主观念及批评政府的可能性[4],由此我们提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新媒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之一。其次,从制度主义分析视角来看,互联网多中心、多方向的互动传播模式为受众营造了更自由的信息交流渠道,过高的负面政治信息曝光、主题式框架呈现方式以及匿名性带来的虚假信息等因素[5],严重削弱了受众对政府的绩效评价。因而政府绩效评价可能是新媒体对政府信任影响机制之二。最后,在新媒体的催化作用下,公众价值层面的更高要求与现实中政府实际绩效无法满足的矛盾更加激化,所以有必要将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因素相结合,探析新媒体通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及政府绩效评价对政府信任的多重中介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标如下:第一,基于媒介使用行为和认知态度的综合测量方法,探究网络新媒体对政府信任的直接影响。第二,从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视角考察网络新媒体对政府信任影响的多重中介作用机制。第三,通过检验和比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政府绩效评价的特定中介效应以及两者连续的复合多重中介效应的差异,打开网络新媒体与政府信任之间的“黑箱”,深入剖析不同中介路径在整体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聚焦产业政策,当前化工企业环保压力逐步加大,化工行业通道缩紧。随着国家环保力度的加大,政策文件屡次提到“一律不批”、“一律关停”等字样,化工企业搬迁、升级改造、关停已是大势所趋。钾盐企业应当进一步关注产业循环经济、绿色环保政策的跟进,做到未雨绸缪。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网络新媒体影响与政府信任
作为一种社会化信任关系,政府信任的产生、演化和消亡始终伴随着信任主客体之间的信息资源交互: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复杂的政治系统中,公众必须更多地依赖于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和观点,形成并不断修正自身对政府认知、态度和情感;另一方面,出于维护政权与强化治理的需要,政府也将媒介作为思想价值宣传和社会信息反馈的重要平台。有关媒介与政府信任关系的探讨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现代传播媒介侧重于对政府负面信息的报道,易导致公众政府信任水平下滑的“媒介抑郁”理论;二是认为频繁的媒介接触有助于塑造民众对政治系统的积极态度,从而促进政府信任提升的“媒介动员”理论[6]。研究结论的差异源自媒介测量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媒介形态[7]、媒介使用频率[8]以及受众的媒介认知态度[9]等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区域间的政治文化和传媒语境差异也会导致媒介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变化:不同于媒介商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在我国始终肩负着思想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职责,因此使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加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10]。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中药标本在教学中的主要应用方式有,将中药标本引进课堂及定期组织学生到中药标本馆参观学习等[3]。中药标本馆是收集、整理和陈列、展示各类中药标本的场馆,但受到固定场所的制约,学生大多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接触到[4]。中药标本进课堂就是让学生在课堂上观察中药标本,通过看、摸、闻、尝等多种途径学习中药的性状特征[5]。目前,标本进课堂形式更加适合我校教学实际情况。
H5政府绩效评价在网络新媒体影响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H1网络新媒体影响与政府信任水平负相关。
沥青混凝料的最佳碾压遍数确定原则为在满足设计密度和孔隙率等前提下的最小碾压遍数来确定。由表4、表6和图2综合分析,沥青混合料的最佳碾压遍数为10遍。
2.2“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在政策的支持下,进一步深化专兼协同的市场营销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强现有专任师资力量的培训和进修,培养双师双能型师资;另一方面,继续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师资力量和教学效果。
H6b“后物质主义”政治价值观与政府绩效评价在网络新媒体影响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发挥多重连续中介作用。
H2a网络新媒体影响与受众的“后物质主义”伦理价值观正相关。
H2b网络新媒体影响与受众的“后物质主义”政治价值观正相关。
政府信任的文化主义解释路径认为,不同思想价值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有研究发现,崇尚民主主义价值的国家信任水平明显高于权威主义国家[19],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权威主义价值观是人们形成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20]。游宇等[21]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负面效应在民主程度低的国家较明显。在以我国公众为对象的研究中,章秀英和戴春林[5]发现权威主义价值和民主意识在网络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李艳霞[22]发现相较于政治价值观,当代中国公众在伦理层面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府信任的负面效果更为显著。因此,网络新媒体可能通过塑造公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实现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GT=β0+β1Xi+β2IN+β3EV+β4PV+β5PE+μ
H3b“后物质主义”政治价值观在网络新媒体影响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2.3政府绩效评价的中介作用
政府绩效是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或产出,是其在行使公共职能、贯彻公共意志过程中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公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和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所接触媒介信息的影响。传统媒体环境下,单向的信息传播模式更有利于政府通过信息筛选、议程设置等方式引导公众的绩效感知。网络新媒体开辟了“人人麦克风”的大众传媒新时代,继而打破了原有传媒与绩效评价的关系。政府不再是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核心权威[23],使得大量凸显社会矛盾的公共议程通过多元化信息渠道呈现在公众面前,无疑会降低其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低廉的接入成本与不完善的监管机制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了谣言的重灾区,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小道消息和虚假传言往往趁虚而入,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网络新媒体影响与公众的政府绩效评价负相关。
制度主义观点认为,政府信任是人们对于政府行为可信度的一种理性评估。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及满意度是形成政府信任的核心判断依据。国外研究发现公众对于政治丑闻、犯罪率上升等负面政治及社会绩效的关注会降低政府信任[24]。胡荣等[25]在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研究中也发现,受访者对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维护治安、反腐等多方面绩效的评价对政府信任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我们认为网络新媒体同样可以通过影响受众对政府绩效评价而作用于政府信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新媒体特有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等特点使其在公共议程设置,改善公共关系,促进社会参与和政治监督等方面表现出更加突出的作用。尽管在理论层面网络新媒体有利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民主化,进而提升政府公信力[11],但经验研究则大多指向相反的结果:人们利用网络获取政治信息[12],网上参与公共事务[13]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信任水平。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2.4“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政府绩效评价的多重中介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政府绩效评价都在网络新媒体影响与政府信任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期望的实现是信任生成的基础,公众对于政府绩效的评判标准,本质上源自于价值取向赋予其对政治系统的期望。后物质主义时代的社会价值转型已经给大量发达工业国家带来了政治议程的转变[15],而这种趋势正在快速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网络新媒体带来的多元社会价值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和认知。个体价值与社会主流价值的碰撞日趋频繁,甚至激化上升为现实的社会纠纷和官民矛盾,导致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严重受损。由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同政府绩效评价的多重连续中介作用,即网络新媒体加速了受众的价值转型,进而影响到其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并最终作用于政府信任水平。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6a“后物质主义”伦理价值观与政府绩效评价在网络新媒体影响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发挥多重连续中介作用。
实验采用五折交叉验证法,将每个数据集等分五份进行五次实验,每次实验记录查全率和查准率,并计算F-value数据,每个数据集进行五次实验的F-value数据如图2;其均值和标准差如表3所示,算法采用MATLAB编程实现。
图4为MFAC-PID和PID仿真比较结果。从图4可见: 在设定值阶跃响应阶段,PID串级控制算法的调整时间为350 s,其超调量约为50%;MFAC-PID串级控制算法的调整时间为250 s,其超调量为30%。在蒸汽扰动阶段,PID串级控制算法的调整时间大于400 s,其超调量高达170%;MFAC-PID串级控制算法的调整时间约为250 s。在给水扰动阶段,PID串级控制算法的震荡回复时间约为250 s,其超调量约为20%;MFAC-PID算法的调整时间为200 s,其超调量为10%。
锆材中杂质元素的常用检测方法多采用分光光度法[5]、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FAAS)[6]、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7-9]等。分光光度法适合于常量元素的分析;FAAS灵敏度高、检出限低,但测定周期长,操作繁琐,不适合多元素的同时分析;而ICP-AES由于具有灵敏度高、检出限低、精密度高、准确度好、动态线性范围宽、基体效应小、多元素同时测定等诸多优点,广泛应用于微量及痕量元素的测定[10-13]。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了一个5条路径的复合多重中介模型如图1。
图1 研究模型与假设
3研究设计
3.1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数据调查库(CNSDA)中的公开数据“网民社会意识调查”。该项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于2015年组织开展,通过在新浪微博、微信和爱调研网等新媒体平台发布问卷答题连接,以网友自愿回答方式进行非概率抽样,共计3781份。其中新浪微博用户占45.1%,爱调研网用户占31.7%,微信用户占12.7%,其余10.5%为当面调查。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调查采用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如限制网络IP的方法避免重复答题,剔除了答题时间过短的低质样本等。为了确保统计结果的准确性与研究的适用性,对问卷数据进行了二次处理:考虑到模型涉及变量数据的缺失值规模较小,对包含缺失值的样本做删除处理;同时,为确保模型变量描述内容的方向一致性,对部分问题的选项进行顺序转置处理。处理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3390个。
3.2变量测量
第一,因变量为政府信任水平。广义上的政府信任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社会成员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行政主体的信任[1]。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数据中选取了询问受访者对中央政府、法院和警察信任程度的变量。对三者进行因子分析降维后提取到一个公因子,将其命名为“政府信任”(GT),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9.20%(大于60%),特征根为2.376(大于1)。
第二,自变量为新媒体影响力。本研究参考马得勇和王丽娜[26]提出的测量公式,将公众从新媒体获取的政治信息数量(使用频率)与接受质量(信任程度)的交乘项作为新媒体实际影响程度测量变量。具体来说,选取询问受访者对于微博(网络社区)和微信获取政治新闻和事实评论的频率及信任程度,相乘后得到了微博社区与微信的影响力变量。尝试对两者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命名为“新媒体影响力”(IN),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6.56%,特征根为1.331。
第三,中介变量包括政府绩效评价以及“后物质主义”的伦理和政治价值观。研究选择受访者对国家总体发展情况、道德风气和社会治安三个维度的政府绩效评价,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命名为“绩效评价”(PE),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96%,特征根为1.889。选择考察受访者对非主流化伦理观点认可程度的题目(非婚性行为与同性恋),与有关民主权利、信息公开及市场自由化等政治观点的题目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出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政治价值观”(PV)与“伦理价值观”(EV),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3.01%,特征根分别为1.927和1.224。
众所周知,中国人具有善于隐蔽、不溢于言表的性格,认为含蓄是一种美。无论是日常的生活学习、文学话语还是艺术欣赏,都体现出含蓄的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含蓄性意味着人们不太喜欢真实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从而使准确、快速深入地理解明白他人的思想看法变得困难。而隐喻,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能帮助人们更容易理解他人的看法、猜透他人的态度。正如张磊(2010)在认知隐喻的社会功能分析一文指出,“隐喻有着显著的社会意义”,隐喻性表达具有委婉功能,感情功能等社会功能。
除此之外,根据以往的研究选取了包括性别(Sex)、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政治面貌(CCP)以及收入情况(Income)等人口学变量来控制个体差异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3.3统计方法与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所有的统计分析。具体包括:首先使用SPSS 24.0进行相关性分析;然后采用Hayes[27]开发的SPSS/SAS宏插件PROCESS考察伦理与政治两方面“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及绩效评价在新媒体影响力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多重中介效用;最后,使用Amos 24.0构建路径分析模型,检验多重中介模型的整体拟合度。为验证网络新媒体对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和多重中介效应,构建了逐步回归的嵌套模型,如(1)~(5)式。
PE=β0+β1Xi+β2IN+β3EV+β4PV+μ
(1)
EV=β0+β1Xi+β2IN+μ
(2)
PV=β0+β1Xi+β2IN+μ
(3)
GT=β0+β1Xi+β2IN+μ
(4)
H3a“后物质主义”伦理价值观在网络新媒体影响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5)
(1)式为网络新媒体与政府信任关系的直接效应模型,(2)~(5)式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其中GT代表因变量政府信任,IN代表自变量新媒体影响力,EV、PV和PE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伦理层面、政治层面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政府绩效评价,Xi代表各项控制变量,βi(i=1,…,5)为各项回归系数,β0和μ为常数项和误差项。
英格尔哈特(Inglehart)认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下,人们的价值观出现了由注重经济利益和基本生活保障等“物质主义”价值向追求自由、人权、生活质量等“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转型。这种价值倾向不仅在政治上体现为强调个体权利和自我表达以实现一个轻等级、重参与的社会[14],还表现出对“环境、堕胎、种族歧视、妇女问题、同性恋解放”[15]等的现代化伦理问题的包容态度。新媒体作为开放式的信息互动平台,既可以为受众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实现民主价值导向[16],又能够推进公民活动[17]和更为积极的政治表达[18]。人们在互联网多样化思潮的长期熏陶下,则更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非主流化的观点和行为。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4研究结果
4.1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媒体影响力与“后物质主义”倾向的伦理价值观(r=0.09,p<0.001)、政治价值观(r=0.28,p<0.001)显著正相关,与绩效评价(r=-0.23,p<0.001)和政府信任(r=-0.12,p<0.001)显著负相关;政府信任与伦理价值观(r=-0.09,p<0.001)、政治价值观(r=-0.49,p<0.001)显著负相关,与绩效评价(r=0.564,p< 0.001)显著正相关;中介变量中,政府绩效评价与政治价值观显著负相关(r=-0.48,p<0.001),但与伦理价值观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直接和中介效应相关假设,但具体情况仍需逐步回归及Bootstrap分析的进一步验证。
52例研究对象先行CT扫描,行桡骨远端冠状位和矢状位,确保两层间距2mm,特殊患者可以间隔1mm,有些患者要增加水平位片拍摄。再对52例患者行X线检测,于腕关节正侧位拍摄X线片。
4.2假设检验结果
表1汇报了多重中介效应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是新媒体影响力对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的验证。报告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新媒体影响力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63,p<0.001),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通过消费者座谈得到最能代表其面部“水光感”程度的区域为:上界限为下眼睑眼下2 cm处,下界限为鼻唇中间线的延长线,左侧/右侧为鼻翼边缘延伸至颧骨外侧,确定此区域为专家视觉评估区域。
依据模型2和模型3结果显示,新媒体影响力对受访者的“后物质主义”伦理价值观(β=0.112,p<0.001)和政治价值观(β=0.220,p<0.001)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假设H2a和H2b均得到验证。为进一步验证两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媒介影响力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假设,模型5将伦理和政治价值观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后物质主义”伦理价值观(β=-0.095,p<0.001)和政治价值观(β=-0.251,p<0.001)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新媒体影响力为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70,p<0.001)。表2中汇报了Bootstrap分析的中介效应显著性结果,从由5000个重复抽样样本导出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可以发现,伦理价值观的间接效应(Me1)已达到显著性水平(Effect=-0.011,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同时政治价值观在新媒体影响力和政府信任之间所产生的间接效应(Me3)也已达到显著性水平(Effect=-0.055,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假设H3a和H3b均得到了验证。
宫腔镜手术比传统手术的优势要明显一些。子宫内膜息肉在妇科中比较多见,也是引起子宫异常出血的重要原因,联众刮宫手术具有盲目性,传统的刮宫方式会导致10%至20%的疾病被遗留,还有误诊和漏诊,而使用宫腔镜内膜息肉切除手术可以直观的对息肉位置进行确定,从蒂部进行息肉的切除,该种手术的出血量比较少,复发率比较低。在子宫粘膜下肌瘤导致的异常子宫出血和不孕症患者传统是采取切除子宫治疗,而宫腔镜电切术则是对病灶位置进行观察和确定,进行切除病灶,不需要开腹治疗,能够保留患者的生育能力。宫腔粘连使用宫腔镜手术可以直观的进行分离和切除粘连,让患者子宫形态得到恢复。
表1 多重中介效应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模型4模型5政府信任 伦理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 绩效评价 政府信任βSEβSEβSEβSEβSESex-0.425∗∗∗0.033-0.0250.0380.415∗∗∗0.034-0.120∗∗∗0.033-0.217∗∗∗0.030Age-0.435∗∗∗0.025-0.178∗∗∗0.0270.428∗∗∗0.024-0.312∗∗∗0.024-0.164∗∗∗0.022Edu-0.0240.0260.059∗0.029-0.0190.0260.082∗∗0.024-0.057∗0.022CCP0.295∗∗∗0.037-0.0200.040-0.243∗∗∗0.0360.0670.0340.170∗∗∗0.031Income0.0140.0140.0130.018-0.0010.0160.048∗∗0.016-0.0030.014IN-0.063∗∗∗0.0160.112∗∗∗0.0170.220∗∗∗0.015-0.087∗∗∗0.0150.070∗∗∗0.014EV-0.042∗∗0.015-0.095∗∗∗0.013PV-0.369∗∗∗0.016-0.251∗∗∗0.016PE0.390∗∗∗0.016R20.1650.0240.2190.2900.409F值111.581∗∗∗14.147∗∗∗158.538∗∗∗172.945∗∗∗259.491∗∗∗
注:*、**、***分别代表5%、1%和0.1%的显著性水平。
表1模型4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媒体影响力会对受众的政府绩效评价产生消极作用(β=-0.087,p<0.001),故假设H4得到验证。模型5中将新媒体影响力与绩效评价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时,发现绩效评价显著正向影响政府信任(β=0.390,p<0.001)。同时,Bootstrap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绩效评价在新媒体影响力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Me5)已达到显著性水平(Effect=-0.034,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假设H5得到了检验。
假设H6a和H6b分别提出在新媒体影响力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两种多重中介效应假设。表1中模型4结果显示,“后物质主义”伦理价值观对政府绩效评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42,p<0.01),而这种影响在政治价值观上表现更加明显(β=-0.369,p<0.001)。表2的Bootstrap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伦理价值观与绩效评价的多重中介模型(Me2)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水平(95%置信区间不包含0),但间接效应估计值非常小(Effect=-0.002),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故认定假设H6a未得到验证。与之相反,政治价值观与绩效评价的多重中介模型(Me4)则完全满足显著性要求(Effect=-0.031,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而假设H6b得到了检验。
为验证整体中介效应与其内部各条中介路径之间的效应差异,表2还汇报了全部中介模型的整体效应(Total)和基于已验证假设的6个对比中介效应(DM1~DM6)。具体来说,总体中介效应值为-0.134,而置信区间不包含0,具有显著性。就中介效应比较情况来看,Me1与Me3的差异DM1,与Me4的差异DM2以及与Me5的差异DM3均达到显著性水平(95%置信区间不包含0)。综合三者的估计效应发现,整体模型中伦理价值观在新媒体影响力与政府信任间的特定中介效应效果最弱。Me3与Me4的差异DM4以及Me3与Me5的差异DM5同样都满足显著性水平(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对比DM1、DM4和DM5的估计效应发现,整体模型中政治价值观在新媒体影响力与政府信任间的特定中介效应效果最强。Me4与Me5的差异DM6的置信区间包含0,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政治价值观与政府绩效相结合产生的多重中介效应与政府绩效的特定中介效应相当。
表2 Bootstrap分析的中介效应显著性结果
中介模型EffectSE95%置信区间下限上限Total-0.1340.010-0.153-0.114Me1:IN→EV→GT-0.0110.002-0.016-0.007Me2:IN→EV→PE→GT-0.0020.001-0.004-0.001Me3:IN→PV→GT-0.0550.006-0.066-0.044Me4:IN→PV→PE→GT-0.0310.003-0.038-0.026Me5:IN→PE→GT-0.0340.002-0.047-0.022DM1=Me1-Me30.0440.0060.0330.056DM2=Me1-Me40.0210.0040.0140.028DM3=Me1-Me50.0230.0070.0100.037DM4=Me3-Me4-0.0230.005-0.034-0.013DM5=Me3-Me5-0.0210.008-0.037-0.004DM6=Me4-Me50.0030.007-0.0110.016
注:用于估算偏差矫正置信区间的重复抽样样本数(Bootstrap samples)为5000。
依据逐步回归和Bootstrap分析对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我们进一步修正了原理论模型:删除伦理价值观与政府绩效评价的多重连续中介效应。为更直观地阐释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使用Amos软件对修正后的整体模型进行路径分析。所得路径分析模型拥有较为理想的模型配适度:绝对拟合指标χ2/df=1.724小于2.00临界值;RMSEA=0.015小于0.05临界值;GFI与AGFI均大于0.90;相对拟合指标NFI、IFI、CFI均大于0.95,达到可接受水平。最终的中介模型路径估计(含完全标准化参数)如图2所示,新媒体影响力与政府信任之间的4条中介路径估计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且系数方向与Bootstrap分析估计结果一致。因此,上述假设验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图2 新媒体影响力对政府信任的间接影响路径
5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中3390个样本的实证分析,本文探讨了网络新媒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重点对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因素的复合多重中介效应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第一,网络新媒体对受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具有负向影响,接收来自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政治信息并对这类信息信赖程度较高的受众,表现出较低的政府信任水平。然而在控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政府绩效评价等变量后这种负向影响则转化为积极作用,说明新媒体影响力对政府信任的削弱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公众的文化价值和绩效评价实现的。第二,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新媒体影响力对政府信任的负向作用存在4条中介路径,即“后物质主义”伦理价值观的特定中介路径、“后物质主义”政治价值观的特定中介路径、政府绩效评价的特定中介路径、“后物质主义”政治价值观与政府绩效评价的连续多重中介路径。第三,在全部中介路径中,“后物质主义”政治价值观的特定中介效应值显著大于其他3个中介路径,而“后物质主义”伦理价值观的特定中介效应则在全部路径中最弱。由政治价值观和政府绩效评价构成的多重连续中介效应同政府绩效评价的特定中介效应同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者在效应值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5.2研究启示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得到如下研究启示:任何技术手段都具有双重社会效应,决定其方向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认知水平。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然而通过对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文化主义与制度主义因素仍然在构建政府信任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新媒体环境下的公民价值文化变迁与制度绩效评价下降,是当前我国政府信任建设面临的核心问题。
首先,“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特定中介效应表明,由公民价值变迁引发的政府信任流失在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已初现端。互联网加速了公民意识觉醒,公众对个体权利、社会监督和公共参与的价值追求与日俱增。政治价值需求的转变与那些经由互联网无限放大的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引发了政府绩效心理预期与现实感知的巨大落差,严重制约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因此,思想宣传和价值引导应成为我国政府信任塑造工程的重中之重,必须积极融入互联网发展思维,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传播优势有序展开。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网络舆论发展动向,善于从舆情分析中总结社会思想价值发展趋势,提升核心价值引领的时效性;要加快推进媒介融合步伐,以媒介技术融合开辟并扩大核心价值传播的新媒体战场,以媒介内容融合构建全新思想宣传和价值传播的内容载体和话语体系。
其次,政府绩效评价的特定中介效应路径表明,受新媒体传播的政治信息影响较大的受众更易对政府绩效表示不满,从而导致政府信任加速流失。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公共舆论交锋的主战场,社会转型时期衍生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情绪在匿名的网络互动空间集中爆发,稍有治理不慎,便会引发舆情危机甚至波及现实社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所以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不仅决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走向,更关系到网络和现实社会的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网络坏境,要推进网络法制化建设,构建完善的网络治理法律体系,还要建立完善的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和处理机制,提升复杂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更要增强网络空间的公共议题设置能力,掌握网络空间内容传播的主动权。
最后,政治价值观与绩效评价的多重中介效应表明,网络新媒体加速了公众对于政治参与、权力监督等后物质主义价值的需求,从而对政府相关制度绩效提出了更高要求。推进持续有效的政府信任建设,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电子政务新媒体建设。信息公开是公众政府信任态度建立的重要前提,相关政府部门不仅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优势积极打造多元信息发布渠道,更需要加强对网络信息公开渠道的维护和运营管理,提升公共信息获取效率。同时,要大力发展电子化民主,形成完善的公共网络参与机制,实现公众与政府的新媒体互动常态化。
参 考 文 献:
[1] Norris P.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9.
[2] Welzel C, Inglehart R. Liberalism, postmaterialism, and the growth of freedom[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5, 15(1): 81-108.
[3] Mischler W, Rose R.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1, (1): 30-62.
[4] Lei Y W.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politic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netizens[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1, 28(3): 291-322.
[5] 章秀英,戴春林.网络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路径——基于9省18个县(市)的问卷调查[J].浙江社会科学,2014,(12):94-100.
[6] Newton K. Mass media effects: mobilization or media malaise[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29(4): 577-599.
[7] Moy P, Pfau M. With malice toward all? The media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0, 77(4): 933-334.
[8] Song C, Lee J. Citizens’ use of social media in government, perceived transparency, and trust in government[J].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2016, 39(2): 430-453.
[9] Miller J M, Krosnick J A. News media impact on the ingredients of presidential evaluations: politically knowledgeable citizens are guided by a trusted source[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 44(2): 301-315.
[10] 胡荣,庄思薇.媒介使用对中国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J].东南学术,2017,(1):94-111.
[11] 漆国生,王琳.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公信力提升的影响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0,(7):21-23.
[12] Lu J. Acquiring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various media channel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rrelate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3, 22(83): 828-849.
[13] 张明新,刘伟.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4,(7):90-103.
[14]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M].叶娟丽,韩瑞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65.
[15]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74.
[16] Dahlgren P.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05, 22(2): 147-162.
[17] Shirky C.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J]. Foreign Affairs, 2011, 90(1): 28-41.
[18] 陈福平.社交网络:技术vs.社会——社交网络使用的跨国数据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3,(6):72-94.
[19] Rainer H, Siedler T. Does democracy foster trust[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 37(2): 251-269.
[20] 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5):79-86.
[21] 游宇,王正绪,余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机构信任的影响研究:民主政治的环境因素[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1):164-177.
[22] 李艳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以代际差异为视角的比较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7,(3):60-72.
[23] 褚松燕.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公信力建设[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5):32-36.
[24] Chanley V A, Rudolph T J, Rahn W M.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 time series analysi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0, 64(3): 239-256.
[25] 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25(1):96-117.
[26] 马得勇,王丽娜.我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J].社会,2015,35(5):142-167.
[27] Hayes A 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2013, 51(3): 335-337.
TheInfluenceofNewMediaonGovernmentTrust——TheMulti-mediatingRoleofCulturalismandInstitutionalism
SUN Lan-ying, CHEN Jia-nan
(CollegeofManagementandEconomy,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072,China)
Abstract:The issue of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mediating model for the new media effects on government trust, and then does the empirical test by the data of “social awareness survey of Chinese netize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new media negatively impacts on public trust on government; there are four mediating paths between them: the special mediating path of post-materialistic ethical values, the special mediating path of post-materialistic political values, the special mediating path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sequenced multi-mediating path of political value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mong all the mediating paths, the special medi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values is far greater than other three mediating paths, while the special mediating effect of ethical values is the weakest among them.
Keywords:government trust; new media; post-materialistic value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ulti-mediating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9)03-0031-07
doi:10.11847/fj.38.3.31
收稿日期:2018-07-04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7JDSZK039)
标签:政府论文; 中介论文; 价值观论文; 媒体论文; 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政治论文; 社会调查和社会分析论文; 《预测》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7JDSZK039)论文; 天津大学管理经济学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