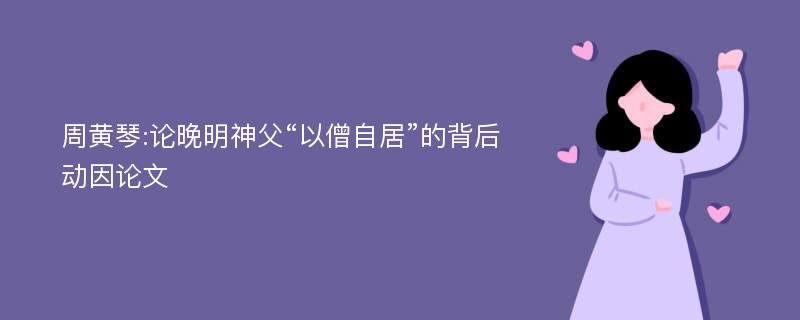
摘 要:晚明时期,作为神父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初期曾“以僧自居”。究其原因,就当时的情境来说,神父们面临着一大棘手的难题,即到中国传教的强烈愿望与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的特令之间构成了巨大冲突。为了解决此矛盾,神父们想通过假借僧人之方式,来破除官方与民众的怀疑,以期达到顺利进入中国之目的。广东官员对此方式予以认可,并积极推动与渲染,在此因缘和合下,“以僧自居”之策略得到了具体实施。
关键词:晚明;神父;以僧自居;动因
翻阅中西文化交流史,令人惊异的是,晚明时期初入中国的神父们曾以僧人自居。其中之缘由到底何在?从现今的研究状况来看,此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故本文试图重新对晚明神父当年“以僧自居”的内在动因做些探究。
一、破除怀疑,以僧入境
从史料记载来看,自沙勿略1551年极度渴望进入中国传教以来,到1582年罗明坚再次从中国大陆失望而归时,期间跨越了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间,神父们虽日思夜想并历尽千辛万苦尝试各种可能性以图进入中国大陆,但最终收获的却是一次次的惨痛失败①据谢和耐《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记载,自沙勿略到罗明坚,其间至少有25名耶稣会士、22名方济各会士、2名奥古斯丁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等50名神父分别想尽办法,力图进入中国,但都以失败告终。(参见谢和耐:《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耿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无疑,期间的苦楚不是一般人可以体味到的,特别是1582年总督通告的打击,彻底把神父推入无边的深渊。正如《中国札记》所载:“鉴于这道命令以及代表们在离开省城后的一个月内所遇到的事情,并考虑到中国人对于洋人的难以置信的嫌恶,神父们好像已失去在中国内地建立居留地的一切希望了”[1]157。
目前,工程上考虑分析成本因素,一般都将风载荷造成的疲劳损伤与波浪造成的疲劳损伤分开计算,根据实际工程经验,这样得到的结果偏于安全。本文重点讨论由波浪载荷对风机基础造成的疲劳损伤。
据资料记载,尽管早期神父一开始只想通过贿赂官员的方式来获得进入中国大陆之机会,但在多次失败后,发现仅靠此方式还是行不通。因为虽然有些官员比较贪婪,但是在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禁令面前,他们还是不敢任意妄为,以怕丢了官位。在困境中,神父发现了一个可假借的、并能减少中国人怀疑与敌视的身份,即僧人。所以,在1583年再次会见广东官员时,当罗明坚把贿赂官员与假借僧人身份之方式兼而用之时,则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即被允许进入广东肇庆居住。
然而,《中国札记》不仅没有论说“以僧入境”之方式,反而包含了大量对僧人与佛教的批判内容。对于此反常之举,只要我们能悉知此书写作的时机与作者心境,即能明了其中所蕴含的意图了。《中国札记》是利玛窦晚年的一个回忆性作品,写作该书时利玛窦与神父们早已抛弃了僧人身份而以儒者自居。而且,从资料的记载上看,对于罗明坚与利玛窦早期“以僧自居”之举,无论在他们生前,还是身后,都曾遭致基督教内部的质疑与批判,或许为了避免或减少遭受此方面的指责,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就尽量避而不谈,抑或是金尼阁对其中涉及到的“以僧自居”的内容作了一些处理。正如裴化行在《利玛窦神父传》中所辩称,“任一行为或外在行动(或称标记)本身并无所谓善恶,除非是外来意志予以定名。况且,并不是异教的一切行动,在未经证明以前,都是罪孽。因此,对异教徒的行动或标志,在弄清楚它们做出或使用的目的之前,不必谴责”[2]82-83。
从神父陈述的内容来看,其极力隐藏的东西主要在于两大方面。
正因如此,基督教的教内书籍不仅很少论及“以僧入境”之方式,而且还把此举之因全然归结为广东官员之强行所为。其实,从众多资料的记载上来看,事实并非全然如此。首先,“以僧传教”之方式并非首创于中国,而是早在日本就已经实施了三四十年;其次,早期神父们的打扮与身份上的有意陈述,就是为了达到让官员们误把他们当作外国僧人从而允许其居住之目的。如据记载,罗明坚见到广东海道则称:“吾等身为僧侣,因仰慕中国良政,离乡浮海来华,希望能下赐寸土,筑室而居以毕天年”[3]68。而且,在面对肇庆知府王泮的问话时,则云:“因仰慕中国良政,由天竺费时三四年到此。为避开澳门商人世俗之喧嚣,望下赐弹丸之地,造一陋室小寺以度余生”[2]72-73。
叶晓晓看着自己的父亲,他暴跳如雷,两手鲜血淋漓的,他不知道,为了买那只剃须刀,叶晓晓舍弃了三条裙子和一件T恤。那一刻,她心里也有些许的恨意升上来,眼泪也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滴到她的膝盖上,滴到抱着膝盖的手指上。
首先,神父们极力撇开与澳门或葡萄牙商人的关系。据记载,鉴于葡萄牙与西班牙人的好战与好利之心,晚明政府与文人对外国人一直抱有敌视与防御心理。因而,尽管神父们在进入中国之前都是以澳门为基地,而且传教的物资亦主要来自于澳门的商人,可是在陈述中,他们却极力撇开与澳门以及澳门商人之关系。即使到了1588年,当神父们被广州的一批耆老们所控告时,神父们还是以来自“天竺国”而非澳门来进行辩诉。
除了以上所想极力隐藏的内容之外,其陈述中还存在着极想凸显的三大内容:其一,盛赞中国的伟大与优秀;其二,凸显他们的僧人身份;其三,强调其与世无争的修行目的。由此可见,为了达到进入中国传教之目的,神父们不仅隐藏了一些真实内容,而且还虚构了一些内容。如他们既不是来自天竺,亦非僧人,而且也不是真的羡慕中国的文明而仅想清净地修行。事实上,他们不仅与澳门的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与中国人极为排斥的葡萄牙商人亦有紧密的关系。更为甚者,他们不是羡慕中国的文明,而是企图用他们的宗教思想来完全替换掉中国已有的传统思想。这些构设的内容显示出神父们不仅窥视到了僧人在中国具有进出之自由,而且还看到了中国人排斥外国人的内在意图。
其次,神父们极力隐藏自己到中国传教的真实目的。《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记载,早期神父“没有在此请愿书上以任何其他方式提及传扬基督教义的事,怕影响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在中国永远居留。中国人是一个傲慢的民族,他们不可能相信有一天会向外国人学习到他们自己书籍里没有记载过的东西。他们最讨厌有人宣传新的宗教,因为他们已经从古代的经验里学到了暴动及骚扰都是以新的宗教为籍口,破坏了国家及人民的安宁”[4]。正是鉴于此种考虑,范礼安要求利玛窦在中国小心谨慎,“缄口不谈耶教”,以至到了南昌,利玛窦仍是绝口不提传教之目的。甚至到了1600年,李贽与利玛窦有过三次会面之后,仍不知利玛窦来自何处,亦不知其来华之真正目的。李贽在致友人的信中云:“承公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万余里矣。……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5]。
而且,从早期神父的中文作品来看,其亦显示出了很强的“以佛传耶”的内在意图。《天主实录》是罗明坚于1584年撰写的第一部中文作品。该书不仅在引文的结尾与正文的开头处分别提到了“天竺国僧书”“天竺国僧辑”等字眼,而且在引文中还多次“以僧自居”,甚至在正文中还有“解释僧道诚心修行升天之正道”的篇章。如引文中云:“僧虽生外国,均人类也,可以不如禽兽而不思所以报本哉?今蒙给地柔远,是即罔极之恩也。然欲报之以金玉、报之以犬马,僧居困乏,而中华亦不少金玉宝马矣。然将何以报之哉?惟以天主行实,原于天竺,流布四方,得以捄拔魂灵升天、免坠地狱。……僧思报答无由,姑述实录而变成唐字,略酬其柔远之恩于万一云尔”[6]。
更为重要的是,沙勿略在耶稣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与影响力,即其为耶稣会教祖罗耀拉最信任与最早的教友之一,因而其对佛教的认知,以及“以佛传耶”的策略都会在耶稣会中产生非常大的反响。甚至从1594年10月12日利玛窦写给高斯塔神父的信中仍可看到沙勿略当时致力到中国传教意图的影子,即力图通过归化中国,从而达到有效教化日本人之目的。所以,在日本学者平川祐弘看来,“沙勿略初到日本时,自称天竺之僧,以贴近日本人的想象。同样来华的神父们也称来自‘天竺’,使用了这个在中国人看来闪烁着西方净土光环的字眼”[3]73。戚印平则指出,被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利玛窦规矩”中,实际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沙勿略方针的深刻烙印”[8]130。由此可见,早期神父在中国“以僧自居”之策略并非首创,而是受到了早期日本传教策略的影响。
因而,对于晚明神父们的“以僧自居”之举,虽然在基督教内部存有不同看法,即理解支持论与批评反对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当时严禁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特令之下,为了能顺利进入中国,除了贿赂官员之方式外,他们唯一可以借鉴的最佳方式就是假借僧人的身份,以获得中国官员与民众的认可。
从图8(a)、图8(b)可以看出,带内误差补偿前,成像场景中强目标距离向旁瓣很高,远端旁瓣数值也较高,会遮盖周围弱目标,成像效果很差。经过带内幅度和相位误差补偿后,旁瓣数值降低十分明显,远端旁瓣对周围目标的影响非常小,成像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综合以上处理结果可知,子带内幅度和相位误差得到了有效的补偿。
二、受日本传教策略的影响
在关于佛教的认知上,葡萄牙人曾犯过把其等同于基督教的错误,即“不是穆斯林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从而不仅把“僧院或神庙”当作“教堂”,而且还相信“在亚洲大陆的腹地存在着前所不知的密密层层的基督信徒”[2]46。随着神父们于16世纪纷纷进驻亚洲各地传教,他们才开始真正接触与认识佛教。令人尴尬的是,尽管同为佛教,但在不同地区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与样貌,这使得神父们难以加以确认。如据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的记载,尽管沙勿略曾在印度呆过,并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当他来到日本后,开始并不知其所遇到的宗教就是佛教,因为它换了形式,“叫做‘天竺’,而且改作唐装了”[2]46。因此,为了传教之需,早期神父们会对亚洲各地的宗教现象进行分析,而且还会对搜集到的各种宗教资料进行分类处理。各地区的神父们还会把各自整理好的宗教资料进行交换,互相交流,以便加深对各地宗教的认识。早期神父在亚洲所积累的宗教知识,特别是关于佛教方面的认知,无疑会对日后神父们在其他地区的传教产生重要影响。
主电路以PS12034功率模块为核心进行电路设计,设计PS12034模块正常工作时所需的外围元件。外围元件结合PS12034内部电路构成变频器整个主电路硬件系统,主电路原理图如图2所示。从PS12034引出SPWMHU、SPWMHV、SPWMHW、SPWMLU、SPWMLV、SPWMLW共6条信号线接收控制电路产生的SPWM信号;C1、C2、C3为自举电容,为逆变桥上桥臂IGBT导通提供电源;C4、C5为整流滤波电容。
据记载,早在1582年,两广总督陈瑞就把神父当僧人看待。如巴范济在1582年12月15日的书信中称:“来人透露可能为神父提供了一处祭祀中国偶像的庙宇作为住处。那样的话,神父就可以久居于此学习汉语了。前些天总督让葡人使节观看了城里的两处寺庙,并说:希望看完后能做出判断,佛寺对罗明坚神父是否有用”[3]60。所以,当罗明坚、巴范济来到肇庆时,就曾被安排在“天宁寺”居住。
首先,从最早到中国传教的先驱者来看,沙勿略在日本传教的过程中萌生了到中国传教的宏愿,在日本期间其曾以僧人身份自居。据记载,尽管随着僧人对基督教教义认识的深入化,佛、耶之间亦曾在日本有过一定的冲突,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沙勿略在日本传教的两年多的时间里(1549—1551),一度曾在日本的菩提、福昌等寺庙传法,而且还与那里的僧人以及福昌寺的住持——忍室和尚,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于其中之因,戚印平在《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中则归结为,“由于缺乏对基督教及其教义的认识,日本僧侣甚至一度将这些来自印度的异国修士视为同道,并对他们表示欢迎”[8]35。但其中令人质疑的是,为何日本僧人会把沙勿略视为同道?其中是否还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即沙勿略为了传教之需而人为地采取了一些迎合佛教之举,从而导致日本的僧人以及民众都把沙勿略误认为僧人呢?
3)冬剪时,主蔓延长蔓剪留0.8~1 m,剪口粗度必须达到0.8 cm以上,延长蔓以下各侧蔓均每隔15~25 cm留1个结果母蔓,剪留2~3个芽,形成龙爪,供下一年结果。
更有意思的是,利玛窦以西克塔斯五世名义致万历帝的书简①该书简发现于20世纪,为利玛窦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协助下所撰。书简撰于1588年,以西克塔斯五世名义致呈万历帝。中亦清晰地显示了其假借僧人身份之事实。如其所载:“吾身居天竺(欧洲),闻之痛心疾首,不念困难重重跋涉之遥出资之巨,派遣博识儒雅之僧侣,遍游世界四方以传授天主之真经。……先年曾有数僧游历贵国,闻其所报,得知贵国统治有方,昌盛繁荣。亦得知贵国人民博学多识。但不幸贵国人民还未曾明晓天主上帝其事。此乃是吾派遣彼德罗、保罗、利诺、马其亚四位僧侣前往贵国的动机。……另有已经滞居大明国的三位僧侣,利玛窦与安东尼将代吾拜见足下,并赠献敝国礼物”[3]158-159。
其次,范礼安神父对“以僧入境”策略不仅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且还督促罗明坚、利玛窦等神父践行下去。尽管在基督教内部,对于早期神父“以佛传耶”之方式与策略存有异议,但在谢和耐看来,“耶稣会士们的修会与嘉布遣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和多明我会相比较的创新之处,便是真正地致力于适应他们打算归化的那些民族的文明,远东耶稣会传教区的伟大组织者范礼安便是这种所谓‘适应’政策的主要缔造人。他于1581至1583年间开始在日本首创这种布道政策,也就是在方济各·沙勿略到达远东的32年之后,并且从一开始就在中国传教区采纳了这种布教政策”[9]。其实,正是基于视察员范礼安的“适应策略”之指示,罗明坚、利玛窦等神父才能够放手在中国采用“以佛传耶”之策略。甚至从《中国札记》的记载上来看,当日后利玛窦在心中出现强烈的以儒者身份替换僧人身份之念时,其并不能马上去实施,而是要等到范礼安从日本返回澳门后,亲自向他提出申请,并经范礼安一年多的思考后才答应实施。
研究理论与框架上,要善于借鉴上位或平行研究领域,如哲学、教育学、数学教育学、数学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来支撑或推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研究.例如哲学中与认识论有关的巴什拉的认识论理论、加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等.每个领域都有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要想让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研究的生命之树保持旺盛持久的生命力,不仅要扎根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一亩三分地,也要扎根其它研究领域,汲取其精髓.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也属于数学教育的子范畴,不能将自己孤立起来,要在保持自己研究领域特色的同时左通右达,才会使HPM的路越走越宽阔.
在《天主实义今注》中,梅谦立还从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与范礼安的《要理本》、罗明坚的《天主实录》之间的承继与演变关系上论证了范礼安、罗明坚等神父的佛教观对利玛窦所产生的深度影响。事实上,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说,在1583年,利玛窦来肇庆时仅是罗明坚的助手而已,故而只能完全遵守罗明坚的“穿和尚的衣服”“剃光头”“不吃肉”等规定。在梅谦立看来,“与在日本一样,耶稣会士在中国对佛教很感兴趣,因为它为表达他们的基督教思想提供了一个土著词汇。与在日本一样,在华的传教士被视为某种佛教僧侣。传教士身上的佛教身份特征,甚至还远超过日本的时候,因为,在广东的十多年里,他们穿着佛教的服饰并剃光头”[7]196。就此段话而言,我们可以读出四大信息:第一,在来华之前以及来华之始,神父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排佛之心,而是相反,对佛教“很感兴趣”;第二,佛教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土著词汇”;第三,神父早在日本就曾“以僧自居”;第四,在形象方面,中国神父只是比日本神父走得更远一些,即不像日本神父仍穿西方的“黑色长袍”,而是穿上了僧人的服饰并剃了光头。
其实,对于晚明神父在中国的“以僧自居”之策略,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中说得更为直白,“第一批入华的耶稣会士们也如同在日本一样,采纳了佛教僧侣们的称号和仪表,希望这样一来能更容易地进入中国并归化中国人”[10]。同时,梅谦立亦指出,“利玛窦关于中国佛教的理解不仅仅在他跟中国僧侣的来往中被塑造起来,并且他也受到了在日本传教的其他耶稣会士的深刻影响”[11]。据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早期神父在觐见中国官员时要极力陈述自己是来自遥远的天竺的僧人。
三、广东官员的推波助澜
不知是误读之因,还是出于贪婪,地方官员们既想能不断地从神父处获得一些物质利益,又可通过神父之僧人形貌来规避一些政治风险,抑或是地方官员想借助于神父之力来缓解或弥补肇庆建崇禧塔所缺少的资金,抑或是以上因素兼而有之,从而导致广东官员不仅把神父当异域僧人来看待,而且在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中国居住的特令下,还允许神父以僧人的身份进入中国并居住。
鉴于在进入中国传教之前,传教士就已经在中国文化圈的日本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传教经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而,当神父们想要进入中国传教时,无论从其传教理念或构想上,还是从传教策略而言,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近邻日本传教过程中所形成的前识观念之影响,甚至在起初阶段,中国的传教方式就是日本传教方式的一种翻版而已。正如梅谦立所言,“在16世纪末,当耶稣会传教士走近中国佛教时,他们已被五十年在日本积累的认识所定格”[7]196。
据《利玛窦神父传》的记载,沙勿略在日本所译教理问答中还存在着运用“佛教用语”之现象。如其曾把基督教的上帝称为“大日”(佛教用语),甚至经过梅奇奥·侬内兹神父的修改,仍发现“危险的词”竟达“五十来个”[2]91。而且,据资料记载,沙勿略起初鄙视与批判日本僧人穿着华美服饰出行,但在自己传教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他很快就依据日本人的习惯做出更换服装之举动。如其云:“这么说是因为日本人对作为他们教师的僧侣极为崇敬,他们只注意装饰在外观上的东西,而且被僧侣们举行的仪式和外观所迷惑。……他们不想与神父交际,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基督教式的谦让和由于爱我主而进行那种有意识的苦行。因为这个原因,神父决定今后与以往不同,穿着更为合适、清洁的服装,为了对我主的爱,在不至于犯罪的限度内尽可能地依从日本人的习惯”[8]161。从这些现象来看,沙勿略在日本传教过程中确曾使用过“以佛传耶”之策略,从而在起初时期能获得日本民众与僧人的认可。正如日本学者平川祐弘所言,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沙勿略就是“来自天竺宣讲佛教新法的和尚”[3]63。
更为甚者,在1583年2月,当罗明坚等神父拜会两广总督、广州都司等地方官员时,不仅被要求日后要穿僧人的衣着,而且还被赐予了僧服。据《利玛窦神父传》所载,“我们谈及服装,他(广州都司)当即自己画了个帽子,说道总督和所有的官员都希望我们穿北京‘神父’的服装……‘这种神父是很受尊重的。’这就是叫我们同化为中国僧侣(或称和尚)”[2]82。对于此事,尽管《中国札记》中并没有记载,但在1583年2月13日利玛窦写给阿桂委瓦的信中有所提及,“尤其神父们声明愿作中国皇帝的顺民时为然,他们应该更换衣服,神父们以为这样很好,于是他(总督)把北京和尚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是他所能恩赐最体面的服饰了”[12]。
实际上,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无论对广东官员还是神父们来说,以僧入住中国乃是两全其美之事。首先,对广东官员来说,此举不仅可以规避政治风险,而且还可从中获利。其次,就神父而言,本来“以僧自居”就是他们力图进入中国传教的一大策略而已,而现中国官员的要求只不过是起了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并没有与其传教策略构成激烈冲突。而且,在他们极度渴望进入中国,但又数次艰辛努力而又失败的情况下,中国官员却能在当时严禁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禁令下,只需他们改变仪表外形,就可获准进入中国并居住,那将是多么荣幸与兴奋之事。所以,在当时,神父们欣然接受,并马上实施,“让人把头和脸都剃得净光,并穿上非常得体的袈裟”[2]82,而且对于这身装束自我感觉亦非常好,甚至认为与天主教神父之装束“相差无几”。
应用SPSS 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分析采用LSD法,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0~40岁成年人至少每5年测量1次血脂(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因而,当1583年9月罗明坚、利玛窦穿着僧服来到肇庆时,肇庆知府王泮完全按照僧人的仪式来接待,并在崇禧塔附近划拨一块地让他们建造住所与寺庙,而当罗明坚提出他们不崇拜偶像,只信天主时,王泮则感到莫名其妙与不可理解。即便如此,当教堂建成后,王泮还是送了“仙花寺”与“西来净土”两块匾额以表祝贺,而这两块匾额却分别被神父悬挂在教堂的正门与中堂上。
而且,即使随着王泮升迁,以及后任知府郑一麟上任,地方官员还是把神父当作僧人看待。如1586年罗明坚曾以僧人的身份被郑一麟邀请到浙江绍兴做佛教法事,期间不仅得到僧人们的热情款待,而且还被安排在寺庙与王泮老家的家庙里居住。裴化行在《利玛窦神父传》中指出,当时神父的“传道活动统统得按照佛教的模式进行,在浙江绍兴就是这样,罗明坚神父在艾美达修士陪同下,在绍兴就住在和尚庙里和和尚中间,在那里布道”[2]120。无疑,浙江之行的经历不仅印证了早期神父“以佛传耶”策略的有效性,而且还强化了此策略的正当性,即“采用僧侣们的生活方式乃是支持中国传教团事业的一种恰当的措施”[1]677-678。实际上,从早期神父进入中国的状态来看,他们“以僧自居”的策略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即不仅获得了进入中国与居住的权利,而且还获得了中国官员与民众的接受与认可。
甚至到了1589年,新任总督刘继文因政治压力而想把神父赶出肇庆时,其考虑到的亦不过两种方案,即遣回澳门或遣送到韶州南华寺,而且总督日后经过韶关时还颇为关心地询问利玛窦为何不愿住在南华寺。即使利玛窦拒绝住在南华寺,但对韶州官员来说,他们眼中的神父仍是僧人。如韶州知县与南雄县丞在拜会利玛窦住处后,分别在救世主画像前捐献了银子作为香炉的“烧香之资”。同时,当利玛窦被英德县令苏大用召去会见其父亲时,仍被安排在佛寺中居住。
在此情形之下,广东民众起初亦无可置疑地把神父当僧人,把教堂当寺庙,把圣母玛利亚当观世音菩萨来看待。在《中国札记》中,利玛窦从护教立场对民众参拜教堂之盛况给予了赞叹,“他们对基督教旨的崇敬,随着对它的钦佩而与日俱增。其中一些人,不经人请求或者告诉,就上香祈福,另一些人给圣灯送油,少数人还自动送东西支援教堂”[1]169。事实上,从老百姓的举动来看,当时老百姓完全是把神父当僧人,把教堂当寺庙来看待。
综上所述,晚明神父“以僧自居”并非出自内心对佛教义理的诚服或认可,亦不是真正在两大宗教之间找到了会话或交流的契合点,而是完全把佛教视为一种策略,以获得当时官员与民众的认可与接受。据此可以理解何以神父们自称“和尚”却又在教理书中大肆批佛。毋庸置疑,“以僧自居”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其真实目的不过是要传播基督教。也正是这种形与神的分离,致使神父们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巨大的风险与危机,最终导致广东民众与秀才们逐步走向激烈的反神父的运动中。
参考文献:
[1]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上册[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 平川祐弘.利玛窦传[M].刘岸伟,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4] 利玛窦.利玛窦全集:第1册[M].刘俊余,译.台北: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124.
[5] 李贽.续焚书: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
[6] 黄兴涛.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4.
[7] 梅谦立.汉语佛学评论:第二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 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 谢和耐.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M].耿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23.
[10]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
[11] 梅谦立.利玛窦佛教观的日本来源及其在中国儒家上的应用[J].孔子研究,2013(1):117.
[12] 利玛窦.利玛窦全集:第3册[M].罗渔,译.台北: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40.
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Priests Who Posed Themselves as Monk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ZHOU Huangqi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 526061,China)
Abstract:In the late Ming Dynasty,the priests posed themselves as monks during their early stage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The reason of this is that the priests,in terms of the situation at that time,faced a thorny problem,which was the great conflict between the priests’strong desire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and the orders strictly forbidding the foreigner entering,relea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the priests tried to make use of the guise of the monk to get rid of the skepticism both in the official and the public,so as to achieve the aim of entering China and residing.But to everyone’s surprise,the official of Guangdong was not only approving this mode,but also actively promoting and rendering this mode,and with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the strategy of posing themselves as monks had been put into effect as well.
Keywords:the late Ming Dynasty;priests;posed themselves as monks;motivation
中图分类号:B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445(2019)01-0012-06
收稿日期:2017-09-15
基金项目:肇庆学院2016年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周黄琴(1973-),女,湖南株洲人,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董 娟)
标签:神父论文; 中国论文; 僧人论文; 佛教论文; 日本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论文; 基督教史论文; 《肇庆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肇庆学院2016年创新团队项目论文;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论文;
